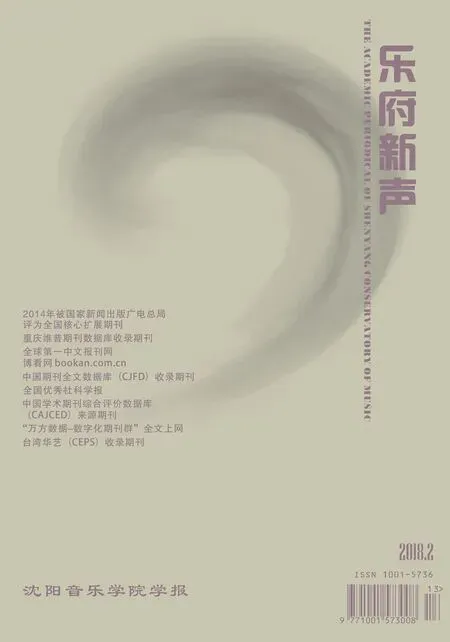在歷史的田野中追蹤歷史
——評陳秉義、楊娜妮的《契丹-遼音樂圖像學考察》
修海林
有位音樂人類學者曾對我說,“歷史是一條干涸的河床”。的確,歷史“原本的生動”是不可能“保鮮”的。其實,凡是在時間中逝去的,哪怕是用現代媒體記錄的已經逝去的歷史,都不可能具有“原本的生動”——尤其對于歷史主體現場參與的歷史活動而言。但是,歷史的記憶乃至遺存則可以是相對“鮮活”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的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隨著歷史主體的退出 ,留下的只是被不斷淡化的、 以各種“歷史遺跡”的形式記錄的歷史。這時,一切對象,都只能成為歷史學的對象。而歷史學,作為“歷時性學科”,正可以運用各種研究方法去有限還原歷史“原本的生動”——無論是在歷時中探求歷史發展的過程與規律,還是在歷時中展開某種文化的共時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人類的記憶,都屬于歷史學意義的記憶;只有歷史學,才是追溯這一人類記憶的學科;也只有歷史學這一門在歷時中追溯歷史的學科,才具有真正的歷時性意義。當“當下”的生動在時間的轉瞬即逝中消失而進入“歷史記憶”范疇時,曾經的“當下”對象,就已經成為歷史學的對象。而這種“轉瞬即逝”的不可逆特性,是支撐不起一門“共時性學科”所必須具備的、能夠確定其“研究對象”的必要條件的。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在歷時中展開某種有限共時性的可能性,而不存在在共時中探求歷時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不僅運動著的空間本身具有時間的意義,并且任何事物的存在與發展,都是在時間的坐標中經歷著興衰起落。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存在失去時間坐標的人文社會科學,而任何一門人文社會科學一旦建立了時間坐標,也就必然進入歷史學范疇。
以上述學術視角看,陳秉義、楊娜妮等撰寫的《契丹一遼音樂圖像學考察》一書,通過對“契丹(Cathay)-遼”音樂文化遺跡的追蹤與考證,為當代中國音樂史研究提供了一部具有“民族-朝代”研究特色、“有限還原歷史‘原本的生動’”的音樂史著述成果。雖然就此成果的呈現形式而言,是一份課題研究報告,除了構成該研究報告主體的3個部分,另外還附有8篇與課題研究相關的論文。但是,就該項成果的性質而言,卻無疑是一份音樂史著述成果,并且是在中國音樂史的通史、斷代史、專題史、區域史研究成果之外,一部獨具特色的“民族-朝代”類音樂史著作。
本文以“民族-朝代”這樣一個特殊的專用概念來說明這樣一本音樂史著述成果撰述內容上的特征,[1]對于本書的研究對象,作者使用的是“契丹(遼)”這樣一個概念。本文采用“契丹-遼”這一語詞,用以體現該書“民族-朝代”的撰寫特點。與元、清時期政權的“大一統”(或曰“多元一體”)政體格局不同,這種表述方式,僅適用于對中國歷史上例如宋、遼、西夏多個政體并存的歷史時期中某個地方民族政體特點的表達。是在對一個對象多側面的認識和把握中,作出的一種表達。就該書的主體內容而言,既非契丹民族音樂史,也非單純的遼代音樂史。事實上,就這項專題研究而言,只要進入該領域,就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若要單純講遼音樂而不講契丹民族的音樂,或只講契丹民族的音樂而不講遼的音樂,不僅做不到,并且難以把握對象的特點。就對象的把握而言,契丹族作為東胡族系,為鮮卑的一支,唐代輾轉臣服于唐朝和突厥之間,至五代、北宋立國;就國號而言,公元916年耶律億稱帝時,國號就叫“契丹”。其后國號在“大遼”、“大契丹”間多次更換。遼于1125年為金所亡;1218年,西遼被蒙古滅,契丹族立國的歷史才告結束。就書中對契丹民族音樂的追溯而言,其中所論,并不僅局限于遼時的契丹音樂,顯而易見的是,如果研究僅限于遼治下209年,對“契丹-遼”音樂的認識,就會有較大的局限。因此,在“契丹-遼”的研究框架中,不僅記述遼,同時還追溯此前的契丹民族音樂,會使我們的認識更為豐富些。因此,該書將“契丹-遼”的音樂文化作為歷史考察對象,有助于加強對這方面歷史知識更全面的了解。該書雖不具有史書的體例,但卻具有史的內容。書中以多項專題研究及其成果集合成書,在相對的意義上,構成一項可謂“在歷時中展開共時”的音樂史綜合研究成果。
該項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說,是“‘文獻分析法’、‘實地考察法’與‘圖像分析法’的交錯運用”,并在“社會-歷史”的多項文化維度中,“從社會變遷、宗教發展以及文化融合等方面,對契丹(遼)的音樂文化進行初步的探討”。在音樂史學領域,對于這樣一個新開拓的研究領域,首先要解決的是史料問題。就這項研究的“不可替代性”和獨特價值而言,若僅僅依據《遼史》、《契丹國志》等文獻史料,寫一本有關遼代音樂的書或一篇論文,也未嘗不可。但是,陳秉義、楊娜妮的這部成果,其中以音樂圖像呈現的音樂實物資料,卻主要來自于他們親歷的、可以稱為“歷史田野”的實地調查。這些資料,堪稱音樂物像史料中的直接證據或經第一手調查而獲得的資料。可以說,正是這項親歷的實地調查,成為啟動和推動這項研究的原動力。
為了撰寫該書,作者一是對分布在遼寧、吉林、內蒙、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尚存的近百座遼塔,逐個進行考察。書中“引言”中有這樣一句數據性的表達:“現存百余座遼塔中,尚有32座存有風采各異的伎樂人,是研究遼代音樂史鮮活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這句表達的背后,付出有多少辛勞,以及駕車在雪路上顛簸滑到溝里……,這些在作者那里,只是一種隨意談笑的話資。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數據,讓人看到作者對學術的執著與鍥而不舍的治學態度。沒有這樣的付出,也就不可能成就這項研究。這些來自實地調查的物像史料,為該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史料在這項研究中的出現、并發揮其獨特而重要的史料價值,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二是通過歷時多年的考察,自駕驅車二萬多公里,對上述省市的十幾座博物館以及文管會收藏的文物以及契丹文化遺址進行了考察,使一些珍貴的音樂文物能夠進入學術視野,為中國音樂物像學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史料。其中有不少文物,甚至從未進入公共學術和專業學術視野,這樣一種發掘性的實物調查,其所獲資料及其獨特價值,也是具“不可替代性”的。
“契丹-遼”音樂在中國古代音樂的歷史發展中,曾打下深刻的文化烙印。從歷史大視野來看,如作者在該書“引言”中表達的,“由于‘契丹曾雄霸東亞二百余年,學術界普遍認為俄語、波斯語、希臘語中的中國均被稱為‘契丹’,當代英語也有用‘Cathay’來表示中國這一名稱,說明了契丹曾在世界、特別是亞洲的影響。”從古代音樂史學科知識拓展的視角來看,該書的研究成果,從許多方面,拓展了認識的空間,提供了不少很有價值的認識。這里僅從下兩個方面對其研究成果作某種述評,以引起同仁后學的關注與重視。
1.作者以新發現的實物圖像為研究的契機,提出歷史上以“海青拿天鵝”為題材內容的琵琶曲,其來源可以上溯至遼代以琵琶等樂器伴奏樂舞的認識。
有關《海青拿天鵝》的最早史料,出自元末詩人楊允孚(其主要活動在元惠宗至正年間,約1354年前后)所作《灤京雜詠》中的“為愛琵琶調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涼州曲,彈出天鵝避海青”一詩。其詩下自注“《海青拿天鵝》,新聲也。”據《四庫全書提要》,楊允孚“順帝時尚食供奉之官,非游士矣。”又說《灤京雜詠》“作于入明之后矣。”并認為“詩中所記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詳。”此曲傳至后世,在音樂史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若想再往前追溯,“海青拿天鵝”作為音樂或樂舞的創作題材得到表現,是否有更早的材料,過去只知道這是草原文化的產物,甚至西亞也有此類風俗。當我在書中看到內蒙扎魯特旗文管會藏遼代小樂舞壁畫的圖像資料(簡稱“扎魯特旗小樂舞壁畫”),并讀了書中多角度展開的有關論述,以及查閱了與此題相關的資料之后,我以為,書中關于內蒙古扎旗文管會收藏的契丹小樂舞中提到的這幅壁畫就是遼代的宮廷樂舞——《海青拿鵝》,舞蹈演員的裝扮是模仿海青的形象這樣一個判斷是可以認同的。
這方面,可以關注到的是,元時灤京為元上都別稱,是一座草原都城。元大都與上都同處于同一軸線,成為元代兩都巡幸政治制度的體現。琵琶曲《海青拿天鵝》,應是作為草原文化的產物,經由兩都巡幸的南北通道傳入北京的。而以海青拿鵝的習俗,并非始于元代,而是曾于遼代風行一時,是遼“四時捺缽”的重要內容。遼帝有四時巡幸的制度,稱“四時捺缽”。據《遼史·營衛志序》記,“出有行營,謂之捺缽。”所謂“捺缽”,即契丹語“行營”、“行帳”一類概念的音譯。其中春季的“捺缽”,就設在便于放鷹捕殺天鵝、野鴨、大雁和鑿冰鉤魚的場所。春季“捺缽”所涉地域范圍很廣。[1]今人對《遼史·營衛志》所記春季“捺缽”之地的考證,有多種說法,在此不作展開。這與契丹人隨水草、逐寒暑,往來游牧漁獵的傳統生活方式有關。扎魯特旗小樂舞壁畫所在地,距遼上京東北方向約兩百公里,是在春季“捺缽”巡幸范圍之內。遼帝春季“捺缽”時,不僅商議國事、處理政事,并且還要大宴群臣、使節,約見各部族首領,接納貢品。春季“捺缽”巡幸中有宮廷伶人表演音樂歌舞活動,也是自然的。
以海青捕鵝,是契丹風俗,更是春季“捺缽”中頗受遼帝、大臣重視的重要活動。該書中提供有內蒙敖漢克力代鄉喇嘛溝遼墓壁畫《備獵圖》,其中有數位髡發的契丹人攜海青、持锨琴以及弓、箭站立待命,他們的身份應是隨行待從及樂人。這幅壁畫的內容,反映的應是“捺缽”巡幸中放鷹捕殺天鵝的現場活動。而在扎魯特旗小樂舞壁畫中,從奏樂(演奏細腰鼓、琵琶、篳篥、橫笛)和行舞者的服飾看,不是契丹族傳統服飾,而是漢人服飾。據《遼史·樂志》中“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遼有散樂蓋由此矣”;“今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漢樂府之遺聲也”的記載,這些著漢服的伶人,其身份就是為遼帝及大臣奏樂的宮廷樂人。這樣的事件,作為墓室壁畫的內容,本身是具有某種權勢、地位的象征意義的。因此,在契丹人的傳統習俗和遼帝春季“捺缽”行為的文化背景下,通過對壁畫中遼宮廷樂人身份以及舞者姿態的認定,判斷扎魯特旗小樂舞壁畫中舞者表演的內容與海青拿天鵝有關,是可以認同的一種學術觀點。至于作為器樂曲的琵琶獨奏曲《海青拿天鵝》又是如何產生的,認識上可以提供的一個參照是,歷史上從歌舞大曲的伴奏音樂轉變為器樂獨奏曲的事例是有的,如著名的琴曲《廣陵散》,就是從同名的漢魏相和大曲演化而來(琴是相和大曲伴奏樂器之一),該曲后獨立成“但曲”,并演化為琴曲《廣陵散》。因此,扎魯特旗小樂舞壁畫中與“海青拿天鵝”樂舞表演直接相關的琵琶伴奏,可以視為后世琵琶曲《海青拿天鵝》的先源之一。
2.作者通過對遼塔的實地調查而獲得的新的實物圖像,對研究三弦類樂器的形成、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并在認識上有所深化。
以此前的古代音樂史研究中,有關三弦的存在,通過南宋、金至元代的文物、文獻史料給予證實,一般沒有疑問。而對于北宋、遼乃至唐、五代時期三弦的認識,由于文獻記載和文物史料的考校、認定本身尚有疑問,故難以判斷。這些問題,在書中皆有論述。作者的表達可以說是謹慎而有余地,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又努力拓展并從新的角度提出問題,以促進認識的深化。古代音樂史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問題意識,才能不斷促進學科的發展。這也是新一代學子需要有所加強的方面。
作者根據所掌握的有關三弦(锨琴、渤海琴)的實物圖像資料,在書中提出,“三弦很可能是一件出現在遼、宋時期中國北方的彈弦樂器”,并通過這方面的實證材料,強化了三弦(锨琴、渤海琴)曾在契丹民族的音樂活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認識。這實際上是告訴我們,若要研究三弦(锨琴、渤海琴)的歷史,是不能離開對歷史上“契丹-遼”音樂研究的。在這個專題研究領域,作者為我們提供的新的實物圖像資料有:北京云接寺遼塔2幅彈三弦伎樂人磚雕、北京云居寺遼塔肩扛(反彈)三弦伎樂飛天磚雕、遼寧朝陽八棱觀遼塔類似三弦伎樂飛天磚雕。其中北京云接寺的三弦伎樂人磚雕所刻三弦,琴箱均呈正方形,與朝陽博物館藏朝陽姑營子耿崇美墓出土的石板彩繪伎樂人、內蒙熬漢克力代鄉喇嘛溝遼墓《備獵圖》伎樂人所彈三弦(锨琴)形狀幾乎一樣。而在姑營子耿崇美墓石板彩繪伎樂人圖像和喇嘛溝遼墓《備獵圖》伎樂人圖像中,彈奏三弦(锨琴)者,都是髡發的契丹人。以此類文物與蔣克謙《琴書大全》中“有锨琴者,狀如锨蒲,正方,鐵為腔,兩面用皮,三弦。十妓抱琴如抱阮,列坐毯上,善渤海之樂云”的記載相映證,可知此樂器在傳播中的名實關系,以及該樂器所奏之樂的地域文化特點。亦如該書作者在相關討論中提到的,“民族遷徒和移民也對音樂文化的傳播起到很大作用”,對三弦(锨琴)的傳播及稱謂上的名實問題,以及在中國北方少數民族中的廣泛流傳乃至通過渤海樂傳至日本等,在較寬的視野中,既作了有依據的推測,也提出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另外,作者對唐崔令欽《教坊記》、段成式《酉陽雜俎》、《舊五代史·晉書八·少帝紀二》中有關三弦類樂器的文字記載,有不同的對待,其表達是謹慎而客觀的。總之,該書的研究,無疑豐富并加深了我們對三弦樂器歷史發展的認識,同時又給我們打開了更大的思考空間。
在該書的研究中,“契丹-遼”的樂舞、樂器以及契丹以及北方各民族和中原音樂的交流,受到較為集中的關注。例如北宋、遼之間在“四部樂”上體現的、各具特色的文化雙向交流與文化認同,特別是遼對漢文化較高的認同度等,是值得探究的課題。這方面的一些音樂傳播、交流的典型事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華夷一體”歷史動蕩中具某種象征意義的音樂文化符號。在民族樂器史研究中,該書提供的一些新見樂器資料,已經成為對以往不少專題研究資料的重要補充。該書為我們提供的不少在遼塔磚雕和遼代銅鏡上看到的音樂物像,是特定歷史時期音樂活動的實證材料。佛塔、銅鏡,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契丹族遺存至今的兩大文化符號。其中與音樂有關的物像,都是對當時音樂文化的折射和反映,值得重視。這類文化符號的原本意義,今天可能已經淡化甚至消失,但在歷史上,卻曾經被視為有意義的文化符號去“聆聽”和理解。
在音樂史研究領域,凌瑞蘭先生的《東北音樂史》研究和陳秉義、楊娜妮的《契丹-遼音樂圖像學考察》這兩項成果,成為沈陽音樂學院音樂學-音樂歷史學科建設中具有鮮明區域音樂史、“民族-朝代”音樂史研究特色的重要成果。這兩項專題研究成果,也是對中國音樂史學科建設不可替代而富有成效的貢獻,他們在這個領域的奉獻精神和學術執著態度,令我們肅然起敬。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