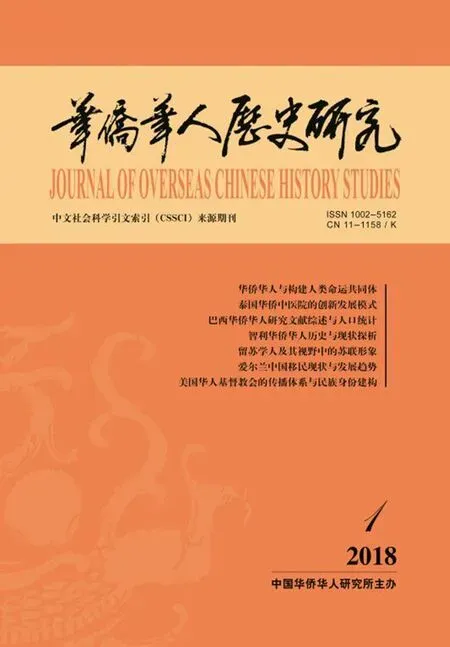延安時期留日歸國群體的歷史作用研究*
趙新利
(中國傳媒大學 廣告學院,北京 100024)
盧溝橋事變之后,留日學生群體中興起了“歸國運動”。從1937年7月7日起,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回國人數便接近4000人。回國之后,他們有的加入國民政府軍隊,也有的加入八路軍、新四軍隊伍。[1]當前,對留學生與抗戰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如下三類。
一是全面抗戰爆發后留日學生回國的相關研究。不少研究關注了全面抗戰爆發后在日本、歐美的中國留學生回國的情況。孔繁嶺的研究指出,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留學海外的學子紛紛選擇回國投身抗戰。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有近4000人回國,到10月下旬,這一數字超過6000人,留日學生幾乎全部回國。[2]徐志民的研究發現,全面抗戰爆發后,在日中國留學生人心惶惶,無心向學,紛紛選擇回國。到1937年11月1日,中華民國在日留學生由“七七事變”前的3995人,降至403人,僅為原有人數的10%。[3]關于全面抗戰爆發后留日學生回國人數,不同研究略有出入。但從中可以看到,全面抗戰爆發導致絕大部分在日中國留學生選擇回國。二是留學生在抗戰中所發揮作用的相關研究。這類研究涵蓋留日學生、留歐學生、留美學生等,且不局限于中國共產黨和延安。《留學生在抗戰中的作用》一文對此有較為全面的梳理,該文統計了1937年回國留學生的年齡、文化程度、專業、職業情況,考察了他們在國際宣傳、軍事斗爭、教育科技等領域所做出的貢獻。[4]三是留日學生奔赴延安的相關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很少,僅有少數回顧性的非學術型文章略有涉及。如,李華雨在《輸入延安的“新鮮血液”》一文中梳理了全面抗戰爆發后,海外中國留學生回國并奔赴抗日根據地的情況。這些留學生群體的具體人數已不可知,粗算大約在200人以上,既有留日回國人士,也有從歐美回國的留學生。[5]
整體上看,現有相關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只關注留學生在抗戰中的作用,對留日歸國群體所發揮作用的研究很少;二是留日回國群體的個案研究多,群體研究少;三是留日歸國群體服務全國抗戰的相關研究多,服務延安等解放區的相關研究少。在此背景下,本文著眼于延安的留日歸國群體,分析他們在中國共產黨對日“二分法”政策的推行、日本俘虜教育、敵情研究等工作中發揮的歷史作用。本文對留日回國群體與對日“二分法”的研究,對理解中國對日政策的源頭具有參考意義,對當前的對日政策和對日工作依然有參考價值;同時,留日回國群體推動的敵情研究,對當前我國的日本問題研究也有一定參考價值。
一、代表人物的回國與入黨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積極吸納留日歸國群體。1937年10月6日發布的《八路軍政治部關于開展日軍政治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充實敵軍工作干部和充分利留日歸國群體。其中規定:“各師團敵軍工作部組織應是得力干部主持工作,并配備適當工作人員,各部分配各部,懂日文的干部、戰士做到每團配備二人(以便營獨立行動時能配一人),旅一人,師二至三人。這些人員多系留日歸國熱忱愛國的青年,應注意從政治上和工作能力上培養他們,(使之)成為敵軍工作之優良干部,在工作中使其發揮創造和自動工作性能,不應以技術人員看待之。”[6]從中可見中國共產黨對“留日歸國熱忱愛國的青年”的重視。這里梳理留日歸國群體的若干代表人物。
(一)王學文
王學文(1895—1985)曾長期擔任敵軍工作部長,是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對日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王學文原名為王守椿,出生于江蘇省徐州,[7]于1910年至1927年間,前后在東京同文書院、第一高等學校預科、金澤第四高等學校、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專業及其研究生院學習。根據他的回憶,1911年“在同文書院學習了兩年之后,正值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打倒了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政府。我立即回國,待了一年之后又回到了東京。”1925年在京都大學留學期間,他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會。當時,社會科學研究會屬于半非法組織,一部分活動是秘密進行的。該研究會得到了京都大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的支持。社會科學研究會中的日本成員,后來大都加入了日本共產黨。[8]到1927年,“從國內傳來周恩來、朱德、賀龍等同志等在江西南昌發動武裝起義,并南下占領汕頭的消息。因此我再次回國。”[9]在日本生活了共計約16年之后,王學文于1937年開始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黨校執教。1940年出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從事對敵軍宣傳及對日本戰俘的教育工作。[10]
(二)張香山
張香山(1914—2009)出生于浙江省,1933年10月至1937年4月曾留學日本。張香山在去日本之前,就于1932年在天津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連盟,并擔任書記。[11]赴日后,他不僅繼續開展左翼文學活動,還積極參加郭沫若等“中國左翼作家”的集會。他在回憶錄里介紹:“1934年冬到1937年春,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峻,救國運動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我索性在東京開展了中國左翼文學活動。”[12]“在東京的時候,我認識了郭沫若,他教會了我很多東西。”[13]張香山最終因參與政治活動于1937年被強制遣返回中國。
回國后,他于1937年加入八路軍,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期間,張香山歷任八路軍129師敵軍工作部副部長、太行軍區敵軍工作部部長、晉冀魯豫軍區敵軍工作部部長等,[14]長期擔任敵軍工作的相關職務,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日本俘虜香川孝志回憶,他剛成為俘虜時,張香山用日語對他說:“請放心,我們八路軍不殺俘虜。”聽到這些話,他才放下心來。[15]據另一位日本俘虜前田光繁的回憶,成為俘虜之后,他同張香山一起生活了10天。期間,張香山盡可能避免正面意見沖突,而是談一些1933年到1937年他在日本留學的事,以及在日本參加的政治活動以及被強行遣返回中國等往事。[16]對于張香山來說,日本的留學經歷為他提供了能與日本俘虜交流的共同話題,他善于借助在日本留學期間經歷的往事,來消除日本俘虜的敵對與不安情緒。
(三)趙安博
趙安博(1915—1999)出生于浙江,于1934年留學日本,1935年至1937年7月在第一高等學校學習,1937年回國并加入八路軍。[17]在其1982年出版的回憶錄里,趙安博表達了對在日留學時期恩師的敬佩之意。回想起當時教授德語的片山敏彥先生時,他寫道,“當時中日關系持續惡化,但片山老師對中國學生仍然非常友好,沒有一點民族歧視,講課的態度也十分認真。”“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越來越猖狂,先生對此非常反感。之后,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先生毅然辭掉了教授一職,轉移到藝術領域來表達自己的反對與不滿。先生的高尚品格,即使現在想起仍然讓我感到敬佩不已。”[18]
在第一高等學校留學時,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趙安博切身感受到中日兩國關系的日益惡化,中國留學生們在日本的學業開始難以繼續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已經考上大學,也不知能不能堅持到畢業。而且,也不知道學費和住宿費今后能否順利從家里寄到日本。于是,他中止了在日本進一步深造的計劃,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不久回到了祖國。[19]
在延安,趙安博長期在敵軍工作部工作,還曾擔任日本共產黨重要領導人野坂參三①野坂參三(1892—1993)是日本共產黨領導人,1940年至1945年在延安協助中國共產黨開展日本問題研究、日本俘虜教育、對日宣傳等工作。在延安期間曾使用“岡野進”“林哲”等名。的秘書,在日本俘虜教育、對日宣傳等領域開展了大量工作。
(四)林植夫
林植夫(1891—1965)出生于福建省,1906年留學日本,并加入了孫文創立的“同盟會”。1920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農林專業。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翻譯的河上肇的著作《資本主義經濟學之歷史的發展》。[20]1938年,他加入新四軍,擔任新四軍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長,主要負責日本俘虜教育和針對日軍的政治宣傳。[21]曾在日本留學的泰國華僑陳子谷也在新四軍的敵軍工作部門工作,在新四軍2支隊向士兵們教授日語口號。他于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新四軍新6團政治處敵軍工作股股長。[22]據陳子谷回憶,當時如果不是共產黨員的話,很難成為軍隊的正式干部。林植夫曾是同盟會會員,也曾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需要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批準。1939年之前,新四軍還沒有日本俘虜,新四軍敵軍工作的日語口號就是林植夫制作的。[23]1941年皖南事變之后,林植夫曾被國民黨俘獲,但由于在日本留學時他與蔣介石、宋美齡相識,且尚未加入共產黨,因此得以免除處罰。[24]
(五)李初梨、李亞農兄弟
李初梨(1900—1994)和李亞農(1906—1962)兄弟是四川江津人,兩人都曾留學日本,而且回國后都從事中國共產黨的敵軍工作。李初梨(排行老三)于1915年赴日本留學,并在1916年帶上了年僅10歲的弟弟李亞農(排行老四)一起在日本學習。全面抗戰期間,李初梨曾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副部長、部長,李亞農曾擔任新四軍敵軍工作部副部長,兩人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初梨1915年開始在日本留學,先后在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京都帝國大學學習。他和在日本的中國左翼作家成仿吾、田漢等接觸頻繁,并開始了解馬克思主義。1927年,李初梨回國后,參加了左翼文學組織“創造社”,1928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后在延安先后擔任新華社負責人、《新中國報》主編。[25]1940年之后,李初梨歷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秘書、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副部長、部長。[26]他作為敵軍工作部副部長,積極參與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日本俘虜教育工作。[27]
李亞農于1916年便開始了日本留學生活,在完成小學課程之后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之后又在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學習。他1927年考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系,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共產黨,通過“留日反帝同盟”等組織參與反日運動。1929年,他被日本警察逮捕,直到1932年才得以回國。
李亞農在抗戰期間擔任新四軍敵軍工作部副部長,負責對日本俘虜的教育工作,1941年進入蘇北抗日根據地,相繼擔任新四軍敵軍工作部副部長等職務。1941年冬,李亞農加入新四軍,被新四軍軍長陳毅任命為敵軍工作部副部長。[28]根據1942年擔任新四軍敵軍工作部部長的劉貫一回憶,李亞農副部長有日本留學經歷,擅長日語,主要負責日本人反戰同盟和朝鮮解放同盟支部的工作。新四軍里有很多日本俘虜,李亞農和他們成為朋友,一起學習日文書及馬克思著作。[29]據1942年擔任華中局《新華報》主編的陳修良回憶:當時,李亞農經常來編輯部,用流利的日語來教育日本俘虜。[30]
二、留日歸國群體與對日“二分法”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一直對日本采取“二分法”,認為侵華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廣大日本人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其實,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已經開始對日本采取“二分法”策略,將發動戰爭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與普通士兵和日本人民相區分,認為日本民眾和普通士兵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但“二分法”的推行曾一度受阻:不少士兵是為了“報仇雪恨”才加入八路軍的,一般民眾也了解日軍暴行,面對被俘虜的普通日兵,告訴他們“這是我們的朋友”,他們其實很難接受。而留日歸國群體對日本有較為全面、客觀的認識,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普通民眾之間的不同有切身的感受,因而對“二分法”有較強的理解與認同,而這正是日后進行日本俘虜教育、敵情研究和瓦解日軍的基礎。
首先,留日歸國群體對日本軍國主義有清醒的認識。延安時期活躍的留日歸國群體有的在去日本留學之前,就在左翼社團活動,有的在日本接觸馬克思主義并積極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活動。例如,張香山在日本留學時曾因參與政治活動而被捕,李亞農在留日期間也曾因組織“留日反帝同盟”而被日本警方逮捕。根據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外事系的極密資料,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共產黨員李亞農的活動被日本內務省警保當局所掌握:“日本反帝同盟組織與中國留日反帝同盟相互合作,以同盟會黨員李亞農為聯絡員,建立起共同戰線。”[31]“中國共產黨員李亞農與日本反帝同盟經過多次協商,最后根據日方提案,將9月1日定為國際無產青年日。”[32]1927年7月27日,在東京都杉并區14號召開了“留日反日同盟”代表大會,李亞農當選為代表會議主席,并被任命為宣傳部委員。[33]李亞農被日本警方逮捕后被處以三年監禁。
其次,留日歸國群體大都感念日本老師的恩情。在日本的留學經歷中,對一般的日本人的印象,如同學、老師、店鋪老板、在公園里玩耍的孩童等,這也影響到留日歸國群體的敵軍工作。王學文在1982年出版的回憶錄《師從于河上肇先生》中,記載了很多留學時代的回憶。除了對日本朋友的回憶,還有對河上肇先生的描述,如“待人親切”“謙虛”等,表達了自己對河上肇先生的尊敬之情。他還回憶道,連回國的旅費都是河上先生給的:“我來到老師的家中見到了師母。日本人非常注重禮節,并不是直接把錢拿出來交給別人。師母將錢放在信封里給了我,我打開一看有20日元。就這樣,我在河上先生和中國朋友的幫助下離開了日本。”[34]從中可以看出,王學文對在日本生活的16年的懷念,以及對日本朋友和老師的情義。
第三,留日歸國群體對日本普通民眾懷有善意。張香山在回憶錄中強調了與日本同學之間的純潔友誼:“那時正處于抗日戰爭前夜,軍部動員了所有輿論來煽動軍國主義。我和日本同學一直都是青年之間純潔的友誼,他們也沒有因為我是中國人而敵視或輕視(我),我們依然是親密的同伴。……我們相互之間沒有芥蒂,只有青年人的熱情與奔放。”[35]這說明,他通過在日本留學,親身感受到了日本民眾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不同。這種對日本民眾的善意,也反映到留日歸國群體對日本俘虜的態度上。抗戰時期,日本俘虜香河正男在新四軍中接受過林植夫的教育,他回憶道:“林部長50歲左右,日語非常精通。政治部把租來的民房當作宿舍,因為林部長就住在我隔壁,所以每天都能看到他。他為人穩重溫厚,非常有人情味,說話也很誠懇。他戴著一副眼鏡,很像日本人。”林植夫曾說過:“這場戰爭必然是日敗我勝。這樣的話,就可以平安返回日本。為了那個時刻的到來,你們要慢慢等,不用勞動,只要認真學習。”[36]林植夫的日本留學經歷和對日本的理解,給日本俘虜帶來了一定的親切感。
最后,留日歸國群體能夠用“二分法”有區別地看待日本。張香山用“二分法”來概括當時的局勢:“從當時的局勢來看,很明顯,日本要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這場戰爭對中日兩國人民都是一場嚴重的災難。同時,這場戰爭為改造中日兩國以及改善兩國關系開辟了道路。”[37]蕭向前曾于1938年到1942年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和東京文理科大學留學,他曾詳細介紹留學生活讓他對日本產生的認識。“在日本,對有些人來說,仍然有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過去,軍國主義者為了培養更多的親日派,耗費了極大精力。他們吸收了很多的留學生,卻得到了相反的結果,產生了更多的抗日派。根據我自己的體驗,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占極少數,絕大多數善良的日本國民都期望日本與中國的友好。他們都期盼改變軍國主義政策獲得民主解放。歷史的結論是,軍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是自掘墳墓,人民才是最終的勝利者。軍國主義者的失敗投降,將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從他們的魔爪下解放出來。從歷史的高度客觀來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抗日派,正是對日本人民的親日派。換句話說,在那種情形之下,親日派不得不變成了抗日派。這就是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結交了很多日本朋友的郭沫若同志,在七七事變之時,如此堅決地回國參加全面抗戰的原因。這也是大多數留學生成為抗日派的根本原因。中日兩國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心情是相同的,最終雙方關系會變好,這是事實。”[38]“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抗日派,正是對日本人民的親日派”,這個觀點顯示了他將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區別對待的態度。
三、留日歸國群體與日本俘虜教育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留日歸國群體發揮其特長,在敵軍工作部等部門從事日本俘虜教育和轉化等敵軍工作。前文提到的王學文、趙安博等代表人物,有的在延安的敵軍工作部工作,也有一些人奔赴前線部隊開展工作。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內部活躍著不少留日歸國人士。除上文所列舉的代表人物外,中國共產黨在各地的部隊都有留日歸國群體的身影。根據覺醒連盟①“覺醒聯盟”是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成立的反戰組織,與中國共產黨攜手開展對日本軍隊的宣傳與瓦解工作。冀魯豫支部的水野靖夫回憶,當時,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的不到30歲的年輕人李仁,擔任八路軍115師343旅政治部的敵軍工作部部長。[39]此外,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把盛華、符然、李特、黃波、王天祥、陳子谷等有日本留學經歷的人才派到前線部隊,讓他們負責敵軍工作。其中,在日本學習舞蹈的吳曉邦也開始在敵軍工作部工作。[40]根據曾留學早稻田大學的王星回憶,在八路軍中,團以下設敵軍工作科,旅以上的部隊設敵軍工作部。他加入八路軍之后,就發揮日語特長,開始負責敵軍工作。[41]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漆克昌以及敵軍工作部的工作人員陳斐琴、唐平鑄、陳重、王星等都曾有過日本留學經歷。[42]漆克昌與張香山、陳斐琴、江右書等精通日語的工作人員,負責對早期俘虜的教育。[43]漆克昌(1910—1988)出生于四川省,1922年赴日本留學,曾在東北帝國大學經濟系學習,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日本被逮捕,1930年回國。同年在上海被捕,1935年加入山西的八路軍隊伍。相繼擔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軍工作部科長、副部長以及部長。[44]根據被新四軍俘虜的香河正男回憶:“敵工部除此之外還有幾名干部,包括曾在日本留學的陳辛人和鮑汗青,留學于明治大學之后擔任第三任駐日大使的宋之光,同樣留學于明治大學之后擔任新四軍第一師敵工部部長的陳超寰,另外還有曾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就讀的謝鎮軍。敵工部有很多這些留學生們從日本帶過來的日語書,我非常吃驚。”[45]
其次,留日歸國群體給日本俘虜帶來巨大心理沖擊。在日本侵華軍隊的扭曲宣傳中,中國共產黨軍隊常常被描繪為“土匪”“山賊”的形象。而在共產黨軍隊中活躍的留日歸國群體大多是曾在日本著名大學留學的精英,日語流利。“土匪”和“精英”之間的巨大反差給日本俘虜帶來巨大的心理沖擊。據1941年被八路軍捕獲的和田真一回憶:“在一群穿粗布軍服人中竟然有從日本大學畢業的人,甚至還有人曾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副官部留學過,這讓我非常吃驚。在敵軍工作部工作的甄科長曾就讀于早稻田大學。”[46]1939年8月,在山東省堂邑縣大李莊戰役中,八路軍129師逮捕了日本士兵秋山良照,他回憶道:“當時為我翻譯以及教我漢語的是譚林夫,他畢業于九州帝國大學,是一位日語十分優秀的年輕人。”譚林夫曾對他說過:“我們做朋友吧,真正的敵人是發動這場不幸戰爭的日本軍閥們。”[47]
第三,留日歸國群體讓日本俘虜的思想教育工作更為有效。據日本俘虜前田光繁回憶:“我們平時接觸的八路軍干部都是會講日語的精英,都非常友好。敵軍工作部的蔡前部長是臺灣人,漆克昌科長有日本留學的經歷,江右書干事和陳干事都曾是留日學生。其中江右書之后在延安擔任敵軍工作干部訓練學校的教員。”[48]據日本俘虜古賀初美回憶,在1941年成為俘虜后,他便跟隨新四軍蘇南第六縱隊來到延安。曾經留學于明治大學的謝敏作為敵軍工作員負責古賀的工作,十分擅長日語,會讓他看小林多喜二的日語小說等。1941年5月末至6月,古賀轉移到蘇中第一師,這里的敵軍工作部部長曾留學明治大學,敵軍工作部的大部分人都有日本留學經歷。同年10月,古賀轉移到新四軍第三師。該團敵軍工作部部長廖一帆(1917—1995),畢業于東京第一高等學校,[49]他幼年時期在馬來西亞學習,1935年起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留學,1937年回國來到延安,之后,相繼擔任延安總政治部敵軍工作訓練隊助教、新四軍敵軍工作干事、敵軍工作科長等職務。[50]
日本學者堀井弘一郎曾在戰后訪談過多位回國的日本俘虜,他指出:“敵軍工作部重視啟用有日本留學經歷、擅長講日語、了解日本文化習慣和日本人情感的人才,八路軍敵軍工作部的王學文部長、李初梨副部長和新四軍敵軍工作部的林植夫部長、李亞農副部長就是典型代表。王學文作為河上肇的學生之一,曾在京都帝國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李初梨和李亞農兄弟都是京都帝國大學的留學生,林植夫是熊本五高、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另外,不太被人們了解的林植夫,據說‘性格溫厚說話誠懇’,非常穩重(藤田證詞)。李亞農經常邀請日本人去自己家里吃飯(大和田證詞)。石堂清倫戰后在大連與李接觸,認為他是‘有出色人格的人’,‘是知識分子、是自由主義者’。出現在陷入屈辱與絕望的日本俘虜面前的,包括工農學校副校長趙安博以及129師敵工部長張香山在內的很多人,都是共產黨首屈一指的知日派知識分子。”[51]
第四,“延安留日同學會”有組織地與日本俘虜開展合作。在全面抗戰的中后期,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發傳單、喊話等方式積極投身對日宣傳活動,與留日歸國群體開展了有效的合作。1941年9月1日,“延安留日同學會”成立。成立大會上有80名成員出席,其中包括吳玉章、王學文、何敬思、李初梨、趙安博、江右書等。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與留日歸國群體在這里攜手合作,日本人反戰同盟①“反戰同盟”是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成立的反戰組織,與中國共產黨攜手開展對日本軍隊的宣傳與瓦解工作。、日本工農學校②日本工農學校成立于1940年,位于延安寶塔山下,主要任務是教育并轉化日本俘虜。的代表松本敏夫發表了致辭。此外,大會還決定設立日語圖書館。1942年2月17日,延安留日同學會邀請了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并共同舉行了聯歡會。當時,65歲的吳玉章在聯歡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在日本留學的很多中國學生,經常頻繁地接近日本人民,從他們那里得到真正的友誼和情愛,得到可靠的幫助和援助。我們是在日本開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從日本獲得大量的書籍和珍貴的文獻。”[52]吳玉章于1903年赴日留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之后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
中國共產黨軍隊中的留日歸國群體所學的專業各不相同,包括文學、哲學、藝術等。在俘虜教育過程中發揮作用最大的,是他們的日語能力和對日本文化的理解。留日歸國群體的出現,極大地消除了日本俘虜的不安,在爭取和轉化日本俘虜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留日歸國群體與敵情研究
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掌握日本和日軍的情況,十分重視“敵情研究”,注重研究日本國內形勢和日軍相關情況。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和中國共產黨軍隊中的留日歸國群體共同推動了敵情研究工作。
據1943年7月13日《解放日報》報道,在延安召開的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1周年紀念大會上,岡野進(野坂參三)提出了三個任務:一是強化理論學習;二是注重研究日本;三是學習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革命經驗。他提到,我們要認真研究本國情況,特別要研究日本資本主義的弱點和勤勞大眾的情況。[53]之后,岡野進向各地的反戰團體組織寫信,宣傳日本反戰組織的敵情研究等三大任務。[54]當時掌握敵情的主要手段有:1.有計劃地實施全面調查研究;2.由專門地區出身的人負責調查;3.從俘虜或投降者那里獲取情報;4.對日軍實施電話監聽;5.通過商販、親屬等收集日軍情報;6.在戰爭中收集日軍文件、信件;7.從報紙等公共刊物中收集情報。[55]這些掌握敵情的手段,大都需要高水平的日語能力,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和留日歸國群體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抗戰時期,針對日本政治、日本經濟、日本軍事、日本革命等各方面開展了敵情研究工作,主要的敵情研究機構和媒體如下。
一是日本問題研究會。總政治部負責人王稼祥召集抗日軍政大學的老師楊憲吾、敵軍工作部的劉型、軍委編譯局的曹汀等人,創立了日本問題研究會。初期階段,該研究會對日本的研究活動主要是由中國人進行的。其中成員之一王子野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發表過多篇與敵情相關的文章。[56]據辛亥革命英雄黃興的兒子黃乃回憶,敵軍工作部設有日本問題研究室,由野坂參三管轄部署。黃乃從1940年到1945年作為日本問題研究室的研究員從事敵情研究,并擔當野坂參三的研究秘書。[57]曾從事改造日本俘虜工作的劉國霖回憶,日本工農學校成立之后,每周六下午在總政治部由野坂主持召開“日本問題研究會”,每次出席人數有20~30人,其中包括總政治部及下屬的敵軍工作部、敵軍工作干部訓練學校、日本工農學校等相關人士。會上,每人分發一本《日本便覽》手冊,里面有介紹日本天皇制等內容。[58]
二是《敵國匯報》。《敵國匯報》是由八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日本問題研究會編輯、八路軍政治部發行的半月刊。它的前身是《敵國匯報》報紙,1941年2月開始作為雜志發行。它的特點是“政治化、大眾化、軍事化”,主要刊載介紹日本政治、經濟、風土等各方面情況的文章,并發表系統研究敵軍的資料。[59]
三是《敵偽研究》。《敵偽研究》是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軍工作部日本問題研究會敵偽研究社編委會編輯的月刊雜志,1941年5月20日發行創刊號。其主要目的是:系統研究和介紹敵偽的各種政策與活動,特別是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盡可能收集各種敵偽資料,為各領域同志開展敵偽研究和對敵戰爭提供參考資料。[60]
四是《解放日報》敵情特輯。《解放日報》會定期發行“敵情特輯”。1941年9月27日,該特輯在《解放日報》創刊后隔周發表,使用《解放日報》的第4版面。截至1945年3月31日,共發行“敵情特輯”66期。“敵情特輯”的主編就是黃乃。他曾在抗日戰爭前赴日本留學,寄宿在宮崎滔天的兒子宮崎龍介的家中,并與世界語提倡者長谷川照子成為朋友。黃乃因參加反戰運動被強制遣返回中國,戰爭開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61]1942年,在馬列學院的開學典禮上,毛澤東發表演講稱:“你只有進行了調查,進行了研究,才有發言權,比如說黃乃,他對日本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進行了調查研究,在日本問題上,他最有發言權。”[62]
五是《八路軍軍政雜志》。《八路軍軍政雜志》是以共產黨部隊的政治工作為中心的研究雜志,定期刊載一些與敵情相關的論文。如,1939年5月15日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刊載了譚政的《敵人在華北的現行政策》,文章介紹了日軍政策與八路軍的對策;[63]同一期也刊載了王思華的《敵軍的現狀》;[64]在第1卷第6期,該雜志刊載了王思華的《戰爭兩年后的日本政治經濟》,詳細分析了日本的政治經濟狀況。[65]
五、結語
綜上所述,延安時期,留日歸國群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利用其較高的日語能力和對日本的深入理解,在對日“二分法”、日本俘虜教育、敵情研究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意義可歸納如下。
第一,留日回國群體對中國共產黨對日“二分法”有較強的理解與認同。“二分法”這一對日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共產黨對日戰略的源頭。對日“二分法”對當前的對日政策和對日工作依然有參考價值。
第二,在留日回國群體的努力下,中國共產黨成功感化了一批日本俘虜。轉變立場的日本俘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全國各地成立覺醒聯盟、反戰同盟,有組織地開展了針對日軍的宣傳、瓦解工作,加速了日軍的潰敗。這些日本俘虜在戰后大都回到日本,成為促進中日友好交流的中堅力量。
第三,留日回國群體推動的敵情研究,為中國共產黨開展日本問題研究起到奠基作用。在信息相對閉塞的延安開展的敵情研究,為中國共產黨的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延安時期的敵情研究,是中國共產黨有組織、科學化研究日本問題的開始,對當前我國的日本問題研究依然有參考價值。
本文聚焦的是留日回國群體在中國共產黨對日工作中的歷史作用,包括對日“二分法”、日本俘虜教育、敵情研究等領域,沒有涉及對內的文藝創作、經濟建設等領域。這方面的研究有待今后另文梳理。
[注釋]
[1]王曉秋:《中國留學生留學日本110年歷史的回顧與啟示》,《留學生》2006年Z1號。
[2]孔繁嶺:《抗戰時期的中國留學教育》,《抗日戰爭研究》2005年第3期。
[3]徐志民:《帝國留學——抗戰時期在日中國留學生的生活實態》,《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4]廖垠雪:《留學生在抗戰中的作用》,《神州學人》2015年第9期。
[5]李華雨:《輸入延安的“新鮮血液”》,《神州學人》2015年第9期。
[6] 《八路軍政治部關于開展日軍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八路軍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第62頁。
[7]葉世昌、丁孝智:《王學文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經濟思想》,《江西財經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
[8]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32~34頁。
[9]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36頁。
[10]北京圖書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6卷),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第45~47頁。
[11]張香山:《中日關系管窺與見證》,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
[12]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58頁。
[13]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561頁。
[14]廖蓋龍、范源:《中國人名大詞典》(現任黨政軍領導人物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第202頁。
[15]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ー延安労農學校の記録)、サイマル出版會、1984年、17頁。
[16]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ー延安労農學校の記録)サイマル出版會、1984年、152頁。
[17]沈殿成:《中國人留學日本百年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50頁。
[18]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78頁。
[19]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85頁。
[20]河上肇著,林植夫譯:《資本主義經濟學之歷史的發展》,商務印書館,1933年。
[21]李一氓:《李一氓回憶錄》,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2~262頁。
[22]李維賢:《華僑愛國志士陳子谷》,《中華魂》1999年第12期。
[23]陳子谷:《懷念林植夫同志》,《革命人物》1985年第S1號。
[24]朱宗漢:《回憶林植夫先生》,《黨史資料與研究》1985年6號。
[25]中華名人協會等編:《中國人物年鑒》第20卷,華藝出版社,1995年,第175頁。
[26]新華社:《李初梨逝世》,《新文學史料》1994年3號。
[27]徐則浩:《從俘虜到戰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4頁。
[28]《史林》編輯部:《光輝的一生——李亞農同志傳略》,《史林》1986年第3號。
[29]劉貫一:《敵軍工作談片》,《新四軍回憶資料(第一卷)》,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79~80頁。
[30]陳修良:《懷念李亞農同志》,《史林》1986年第3號。
[31] 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外事係「極秘,中國共産黨日本特別支部検挙事件」早稲田大學中央図書館、ヲ1-5913-31,47頁。
[32] 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外事係「極秘,中國共産黨日本特別支部検挙事件」早稲田大學中央図書館、ヲ1-5913-31、48頁。
[33]王宜田、丁偉:《中共黨史上的東京事件》,《中共黨史資料》2009年第4號。
[34]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37頁。
[35]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62頁。
[36]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66~167頁。
[37]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63頁。
[38]人民中國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國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方書店、1982年、196頁。
[39]水野靖夫『日本軍と戦った日本兵:一反戦兵士の手記』、白石書店、1974年、107頁。
[40]陳子谷:《懷念林植夫同志》,《革命人物》1985年第S1號。
[41]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爭下中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198~200頁。
[42]劉國霖、鈴木傳三郎:《一個老八路和日本俘虜的回憶》,學苑出版社,2000年,第38頁。
[43]劉國霖、鈴木傳三郎:《一個老八路和日本俘虜的回憶》,學苑出版社,2000年,第39頁。
[44]王鴻賓:《東北人物大辭典》第2卷第2部,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20頁。
[45]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爭下中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166~167頁。
[46] 和田真一《生と死の岐路》、反戦同盟記録編集委員會編『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日本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出版部、1963年、69頁。
[47] 秋山良照「西瓜と焼餅」、反戦同盟記録編集委員會編『反戦兵士物語:在華日本人反戦同盟員の記録』、日本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出版部、1963年、51頁。
[48]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ー延安労農學校の記録』、サイマル出版會、1984年、159頁。
[49]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爭下中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174~175頁。
[50]楊增培:《梅州市志》第三卷,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24頁。
[51]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爭下中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66頁。
[52]孫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戰斗爭》,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01~202頁。
[53] 《岡野進同志指示留延日人,一致參加保衛邊區,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舉行周年紀念》,《解放日報》1943年7月13日,第2版。
[54]《岡野進函覆各地日人反戰團體,學習中共斗爭經驗》,《解放日報》1943年7月21日,第2版。
[55]周煥中主編:《特殊的戰線》,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7頁。
[56]徐則浩:《從俘虜到戰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41頁。
[57]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國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蕓春秋、2006年、122頁。
[58]姫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爭下中國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青木書店、1999年、249頁
[59]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日本問題研究會編:《敵國匯報》,1941年第二卷。
[60]八路軍野戰政治部敵工部日本問題研究會敵偽研究社編委會:《發刊詞》,《敵偽研究》1941年第1期。
[61]水谷尚子「『反日』以前:中國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文蕓春秋、2006年、113頁。
[62]張華:《黃乃:凸點符號里的傳奇》,《國際人才交流》1997年6號。
[63]譚政:《敵人在華北的現行政策》,《八路軍軍政雜志》第1卷第5號。
[64]王思華:《敵軍的現狀》,《八路軍軍政雜志》第1卷第5號。
[65]王思華:《戰爭兩年后的日本政治經濟》,《八路軍軍政雜志》第1卷第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