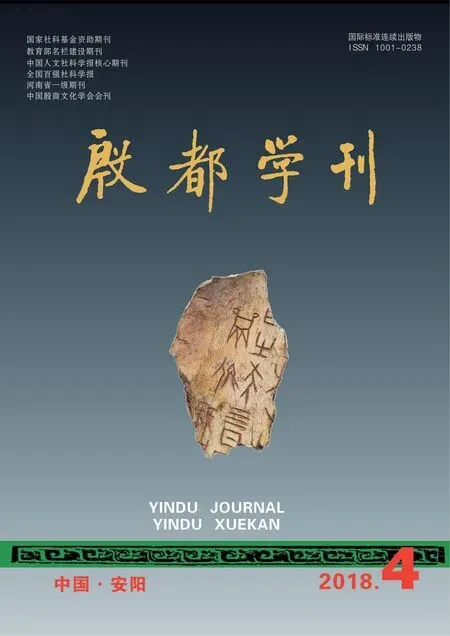北方幕府文人與元初北方文壇
任紅敏
(安陽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安陽 455000)
雖然金元之際北方中原一帶干戈寥落,兵荒馬亂,但北方文壇并不是寂寥的。這一時期,作為文化載體的儒士文人,處境是很艱難的,他們流離失所,朝不保夕,萍漂梗泛,為避兵燹,為謀生計,有的直接為蒙古統治者所用,如耶律楚材;有的歸隱林泉或遁入佛道以求全身遠禍,如李俊民、劉祁、杜瑛以及段克己、段成己等“河汾諸老”,依然進行著他們的創作;還有一部分文人到北方漢族世侯統治區域和忽必烈的金蓮川幕府,因漢人世侯和忽必烈優待文士、推崇儒學,金亡前后,這些地方更成為北方文士避難之所。他們散居各地,依憑這些世侯幕府和忽必烈的金蓮川幕府,在其轄地聚合成大大小小的文人群體。北方文人也借助漢人世侯幕府和忽必烈金蓮川幕府,互相往來交流,自然形成了這樣那樣的關系。
一
以真定史氏、東平嚴氏、順天張氏等為主的漢人世侯,重教崇儒,保護文人學士,許多亡金名士便留寓其間。真定史氏,據王惲記載說:“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颙軒,為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庵、張條山、孫議事,擢府薦達至光顯云”(《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1](卷48)。金末文壇盟主王(滹南)若虛,元(遺山)好問、李(敬齋)冶,都曾留寓真定。白(樞判)華,也在真定定居,白華之子白樸,即為“元曲四大家”之一,幼時鞠育于元好問家中,十多歲即隨父投靠史天澤,其后深受史天澤器重,可見當時真定文士云集的情形。東平地處齊、魯、魏文化的結合點上,文化底蘊深厚,吸引的儒士文人也最多。嚴實軍旅之暇,常與文士名流觴詠游從,講論經史。金亡前后,汴京地區的文人士大夫不少都輾轉流寓到了東平境內,據《新元史·嚴實傳》記載:“實在東平以宋子貞為評議官兼提舉學校,延致名儒康曄、李昶、徐世隆、孟祺等于幕府,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文學彬彬稱盛。實亦折節自厲,從儒者問古今成敗,至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2](P2380)元好問也在其中,且“客東平嚴實幕下最久” (趙翼《甌北詩話》),與東平文人群體交往密切,據蘇天爵記載:“我國肇定河朔,有若金進士元公好問,獨以文鳴,歌詩最其所長。及嚴侯興學東方,元公為之師,齊魯綴文之士,云起風生,以詞章相雄長,而閻、徐、李、孟之徒,世所謂杰然者也。”[3](卷5《西林李先生詩集》)東平人才薈萃,王磐、耶律有尚、陳膺、張澄父子、康曄、賈居貞、賈起、李昶、胡德安等均匯集東平,還有元好問曾向耶律楚材上書推薦“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寄中書耶律公書》)[4](P804)并要求重點保護的中州五十四名士當中的衍圣公孔元措、楊灸、張圣予、李世弼、徐世隆、杜仁杰、張澄、商挺、楊鴻、勾龍瀛、趙維道等十余人也匯聚東平,形成一個以東平為文化中心的所謂東平文人群體。據史籍所載,“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于他鎮”[5](P3736),張澄也曾作詩贊曰:“方今河朔藩鎮雄,衣冠往往羅其中。”[6](P181)元袁桷談到當時情況曾這樣評說:
朝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圣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渟伏,昔東諸侯闡興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于黌序,有自來矣。”桷向為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7](卷24《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其所謂“東諸侯”,即東平行臺。東平嚴氏世侯為保護儒士文人做出了很大貢獻,許多北方著名的文士都曾留居東平,其后元文壇大家虞集也有這樣的說法:“某蚤歲游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8](P532)順天,也是人才薈萃之地,“四方賢士,翕然來歸,冠佩藹然,有平原、稷下之盛。故好賢之譽日隆,事之利病日益聞,政化修明,人有生賴,既富而教,骎骎乎治平之世。”(《左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9](卷35)郝經、王鶚、樂夔、敬鉉等人均曾在張氏幕下。
這些文人名儒不僅在這些漢族世侯轄區形成一個個文人群體,相互之間交往密切,常酬唱贈答或游宴題詠,而且,不同轄區,處于不同地域文人之間也交游頗為頻繁密切。金源詩文大家元好問,“自中州斫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徐世隆《元遺山集序》)[10](P388)自金朝滅亡之后,元好問頻繁往來于齊、魯、燕、趙、晉、魏等地,依憑他在文壇的地位和聲望與各地文人交往頻繁,很多文人出自他的門下,如元初著名文人學士白樸、王惲、閻復、郝經、商琥等數十人都出自他的門下。在蒙古滅金后的數十年中,他搶救文獻,完成《中州集》和《壬辰雜編》二書,保存金源文脈,并上書耶律楚材推薦并要求保護中州五十四名士,并培養了白樸、王惲、閻復、郝經、商琥等元初著名文人學士,使得文明一脈不斷,元初北方之學術與詩文,蔚然稱盛。又如郝經,曾居于張柔幕下,后入仕忽必烈藩府。郝經長居北方并廣泛游歷燕京、東平、曲阜等地,與藩府文人以及依附漢族世侯的文士砥礪斯文,談經論藝,“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閻復《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墓志銘》)[11](卷5)這樣,在金末元初文脈存亡續絕之際,北方的文化和文學能夠繼續發展,得力于這些漢人世侯的庇護。
其后又有大批舊金文士進入蒙古統治區,有的進入蒙古政權,首當以忽必烈金蓮川藩府文人群體為主。蒙哥汗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開府金蓮川,思“大有為于天下”,廣延藩府舊臣與四方文學之士,形成了一個有著相同的政治目標和生活環境的特殊的文人群體,即所謂忽必烈金蓮川藩府文人群體[注]忽必烈金蓮川藩府文人包括:懷衛理學家群:姚樞、許衡、竇默、郝經和智迂等人;邢州學派:劉秉忠、劉秉恕、張文謙、張易、王恂、趙秉溫等人;從東平、真定、順天三個漢族世侯幕府均招攬了一些文士進入金蓮川藩府,其中,從東平嚴氏收攬的文士徐世隆、宋子貞、王磐、商挺、劉肅等人,從真定史氏招納的是張德輝、楊果、賈居貞、張礎、周惠等人,從順天張柔延攬的名儒王鶚,此外,還有趙璧、李簡、張耕、楊惟中、宋衜、楊果、馬亨、李克忠、杜思敬、周定甫、陳思濟、王博文、寇元德、王利用、李德輝、李庭等其他金源文士謀臣。金蓮川藩府侍從中的文士,主要分為兩類,一是精通儒學的漢族藩府侍衛,有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趙炳、高良弼、許國禎、許扆、譚澄、柴禎、姚天福、趙弼、崔斌等人;二是深受儒學影響有很高的漢文化造詣的非漢族侍衛謀臣,包括蒙古侍從文人闊闊、脫脫、禿忽魯、乃燕、霸突魯等,以及西域色目文人侍從孟速思、廉希憲、愛薛、也黑迭兒等人,以及女真人趙良弼等。。金蓮川藩府士人群體是一個較復雜的文人集團,人數眾多,來源廣泛,文化淵源和師承各異,他們大多是金末山東、山西、陜西、河北等不同地域的儒學、文學等領域的精英。這一文人群體不僅人數眾多、民族與地域來源廣泛,文化淵源和師承各異,而且各族文人經常接觸,廣泛交流,尊重理解,超越了種族的藩籬,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多族文人群體。在金蓮川藩府之中,集中的是當時北方一些代表性的詩文作家,比較突出的有郝經、劉秉忠、王磐、許衡等人,他們用自己的創作,創造了北方文壇的繁榮。再者,從東平、真定、順天三個漢族幕府,先后有徐世隆、宋子貞、王磐、商挺、劉肅、張德輝、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賈居貞、張礎、周惠、王鶚等人入侍忽必烈金蓮川藩府。他們進入了忽必烈潛邸,又未曾脫離原來的幕府,依然和原來的文人圈保持聯系,因而,他們無論在東平、真定、順天等地,還是在金蓮川藩府文人群體中,都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系,文人之間相互交往,酬唱贈答。可以說,漢族世侯和忽必烈藩府的文人群體以及依附漢人世侯庇護的北方文人之間有著這樣或者那樣的聯系,而且不同地區的文人之間又通過這些入侍、留寓幕府及世侯的儒士文人群體互相交流與融合。
二
可以說,元初北方文壇并不寂寥,元好問、楊奐、許衡、姚樞、郝經等幕府文人和部分遺民作家開創了元初北方文學的繁榮。元好問在元代生活了近三十年,對元代前期北方文壇影響巨大,作為當時文壇的集大成者,處于北方文壇盟主地位,在金元之際的學術史、文學史上地位極高,影響力極大,可以說他總結了金代文學和文化并開啟元代文學文化,其弟子郝經這樣評價他:“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方吾道壞爛,文曜噎昩,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脈系而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也。”[9](卷35)“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9](卷21)這并非過譽之詞,清代趙翼也有“兩朝文獻一衰翁”[注](清)趙翼《甌北集》卷三三《題元遺山集》,清嘉慶十七年湛貽堂刻本。詩云:“身閱興亡浩劫空,兩朝文獻一衰翁。無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行殿幽蘭悲夜火,故都喬木泣秋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之說法,他憑借個人的影響力,從事著文化恢復和重建事業,影響了當時北方一個時代的文學走向。清人顧嗣立在《元詩選》袁桷小傳中談元詩發展說:
元興承金宋之季,遺山元裕之以鴻朗高華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劉夢吉之徒繼之,故北方之學,至中統、至元而大盛;趙子昂以宋王孫入仕,風流儒雅,冠絕一時,鄧善之、袁伯長輩從而和之,而詩學又為之一變。于是虞、楊、范、揭,一時并起。至治、天歷之盛,實開于大德、延祐之間。[12](P593)
另外一點,元好問和元初活躍于文壇的忽必烈金蓮川藩府文人、東平行臺幕府文人以及河北和河汾地區儒士均有聯系。在滅金后的北方,元好問(遺山)及其弟子郝經(伯常),以及仰慕元好問的劉因(夢吉)為當時詩壇宗主。郝經和后起的著名詩人劉因,是元初北方詩學大宗,郝經和劉因的詩學思想和理論均受到元好問的影響。清代宋犖《漫堂說詩》云:“元初襲金源派,以好問為大宗。”[13](卷27)金之末造,北方詩歌是蘇、黃的天下,北方詩人尹拓曾有“學蘇、黃則卑猥也”之說[14](P86)。當時南北詩壇同時有向唐詩回歸的傾象,北方詩壇是學盛唐詩歌,學盛唐之氣勢,但并未學到其渾厚而是流于粗豪,因而是“金、宋季世之弊”,南方則是學晚唐之清圓但又流于萎弱。元好問的詩學觀念秉承金趙秉文所倡導的唐詩,宗法“多法唐人李杜諸公”,論詩也多有“以唐人為指歸”之論[注](元)元好問:《楊叔能小亨集引》,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頁。按元好問晚年論詩“以唐人為指歸”,其所謂“唐人”,具體所指則為“開宋調”的韓愈。所以,其論詩宗趣,倒傾向于宋詩。見拙撰《借鑒中求超越:在唐宋詩之外求出路——元好問關于詩歌發展之路的思考》。,推尊杜甫,為元代的唐詩學開端定調。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集詩學理論為一體,所編金詩總集《中州集》,成書于元,其中詩人小傳包含了豐富而精到的詩學思想,且大量的詩集序引題跋,多作于入元后,成為重要和珍貴的詩學文獻。
元好問也是金元之際的文章大家,被譽為“元文章之祖”,文章內容浩博,旁征博引,才力雄厚,近代學術大師鄭振鐸曾指出元好問文壇宗主地位:“元初的散文,仍以元好問為宗匠。”元徐世隆在《元遺山文集序》中更是特別強調了元好問在金末元初文壇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
自中州斵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跡益窮,其文益富,而其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后進,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為泛愛,至于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后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15](P414)
元好問認為文章乃是“千古事業”、“經綸之業”,追求“文以存史”,追溯唐宋文章風格,兼容唐宋各大家之長而自成一家,正如徐世隆評價的:“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 其文風平易暢達而又雄渾挺拔,宏肆軼蕩而不失清新雋永,尤其是金亡后創作的文章更加老成渾厚,如同杜甫經歷了安史之亂后的詩更加渾厚而沉郁頓挫,世亂時移反而成就了元好問的文章發展,李冶曾評價道:“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珍矣。”(李冶:《元遺山集序》)[10](P20)元好問碑志文的史學價值和文學成就都很高,如《孫伯英墓銘》、《族祖處士墓銘》、《劉景玄墓銘》、《敏之兄墓銘》、《清涼相禪師墓銘》、《聶孝女墓銘》等,“以文存史”,有著豐富深刻的社會內容。
當然,一個王朝的興亡和一代文學的興亡不是完全同軌的。金代文學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因為地域和文化的差異,有不同于南方宋王朝的特色。清人張金吾在金文總集《金文最》序言中也指出:“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瀆有其三,川岳炳靈,文學之士后先相望。惟時士大夫察雄深渾厚之氣,習峻厲嚴肅之俗,風教固殊,氣象亦異,故發為文章,類皆華實相扶,骨力遒上……后之人讀其遺文,考其體裁,而知北地之堅強,絕勝江南之柔弱。”[16](P10)1234年蒙古滅金,以此為標志,北方的學術與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也即是元代學術史和文學史的開端,而汴京依然是當時北方最大的文化中心,許多金源文人聚集于此。
在元初的北方文壇,還有一部分遺民作家在金亡之后起到傳承文脈的關鍵作用,清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元初北方遺民作家說:“諸老以金源遺逸,抗節林泉,均有淵明義熙之志,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王若虛、麻革、段克己、段成己兄弟,李俊民、杜仁杰、陳賡、陳庚兄弟,劉祁、曹之謙等人,以金遺民的身份存在,他們把對故國的感情和山林隱逸之情志融于詩文創作中,其文章風格自然是超邁拔俗。在這期間,元好問和這些遺民文人來往密切,如元初的王惲在《西巖趙君文集序》中已經指出:“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脈,不絕如線,賴元、李、杜、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17](P205)所列金元易代之際的名家包括元好問、李庭、杜仁杰、曹之謙、麻革和劉祁(麻革與劉祁是太學同學)等人。金亡之后,元好問奔走于太原、大名、濟南、東平、燕都之間,河汾諸老中的麻革、曹之謙于1239年之后主持平陽經籍所,陳庚、張宇都在平陽,段成己于1252年徙居平陽,1253年曹之謙因眼疾“膜廢于家”,由陳庚接替其工作,麻革赴陜看望好友李庭,爾后隱居晉南虞鄉王官谷。麻革好友魏璠和李庭入仕忽必烈金蓮川藩府,麻革雖未入仕忽必烈藩府,但他和藩府文人也有著各種關系。金元之際的北方文壇,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寂寥。清人顧嗣立在《元詩選》之袁桷小傳中說:“元興,承金宋之季,遺山元裕之以鴻朗高華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劉夢吉之徒繼之,故北方之學,至中統、至元而大盛。”[12](P593)金南渡后的文壇,學唐成為風氣。劉祁《歸潛志》卷八載:“南渡后,文風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于人。已而麻知幾、李晨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后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為法也。”[14](P85)
清顧嗣立論元初北方之學:“北方之學,變于元初。自遺山以風雅開宗,蘇門以理學探本。一時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陽始升,春卉方茁,宜其風尚之日趣于盛也。”[12](P444)指出了開創元初北方學術、文章格局的兩大宗,一個是作為金元一代文宗的元好問,元好問以及河汾諸老在金末元初文壇的活動對元初文壇的影響甚大,在北方文壇“以風雅開宗”;另外一個是蘇門理學,因當年許衡、姚樞等人在蘇門山講道而得名[注]《元詩選》二集姚樞小傳述蘇門學派形成的過程說:“初,雪齋與惟中從太子闊出南征,軍中得名儒趙復,始得程朱之書。后棄官攜家來輝,中堂龕孔子容,旁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自板諸經,散之四方。時河內許衡平仲、廣平竇默漢卿并在衛,雪齋時過漢卿茅齋,而平仲亦特造蘇門,盡室相依以居。三人互相講習,而北方之學者始聞進學之序焉。”,蘇門理學文人多入仕忽必烈藩府,和蒙古上層關系密切。姚樞、許衡等“以理學探本”,以學術而不以詩文名世。這就涉及到了一件在元代學術史上帶有某種標志性意義的大事:在蒙古滅金的第二年(1335),蒙古太子闊出率大軍南征侵宋,拔德安(今湖北安陸),俘獲宋儒士趙復。忽必烈藩府儒士楊惟中和姚樞當時在軍中尋求精通儒、釋、道、醫、卜、百工等人才。他們帶趙復北上,于燕京周子(周敦頤)祠及太極書院,請趙復講學其中。趙復開始在北方傳授程朱理學,于是程朱之學深受北方儒生歡迎,在北方迅速而廣泛傳播。北方學者,在原有學術基礎之上,大多吸收了朱熹之學,其中包括忽必烈藩府理學家姚樞、許衡、郝經,還有北方理學家劉因等人。
蘇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許衡,后世史學家稱之為元朝開國大儒。許衡(1209—1281),字仲平,號魯齋,卒謚文正,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元人揭傒斯奉詔撰吳澄《神道碑》,以恢弘之論開篇:“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18](P505)許衡之學并非重在心性義理的探討,所關注的乃是經世致用,主要是當時所迫切和急需的社會和道德重建。忽必烈在潛邸,“思大有為于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5](P57),姚樞等被召。蒙哥汗四年(1254),忽必烈出為秦王,召許衡為京兆提學。元世祖至元初,許衡上《時務五事》疏,建言行漢法,重農桑,興學校。其后又參與元代的朝儀和官制的制定,以后又創國子學,與郭守敬等編定《授時歷》。他和劉秉忠等人,共同奠定了元代的開國規模,人們贊其歷史功績,稱其為“孔顏正脈,斯文之宗。用夏變夷,千古人龍。”[19](卷14《唐山李天秩祭文》)在元代學術和文學發展史上許衡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深遠影響。世祖至元八年(1271),任命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授蒙古子弟。許衡奏請弟子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等十二人入國學為侍讀,以陶冶蒙古生員。許衡一生,主要從事教育和理學的推廣和實行,以影響和改變蒙古貴族,即所謂“用夏變夷”。虞集評價許衡對理學傳播的貢獻說:“使國人知有圣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矣。”[19](卷14《先儒議論》)許衡對元代儒學的傳播和各族子弟培養的首創之功無人可及,確實是“圣朝道學一脈,乃自先生(許衡)發之。”[20](卷8《左丞許文正公》)在忽必烈時期,蘇門學術在北方的地位和影響,逐漸超過了元好問一派。
許衡認為:“凡人為詩文,出于何而能若是?曰:出于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蓋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鹽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19](卷1《語錄上》)他一生所致力的,既不是文章家的辭章文字之工,也不是理學家的天理性命之奧,而是將儒學或說理學應用于政治實踐。他關注的依然是經世致用,是日用常行,與傳統儒學主內斂而更重視個人心性修養是不同的,許衡學術的基本精神是重實踐性的。正如明人何瑭《表彰文正公碑記》所言:“學以躬行為急,而不徒事乎語言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為先,而不徒極乎性命之奧。其所得者,蓋純乎正而不可加矣。”他并不“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而著意于“修齊治平之方,義利取舍之分”[19](卷14《先儒議論》)。
許衡認為:“能文之士必蔽。彼將天地間文理,都于紙上布擺成文,則事物之當文者所闕多矣”,“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21](P68)有文名必然會導致身心之累,你一旦成為文章名家,各色人等都來求文。面對求文者,就像面對手執弓矢利器的進攻者一樣,你將非常被動,要做到與所當與、拒所當拒是很難的,你將很難做人。這即是文名之累。許衡認為,文士不能治國,因為按他的邏輯推理,文高必然德下,于是文高就只能位下。他說:
唯仁者宜在高位,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謂此理得之于心也。后世以智術文才之士君國子民,此等人豈可在君長之位?縱文章如蘇、黃,也服不得不識字人。有德則萬人皆服,是萬人共尊者。非一藝一能服其同類者也。[19](卷2《語錄下》)
這樣看來,文為德之累,文也就為身之累。許衡總是以倫理的、社會功利的、理性的眼光而不是藝術的、審美的眼光審視文學。許衡反對專意為文,若要提高文章寫作水平,不是靠詞章,而在于修養身心,提高德行,圣人之文便是“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19](卷2《語錄下》),無意為文而文自生,這樣的文章當然不會害道。
許衡人格風范自是大家風度,他的弟子門人非常佩服和景仰老師的人格魅力,據《門人白棟題思親亭記》所記:“魯齋先生之寓是邑也,時與門弟子一至泉上,吟風詠月,悠然而歸。家無儋石之儲,心有天地之春。雖曾點之風乎舞雩,明道之過乎前川,樂不逾是。”[19](卷14《古今題詠》)大有孔夫子之灑落襟懷,超塵出俗,不為世事所累,而且是很有情趣的人。他的文章簡潔明了、醇正溫厚,乃典型的儒者文風,四庫館臣評價說:“其文章無意修詞,而自然明白醇正。諸體詩亦具有風格,尤講學家所難得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魯齋遺書》提要)。作為一位講學家能取得相當的文學成就,是文學主張與人格風范融合的結果。許衡追求散文風格的平實簡易,有溫柔敦厚之旨,并且含蓄蘊藉。他現存的散文,可以分成語錄體和古文體兩類。宋代理學家以為文章害道,于是以語錄傳道,他們遠法先秦諸子,近取禪宗語體,創立新語錄體散文。許衡的語錄體散文即承此而來,其語錄文章樸實無華,簡要而名理,不夸張不修飾不鋪排,而是直奔主題,揭示本質,娓娓而談從容和緩,顯示出溫柔敦厚、含蓄和緩、雍容正大的氣象。許衡文章有疏、說、序、書、祭文、書狀等體裁,作文長于論說,最有影響的文章是上忽必烈《時務五事》疏,如推心置腹,坦然告白,如細雨潤物,讀者在渾然不覺中已經接受其意見。雖然許衡聲稱不專意為文,其實具有很高的文章寫作技巧,這類文章顯然是精心打造的,并且很講究文法。
許衡的《魯齋遺書》卷十一存詩一卷,收各體詩84首,詞5首。其詩無雕琢而有深渾氣象,風格近于杜甫。如其七律《題武郎中桃溪歸隱圖》五首之四則閑靜而恬淡,有陶詩風味:
門外秋千擺翠煙,籬邊雞犬亦閑閑。更教爛熳花千樹,對著縈紆水一灣。好景已憑摩詰畫,他年重約長卿還。尋思此世人心別,又愛功名又愛山。[12](P439)
詩是可愛的,詩人的形象因而也是可愛的,這形象和古板迂執的理學先生很難聯系起來。七言絕句《宿卓水》五首之二:“寒釭挑盡火重生,竹有清聲月有明。一夜客窗眠不穩,卻聽山犬吠柴荊。”有意象,有境界,有韻致,有風味,有情趣,也有性情,很能見出詩人情性。人們認為,宋及元初理學家詩風受北宋邵雍影響,有所謂詞旨質直、自然見道的“擊壤體”。許衡的詩作,決不是“擊壤”一路。
許衡也能詞,其詞清雅中蘊含風致,不同于《鳴鶴余音》一類淡乎寡味之作。其[滿江紅]《別大名親舊》云: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后、此般憔悴,怎禁離別。淚苦滴成襟畔濕,愁多擁就心頭結。倚東風、搔首謾無聊,總難說。 黃卷內,消白日。青鏡里,增華發。念歲寒交友,故山煙月。虛道人生歸去好,誰知美事難雙得。計從今、佳會幾何時,長相憶。[注]此作除載《魯齋遺書》卷十一外,收入《元草堂詩余》卷上、《中州名賢文表》卷五、《花草粹編》卷一七、《歷代詩余》卷五六、《詞綜》卷二七。總集所收與《魯齋遺書》所載文字略有出入,此從《元草堂詩余》。
清《歷代詩餘》卷一一九引《古今詞話》云:“此被召時作也。又嘗自言曰:生平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其心亦可哀矣。”詞的感情是真摯的,因而也是很感人的。就藝術水平說,雖稱不上杰作,但也是優秀的作品,并不平庸。
蘇門學派的開創者姚樞(1203—1280),是忽必烈最器重的儒臣之一,字公茂,號敬齋,又號雪齋,河南洛陽人。他邀請儒士趙復北上燕京(今北京),請趙復講學并大力推崇朱熹理學。太宗窩闊臺十三年(1241年),姚樞授燕京行臺郎中,行臺牙魯瓦赤惟事財貨,不行漢法,姚樞身為幕長,因道、志不同而毅然辭官,攜家隱居輝州蘇門山(今屬河南),致力于理學的研究和傳播。由此形成了元初的蘇門之學。元許有壬撰《雪齋書院記》稱:“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于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得也。皇元啟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姚公焉。”[22](卷6)表彰他在當時北方傳播朱學之功。
姚樞是較早進入蒙古政權的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漢人,學術和詩文,都非其優長,但他卻有一個明確的意識:積極地用中原文化去影響蒙古當權者。他能詩也能文,他存世的詩文,僅有《元詩選》二集所收詩25首,題《雪齋集》;另有《宋元詩會》卷六十七所收七言古詩二首,這兩首寫得大氣磅礴,卓有盛唐風致,但卻又見于郝經《陵川集》卷十,當是郝經之作。文章則有《全元文》卷六十四所收文三篇。《元詩選》所收25首,有21首是一組,乃唱和劉秉忠韻而作《聰仲晦古意廿一首愛而和之仍次其韻》,這21首詩,顯然受宋詩影響,以詩言理,淡乎寡味。其中也有比較好的,如其十七:“有士氣凌云,孤松挺高節。壯懷入酣歌,歌長擊壺缺。鬢發日以秋,肝腸老于鐵。從知養浩然,此意潛消歇。”[23](P129)詩風質實而厚重,沒有金末詩的尖新,也沒有宋末之纖瑣。姚樞能文,但其文章幾乎無傳,今人編《全元文》,輯得其文三篇:《請申止殺詔》、《言大本遠業疏》、《論救時之弊三十條》。姚樞在北方文壇的影響主要是他在忽必烈政權的地位和理學上的地位,并非其詩文創作。
楊奐(1186—1255),本名煥,改奐,又名知章,又或作英,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今陜西乾縣)人,金末名士。蒙古窩闊臺汗十年(1238)選試東平,詞賦、論兩科皆中第一,其后任河南路征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卒謚文憲。楊奐也曾入仕忽必烈藩府,和許衡、姚樞等人有過交往,也屬于蘇門學派,《宋元學案》卷九〇《魯齋學案》列其為“雪齋(姚樞)學侶”,他在學術和理學上的成就得到北上儒士趙復的肯定,且據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書,明圣賢之出處,辯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三《廉訪使楊文憲公》)說明了楊奐在理學上的成就。
楊奐在元初北方文壇據有極高的地位,時人稱“遺山、紫陽一代宗盟”,與元好問一起成為一代文壇宗主,又稱其“文章、道德為第一流人物”(魏初《青崖集》卷五《跋宋漢臣諸賢尺版手軸》)。楊奐是金元之際文章名家,文風宗法韓愈,元好問《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稱其:“作文刬刮塵爛,創為裁制,以蹈襲剽竊為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遺山先生集》卷二三)楊奐對韓愈情有獨鐘,學習、整理韓愈作品而編輯成《韓子》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六《還山遺稿》提要對楊奐詩文做出客觀評價:“奐詩文皆光明俊偉,有中原文獻之遺,非南宋江湖諸人氣含蔬筍者可及。”他遺存下來的《還山遺稿》二卷中《射虎記》、《重修岳云宮記》、《與姚公茂書》、《汴故宮記》、《東游記》以及《全元文》所收的《重修太清觀記》、《京兆劉處士墓碣》等都是寫得非常好的文章,文字簡凈,不枝不蔓,有韓愈為文“陳言勿去”和“詞必己出”的風格,尤其是《京兆劉處士墓碣》一文最為精彩,以傳奇筆法寫劉處士這位奇人的奇學異才、奇行異貌、奇異性格、奇志大節,乃奇文一篇,開元代以傳奇為傳記的先河[注]元代受傳奇小說影響,以傳奇筆法寫傳記,寫奇人奇事,這類文章很多,元代的文章大家多有此類文章,如姚燧的《南京路總管張公墓志銘》、《太華真隱褚君傳》,虞集的《孝女贊序》,黃溍的《秋江黃君墓志銘》,元末宋濂的《秦士錄》、《竹溪逸民傳》、《抱甕子傳》、《吾衍傳》、《樗散生傳》,王袆的《吾丘子行傳》等,這一系列作品,在中國散文史上顯示出特異的光彩。。楊奐詩文“光明俊偉”,文如此,詩也如此。今存《還山遺稿》卷下收五絕、五律、七絕、七律、五古、七古共62題102首。20世紀初,張鈞衡又從顧嗣立《元詩選》二集中輯得15首,編為補遺一卷。其留詩的數量是可觀的。楊奐詩確實沒有南宋江湖詩的枯寂和清苦,他秉承中原地域厚重之氣,其詩渾厚而豐潤,有大山廣澤之氣象,舒徐之中自有深醇。
郝經本是元好問弟子,受元好問影響是最直接的,所以他論詩崇尚雄奇,推崇高古,與元好問一樣,體現了“中州千古英雄氣”。他發揮理學思維而創“內游”說,則可看做他的理學文論與詩論的創造性貢獻。元初北方理學大師劉因也是在北方學術背景上接受朱熹理學的,劉因論詩的文字不多,但他以禮、樂、御、射、書、數“六藝”為“古之藝”,而以詩、文、書、畫為“今之藝”,認為今人也應與古人一樣“游于藝”,游古藝已不可能,則應游“今之藝”。“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身”,“如是而為詩文,如是而為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為君相,可以為將帥,可以致君為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一《述學》)表現了令人佩服的通達眼光。郝經和劉因均是元初北方文壇影響一代的名家,郝經文章大氣包舉,蒼渾綺麗,雄奇奔放、汪洋恣肆,詩歌風格多樣,剛柔相濟,或慷慨悲愴,或含蓄蒼涼,或清新綺麗,或明秀清雅,亦或豪邁奇崛。劉因學問通達,文章醇厚樸實,條理清晰,詩歌情韻深厚,于平淡中寓豪放,深醇中寓迂闊,平粹中寓思辯。他們二人在元初北方文壇是當之無愧的詩文大宗。
不過,蘇門理學一派在許衡之后就發生變異,明薛瑄《讀書錄》卷二說:“魯齋學徒,在當時為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24](P1066)蘇門理學沒有傳人。蘇門學派第二代突出的代表是姚燧,他與蘇門第一代三位主要人物之間都有最為密切的關系:他是許衡的弟子,姚樞的侄子,楊奐的女婿。但他沒有繼承蘇門理學,而成為一代文章宗匠,流為文章家了,于是許衡等開創的蘇門學派,到他這里就演變成了一個文派。
因而,可以肯定,金末元初北方文壇非但并不沉寂,還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繁榮。在真定史氏、東平嚴氏、順天張氏等漢人世侯幕府以及著名的忽必烈金蓮川藩府聚集了許多北方的儒士文人,并聚合成大大小小的文人群體,這些文人群體以及依附漢人世侯庇護的北方文人之間又形成了這樣或者那樣的聯系,不同地區的文人之間又通過這些入侍、留寓幕府和世侯的文人互相交流與融合。元好問、楊奐、耶律楚材、楊弘道、許衡、姚樞、郝經等幕府文人及一部分遺民作家開創了元初北方文學的繁榮并引領了元初北方文壇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