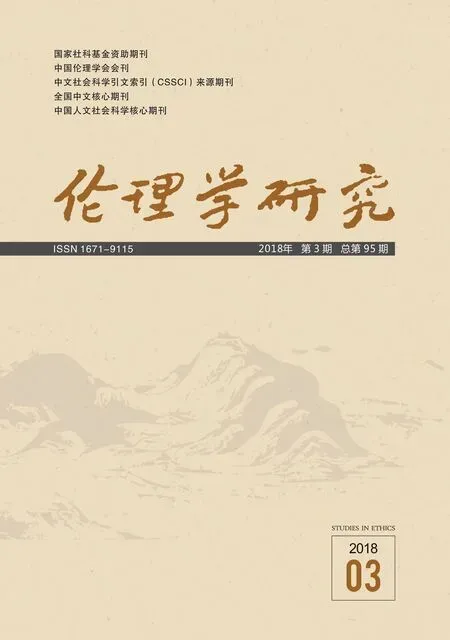普適傳播的技術邏輯與倫理審視
謝亞可
人類傳播史就是一部科技進化史。科技進步不斷推動媒介形態、傳播方式的革新和人類生產生活及交往方式的重塑。人類社會歷經語言傳播、書寫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網絡傳播等五次傳播革命,現已跨入移動傳播時代。在我們欣喜于數字化、移動化、社會化媒介所編制的傳播圖景之時,一場以普適計算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合創新正在催生一場新的傳播革命,本文將其定義為“普適傳播”。互聯網發軔之始,美國學者馬克·維瑟提出了普適計算(Ubiquitous Computing)的設想:趨于微型化、植入化、低廉化的計算設備融入網絡、融入環境、融入生活,像空氣一樣難以察覺,甚至從人們意識中消失卻又隨時隨地提供信息和服務。“U-biquitous”意為“無處不在”,常被來形容無處不在的上帝。馬克·維瑟認為:“只有當計算進入人們生活環境而不是強迫人們進入計算的世界時,機器的使用才能像林中漫步一樣新鮮有趣。”[1]20多年來,普適計算作為一種看似遙遠的科技預想并未進入大眾視野,而與之概念相近的物聯網(IoT)已經成為業界、學界和公眾認知領域的熱詞。物聯網是互聯網的拓展和深化,也是普適計算的雛形和前奏。隨著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信息技術融合創新,普適計算的夢想正在照入現實。普適計算開創了一種“無所不在、無時不有、智能進化”的普適傳播環境:傳播主體從人和特定媒介延伸到智能設備、物品乃至環境本身;傳播網絡從互聯網拓展到物聯網、泛在網;傳播形式從文字、圖片、音視頻拓展到VR、AR、體感、全息投影等全媒體全感知;傳播服務從新聞資訊、社會教育、大眾娛樂升級為一體化、貼身式智慧服務;傳播體驗從數字化、互動化升級為智能化、沉浸化、臨境化。普適傳播具有鮮明的泛在化特征,即泛主體、泛網絡、泛內容、泛智能、泛時域、泛空域、泛終端等,信息傳播突破主體、渠道和時空限制,人們可以在適宜的時域、空域、場景,以適宜的媒介形式自由便捷地獲取適宜的媒介信息和服務,并實現與他人(組織)、智能設備和物品之間的智能交流。
一、普適傳播的技術邏輯
技術是推動人類傳播變革的本源動力,人類社會的每一次技術躍遷都開創了新的傳播時代。縱觀人類傳播進化史,基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標志性技術形成了不同的傳播范式:基于“印刷術”的印刷傳播讓信息得以高效復制,人類由人際傳播進入大眾傳播;基于“電波、電視、電話等”的電子傳播跨越時空藩籬,人類由大眾傳播進入全球傳播;基于“互聯網、桌面PC”的網絡傳播讓麥克盧漢的“地球村”預言成為現實,人類進入信息化時代;基于“WIFI、4G、手機、移動終端等”的移動傳播進一步突破時空局限,人類進入媒介化生存時代。移動傳播之后,人類將進入以普適計算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集群為技術基礎的普適傳播時代。2017年底上線的國內首個AI媒體平臺——“媒體大腦”以“憑計算之力、求數據洞察、賦萬物為媒、迎智能時代”為愿景,已經向世人展示了未來普適傳播的美好云圖。新興信息技術在加速傳播網絡、媒介終端智能升級的同時,正在推動新一輪媒介生產流程、產品形態、產業生態的重構。在以普適計算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驅動下,“無處不在的感知、無處不在的網絡、無處不在的計算、不知不覺的服務(透明感知)”正在成為現實,并引發人類生產生活各領域的顛覆變革,也必然加速人類媒介形態、傳播方式的進化。無處不在的微型化、植入化的傳感器、可穿戴設備、生物芯片猶如高度敏感的感官和神經末梢,對人體、環境、設備和物體全面透徹感知,為一切的交互、計算和服務奠定基礎。無處不在的泛在網絡猶如通暢無礙的“血脈”,連通一切人、機、物,實現復雜環境下海量異構節點間的無縫連接和實時交互。無處不在的感知、網絡匯聚海量信息、數據和知識形成大數據,猶如“超能記憶庫”。基于云計算的無處不在的計算猶如“超強大腦”,海量小型化乃至納米級、量子級終端彌布于人們生活的每一處角落,通過云服務器向不同時空場景下的用戶提供優質高效的信息和服務。借助人工智能技術,信息感知、傳輸、存儲、運算、發布等過程被注入“思維”和“靈魂”,智能終端化身為如影隨形的“私人管家”和“靈魂伴侶”,人們趨于把更多更大的決策權交由媒介設備,在免打擾或少受打擾的環境下實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而又不可見”的普適傳播夢想。
簡而言之,普適傳播是傳播數字化、個性化、智能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是隨著信息科技的極大發展、傳播主體的無限拓展、媒介形態的極大豐富、傳播網絡的無縫覆蓋、媒介環境的無限放大、信息服務的智能升級、虛擬與現實的交匯融合而產生的一場新傳播革命。與網絡傳播、移動傳播相比,普適傳播呈現出泛感知、泛網絡、泛媒介、泛智能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技術底色。
泛感知:萬物可感,度量一切。普適傳播時代,無處不在的傳感設備賦予萬物動態感知、自我呈現功能,物體從一堆冰冷的物理材料升格為信息收集、加工和傳播的主體。萬物可感標志著物體信源地位的確立,同時也是傳播行為的主動性與能動性的實現前提。智能感知設備的普及讓“物—人”信息交互成為常態,“物”感信息通過“物—人”信息系統可以直達受眾。無所不在的智能感知設備作為人體器官的延伸極大拓展了人類的感知范圍和維度,并有效避免了經驗感知和中介感知無法避免的信息失真和信息噪聲。而借助虛擬現實技術,人類對現實世界的感知將由視聽覺體驗延伸至全方位的感官體驗。
泛網絡:萬物互聯,連接一切。從互聯網、WIFI、3G/4G到以傳感技術、射頻識別技術、5G等為基礎的泛在網,從電腦、電子設備之間的連接到人、機、物之間的萬物互聯,從網絡的環境化到環境的網絡化,人類社會連接的維度、深度不斷延展。泛在網既是新一代的信息傳播工具和傳播平臺,又是普適傳播時代的公共基礎設施。泛在網具有全域覆蓋、實時在線、高質高效傳輸等特點,信息傳輸在技術層面將徹底擺脫時空限制,海量節點間實現隨時隨地“一對一”“一對多”“多對多”的連接。萬物互聯的深層意義還在于超越技術層面的信息傳輸,進而實現節點之間、節點與網絡之間的智能化、交互式、自主態對話。
泛媒介:萬物皆媒,人亦媒化。普適傳播時代,媒介形態和范圍無限延展,媒介與非媒介的邊界模糊甚至消失,信息傳播必須依賴特定媒介的傳播規則被徹底顛覆。智能設備、物品甚至人體和環境本身開始成為媒介,一切能夠采集、存儲、加工、傳播、展示和接收信息的人、機、物都被賦予媒介功能。隨著生物傳感、腦機融合、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媒介將不僅只是人體延伸,而是呈現出“人媒合一”形態,成為最高層級的媒介終端。
泛智能:媒介有靈,智能服務。泛智能是泛感知、泛網絡、泛媒介的綜合體現和必然要求。無所不在的“人·機·物”傳播依賴智能感知、網絡和媒介設備以人為中心的智能服務。普適傳播是一個“感知→定位→傳播→反饋→再感知……”的動態定制過程。智能媒體基于不同場景下用戶特征、需求的多維度提取,完成用戶精準畫像,提供從內容預測、生產到分發、體驗等一系列更具人性化和個性化的媒體服務,并根據實時采集的用戶反饋數據優化傳播形式和內容實現更為精準的用戶匹配。此外,智能感知設備喚醒了所有沉睡的信息資源,在新華社“媒體大腦·2410智能媒體生產平臺”的設想中,傳感器成為媒體之眼,從傳感器設備智能識別、檢測而獲取新聞線索,快速生產富媒體內容,結合數據,快速生成可視化內容。
“未來的高度發達的虛擬環境傳播將極大地不同于現代媒介傳播,未來傳播滲透于整個社會生活之中,媒介(網絡)不再顯其蹤影,而是消弭于整個環境之中……”[2]。普適傳播的終極演進趨勢是媒介的“無形無象”和傳播的“自然而然”。專門化的媒介終端在人們視線中消失,物理意義上的“屏幕”“界面”隱匿不見,“媒介”在人類心理層面趨于模糊,人與媒介、媒介與環境融為一體,以自然面目出現的終端隨處可見、觸手可及,傳播行為“自然而然”,就像空氣一樣融在環境中,人類似乎從發明和使用媒介的時代“后退”到了“隱形媒介時代”。正如馬克·維瑟所說:“技術應該創造安靜……最好的計算機是安靜的、看不見的奴隸。”[1]
二、普適傳播的倫理審視
加拿大經濟史學家、傳播學家英尼斯曾說:“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3]普適傳播技術的“野蠻生長”不斷重塑媒介生態,改寫傳播規則,并引發社會結構和人類生活方式的變革。與此同時,新媒介技術的弊端也將顯露并引發或加劇一系列倫理風險。
1.透明化生存與隱私風險加劇
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將人類帶入一個透明化生存的時代。原本擁有“全視之眼”的上帝才能聽到、看到、想到的,超級視頻監控云、大數據系統、人工智能系統也能聽到、看到、想到。當我們生活在智能媒介無處不在、信息高度共享的普適傳播時代,就必須面對一個“細思恐疾”的現實:越來越多的我們的媒介接觸習慣(時長、時段、內容偏好等),甚至何人何時何地以何種形式向何人發送何種信息(或接收到何人何種信息)產生了何種影響,都可能隨時被感知、搜集、利用……好象我們越來越從一個被包裹著的私密環境中被一層層褪去衣裳,成為被第三者透視眼能看得一清二楚的“楚門”。隱私意識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物種的顯著特征之一,人類基于人性本能趨于展示精致利己的信息、隱藏或敏感或暴露內心真實欲望的信息。在人類進化過程中,隱私成為人與人、人與社會互動的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隨著泛感知、泛網絡、泛媒介、泛智能傳播社會的到來,人類的隱私底線正在被一步步消除。隱于環境、藏于物品、植入人體的智能媒介作為人體的無限延伸卻無法為人體所完全掌控,成為源源不斷竊取人們行動軌跡、生理指標、生活方式、媒介接觸習慣甚至內心欲望的“隱私神偷”。在知情同意機制不再奏效和大數據技術日益成熟的背景下,通過數據挖掘整合能夠實現對個體數據的多維度、全方位利用。在原始數據整合分析之前,原始數據具有無限的價值可能:數據使用者無法精確預知并征得數據主體的知情同意,數據主體也難以預測數據的潛在價值可能。如果說在互聯網時代人類尚有“離線”“斷網”的自由,或通過匿名身份和審慎的數字化行為為個人隱私留下方寸空間。那么,在即將到來的普適傳播時代,隱私觀或將被徹底顛覆:過度陶醉于新媒介技術搭建的美好圖景,人們將逐漸喪失“離線”的自由和渴望,“在線”成為一種常態和習慣,“監視”成為一種必然和無奈,擅自“離線”意味著風險、異類和寸步難行,“飛行模式”成為一種古老而美好的記憶。或許人們會逐步適應人口學、社會學層面的個人隱私暴露與信息共享,但人性底色的曝光、內心世界的裸示又會將人類置于何種境地?
2.現實虛擬化與虛擬現實化
美國媒介理論家保羅·萊文森提出:“一切媒介的進化趨勢都是復制真實世界的程度越來越高。”[4](P86)移動媒介將人們從固定的空間中解放出來,在空間的移動性上增強了復制前技術環境的精準度。普適傳播時代,人工智能、AR、VR等技術從人的感官的方方面面進一步精準復制前技術環境,推動虛擬和現實之間的融合,人們將深度沉浸于媒介之中,在現實和虛擬之間穿梭,甚至無法明確區分現實和虛擬的界限,從逼近現實的虛幻之中尋找樂趣、排遣孤獨。美國哲學家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一書中寫道:“(當月食來臨時)人們本來把頭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實的東西,但是他們卻寧愿在熒光屏上凝視它的映像”[5]。馬克·維瑟早在20多年前就提醒我們:“虛擬現實的目的是愚弄用戶,使人遠離真實的物理世界。這與計算機融入人類生活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1]在不遠的將來,人機交往或取代人際交往成為主要交往形式,傳統屏幕在向交互式的人機界面形態轉變,實體屏幕行將消失,全息投影、體感交互成為常態。“技術信息趨向替代現實,甚至淹沒現實;它們的趣味化、仿真化和透明化等使實際現實顯得乏味、粗糙和繁重;人們將對‘超現實’信息的消費、體驗和認知‘誤認為’是對實際現實的參與、體驗和認知。”[6]智能設備所構造的“虛擬世界”是一種典型的“擬態環境”,而非現實世界的完全再現。無論技術如何進化,也無法完全取代現實世界的真實感受。現階段的虛擬現實技術雖然已經可以模擬人的感官系統和經驗系統,但在心理層面人們依然清醒:一切感知和場景的背后都不過是一堆二進制代碼。虛擬現實技術的進化邏輯是從“自欺欺人”到“信以為真”,從心理層面完全消除虛擬與現實的邊界,感知系統失衡失靈以至于無法分辨何為真實何為虛擬。這對于人類來說或許是一場災難。人們為了逃避現實可以長時間沉浸于理想化世界中成為“虛擬人”,漸漸產生與現實的脫節和隔離,造成身心透支之后更為嚴重的心理錯位與精神空虛。別有用心之人借助虛擬技術可以實施精神控制甚至將人或動物囚禁于虛擬世界中成為“靈魂囚徒”……
3.媒介技術逞威與人的異化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技術時代里已經不再是人控制技術,而是技術束縛、統治和支配人的行動。在技術至上的時代,作為主體的“人”有淪為技術的“應聲蟲”的危險。隨著移動終端的普及,人類進入媒介化生存時代。媒介成為一種人們須臾不可分離的存在,“接觸媒介”成為一種習慣和儀式,其重要性甚至遠超媒介內容本身。人們時不時摸摸口袋(包包)確認手機是否安然無恙,每隔幾分鐘點亮屏幕確認是否有新的信息或提示(哪怕是一條垃圾短信或一封廣告郵件),每到一處新環境首先確認是否覆蓋網絡信號,一旦離開手機或沒有網絡就會產生焦慮、空虛感。普適傳播時代,這種對媒介的深度依賴將愈加嚴重,作為主體的個人不過是普適傳播網絡中的一個“節點”,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智能媒介系統如同顯靈的上帝一般,賦予人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建議,人類如同“媒介傀儡”般按照“系統指示”一步步滑入現代技術的深淵。正如麥克盧漢所言:“人們對自己在任何材料中的延伸會立即產生迷戀……延伸會使我們麻木……延伸意味著截除。”[7](P124)無處不在、有形或無形的媒介無限延伸和強化了我們的“六根”①,同時也“麻木”和“截除”了我們的判斷力和思維力。智能感知裝備代替了感官,AI和云計算代替了人腦,大數據代替了記憶,算法代替了判斷……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術的進步可以被看作是人類的倒退,這才是媒介技術對人類更深層意義上的危害。
4.信息繭房與算法陷阱
2006年,凱斯·桑斯坦提出“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概念。桑斯坦認為,人們在媒介內容選擇方面具有強烈的偏向性——只選擇那些愉悅自己或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最終桎梏于像蠶繭一般封閉的信息世界中。普適傳播時代將是一個高度媒介化、高度智能化的時代,媒介信息和服務被恰到好處地嵌入到場景中,隨時隨地滿足用戶的個性化、動態化需求。智能媒介服務的背后是基于大數據分析和深度學習技術的各種算法。在信息大爆炸的時代,算法猶如熟知并竭力迎合人們信息偏好的“信息大廚”,總是在第一時間為人們奉上貼心的“專屬信息大餐”,被寵壞的人們反而患上“信息營養不良癥”。算法經常披著智能化、人性化、客觀化的外衣大行其道。人們以暴露個人喜好、行蹤軌跡和內心欲望為代價,欣然接受算法精心設置的議程、智能過濾的信息、個性推薦的服務,在這種“智能化陷阱”中編制著一個又一個愈加堅固的“信息繭房”。在傳播學領域,“選擇性接觸”“選擇性記憶”“選擇性接受”等理論也揭示了選擇性心理對人們的媒介使用行為的影響。“信息繭房”形成了一個帶有濃重個人主義色彩的“擬態環境”,在這種環境中“沉默的螺旋”效應也頻頻應驗。如果我們毫無警覺地偏信、濫用算法,我們會一次次因算法而誤入歧途。魏則西曾滿懷期待地在搜索引擎中輸入“滑膜肉瘤”,卻被引入了“生物免疫療法”的不歸路。算法可以提高信息選擇效率、滿足個性需求、提升媒介體驗,卻未必能完全讀懂人性。數學家Cathy O'Neil在《數學殺傷性武器》一書中提醒我們:“機器和算法的表現,最終體現的其實是制造機器、設計算法的人的意志。如果設計算法的人不考慮人性的因素,那么機器是不會自動考慮人性的。”[8](P136)算法在本質上是一種精心的人為設計,在高度智能的普適計算時代,盡信算法不如無算法,我們應當先當“評判員”再當“消費者”,時刻保持對現實世界的洞察和判斷。
5.泛媒介隔離與人類情感疏離
麥克盧漢1964年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書中預言:電子媒介的出現壓縮了時空距離,分散于不同地域、文化、階層的人們重新連接到一起,人類社會將“重返部落化”并形成“地球村”。40年后,萬維網的誕生讓“地球村”的預言成真。然而,人類的“重返部落化”也導致了人與媒介關系的異化。隨著VR、AR、全息投影等新一代信息交互技術的發展,人與媒介之間關系的異化愈演愈烈。口語傳播時期,語言、空間和地域的限制使得人們生活在相對集中的部落中,“現場式”口語交流讓彼此之間的關系親密。隨著報紙、書刊、電波、網絡、智能終端等媒介的出現和普及,人類交往的媒介化程度越來越深。在泛媒介、泛網絡、泛感知的普適傳播時代,“人—物”“物—物”傳播普及將進一步拓展人類交流形態和維度,提升溝通效率和頻次,其負效應是大大降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直面溝通的必要。美國心理學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在《群體性孤獨》一書中寫道:“各種數碼設備為我們制造一種假象——我們被陪伴著,哪怕沒有友誼,沒有愛情,那些設備仍然愿意滿足我們的需求。它們成為我們的‘親密朋友’甚至是‘精神伴侶’”[9](P28)。新媒介設備對人的陪伴只是一種假象。普適傳播模糊了人與媒介、媒介與非媒介的界限,一切有形的、無形的媒介最大限度地將人與社會、自然和自我隔離開來。“虛擬交流”“人機交互”越來越取代“自然交互”,交流越來越媒介化——增加了泛媒介的“隔離”,從面對面的“強聯系”變成了空對空的“弱聯系”,“情感溫度”直逼冰點。媒介本來是改善和強化溝通的工具,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泛媒介”卻越來越像一堵堵無形的限制情感交流、阻礙深度溝通的“隔離墻”。人們趨向于與不斷迭代進化的智能媒介交流,對現實世界中的人際往來愈發排斥,一切必要的、非必要的現實交往似乎都可以被虛擬交互所替代,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越來越遠、情感溫度不斷降低。全息投影可以實現“面對面”的無礙交流,甚至模擬現實人際交流的觸感、味感,但一千次的“虛擬擁抱”也難抵現實中的一個不經意間的眼神交流。人與自然越來越疏離,人與非人物種間的自然對話輕易地被虛擬現實替代,人們在“遠離自然勝似自然”的超現實幻境中沉醉不已。人與自我也越來越陌生,空間和技術的智能化讓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時空的間隙被數字、信息和娛樂填滿,靈魂距離身體越來越遠。
6.泛娛樂化傾向與人類意義崩塌
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家道格拉斯·凱爾納指出:“媒體信息和符號制造術四處撒播,滲透到了社會領域,意義在中性化了的信息、娛樂、廣告以及政治流中變得平淡無奇。”[10]從電子傳播至網絡傳播、移動傳播、普適傳播,媒介內容的視頻化、碎片化、快餐化、庸俗化傾向不斷滋長蔓延,造就了大批“知道分子”和“享樂分子”。紛繁復雜的媒介以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強行占用了人們的閑暇,奪走了人們從事其他原味活動的時間,即時、膚淺、庸俗、虛幻的快餐信息和感官體驗大行其道,唯美畫面、凄美劇情、宏偉游戲編制的虛擬世界讓人如癡如醉。后現代主義倡導的消費文化語境下,碎片化信息的“連番轟炸”和感官化娛樂的“持續麻醉”讓現代人成為馬爾庫塞筆下的“單向度的人”,人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追求嚴肅和沉重的東西,紙版閱讀、靜心思考和理性批判成為奢侈。娛樂原本是一種短暫的身心調適,在媒介化生活方式點燃的全民狂歡中,娛樂好比是合法且被濫用的“電子海洛因”和“生活麻醉劑”,成為“幸福”的代名詞和生活的終極訴求,享有娛樂設備、資源的多少仿佛與個人幸福感、滿足感成正比。娛樂過后,“人們沒有感受到輕松閑適,而是身心俱疲;沒有體驗到愉悅幸福,而是更加心態失衡”[11]。當信息、物質和娛樂變得輕而易舉時,我們也正在從物質的廢墟滑入價值意義的廢墟中,那將是不同于戰爭時代或物質匱乏時代的全新痛苦。
此外,普適傳播還將進一步加劇信息大爆炸與認知迷茫、信息鴻溝拉大與社會分化、社會風險的媒介化與信息自由失控等風險。普適傳播時代,基于泛感知、泛網絡、泛媒介的海量信息無限匯聚導致人類信息大爆炸,人類長久以來的“信息匱乏癥”被徹底治愈,卻又患上了“信息超載癥”和“信息選擇焦慮癥”。信息大爆炸時代,缺的不是信息,而是有價值的信息以及尋找有價值信息的能力和對海量信息的批判、分析、整合能力。海量冗余、虛假、暴力、色情信息的存在稀釋了信息的價值度,消解了信息的權威性,人們習慣性地接受信息,無可救藥地依賴信息,最終淹沒在低質信息的海洋里。另一方面,普適傳播時代的信息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源、財富和權力,成為重新劃分社會等級的重要力量,優質信息、前沿信息、深度信息通過市場化流動導致信息資源的重新分配,進而拉大不同地域、階層、群體間的信息落差。不同群體間的智能媒介設備接入能力、使用能力的差異將引發更為嚴峻的信息鴻溝:一邊是優先享受技術紅利的高階群體,一邊是被排除在這場技術盛宴外的弱勢群體。或許人們一開始不會介意VR新聞、全息影像與電視直播的差別,但技術進步最終可能將信息弱勢群體遠遠拋在技術發展曲線的尾端,這種差別就像是“烽火預警”與“衛星監控”的區別。此外,普適傳播打通了“人—機—物”之間的傳播通道,消除了固有的線性層級傳播結構,消解了大眾媒介和意見領袖的權威和權力,人與智能設備、物品被賦予相對平等的傳播權力,信息流通呈現出非線性的泛化形態,同時也將極大增加信息傳播管控難度并可能加劇現有的社會風險。作為“第四權力”的媒介在普適傳播時代將成為更強大的社會力量,在新的傳播管控機制成熟之前,這股游走在理性軌道邊緣的洪荒之力一旦脫軌將引發難以預知的社會風險和災難。正如甘姆森(Gamson)所言:“媒介參與了風險的建構或形塑,媒介自身也是各種界定風險的權力力量的角斗場”[12]。
三、結 語
普適傳播是一場全新的傳播革命,雖然目前尚處于萌芽階段,但其顛覆媒介生態、重構傳播倫理的步伐已然勢不可擋。所謂物壯則老、日極則仄,媒介傳播科技的跨越式進化很容易突破合理與適度的區間,成為限制人類思維、想象、批判與自由的幫兇。法國哲學家福柯說:“我們都是自我的俘虜,生活在自己創造的監獄里。”[13]普適傳播時代的媒介化生活空間猶如一座美輪美奐、功能齊備的“監獄”,我們自困其中卻又理所當然地享受著這座豪華“監獄”帶來的便利和快感。在高度媒介化社會中,人人都是“楚門”,但又有多少人會像“楚門”一樣義無反顧逃離媒介幻影、不惜代價重返未知的自由王國?面對普適傳播的迅猛發展,我們要以審慎的態度和前瞻的視角合理預見其發展趨勢及道德后果。面對普適傳播技術的誘惑,我們要站在批判與反思的角度,對新媒介技術進行“祛魅化”表達,抵制媒介技術對人的異化和生產生活的全面入侵,避免成為被媒介主宰和奴役的“傀儡”。媒介始終是為人服務的,唯有以高度的自決性、自主性和自控性駕馭媒介、超越媒介,堅守人類在媒介高度發達時代的主體地位,才能最終迎來給人以無限美好想象的普適傳播時代。
[注 釋]
①六根,佛教用語。指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個感官器官。
[1]Mark Weiser.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J].Scientific American,1991(3).
[2]朱光烈.人的終結與傳播學的終結[J].現代傳播,2004(3).
[3]李沁.泛在時代的“傳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J].國際新聞界,2015(5).
[4]保羅·萊文森.萊文森精粹[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單波,王冰.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論想象[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0(2).
[6]李波,李倫.技術信息超現實問題的倫理反思——基于伯格曼的技術哲學和信息哲學[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7(2).
[7]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8]Cathy O'Neil.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M].Crown,2016.
[9]Sherry Turkle.Alone Together[M].Basic Books,2012.
[10]葛自發.新媒體對“積極受眾”的建構與解構[J].當代傳播,2014(1).
[11]李琦.眾聲喧嘩與眾生失語——當下媒介文化的人文反思[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5).
[12]洪長暉.混合現代性:媒介化社會的傳播圖景[D].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13.
[13]顧琴.從《楚門的世界》看現代媒介化生存[J].新聞窗,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