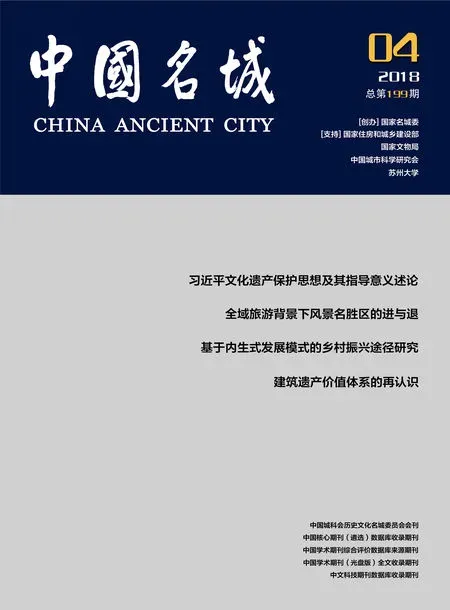逆城市化:一個概念辨析*
沈東
自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布萊恩·貝利(Brian J. L Berry)教授提出“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以來,這一概念風靡全球,成為經濟學、地理學、人口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等專業學者爭相追捧的學術議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①中國學者圍繞“逆城市化”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度論述與持續交流,取得了一定的共識。[1]然而,中國學界關于“逆城市化”的研究,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爭議,具體表現為:逆城市化是真還是偽?是同質還是多樣?是阻礙還是促進?[2]本文認為,之所以會產生這些爭議,從根本上看,取決于我們如果定義“逆城市化”,即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從實際看,“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衍生出的一個概念,同時,與“反城市化”和“郊區化”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成為表征城鄉人口遷移的重要學術概念。只有對這些概念進行準確的把握和界定,才能進行分析與對話,避免不必要的誤解與爭議。②本文試圖辨析“逆城市化”與“城市化”的關系,廓清與“反城市化”和“郊區化”的區別,在此基礎之上,促進逆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的本土重構。
1 城市化進程中“逆城市化”
最早論及“城市化”(Urbanization)這一概念的,是經典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他在1858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寫道:“現代的歷史是鄉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3]。此后,這一概念風靡全球,為各國學者所接受。自這一概念誕生以來,“城市化”便成為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問題,不僅有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的介入,同時還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法學等社會學科的深入研究,不僅有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先行研究,同時還有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的及時跟進。可以說,城市化當之無愧的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學術議題。與之對應,20世紀70年代以來,逆城市化成為一個廣泛使用的概念,同時也是一個被混亂使用的概念。不同國家的學者,針對不同的實踐,會賦予“逆城市化”不同的內涵。基于不同的學科視角,不同專業學者會對“逆城市化”作出富有所在學科特色的解讀。
第一,國外學者的定義。布萊恩·貝利(Brian J. L Berry)教授最早對逆城市化作出概念解釋,他通過數據統計分析發現,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都市區人口增長率不及非大都市區,城市人口向郊區以及農村回流,并將這一現象稱之為“逆城市化”[4]。恰在此時,西方各主要國家均發生過由于環境污染、交通擁擠以及治安混亂等城市問題,大城市發展出現了遲滯,[5]城市人口外流的現象。也就是說,實踐層面的“城市問題”為“逆城市化”在西方學界的流行創造了外部條件。有學者注意到了西方學界對“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缺乏一致性,提出從不同的維度去分析這一人口的空間再分布的過程。[6]有學者對逆城市化這一概念在學術研究中的歷史演變進行了考察,認為其本質是“人口向農村地區遷移的過程”[7]。一方面,由于問題意識和學科背景的差異,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對“逆城市化”進行解讀;另一方面,各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存在差距,因而其逆城市化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對“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仍然存在多樣化的趨勢。不同國家、不同專業、不同時期的學者,基于不同的問題意識、不同的研究進路、不同的資料選擇,都會產生不同的“逆城市化”認識取向。
統觀西方學界的逆城市化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研究人員以人口學、地理學以及經濟學等3個學科為主,其研究成果大多通過量化分析,對逆城市化的人口遷移、人口分布等狀況作出事實描述。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不同國家、不同專業、不同時段的西方學者,對“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存在諸多差異,但是一個共同的特征卻是立足于西方高度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病”觸發的“城市人口外流”這一社會事實,遵循的是“從實踐到理論”的研究進路。而且,在西方語境下,“城市人口”主要指的是“富人階層與中產階級”,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觸發的產業布局、公共服務以及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獨立于中心城區的衛星城或新城。然而,這一理論傳導到國內,受制于西方逆城市化理論的“先發優勢”和“認知局限”,國內學者對“逆城市化”的問題意識、分析視角、概念界定以及理論觀點存在一定程度的爭議,并影響到了中國逆城市化研究的持續深入。
第二,國內學者的定義。國內學者關于逆城市化的研究,起源于對西方逆城市化現象的介紹。有學者認為:逆城市化就是“大城市明顯萎縮,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區乃至更外圍的鄉村地區遷移.......導致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的絕對下降”[8]。有學者則對“逆城市化”這一概念的實踐基礎進行了質疑,認為“逆城市化的立論依據有待推敲”、“郊區化不能等同于逆城市化”[9]。有學者認為,逆城市化并非反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的進一步延伸,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逆向擴張,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與自然的關系。[10]有學者認為,“逆城市化的實質是城市有機體的進一步膨脹,是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擴散,而不是城市化的反向運動”[11]。還有學者對逆城市化作了頗具本土意味的定義,主要表現為“人口頻繁的由城市向農村遷移”[12]。有學者認為,逆城市化是郊區化的升級版,是城市化進程的必然產物。[13]有學者認為,逆城市化的本質就是城鄉一體化,一般是指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美等發達國家城市人口向農村或小城鎮遷移的反向人口流動現象。[14]有學者認為,“逆城市化是城市向農村滲透的方式,既作為城市化的階段而存在,亦是推進城市化的積極因素”[15]。
與國外學者相比,國內學者關于逆城市化的定義就要復雜的多。這不僅因為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表現出復雜的實踐形式,更加是由于對國內學者而言,“逆城市化”這一學術概念是“舶來品”,在研究過程中需要處理與西方逆城市化的關系,即在何種語境下來理解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現象?可以發現,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學者對西方逆城市化研究的介紹,還是世紀之交學者們對逆城市化的質疑、否定,亦或是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開始對逆城市化進行的肯定性研究,“逆城市化”這一學術概念,在中國的傳播語境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斷裂”[16]。國內學者對“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蘊含著強烈的西方情感底色,大多以西方的逆城市化現象為參照。只不過,有學者側重于在介紹西方逆城市化現象的同時,來界定這一概念;有學者以西方逆城市化現象為標桿,對這一概念的本土實踐進行質疑、批判;還有學者受西方逆城市化研究的啟發,嘗試對當代中國的各類逆城市化現象展開研究。
由上可知,在全球化語境中,“逆城市化”缺乏一個明確而統一的概念。不同國家、不同專業、不同時期的學者,針對不同的問題,賦予“逆城市化”不同的內涵,對“逆城市化”進行不同層面的解讀。這種狀況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逆城市化實踐的多樣性決定的,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不同的學者基于不同的專業視角而進行的不同層面的解讀。也就是說,多樣的逆城市化概念,取決于多樣的逆城市化實踐。正是由于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發生了不同類型的逆城市化實踐,不同專業的學者,基于不同的分析視角,才會對“城市人口外流”這一社會事實,進行不同維度的逆城市化概念界定。因此,國內外關于“逆城市化”的學術概念,才會呈現出一種復雜、多樣而又混亂的圖景。只不過,美國學者出于強烈的“問題意識”,率先提出了“逆城市化”這一概念,用以對經驗事實作出學理分析。后來的學者在此基礎上,或肯定、或否定、或修正的延續了“逆城市化”這一知識脈絡。
從現有的知識存量來看,盡管國內外學者對“逆城市化”缺乏明確統一的認識。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不同國家、不同專業的學術概念中找尋出“逆城市化”的共同特質。具體來說:學者們大多將逆城市化看成是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一個帶有“悖論”色彩的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的現象,而且,這種人口逆城市化實踐大多發生于“高度城市化”背景之下,由“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犯罪增加”等“城市病”觸發的“富人階層與中產階級”向郊區以及農村的遷移,緊隨其后發生了“產業布局、公共服務以及基礎設施”的完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帶動了城市人口的逆城市化遷移。現有的關于“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大多指稱這一“完整而確定”的社會事實,而相關的學術爭議,也大多聚焦于這一事實有沒有完整而明確的存在。只不過,在紛繁復雜的爭議當中,存在一個確定性的學術共識,即城市化進程中的“逆城市化”。
2 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
在中國語境中,“反”與“正”是相對而言的。如果說,城市化是對“人口向城市集聚”這一人口流動現象作“正面”解讀的話。那么,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③則是從“反面”對這一現象作出了否定性解答,即對“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對“城市化”這一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提出反對看法,進而從對立面的角度對城市化進行批判、質疑。④反城市化是一個與城市化相對立的概念,從根本上表征著“反對”城市化,反映了“城市農村化、工業農業化以及市民農民化”⑤,蘊藏著強烈的價值判斷與情感預設。⑥
城市化是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以至于城市化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實踐真理,進而上升成為一種價值理想。反城市化指向的是一種對“城市化”的反叛與背離,不僅從觀念上對各種城市化理論進行批判和否定,而且在實踐層面對城市化進行抵制和反抗,試圖通過反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表達,扭轉城市化的基本趨勢,阻礙城市化的歷史發展進程。[17]如果說,與城市化相伴隨發生的是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化以及農民市民化,那么,反城市化則是一種工業農業化、城市農村化以及市民農民化的反向演變過程。反城市化與城市化相對立而存在,凡是城市化所要表達和堅持的,便是反城市化所要批判與否定的。反城市化就是以“城市化”為批判目標而存在,通過對城市化的否定來論證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反城市化蘊藏著強烈的價值判斷。
從亞非拉到歐美日,盡管城市化的實踐進路存在諸多差異,但是,城市化的共同特征均表現為人口向城市集聚的過程。這一特征存在于事實層面,并成為各個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戰略選擇。反城市化只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而存在,⑦更多的表現為一種非主流的社會文化思潮。⑧在事實層面,反城市化缺乏實踐基礎;在理論層面,反城市化缺乏立論依據。也就是說,“在城市化席卷而來的同時,也激起了與之相抗衡的反城市化運動”[18],反城市化更多的表現為對城市化的不滿。如果說,城市化表征的是人口向城市集聚的過程,那么,反城市化則試圖在實踐層面改變這一趨勢。只不過,與城市化相比,反城市化不僅缺乏理論基礎,而且在事實層面也難以成為一種指導實踐的社會理論。進一步講,反城市化難以在實踐層面對城市化構成威脅,更加不可能在理論層面消解城市化的基本取向。因而,更多的只能作為一種反對城市化的社會文化思潮而存在。
在實踐層面,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但是,城市化并非是一劑萬能的解藥,特定時空范圍內,也會產生各種“城市化后遺癥”。這些后遺癥的存在,正好成為反城市化的突破口。在理論層面,城市化也并非是一個可以解釋所有社會實踐的理論成果,而是存在各種理論解釋的盲點,在指導實踐過程中,更是會產生各種偏差。這種城市化理論和實踐的脫節,更是為反城市化思潮提供了空間。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城市化占據絕對主導地位,而反城市化卻如影隨形,始終作為一種反對的聲音而存在。可以說,不同的城市化實踐,產生不同的反城市化社會文化思潮;不同的城市化發展階段,反城市化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呈現;正是在反城市化的質疑批判聲中,世界各國的城市化不斷得以提升。也就是說,反城市化產生于城市化,與城市化相伴隨而存在,在彼此對立中共生發展。
由此可知,反城市化以批判、質疑城市化為己任,在實踐中試圖扭轉城市化的基本趨勢,在理論上消解城市化的價值取向,從根本上否定城市化理論與實踐。進一步說,反城市化作為城市化的對立面而存在,其基本觀點和實踐進路存在諸多差別,但是,二者存在相同的社會發展訴求。城市化試圖通過“人口向城市集聚”來實現人類美好的生活訴求,而反城市化則抓住了城市化后遺癥,以此來攻擊、否定城市化的基本趨勢,試圖為社會發展提供另外的出路。[19]只不過,反城市化在“反對”城市化的同時,卻提供不了有效的社會發展“藥方”,其“反”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情感”上,無法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對城市化構成威脅,更加無法構建具有科學形態的反城市化理論成果,也無法引導出反城市化實踐。與城市化理論與實踐相比,反城市化只能作為一種價值判斷而處于從屬位置。
逆城市化與反城市化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別在于,與逆城市化相比,反城市化并非是一個事實判斷,更多的展現為一種“反對”城市化的社會文化思潮,廣泛的存在并發生于全球各個國家的城市化實踐當中;而逆城市化卻是作為一個社會事實而存在,更多的展現為對“城市人口外流”這一人口遷移現象進行事實判斷,獨立自主客觀的發生于主流的城市化進程之中。聯系在于,二者均與城市化實踐發生聯系,一定程度上均受制于不同的城市化實踐。也就是說,逆城市化是城市化“溢出效應”的結果,是個體對城市化不滿之后而進行“從城市向農村遷移”的社會實踐;反城市化也是城市化作用的結果,只不過更多的表現在個體情感和社會思潮層面。在實踐中,個體可以采取“從城市向農村遷移”的“逆向遷移”,卻無法發生“反城市化”的社會實踐,而只能作出“反城市化”的情感態度表達。
城市化進程中,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⑨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二者存在本質性的區分。一方面,如果我們將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人口外流”當成“反城市化”,便可能否定逆城市化的實踐基礎,混淆逆城市化與反城市化的區別與聯系,進而削弱對經驗事實進行理論提升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反城市化”與逆城市化劃等號,則會遮蔽對逆城市化實踐多樣性觀察與思考,而且,也無法對逆城市化與城市化的關系作出準確有效的解釋判斷。更為重要的是,在政策操作層面,逆城市化與反城市化存在極為關鍵的區分。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反城市化更多的只是表現為一種情感態度,而無需過多的政策介入與操作。然而,逆城市化實踐的發生,卻與相關的土地、戶籍以及財稅等政策制定存在極為密切的關聯。一旦政策處理不慎,便可能在實踐層面誘發利益沖突與關系緊張,進而影響宏觀的城市化進程。鑒于此,必須在理論、實踐以及政策等3個層面明確界定:逆城市化不是“反城市化”。
3 逆城市化與“郊區化”的區別
在中國,“郊區”并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只是作為“中心城區”的對立面而存在,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人口、產業以及其他各項城市功能“從城市中心向郊區擴散的過程”[20]。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原先的郊區會被卷入城市化建設,演變成為中心城區,而原來不屬于“郊區”的偏遠農村,則可能受到城市化的作用力,演變成為“郊區”。一般認為,“郊區化”(Suburbanization)是指人口從中心城區向郊區的遷移過程。[21]郊區化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的郊區化是指中心城區的人口、產業以及職能向郊區轉移的過程。狹義的郊區化則特指由于中心城區的停滯或衰退,引發的人口、產業以及職能外遷的過程。[22]由于郊區的變動性,在中國,各級政府的數據統計口徑中,并不存在相應的“郊區人口”“郊區面積”等專欄。⑩在制度設計上,“郊區”并不是獨立于城鄉社會而存在的“第三空間”,始終處于一種動態發展過程之中。
郊區既可以是距離城市較近的“農村”,也可以是城市邊緣的“鎮、街道”等行政轄區單位,更加可以是城鄉結合部的轉型社區。在中國語境下,郊區往往成為連接城鄉空間的地域代名詞。“郊區化”首先指的是一個人口遷移的事實判斷:即人口從中心城區遷往郊區的過程。[11]也就是說,郊區化首先是作為一種社會事實而存在,是對“人口從中心城區遷往郊區”這一社會實踐的事實描述。這種事實描述,無關乎價值判斷,更沒有牽涉到價值介入,是一種對社會事實的概念化表達。或者說,在城市化作為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雙重呈現背景下,郊區化并沒有上升成為一種價值理念而對城市化構成威脅,更多的情況下只是作為一種“事實”存在于城市化語境之中,既服從于價值理念層面城市化的整體目標定位,也內嵌于“人口往城市集聚”的城市化事實判斷。
郊區化并非是城市化的對立與反叛,而是城市化的產物。在一定時期內,城市社會固有的人口、就業、環境等資源承載量是有限的。一旦城市社會的資源承載量達到極限,便會發生各種形式的“溢出”效應,即所謂的“郊區化”。一方面,城市政府會根據既有的城市發展規劃,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布局規劃,從而帶動了人口的郊區化;另一方面,城市經濟發展也會進行周期性的調整,這種調整也在無形中促進了城市人口、產業以及職能的郊區化。郊區化既是城市化發展的客觀結果,同時還會反過來促進城市化水平和質量的提升。對于中心城區而言,郊區化不僅成為解決問題的重要渠道,同時還會為中心城區的城市化提供進一步的發展空間,以至于在實踐中,郊區往往成為中心城區進行人口調控、產業轉移和資源利用的重要載體。
與郊區化相伴隨的,不僅是人口、產業以及功能向郊區轉移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城市化的擴散過程。[12]因為,作為城市郊區,相關的人口規模、產業結構以及空間布局介于城市和農村之間,本身兼具城市和農村雙重特性。而郊區化的發生,恰恰打破了這種城鄉的雙重特性,使郊區開始步入城市化的軌道,在人口規模、產業結構以及空間布局等方面,越來越強調城市的一面。不僅大量中心城區的人口開始遷移到郊區,與之匹配的產業集群、公共服務也開始向郊區傾斜。而且,原先郊區鄉土性的一面也開始逐漸退去,城市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方式開始導入郊區,為郊區社會所接受。可以說,以人口、產業以及功能向郊區遷移為表現形式的郊區化,本質是一個城市化的擴散過程。
綜上所述,郊區化作為城市化的特定階段而存在,[13]是城市化“溢出”效應的產物,并且呈現出“交錯式發展”[23]的態勢。從價值判斷層面看,郊區化服從于城市化的整體戰略定位,以不妨礙城市化的推進為前提;從事實判斷層面看,郊區化是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從中心城區向郊區流動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從價值判斷到事實描述,郊區化與城市化的總體方向相一致,所指向的,都是為了更好的推進城市化。在城市化的整體定位下,人口從中心城區遷移到郊區,并非是對城市化的背離,而是在“城市性”不足的情況下,通過郊區化的遷移,來實現城市化的擴散,促進郊區城市化,進而充實城市性。郊區化反而成為城市化的手段和載體,通過郊區化,城市化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城市化制度安排日漸擴張,城市化建設一步步推進,郊區化成為城市化的重要動力。
從概念上看,逆城市化與“郊區化”存在顯著的區別。“郊區化”暗含著“中心城區——郊區”這種二元對立的劃分方式,而逆城市化則暗含著“城市——農村”這樣的地域界定。“郊區化”中的“中心城區——郊區”,時刻處于時空變動之中,在城市化的作用下,原先的“郊區”會演變成為“中心城區”,“中心城區”的地域范圍也逐步擴展,“郊區”的地域空間也在不斷的外擴,“郊區”更多的是隨著“中心城區”的變動而變動。“逆城市化”中的“城市——農村”,存在明確的界定。在中國,但凡土地是國家所有,在制度上則被稱之為“城市”,而只要土地屬于“集體所有”,在制度上則被定義為“農村”。也就是說,“城市”和“農村”存在著明確的分野,“逆城市化”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得到明確而清晰的界定。逆城市化與郊區化均作為社會事實而存在,只不過,二者表征不同的社會事實,牽涉到不同分析視角,折射出不同的城市化實踐。
進一步說,逆城市化與郊區化均存在相應的實踐基礎。只不過,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基于不同的制度設計、政策實施、資源分配以及內外環境,或發生郊區化、或發生逆城市化。二者孰先孰后、孰強孰弱,沒有統一標準,更加不存在一致的時間順序。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實踐來看,郊區化先于逆城市化而發生,以至于國內學者總結西方城市化實踐規律的時候,會線性得出“中心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規律認知,并進一步將其上升到中國乃至全球城市化的一般規律。其實,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應當立足于特定時空、特定對象的城市化實踐。從全球范圍內看,與西方國家的城市化實踐相比,中國城市化在發生時間、制度設計、政策實施、資源分配、內外環境以及發展階段上,表現出較大的特殊性。正是中國城市化實踐的特殊性,決定了郊區化與逆城市化的復雜性與多樣性 ,也因此而決定了不存在一個普世的、一般性的城市化規律。
4 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面向實踐的維度
本文對“逆城市化”這一概念的界定,不局限于國外學者的概念界定,也并非聚焦于國內學者的抽象爭議,而是從本土復雜性、多樣性的社會實踐出發,聚焦于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這一“社會事實”。也就是說,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需要面向實踐。無論國內外學界關于“城市化”的概念界定有多少爭議,但是,一個共同的本質性特征就是:人口不斷向城市聚集的過程。同理,無論國內外學界關于“逆城市化”的爭議有多大,也不論學者們在何種語境下去討論“逆城市化”。從現有的文獻來看,“逆城市化”的本質特征,指稱的是一個城市人口“逆向”遷移過程,是“城市化達到一定高度后的揚棄”[24],在不同國家的實踐中,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此,可以發現,逆城市化的概念界定,便存在一個共同的內涵: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只不過,在中國語境下,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這一內涵界定,存在不同的外延:即逆城市化的多樣實踐形式。
需要強調的是,由于中國城市化實踐的特殊性,本文對“逆城市化”的外延界定,并非是一般意義上城鄉人口的空間位移,同時還涉及戶籍制度層面的城鄉人口遷移。因為,1949年以后,中國的城市化實踐,受到戶籍制度的強烈形塑,離開戶籍制度,無法準確有效的理解中國城市化實踐。而且,中國城市化實踐,也十分清晰明確的體現在戶籍制度層面。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本文借鑒政府人口統計時所采用的標準: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因為,國家統計局在發布城市化率時,存在兩個不同的統計口徑,一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二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這兩個城市化率從不同層面反映了當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并且逐漸成為政府、學界以及社會大眾分析當代中國城市化水平和質量的重要指標。因此,“逆城市化”的外延展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常住人口層面的逆城市化,二是戶籍人口層面的逆城市化。二者均表征當代中國人口“從城市向農村的遷移”的逆城市化實踐。
其一,常住人口層面的農民工“離城返鄉”。[14]從全球各個國家的城市化實踐來看,在制度設計、政策實施、資源分配以及發展階段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是,在差異化的實踐背后,一個共同的基本事實就是:人口不斷的向城市集聚。中國的城市化概莫能免。1949年以后,中國常住人口呈現出的一個主流的遷移趨勢就是: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實現非農就業,進行戶籍身份轉換,進而實現“市民化”的角色轉型。然而,在這一主流的人口遷移趨勢下,21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以后,中國社會發生了大規模的農民工“離城返鄉”。一方面,從國家的統計口徑來看,農民工屬于“城市人口”范疇,其返鄉行為的發生,無形中影響到了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另一方面,農民工的“離城返鄉”,與主流的城市化趨勢背道而馳,是城市化的理論與實踐始料未及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的“離城返鄉”,直觀上呈現出人口“從城市向農村的遷移”這一社會事實,從更深層次則折射出城市化的“逆向”人口遷移。基于這兩個層面的考慮,本文將農民工“離城返鄉”視為逆城市化的本土實踐形式。[25]
其二,戶籍人口層面的“非轉農”。眾所周知,當代中國的城鄉關系受到了戶籍制度的強烈形塑,與主流城市化相匹配的,是一個“農業戶口”向“非農業戶口”轉換,即“農轉非”的過程。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不同程度的出現了戶籍人口“非轉農”利益訴求,并在隨后的實踐中,得到了政策確認。如果我們將戶籍人口的“農轉非”定義為城市化,那么,戶籍人口的“非轉農”也同樣可以成為逆城市化的本土實踐形式。[26]因為,戶籍是當代中國城鄉資源分配的重要標識,[15]是當代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制度支持,是當代中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的重要憑據。自1958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來,雖然戶籍制度幾經改革,但從整體上看,戶籍制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動。而且,每一階段的戶籍制度改革,均是為了配合宏觀的城市化戰略,以不妨礙城市化的整體推進為底線。在這種情況下,“非轉農”的訴求與實踐,與主流的戶籍人口城市化相比,就顯得格格不入,進而成為戶籍人口逆城市化的重要實踐形式。[27]
任何學術概念,都是針對特定實踐、特定事實所闡發的,是理論思維對經驗事實的抽象表達。學者們對“逆城市化”這一學術概念的爭議與誤解,首先源自于經驗事實層面逆城市化的復雜性與多樣性。這表現為:不同國家發生了不同類型的逆城市化實踐,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發生不同類型的逆城市化實踐,不同專業學者基于不同視角對逆城市化展開了不同維度的分析。逆城市化實踐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決定了逆城市化概念界定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不同國家之所以會發生復雜多樣的逆城市化實踐,取決于不同的城市化實踐。從全球范圍內看,基于歷史傳統、現實目標、制度設計以及發展階段的特殊性,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均會選擇不同的城市化實踐方式。1949年以后,中國的城市化實踐表現出較大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發生時間、制度設計、政策實施、資源分配以及內外環境等方面,這種城市化實踐的特殊性,決定了當代中國逆城市化實踐的復雜性與多樣性。
5 結語
全球化背景下,“逆城市化”作為一個知識脈絡而存在。本文對“逆城市化”的概念辨析,并非為了“證實”或“證偽”這一學術概念在本土語境中的有效性和解釋性,其最終目標在于實現逆城市化本土實踐基礎上的理論重構,進而實現逆城市化中西理論的對話與交流,重新認識1949年以后中國的城市化實踐。而且,構建中國本土的城市化理論,并不拒斥任何西方的、外來的知識體系。與先行的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實踐相比,1949年以后的中國城市化實踐,既表現出人口、土地、要素、資本、空間等城市化集聚的普遍性,又呈現出時間、歷史、制度、政策、環境等城市化實踐的特殊性。中西城市化實踐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并存,為中西逆城市化理論的交流與對話提供了可能性與可行性。面向實踐的維度,對“逆城市化”進行本土概念界定,一方面有助于對照西方知識脈絡“接著講”,另一方面則有利于進一步以“中國實踐”為根基,構建本土性的“中國逆城市化理論”,激活中國城市化理論的想象力。
注釋:
①在國內學界中,最早對“逆城市化”展開研究的,當屬華東師范大學張善余教授。參見:張善余:《逆城市化——最發達國家人口地理中的新趨向》,《人口與經濟》,1987年第2期,第57-62頁。
②相當多的誤解和爭議,都是由于概念界定不清造成的。比如,將“逆城市化”理解成為“反城市化”,進而否定“逆城市化”的實踐基礎與理論成果;將“逆城市化”與“郊區化”混為一談,進而認為“逆城市化”的本質就是“郊區化”。本文認為,每一個學術概念的背后,都表征的一種“社會事實”,折射出一種分析問題的視角。
③相當多的學者對“逆城市化”和“反城市化”并未作出嚴格區分,而是在同一個層面上交替使用,這在無形中造成了不必要的誤解。
④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的快速城市化會造成“精神慰藉的離別、人文關懷的缺失、個體挫折感和失落感”,由此而引發“反城市化”傾向。參見:姜建成:《價值訴求、目標與善治:當代中國城市化發展中人文關懷問題探析》,《哲學研究》,2004年第11期,第79-83頁。
⑤反城市化深深植根于農業社會與鄉土文明的土壤之中,與主流的城市化潮流是背道而馳的。參見:涂文學、高路:《罪惡的淵藪,還是文明的階梯?——1900—1930年代中國的“反城市化”思潮論析》,《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第141-144頁。
⑥與“反城市化”相關的,還有“反城市主義”這一提法,指的是對城市與城市化的反對與批評。參見:潘允康:《城市化與“反城市主義”》,《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110-114頁。
⑦與反城市化相伴隨的,還有反工業化、反中心化以及城市衰落等現象。參見:黃志宏:《現代西方國家反城市化過程的幾點思考》,《經濟地理》,1998年第4期,第19-21頁。
⑧有學者對中國的“反城市化”思潮進行了追溯,認為在20世紀初在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就持有“反城市化”觀點。參見:涂文學、高路:《罪惡的淵藪,還是文明的階梯?——1900—1930年代中國的“反城市化”思潮論析》,《天津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第141-144頁。
⑨有學者認為,與西方逆城市化相比,中國的逆城市化不具有典型性,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逆城市化本土實踐的確定性。李培林:《逆城鎮化大潮來了嗎?》,《人民論壇》,2017年第3期,第60-61頁。
⑩無論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還是地方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均不存在“郊區人口”“郊區面積”等專欄,而只有“城市人口”“城市面積”“農村人口”“農村面積”等欄目。
[11]美國主流學界觀點認為,郊區化就是白人中產階級遷往郊區的歷史。然而,近來有學者研究發現,在西方國家大城市人口郊區化過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人郊區化”。參見:王旭、王宇翔:《被遺忘的工人郊區化——以洛杉磯大都市區為例(1920—1940)》,《安徽史學》,2016年第2期,第107-116頁。
[12]有學者認為,過去過于重視“集中型城市化”研究,進入21世紀以來,學界開始關注“分散型城市化”研究,“郊區化”則是“分散型城市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參見:馮健、周一星:《杭州市人口的空間變動與郊區化研究》,《城市規劃》,2002年第1期,第58-65頁。
[13]郊區化起源于現代美國,但是,卻并非是美國現代城市化進程中的獨有現象,對郊區化歷史的追溯,可以發現,早在19世紀初期,美國工業化剛展開,郊區化進程即已啟動;19世紀后期,郊區化進程加快;20世紀20年代,美國現代城市郊區化的開端;到1970年代,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初步郊區化國家;到2000年,郊區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50%,美國成為真正的郊區化國家。參見:孫群郎:《美國郊區化進程中的黑人種族隔離》,《歷史研究》,2012年第6期,第97-112頁;孫群郎:《美國城市郊區化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14]有一種觀點認為:農民工尚沒有完全實現城市化,因此也就不存在“逆城市化”之說。本文認為,需要區分“城市化”和“市民化”這兩個概念。城市化指稱的是農民工在城鄉之間的空間位移,反映在政府的城市化率的統計上;而“市民化”則表征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即進城之后的身份轉化與角色轉型。
[15]在城鄉二元空間內,資源配置和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等級化差別。參見:Cheng Tiejun&Mark Selden,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vol. 139(Sept.1994),pp.645-668.
參考文獻:
[1]孔鐸,劉士林.我國逆城市化研究發展述評[J].學術界,2011(11):214-222.
[2]劉友富,李向平.“逆城市化”還是“偽城市化”?——反思大學生、農民“離城返鄉”問題兼與沈東商榷[J].中國青年研究,2017(6):24-30.
[3]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Berry, B. J. L.(1976).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Vol. 11).SAGE Publications,Incorporated.
[5] Fielding, A. J.(1982).Counterurbanisation in western Europe. Progress in planning,17,1-52.
[6] Mitchell, C. J.(2004).Making sense of counterurbaniz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15-34.
[7]?imon, M.(2011).Counterurbanization:Condemned to Be a Chaotic Conception?(Kontraurbanizace: Chaoticky Koncept?).Geografie,116,231-255.
[8]張善余.逆城市化——最發達國家人口地理中的新趨向[J].人口與經濟,1987(2):57-62.
[9]王旭.“逆城市化”論質疑[J].史學理論研究,2002(2):5-15.
[10]謝舜.城市化與市民生活空間的合理化建構[J].河北學刊,2005(2):113-117.
[11]孫群郎.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逆城市化”現象及其實質[J].世界歷史,2005(1):19-27.
[12]邱國盛.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研究(1949-1978)[J].社會科學輯刊,2006(3):171-176.
[13]劉新靜.郊區化與逆城市化:中國都市群發展的重要模式[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16-22.
[14]李培林.城市化與我國新成長階段——我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J].江蘇社會科學,2012(5):38-46.
[15]陶鐘太朗,楊環.論作為新型城鎮化自主動因的逆城市化[J].甘肅社會科學,2015(2):104-108.
[16]孔鐸,劉士林.我國逆城市化研究發展述評[J].學術界,2011(11):214-222.
[17]涂文學,高路.罪惡的淵藪,還是文明的階梯?——1900—1930年代中國的“反城市化”思潮論析[J].天津社會科學,2013(1):141-144.
[18]李翠玲.珠三角“村改居”與反城市化現象探析[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129-135.
[19]謝舜.城市化與市民生活空間的合理化建構[J].河北學刊,2005(2):113-117.
[20]王放.從第六次人口普查看北京市郊區化的發展[J].人口與發展,2015(6):30-37.
[21]高向東,張善余.上海城市人口郊區化及其發展趨勢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118-125.
[22]高向東,張善余.上海城市人口郊區化及其發展趨勢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2):118-125.
[23]孫群郎.試析美國城市郊區化的起源[J].史學理論研究,2004(3):44-54.
[24]顧海兵.再城市化:深度城市化與逆向城市化的同步推進[J].江海學刊,2002(2):73-77.
[25]沈東.當代中國農民工逆城市化的實踐及反思[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6(2):159-165.
[26]沈東.非轉農:逆城市化的本土實踐與現實反思[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5):98-105.
[27]沈東,張方旭.從“農轉非”到“非轉農”:大學生逆城市化流動的個案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7(2):2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