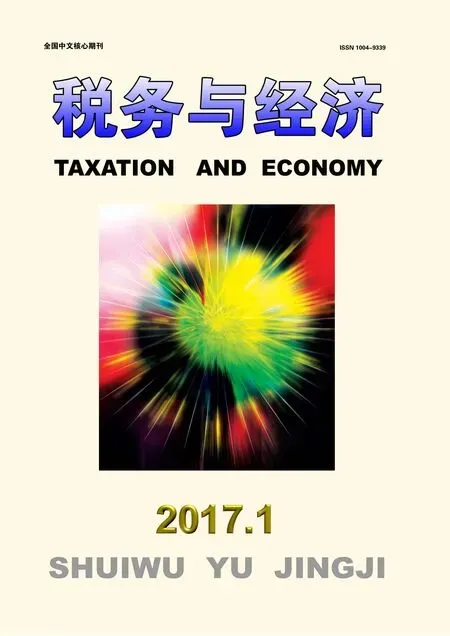公共安全支出對犯罪抑制作用的實證檢驗
張 麗, 呂康銀, 陳漫雪
(1.東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024; 2.吉林警察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一、引 言
長期以來,為了遏制犯罪率的上升,維護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各級政府都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國內公共安全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由1989年的2.92%增加到2014年的5.5%,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0.49%增加到1.31%。犯罪作為非法勞動,其多寡可以解釋為勞動者在合法市場與非法市場中勞動時間的分配,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犯罪行為不再僅僅是個別家庭或社區具體因素影響下的犯罪個體的非理性選擇,而是社會經濟因素及個體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在社會轉型期,社會化因素對犯罪的影響更加顯著,經濟水平、教育水平、社會保障等社會化因素帶來的勞動力市場變化已經為中國刑事犯罪的趨勢和特征打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面對犯罪誘因的社會化,政府的犯罪治理依然僅僅指向懲罰和個體動因, 司法手段是否還是預防打擊犯罪最立竿見影的選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早期的犯罪經濟學的研究中,一般認為司法支出的增加一方面可以增加犯罪的懲戒概率,減少犯罪,另一方面可以對尚未發生的犯罪產生威懾,從而降低犯罪參與的選擇(Becker,1968)。[1]然而在此后的實證研究中,卻沒有得出理論預期的結果(Humphries和Wallace,1980;Jacob和Rich,1980)。隨著實證研究的擴展,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了司法支出與犯罪率之間互為因果的關系,于是為了減少內生性的影響,部分研究選擇了滯后內生變量的手段(Greenberg等,1983;Lundman,1997),另有研究采用添加工具變量的方法來糾正此前實證的偏差(Levitt,1996,1997,2002;陳碩,2015)。[2]此外,隨著模型的不斷擴展,在陳剛(2010)的研究中還比較了司法支出、教育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的差異,實證結果表明教育及社會保障支出對犯罪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3]但不同犯罪類型對刑罰威懾及經濟社會條件變化的響應方式并不相同(Kelly,2000; Levitt和Miles, 2007) 。[4,5]例如,尋釁滋事犯罪和以侵財為主要目的的詐騙犯罪,其司法支出的作用效果必然不同。但目前對犯罪的分類實證研究僅限于收入差距對不同類型犯罪的影響(陳春良,2014)。[6]因此,根據現有犯罪數據,將犯罪進行分類處理,以全國的時間序列數據為基礎,估計司法支出對不同類型犯罪的作用,以科學衡量公共安全支出的犯罪治理效果,對理論研究的充實以及相關政策的制定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數據描述與模型選擇
應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計量工具衡量公共安全支出對刑事犯罪的實際影響,主要選用犯罪經濟學的分析模型。該模型最早源于Becker(1968)的研究,該研究認為人們參與犯罪的概率取決于犯罪的收益及遭受懲罰的可能和程度。
根據這一理論,將被解釋變量設定為犯罪率,同時將犯罪劃分為暴力犯罪、侵財犯罪和經濟犯罪。其中暴力犯罪包括危害公共安全和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以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行為;經濟犯罪主要包括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以及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妨害政府市場調控行為的犯罪;侵財犯罪則主要指盜竊、詐騙等以非法手段謀求他人財富,但并不直接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其中,被解釋變量的數據主要來源于2005年以來的《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的整理。
模型的解釋變量主要包括三類,一類是犯罪收益變量,一類是犯罪懲罰變量,一類是控制變量。基本回歸方程如下:
yi=β0+β1x1+β2x2+Ciβ3+εi
其中,yi為犯罪指標,x1為犯罪懲罰變量公共安全支出,x2為犯罪收益變量收入差距,Ci為控制變量向量,包括經濟水平、就業狀況、民生型財政支出。考慮Ehrlich(1973)[7]從勞動力市場的時間配置角度提出犯罪作為非法勞動,其收益可看作宏觀收入差距的論斷,將犯罪收益變量設定為行業收入差距,即金融行業(高收入行業)和農林行業(低收入行業)的平均工資差距,而犯罪懲罰變量則是研究主要考察的核心變量,在此選取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公共安全支出來代表。而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國內生產總值、教育、社保支出、城鎮失業人數。以上變量的數據同樣來源于2005年以來的《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的整理。模型及變量定義參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與統計描述
三、回歸與計量結果討論
此前,學者們普遍認為公共安全支出與犯罪率之間互為因果,但由于變量選取以及不同國家、地區公共安全治理機制相異,所以,研究試圖先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來驗證此次選取的公共安全支出與犯罪率變量是否存在內生性的問題。
如表2所示,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可以確定,總體刑事犯罪(y1)、暴力犯罪(y2)、侵財犯罪(y3)以及經濟犯罪(y4)并不是公共安全支出的格蘭杰原因,檢驗接受了原假設,而公共安全支出卻是侵財犯罪和經濟犯罪的格蘭杰原因,檢驗拒絕了原假設。雖然格蘭杰因果檢驗并不意味著一個變量是另一個變量的結果,但至少能夠說明一個變量前期的信息對另一個變量最優測度的貢獻,通過這一檢驗可以看到研究所選取的變量,公共安全支出與犯罪率之間并不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研究模型的設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核心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內生性問題。

表2 公共安全支出與犯罪率的格蘭杰檢驗
在此基礎上,首先選用了最小二乘法來進行回歸分析,從而驗證公共安全支出對不同類型犯罪的作用,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采用最小二乘法的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0.1、0.5和0.01平上顯著;括號中的數值為t值。
回歸結果顯示,公共安全支出與總體刑事犯罪、侵財犯罪顯著負相關,即公共安全支出的增加能夠減少總體刑事犯罪及侵財犯罪,但公共安全支出對暴力犯罪的作用不顯著。行業工資差距對除經濟犯罪以外其他犯罪類型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控制變量中,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民生型支出對犯罪的作用卻與預期相反,出現了顯著為正的情況。在筆者此前的研究中也曾證實教育等民生型支出與犯罪成倒U關系,即民生型支出增加到一定程度才會切實減少犯罪參與。[8]
在最小二乘法的估計中,暴力犯罪和經濟犯罪與各變量的關系并不顯著,而且作用方向也與理論不符,這可能與最小二乘法嚴格的假設條件有關,或者與可能存在的異方差、自相關等因素有關。為了避免對變量的錯誤估計,估計方程后,采用相關圖和Q統計量檢驗回歸方程殘差的序列相關,結果除對經濟犯罪的估計以外,犯罪總量、暴力犯罪、侵財犯罪的估計中Q統計量的P值較大,不存在序列相關。之后,在檢查序列平穩性的單位根檢驗中,對回歸方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除對暴力犯罪的估計外,對總體刑事犯罪、侵財犯罪、經濟犯罪的估計分別在10%、5%和1%的水平下,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殘差序列平穩,回歸方程不是偽回歸。
為了使回歸方程的估計更為準確,考慮未知形式的異方差以及暴力犯罪估計中的非平穩以及經濟犯罪估計的序列相關性問題,研究進一步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HAC一致協方差和采用AR模型來修正回歸方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修正后的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0.1、0.5和0.01水平上顯著;括號中的數值為t值。
相比于暴力犯罪、侵財犯罪,公共安全支出對危害市場經濟秩序的經濟犯罪其作用方向與預期一致,但作用不顯著。就目前的犯罪結構,侵犯市場經濟秩序的經濟犯罪在總體刑事犯罪中的占比雖然連年增長,但直到2014年經濟犯罪的犯罪人數也僅占刑事犯罪總人數的6.2%,所以在日常的公安工作中,經濟犯罪的治理相比于其他刑事犯罪的重視程度、打擊程度不足,而且作為法定犯,經濟犯罪的打擊口徑和程度也在隨著市場經濟法制化的發育不斷改變,公安機關打擊經濟犯罪的目的在于維護市場經濟秩序,通常不會為了打擊犯罪而影響企業的經營從而導致更大的經濟損失。在懲戒力度方面不及其他犯罪類型的同時,經濟犯罪又有顯著的智能性和隱蔽性,導致其被懲罰的概率下降。綜合以上因素,必然形成公共安全支出對經濟犯罪抑制作用不顯著的結果。然而,經濟犯罪雖然在參與人數上不及其他犯罪類型,但涉案金額巨大,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深遠,如不能實現有效控制,將導致市場資源配置的偏差,降低經濟運行的效率和效果。
相比于公共安全支出,行業工資差距對不同類型犯罪參與的引致作用均與理論預期一致,并表現出較強的顯著性,其中侵財犯罪的顯著性要高于暴力犯罪和經濟犯罪的顯著性。由此可見,目前我國刑事犯罪的職業化傾向正在增強,犯罪作為非法勞動甚至成為部分犯罪人員的職業選擇。絕大多數的犯罪動機是為了獲取更高的收入,而由于犯罪人員自身的素質及勞動力市場分割等問題的制約,導致部分低水平勞動力選擇非法勞動來獲取較高的收入。所以,犯罪治理一方面是要增加公共安全支出,增強其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還要采取綜合治理措施,以提升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配置效率。
對于控制變量的估計,各類刑事犯罪與經濟水平變量(國內生產總值)顯著負相關,與理論預期一致,而就業情況(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對各類刑事犯罪的作用卻與理論預期不一致,城鎮失業人數增加、就業情況惡化時,犯罪反而減少。得出這樣的估計結論,一方面可以認為由于勞動力市場分割及犯罪參與人員多為低素質勞動力,所以就業情況好轉并未對犯罪產生有益的控制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城鎮登記失業人數是由有勞動能力并有意愿進入合法勞動力市場就業的人員主動登記而形成的數據,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越多,說明想進入合法勞動力市場就業的人數越多,而勞動力在一定時期的總人數是穩定的,相對而言,意欲進入非法勞動力市場的人數就會減少,所以回歸結果也符合實際情況。對于教育、社保、醫療等民生型支出對各類刑事犯罪并沒有起到預期的抑制作用,主要考慮該項支出對于收入狀況的改善作用有限,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分配不平等問題。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為應對刑事犯罪持續增加的形勢,我國政府在公共安全管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對犯罪參與起到的抑制和威懾作用是顯著的。但是在對犯罪的分類考察中我們也看到,公共安全支出對侵財犯罪抑制作用顯著,而對暴力犯罪、經濟犯罪的作用卻不理想,為此,除了需要考慮犯罪本身的特點造成的影響,更應當關注公共安全支出結構和使用效率中的問題。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公共安全部門,只有在運行效率、執法效果、隊伍建設等方面得到有效的提升,才能更好地回應廣大民眾的社會安全需求。
目前中國刑事犯罪的社會化、職業化傾向越發明顯,犯罪數量、犯罪結構和犯罪動機受經濟水平、收入差距、勞動力市場狀況的影響越發顯著。總體刑事犯罪中侵財犯罪的占比最高,經濟犯罪也連年攀升且涉案金額巨大。由此可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催生的以經濟利益為主的犯罪形式已經成為犯罪的主流,絕大多數犯罪參與者的犯罪行為是源于經濟利益驅動的理性犯罪,如此公共安全支出增加所帶來的犯罪懲處力度的增強,必然增加此類犯罪的成本,從而達到減少犯罪的目的。然而,由于我國長期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問題,導致部分勞動力無法進入合法市場或者進入市場之后無法獲取相應的收入,從而即使存在較強的犯罪威懾,個別人仍會選擇非法勞動,以滿足自身不正當的利益需求。由此可見,單純依靠增加公共安全投入進行犯罪治理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而通過增加民生型支出改善收入差距,提升勞動力素質的舉措,對于減抑犯罪以及社會的良性發展將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在目前的研究中,教育、醫療以及社會保障等民生型支出對于犯罪的減抑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與民生型支出的總量、結構、質量和公平性等密切相關。
[1]Becker, G S.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8,76(2):169-217.
[2]陳碩,章元.治亂無需重典:轉型期中國刑事政策效果分[J].經濟學:季刊,2014,(4):1461-1484.
[3]陳剛,等.中國犯罪治理的財政支出偏向:選擇“大棒”還是“胡蘿卜”?[J].南開經濟研究,2010,(2):117-135.
[4]Kelly, M..Inequality and Crim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0,82(4):530 -539.
[5]Levitt,S. D.,Miles T.Empirical Study of Criminal Punishment in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M].Aolinsky and Shavell, Elsevier,2007.
[6]陳春良.收入差距與刑事犯罪:基于不同犯罪類型的再考察[J].制度經濟學研究,2014,(3):23-45.
[7]Ehrlich, I. Participation in Illegitimate Activiti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81(3): 521-565.
[8]張麗,等.實證檢驗教育擴展對犯罪參與的影響[J].教育科學,2014,(4):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