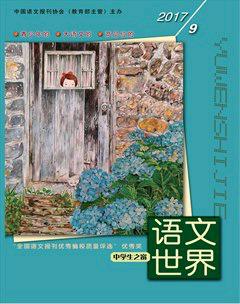余 生
喬心怡
江南,二月早春。貫穿小城的河,沿岸的柳樹蒙上一層灰綠。
在橋頭一坐,看水中倒映的橋影,看橋上過往的行人,透著潮氣的木桌上,是一碗熱騰騰的小餛飩,撒著細碎的蝦米和胡椒,薄至透明的面皮在湯水中上下浮動。
生長在一座典型的江南小城中,習慣了水鄉的樸素溫和,多年后的數個晚上,在異鄉度過,卻無法忘記家鄉的景。暮色微微,水在那里,橋在那里,不大,不小,不遠,不近,不耀武揚威,不唯唯諾諾,搭配得極為妥貼。長大后的我,不知為何,時常想起兒時這樣的江南。
幼時住在運河邊,斑駁的白墻,老舊的磚瓦,都是歲月的遺留,傍晚時分,微風陣陣,各家的飯香、菜香夾雜著水汽在一條街飄過。這條河流,大約是京杭大運河的分支,是早已不通航的了。曾經為了方便走大船的橋洞,如今看來,因為高高聳起而稍顯突兀,疏朗的風格又與其他水鄉略有區別,如今這里的水太過平靜,若非游船,便只有風的拂動才會蕩起層層漣漪。也許,暢達從容,才是江南的本色。
兒時的辰光仿佛稍縱即逝,從街頭到街尾,走走停停,恰好一個上午的時間。孩子好奇多動的天性總給年幼的自己造成困擾,跑進一戶人家,十有八九會被門檻絆倒,然后被主人扶起,與別家的孩子一起玩耍。有時便會征得家長同意,和孩子們一起看戲。
只是,彼時哪里懂什么情啊愛啊,更不要說那些國恨家仇,何況錫劇里也很少提及這些氣勢磅礴的“大事”。孩子看戲哪里懂得如此之多的門道,只知道看個形式,內容也不太記得。印象里,場子很小,搭在中庭的院落,空余的地方便是隨意排放的椅子,每周只演兩場,雖然談不上喜歡,卻也愛看那些扮相。開場的鑼鼓響起,演員踱著步子走出來,形態沉郁,多半是在扮演心事重重的角色。錫劇中的名章不多,最有名的不過《雙推磨》《珍珠塔》,也不過兒女情長,未曾有晦澀的念白。吳地之音多軟綿,唱起來便更加酥身,一幕下來,清脆的嗓音余味悠長,一開始滿場亂跑的孩子,到后來便也安靜地坐在大人懷里看戲了。
一出戲結束,離各家開飯還有一段時間,便游走在弄堂之間。那些宅邸圍墻之間,夾出隨處可見的里弄,是主街之外靈活的便道,像江南人千回百轉的柔腸,有各種各樣的姿態,通向千百種可能。還有一些袖珍的弄,直接通到水邊,跑累了,走過去坐下來,把雙腳在空中蕩啊蕩,冷不防就沾濕了鞋子。偶爾天色暗了也不回家,慢慢地,真正的黑夜開始了,遠處別人的說話聲,被疏離得縹緲起來。我們自己聊了些什么如今已經忘光了,無非是那個年紀的真話、假話和大話,那些話語也紛紛散在江南夜下的霧氣里,那團團升起的霧氣,模糊了一座座石橋的輪廓,一切都是這么近,又那么遠。
這自然是江南小鎮上最平常的景象,讓人會一時忘了具體的所在,但它的趣味,則并非那些游人所尋的。江南的美,于我而言,并不在這流水小橋的溫柔之中,而在于圍墻里的生活。雖說是古城,但幾百年前的前塵舊事,又哪里敵得過家長里短的輕描淡寫。街墻斑駁,古道鏗鏘,并不是被歲月遺忘。有些東西,被歲月勾勒得太久,便會愈來愈清晰。
如今早已不在這樣的住處,自由奔跑的年紀也早已遠去。現在再回想起童年的時光,玩伴雖多,卻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孤獨,無法自我表達,甚至在很多事情的面前,自我辯駁的機會也不曾擁有。也許正是因為童年時的表達欲望沒有得到充分滿足,長大后才會選擇寫字的途徑來彌補。我在這個不斷老去的江南小城里自由生長,余生漫長,我清楚地知道總有一天我要離開它。但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一定會想念過去貪戀著它、不愿離開的自己。它會影響我絕大部分的人生選擇。
后來的某個傍晚,一個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夾雜著水汽的晚風一陣陣輕拂著這座城市。那種熟悉的感覺再一次從身體里蔓延開來,就在那里,童年時一個人在河邊,那種不知所措的寂寞感,真實地憑空出現,那樣柔軟的憂愁,從江南倒映著燈火的水面上蕩來,從墻角夏蟲的低吟中傳來,從綿軟悠長的吳音軟語中飄來,從店鋪凹凸地面上晃動的吊扇影子里投來,它穿越時間,向我洶涌地襲來。那感覺像幼時長輩祭祀用的一炷香,在我疲憊的身體里升騰,彌散,繚繞于心,越聚越濃。
找不到出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