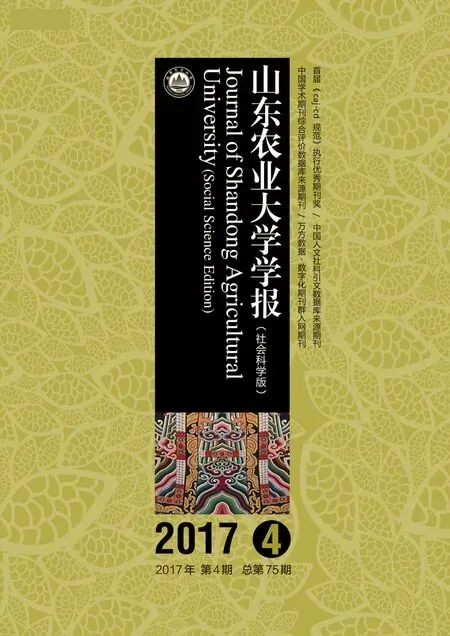唐代山東地區手工業發展與森林變遷
□吳家洲
唐代山東地區手工業發展與森林變遷
□吳家洲
唐代山東地區的礦冶業、制瓷業、煮鹽業、造船業等手工業部門都十分發達,森林為這些手工業部門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燃料,但這些部門的發展卻使森林面積不斷減小。通過分析唐代這些手工業部分的分布情況,結合歷史文獻描述、考古發掘資料及現代研究成果,并經過嚴格的定量分析,估算出各個手工業部門發展消耗的森林面積,更直觀地反映手工業發展對森林的破壞程度。指出手工業發展程度和森林面積成反比關系,在唐代時人還沒有太多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情況下,手工業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以犧牲森林為代價的。
唐代;山東;手工業;森林
本文所討論的手工業主要指的是礦冶業、制瓷業、煮鹽業、造船業等會消耗很多林木、對生態環境造成重大破壞的行業;山東地區指的是今山東省的地域范圍。手工業的發展與生態環境條件密切相關,唐代山東地區有較為豐富的森林資源、便利的水陸交通、充足的水資源,都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在良好生態環境條件的促進下,唐代山東地區手工業發展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礦冶業、制瓷業、煮鹽業、造船業等都非常發達,中唐之前,可以說是全國手工業經濟中心之一。[1]隨著手工業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干預力度也逐漸加大,尤其是對林木資源的過度消耗,使山東地區的生態環境面臨巨大的壓力。
一、唐代山東地區礦冶業對森林的破壞
在某種程度上說,“一部中華文明史,其實就是一部由銅和鐵鑄就的文明史”[2]。礦冶業是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礦冶業包括開礦業和冶煉業兩個部分。現有的考古資料表明,中國在距今4000年已進入青銅時代[3],從公元前6世紀末至公元前5世紀初進入鐵器時代,到唐朝時礦產的種類和
開采數量有了明顯的提高,管理機構更加完善,礦冶技術更加先進,進入了繁榮時期[4]68。朝廷設有專門的掌冶署“掌范熔金銀銅鐵及涂飾琉璃玉作”[5]1271,其令“掌熔鑄銅鐵器物之事,丞為之貳”[6],地方要按時上供官營手工業所需的原料。后又規定:除了西北地區外,“凡天下出銅鐵州府,聽人私采,官收其稅”[7]1894,礦冶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隨著礦冶業的持續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力度也逐漸加大,礦區生態問題不斷惡化。
(一)唐代山東地區金屬礦產分布情況
金屬礦產是礦冶業發展的基礎,金屬礦產的分布情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礦冶業的發展情況。唐代山東地區的金屬礦產具體分布情況如表1。

表1 唐代山東地區金屬礦產分布表
從表1中可以看出,唐代山東地區金屬礦產種類豐富,已開采的有五種;總共有11處金屬礦產地。鐵的產地最多,有6處,分布在5個州;銅的產地有2處,分布在2個州;錫、銀、金的產地各有1處,分布在3個州。兗州萊蕪縣的礦產種類最豐富,有3種;萊州昌陽縣其次,有2種。兗州有4處礦產地,萊州有2處,青、齊、淄、沂、登州各1處。從整體上看,山東地區的金屬礦產分布十分集中,基本上都在中部山區和東部丘陵地帶,而這些地區正是森林茂密的地區。
唐朝時期,山東半島的礦冶業發展迅速,兗州、萊州是礦冶中心,特別是兗州的萊蕪縣最集中,縣西北的韶山出鐵,“漢置鐵官,至今鼓鑄不絕”[8]268,還有銅和錫,礦區及冶煉工場格外密集[9]17,可以說是礦業最發達的區域。萊州昌陽縣的的冶銀也很有名,縣東有黃銀坑,“隋開皇十八年,牟州刺史辛公義于此坑冶鑄,得黃銀獻之。大業末,貞觀初,更沙汰得之。”[8]308齊州歷城縣、青州北海縣、兗州鄒縣都是冶鐵基地。此外,沂州沂水縣產銅,登州牟平縣還出產金礦。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五月,侯希逸開始割據淄青鎮后,礦冶收入被軍鎮截留長達 57年之久[9]17,時“兗、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余萬”[7]4404,收復淄青鎮后,這“三道十二州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5]5318,可見山東半島礦冶的產量豐富、利潤豐厚。唐代中期以后,“兗海等道,銅鐵甚多……審見滋饒,已令開發”[10],山東礦冶業的發展更為迅速。中朝地臺——河淮凹陷、魯中突起等地質構造帶是著名的鐵礦分布帶,郭聲波先生對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的鐵冶點進行統計,隋唐時豫西山地、魯西山地占18%;[11]48山東半島地帶直到明清時還是著名的礦冶區域[12]20-22。
(二)唐代山東地區礦冶業消耗森林分析
開采礦產的過程本來就是要把礦區的山體植被清理干凈的過程,直接造成森林覆蓋面積的減少。唐代開采礦產所用的方法是“火爆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令礦脈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動錘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13]177單單開采礦產就需要大片、不及段數的木柴,連續大火燒一夜才可以開采,這只是一階段的過程,等變柔脆的礦開采完了一層,還要繼續火燒,周而復始,消耗的柴木更是不計其數。
唐代山東地區的煉銅采用的是火法煉銅技術。《大冶賦》中有相關的記載,包括采礦、焙燒、入爐、點火、融化礦石、出銅等步[14];《菽園雜記》則有更詳細的描寫,“每秤銅一料,用礦二百五十籮,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用柴炭裝迭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亙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頭出于礦面。火愈熾,則鉛液成駝。候冷,以鐵錘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烹。有生烹虧銅者,必碓磨為末,淘去粗濁,留精英,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夜,是謂成鈲鈲者,粗濁既出,漸兒銅體矣。次將鈲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兩日兩夜,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擊碎,依前入旋風爐镕煉,如镕銀之法。”[13]177可見,處理這種礦石,在熔燒后,需要經過三次粉碎,三次開動大旋風爐烹煉,才能煉出生銅。[4]267熔燒、烹煮等都需要消耗巨量的柴炭。按每秤銅,需要炭七百擔,一擔等于一百斤,就是需要3.5噸的炭,按現代人工栽植的專用薪炭林平均每公頃每年可獲薪材量,闊葉矮林為10-20立方米,灌木林為10-20噸,馬尾松林為5-10噸;[15]假設唐代山東地區每公頃森林可以得到的薪材量為15噸,那么每秤銅就需要消耗0.233公頃的森林。而在清代冶煉含銅成分極高的云南銅礦石,也需要“要用炭一千二、三百斤,始能鍛礦千斤,得銅百斤”[16],而且炭必須是松木炭[17]。在明、清時期技術已經十分先進的情況下,冶煉尚需消耗如此多的柴炭,更不用說唐代。
唐宋時礦業所用之燃料,尚為木料或木炭。[18]112尤其是唐朝時期,林木還是作為最主要的燃料來源。在“有山可薪”[19]64之處,“治炭其中,起鐵冶其居旁”[19]64。冶煉爐都需要非常高的溫度,只有持續不斷地柴炭投入才能夠維持。春秋時期,齊國國都臨淄的郊外有一座牛山,“牛山之木嘗美矣”[20],連齊景公都贊嘆“美哉國乎,郁郁芊芊”[21],后“斷山木,鼓山鐵”[22]1448,大力冶鐵,變成了濯濯童山。而據考古研究,經過嚴密的計算,河南漢代古滎冶鐵遺址的一號高爐每生產一噸生鐵,約需鐵礦石二噸,石灰石一百三十公斤,木炭七噸左右,渣量六百公斤多,日產約五百公斤。[23]按日產500千克計算,一年約需要木炭1278噸,關于木材的出炭率有大約為20%[11]54和大約為30%[24]145兩種觀點,取其中間值25%計算,木材比重以0.6噸/m3計算,一噸木炭約需要2.4立方米的木材,則一年約需要消耗3067.2m3的木材。按1畝林裁木1m3計算[11]54,一座鐵爐一年約可以消滅3000多畝即2.04平方千米的山林。假設每年產量相同,按唐朝統治時間279年計算,約569.16平方千米的森林會消失,和兗州市面積648平方千米相當。古書有載從采銅礦到煉成生銅,要用相當數量柴炭連燒二十余個日夜;[13]177-178許惠民先生通過研究,也指出煉銅需要的燃料是煉鐵的數倍[24]147;消耗的森林更是無法估量。
唐代隨著工農業的發展、軍事的需要、鑄幣的需求,鐵只是勉強夠用,銅則顯得有些不足。[12]18因高宗、宣宗時大量廢銅冶,而新增銅冶無幾,導致銅產量大幅度下降。[25]為此還不得不實行“銅禁”,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詔“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5]1385。為了獲得更多的銅和鐵,肯定會加大礦山的開采力度,加多冶煉爐的開工頻率,就意味著更多的森林破壞,更大的環境污染。北宋時,山東半島的萊蕪還是“采礦伐炭”[26]、“斬木鼓鐵”[27],不斷砍伐森林,以致沈括嘆道:“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28]從中也可見礦冶業對森林的破壞之大。
此外,采礦需要的裝載、提運工具,如竹簍、竹筐、藤簍、木轆轤等;排水工具,如大水槽、木桶等,都是木制品。而大概唐宋礦區,如離水近,即多用水排,否則亦用木扇。[18]110水排、木扇也是木制品,大型水排更是對水源的巨大消耗,礦渣排入水中還會污染水源,影響植物生長。“產鐵之山,有林木方可開爐,山苛童然,雖多鐵亦無所用”[29],充足的林木是開爐的前提,礦山的開發就意味著森林面積的減少,當沒有森林時也就意味著礦冶業的衰落。而且冶煉過程中產生的礦渣就直接被堆在空地上,不僅直接覆蓋了地表的植被[30],礦渣中的金屬成分隨著雨水滲入地表,會污染土壤、地下水,也會使周圍植被營養不良。
二、唐代山東地區制瓷業對森林的消耗
我國是世界上燒制瓷器最早的國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時代就創造出了釉陶或原始青瓷[31]。唐代制瓷業是我國陶瓷史上承前啟后的階段[32]36,唐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繁榮,加上唐朝廷禁用銅器、唐中后期飲茶之風盛行及交往、禮節的需要等,促進了制瓷業的大發展,各地陶瓷作坊蓬勃興起。唐朝還設有專門的官員——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石磬碑碣、石人獸馬、碾硙磚瓦、瓶缶之器、喪葬明器,皆供之。”[7]1896但制瓷業畢竟是消耗森林的大戶,它需要森林提供充足的燃料才能繼續發展,它的發展正在侵蝕越來越多的森林。
(一)唐代山東地區瓷窯作坊遺址分布
山東地區是唐代北方地區的制瓷中心之一,經發掘,唐代山東地區的瓷窯作坊遺址有山東淄博磁村[33]、泰安、曲阜、泗水等處,分布廣泛。隨著一些考古學家及山東大學等歷史系考古學專業的師生對山東地區的考古發掘調查[34]1121,越來越多的瓷窯遺址被發現。具體情況如表2。

表2 唐代山東地區瓷窯遺址情況表序號
從表2中可以看出,唐代山東地區的瓷器窯址總共有9處;兗州最多,有8處,幾乎占全部;淄州有1處;主要集中在今山東中部山區的森林茂密地帶。山東地區瓷窯生產的陶瓷品種,以青瓷和白瓷為主,但還有其他陶瓷類型,如淄博窯兼燒醬釉[35]48,大泉窯兼燒黑、褐釉[34]1124,山東淄博的黑釉更是佳品[32]37。即使一個瓷窯遺址也不意味著就僅有一個瓷窯,如磁村古窯址分為四區等[35]46。有些窯的歷史悠久,如中淳于村窯[36]、宋家村窯[37]都從北朝就開始燒制瓷器。
(二)唐代山東地區制瓷業消耗森林分析
充足的水源、豐富的林木資源、良好的瓷土條件是制瓷業發展的前提[34]1125,豐富的林木資源為瓷窯提供充足的燃料,瓷窯的規模越大對森林的破壞也越嚴重。建造瓷窯作坊時,就需要把附近的植物清理干凈,挖掘瓷土更是和開采礦山是一個性質,會造成局部童山。按《陶冶圖說》,制瓷需要經過二十個步驟[38],唐時瓷窯基本上都采用柴燒,入窯燒造要保證窯爐的溫度,通常需要達到1000℃以上,就需要充足的燃料,而森林正是燃料的主要來源。
鄭州大學的歷史學工作者根據1974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禹州鈞臺發掘的宋鈞官窯情況,復原了1號窯爐,窯爐包括簾門、觀火孔、火腔、密室、煙函、密道等部分,其中窯室呈長方形,底部長3.61米、寬1.56米,進行模擬燒瓷實驗。[39]經過反復試驗,最后成功燒制出比較理想的產品,得出結論:燒100件產品,需要用柴3500公斤。可以得出每燒一件產品約需要用柴35公斤。關于各個瓷窯的具體產量,沒有確切的文獻記載。1976,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聯合相關部門對淄博地區的部分古窯址進行復查,至少發現窯爐15座。[35]46假設每個瓷窯遺址就一處瓷窯,每處瓷窯有15座窯爐,每個窯爐的年產量為100件,則每個瓷窯的年產量為1500件,不分種類,則山東地區的瓷器年生產總量為13500件,需要消耗柴火47.25萬公斤,即472.5噸。按每公頃森林可以得到的薪材量為15噸,那么山東地區一年的制瓷業生產就要消耗31.5公頃即0.315平方千米的森林。如果終唐一朝每年都是這樣的產量,那么需要消耗87.89平方千米的森林,約相當于今兗州市面積的九分之一,可見制瓷業消耗森林之巨。且制瓷業本身就是一個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不僅消耗了大量的礦產和森林,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等也會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40]。
三、煮鹽業、造船業對森林的破壞
(一)唐代山東地區煮鹽業對森林的破壞
山東東部沿海地區煮鹽業歷史悠久,《管子·輕重甲》說:“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22]1422《史記》也說:“山東多魚、鹽、……”[41]3253。西漢有海鹽之饒的地方是山東地區的燕、齊及南方東楚。[42]東郭咸陽在武帝時以“齊之大煮鹽”[41]1428的身份掌鹽鐵事物。漢在千乘郡千乘縣[8]274、瑯琊郡海曲縣[8]300、東萊郡昌陽縣[8]308和牟平縣[8]312都設有鹽官。青州是古代齊國區域,更是“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43]2490。唐朝時,日常生活及手工業、農業用鹽等各方面的需求,使山東地區的煮鹽業蓬勃發展,成為該地區的支柱行業[9]16。唐代山東地區海鹽產地的具體分布情況如表3。

表3 唐代山東地區海鹽產地分布表序號
從表3中可以看出,河南道的海鹽產地有8處,分布在沿海各州。萊州最多,有3處;密州、青州各有2處;登州1處。此外還有不確定的地區,如登州牟平縣、登州文登縣、萊州昌陽縣等在漢時就已產鹽。而且,每個州擁有的煮鹽地也不盡相同,如諸城縣“縣理東南一百三十里濱海有鹵澤九所,煮鹽,今古多收其利”[8]299;膠水縣西北的平度故城“有土山,古今煮鹽處”[8]308。
宋朝以前,海鹽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是煎煮[46]107,即“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者也”[47],或叫作刺土成鹽法。盧綸詩云:“潮作澆田雨,云成煮海鹽”[48],就是對這種方法的形象描述。《太平寰宇記》中則有具體的描寫,主要包括刮咸取鹵、驗鹵、煎煮三道程序[45]2569,煎煮是最重要的環節。煎煮前要做好制作鹽盤、搭砌灶火、搜集柴火等準備工作[46]108。煮鹽的鹽盤,俗稱大鐵鍋,“漢謂之牢盆”[49],“鍋下一排灶同時點火,多的有十二、三眼灶,少的也有七、八個灶,共同燒火”[50]33。牢盆大者煎鹽多、用柴亦多,小者煎鹽少、用柴亦少。[13]148需要一直熬煮到鹵水沸騰后慢慢成鹽,方才結束燒火。煮海鹽需要用掉多少的木材并沒有統計,但可以用井鹽的熬煮用材量來大概估計。據《丹淵集》載:陵州“惟管內仁壽等四縣,百姓每歲輸陵井監煎鹽木柴,共計三十八萬四千二百余束也”[51]756。關于陵井的產量,《太平寰宇記》記載:“陵井監井諸縣計十井,日收鹽四千三百二十三斤”[45]1698;《玉壺清話》曰:“蜀置監,歲煉鹽八十萬斤”[52];李燾認為宋初日產約三千六百斤[53];而《文獻通考》載:“陵井監及二十八井,歲煮一百十四萬五千余斤”[43]155。宋代在四川設監,監下設場務管轄鹽井[54]。陵井監設置十一場務,其管轄范圍包括陵州境內的所有官營鹽井[55]。按日收4323斤計,則一年收鹽157.79萬余斤;按日產3600斤計,則年產量是131.4萬斤;但一年中每天的產量不是恒定的。而從后蜀時期的80萬斤增加到宋時的114.5萬余斤,日產約3137斤,與前面兩組數字比較,更為合理。所以取歲收114.5萬余斤,每束木柴按5公斤計算[56],每年約需要消耗木柴192.1萬公斤,則每斤鹽約需消耗木柴1.68公斤。怪不得為了上交煎鹽木柴會導致“山谷童禿,極望如赭。縱有余蘗,才及丈尺,已為刀斧所環爭相翦伐,去輸官矣。人既匱極,草木亦不得盡其生意”[51]756。井鹽用的僅是中號鍋[50]37,就耗材這么多,更不用說大號的牢盆了。
肅宗、代宗時期,朝廷曾設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以主持該區域稅收[57],包括征收鹽稅,但不久后便廢,山東地區更長期處于淄清藩鎮的控制下,鹽稅長期被截留。長慶二年(公元822年)五月敕曰:“聞淄青鄆三道,往年糶鹽價錢,近收七十萬貫”[58],這應該是淄青藩鎮割據時的鹽產數額[59]93。按當時的鹽價估算,淄青兗鄆沿海地區元和中產鹽約計 28萬石[59]93。按唐1石容6萬毫升[60],食鹽的密度取2.65克每毫升,唐1石食鹽約為159公斤,那么山東地區每年鹽產數額為4452萬公斤。雖然池鹽和海鹽的耗材比例不同,我們姑且認為相當,按每斤鹽需耗材1.68公斤計算,則山東地區每年產鹽約需要消耗柴木14958.72萬公斤,即約15萬噸木柴。按唐代山東地區每公頃森林產薪材15噸計算,需要砍伐1萬公頃的森林,也就是消滅了100平方千米的樹木,約相當于今曲阜市九分之一的面積。且煮鹽用的鐵鍋的生產也是用犧牲森林換來的,可見煮鹽業對森林的破壞也相當嚴重。
(二)唐代山東地區造船業對森林的破壞
唐代的航運業繁榮,“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7]2998。還專門設立了“水部郎中”[7]1841、“舟楫署令”[7]1897等官職,專門管理造船、航運和水上防務[61]79。今山東半島的東萊地區是隋代重要的造船基地[62]7,隋朝征伐高麗就在此制造了大量船舶,唐代在隋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9]18。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張亮率“勁卒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7]5322;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馀人,乘樓船自萊州泛海而入”[63]6245-6246;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馀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63]6252;唐太宗發動的這些征伐高麗的戰爭都是從膠東地區出發的,其中應有部分該地區造的戰船。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統眾浮海赴熊津,以益仁愿之眾”[7]5322,如此大規模的從山東半島沿海各州召集船只,即使船只不是此地制造,船只的修繕、維護工作也不小。史料顯示,有大型的船舶修理場在密州大珠山地區發現。[9]18大師圓仁的船隊“于密州管東岸,有大珠山。今得南風,更到彼山修理船”[64]134,張同軍由于在牟平縣乳山浦造船場“貪造舟”[64]505而遭人檢舉[9]18。膠東地區作為大軍唯一的出海口,所具備的海船制造業必定仍保持一定的規模。[62]7
船廠一般選取山林可伐、水陸交通便利的地區專門打造[65]85。豐富的林木資源、便利的航運交通、充沛的水資源等生態環境因子,是造船業發展的外在環境條件。[65]85唐朝的船幾乎都是木制的,故豐富的林木資源是制造船舶的基礎條件。隨著水密艙壁的使用和造船工藝的進步[66],唐代可以造出“船上建樓三重”[67]的樓船,也可以造出“不啻載萬”[68]的商船。1974年6月,江蘇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身殘長17.32米,復原后約為18米,船最寬處2.58米、最窄處1.3米,船深1.6米;船舷木板厚40-70毫米,船底木板厚80-120毫米。[69]據估算,改船排水量為30-35噸[70]。取船長18米,船寬取平均值1.94米,船舷木板厚取0.055米,船底木板厚取0.1米,假設船面和船底同寬,計算出船身木料的體積約為6.89立方米,沒有把船體內部構造的木料計算在內。如果按排水量估計,船的重量取32.5噸,假設船上的物品全部都是用樟木制造,樟木的密度為800千克每立方米,則木料的體積為40.63立方米。1960年3月在江蘇揚州施橋鎮發掘的唐代1號木船大小和如皋出土的相仿[71],估計都是比較常見的商用貿易運輸船舶。假設河南道僅生產了1千艘這樣的船舶,僅按船身的體積計算,就約需要6890立方米的材木,按1畝林裁木1立方米計算,約需要6890畝即4.593平方千米的森林;如果按每船需木料40.63立方米,則需要27.085平方千米的森林;且河南道的船舶產量肯定遠不止1千艘。在唐代來說,這只是中小型的船舶,據研究,赴日貿易的唐船的船身許多都超過30米、船最寬處都超過5.5米、船高超過6米[72];唐代的客船,長20余丈,載六七百人很普遍;[61]82貨船“大者受萬斛也”[73],約載重五百余噸;更不用說更加高大的樓船、艨艟等大戰船。這些船舶需要的材木又都是材質比較好的,對森林的破壞就更加嚴重。而且河南道地區水產資源豐富,漁民們靠水吃水,建造了大量的漁舟捕魚,漁舟都是木制的,也是對森林的一大消耗。
綜上所述,不管是礦冶業、制瓷業、煮鹽業等以林木為燃料的行業,還是造船業等以林木為原料的行業,都是以犧牲森林為代價獲得快速發展的。這些行業的繁榮是建立在森林減少的基礎上的,唐代的人們還意識不到手工業生產對森林的破壞,他們還沒有太多的生態環境保護概念,對他們來說,林木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多砍伐森林還能創造更多的經濟效益。而手工業對森林的需求是大量而密集的,對森林的破壞速度遠遠超過森林的自我恢復速度,直接的后果就是導致森林面積減少,環境不斷惡化。
注釋:
①把隋朝的礦產記錄在內,礦產的開采周期一般都比較長,到唐時不應廢棄。
②每立方米木材重量因木材種類、重量、質地不同而不同,龔勝生先生認為比重為0.4噸/m3,許惠民先生認為是0.8噸/m3,這里取中間值0.6噸/m3。
③鈞官窯屬于半倒焰窯,技術成熟,估計當時的匠人可以用更少的柴燒成,這里以實驗數據為準。且各地瓷窯的燒制技術不同,需要消耗的薪柴也不一致,這里不作分別論述。
④[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1.3.表中《新唐書》版本均與此同。
⑤郭正忠在《中國鹽業史·古代編》中也持相同觀點。
⑥船左右側面木料體積為3.168m3,船前后面木料體積為0.229m3,船底木料體積為3.492m3。
[1] 寧可.中國經濟通史·隋唐五代經濟卷[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301.
[2] 謝乾豐.略論中國古代冶金技術文化[J].前沿,2008,(9):187.
[3] 孫淑云,李延祥.中國古代冶金技術專論[ M].北京: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3:1-2.
[4]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M].北京:地質出版社,1980.
[5]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1.
[6] [唐]李林甫.唐六典[M].陳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577.
[7] [后晉]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8]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6.
[9] 尚旭華.唐宋山東經濟盛衰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10] [宋]王欽若.宋本冊府元龜[M].北京:中華書局,1989:1238.
[11] 郭聲波.歷代黃河流域鐵冶點的地理布局及其演變[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3).
[12] 張鑑模.從中國古代礦業看金屬礦產的分布——兼論“歷史報礦”[J].科學通報,1955,(9).
[13] [明]陸容.菽園雜記[M].佚之,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5:177.
[14] [宋]洪咨夔.平齋文集[M].清影宋抄本.學識齋,1868:762-765.
[15] 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林業卷編輯委員會.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林業卷下[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694.
[16] 嚴中平.清代云南銅政考[M].北京:中華書局,1957:63.
[17] 許書理.略論中國古代火法煉銅技術[J].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8,(2):140.
[18] 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M].陶希圣,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19] [宋]岳珂.桯史[M].吳企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
[20] [戰國]孟軻.孟子[M].萬麗華,藍旭,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249.
[21]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385.
[22] 黎翔鳳撰.管子校注[M].梁運華,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4:1448.
[23] 《中國冶金史》編寫組等.河南漢代冶鐵技術初探[J].考古學報,1978,(1):9.
[24] 許惠民.北宋時期煤炭的開發利用[J].中國史研究,1987,(2).
[25] 徐東升.唐代鑄錢散論[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7,(2):15.
[26] [清]姚鼐.古文辭類纂[M].徐樹錚,集評.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58.
[27] [宋]李昭玘.樂靜先生李文公集[M].清道光四年劉氏味經書屋鈔本,1824:754.
[28] [宋]沈括.夢溪筆談[M].張富祥,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260.
[29]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M].北京:中華書局,1985:408.
[30] 李錦偉,劉英.明清時期梵凈山地區手工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萬山汞業生產為例[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S2):17.
[31] 葉宏明,曹鶴鳴.關于我國瓷器起源的看法[J].文物,1978,(10):85.
[32] 盧建國.論唐代制瓷業的大發展[J].文博,1985,(2).
[3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J].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636.
[34] 宋百川,劉鳳君.山東地區北朝晚期和隋唐時期瓷窯遺址的分布與分期[J].考古,1986,(12).
[35] 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山東淄博市淄川區磁村古窯址試掘簡報[J].文物,1978,(6).
[36] 李發林.山東泰安縣中淳于古代瓷窯遺址調查[J].文物,1986,(1):39.
[37] 宋百川,劉鳳君,杜金鵬.曲阜宋家村古代瓷器窯址的初步調查[J].景德鎮陶瓷》,1984,(S1):167.
[38] [清]唐英.陶冶圖說[M].北京:中國書店,1993:2-18.
[39] 閻飛.中原古代陶瓷窯爐實驗考古研究[D].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100-107.
[40] 陶瓷業發展不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J].建材發展導向,2016,(16):99.
[41] [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42] 董咸明.唐代的自然生產力與經濟重心南移——試論森林襯唐代農業、手工業生產的影響[J].云南社會科學,1985,(6):105.
[43]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4] [宋]李昉.太平廣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6:1836.
[45]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M].王文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408.
[46] 郭正忠.中國鹽業史:古代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7] [宋]方勺.泊宅編[M].許沛藻,楊立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14.
[48] [清]彭定求.全唐詩: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1992:3182.
[49] [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100.
[50]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譯注[M].潘吉星,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1] [宋]文同.丹淵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2]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4:27.
[5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194.
[54] 程龍剛.宋元時期的四川鹽業[G]//鹽文化研究論叢: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08:31.
[55] 張連偉.陵井考述[J].鹽業史研究,2014,(2):48.
[56] 龔勝生.唐長安城薪炭供銷的初步研究[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3):143.
[57]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顧學頡,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99:922.
[58] [宋]王溥.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5.6:1606.
[59] 李青淼.唐代鹽業地理[D].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60] 吳慧.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度量衡[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3):16.
[61] 唐志拔.中國艦船史[M].北京:海軍出版社,1989.
[62] 姜浩.隋唐造船業研究[D].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63]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M].[元]胡三省,音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
[64] [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M].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
[65] 譚靜怡.生態環境視域下宋代長江沿線的手工業活動[J].北方論叢,2016,(3):85.
[66] 程曉.我國古代造船技術的興衰及其啟示[D].武漢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11-12.
[67] [宋]李昉.太平御覽[M].北京:中華書局,1966:1536.
[68] [唐]李肇.唐國史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2.
[69] 南京博物院.如皋發現的唐代木船[J].文物,1974,(5):84.
[70] 席龍飛.中國造船史[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14.
[71] 江蘇省文物工作隊.揚州施橋發現了古代木船[J].文物,1961,(6):53.
[72] 辛元歐.中外船史圖說[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183.
[73]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M].[清]阮元,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14.
K242
A
1008-8091(2017)04-0014-08
2017-02-10
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福建 福州,350007
吳家洲(1986- ),男,漢族,福建省三明市人,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國史歷史地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