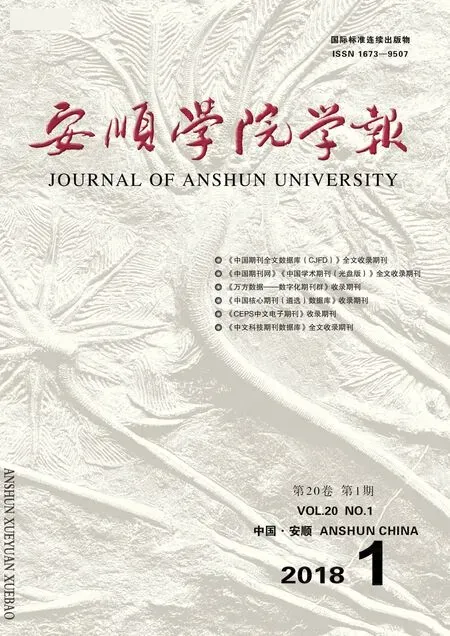清代改衛歸流研究芻論
(安順學院人文學院;貴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中心,貴州 安順561000 )
引言
明朝政府在邊疆民族地區設置的實土或準實土的衛所(不含羈縻衛所),通常被時人或后人視作流官政治的一部分。相對于土司而言,明代衛所因其表征王朝正統的身份而被歸入流官體制似無疑義,但由于衛所職役世襲制度的推行,它并非完整意義上的流官政治。相較于從土司制度到經制州縣的“改土歸流”而言,清前中期對前朝衛所的裁撤、歸并及改置州縣,同樣屬于裁汰消解世襲制度的范疇。在未裁撤廢除之前,衛所與土司一樣,都是以世襲制度為支撐的地方管理制度,兼具轄土治民的地方政府職能,皆具地方政區(準政區)性質。在淘汰消解世襲制度的層面上,裁撤土司與取消衛所的目的一樣,都指向地方管理的流官體制。因此,廢除土司可謂“改土歸流”,裁撤衛所亦可稱之“改衛歸流”。
相對于“改土歸流”而言,“改衛歸流”的提法可能值得商榷甚至受到質疑。但是,不僅土司職官具有世襲特點,衛所職役同樣具有世襲的特點。因此,在消除世襲制度的意義上,衛所亦存在“歸流”問題。清政府裁撤前朝所設衛所,以其土田、戶口歸并或改置州縣的過程可稱之為“改衛歸流”。衛所同土司一樣,在很大程度上都屬于明朝問題在清代的延續,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改衛歸流”并沒有同“改土歸流”一樣得到學界認可并予以高度重視。已故明史研究專家顧誠先生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將清代衛所裁撤問題等同于“改土歸流”提出來,顧氏謂:
史學界對于雍正年間的“改土歸流”一直非常注意,發表的文章很不少。可是,對于雍正年間基本完成的并衛所入州縣、改衛所為府、州、縣這一觸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管理體制的改革卻很少有人注意。主要原因看來還是對明代的衛所制度缺乏研究,因而史籍中經常出現的衛所材料往往被忽略過去。[1]
時至今日,不僅明代衛所已成為明史研究的熱點,衛所的清代變革及其后世影響也逐漸受到學界重視。明代衛所的后世影響并不因清代衛所的裁撤而結束。在衛所裁撤之后的相當長的時間里,原衛所造成的插花地問題仍持續且大量地存在,屯田賦役與州縣民田在輸納方式與水平上仍存在較大差別,衛所基層社會結構與組織在其歸并州縣以后仍在相當程度上繼續存在,基于衛所移民及其在地化發展而形成的族群和文化仍然得到延續。關注明代衛所及其清代延續問題,不能至衛所裁撤為止,而應以之為新的起點,繼續討論衛所制度的長期實踐對基層社會所造成的深刻而持續的影響。本文提出“改衛歸流”的概念,并認為衛所的裁撤并不標志“歸流”的完成,其后續影響在經制州縣管理框架下的基本消弭才是“改衛歸流”完成的體現。
一、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
明代的衛所在清代仍然延續了很長時間,是因為大部分衛所皆有其管轄的地盤,它們對轄區內軍、旗、舍、余征收的子粒同行政系統的州縣征收的賦稅在數量上和方法上相距甚遠,力役制度也有很大差別[2]。面對衛所轄地與州縣轄地在賦役制度上的巨大差別,清政府對于前朝已經逐漸失去軍事職能的衛所只能暫時采取維持現狀的的辦法。針對衛所在清代的延續,顧誠先生指出:
衛所作為同州縣類似的地方管轄單位在清代大約存在了80多年,在此期間,都司、衛、所經歷了一個軌跡鮮明的變化過程。其特點是:一、都司、衛、所官員由世襲制改為任命制;二、衛所內部的“民化”、轄地的“行政化”過程加速;三、最后以拼入或改為州縣使衛所制度化作歷史陳跡,從而完成了全國地方體制的基本劃一。[1]15
顧氏著眼于明代衛所在清代的變革,指出清政府將衛所裁并或改置州縣,不僅明代衛所制度化作歷史陳跡,更是全國地方體制基本劃一的體現,標志著明朝政府所建立的在疆土管理方面的軍民二元體制的終結。李巨瀾強調清代衛所的存在,指出清代衛所制度是對明代衛所制度的改造和調整,其官員由世襲改為任命,職能由原先的軍事、經濟相結合轉變為純粹的經濟職能。衛軍改為屯丁和運丁,專事屯田與漕運,另外衛所還承擔著一定的民事職能[3]。顧、李二氏都在探討清代衛所變革問題,但出發點卻不相同。前者以明代衛所為出發點,落腳于清政府對前朝衛所的處置;后者以清政府借鑒和調整前朝衛所制度為出發點,旨在整體評價清代的衛所制度。清政府裁撤明設衛所的同時,在西北關西和湘黔苗疆等局部民族地區仍新設諸衛,仍以屯田支撐京畿漕運系統。
討論清代“改衛歸流”問題,其關注點在明代衛所制度及其實踐的清代延續,并非清代新設的關西或苗疆諸衛,也非清代的漕運諸衛。明代衛所作為地理管轄單位(或者說政區、準政區單位,實土、準實土單位),清代撤衛所實即以其土田、戶口歸并或改置州縣。
二、衛所裁撤與改置州縣
衛所裁并、裁撤或改置州縣的過程,《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一文已有梗概地梳理:清順治年間,衛所官員雖仍被視作武職,但其職責范圍同行政系統的府州縣官越來越接近,沿邊和在內衛所常有裁并之舉;清康熙時期,一方面保留了衛所名稱,另一方面又繼續了明后期的勢頭,把部分衛所改為州縣;而大規模的改衛所為州縣是在清世宗統治期間進行的[1]。
目前,對于衛所歸并或改置州縣問題,除了顧氏的整體論述外,大多是局部或個案的實證研究,例如明清潼關衛——潼關縣——潼關廳,蔚州——蔚州衛——蔚縣,九溪、永定二衛——安福縣——安福、永定二縣的變遷個案,都是清代衛所裁撤與州縣改置的典型案例。
臺灣于志嘉以潼關衛為例,指出潼關廢衛改縣,其初猶為兵餉供應、屯糧征收之便保持原潼關衛屯的完整性,然終究難抵屯地分散兩省十一州縣所帶來的困擾,逐步縮編成僅掌管潼關、華陰兩境內屯地的潼關廳,明初以來以“犬牙相制”為目的建立的機制一步步邁向土崩瓦解的境地[4]。
鄧慶平以明清蔚州為中心,梳理了明代蔚州州、衛分立到清代蔚州衛改設蔚縣的過程。明代蔚州與蔚州衛同城而治,二者在在戶籍編制、賦役征派方式等方有明確的區分,而在公共設施、文化資源、經濟利益的共享方面又打破了州——衛隔離的特點。清初,蔚州衛改為蔚縣,原州——衛系統下疆界糾葛、資源共享的狀態被打破,資源在新的蔚州一蔚縣系統下進行重新配置,矛盾和糾紛亦因之而起,這使得清廷幾次進行政區調整,最后以并蔚縣入蔚州的方式解決[5]。
孟凡松梳理湘西北九溪、永定二衛裁撤設縣的歷程,認為經過初設安福縣、再設永定縣等連續兩次設縣,才在田土、戶口歸屬的意義上最終完成了該地區的衛所裁撤問題。設置于雍正七年(1729年)年底的安福縣是直接裁革九溪、永定二衛的結果,它并未改變原衛所田土、戶口錯雜分布于各屬州縣境內的格局,也使得新設安福縣難以對其轄境實施有效管理。因此,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設永定縣,完全打亂原存民、屯田地原有的管轄格局,以保證州縣轄境的相對完整性為基本原則,在州縣之間對土地和戶口的歸屬作了相當徹底的調整[6][7]。
衛所裁并固然屬于清代行政區劃與地方行政管理體系調整的重要舉措,然而這一清代行政史上重大的改革,統治當局并無統一的規劃,也沒有與之配套的實施預案。在大多數情況下,衛所的歸并、裁撤或改置州縣都是分省進行的,甚至同一省區的衛所裁撤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易后難,分步實施。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種先裁撤衛所后解決具體問題的被動局面。裁撤衛所歸并或改設州縣,最初僅涉及“上層建筑”層面,原衛所田賦、徭役的征解額度、方式以及因之而構建起來的基層社會組織體系等“經濟基礎”領域并未涉及。因此,這就帶來了衛所裁并、改置州縣的后續調整問題,如插花地劃撥、屯賦調整與基層社會組織重構,都是“作為地理單位的衛所成了歷史遺跡”[1]之后,“改衛歸流”進一步深化的體現。
清代裁撤衛所并以其土田、戶口歸并或改設州縣,涉及明代沿邊、沿海、內地和在內衛所,從清初至雍正年間,屬于持續性、全國性的改革行為。據楊晨宇統計,有清一朝共有817個衛所被裁并,其中21個衛所經歷了裁并——復設——裁并的歷程,22個衛所為清代新設但之后也同樣被裁并,67個衛所被改置為府、廳、州、縣,衛所改置州縣主要集中于康雍乾三朝,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區[8]。關于清代衛所裁并、改置州縣的研究,誠如楊晨宇所言,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少數幾個史料記載比較豐富的區域和時段,而對于其他一些衛所裁并資料相對欠缺的地區和時段則少有問津,仍缺乏從全國范圍和整體角度來看的宏觀研究[9]。實際上,不僅全國范圍和整體角度的宏觀研究缺乏,且區域性、時段性的個案研究也仍不充分。有鑒于此,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宏觀視野下的微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基礎上的宏觀總結都應該得到重視。
三、插花地及其劃撥
清代裁撤衛所,或將之歸并州縣,或以之改設州縣,都要面臨原衛所田土與人口管轄權屬的轉移和管轄制度的調整問題。問題在于,明代衛所轄地多與鄰近州縣相互插花,其在邊疆、海疆與省際交界地區尤其嚴重。在清代裁撤衛所,歸并或改設州縣,插花地劃撥問題相應而生。
因衛所原因造成插花地在明代屬于相當普遍的現象,其在貴州表現尤其突出。馬琦等通過探討清末貴州插花地認為:清末貴州81%的縣級政區存在插花地,其中以安順、貴陽、鎮遠、思州、黎平等府親轄地及其附郭縣的插花地最為集中;貴州插花地眾多與其政區設置的方式有關,貴州府、縣政區或在原衛所屯田之地,或在土司所轄領地,或在剿撫土著居民聚居區設置,衛所、土司與原住民聚居區域相互穿插導致貴州插花地的產生[10]。楊斌認為明代的衛所、元明土司及“地隨人走”的地權轉移傳統等都屬于川黔交界地區插花地產生的原因[11]。
明代衛所在腹里地區的土地多通過開墾荒地、隙地,占種籍沒地等方式獲得,土地難以連片故多插花形態;而在沿邊民族地區,亦多墾辟強占原住居民或土司土地,故與土司、原住民土地呈插花形態分布。總之,由于明代衛所土地來源的特殊性和衛所曾長期存在的結果,插花地并非個案,也非裁撤衛所便可直接解決的。裁撤衛所,以其土田、戶口并歸州縣或改置州縣,插花地都是需要充分考量的存在。
無論是基于衛所、土司還是雕剿、投獻而來的州縣土田,之所以作為插花地問題長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及附著于土地的戶口,其承載田賦、徭役的水平及輸納、僉派賦役所依托的基層社會因應體系的差異。插花地不僅關乎政區轄地的空間問題,更在于轄地所彰顯的制度與身份差異。換句話說,若插花地僅是空間問題,以山川形便為前提,遵循就近劃撥州縣原則即可解決之;但若插花地是一個制度和社會問題,涉及田賦多少、徭役分擔、基層社會組織系統和地方精英利益及民眾的政區認同心理等,大多數情況下就不是區區州縣親民官所能調解的,非地方大吏親自主持且歷有年月難以成功。明代衛所造成的插花地問題,在衛所裁撤之后,仍歷至清代中后期乃至民國以后方漸次解決,其原因即在于此。關于明清插花地延續及其劃撥、消解的研究,仍有待于更多的分省研究或個案研究為基礎,方能作全國性和長時段的整體觀察。
四、屯田與屯賦調整
前述清代民國插花地劃撥的主要困難在其所承載的賦役水平和方式與鄰近土地的參差有別上。具體地說,在衛所裁撤之后,首要面臨的問題就是衛所屯賦水平的調整與屯丁的歸并問題。
對于明清衛所屯田的所有權形態問題,毛亦可認為應以清代雍正五年至七年(1727—1729年)的屯田私有化政策為界,之前完全為國有制,之后轉以私有制為主。屯田國有制時期又可區分為領種制和租佃制兩個階段,在明代宣德十年至正統二年(1435—1437年)“詔免正糧上倉”之后,屯軍逐漸擁有屯田的永佃權、田面權,這對屯田私有化起到關鍵作用。清代雍正年間,朝廷頒布屯田私有化政策,并在歸并州縣的衛所屯田中切實推行[12]。
從貴州的案例來看,衛所的土地包括屯田和科田,且衛所田土的私下交易在明中期已儼然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以故嘉靖《貴州通志》感嘆貴州土田的“欺隱之弊,逋負之奸”[13]卷3《土田》,277。“欺隱”針對土地權屬而言,詭寄飛灑,化屯作科,私相授受,皆謂欺隱;“逋負”針對錢糧而言,遷延不納,逃亡難追,皆屬逋負。雍正年間屯田買賣合法化,屯田交易由地下的、變相的形式轉變為公開的、合法的形式。據所見,不僅福建省的屯田契約文書展示了屯田交易實態的變遷[12],貴州黔中屯堡地區存在的關于水田、旱地的交易同樣體現了這一實態[14]。
但是,針對裁撤之后的衛所土地而言,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其是否存在私下的或公開的交易行為,而在于衛所屯田、科田與州縣民田及土司土民秋糧田之間存在的稅則、徭役上的差別。同一地域之內,若田制科則及輸納方式、水平存在較為顯著的差異,民間社會就會在彼此之間進行比較權衡,趨利避害,避重就輕,以此達到賦役規避的目的。孟凡松通過明清湘鄂西地區的考察證明,不同類型的政區意味著不同的賦役制度與管理方式,在土司、衛所與州縣權勢彼此消長的背景下,導致土司與州縣、土司與衛所、衛所與州縣之間彼此交織的種種土地糾紛與賦役規避問題。清雍正間,通過改衛歸流與改土歸流,三者之間的土地與賦役糾紛隨著衛所、土司的取消與州縣政區主體地位的確立而逐漸消弭[15]。
為了避免或減少民間社會的賦役規避現象,調整民、屯賦役水平及征派方式,使之相近甚至相同就有了政策上的必要。但是,受定額財政體制的限制,州縣地方在賦役調整方面的主動性是相當有限的。屯賦的調整,除了自上而下地執行相對簡單外,自下而上的申報常常難上加難。清代湖南寶慶屯賦調整一案,經歷順康雍乾四朝,多任督撫申報才最終實現就是最好的證明①。清代貴州安平縣(后改平壩縣)也存在嚴重的“改屯作科”問題,屯田賦重而科田賦輕,賦重則價低,賦輕則價高,屯田擁有者為追求較高的土地售價,遂將之當作科田售賣,而自己承擔改屯作科造成的田賦差額,是即“改屯作科”,“甘納空糧,以圖受價”者也[16]卷4《田賦》,77-78、82。
屯田賦役調整水平和征收方式,使之與州縣民田所承載的賦役相一致,是清代康雍乾時期地方賦役制度改革與調整的重要內容。清代州縣賦役多列有“屯賦”名目,但大多研究者對于屯賦、民賦之間的區別以及這種區別對地方社會的意蘊卻不甚留意。施劍等在關注貴州衛所裁撤的同時,已注意其屯田的處置問題[17]。相對于衛所裁撤而言,屯田處置其實是脫節和滯后的。這種滯后性恰恰凸顯了州縣民田和原衛所屯田、科田之間的差別。民、屯科則及戶丁徭役的差別,給地方政府征收田賦、派發力役等皆造成了一定的困境,也為民間社會的賦役規避提供了契機,這也是因衛所等原因造成的插花地問題長期存在且在衛所等裁撤以后仍難以解決的根本所在。州縣官員在應對這一問題時,除了一再呼吁、個案處置或想方設法使田賦有具體村寨及戶丁承擔以保障足額征解錢糧外,在均平賦役、調整科則方面則受制于定額財政制度和“舊例”“舊額”的傳統約束,幾乎難有作為可言。
目前,諸如寶慶府或安平縣之類基于府州縣等局部視域的屯賦調整案件的研究仍相當缺乏,而這類事件在內地、沿海與沿邊仍有較多的存在,尚有鼓勵個案研究的必要。當然,以個案關注為基礎,進一步對屯田賦稅及戶丁徭役變革作分省區或全國性的宏觀探討也是值得期待的。
五、衛所基層組織的因襲與里甲重構
衛所撤并或改設州縣之后,原衛所轄區以屯旗、屯堡為單位的基層組織或被編入州縣里甲體系,或因衛所原有基層組織體系而整頓調劑之。在衛所改設州縣或衛所影響地方社會較為深遠的地區,歸并或改設州縣之后,原衛所基層社會組織體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下來。考察這類地區的基層社會結構與組織形態,仍需要溯源衛所制度的明代實踐。
因應于地方政府在戶籍、賦稅與征役等方面的制度差異,諸如里甲之類的基層社會組織體系,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為了對應賦役征發而存在的。因此,改衛歸流落實到基層社會的時候,原衛所的基層組織體系也要作相應的調整,以適應新的州縣管理體制和理念。在西北、西南不少地區,由于衛所基層組織曾長期存在,即使它們經歷過清代里甲組織體系重新改編整頓,但至今仍有大量鄉鎮村寨的地名保留了衛所基層社會組織留下的痕跡。清代改衛歸流體現在基層社會組織體系上,就是原衛所屯堡組織的里甲重組。明代衛所相當部分屯、科土地交錯在州縣、土司境內,二者科則不同,輸納各異,歸屬不同的管理系統。清代以之歸并或改置州縣,必然重建或調整里甲系統以接納、消化這部分田土、戶口,就不得不面對原來衛所的基層組織系統,并只能在此基礎上因革損益而為之。
前述于志嘉、鄧慶平等人的研究已經注意到衛所裁撤之后,其原有基層組織的沿襲、變革及州縣里甲體系在此基礎上的整頓重構問題。然而,衛所裁撤導致的州縣里甲重構作為康熙、雍正以后相對普遍的存在,僅有邊疆或民族地區的少數個案研究顯然不夠,討論衛所影響的逐步消解問題也必然將視角“下移”基層社會,從里甲組織乃至民間社會的因應上進行觀察。
六、明代衛所的后世遺產與清代改衛歸流的歷史評估
明初所構建的軍、民二元管理體制以及與之相輔而行的漢、土二元管理體制,秉持“軍民分際”與“漢土分際”的統治原則執行了二百數十年,即使明中后期衛所行政化(州縣化)與土司政治中的流官滲透在整體上不斷加強,但該二元體制仍長期存在,該統治原則長期執行所產生的深遠歷史影響卻不能因改朝換代或改弦更張而被低估或忽視。明朝疆土管理體制是由軍事和行政兩大系統構成的,這種二元體制自有其建立、延續和消解的過程。明代衛所在清朝的階段性存在及其最終裁撤,實際上是明朝疆土的二元管理體制在清代延續和消解的體現。裁撤政區(地理)意義上的衛所僅僅是二元體制在“上層建筑”(政區)層面的消除,但并不意味著其在“經濟基礎”(社會)層面的結束,這就是清代“改衛歸流”研究的起點和價值所在。
前文所述清代“改衛歸流”所涉及的州縣政區調整、插花地劃撥、基層社會的賦役調整和里甲重組等,歸根結底都是清朝中央與地方為消除前朝軍民二元體制所作的努力。明朝的疆土由行政系統和軍事系統分別管轄,也即軍事與行政系統的二元體制,這個問題顧誠先生在《明前期耕地數新探》《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等文中已有充分的論述。然而,如何接收消化這種體制,鞏固其既有成果,并消解其消極影響,卻成為清朝前中統治者必須面臨的重要問題。清代“改衛歸流”,對政府而言,即廢除明代軍民二元體制并消解其消極影響過程;對于民間社會來說,即軍民二元體制從制度層面瓦解之后,面對州縣管理體制如何應對和調適的問題。
清代的改衛歸流,不應該僅僅被看成是裁撤衛所歸并或改設州縣的行政行為,它應該包括上述衛所插花地劃撥、屯科賦役調整、屯堡到里甲的社會組織重構等“落地”于基層社會的諸多體現,而這些深層次的社會經濟變革必須通過長期漸進的因應、調整方能實現。
討論清代改衛歸流問題,必須將之置于整個明代二元體制建立、延續及其清代調整、消解的整體性、連續性視野中考察。至明朝中后期,這種軍民二元體制已然造成持續而嚴重的消極影響,諸如川滇黔、湘黔桂等省區交界區域的犬牙相制不再具有預期的制度成效,“黔府湖衛”或“州衛同城”“司衛同城”導致的矛盾沖突難以調節。但是,所有這些也不能否認它在維系明朝疆土管理及拓展中國地理與文化邊疆過程中的重大意義。清代改衛歸流正是消弭明代軍民二元體制的消極影響,鞏固其既有統治成果的自然趨勢。可以說,更加積極地評價明代衛所與衛所制度的后世遺產,評價明代軍民二元體制發生的必然性與階段性,評價清代改衛歸流“落地”于基層社會的歷史價值是必要的。
注釋:
①道光《寶慶府志》等諸種地方志均較為詳盡地記載了原寶慶等衛屯賦在清中前期艱難調整的歷程,而相關研究成果則仍未刊布。
參考文獻:
[1]顧誠.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8(2):15-22.
[2]顧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J].中國社會科學,1986(4):193-213.
[3]李巨瀾.清代衛所制度述略[J].史學月刊,2002(3):36-40.
[4]于志嘉.犬牙相制:以明清時代的潼關衛為例[A].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9(80—1).
[5]鄧慶平.衛所制度變遷與基層社會的資源配置——以明清蔚州為中心的考察[J].求是學刊,2007(6):150-155.
[6]孟凡松.安福、永定二縣的設置與清代州縣行政管理體制在湘西北的確立[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1):81-86.
[7]孟凡松.衛所沿革與明清時期澧州地區地方行政制度變遷——以九溪、永定二衛及其屬所為中心[J].歷史地理,2008(1):53-64.
[8]楊晨宇.清代衛所裁并總論[J].史志學刊,2017(3):6-13.
[9]楊晨宇.清代衛所裁并研究綜述[J].史志學刊,2017(6):83-91.
[10]馬琦,韓昭慶,孫濤.明清貴州插花地研究[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122-128.
[11]楊斌.明清以來川(含渝)黔交界地區插花地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12]毛亦可.論明清屯田的私有化歷程[J].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2):35-48.
[13]嘉靖《貴州通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1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
[14]孫兆霞.吉昌契約文化匯編[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15]孟凡松.賦役制度與政區邊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區的考察[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2):60-69.
[16]道光《安平縣志》[M].中國地方志集成·貴州府縣志輯(第44冊),成都:巴蜀書社,2006.
[17]施劍.清前期貴州衛所之裁撤及其屯田處置[J].歷史檔案,2014(2):5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