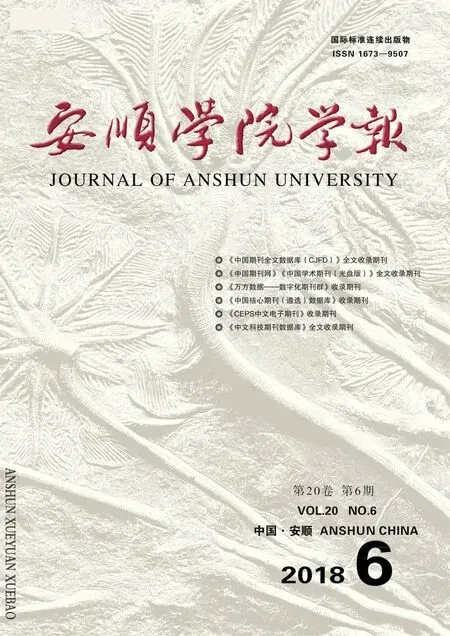接受與創新:兩部《灰闌記》的差異性比較
翁 瑜
(安順學院人文學院,貴州 安順561000)
中國元代的李行道是一位閉門讀書、不問世事的“高隱”,在元代及其后都并非大家,所作的雜劇也僅有傳世的《包待制智勘灰闌記》(以下簡稱《灰闌記》),但卻是古代中國較早傳入歐洲并產生較大影響的戲曲作品。李行道的《灰闌記》在情節上與《圣經·舊約》中所羅門斷子案很相似,所以這個戲曲傳入西方后立刻引起了人們的閱讀興趣,很快被譯為法文、德文,流傳甚廣。1924年,德國著名導演萊茵哈特(Reinhardt)將它搬上戲劇舞臺,獲得極高贊譽。“自此以后,西方人一反以往偏執輕視的態度,開始努力不懈地來了解東方各國的藝術文學。”[1]20世紀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在柏林觀看此劇的演出之后,激動不已,由此觸發了他的創作沖動。但由于各種原因,直到16年后才完成他對《灰闌記》的第一次翻新——《奧格斯堡灰闌記》,這為他1944年創作完成著名作品《高加索灰闌記》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在20世紀的西方劇壇上,布萊希特對中國戲劇情有獨鐘,他的戲劇創作與中國的淵源較深,他的主要作品幾乎都有中國文學的影子,他也成為深受中國文學影響的一個典型。他借鑒了李行道《灰闌記》的情節模式,善于改編并創新,創作出了著名的《高加索灰闌記》,這部作品在形式與內容上都體現了他獨特的藝術技巧與創作思想,并且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重要作品。布萊希特在《高加索灰闌記》楔子《山谷之爭》中就明確指出:劇本故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傳說。它叫《灰闌記》,從中國來的。”[2]但布萊希特雖以李行道的《灰闌記》為藍本進行創作,卻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極有新意的再創作。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在主題思想內涵、人物形象、情節發展模式方面都表現出了與原作的差異性。
一、主題思想內涵的差異
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與李行道的《灰闌記》具有相同的主題——“灰闌斷子”,所不同的是,李行道通過“灰闌斷子”表達了東方血親倫理、宗法關系至上的觀念以及對社會吏治黑暗的控訴。而布萊希特則將這個故事置換在新的時代,并賦予新的靈魂,表現了布萊希特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和倫理意識。兩劇在主題思想內涵的表達上存在較大差異。
1.“親者原來則是親”
李行道的《灰闌記》是一部公案劇,描寫張海棠為家計所迫淪為妓女,后從良于員外馬均卿,并得寵生下一子名壽郎。馬員外正妻與州衙趙令史私通,嫉恨張海棠,于是以毒藥害死馬員外,又買通鄉鄰證言,誣告張海棠謀殺親夫、強奪人子,企圖將壽郎收為己有并達到霸占馬員外財產的目的。包拯審案時發現端倪,無奈無人作證。于是以“灰闌斷子”,命馬員外正妻和張海棠對拉闌中之子,而張海棠恐孩兒受傷不忍用力,包拯據此斷定孩子生母,張海棠得以洗刷冤屈并得到了孩子及財產,奸夫淫婦最終受到法辦。
包拯正直無私、秉公執法,他對人性之母愛有著深刻的理解,并以母愛作為標尺檢驗了真假母親,最終確定了生怕孩子受傷不敢用力拉扯的張海棠生母身份,劇本在突出包拯超人智慧的同時,也表現了母愛的無私與可貴。包拯不僅將孩子歸還生母,而且把家產也判給了張海棠。子承父業在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中天經地義,男孩天然享有財產繼承權,這種繼承權是以血緣關系為重要基礎的,“孩子歸誰”其實在傳統社會中隱含了財產歸誰的判斷,這種繼承關系是幾乎所有傳統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張海棠得回親子及財產的情節正表現了東方血親倫理、宗法關系至上的觀念。正如劇本中提到的“親者原來則是親”[3],突出表現了對倫理血親關系的重視。同時,李行道也通過張海棠的不幸遭遇表達了對社會吏治黑暗的控訴以及對清明政治的期盼,體現了特定時代的社會內容與思想烙印。
2.“一切歸屬善于對待的”
李行道《灰闌記》中清官包拯根據“親者原來則是親”的倫理血親原則將孩子判給了親生母親,而布萊希特卻獨具創意,將孩子判給了“善于對待的”人,這種人道主義思想的表現使得劇本主題思想具有了全新的意義。
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通過劇中劇的手法展開故事,借用中國的古老傳說解決了山谷歸屬的爭端問題。劇本講述了格魯吉亞發生貴族叛亂,大公不知所蹤,總督被殺,總督夫人在逃離之際,只想到自己的漂亮衣服、精致靴子,卻將自己的幼子棄之不顧。女仆格魯雪冒險救下和自己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并帶著孩子艱難逃亡,為孩子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含辛茹苦地撫養孩子。戰亂結束后,總督夫人為謀得遺產而要強行索回孩子,將格魯雪告上法庭,法官阿茲達克最終將孩子判給了養母格魯雪。
在劇中,法官阿茲達克雖然也以“灰闌斷子”,但是孩子卻沒有判給親生母親而是判給了與孩子沒有血緣關系但對孩子付出了無私真愛的養母格魯雪,突出表現了格魯雪對孩子不是親生勝親生的無私母愛。劇本表現的不再是一個丈夫與兩個女人的故事,而是明確代表著對立階級的主仆之爭。格魯雪不愿將孩子交給總督夫人,為的是怕孩子養成富貴的壞蛋,“穿上金縷鞋,長出鬼心眼……心腸變石頭……日夜刮歪風。”[4]她從小讓孩子力所能及地勞動,“教孩子對大家都和善。”[5]讓孩子明白以善待人的樸素道理。最后格魯雪和戀人西蒙得回孩子,并沒有繼承總督的財產,而是將之用于兒童樂園的興建。劇本結尾的一首詩表達了作品思想內涵的升華:
《灰闌記》故事的聽眾,
請記住古人的教訓:
一切歸善于對待的,比如說
孩子歸慈愛的母親,為了成材成器,
車輛歸好車夫,開起來順利,
山谷歸灌溉人,好讓它開花結果。[6]
布萊希特通過戲中戲的故事,闡述了一切事物都應歸屬善于對待的樸實哲理。看到這里,觀眾自會領悟到戰后山谷的歸屬問題如何解決。布萊希特雖套用的是中國古代戲曲的情節,但卻為解決現實存在的矛盾提供了經驗和啟示。
布萊希特生活在發展創新的時代,在他身上跳動著社會進步的脈搏,他一直以來堅持的社會理想早已內化為奮進的精神、變革的力量。他打破了倫理血緣的母子關系,以個體事件得出普世的原則,認為孩子歸慈愛的母親、車輛歸好車夫、山谷歸灌溉人,一切都應歸屬善于對待的,這句話既點明了全劇的主旨,也賦予了母愛新的思想內涵,使得劇本主題體現了一種嶄新的時代精神。正如劇本中所提示:“哦,大人物的盲目!他們好像永遠是來去自如,騎在佝僂的背上不可一世,不提防雇用來的拳頭,信賴他們保持到年深月久的權勢。但是,長久并不是永遠。哦,時代的變遷!人民的希望!”[7]主題的表現與時代的發展遙相呼應。對此,前蘇聯學者喬爾娜雅和梅里尼柯夫說,《高加索灰闌記》中“包含著重大的社會沖突和高度的社會熱情,其主要目的在于改造社會。”[8]
二、人物形象的性格差異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布萊希特筆下的人物形象與李行道《灰闌記》中的人物明顯存在對應關系,即“二婦一子一法官”。李劇中二婦是馬員外的大渾家和小妾張海棠,敢于為民伸張正義的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包拯。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中二婦是生母總督夫人與養母格魯雪,法官是出身下層的阿茲達克。盡管兩劇人物存在明顯的對應關系,但是對二者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明顯的不同,布萊希特筆下的人物與原作相比,更體現了現實性與時代性,具有深厚的思想內蘊。
1.真假母親——張海棠與格魯雪
張海棠與格魯雪分別是兩劇的女主人公,她們都處于社會生活的底層,都為孩子付出了真愛,最后孩子也判給了她們。但是細究之下,兩人在性格及命運上都存在差異,同時也分別承載著不同的社會意義。
李行道《灰闌記》中的張海棠作為妾室,在封建社會中無疑是地位低下的,而她曾為娼妓的身份更使她低人一等。她善良本分但性格柔弱,從良于馬員外之后雖得到馬員外的憐惜和照顧,卻在大渾家的嫉恨中畏畏縮縮,從不敢有所埋怨。在哥哥急需資助之時雖有心卻無力,才讓大渾家有了可乘之機,繼而被誣私通殺夫,此時的張海棠也只想到苦苦哀求大渾家放過她和孩兒。她既不懂得官場的奸詐,也不了解人心的險惡,最終在昏官的嚴刑拷打下屈打成招,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毫無反抗之力,只能絕望地哭訴自己的不幸,并將洗刷冤屈的希望寄托于清官的出現。“則您那官吏每忒狠毒,將我這百姓們忒凌虐。葫蘆提點紙將我罪名招,我這里哭啼啼告天天又高。幾時節盼的個清官來到。”[9]張海棠作為封建社會的弱女子,沒有能力扭轉自己的命運,面對不幸,只會痛哭流涕、聽天由命。幸虧包拯在重申此案時發現端倪,巧用“灰闌斷子”分辨出真假母親,張海棠才得以沉冤昭雪。
李行道筆下的張海棠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傳統婦女形象,嫁做人婦后恪守婦道,以夫為天,生活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遇事毫無主見,缺乏人格上和行動上的獨立性,遭受大渾家的陷害之后,哭哭啼啼,除了寄希望于清官之外,沒有反抗精神和自救能力,而布萊希特筆下的格魯雪卻截然不同。
《高加索灰闌記》中孩子的養母格魯雪雖然也出身下層,但卻勇敢剛毅,富有反抗精神,為與自己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無怨無悔地付出,和逃命時只顧帶走漂亮衣服和精致靴子的孩子生母相比更高貴。弩卡城發生暴動時她并不是主動要搭救總督的孩子,而是混亂中孩子被轉手到她懷中,此時的她完全可以扔下孩子趁亂逃走,畢竟她與孩子沒有血緣關系,也沒有照顧孩子的義務,而且此時暴動者懸賞一千元斬殺總督之子,和孩子在一起就意味著危險。但是正直善良的格魯雪沒有扔下孩子,在確定不會有人來搭救孩子之后,她毅然將孩子抱走,從此陪伴孩子踏上了逃亡之路。在逃亡的過程中,格魯雪無微不至地照顧孩子,寧可自己挨凍受餓也不愿委屈孩子。不惜用自己兩個星期的工資買一壺奶;在孩子餓得直哭時無奈將自己的乳頭塞到孩子口中,而她還是一個未婚姑娘;在救走被追兵發現的孩子時,格魯雪情急之下用木棍打傷了鐵甲兵;為了躲避鐵甲兵的追捕,她抱著孩子冒著生命危險沖過橋身一半已經摔向深淵的索橋。經歷了這一切的格魯雪再也不愿與孩子分開,把他當做自己的孩子來疼愛。善良的格魯雪為孩子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也許一開始她只是出于善心救下孩子,但在與孩子患難與共的相處中,她和孩子之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她對孩子的愛心早已超出了血緣關系,她為孩子的安然成長傾其所有,她為養子的無私付出與張海棠為親子受難兩相比較,更彰顯了她善良人性的可貴,高尚品質的偉大!而作家也意在通過格魯雪從少女成長為母親的過程,闡明“孩子應歸慈愛的母親”的樸素真理,突出了這種具有真情實感的母子關系遠超于只有血緣的自然關系,使格魯雪的形象也因此更真實更感人。
兩部《灰闌記》都以真假母親的行為對比表現了母愛的偉大。不同的是李行道在劇中以假母親的狠心突出了真母親的親情,而布萊希特則是以真母親的功利反襯出假母親的高尚。真母親張海棠老實本分、生性懦弱,面對邪惡勢力的迫害無力反抗;假母親格魯雪勇敢堅韌、正直善良,為一個與自己毫無血緣關系的孩子歷經磨難、嘗盡艱辛,不是母子似母子,不是親生勝親生。她對孩子的愛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母愛,體現了一種人性之美的升華。在兩者的對比中,顯然情義重于血緣。布萊希特以格魯雪的勝利表明詮釋了新的社會關系,“親者原來則是親”固然有天然的血緣關系,但是人與人之間情義更重要,如果沒有發自內心的愛與真情,有血緣關系的母子也不是真正的母子,如果有了這樣的情義,天然的血緣關系也無法與之相比,沒有血緣關系的母子也能成為真正的母子。布萊希特理想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就應該是這種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而以真情實感為依據的和諧狀態。
2.真假法官——包拯與阿茲達克
李行道筆下的包拯與布萊希特筆下的阿茲達克都敢于為人民伸張正義,不畏強權。在劇中他們都主持正義,將孩子判給了真正愛護他們的人。兩位作家作為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創作者,他們投射在人物身上的情感以及所表現的價值觀念是不同的。包拯與阿茲達克在性格表現上也存在差異,包拯的形象較為類型化,而阿茲達克的形象則彰顯個性化特征。
元代吏治黑暗、冤案不斷,受盡強權欺壓的貧苦百姓迫切期望能夠出現鋤奸懲惡的清官,包拯的形象正迎合了人們的這一心理愿望。李行道《灰闌記》中的包拯為官數十載,為人剛正不阿。他受皇帝欽命,自覺維護正義、懲治奸惡,對貪官污吏絕不包庇姑息。斷案嚴謹認真,以是否觸犯律法為根據,毫不偏頗。既不錯判一個好人,也絕不放過一個壞人。在“灰闌斷子”中秉公執法,以倫理血親關系為依據,將孩子判給生母張海棠,也為張海棠洗刷了冤屈。他清正廉明、愛民如子、維護公平正義的形象深入人心。性格表現堪稱完美,沒有一絲缺陷。在很多包公戲中,人們都是按照既定的模式欣賞這個形象,包拯就是剛正不阿、公平正義的代名詞。
《高加索灰闌記》中法官阿茲達克對應原作中包拯的形象,但是這絕非是一種簡單的對應,與包拯相比,阿茲達克的形象較為復雜豐滿。雖然阿茲達克和包拯一樣敢于為民做主、伸張正義,但秉性卻與包拯不同,甚至存在著一些原則上的區別。阿茲達克出身下層,包拯則是正規科班出身;阿茲達克在混亂中被鐵甲兵擁為法官,包拯則是皇帝欽命;包拯一身正氣,既不屈從于權貴也不偏頗于百姓,他的原則便是朝廷律法,不管何人觸犯,一律依法處置,毫無人情可言。而阿茲達克滿口粗言,審案就像是胡鬧,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且有意識地偏向窮人。“灰闌斷案”中,包拯以事實為依據,根據“親者原來則是親”的道理,將孩子判給了生身母親張海棠;而阿茲達克斷言,真正的母親會從灰闌中拉出孩子,但卻在總督夫人兩次從灰闌中拉出孩子之后,當面出爾反爾,將孩子判給了養母格魯雪。顯然阿茲達克的這種斷案方式和素有“青天”之稱的包拯有很大的不同,他既不以律法制度為標準,也不以事實為依據。表面上看來是一個無賴醉鬼隨意作出的判決,而實際上在隨意之下他有自己的原則,那就是維護窮人的利益,懲治富人。
包拯是典型的清官,沒有一絲缺陷,完美無缺,是公理正義的化身,他剛正不阿、堅持律法、明斷是非的性格表現已經成為一個固定的模式,他的形象也是類型化的。而阿茲達克的形象則充滿矛盾,從外表上看,他沒有一點法官應有的莊重嚴肅,放浪形骸、玩世不恭、酗酒貪杯,甚至理所當然地收受賄賂,但在他貪利、滑稽、糊涂的外表之下,卻有一顆正義、嚴肅、理智的仁心。這個形象內外矛盾的性格表現,體現了真實的生活存在,是一個血肉豐滿、性格復雜的人物。
通過對劇中主要人物的對比,可以看出《高加索灰闌記》在塑造人物時,雖對《灰闌記》有所借鑒,但《高》劇中格魯雪和阿茲達克的形象更豐滿、更復雜,也更真實。而且布萊希特力圖刻畫兩個身處下層的普通人心地善良、品德高尚,突出表現了他的現實思想與政治立場。顯然,布萊希特是從階級的角度區分善惡,富人富有但為富不仁,窮人貧窮卻品德高尚,布萊希特正是從財產關系界定階級關系,繼而界定人的道德狀況。正如前蘇聯學者喬爾娜雅和梅里尼柯夫所評價的,布萊希特在《高加索灰闌記》中“為我們塑造了來自民間的英雄人物形象,他們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動。”[10]他們“都是特定階級的代表人物的社會性格。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暴虐,貪婪,殘酷,寄生性;而另一方面卻是人性,寬和,善良和勤勞。”[11]從這個意義上說,《高加索灰闌記》具有比李行道的《灰闌記》更加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思想意義。如果說李行道的劇本突出表現的是人性的善惡,那么《高加索灰闌記》則在表現人性善惡的同時更帶有濃厚的階級色彩。
三、情節結構與表現手法的差異
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與李行道的《灰闌記》雖然情節發展模式相似,都是好人與壞人之爭,但是布萊希特在情節結構上進行了自己的獨特創新,在保留李劇“二母爭子”和“灰闌斷案”基本情節的基礎上,將李劇單線結構改變為劇中劇的結構,并且在表現手法上將中國古代戲曲中的“自報家門”發展為他倡導的戲劇表演的“陌生化”,通過對故事的“間離”,成功阻止觀眾的移情,使觀眾始終保持在理性的層面上欣賞戲劇,不把自己沉迷在故事之中,從而能夠對戲劇作出理性的思考與判斷。
1.《灰闌記》的單線結構與自報家門的表現手法
元雜劇一般采用單線型結構。單線型結構的特點是情節較為集中、內容簡單精煉、主要人物少,而且一般以順時敘事的方式展開故事,以一人一事為中心,略去旁生枝節,緊扣核心事件情節進行敘述,表現故事發生、發展、高潮、結局的全過程。這種單線敘述方式,能夠將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故事情節也較為完整統一。在場次安排上一般為“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四折一楔子”,即每個劇本由四折戲和一個楔子組成。所謂“折”就是全劇矛盾沖突的自然段落,即開端、發展、高潮、結尾四個階段。元雜劇在四折戲之外,為了交代情節或貫穿線索,往往在全劇之首或折與折之間加上一小段獨立的戲,稱為“楔子”。相當于現代劇的序幕,用來說明情節,介紹人物。
李行道的《灰闌記》是中國元雜劇典型的“一楔四折”。在楔子中首先自報家門,自報家門是中國古代戲曲中介紹人物的一種傳統手法,是戲曲中主要人物出場時的自我介紹。一出場首先把角色的名姓、家世、來歷介紹給觀眾,讓觀眾知曉了前因,也明白了即將發生的后事。李劇楔子中第一位上場的是張海棠的母親,通過她的自述,觀眾了解到張家由于“家業凋零,無人養濟”[12],無奈之下只得靠女兒張海棠賣俏求食。接下來出場的依次是張海棠哥哥張林、張海棠和員外馬均卿,張林自述因為妹妹“辱門敗戶”羞于見人,前往汴京投靠舅舅。馬員外坦言與張海棠兩意相投想將她娶回家。張海棠不堪忍受哥哥的辱罵,為擺脫困境、養活母親,愿意嫁與馬均卿。在楔子中,通過劇中幾位人物的自述,觀眾弄清楚了故事的緣由以及人物之間的關系。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四折的情節內容緊湊,矛盾集中,按照時間順序展開故事。張海棠以為嫁給馬員外后,“伴著個有疼熱的夫主”[13]能夠苦盡甘來,誰曾想陰險狠毒的大渾家為達到與趙令史雙宿雙棲的目的,不惜害死親夫,嫁禍無辜。張海棠不可避免地落入大渾家設下的陷阱,繼而被貪圖錢財的昏官認定為殺人兇手,眼看就要失去親子,冤死獄中,幸而被明察秋毫的包拯發現端倪,通過灰闌拉子之計智斷真假,最終平反了這場冤假錯案。
《灰闌記》以元雜劇常用的單線敘述模式,展示了兄妹矛盾、妻妾矛盾的產生發展,以“灰闌斷子”為點睛之筆,以孩子的歸屬作為斷案的關鍵,分辨真假善惡,最終善惡因果終有報。整個劇本結構緊湊,楔子說明事件緣起、人物關系,為以后情節的發展做好鋪墊,開場之后很快就將人物之間的矛盾呈現在觀眾面前,如兄妹矛盾、妻妾矛盾,隨著矛盾的點燃和爆發,高潮迭起,情節的展開步步緊逼、環環相扣、不枝不蔓。這種集中緊湊的單線敘述模式使得觀眾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張海棠如何遭到大渾家陷害、又如何得以平冤、最終親子失而復得的主線上,不受旁枝末節的干擾,顯得嚴謹而縝密。
2.《高加索灰闌記》雙線結構和“陌生化”的表現手法
布萊希特在套用李行道《灰闌記》結構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創新,將李劇的“一楔四折”改為“一楔五幕”,并以雙線敘事模式取代了李劇的單線敘事模式。他不僅在戲劇結構上進行了創新,而且在劇中創造性地使用了“陌生化”的表現手法。
《高加索灰闌記》的正劇中有兩條主線:女仆救子和法官斷案。這兩條主線在第五幕“灰闌斷案”中合并,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與“楔子”構成劇中劇的情節模式。
正劇的內容分為五場,第一場“貴子”、第二場“逃奔北山”、第三場“在北山中”、第四場“法官的故事”、第五場“灰闌斷案”。前三場以格魯雪為中心,講述她帶著被遺棄的孩子四處逃亡,歷盡艱險,與孩子建立深厚感情的故事。這個部分的情節發展緊張激烈、扣人心弦,以塑造格魯雪的性格為中心展開故事,觀眾完全不會想到戲劇還有另外一個主人公。而在第四場《法官的故事》中,布萊希特卻集中刻畫了一個好酒貪杯、荒唐滑稽的法官形象,他玩世不恭卻沒有惡德敗行,酗酒貪杯卻又頭腦清醒,他貪財受賄卻又不收刮斂財,且不讓行賄者勝訴。他行事看似毫無章法,實際維護窮人的利益,是人民大眾的“青天”。阿茲達克陰差陽錯成為法官,他的審案令人啼笑皆非,戲劇氣氛也從緊張激烈轉變為詼諧幽默。顯然,布萊希特是將格魯雪和阿茲達克作為劇中的主要人物在各自的線索中進行形象演繹,最后兩人在第五幕中交匯,將戲劇矛盾推向高潮,通過“灰闌斷案”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從內容上看,《高加索灰闌記》的“楔子”與正劇情節似乎沒有關聯。楔子名為“山谷之爭”,講述兩個集體農莊在戰后為一條山谷的歸屬問題發生了爭執,加林斯克牧羊農莊是這個山谷原來的擁有者,由于德寇的入侵不得已而遷移。臨近的羅莎·盧森堡蘋果栽植農莊在戰爭中來到這個山谷與敵人展開游擊戰,戰后認為山谷理所當然歸自己所有,而且他們認為這個山谷牧草的長勢并不好,發展經濟林栽植蘋果和葡萄更能物盡其用。經過專家的論辯,最后是羅莎·盧森堡蘋果栽植農莊獲得了山谷的所有權。為了表示慶祝,他們演出了“高加索灰闌記”。
一般來說,元雜劇的“楔子”往往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交待故事緣由并為故事的展開做好鋪墊,因此“楔子”與正劇情節之間關系密切,而《高加索灰闌記》的楔子似乎游離于情節之外。但實際上布萊希特是創造性地使用了“陌生化”的表現手法,有意而為之。
“陌生化”是布萊希特戲劇理論與美學思想的重要概念,德語為Verfremdung,意為間離或異化。“間離”意味著使事物變得陌生,在“灰闌故事”中布萊希特逆轉了原作的故事情節,中國版故事中是生母得到了孩子,而在布萊希特故事中是養母得到了孩子,這種判決對觀眾而言的確是“陌生”的,這就使得觀眾能夠在這種陌生感的刺激下不會一味接受舞臺上演出的事件,而能有自己的理性思維。
從表面上看,楔子中的農莊之爭與正劇中的孩子之爭沒有情節上的關聯,但事實上,布萊希特在對故事的“間離”中誘發觀眾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阿茲達克之所以將孩子判給養母格魯雪是因為她真正愛這個孩子,而在楔子中,羅莎·盧森堡蘋果栽植農莊之所以獲得山谷的所有權也是因為他們能更好地開發這片土地,最終“一切歸屬善于對待的”。布萊希特在戲劇創作中,力求舞臺上展示的事件既要讓觀眾覺得是真實的生活,同時又清醒地認識到是藝術虛構,在真實生活與藝術虛構之間有意設置的距離中,讓觀眾始終能以一種旁觀者的身份作出理性的判斷。
李行道的《灰闌記》作為在西方產生較大影響的中國戲曲,在與西方文化交融之后必然會與原作存在較大差異。布萊希特對中國戲曲的改編不是簡單模仿或者照搬,而是在吸收借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融入20世紀的理念與思想。可以說布萊希特的戲劇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個典型。他終身的藝術伴侶海倫·魏格爾說過,“布萊希特的哲學思想和藝術原則和中國有著密切的關系,布萊希特戲劇里流著中國戲劇的血液。”[14]對于同類作品而言,對比閱讀通常是了解作品的有效手段,尤其是通過兩者鮮明的差異性進行分析,能夠挖掘作品背后蘊含的深刻涵義。通過兩部作品的比較,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戲曲對西方戲劇的影響,但因不同的文化環境而使兩者各有特色,也各有所長。在文學交流的長河中,應互相借鑒,從而促進自身的不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