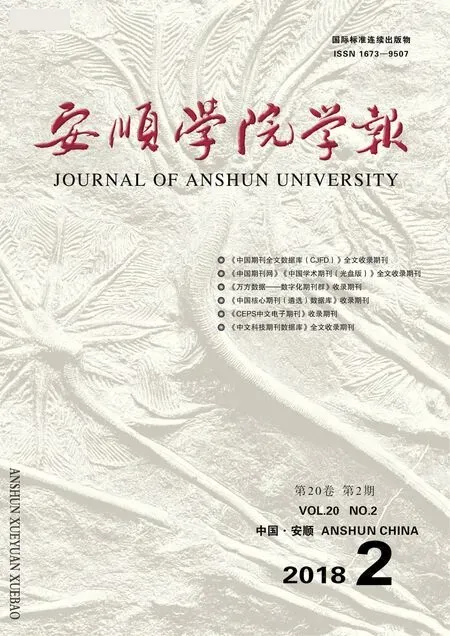玉汝于成:賦學文獻研究的新境地
——評蹤凡教授《賦學文獻論稿》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 貴陽550001)
當前,學界的賦學文獻研究如火如荼,呈現總結集成之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賦學文本資料的匯編與整理,如2014年湖南文藝出版社歷時20年出版的《歷代辭賦總匯》,是有史以來最大最全的賦體文學總匯。而許結教授歷時多年打造的《歷代賦匯》(點校本)亦即將面世。二是賦論資料的選編,如王冠《賦話廣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孫福軒《歷代賦論匯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等,尤其是以首都師范大學蹤凡教授《歷代賦學文獻輯刊》(全200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的出版最為卓著。中國賦學會會長、南京大學許結教授給予高度評價和期待:“有了這一鴻篇巨制,賦學同仁宜考慮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做好賦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如出版賦學文獻系列點校、箋注本”。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石,離開文獻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可以想見,對推動中國賦學研究的力度上,蹤教授此舉厥功甚偉。在長時期舉力蒐輯、考辨甄別的摸索中,編者進一步深化提升,將近二十年賦學研究的創見與心得匯于一書,于是又有《賦學文獻論稿》出版(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為學界的賦學文獻研究呈上精彩典范。以筆者之見,《賦學文獻論稿》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一、元典考論:中國賦學文獻與批評史特征
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說:“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賦學文獻分散在全國各大圖書館,十分不易搜集。有時某種文獻的重要版本甚至需要跨境、跨國去尋訪。蹤教授利用各種途徑,以此為基礎開展研究,不僅花費很大力氣去搜集各種文獻,獲得第一手資料,還特別注重對各版本進行比勘和研究。如《會稽三賦》的注本與版本問題,經作者查考,目前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10種版本,共12套;而國家圖書館則藏有該書的16種版本,共23套。而將兩館所藏諸本進行歸納、梳理后,進而又可揭示出三賦在宋元明清時期被解讀和傳播的情況。又如明代以來輯錄的司馬相如文集有十余種之多。《<司馬相如集>版本敘錄》一文在描述其版本狀態的基礎上,指出它們或本于《漢書》,或源出《文選》,或廣蓃佚文,或詳加校注,有的還匯集了較為豐富的研究資料,對于司馬相如作品的保存、研究、傳播與普及做出了積極貢獻。值得提出的是,早在2008年,作者即有《司馬相如資料匯編》一書出版,可見該文深厚的文獻基礎。又《事類賦》現存不同版本達21種之多,蹤教授一一說明其版式藏地等信息,指出是編既具類書功能,亦表現出鮮明的文學特色,是清代以來學者輯佚、校勘古書的重要資料來源,因此有著珍貴的文獻價值。這種以元典文獻為基礎的研究方式,論證有據,論點可信,路徑可循,成果可期,是學術研究的根本方法和必由之路。誠如作者所說,“本著‘一分耕耘一分收獲’‘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原則,認真閱讀賦學元典和相關史料,尤其注重對文獻版本的考察和甄別,對出土文獻的關注和研討,對古代“小學”著作的挖掘和利用……以原始資料為據而得出的觀點,自己心里感到踏實”(《前言》)。
是編以文獻為基本線索,文獻與批評結合,以點帶面,考論并重,由此展示出中國賦學批評史的基本特征。作者并沒有對中國賦論史作全面論析,而是將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深遠或意義重大的賦學典籍進行深入挖掘與研究,或抉發其價值,或歸納其特點,或指摘其闕失,或臚列其版本,既能統籌賦學批評全局,又頗顧及個體價值地位。如對漢魏六朝時期的賦學批評,由于賦學文獻十不存一,那么重點在辭賦的編集、傳播、注釋等情況。蹤教授首先對賦體考鏡源流,正本清源,突破了傳統的詩源說、楚辭說、縱橫家言說、隱語說、俳詞說、多源說等固有觀念,得出賦體文學源于先秦民間韻語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就賈誼、司馬相如、檀道鸞等影響較大的賦家,或探討辭賦的著錄與傳播,或考辨版本迷霧,或評析價值地位等,與此期賦學批評相得益彰。唐宋元三代賦集編纂成果不多,蹤教授主要關注類書、韻書及大型詩文總集等對保存賦體及由此產生的意義和價值。明清時期歷史風云的變化,文學形式也隨之改變。在賦學研究領域,則以賦話的產生、評點的繁榮及賦總集的大量出現為特征,因此蹤教授關注的重點又以重要作家、重要賦集如《辭賦標義》《賦海補遺》《賦珍》《賦略》《賦海大觀》等文獻為主。對于當代賦學著作,蹤教授首先對龔克昌先生的《中國辭賦研究》《全漢賦評注》《全三國賦評注》分別進行介紹和評論。之后對新時期第一部專門研究唐賦的學術專著,廣西師范大學韓暉先生的《隋及初盛唐賦風研究》做了介紹。而賦論及賦集的編纂,則以湖北大學何新文教授的《中國賦論史稿》《中國賦論史》和中國賦學會第一任會長、湖南師范大學馬積高先生主編,六十余位賦學研究者通力合作的《歷代辭賦總匯》為代表。全書以文獻為主,由一系列典型個案的研究自然形成中國賦學文獻批評的歷史進程與變遷,為學界賦學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二、填補空白:賦學研究深度與廣度的突破
蹤教授的賦學研究,不懼冷僻,不避熱點,孜孜矻矻,開拓創新。其《論稿》對學界未關注或關注較少的領域均敢于耕耘,創獲頗豐,代表著中國賦學文獻研究的最新前沿。如對于先唐賦論,大都將眼光聚焦于揚雄、班固、劉勰等理論家,對于南朝宋檀道鸞,則幾乎無人關注。蹤教授從《世說新語·文學篇》劉孝標注中鉤稽出一段檀道鸞《續晉陽秋》的佚文,通過考辨與辨析,寫出《檀道鸞賦論發微》一文,認為檀道鸞不僅極力主張詩騷傳統,而且第一次將楚辭與賦分而論之,并率先從《詩經》、楚辭、諸子百家凡三個方面探討了賦體淵源。這不僅在劉宋時絕無僅有,在整個中國賦學批評史上也難得一見。又如作為明代前七子中的重要作家,何景明的辭賦主要見于其《何大復先生集》,作者卻在《(雍正)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發現了佚文《石樓賦》,該賦對了解何景明的復古理論與創作的關系有重要參考價值。唐宋以后,對于保存賦學文獻較多的類書、韻書、賦集、文集等均有關注,如《藝文類聚》對中國賦學的貢獻,從賦學視域看《韻補》,及明清時期的大型賦集《辭賦標義》《賦珍》《賦海補遺》《賦略》《宋金元明賦選》《賦海大觀》等,前者看似與賦學無關,較為冷僻;后者多藏身京師,翻閱不易,故學界探討不多。《論稿》或考察其編者,或辨析其版本,或挖掘其賦學思想,或考證其闕誤,將賦學研究的觸角向更深更廣的領域推進,因此均可稱為嘉惠學林、導夫先路之作。
值得提出的是,現代學界關于漢賦的研究,有從文學史、制度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風俗史及考古學等多個角度進行考察,碩果累累。漢賦研究亟須尋求新的研究視野與方式,才能走向全面創新與發展。然漢賦大家多是小學宗匠,如司馬相如作有《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與《方言》,班固有《續訓纂篇》,可知西漢文人如揚雄、司馬相如等,均洞明字學。“綜兩京文賦,諸家莫不洞悉經史,鉆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儷字。”[2]因此漢賦與小學的關系不容忽視,亦是漢賦研究的新亮點。臺灣簡宗梧先生,大陸學者易聞曉等均倡此論,并身體力行,試圖開辟賦學研究新天地。因交叉學科涉及面廣,又有專業差異,因此,非涉獵廣博、學養深厚者不能為之。蹤凡教授早在《漢賦研究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中就已注意到古人漢賦研究的語言學視角,近十年后,《論稿》再次指出,賦體文學的研究,大多學者從史書、總集、別集、詩文評等各類著述中查找資料,卻很少注意語言文字學著作。其《古代語言文字學著作中的漢賦資料》一文發現,文字學著作如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一書征引前代賦多達206條,全部集中在漢魏六朝賦,隋唐賦1條也沒有。這些引文為后人研究漢賦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異文資料及闡釋材料,十分珍貴;音韻學著作如吳棫《韻補》征引先秦至北宋賦多達682條,其所征引的漢賦并不限于名篇,常常涉及一些不甚知名的作家作品,是后人輯佚工作重要的資料庫;訓詁學著作如羅愿《爾雅翼》、方以智《通雅》等書對漢賦語詞、名物有較多研究。此外,作者不僅對東漢時期賦注家及其賦注有詳細考述,還對出土文獻密切關注,并考證審慎,如《神烏傅(賦)》于1993年出土于江蘇省連云港市尹灣村漢墓,是目前唯一的一篇保持原始狀況的漢賦作品。迄今為止,海內外研究者對許多問題都取得重大進展,但不少問題仍是聚訟紛紜,《神烏賦集校集釋》一文不僅對十余年間《神烏賦》考釋的成果進行歸納、總結,還就學界爭議較多,分歧較大的問題提出創見,深見功力。
三、賦境開拓:古今貫通與上下求索
在時間上,本書橫跨先秦至當代,內容廣及類書、方志、出土文獻、小學文獻及賦家、賦集等,視野廣博,然又深入細致。業師許結先生曾說,古代文學的研究,已有的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只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再往前一步,哪怕是半步,就是好的。對某些常人較少問津的大部頭賦學文獻,蹤教授都有認真的考證工作,考其闕誤,評其價值,前進之路,遠非可尺可量。
作為一代文學之勝,兩漢時期的賦家賦作可謂彬彬日盛。班固《兩都賦序》云:“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3]至《漢書·藝文志》著錄四類78家共1004篇,漢賦已散佚良多。自漢至今,留存下來的漢賦更是十不余一。今人費正剛等輯校《全漢賦》(1993年版、2005年增補版)、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的附錄《先唐賦輯補》、《先唐賦存目考》等均對漢賦存佚情況作了竭澤而漁式的整理,因此很難再發現一些新材料。然蹤教授《嚴可均<全漢文>、<全后漢文>輯錄漢賦之貢獻及闕誤》一文據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七十引文發現賦圣司馬相如有《玉如意賦》,又據明解縉等《永樂大典》卷一二〇四三“酒”部“賜方朔牛酒” 條引《古今事通啟顏錄》錄東方朔《大言賦》。如此之評功正訛,補益良多,《論稿》舉不勝舉,是學界賦學研究繞不開的重要參考文獻。又《賦珍》一書,海內外有四家圖書館收藏,分別是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及西北大學圖書館藏本。蹤教授根據程章燦《賦珍考論》一文中“卷五《機賦》,作者為漢代王逸而誤為漢王起”,而國內三本皆刻作“漢王逸”,得出程先生所據的哈佛本必與國內三個版本不同。又通過考察發現,西北大學藏本在吳宗達序之下刻有《賦珍總目》,這是西北大學藏本與其他藏本的最大區別。繼而對《總目》與原文作了比對,并正其訛誤。作者不僅為讀者提供了各版本的區別,還對是編的編纂、內容及批評有詳細介紹,為《賦珍》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與參考價值。眾所周知,清末光緒年間鴻寶齋書局編印的《賦海大觀》是歷史上規模最大、收賦最多、分類最繁細的賦體文學總集,規模是清康熙年間陳元龍奉敕編纂的《歷代賦匯》的三倍之多。如此體制宏大,內容浩博的賦體總集,雖一再影印,卻石印袖珍,字如螻蟻,實難觀感。作為清代律賦淵藪,還存在著分類失當、次序錯亂、篇目缺漏、誤收重出、篇名錯訛、作者闕誤、內容闕誤、體例混亂等問題,如作者標注之誤,卷一“天文類”“風”目收有《颶風賦》1篇,題為蘇軾作,據《宋文鑒》《古賦辨體》等書,當為蘇軾之子蘇過所作;篇名之誤,卷三“地”目有唐錢起《益地圖賦》,據《文苑英華》卷二十五和《歷代賦匯》正集卷十四,賦題當為《蓋地圖賦》,“蓋”“益”形近而訛;重出之誤,如卷八“典禮”類“祭祀”目收錄唐石貫《藉田賦》1篇,同卷“耕藉”目又收此賦,文字相同,只是未標出作者朝代;那么《<賦海大觀>之闕誤》一文對此一一校核辨析,需要何其大的耐心和毅力!
蹤教授的賦學研究,謙虛寬容、嚴謹細致并持之以恒,其對某一問題的看法獨到而有遠見,并不隨著成果的問世而終止。如《<神烏賦>集校集釋》一文原載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先秦兩漢學術》,2006年第6期。在發表的同時及以后,又有數篇考釋《神烏賦》的論文,未能吸收。然在本書出版時,蹤教授將這些論文附錄在文后。一方面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更多的線索和參考,另一方面表明其對此問題的長期關注。蹤教授還在書中留下了自己賦學研究的路徑與方法,如《<藝文類聚>與中國賦學》一文,他在文后不僅羅列了研究類書與文學關系的著作,如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系》、唐光榮《唐代類書與文學》、田媛《隋暨初唐類書編纂與文學》等,還有專門研究《藝文類聚》的著作,如郭醒博士論文《<藝文類聚>研究》、孫翠翠碩士論文《<藝文類聚>》所引“藝文”研究》等,由此可知,蹤先生在研究《藝文類聚》與賦學的關系時,不僅詳細比較了《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所載賦的異同,還將視角延伸到類書與文學的關系,以小見大,洞見隨出。又作者在《<事類賦>版本敘錄》文后指出,研究《事類賦》,首先應該參考冀勤等點校的《事類賦注》,(中華書局1989年版),研究論文有權儒學《宋刻本吳淑<事類賦>》(《文獻》1990年第2期)等。或為讀者指明路徑,或介紹自己的研究方法,不失為學界賦學文獻研究的典范力作。
參考文獻:
[1](清)張之洞.書目答問[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1.
[2]孫梅.四六叢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2.
[3](南朝梁)蕭統.文選[M].北京:中華書局,197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