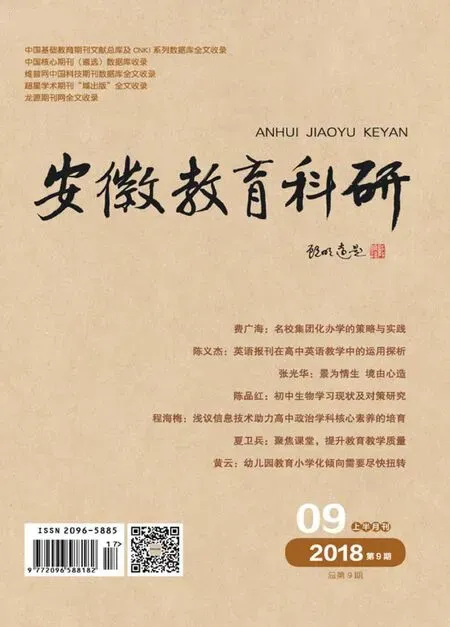景為情生 境由心造
張光華
(合肥市五十中學(xué)東校西園校區(qū) 安徽合肥 230001)
柳宗元的《小石潭記》是古代山水游記的名篇,歷來為后人所傳誦。其文是畫,是詩,有色彩,有聲音,有濃厚的感情色彩,構(gòu)成高度的藝術(shù)魅力。教學(xué)中,可從如下三個(gè)方面洞悉其文字之美、情感之悲和靈魂之孤獨(dú)。
一、欣賞小石潭宜人的景色
《小石潭記》篇幅短小,卻意蘊(yùn)深長(zhǎng)。全文內(nèi)容可分作五部分,脈絡(luò)清楚。第一部分起筆從小丘開始,接著寫小石潭。先寫遠(yuǎn)遠(yuǎn)聽到的聲音,然后尋著聲音一路往前。景物若隱若現(xiàn),愈發(fā)引人向往。第二部分寫小石潭的本身,重點(diǎn)刻畫清澈的潭水,活潑的游魚,但寫法又不盡相同。前者是暗寫,后者是明寫。第三部分寫潭外的水流,突出水流的曲折深遠(yuǎn),增添了景致的層次,營(yíng)造出山重水復(fù)的效果。第四部分寫法上有了變換。從上文的寫形態(tài),深入一層,改為寫意境。這樣一來,環(huán)境的清冷和作者身世的悲涼就對(duì)應(yīng)了起來。最后一部分是記述游歷的同伴,作為游記的收尾。
景物寫的形象逼真是這篇寫景游記散文最突出的亮點(diǎn)。柳宗元擅長(zhǎng)描畫景物,總是用凝練的語言輕輕勾畫幾筆,使人猶如置身在鮮明的圖畫中。作者描寫流水的聲音,沒有使用慣常的汩汩、潺潺、涓涓等詞語,而是以佩環(huán)之音來寫水聲。玉石相擊,其音清越,聽來使人身心愉悅,而且還能以水聲烘托山林中幽僻靜謐,再以山林的靜寂來映襯水聲的清朗,二者交互起來,帶給人美妙的感受。
潭邊和岸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堪為巖。青樹翠蔓,蒙絡(luò)搖綴,參差披拂。”潭中怪石交錯(cuò)、岸上枝蔓交映的生動(dòng)景象濃縮在這二十余字里。對(duì)于青樹翠蔓的描繪只用“蒙絡(luò)搖綴,參差披拂”八個(gè)字,逼真細(xì)膩。“蒙”是遮住蓋著,形容蓊郁茂盛,遮遮掩掩;“絡(luò)”是糾結(jié)在一起,攀緣纏繞;“搖”是搖搖擺擺,來回晃動(dòng);“綴”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牽連。這四個(gè)動(dòng)詞形象地描繪了樹枝藤蔓的各種奇特狀態(tài)。“參差披拂”將繁衍伸展開來長(zhǎng)短不齊的枝蔓,在微風(fēng)中輕柔地飄曳的動(dòng)態(tài)生動(dòng)再現(xiàn)。這豐富的不僅是石潭周圍的景物,而且也給石潭抹上一層濃濃的生命之綠,使人感到盎然生機(jī)。
同樣精彩的是對(duì)潭水和游魚的描寫,作者想表現(xiàn)潭水的清澈,卻不直接寫潭水,而寫魚“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從表意看“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只字未提及水,但我們已經(jīng)能充分感受到潭水的澄澈透明。“日光下澈,影布石上。”陽光透過清澈的潭水,把一條條小魚的影兒刻印在潭底的全石上,猶如一幅畫。魚在水中游動(dòng),卻像在空中沒有憑依,陽光直射下來,照見石潭底部。這反過來襯托了潭水的清澈透明。寫游魚,作者從靜止到活動(dòng)兩個(gè)方面來表現(xiàn)。靜止時(shí)游魚呆呆不動(dòng);活動(dòng)時(shí)是一會(huì)兒游向遠(yuǎn)處,一會(huì)兒躥向這邊。僅僅十二個(gè)字就抓住游魚的特點(diǎn),構(gòu)成了一幅魚影交映的生動(dòng)圖畫。作者用“佁然”“俶爾”“翕忽”分別反映小魚的靜態(tài)和動(dòng)態(tài)。“佁然”形容小魚憨態(tài)可掬,紋絲不動(dòng);“俶爾”是寫小魚曳尾而去,一閃動(dòng)就不見了;“翕忽”是刻畫了小魚靈巧輕捷,輕快自由地游動(dòng)。“似與游者相樂”這是作者將自己游樂的心情投射到魚兒的身上,仿佛魚兒也會(huì)和人一樣感到快樂。
作者以大畫家的筆法生動(dòng)地描繪出山水的形象。讀作者的游記就像看山水畫一般。作者將山水的位置、形狀、特征都清晰地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尤其表現(xiàn)在使用鮮明的色彩勾勒出光線的明暗效果。“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shì)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就溪身而言,是靜態(tài)的,因此比作曲折的北斗星;溪流是流動(dòng)的,所以比作像游走的蛇。由于溪身蜿蜒曲折,望過去,一段看得見,一段看不見。溪身看得見的一段由于陽光的反射就是亮的,看不見的一段就顯得暗了。“明滅可見”凝練地寫出這種光線給人的感受。溪岸也是如此,像狗牙那樣參差不齊。“斗折”呈現(xiàn)的是靜態(tài),“蛇行”描繪的是動(dòng)態(tài),一動(dòng)一靜構(gòu)成貼切的對(duì)稱,恰好用來形容溪身和溪流。接下去,“明滅”是指溪流,“犬牙”比擬溪身。正是成為動(dòng)與靜的對(duì)稱,顯出作者狀物繪景的杰出的藝術(shù)手腕。
二、感知貶謫人悲涼的心情
小石潭風(fēng)景搖曳并非一時(shí),千百年來卻寂然于永州荒野之中。柳宗元造訪,覺得這樣美好的山水隱沒在荒涼的地方實(shí)在可惜。好比有才能的人受到排擠被放逐到邊遠(yuǎn)地方去一樣。這樣的貶謫人不正和自己同病相憐嗎?回想起自己被貶出朝廷的一幕是何等的令人心碎?安史之亂使盛唐的燦爛光輝黯然消隱,曾經(jīng)盛極一時(shí)的唐帝國奏起的竟是江河日下的悲歌。痛定思痛,亂后思治,有理想有抱負(fù)的仁人志士對(duì)國勢(shì)的衰微痛心疾首,他們呼喊于朝,奔走于野,于是一股強(qiáng)大的中興思潮就在社會(huì)上奔涌激蕩。德宗貞元九年(793年)20歲的柳宗元考中進(jìn)士,可謂志得意滿。順宗即位,柳宗元擢禮部員外郎,一時(shí)位高權(quán)重。歷史給了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一次機(jī)會(huì)。柳宗元和劉禹錫等人積極推動(dòng)王叔文領(lǐng)導(dǎo)的政治革新運(yùn)動(dòng),拉開了“永貞革新”的序幕。他們懲辦污吏,削弱藩鎮(zhèn),整頓財(cái)政,打擊宦官,雷厲風(fēng)行的新政給百姓帶了希望,給國家?guī)砹耸锕狻K麄兿敫锍瞥谋渍瑓s遭到了陰陽其人的宦官、肉食者鄙的官僚和飛揚(yáng)跋扈的藩鎮(zhèn)的聯(lián)合嫉妒與排斥。剛剛呈現(xiàn)的一抹希望瞬間成了曇花一現(xiàn)。永貞元年(805年)八月,順宗被迫禪位于憲宗,革新宣告失敗,柳宗元初貶邵州刺史,未至,再貶永州司馬。他在永州把四野的山巒視為囚禁他壯年和生命的牢籠。但是,痛苦的心靈需要解脫之時(shí),山水成了慰藉苦痛靈魂的好友,醫(yī)治作者心靈創(chuàng)傷的良藥,于是美好的山水就常常成為柳宗元人格的象征,寄托著他的情感。
柳宗元借山水抒懷,把自己的思想以及感情寫進(jìn)山水里去了。本來想借山水來散心,可惜剛剛被游魚逗樂的心境又因景物的變化而發(fā)生了改變。“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shì)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當(dāng)作者向西南方向望去,見到了水流曲折幽邃,忽明忽暗,岸勢(shì)如犬牙一般交錯(cuò)。于是有一種幽深不可測(cè)度的內(nèi)心感受涌上心頭。溪流的源頭不知在哪里,自己未來的方向又在何處呢?于是眼前的景象不再是先前的“蒙絡(luò)搖綴,參差披拂”的盎然生機(jī),而是“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的凄涼清冷。于是周圍環(huán)境與個(gè)人感受就自然地結(jié)合起來,個(gè)人的孤寂、凄涼、哀怨的心境也就浸透在文字里了,進(jìn)而讓自己覺得“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久居荒遠(yuǎn)的凄涼盡在其中。
再回頭來看,游魚可以“佁然不動(dòng)”,可以“俶爾遠(yuǎn)逝”,自由活潑,輕快敏捷。游魚出游從容,自由自在游弋在水里。水是魚的世界,魚盡情地在水里撒歡。可是自己的舞臺(tái)在哪里?自己也能如游魚一般或“佁然不動(dòng)”或“俶爾遠(yuǎn)逝”嗎?這樣魚的活潑游弋與貶謫人的壓抑苦悶形成對(duì)比,而這種悲涼的心境一經(jīng)凄清環(huán)境的觸發(fā)就盤踞在柳宗元的內(nèi)心。外景雖好,獨(dú)不能撫平內(nèi)心的憂傷。
三、體悟失意人孤獨(dú)的靈魂
如果只是分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huán)合,寂寥無人”,似乎是作者只身一人,獨(dú)得小石潭的幽靜,因此感到寂靜遼遠(yuǎn),空無一人。可是文章在結(jié)尾記述游歷的侶伴明明是五個(gè)人,怎么還說“寂寥無人”呢?其實(shí)這種感受與作者當(dāng)時(shí)沉浸在寂寥無人的心境有關(guān)。外景的景象與作者貶謫后長(zhǎng)期的抑郁心境又是天意弄人的吻合,相互作用。同行的五個(gè)人都是柳宗元的親友,也經(jīng)歷了打擊和磨難,如吳武陵和少年得志,年紀(jì)輕輕就考取了進(jìn)士,但第二年因得罪了當(dāng)朝宰相,就被流放到了永州。崔氏二小生是柳宗元姐夫崔簡(jiǎn)的兒子,而崔簡(jiǎn)的命運(yùn)和柳宗元相似,也不幸遭流放。相似的遭遇怎能不產(chǎn)生相似的情緒呢?友誼是人生的調(diào)味品,也是止痛的良藥。如果單就受到的打擊和磨難而言,作者與這五個(gè)人是有心靈契合的地方的,但柳宗元的失意和痛苦又絕非眼前的茍且。
永州在唐朝是偏遠(yuǎn)地區(qū),山嶺險(xiǎn)峻,人煙稀少,通常只有罪犯才發(fā)配到這里。現(xiàn)在柳宗元到永州不是有具體政務(wù)的官員,而是戴罪流放的囚徒。偏偏柳宗元不該被稱為罪犯啊。柳宗元出身于封侯拜相的士林盛族,雖已衰落,其本人絕非古今皆然的那種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紈绔子弟,而是繼承了父親剛直倔強(qiáng)的性格。父親的熱血在他的血管中奔流,自幼傳承的儒家“仁政”“民本”的觀念,使得柳宗元自幼就有著強(qiáng)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憂患意識(shí),他決心奮發(fā)有為,實(shí)現(xiàn)個(gè)人理想,同時(shí)肩負(fù)起振興國家的使命。一心為國謀劃興利除弊,“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罷官貶職的致命打擊猶如一盆冷水,澆濕了為國效力、竭盡心力的熱忱,可是這些能說出來嗎?說出來,周圍人又能理解嗎?難道這種情形不是《始得西山宴游記》里西山命運(yùn)的重演嗎?
滿眼山水秀美之景,沒能溫暖柳宗元凄涼的內(nèi)心,更沒有釋放柳宗元靈魂的孤獨(dú)。潭水清澈,映照出柳宗元的身影,孤獨(dú)而又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