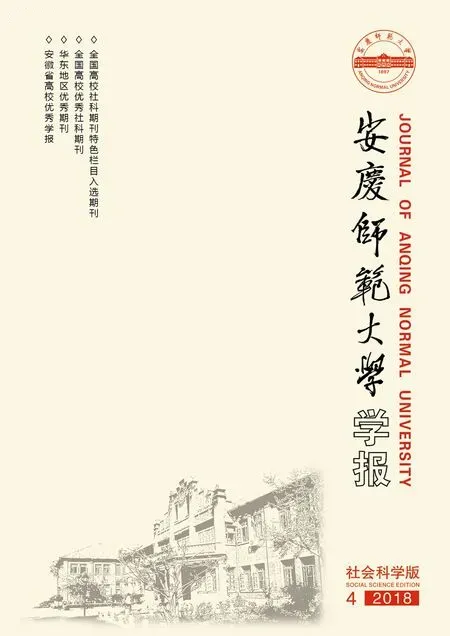漢語成語認知研究述評
劉洋洋
(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漢語成語研究歷史久遠,從本體到文化再到認知,研究在一步步深化。而這一深化,得益于認知的方法和視角。束定芳認為:“認知語言學的魅力在于對語言事實及規律較強的解釋力和一定的預測性,以及它對語言使用者心理現實性和相關文化、語言特性的充分考慮。”[1]很明顯,成語研究若要有所突破,若要對成語結構的生成、理解模式機制做出深層次的解釋,非認知方法莫屬。但同時,使用認知的框架合理有效地研究本土語言現象是一條長期的道路。本文概述了漢語成語認知研究的發展歷程,總結其特點和成績,指出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并探討其未來的研究方向和趨勢。
一、漢語成語生成機理的認知研究
漢語成語言簡意賅,其構成一直是學者們的研究課題之一。對于漢語成語生成機理的認知研究,貢獻巨大的首先是徐盛桓先生。徐盛桓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使用“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規推理”為理論框架,以相鄰和相似兩種關系為中介,成功建構了一個“自主—依存分析框架”[2]。這一框架的建構、推理過程中,所用到的舉例多是漢語成語。
2004年,徐先生發表文章《成語的生成》,文中指出成語所具有的四點特性和三種品格,而這些特性和品格并不是成語所獨有的,不透明性、不完備性和蘊含力在日常話語中也有體現,只不過這種不透明和不完備在成語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更為集中[3]。所以,徐認為成語這種“表里不一”本質上也是含意現象,可以用含意本體論的“語句解讀常規關系理論模型”來做出解釋。
之后,為了進一步說明成語形成的機理,徐又發表《相鄰與補足》[4]《相鄰和相似》[5]兩篇文章,把常規關系抽象為[相鄰+-]和[相似+-]兩個維度,并用以此為核心概念建構起來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來研究成語的生成。《相鄰與補足》指出成語犧牲了語法-語義的完備性來成全其經濟性,這同日常話語語句的顯性表述通常都是不完備的是相類似的。而且,徐引入“構塊”(現多稱為“構式”)的概念將漢語成語各種不同的顯性表述從不完備表達到相對較完備表達分類為語法外構塊、假語法構塊、超語法構塊、準語法構塊、語法構塊。這種對成語的再分類,引出了成語形成的推理規則[4]。
《相鄰和相似》一文中,徐先生建設性地論證了用構式語法(原文稱之為“構塊語法”)的理論框架來分析漢語成語并不是最理想的。Fillmore等人對英語成語的研究開啟了構式語法研究的序幕,對漢語成語的研究有很多的啟發,但是徐認為這一事實僅說明成語跟一般句法構型一樣,都可以用構式的形式來表征,并不能說明成語形成的機理,而且漢語成語的特點使成語的構式分析產生了一定的困難,成語的生成機理最理想的解釋還是以“相鄰/相似”為核心概念建構的“自主—依存分析框架”。
徐又將研究推進一步,用“象征性”解釋成語結構的“不講語法”為什么可能。徐先生總結了漢語成語認知研究的主要問題,即成語的語義加工和語言結構的問題,然后從“相似性”、“格式塔轉換”角度分析得出成語的結構生成是符合認知特點和認知過程的,最后,結合他前期的“相鄰/相似”關系解釋,加之于“蘊涵”關系,將成語的語義加工情況分析為兩大類七小類,回答了成語生成和理解的語義加工過程為什么可能的問題[6]。
徐先生的跨領域研究可謂漢語成語研究的一個重大突破。首先,徐先生嘗試用認知、心智理論來解釋漢語成語的生成,打破了以往成語本體研究的套路,他的研究引入了“含意本體論”、“構式語法”、“常規關系”等一系列嶄新的解釋方法,開創了成語研究的新篇章。而且,徐文在語言共性研究的大環境下研究漢語成語,推導出成語形成和解讀的常規關系推理原則和相關推論,跳出了成語研究的窠臼。沈家煊提出,語法研究要以預測和解釋合乎和不合乎語法的現象為目標[7],徐先生的研究將漢語成語的研究朝著這個方向推進了一大步。
成語的生成,本不是任何一種單一的理論、單一的模式所能全面解釋的,必然涉及經驗基礎、知識結構和文化模式等多領域,在認知科學的框架下研究成語的生成必然是有效途徑。而且,概念隱喻理論也適用于成語生成機制的研究,值得借鑒。
二、漢語成語語義構成及理解的認知研究
言簡意賅的成語能夠表達豐富的內涵,并且能夠為人們理解使用,所以成語的語義構成和理解也是值得研究的。在這一領域,做出巨大貢獻的一位學者是張輝。早在2003年,張先生出版了專著《熟語及其理解的認知語義學研究》,以具有雙層意義的漢語四字成語為對象,以認知語義學理論為框架,探討了漢語成語的語義構成[8]。張輝證明了熟語是一種凝固化的常規映現模式(mapping patterns),熟語在產生、使用和理解的過程中,人們無意識地運用了隱喻和轉喻的機制,他將隱喻、轉喻和概念整合綜合為統一的框架,形成了熟語心理空間的概念。張先生還指出,熟語的常規化導致了轉喻超轉喻化和隱喻的超隱喻化,一個熟語可以同時分析為隱喻和轉喻。張先生在研究漢語成語時,主要研究對象是典故成語。漢語中存在許多這樣的轉喻或隱喻性成語,由于其使用的頻繁和常規化的發生,進而演變成超轉喻或超隱喻性成語。雖然成語本身的轉喻或隱喻性仍舊存在,但是其映射關系幾乎已經消失,這種消失并不是真正的消失,一旦有外界因素的刺激,還是會重現的[8][9]。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對這樣的成語已經有了一定的熟悉度,在使用和理解時,會不自覺地受到這種沒有完全消失的映射關系的影響,不去考慮其字面義,而直接采用其喻義。
朱風云、張輝對國外學者的各種熟語語義加工模式進行了思考與述評,其研究對象和范圍雖然是英語熟語,但對漢語的成語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10]。張輝、季鋒考察對象是動賓結構的英語熟語和雙動賓結構的漢語成語,研究模式是國外的復合場鏡、棱鏡和熟語激活模式,考察目標是熟語特性、語法地位、組構假設、語義結構混雜性等問題,指出了這些模式在實證研究方面的不足[11]。
張輝等學者對成語的研究突破了成語本體研究的套路,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首先,這些研究使用了隱喻、轉喻、心理空間、概念整合等新的研究框架來探索成語的語義構成和理解機制,解釋了諸多以往研究中無法解釋的問題;其次,他們的研究引入了世界先進的研究理論和方法,而且其研究趨勢是認知語言學理論分析和神經語言學實證研究的結合,這一趨勢的開拓必將取得更有效的發現并深入影響語言學其他領域的研究。
對于漢語成語語義構成和理解的認知研究不僅有大的突破,還有點滴的成果。唐雪凝、許浩對現代漢語常用成語的語義研究不僅運用了認知理論,還結合了述謂結構理論。深入分析語料庫語料后,他們探討了成語內部豐富的論元結構關系,繼而歸納、解釋成語語義構成的規律,總結成語語義結構成分的隱現機制和原則,深化了對成語的研究和認識[12]。
又如葉琳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框架下,使用心理語言學實驗方法,對英語習語和漢語成語的理解過程進行實證研究,然后擬構出了適用于英漢習語理解加工的模式[13]。
點滴成果同樣可以匯聚為巨大的進步。對于成語語義和理解的認知研究論文層出不窮,其研究趨勢亦是走理論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道路。語義和理解,本就是人腦的復雜活動,開展實驗研究,可以更準確明了地了解和解釋這一過程。但是,實驗研究不僅需要跨學科的扎實理論基礎,更需要先進的實驗設備以及完備有效的實驗設計和操作,所以,目前在國內研究中尚不能普及,盡管如此,語言學、認知科學、心理學相結合進行漢語成語的生成和理解研究,還是很令人期待的。
三、漢語成語變異的認知研究
漢語成語深受使用者喜歡,經常出現在人們的唇吻筆端,因此,生活中,為了追求一定的修辭效果,也經常被部分改變其形式或意義來使用,即成語的仿用。以往,學界就成語的仿用研究主要從其分類、修辭效果、利弊和如何有效地仿用等角度展開。自構式語法傳入中國,因為成語是構式的一種,用構式語法理論研究成語的仿用應勢而生。劉宇紅、謝亞軍指出成語在仿用的過程中發生了語義壓制(semantic coercion),沒有被扭曲的成分是壓制者,或叫做壓制因子,被扭曲的成分是被壓制者。壓制力源于構式本身相對固化的語言形式和語義內容。語義壓制過程是一個認知心理操作過程,其效果受到壓制力和抗拒壓制力的大小兩方面因素的制約[14]。劉文通過具體的成語仿用實例證明:壓制因子與構式的結構和意義越接近,壓制力越大;被壓制者和原語言成分在音系、語義或字形上越相似,抗拒壓制力就越小。
構式語法理論是在認知語言學對TG語法進行反思的過程中形成的新興語法理論,現已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和接受,解釋了很多一直以來困惑語言學界的問題。對于成語的研究,借用構式語法理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例如羅遠晗從構式的視角解釋了漢語成語的活用[15],黃曼借助構式理論對比研究了漢英習語的變異[16]。
沈志和基于封閉語料庫對漢語仿擬成語中的語音隱喻進行認知分析。此文重點對仿擬成語的語音隱喻進行分類研究,即語音突顯、語音壓制和語音隱喻[17]。文章立意新穎,語料搜集科學嚴謹,詳細分類成語語音隱喻仿擬方式,缺憾是未對此語音隱喻機制做出細致的認知闡釋。后來,他又以該封閉語料庫為基礎,對漢語成語仿擬的認知運作機制進行了闡釋,改進了前文的不足,理論性更強[18]。
成語的變異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語言現象,不僅如此,網絡的普及還催生了另類的四字“類成語”,如“不明覺厲”“喜大普奔”等。這些新型“類成語”出現時日不長,其接受程度自然無法與“黃粱一夢”等沿用已久的成語相提并論,但是現代社會發達的網絡系統為語言的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快捷通道,而且已有媒體以“新成語”命名這些四字結構。因此,成語的變異研究亦任重道遠。其實,無論是成語的變異體還是新型四字結構,都是非語法性的表達式,都是基于語境產生的,識解這些表達,都需要語境做支撐,結合語境從動態的角度去深入探討,定會有所收獲。
四、漢語成語與英語習語認知對比研究
認知語言學的興起主要建立在對英語語言研究的基礎上,因此,將漢語成語與英語做認知對比研究會促進理論的檢驗和研究的深入。對漢英成語的認知對比考察,成果較突出的有王文斌、姚俊。王文斌、姚俊利用“理想化認知模型”(ICMs)和“概念整合”(CB)理論分析了漢英隱喻習語認知機制方面的同與異。人類認知模型的形成和與客觀世界的互動有關,漢英民族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雖然文化背景不同,但是隱喻習語表現出相似的ICM,即漢英習語在隱喻方面會使用類似的源域來隱喻同一目標域。之后,王文重點分析了漢英隱喻習語的異質性、內在的隱喻機制和存在差異的原因。漢語隱喻成語往往借用雙源域來映射同一個目標域,而英語隱喻習語則往往借用單源域來映射一個目標域。究其原因有二:第一,漢民族的形象思維和英民族的抽象思維,第二,漢民族的平衡和諧性思維和英民族把一切事物分成兩個相對立的方面的思維傾向[19]。以上兩種思維差異,體現在語言中,就形成了漢英隱喻習語的雙源域映射和單源域映射的區別。
王文對漢英隱喻習語的認知對比研究,對外語教學和成語的漢英互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同時王文也指出漢語隱喻習語的雙源域和單源域映射差異并不是絕對的,英語也有雙源域映射習語,反之,漢語也存在單源域映射成語。只是從數量上而言,這種差異是明顯的。但是這種差異到底存在的比例有多大,值得進一步統計和研究。另外,漢語隱喻成語使用雙源域映射是否會使得目標域的特征凸顯,反之,英語習語會否使得目標域特征降低?概念整合的過程在兩種語言中是否還有個性差異?以上兩個問題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周京勵以Geeraerts提出的“棱柱形模式”[20]為理論框架,以漢語和英語中的對等習語為對象,研究了習語中隱喻和轉喻的互動和隱喻義產生的認知過程。周文以英漢習語為例,詳細分析了隱喻和轉喻連續發生、并行發生和交替發生的認知過程,并輔以棱柱圖示解釋了漢英對等習語隱喻和轉喻不同的互動認知過程,即漢語成語是并行發生而英語習語是連續發生[21]。周文認為棱柱型模式的隱喻和轉喻的三種互動形式在漢英習語中都存在,其中交替發生模式存在數量較少,對等習語中可以用同一種模式闡釋的習語數量非常多,但是漢語習語中以連續發生和并行發生為模式的習語數量相當,而英語習語中連續發生模式遠遠多于并行發生模式。周文大膽地借鑒國外先進的習語研究模式來分析漢語成語,對漢英成語的認知研究、翻譯研究和教學都有一定的價值。
無論是漢語成語還是英語習語,都是文化的產物,盡管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但是以同樣的大腦為物質基礎,以同一個地球為物理環境,決定了人類思維的基本共性,其中之一便是概念隱喻這種人類基本的認知方式。目前的成語認知對比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漢語成語和其他語言成語的隱喻機理的異同方面。本文認為,研究相同之處,可以揭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人類的概念思維是相同的,而研究相異之處,切入點則較多,比如可以就成語進行分類細化研究,也可以從始源域入手,分析總結成語隱喻的始源域,或者就某個主題,分析其作為目標域如何通過隱喻得以認知。
五、漢語成語心理學視角的研究
上個世紀末,周光慶認為在成語的音義結合關系中,有一種意象充當著中介符號。成語的這種“表意之象”,是一種建構性圖像,這種圖像表達了我們對事物的特定性狀特征的一種體驗。這種圖像的形成主要借助隱喻、示觀、象征等方式。周文還認為,成語中的意象之所以具有表達功能,原因是格式塔心理學所證明的“異質同構”原理。周文在此理論認識上,對現代漢語中約700個常用成語先以內部形式表現的對象特征為標準,劃分成了十二個類型,如:神情類、姿態類、行為類、作風類、方式類、途徑類等;而后以選取物象的原則為標準分成三類,即自然的、人生的和神話寓言的;最后,以表意方式為標準,又將成語的意象符號分為三類:比喻性意象、象征性意象和示觀性意象[22][23]。
周文關于成語中介符號的系列研究,已經涉及了成語理解的認知模式,使用了認知、心理方面的原理,是成語表義、理解認知分析的初探。鑒于當時國內認知語言學體系還不完善,詳細透徹地使用認知方法來研究成語亦不太可能。之后,周先生提倡從哲學本體論的角度與高度研究漢語詞匯,并構建了“認知、解釋——文化——哲學”的研究思路[24]。周先生對于漢語成語及詞匯的系列研究打破了結構主義框架,開啟了成語研究的多維視角,突出了人與生存空間的互動。
劉振前的博士論文主要探討了漢語成語的對稱特征與認知[25]。后來,發表一系列有關論文繼續研究漢語成語。劉振前、邢梅萍指出漢語四字格成語中語義結構具有對稱性的占很大的比例,并結合實驗,從格式塔心理學、信息論等角度解釋了語義結構對稱的成語顯然比非對稱的成語易于認知[26]。劉振前、邢梅萍對四字格成語的音韻復沓形式進行了分類統計分析,并運用心理語言學方法對音韻復沓形式與認知的關系進行了實驗研究,對漢語語言教學提出了大膽的設想[27]。劉振前研究了漢語四字格成語平仄搭配的對稱性與認知,通過實驗得出,漢語四字成語按平仄區別不同聲調搭配形式有一定理據性,分類呈現總的來說對記憶和保持的影響比隨機呈現大[28]。劉振前的系列研究運用心理學理論和實驗的方法,以漢語成語的認知理解和記憶為重點,詳細探討成語本身的對稱特征外,對成語的教學和習得貢獻顯著。
黃希庭等和陳傳鋒等通過心理實驗考察了漢語結構對稱性成語和非對稱性成語的視覺識別、再認特點和與成語的熟悉度的關系。兩次實驗的結論顯示:在成語的識別和再認過程中,都存在顯著的結構對稱效應,對結構對稱性成語的識別和再認反應時明顯短于非結構對稱性成語,而熟悉度效應只在成語識別中顯著,尤其是在非結構對稱性成語的識別過程中;在結構對稱性成語中存在特有的“格式塔詞素”,促進了成語的識別過程。黃文還指出無法用以西方拼音文字為實驗材料所建立的認知模型來解釋漢語成語的對稱性和非對稱性的認知差異[29][30]。
漢語成語的理解和使用,無論是對本族學習者還是外語學習者,都是有一定難度的。語言學領域中的研究成果已經無法滿足教學和習得的需要。心理語言學對成語的研究集中在成語理解的潛在認知機制。黃文和陳文的研究成果服務漢語成語習得和教學的同時,無疑對漢語成語的認知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首先,我們應該建立什么樣的理論模型來解釋漢語成語的認知過程?而且,成語的再認反應錯誤率表明,成語的整體語義超過了格式塔詞素結構的作用,這一點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實驗。再者,成語認知研究的新趨勢必然是理論研究結合實證考察,走跨學科路線,而這一點,既是挑戰,又是機遇。
六、漢語成語認知研究的優勢和發展
束定芳認為:“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研究對語義和廣義語境作為語言研究重心的回歸,更符合漢語語言的特點。”[1]“認知語法能夠挖掘出一些用以往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所不易發現的語法現象。”[1]在漢語成語研究方面,認知語法同樣表現出了絕對的優勢。
第一,用認知語言學的方法研究漢語成語,不僅僅就成語的本體或文化談成語,而是把成語視為概念系統的產物,結合人類的經驗、知識和文化進行研究,從認知思維著手,必要時輔以實證實驗,是順應研究趨勢的,是現實的需要,也是歷史發展的結果。
第二,直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語言學家對漢語語法的研究一直使用的是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隨著研究的深入,問題也愈加增多,為了走出研究困境,部分語言學家開始嘗試認知的道路。認知語言學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致力于概括性承諾和認知承諾,其語法觀以使用為基礎,語義觀基于百科知識框架,在充分解釋語言現象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對語言事實及規律解釋力較強,因為認知語法對語言使用者的心理現實性、相關文化和語言特性做了充分的考慮[31]。漢語成語的文化底蘊深厚,使用靈活,從認知角度研究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
第三,用認知方法研究成語,洋為中用,一方面為漢語成語研究注入新鮮活力,另一方面,可以驗證認知語言學理論的普適性。這樣一來,和認知語言學建立最具有概括性的統一理論模式,進行最廣范圍的趨同證明這一研究目標一致。
從本文的回顧和分析可以看出,用認知方法研究漢語成語是一條光明之路,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正如以上優勢二所述,認知語言學是一種新型的理論框架,“在我國的發展正處于發展、反思與國際化階段”[1],任何理論都不是萬能鑰匙,在研究中漢語的一些個性特征尤其值得思考。比如漢語成語結構上整齊的特點就與英語習語不同,而且,漢語成語使用的頻率也遠遠高于英語習語,這就需要在研究中要細致對比、檢驗理論的解釋力和有效性。
第二,認知語言學是新興理論,本身處于發展階段,還有待完備,勢必會造成研究的局限性,因此,漢語成語的認知研究也不能不說是處在起步階段。學者們從一些不同的角度入手,利用不同的認知概念,難免會出現片面、缺乏系統性的缺點,而且缺乏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從知網的論文檢索結果就可以看出,漢語成語的認知研究重復較多,優秀論文不多,缺乏創新。
第三,就國內漢語成語的認知研究,學者們之間也存在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徐盛桓認為,“成語是人們頭腦中心理模型的類層級知識結構在線加工的結果,不一定都是概念隱喻”[6],而其他學者不都這么認為。類似這些未決的問題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間。我們的任務是要解決這些問題,進而建立漢語成語理解和語義加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