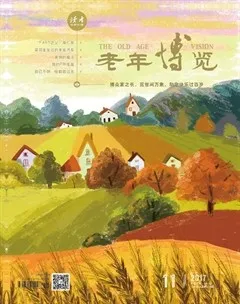我的FBI生涯
作為聯邦調查局局長,我面臨的第一個巨大挑戰竟然是進入總部大樓參加自己的宣誓就職儀式。瑪麗蓮、我和四個孩子提前抵達了第九大街通往地下停車場的入口,我們都擠在一輛沃爾沃旅行車里。總統快到了。我急切地想結束這些繁文縟節,然后投入工作。但在地下停車場入口,身穿制服、正在執勤的聯邦調查局警員卻把我攔住了。
“你有身份證嗎?”他問我。
我拿出我的駕照給他。
“不行。”他說,“你有聯邦調查局徽章嗎?”
“還沒有。”我告訴他,“但我快有了。有沒有人提到過今天要為新局長舉行宣誓就職儀式?”
他知道這事,但他沒有客人清單。
“好吧,聽著,”我說,“我就是要宣誓就職的人!”
至少這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
當天晚些時候,也許是為了彌補對新老板的冒犯,聯邦調查局安全特遣隊派了3輛車跟在我的沃爾沃后面上了街,經過30個街區,跨過波托馬克河,到達我們準備下榻的基橋萬豪酒店。這幾輛車等了幾個小時后,又跟隨我們去用晚餐,接著跟隨我們離開餐廳,然后直到第二天上午我們準備離開酒店的時候還在等候。
“你們是不是還準備跟著我一段時間?”我問其中一名司機。
“一直跟著。”他說,而且確實打算這么做。
我們很快就搬入了弗吉尼亞州大瀑布城一幢租來的房子,這里處于華盛頓大都市區郊區的邊緣地帶。
我們認為大瀑布城是個養育孩子的好地方,就想一邊物色房子,一邊讓孩子們在這里上學。幾天后,安全特遣隊的隊長來見我。
“局長,我們考慮在你家外面放一個活動房,這樣我們就可以安排人員全天待在那里了。”
“你們不能這么做。”我告訴他,“你們不能在那里放活動房。”
“那好吧,”他說,“我們把活動房放在后院。”
“那更不行!”
當然,孩子們喜歡受到關注。我們去看足球賽、去超市、去所有的地方時都有警衛。除了出行時像名人一樣,我的新身份還給了孩子們第二個好處。
在我做局長的初期,有個周六,我們在警衛的陪同下去了百仕達(美國的一家音像連鎖店—譯者注),我的一個兒子當時就說:“這太酷了!”
“別瞎說,”我跟他說,“你不覺得警衛到處跟著咱們太煩了嗎?”
“不煩。這樣,當著別人的面,你就不會對我們大喊大叫了!”
那一刻我意識到他說得非常對。孩子們去哪里都有6名特工看著他們,這樣我就必須始終做個模范父親了!于是我決定:我不需要保護。
我的前任威廉·塞辛斯所喜愛的龐大的安全特遣隊很自然地傳到了我的手中。我不能簡單地將他們全部開除,但在此后的幾個月里,我設法將所有人都安排到了他們想去的地方或他們想干的職位,最后就留下了兩位司機做我的安全特遣隊隊員:一位很快就要退休了;另一位叫約翰·格利格里奧尼,從前是愛荷華大學橄欖球隊的隊員,曾經做過聯邦警察,所以他可以帶槍。
出于責任感,約翰在與我一起制訂新的安全措施時,帶我來到聯邦調查局停車場的深處,給我看了那輛局長們外出時偶爾乘坐的重達3噸的防彈轎車。
“我們用不著這個。”我告訴他,“它就像喜歌劇里的東西。”
“那太好了!”他說,“我討厭開這玩意兒,每開幾百英里就得給它換剎車。”
于是,我們總開一輛雪佛蘭郊外型車往返于調查局和大瀑布城之間。約翰帶著他的槍,我帶著我的槍。在車里和差不多一切所到之處,我們都帶著槍。作為后備,我們還有一挺機槍放在儀表盤下。這就是我們新的安全措施。(隨身帶槍并不是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傳統做法,雖然規章允許這么做。但對我而言,這是代替安全特遣隊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如果有情況,”我告訴約翰,“你開車,我射擊!”
作為聯邦調查局局長,我當然不能忽視針對我家庭和我個人的威脅。我拒絕了護衛車、后院的安全活動房屋,也不讓防彈大怪物拉著我到處跑,因為瑪麗蓮和我不想讓我們一家生活在保護罩里—我們住在華盛頓特區樹木蔥蘢的郊區,不是在貝魯特分界線或巴格達綠區。但我也盡量讓自己不要顯得過于愚蠢。
自從當上局長的那一刻開始,我的人生就暴露在人類心靈的黑暗里了。我的朋友喬瓦尼·法爾科內和他的妻子在西西里被炸死。海倫·萬斯受重傷后不久我去看了她,她的丈夫羅伯特·萬斯法官被羅伊·穆迪的一枚郵件炸彈殘忍地殺害了。無論事實如何,我不得不假設壞人已將我鎖定為目標,因為我將本·拉登納入了聯邦調查局“十大通緝犯”的名單,并且監督了對他的調查、控告和追捕。我一直假設我的家人和我都是他們的主要目標。
我們的郵件會經過處理。我們所有的包裹和信件都經聯邦調查局攔截,在確認安全后才會送到我們家。這是目前保護高級政府官員的標準程序。
在我8年多的局長任期內,瑪麗蓮和我一直在擔心孩子們的安全。除非將他們納入證人保護計劃,否則無法完全保證孩子們的安全,但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里,零風險是不存在的。
對于讓特工跟著孩子們整天待在學校里這個問題,我的想法是:這根本不是孩子們自然成長的方式。因此,我們選擇了簡單實用的替代措施。由于可預測的線路上最容易發生襲擊和劫持,所以我們的人會跟著孩子們往返于學校。我們還確保學校的管理人員和教師了解我們對孩子安全的擔憂。感謝這些學校的官員在這方面的出色工作,他們采取了對進入大樓的每個人進行安檢的措施。在弗吉尼亞州的費爾法克斯縣,警察會一天數次在我們家周圍巡邏,他們是我們出現緊急情況時的第一回應者。
至于家庭旅行,我們每次都盡可能悄悄地離開,到哪里都不大張旗鼓,即使玩得高興時也保持低調,但這未必總能奏效。有一次我們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希爾頓黑德度假,我的小兒子受傷了,我就帶他去醫院并坐在他身邊等著大夫來縫針。當時正好有幾名當地的副警長押著4名戴著手銬的犯人去治療。
“等會兒,”其中一名犯人邊說邊盯著我看,“我在哪兒見過你。”
“不會,”我告訴他,“我們是從外地來的。”
“不,不,”他堅持道,“我見過你!”
“你當然見過他,”其中一名副警長最后大聲說,“他是聯邦調查局局長。”
“謝了。”我再一次暴露了。
當我離開家或辦公室時,走到賓夕法尼亞大道去喝咖啡時,去見司法部長時,在白宮或中央情報局時,在飛機和火車上時,在教堂時,觀看校園演出時,開著家里的車去度假時,晚上在我的家庭辦公室里工作時,我都會隨身攜帶一把9毫米口徑的手槍。大概我唯一不帶槍的時候就是睡覺(這時候槍在床頭柜上,一伸手就能拿到)和清晨出去慢跑的時候(我知道這不是非常理性的做法,因為我是獨自一人跑在陰暗的街道上,但有些事你只能仰仗自己的信仰)。
其實我想,如果真有高手決定要我的命,他們很可能會成功,無論我帶不帶我那可靠的9毫米口徑手槍或者身邊有沒有愿意舍身保護我的特工。但我依然把它帶在身邊,既是為了保護自己,也是為了不斷提醒自己絕不要讓我的警衛倒下。多年來,這可能已經成了我的個人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