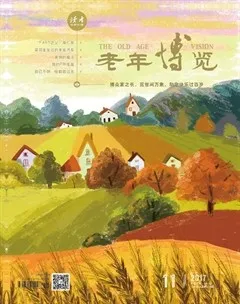隨意的美好
在北方養蘭花,難。“我從山中來,采得蘭花草。”采蘭種蘭,總盼望它能開花,久養而無花,掃興。
但我以為,蘭花即使不開花,葉子疏疏落落的,也好看。養蘭花要用古陶盆,很大的盆子,零落松散地栽那么幾株,讓它慢慢長。若有上好的太湖石,可以來個一拳兩拳,配在蘭花邊。無事時與其對坐,捧一卷線裝書,任天邊日影緩緩移動,歲月靜好。
我奶奶喜歡各種花。她每日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前院去看花。奶奶個頭小,看蜀葵時總要仰著臉。她把蜀葵叫“大花花”。蜀葵花好看,且好養,根本不用怎么照料,不知不覺,它就長起來了;不知不覺,就已經開花了!花色多,白到粉,粉到紅,紅到紫,淺紫深紫,從花株尾巴處漸漸往上,一路開起,一直開到霜降。
小院里種了很多草茉莉,顏色很雜,奶奶叫它“地雷花”,汪曾祺先生在書里叫它“晚飯花”。這花傍晚時開得最盛,所以也有人喜歡叫它“夜嬌嬌”或“夜晚花”。院里還有那種花色濃黃、花朵甚小的雛菊,我纏著奶奶把它們移入花盆幾次,每每死掉。
大麗菊是一種花瓣重復再重復的花,圓圓大大的,像饅頭,奶奶干脆就叫它“饅頭花”。晉北地區習慣稱其為“蘿卜花”,因為它的根像蘿卜。父親有一次畫大麗菊,不加一點顏色,朵朵用筆有力,有種木刻的味道。
人們種花養花,看花開,看葉子與枝干,誰會留意根呢?唯有大麗菊,一年一度,奶奶會把它的根從地里小心地掘出來藏好,不然會凍死。大麗菊到處可見,是民間隨意的美好。我曾見過一張老照片,照片上蔣先生與夫人坐在那里說笑,茶幾上擺了一瓶插花,就是紫色大麗菊。親切的繁華才是真繁華,如同世間之事,隨意,才讓人覺得真心真意。
奶奶在世的最后那年開始喜歡吊蘭。吊蘭算不算蘭花?父親喜歡畫吊蘭,說它比蘭花更入畫,更有筆墨味道。一叢一叢長起來,抽出花莖,長長的,緩緩垂下,然后又一叢一叢長出新葉。吊蘭開的花小小的,讓人心生憐愛。花蕊一點嬌黃,淡淡的,很可愛。遠遠地看它,像小溪潺潺。奶奶去世后,父親把她親手種的一大盆吊蘭搬了回來。它一長再長,父親一分再分,左一盆右一盆,最后家里到處都是吊蘭。
有一次我去某餐廳吃飯,忽然看到吊蘭。我眼前浮現出奶奶的臉,她笑瞇瞇地看著我,不說話。我跟吊蘭合了影。那吊蘭正在開花,一小朵一小朵,碎俏俏的。我要多看它幾眼—就當是替奶奶看,也不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