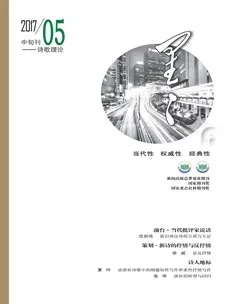“時間的沙漏有著合攏手掌的形狀”
2017-12-29 00:00:00霍俊明
星星·詩歌理論
2017年5期
我是1990年代在閱讀民間詩刊《存在詩刊》(創刊于1994年冬天)的時候,于文字中結識了陶春和劉澤球,至于現實生活中的相見則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劉澤球是擅長于寫作長詩的詩人,是不多見的具備寫作長詩的雄心和能力的詩人。時隔多年,當下仍然不乏長詩寫作者——甚至有代表性的長詩文本出現,但是平心而論我內心對于當今的長詩寫作有著諸多狐疑。在這個碎片化的價值漶散的時代,在思想越來越平庸的當口,一首長詩該用什么來獲得有力的支撐?光靠所謂的修辭、技術、情感和拉雜的隨感式的思想的余唾么?當這次集中閱讀劉澤球的一般意義上的短詩,我想這對于綜合理解劉澤球的詩歌狀貌甚至精神底里都是一次不錯的“漫游”。
我比較感興趣于詩人和空間之間的關系,這既可以具象化為日常化的細節、場景和意象群,也可以還原為寫作者與地方性知識之間的對話關系——即一個寫作者如何在一個熟悉或異己的空間最終找到屬于自我的發聲裝置并進行有效的命名。
劉澤球這部詩集《我走進昨日一般的巷子》的第一輯是“西行記”。“西部”顯然帶有逸出了這個時代的某些被忽視的精神地貌或歷史遺跡。在兩種空間和相對應的時間體驗中,在共置的歷史和現實的對話中我聽到了一個詩人在目力所及中對所見之物的細微而精神化的勘測——“從前河水里的事物 / 現在都在空中漂流”。而一個詩人光靠“目力”是難以真正打開現實和語言空間的。……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