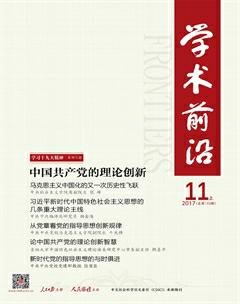“互聯網+”背景下的村落共同體重塑
朱啟彬
【摘要】我國鄉村中村落共同體日漸衰微,致使基層社會治理面臨困境。隨著“互聯網+”時代的來臨,村落共同體的重塑迎來新機遇。通過網絡社會與實體社會的相互融合,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村落外出村民與留守村民之間的城鄉聯動、基層政府與村民之間的上下聯動,營造出新型的村落共同體,促進鄉村社會的穩定、有序、和諧。
【關鍵詞】“互聯網+” 社會治理 村落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 C91 【文獻標識碼】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1.011
共同體又稱為社區,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意指在傳統的親密、單純的共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聯系緊密、互動頻繁、親密無間、守望相助的小規模群體。它是特定區域內具有共同意識和共同生活的人們組成的社會實體。村落共同體曾經是中國鄉村社會最基本的結構單元,它維系著鄉村的社會秩序,使基層社會處于安定和諧的狀態。但隨著我國市場化的不斷深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進,鄉村中的青壯年勞動力開始陸續來到城市尋找生計。成員的流動使得村落共同體內共同的活動減少,成員互動頻次降低,對集體的認同感逐漸弱化以致村落共同體逐步衰微與瓦解。村落共同體的解體帶來了多重社會后果,農村的養老問題、夫妻情感問題及子女教育問題日益嚴峻,鄉村地區社會治安狀況出現惡化態勢,基層社會治理面臨困境。因此,如何重塑村落共同體一直是各方深切關注的重點課題。
傳統村落共同體的瓦解
傳統的村落共同體處于一種相對自治的狀態。在傳統時期,中國基層的村落內部人員缺乏流動、成員間互動頻繁、社會空間相對封閉。由于在鄉村社會中人們的生計方式以種植業和手工業為主,日常生產生活多圍繞土地開展,因此人們扎根在泥土中,很少發生遷移。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世代繁衍,相互熟知,知根知底,成員的社會交往頻次較多,交往所涉范圍較廣。傳統村落在自然空間上的限制也影響了村落的社會空間范圍,成員的生產生活均富于地方特色,不同村落的成員相互之間的交往范圍有限。在相對封閉的村落中,穩定而持久的傳統力量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人們的行為規范準則依據的是世代沿襲下來的禮俗。村落成員的行為若是有違禮俗,則會受到其他成員的輿論譴責,甚至喪失村落成員的資格。因此,村落便在禮俗的作用下安定有序。
隨著市場的介入,村落共同體開始逐步瓦解。市場化改變了人們的謀生模式。在傳統的村落中,成員除了少量的生產生活用品外,大部分均是自產,在自家的田地種上糧食便可吃飽,用手工織成布匹便可穿暖。市場的介入使種植業和手工業均受到很大沖擊。農業生產更多地依靠化肥農藥及機械化作業,生活中的必需品也多為村落不能自產的工業產品。原先村落自給自足的狀況因市場的介入而變得難以為繼,村落成員的交往范圍擴大,和外部世界建立起各式各樣的聯系。在和外界取得廣泛聯系的同時,村落內部成員之間的互動開始逐漸減少,鄰里之間日常的相互幫助逐漸被專業化的服務所代替。市場化也使得村落成員的價值取向趨于多元,原先奠基于農民道義基礎上的行為逐步被經濟理性所代替,換工等行為被雇傭關系所代替,村落成員間的感情開始趨于淡薄。
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也加速了村落共同體的瓦解。城市化促進了村落人口的快速流動。城市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村落中的青壯年勞動力開始奔向城市尋找生存空間,留在村落中的是一些在城市中不易尋得工作機會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大批村落人口向城市的遷移,使得村落逐步成為一種無主體的熟人社會。人口流動使得村落內部的相互交流機會減少。外出務工人員不再參加或很少參加村落的公共事務,與村內的聯系往往局限在家庭或家族內部,而且這種聯系依靠非面對面的互動完成,相互之間的交流僅停留在表層,缺乏深度與廣度。人口流動使得村落既有的行為規范失去效力,內生于村落共同體的禮俗失去了往日效力,年輕人的行為更多地遵循在城市中學習到的規范。而當這種規范與村落中的禮俗相背離時,他們更愿意接受城市中習得的、更貼近于自身生活經驗的“城市規范”。
基層社會治理呼喚村落共同體的復歸
村落共同體瓦解后鄉村社會呈現出新樣貌。首先,村落的邊界變得模糊起來,成員之間雖然相互認識但缺乏了解。一方面,村落內部分成員流向城市,只是在過年過節或家中有重要事項的時候才回到村中。和村落的其他成員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必要的往來,缺乏對他們的了解。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動不僅包括村落內部人員的流出,也包括村落外部人員對村落日常生活的介入。由于村落的逐步開放,一些村落外部人員也獲得了在村落內生存下去的機會,這些外來的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充分參與村落的公共生活。其次,村落成員之間的關系變得淡薄,日常生活集中在家庭中,對于村集體的活動參與熱情不高。外出務工人員更關心留在村落內的其他家庭成員的生活狀況,比如父母的健康狀況、子女的教育狀況等,而對于村落的集體事務往往不愿意投入過多的時間與精力。留在村落內的成員對于集體事務則缺乏足夠的能力,也不愿投入足夠的熱情。再次,隨著村落邊界的日益模糊,村落成員對村落的集體認同感降低。村落作為一個整體,很難在生產與生活中給其成員提供足夠的保障。外部力量對村落的滲透也使得村落成員不再完全依賴村落提供的資源生活。在此情景下,村落成員對于村落集體的認同感降低,村落發展得好壞和成員的切身利益關系不再那么緊密。
隨著村落共同體的瓦解,中國的基層社會治理面臨著諸多困難。首先,村落成員的行為準則趨向多元,禮俗難以形成有效的規范約束村落成員的行為。隨著進城務工人員的增多,他們的行為方式逐漸脫離村落中的固有模式,開始向城市中的市民看齊,更加注重行動的效率,追求合乎經濟理性的行為目標。而在村落中,許多年長的村民仍然固守著禮俗所形成的規范。這樣,村落中便同時存在多種行為準則,以致不同類型的村民相互不認同彼此的行為觀念。其次,村落成員的行為失范造成村落社會秩序的混亂。村落成員在行為意識上的差異逐步擴展到實踐中的具體行動。有些人過度追求經濟理性而輕視傳統禮俗的約束力量。再次,隨著村落共同體的解體,村落內部自治出現問題的同時,基層政府對于村落的管理也面臨著許多困難。村落中成員的高流動性造成基層政府管理上的困難。許多時候,政府在村落的管理上面對的群眾多為老人、婦女和兒童,而村中的青壯年勞動力由于分處全國各地而很難納入有效的管理范圍內。村落中人們行為方式的多樣化也使得基層管理出現困難。比如年輕人傾向于依法辦事而不能充分考慮當地的禮俗,結果是雖合法但不受村民尤其是老年村民的認同,進而產生各類矛盾,增加基層治理的困難。endprint
互聯網的普及給村落共同體的重塑提供了契機。首先,互聯網加強了城鄉之間的聯系。通過電腦、手機等設備,分處城鄉之間的人們可以進行通話、視頻,互換信息,交流情感。其次,互聯網也使得城鄉之間在信息上實現了一體化發展。在城鎮中能獲取的最新資訊,通過互聯網在農村地區也可以同時獲得。城鄉之間信息的交流也增強了村落內部成員的互動頻次,加強了彼此之間的相互聯系。隨著村落共同體的重塑,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局面也逐步得到好轉。
“互聯網+”背景下村落共同體的重塑
在村落共同體瓦解的同時我國逐漸步入了網絡社會階段。2015年,《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發布,提出要形成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創新要素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之后,伴隨著“寬帶中國”戰略的實施,互聯網在我國逐漸普及開來。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2017年初發布的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至2016年底中國網民規模已達7.31億人,其中農村網民有2.01億人,占比27.4%。在2016年全國新增網民4299萬人中,使用手機上網的群體占比達到80.7%。新增網民呈現兩極化趨勢,19歲以下、40歲以上人群占比分別為45.8%和40.5%,互聯網向低齡、高齡人群滲透明顯,農村網民呈現快速增長態勢。而農村網民中互聯網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娛樂、溝通類基礎應用。2016年,網民手機端中最經常使用的APP為微信,占網民總數的79.6%,其次為QQ,占網民總數的60%。依此基礎性的技術支持,在農村地區可以依靠互聯網的應用對村落共同體進行重塑。
在人口流動性增強的背景下,可以依靠互聯網構建新型村落共同體。傳統的村落共同體變遷緩慢,缺乏變動,處于一種相對靜止的狀態。當前,隨著人口流動性的增強,原先的村落共同體已失去其存在的土壤。通過互聯網的應用,村民雖然處于流動中,但以村落為單位的微信群、QQ群等把相對分散的村落成員重新聚合在一個相同的網絡空間內。不管村落成員如何流動,網絡空間處于一種相對固定的狀態,這就為村落共同體的重塑提供了可能。在重新塑造的共同體內,傳統村落共同體的聯系緊密、互動頻繁等特點仍然得以體現。具體塑造途徑如下。
首先,通過村落微信群、QQ群的建設實現城鄉之間的聯動。網絡社會時期,要使現實世界和網絡世界實現有機融合,在村落中由于人口的分散,可以借助各類群體共享的網絡空間把村落成員重新聚合在一起。一方面,要加強村落共享網絡空間的建設。通過熱心村落集體事務的成員建起村落微信群、QQ群,至少保證每個家庭有成員入群,這樣在信息上便可保障全體村落成員的共享。在已經擁有了微信群、QQ群的村落中,村內成員的關系由于參與討論共同的話題而使得彼此間關系變得親密。某位成員外出務工的職業、收入、生存狀況等均可被其他村落成員獲悉,在增強群內成員感情的同時,更是給其他成員的個人發展提供了機會與參考。通過網絡空間的討論不僅可以增進成員之間的互動,還可以劃分出村落的社會邊界,增強成員對村落的認同感。另一方面,要加強村落共享網絡空間的管理。微信群、QQ群的管理者應該積極引導群內成員參與村落中的公共事務,并把網絡空間中的討論轉化成現實生活中的行動。在共享群內成員外出的各類信息的同時,還可以討論村落內存在的老人養老、兒童教育等大家共同關心的話題,并找出適當的方法實現彼此間的互助。隨著成員間互動頻次的增加與范圍的加深,成員間的感情日益深厚,村落內各類矛盾日益減少。
其次,通過基層政府官方微信、網頁等信息的發布實現上下之間的聯動。一方面,基層政府要加強自身政策的宣傳,讓互聯網成為基層政府的傳聲筒。針對農村中大量的網民,基層政府可以通過網絡空間實現對村落的基層治理。可利用合適的形式在網絡上發布各類政策、地方生活資訊,讓普通村民了解基層政府最新的工作動態,以便理解并配合基層政府的行動。通過網絡空間,基層政府的信息也被身處全國各地的在外務工人員第一時間獲悉,并和村內成員商定應對方案,以此實現對村落公共事務的參與。而基層政府在此過程中也順利實現對分散的村內成員的“跨區域管轄”。另一方面,基層政府要注意傾聽村民的心聲,通過互聯網收集民意。通過網絡空間中的留言板塊,及時全面地了解村民對某項政策的具體看法,不妥之處可實現最快速的糾正。基層政府還可以通過網絡空間監督政策的實施,讓村民真正享受到政策帶來的益處,盡可能及時地避免工作中的失誤。通過上下之間的互動,讓互聯網真正成為連接基層政府與普通村民之間的橋梁,讓基層治理工作變得順暢。
需要指出的是,村落共同體的重塑不是指傳統村落共同體的跨時空移植,而是指在新的條件下借助互聯網讓網絡社會和現實社會實現有效融合,借助互聯網的力量塑造安定有序的鄉村。在村落共同體的重塑過程中,落腳點要放在村落內部,借助村落本身的內生力量實現村落的有效治理,同時輔以基層政府的具體工作跟進。通過村落成員內部在網絡空間中的互動,實現村落成員相互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培養成員之間的親密感、對村落的認同感等,進而塑造村落安定的秩序。在此基礎上,政府的基層社會治理難題便會迎刃而解。相信隨著村落共同體的重塑,定會建成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參考文獻
劉芳,2011,《社會學視域下“共同體”概念的發展與流變——兼論中國鄉村社會學的共同體研究》,《理論界》,第11期。
劉玉照,2002,《村落共同體、基層市場共同體與基層生產共同體——中國鄉村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社會科學戰線》,第5期。
費孝通,1998,《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
責 編∕樊保玲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villages in rural China is getting weak,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anage the primary-level community. With the incoming era of "Internet +",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has embraced new opportunities. Through the fusion of the real society and the network,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can help to maintain the close ties between villagers working in the city and those staying at home and between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the villagers, and thus create a new type of village community, so as to build a stable, orderly and harmonious rural society.
Keywords: "Internet +", social governance, village communit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