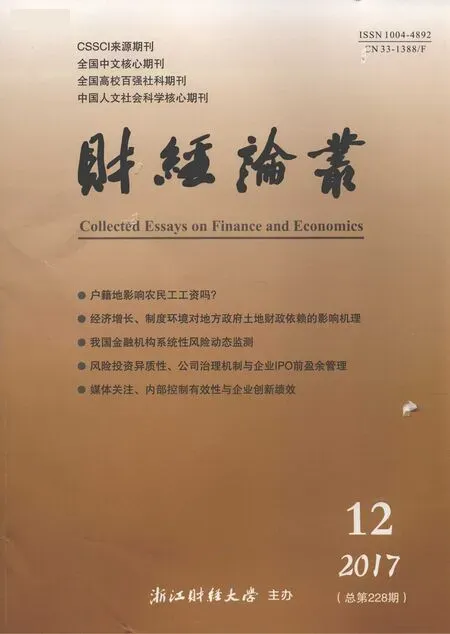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分析
姚林如,楊海軍,王 笑
(南昌航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63)
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分析
姚林如,楊海軍,王 笑
(南昌航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 330063)
為權衡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工具的利弊,本文從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構建一個不同環境規制工具的統一理論框架,比較分析各種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結合我國環境規制的執行情況及相關數據,實證檢驗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程度,結果發現企業績效與命令型環境規制工具呈顯著負相關,而與市場型呈顯著正相關,據此為環境規制部門合理選擇環境規制工具給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命令型環境規制工具;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企業績效
一、引 言
一直以來,不同環境規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程度是學者們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Weitzman(1974)通過理論證明當預期邊際收益較為平坦時,環境稅收方式比采用單一的命令控制型的環境規制工具更利于企業的利潤[1]。李永友和沈坤榮(2008)則通過分析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下企業的污染減排曲線,發現短期內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對污染的降低比較明顯,但在長期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的污染排放,也無法激勵企業的技術創新[2]。馬富萍和茶娜(2012)、賈瑞躍等(2013)的研究表明污染企業之間的治污成本若存在很大差異,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就比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更有效率,對企業績效產生的正影響更加顯著[3][4]。而宋爽(2017)認為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緣于不同區域不同發展階段決定了其對環境保護的差異化訴求,因此有必要選擇恰當的環境規制工具或遞增的環境規制強度,以實現預期的效果[5][6]。
區別于以往研究側重于單一環境規制工具的分析范式,本文建立一個簡單的不同環境規制工具的統一理論模型框架,以便于比較分析各種環境規制工具下企業產量、價格和利潤的均衡結果。結合我國環境規制的執行情況,本文利用《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等統計數據,實證分析不同環境規制工具下企業績效影響程度,并根據分析結果為選擇合適的環境規制工具給出相關建議。
二、理論研究模型
假設企業績效簡化為利潤指標,而環境規制部門是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在一個競爭性市場上存在n家制造型企業,生產某種同質產品。這n家企業產生的總污染物為M,M與產量呈正相關、與治污力度呈負相關。D(M)代表污染物排放對社會造成的損失,我們采用思德納(2005)的社會福利函數W=-D(M)[7],具體形式為:
W=(pq-c1q-c2e)-D(M(q,e))
其中,q為產品在市場上的總供給量,p為產品價格,c1為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c2為企業一單位的污染物的治理成本,e為某種環境規制工具下污染物的治理量。M為企業排放的污染物數量,與產量呈正相關、與污染物的治理量呈負相關。因此,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條件為:

(1)

(2)
式(1)的左邊可看成是增加一單位產量企業獲得的收益,右邊是增加一單位產量而提高的成本。其中,既有企業的私人成本,也有企業排放的污染物產生的外部成本。式(2)表示企業一單位的污染物的治理成本是污染物對社會的邊際損害和企業的邊際治污力度的函數。 也就是說,在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企業最佳邊際治污成本等于對社會邊際損害成本。因此,在以下分析不同環境規制工具下的社會福利函數時僅考慮企業最佳邊際治污成本。
(一)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
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主要包括強制性技術和績效標準,它們在靈活性、減污效率及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上有所不同。在競爭性市場中,設a為市場容量且a>0,b為產品的供給彈性且b>0。企業i的單位生產成本為c1,單位產品的污染量為v。在強制性技術的環境規制工具下,假設單位污染物的末端處理成本為m,其利潤函數為πm1=(a-nbq)q-c1q-mvq。而在績效標準規制下,假設規制者為企業i設置的最大排污量為e0,對單位產品產生的污染量,企業的治理水平為α,單位污染物的治理成本為c2,當企業排污量大于排放標準時,排放單位污染量將受到環境部門的懲罰pe,此時的利潤函數為πm2=(a-nbq)q-c1q-c2αvq-pe[e0-(1-α)vq]。按照式(1)、(2)的分析框架,企業利潤最大化時的均衡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下的均衡結果

(二)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
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主要有排污稅、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補貼和押金返還制度等。(1)考慮排污稅時,令τ為單位污染物的稅率,其利潤函數為πs1=(a-nbq)q-c1q-c2αvq-τ(1-α)vq。(2)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根據初始排污許可量的分配分為兩種情形。在有償分配下,假設企業i購買的排污許可證的數量為ef,費用為f,其利潤函數為πs2=(a-nbq)q-c1q-c2αvq+pe[ef-(1-α)vq]-f;在無償分配下,ef則為企業i無償得到的初始排污許可量,超出的排污許可量的支付成本類似于超過命令控制型績效標準時每單位污染量受到的罰金pe,其利潤函數為πs3=[a-c1-c2αv-pev(1-α)]2/4nb+peef-f。(3)考慮環境補貼時,假設企業每減少一單位的排污量,政府給予的補貼為s,其利潤函數為πs4= (a-nbq)q-c1q-c2αvq+sαvq。(4)考慮押金返還制度時,令d為每單位污染物應繳納的押金,pe同樣類似于超過績效標準時每單位污染量受到的罰金,其利潤函數為πs5=(a-nbq)q-c1q-(c2+d)αvq-pe(1-α)vq。按照式(1)、(2)的分析框架,企業利潤最大化時的均衡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下的均衡結果

1.比較排污稅和排污權有償分配的均衡結果
如果環境規制部門制定的環境稅率是合理的,那么理論上單位排污許可證的價格和排污稅率應該是相等的(即τ=Pe),這兩種規制工具下的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均衡價格和產量是相同的。如果環境規制部門在初始排污權分配時價格合理(即f/ef=pe),則這兩種規制工具下的企業最大利潤也相等。但在使用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時,為鼓勵排污企業進行治理污染,環境規制部門在初始排污權有償分配時制定的單位排污許可證的價格較低,此時治污效率高的企業就可額外受益。
2.比較排污稅和初始權無償分配下排污權的均衡結果

3.比較排污稅和政府補貼的均衡結果

4.比較排污稅和押金返還制度的均衡結果

三、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計量模型的設定
根據上述的理論模型,并借鑒馬富萍和茶娜(2012)、賈瑞躍等(2013)關于計量模型的設計思路[3][4],本文的企業利潤函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形式,并對函數兩邊取對數處理。具體的計量模型如下:
lnlrit=α+β1lnstsit+β2lnpwfit+β3lnzwit+β4lnkyit+ui+eit
其中,β1、β2、β3、β4是待估項,i、t分別代表不同區域的不同年份,α表示不隨單個數據變化而變化的截距,ui表示個體效應,eit代表隨機誤差。關于其他變量,下文再予以詳細解釋。
(二)變量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從《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獲得。鑒于三同時制度執行合格率為非常重要且不可取代的指標,但該指標的統計在2010年后相關年鑒上不再更新,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我們選取2003~2010年的面板數據,時間跨度為8年。由于環境污染的來源主要是工業產業,所以相關變量的數據選取的是我國規模以上的大中型工業企業(見表3所示)。

表3 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被解釋變量為企業績效,但企業績效由很多方面構成(如企業利潤、市場規模、企業競爭力和生產率等)。基于此,研究企業績效和環境規制的關系時,我們選擇企業利潤(lr)作為企業績效指標,采用我國各個省份規模以上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利潤數據。
核心解釋變量為命令控制型和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在我國,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的強制性技術和績效標準具體應用形式為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三同時制度”。其中,“三同時”制度的使用時間最長、范圍最廣,最能代表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在我國的應用狀況,故我們選取“三同時”制度(sts)的執行合格率作為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的執行情況。從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應用來看,除排污收費制度從2003來在全國普遍使用外,其他的一些制度在國內使用率不高,像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制度只是在某些城市進行試點。因此,本文選取排污收費制度來代表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以各個省份的排污收費(pwf)總額作為排污收費制度在我國的執行情況。
在研究環境規制對企業績效影響時,除需考慮使用的環境規制方式外,還應考慮企業的治污投入(zw)和生產上的科研投入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借鑒賈瑞躍等(2013)的做法,本文采用我國規模以上企業廢水廢氣處理設備每年的運行總費用代表治污投入,以大多數學者運用的企業每年用于生產性科技研發(ky)的內部支出費用代表生產上的科研投入。
(三)數據分析
1.相關性分析
我們運用stata13.1對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相關性系數矩陣(如表4所示)。從表4可看出,企業的利潤與大部分自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相關,這初步表明因變量和自變量在統計水平上具有相關性。核心解釋變量sts和pwf的相關性系數不高且不顯著,所以核心解釋變量不存在共線性問題。另外,觀察到某些控制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且系數在0.4~0.8之間,但隨后的回歸分析中方差膨脹因子(VIF)均超過1.0,表明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并未對后續的回歸分析造成影響。

表4 變量的相關性分析及方差膨脹因子檢驗結果
注:N=240,p<0.05。
2.平穩性檢驗
因采用面板數據易出現偽回歸問題,在正式回歸前先對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面板數據n大t小的具體特征,我們選擇適合該面板數據的Levinlin單位根檢驗。對數據進行一階滯后的Levinlin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從檢驗的結果可看出,數據的單位根檢驗結果明顯小于0.05,說明選取的數據是平穩的,可做相關性回歸分析。

表5 相關變量的一階滯后的Levinlin檢驗結果
(四)實證結果分析
根據上述對數據相關性分析,我們選取的數據不存在嚴重的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且數據是平穩的。因此,本文采用處理面板數據最常用方法中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運用stata13.1軟件后得到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從結果來看,F值比較顯著,進一步說明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是比較合適的。考慮到環境政策的實施對企業的利潤可能存在滯后效應,所以本文對模型進行滯后一期、滯后二期和滯后三期的檢驗。從回歸結果可看出,統計量F的概率均為0.0000,說明模型的整體擬合度比較高,模型整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的“三同時”制度的實施對企業績效產生顯著的負影響。特別是在實施的即期,產生的負面影響比較大,雖然在滯后一、二、三期對企業績效的負面影響降低了,但依然比較明顯且趨于穩定。由于“三同時”制度在我國已實行三十多年,樣本期間內的平均執行率已達到95%以上,說明這項制度在我國執行得很好,但“三同時”制度設置環境標準缺乏一定的靈活性,企業缺乏減排的激勵,不利于企業的績效提升。
排污收費制度的實施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即期、滯后一期、滯后二期和滯后三期的回歸結果均顯示,排污收費制度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影響。一方面,這可能是因為排污收費制度的實施使治污效率高的企業治理更多的污染,繳納更少的排污費,而治污效率低的企業權衡污染物的單位排污費和企業單位治理成本后決定治理多少單位污染,最終有利于企業利潤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排污收費制度的實施使企業積極尋找治污成本低的技術,或使用更高生產率的技術以產生更少的污染,從而使生產效率提高,企業的績效明顯改善,這即是環境規制帶來的創新補償效應。
治污投入對企業的績效產生正向影響。這可能是因為企業的治污投入使企業產生的污染物減少,進而免受政府環境部門的懲罰。企業對治理污染的投入一定程度上還有利于企業的社會聲譽,消費者更擁護環保企業的產品,這對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的提升產生巨大的動力,從而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
生產性的科研投入對企業績效的提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現有研究相同的是,我們的實證結果進一步證實企業的生產性科研投入雖在短期給企業帶來成本的增加,但長期由于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和治污效率,最終促進企業業績的提升。

表6 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
注:括號內為標準誤差;滯后一期是指一年。
四、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的理論研究模型表明,比較命令控制型兩種環境規制工具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使用強制性技術時企業利潤大于使用績效標準時的情形。相比于命令控制型的環境規制工具,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擁有更多的靈活性。通過比較分析后發現,如果政府部門的環境稅設置得比較合理,那么使用環境稅和有償的可交易排污許可證制度時對企業的績效影響是相同的;相對于排污稅而言,初始權無償分配的可交易排污許可證對企業績效的提高更有好處,政府補貼情況下有利于提升企業的利潤,但押金返還制度下企業的利潤比實施排污稅時要小。從實證檢驗結果來看,我們發現命令控制型的“三同時”制度的實施對企業績效產生顯著的負影響,排污收費制度的實施有利于企業績效的提高。據此,我們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一)創新環境規制工具類型,采用更有效率的環境規制工具
不同的經濟運行體制決定了不同環境規制工具的作用機制和實施效果。我國現階段的環境規制大多采用單一的工具,且以命令控制型的環境規制工具為主。它不僅使規制部門的監管成本較大,而且可能阻礙企業績效的提升。隨著我國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應成為主要的選擇類型。
(二)實現環境政策的預期效果需堅持環境規制工具的組合拳
理論和實證分析表明,命令控制型環境規制工具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排污企業的懲處力度。若對排污企業的處罰力度小,則無法形成相應的減排激勵機制。而市場型環境規制工具雖會顯著降低行政成本,但其效果取決于市場機制的完善程度。因此,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要實現環境政策效果,就需堅持環境規制工具組合政策,相互之間取長補短,從而創造一個更有效率目標導向的環境激勵。
[1] Weitzman M.L. Price vs Quantiti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41(4):477-491.
[2] 李永友,沈坤榮.我國污染控制政策的減排效果——基于省際工業污染數據的實證分析[J].管理世界, 2008,(7):7-17.
[3] 馬富萍,茶娜.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制度環境的調節作用[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2,(1):60-66.
[4] 賈瑞躍,魏玖長,趙定濤.環境規制和生產技術進步:基于規制工具視角的實證分析[J].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報,2013,(3):217-222.
[5] 宋爽.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影響污染產業投資的區域差異研究——基于省級工業面板數據對我國四大區域的實證分析[J].西部論壇,2017, (2):90-99.
[6] 夏勇,鐘茂初.環境規制能促進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脫鉤嗎?——基于中國271個地級城市的工業SO2排放數據的實證分析[J]. 商業經濟與管理,2016,(11):69-78.
[7] [瑞]思德納著,張蔚文,黃祖輝譯.環境與自然資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AnalysisontheInfluenceofDifferentEnvironmentalRegulationToolsonEnterprise’Performance
YAO Linru,YANG Haijun,WANG Xi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
In order to weig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simple unified theoretical model framework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from the angle of maximizing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the above mode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en, combin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related data of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rporate performance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ommand-control environment regulation tools, and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 regulation tool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offers some proposals abou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selection for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epartment.
Comm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Enterprises’ Performance
2017-01-12
江西省教育廳科技研究基金資助項目(GJJ11506);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資助項目(12YJ30);江西省軟科學研究計劃資助項目(20132BBA10013)
姚林如(1972-),男,江西樟樹人,南昌航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楊海軍(1970-),男,江西高安人,南昌航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王笑(1990-),女,河南商丘人,南昌航空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生。
F270
A
1004-4892(2017)12-0107-07
(責任編輯:化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