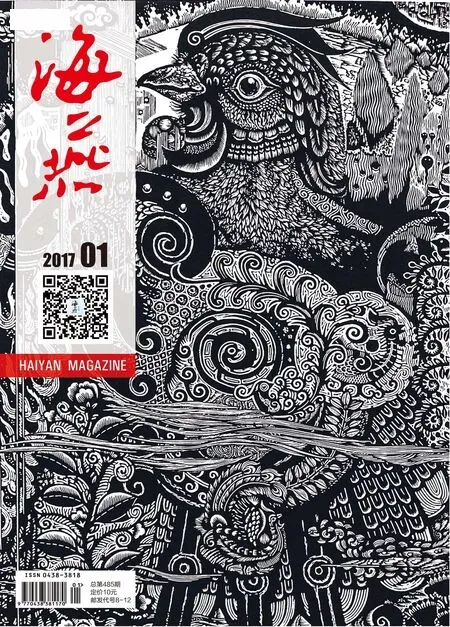春天是喊出來的
□喻言
春天是喊出來的
□喻言
靈魂是身體的搬運工
我把身體從北京搬到成都
再從成都搬回北京
這么多年,來來回回不知有多少回
對于這具身體,這條航線上的空姐
可能比對自己的男朋友還熟悉
當然,我偶爾也把它搬到別的地方
就像一次投錯了的包裹
很快又退回原址
江湖上有太多的大事
需要它親自出場
我把各種表情安放在它臉上
我把溫度調節在它皮膚上
在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表情
與不同的人握手
讓他們感受到它手上傳遞的溫暖
有時,它實在太忙
躲在幕后,用聲音發出指示
有時用文字和圖片
在微信朋友圈發兩首小詩
表示它在,一直都在
低調、親和、五湖四海
這個世界上,太多的事身不由己
它卻分身乏術
這么多年就只能把它不停搬來搬去
它變得越來越龐大,越來越沉重
我想總會有一天,再也無力搬動它
也許那一天我會從骨頭里鉆出來
去見一見那些相交多年的兄弟
會一會那些一見如故的朋友
空氣
空氣像一塊尖銳的玻璃
透明的危險,往往視而不見
細菌、病毒、霾…
一切肉眼看不到的物質
混身在陽光和氧氣中間
裝扮成平民的恐怖分子
悄無聲息侵入呼吸道
對肺葉發動閃電戰
潛入血液,抵達體內每一個角落
把基因組織發展為基地組織
把每一個細胞都演變成肉體炸彈
讓每一片黏膜千瘡百孔
讓每一根神經命懸一線
我們全部的抵抗就是屏住呼吸
不得開聲吐氣,大聲喧嘩
或者戴上口罩,重重疊疊的棉布
就像一層層審查機構
我們內心的憤怒被層層過濾
變成一聲長長的喘息
冬天的稻草人
城市化的郊區,稻草人正在消失
冬日空寂的田野,這個孤零零的幸存者
身軀歪斜,肢體殘缺
一只眼睛空洞洞泄露身后的秘密
一只眼睛偏執地堅守身前的一切
霧霾中的祖國面目模糊
消瘦的河流、干枯的山巒退向遠方
鋼鐵的塔吊正在逼近
他的獨臂斜指天空
張大嘴卻發不出聲音
七月,記憶中蟬鳴的午后
一陣暖風壓低了莊稼沉甸甸的頭顱
露出稻草人挺拔的雄姿
天空的鳥兒,盜竊糧食的飛賊
驚慌逃竄,墜落遠方的屋脊
城市龐大的輪廓線越來越清晰
佇立在烈日下的身影紋絲不動
稻草人身后的村莊
炊煙裊裊升起
殘存的記憶是一瓶打翻了的鏹水
蝕穿了稻草人驕傲的骨頭
他吐出心、吐出肝、吐出肺
剩下的身體被雨水泡脹
一陣風就骨肉疏離
他站在這里,站在南方
陰冷潮濕的空氣中
一種殘忍的意志支撐著
歷經冬天的煎熬
曬太陽
像出水的八爪魚一樣攤開
冬日霧霾中發霉的身體
需要一次充分的晾曬
陽光的溫暖由表及里
血管里液體一點點加速
靜謐中聽見遠方溪水的流淌
這部老朽的機器
每一個零件都已銹蝕
陽光的絨布輕輕擦拭
那些生命細節中的積垢
需要加力,再加力一些
天空中飄來的風
有一絲涼意
猶如最后一道拋光工藝
陶醉在陽光中的肢體
猛然驚起
灰塵
這不起眼的小東西
有時是我們前生
有時是我們后世
飛舞在空氣中的
跌落在案臺上的
我們都無法把握
甚至無法看清
它爬在我們睫毛上
如雪掛在樹枝上
從早到晚,越結越厚
厚到睫毛無法承重
枝斷雪崩
我們疲憊地閉上眼睛
它從鼻孔鉆進我們身體
如一種主義鉆進我們思想
它順著呼吸管爬進去
一直爬到肺部停下來
日積月累,最后像一座山壓在那里
讓我們無法呼吸
如果某一天我們壽終正寢
最終化為灰塵
與別的灰塵混為一體
如果靈魂不死
這些灰塵或許重新匯聚
長出一具嶄新的身體
氣球
被風灌滿
輕浮得像一個
在異鄉街頭尋找愛情的少年
我的內在如此充實
我的外在如此龐大
貼著摩天大樓的玻璃幕墻
看見自己的身影
節節攀升,毫無阻礙
我的身下是仰視的目光
以及模糊不清的驚嘆和歡呼
我已無法停下
比空氣更輕盈的身體
被風輕輕一抬
無法遏止的上升比欲望更強烈
升上去,升上去
摩天大樓之上
天空的皮膚輕薄得
像一個即將破滅的夢
登頂的瞬間
金屬的銳角露出猙獰
身體輕撞,發出一聲嘶喊
突然變得如此空虛
空虛得只剩下一層皮
如同被炮火擊碎的半面殘旗
飄飄搖搖墜向大地
春天是喊出來的
脫下棉衣那一刻,我就開始喊
脫下秋衣秋褲,我接著喊
脫光所有的一切,我還在喊
陽光下喊
霧霾中喊
從早晨喊到傍晚
喊得夕陽西沉不斷推遲
喊得風中的寒意漸漸消散
我對著荒蕪的原野喊
一縷縷新綠拱出地面
我對著空寂的村莊喊
一扇扇門窗紛紛打開
我對著河流喊、對著山麓和森林喊
對著星空下的城池喊
喊出浪花飛濺
喊出蟲鳥和鳴
喊出彩旗飄飄
一匹馬打城邊跑過
一群馬打城邊跑過
夜深人靜,我聲嘶力竭地喊
喊出心中淤積的塊壘
喊出靈魂深處那一股執念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跟著我
一起喊
喊著、喊著
春天就這樣降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