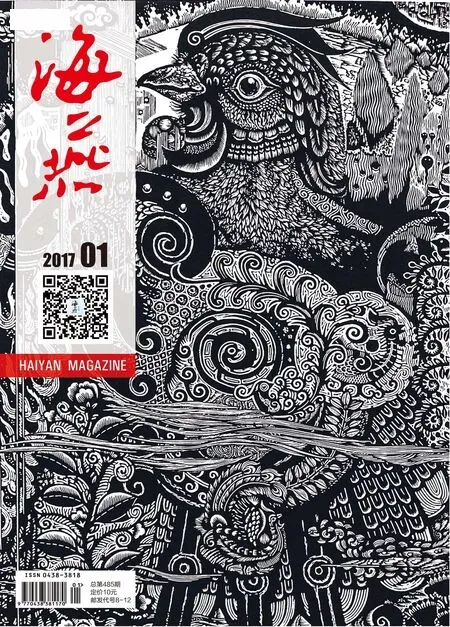大編輯的文字風景
——從《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談何啟治老師
□王玉琴
大編輯的文字風景
——從《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談何啟治老師
□王玉琴
一
我的書柜里,有一排位置,整齊地排放著何啟治老師的贈書,這些書,大多結集、完成于他退休之后。2016年國慶節前夕,當我將新收到的何老師的新著《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歸類放進書柜的時候,對這位剛剛榮升80后的忘年老友再生敬意——生于1936年9月的何老師,十幾年來漸行漸歌,將自己幾十年經過的路,凝結成文字,不僅僅外化了他內心的景致,還以自己的生命狀態,裝點出了一道別致的文化風景。由于收錄在《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中的文章,大多首發于他在《海燕》雜志開辟的“文壇師友錄”專欄,由于何老師將他的手稿陸陸續續地寄給我,再由我轉交編輯部,在將這些手稿轉換成電子版的過程中,我也就做了一些辨識筆跡、幫助校對的工作,有幸成為某些文章的第一讀者。但重讀這本書的過程。則是從整體上領略何老師通過文字展示紀實散文的藝術魅力和思想力量的過程,正如何老師所言,他通過這些回憶文章所追求的,無非是披露真相、表達真情、探求真理。而蘊含了真相、真情、真理的文字,意義非凡,當得起百讀不厭。
我認識何老師,應該是在1991年夏天。他去西北參加某位作家的作品研討會,借道西寧去看我的朋友楊志軍(《藏獒》的作者)。我便在志軍處巧遇了年過半百的何老師,談起和青海的緣分,何老師說他1974年到1976年,作為當時中央出版系統派出的唯一的援藏教師,在青海的格爾木工作過,而后強調他臉上的類似醉酒的酡紅和紅血絲,就是拜那兩年的高原生活所賜,他認真而堅持地稱其為高原紅。他的認真和堅持,讓當時生長在高原已經25年的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在我的常識中,真正的青海人若到平原生活幾年,就會褪去高原紅。哪有平原人在青海待了兩年,高原紅便經久不褪的道理。
最初得到何老師的贈書,應該是在1991年年底。我去北京出差,志軍托我給何老師捎東西。在朝內166號何老師的辦公室,我完成任務的同時,得到了何老師的贈書《少年魯迅的故事》。還記得他當時的絮叨,大致是他做編輯若干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給別人做嫁衣裳,這么多年時間,他只有自己的這么一點點可看的文字,送給我,讓我有時間的時候翻翻。不過,不久的將來,他又會有一本自己的書出版。他說他正在用業余時間一點點地完成一本小說,藍本是自己1989年6月到1990年6月在美國探親并一度到唐人街華人餐館打工的經歷。關于那次見面,我記住了兩個細節,一個是何老師談到自己只有這么一點點自己的文字時,流露出的很深的不好意思;一個是何老師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本好看的書問世。兩年后,調動工作至大連日報文藝部任小編輯的我,向他這位大編輯約稿,他也就很慷慨地支持了我這個小編輯的工作。大連日報也就有幸以《中國教授在紐約》為名,連載了他的這部紀實文學作品。二十幾年后,做了若干年編輯的我,感同身受著何老師當年流露出的不好意思——因為我至今沒有太多的文字可以拿出來說明自己的寫作水平。而何老師,在退休之后的十幾年時間里,則積累了很多屬于他自己的文字,這對還沒有退休的我,起著路標和榜樣的作用。從有樣學樣的簡單道理出發,我也就對自己將來退休之后會創造出作品來,充滿期待。
二
如果問我當代文學作品里最心儀的是哪一部,我的回答是:《白鹿原》!這部雅俗共賞堪稱經典的作品,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感受,我的體會是,這本小說從兩個方面啟發了我的人生。一是通過最良善最直心最美好的主人公們被戕害的命運震撼了我,讓我有機會以懷疑的目光打量人云亦云的歷史,使我自此能夠思考著不盲從地從青年一枚生活到了知天命之年;一是通過陳忠實塑造的活靈活現的朱先生這個人物,讓我形象地了解到了中華文化的精髓會凝結出怎樣的個體生命。受此啟發,我從此心無旁騖地在中華文化儒釋道間來回逡巡,而后一門深入,立下了不追到究竟處一定不罷休的宏愿,使此生余下的時間里不再有猶豫不決。
能有這樣的明白與篤定,需要感恩的人和事有很多,師恩、父母恩、眾生恩之外,之一是要感恩從未謀面的作家陳忠實,之二則要感恩我的忘年之友何啟治老師,他是《白鹿原》的審稿編輯之一和責任編輯之一。早在1973年冬天,何啟治老師便初識陳忠實,并約請他寫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1990年10月24日,陳忠實寫信給何老師回應自己的長篇創作,真可謂是踐行經17年之約,是他們幾十年的積淀和努力,啟發、激蕩了我的靈魂。
關于《白鹿原》和陳忠實,何老師累計有十多萬字近十篇文章對其進行毫不猶豫、理直氣壯的肯定與贊美。我做了第一讀者的,是首發在《海燕》雜志上的《陳忠實與永遠的〈白鹿原〉》。何老師這個80后。一直沒有隨時代的變化完成換筆這個動作。收到他手寫的、我代《海燕》雜志約的稿件,辨識筆跡、幫助校對、保證無誤出版也就成了我當仁不讓的一件工作。工作的過程也就是學習和感動的過程,了解著一本書怎樣凝結著大作家和大編輯的深情和厚誼,就是在體會著文學的神圣與美好,感動于他們老哥倆隨時光流轉的友誼。我期待著那些記載著他們兩人與《白鹿原》的故事和細節結集成書的日子,因為,他們之間的傳奇,是真正的人間佳話,佳話,當得起爭相傳頌。
三
如果問我最喜歡的當代詩人是哪一個,我的回答是:牛漢!
最初了解牛漢的詩,是因為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集,責任編輯谷風將《牛漢抒情詩集》送給了我,一讀,便手不能釋卷地喜歡。當其時,有那么一些寫詩的人們,爭相將簡單的道理用復雜的語言和表現形式反復纏裹著,讀來讓我不知所云,便直言不喜歡。而牛漢的詩,則為我打開了一扇門,門里面的風景,居然可以用最簡單的語言闡釋出顛撲不滅的景致,入心入魂。于是我一讀再讀,換了角度學習,依舊望塵莫及,由于不知該如何表達,于是直言最喜歡。還記得是在1992年春天,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因為在北京,就有見何老師的機會,聊天中,我告訴了何老師我對牛漢的詩的喜歡,他當時很神秘地一笑,讓我難解其意。沒想到,過了不幾天,何老師給了我一個天大的驚喜,他到魯迅文學院找我,推著一輛自行車,將我引到了牛漢的面前!
那個人生瞬間從此定格在了我的生命中。高大、健碩、開朗、明亮、慈愛、智慧,堅強……窮盡詞匯,我不能描繪出牛漢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他的精神世界該有多么豐盈,才能使這樣的一個生活在凡塵中的肉身,如此地纖塵不染。所有的人間不幸和磨難,落到他的身上,居然都能夠輕輕地抖落,該需要怎樣的心力和胸襟?而他就那么不經意間地輕輕一抖,非凡的光芒便開始四射。
見過牛漢,我便明白,所謂的詩,根本就不是寫出來的。所謂的詩人,其實是一個初心不改的存在。真正的詩人和真正的詩,是天成的,非后天的努力可以達成。
這一認識,直接導致我自詩歌《諦聽雨聲》問世后,不敢再提筆問詩,問詩便擔心顯出清淺。直到二十年后,我才能夠有詩歌《活在當下》從筆端流瀉,此后的心得是:如果我不能夠“在狀態”,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詩出現。而那個“在狀態”,卻又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言語道斷的一個存在。
2008年秋天,退休將近10年,已經72歲的何老師將一本《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放在了我的面前。我無法用準確的語言描繪那個瞬間我復雜的思緒,不知是該羞愧自己的虛度光陰,還是敬佩何老師不教日月等閑過的勤勉。細細地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無數次地灑下淚水,或擊節,或慨嘆,不僅僅為這本書的厚重,更為完成這本書的兩個人的豪情——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何老師是69周歲的小老弟,牛漢是82歲的老大哥。三年后,這本書由三聯書店出版,何老師這個小老弟72歲,牛漢這個老大哥85歲,他們兄弟倆,以157歲的高齡,完成了一本巨著。
曾經多次和何老師談過這本自傳,何老師說,他自己也暗自慶幸,為編輯、出版這部沉重而真實的《牛漢自述》所盡的綿薄之力。
他說這話時的舉重若輕,讓我體會到了他這個人內心里宏大的力量,這力量可以用心去體會,卻無法用語言去準確表達。
2012年12月,在為《海燕》雜志整理何老師手寫的《可敬可愛的牛大哥》一文時,我和何老師有過多次關于牛漢的專題電話。何老師說,牛漢對他有一個評價,也算是批評,說他性格里缺少了一點點勇敢。我反問何老師,你自己怎樣判斷自己?何老師說,他認為牛漢對他的評價很客觀。感受到何老師對自己的人生有些近乎苛求,我認真地告訴何老師,別為難自己,也別去想象自己外化的勇敢,千人千面。因為有了《白鹿原》和《牛漢自述》這兩本書做印證,他有一顆什么樣的心,已經一目了然。如果說《白鹿原》尚有冥冥中的命運的牽引,表面看來似乎是某一種幸運偏偏就眷顧了他,那么,對《牛漢自述》這本書的選題把握,見出的就是他的大丈夫胸襟。
2013年9月29日,詩人牛漢辭世,驚聞這一消息,我打電話給何老師,擔心他不能接受這驟然而至的打擊,想幫他緩沖一下情緒。他仔細地告訴我獲知這一消息的過程,我則慨嘆牛漢老前輩堪稱“同輩人的鏡子,后來人的楷模”。我們分享著心靈里共同的不舍,一起慶幸歷盡磨難的詩人這一次走得沒有一點痛苦,堅信他一定去了一個光明而溫暖的地方。沒出半個月,我就收到了何老師寄來的手稿《天堂已傳來迎賓的歌聲——敬悼詩人牛漢》,我在為《海燕》雜志整理文字時,心里明白無誤地感受到,我們這是在懷念我們共同的親人。
四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我的年齡的增長和閱歷的豐富,我和何老師之間的話題,漸次豐富。我對何老師的了解,也漸漸深入,我們之間的忘年情誼,漸漸展開,但我們的話題,永遠離不開書。
何老師是在1999年從工作崗位上退休的,已經63歲的他,在這十七年時間里,出版了近十本書。它們依次是《文學編輯四十年》《陳忠實散文點評》《何啟治散文》《何啟治作品自選集》《美麗的選擇》《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生正逢時——屠岸自述》《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還有一本《我與陳忠實和他的〈白鹿原〉》將于陳忠實去世一周年的紀念日面世。
而我的這十七年,在文字上幾乎是一個空白。1999年底,我因為一場感冒遷延不愈長達三個月誘發了甲亢,之后的時光就在堅持工作、治療疾病、恢復健康中度過。期間偶有日月平穩的日子,曾經同何老師談過我對創作經濟類題材的小說已經有素材上的積累,他立即寄來周梅森的《天下財富》等小說讓我做參考。2015年一次見面時,我對何老師說,我應該拿出時間和精力研究牛漢,他立即將書柜里若干本馬上可以拿到的、關于牛漢的資料拿給我。聯想到我因為青春年少而虛度光陰的日子里,何老師曾經對我有過“你若不寫作,我對你便一無用處”的恫嚇,心里是知道他這個大編輯,對我是有所期待的。只是我不大明白,他對我的期待,是出于他的“職業疾患”,還是他有著一雙慧眼,發現了我身上有著寫作潛力。前幾天和何老師通電話,他很關心地問起我職業生涯里的高級編輯職稱評審情況,他追問我有什么優勢,我回答說,所謂優勢,就是我是報社參評人員里年齡最大的一個。他則不失時機地追問,你有沒有一本書可以說明你的水平?我在電話的這一端嘿嘿地笑,不中他的招地說,我參加的這個評審,不需要文學作品來做業務說明。他在電話的那一端也嘿嘿地笑,遺憾我沒有中他的招。
我知道,如果我不寫出一本書來,這一事實,就是我和何老師之間的一個傷疤,他對我的成長,是費了心的。而我也是想寫一本像樣的書的,但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加,我發現,我的準備不足。這準備,不僅僅是素材上的、知識上的,還有心力、體力和耐力方面的準備。
由于何老師的近視眼在2006年的時候就已經達到了1450度,近幾年我換了多個角度勸他放棄寫作,放棄閱讀。我勸說他,老年人一定要學會虛度光陰,要把曬太陽、看風景當作每一天的重要生活內容。但就在這個勸說的過程中,我們依舊談我們之間永恒的話題——文學。期間我介紹多年的朋友、《海燕》雜志的主編李皓和他相識,意在幫助李皓重新熟悉一下一度因為新聞和廣告工作而有了陌生的文學圈。何老師慨然應允,立即呼朋喚友地組織親友團力挺,隨后則身體力行地以寫稿的方式支持《海燕》。先是有零星的單篇游記和散文寄過來,我以為是怡情悅性之作,后來則發展成開了一個叫作“文壇師友錄”的專欄。自此一發不可收,橫跨2013、2014、2015三個年度才收手。在這些文章里,他側重寫自己和當事人的交往,或者是一個剪影,或者是一幅速寫。這些首發在《海燕》雜志上的文章,就是結集出版的《朝內166:我親歷的當代文學》中的絕大部分文字,而他在這本書的最后一頁,則留下這樣的文字。其時我的眼睛已經因為黃斑變性和視網膜劈裂而幾乎失去閱讀和寫作的能力。
真是大音希聲。
五
和何老師最近的一次見面,是在2015年10月。我去他位于北京東中街的家看望他,意在了解一下視力急劇下降的何老師怎樣安排生活。
此行最大的收獲是發現他的身邊有一位很好的保姆。那是一位來自山西的大姐,本色而天然,質樸得能讓我聞見黃土高原的泥土香氣。吃飯的時候,我問何老師是不是自從用了這位大姐,生活質量沒有下降但金錢支出卻驟然下降,何老師很詫異我居然能夠很準確地把握到他生活里出現的這個新變化,問我何以會有如此神通。我則笑而不答,心里則是一份因為了解了生活之后才有的自在,并因何老師對日常生活的隨遇而安而心安。知道那位保姆大姐會讀書給何老師聽,我對她真是心懷感激。談話間了解到她生活里頗多坎坷與不順心,離開老家到北京應聘照顧何老師的生活,也算是躲開復雜取一簡單,過幾日沒有煩憂的生活。何老師和我談到,保姆在讀孫惠芬的《生死十日談》給他聽時曾失聲痛哭,何老師則囑咐孫惠芬送她簽名的著作。此一細節,依舊是非何老師不能為,因為本色如此。我看看保姆大姐,看看何老師,笑問何老師,過個幾年,你將我這保姆大姐調教成作家的可能性有沒有?何老師將目光投向虛空中,并不作答,而我因為何老師的不作答,對這位保姆大姐未來會成為作家,充滿信心。
因為擔心何老師的寂寞,在聽聞王蒙老年又遇幸福的時候,我真心的希望,這樣的幸運也能降臨到何老師的生命里。為此我梳理了一遍我身邊的單身女友,試圖按圖索驥,結果希望渺茫。可我心念里有了這樣一個想法,便很難滅去,有時和文學圈的老朋友見面,我會問他們身邊有無合適的人選。被反問怎樣的人選才合適時,我訥訥地說,我就一個想法,那個人,怎么也得有這個水準——不能把何老師那滿柜子的當代作家簽名贈書稱斤論兩地賣到廢品站去,至少要有能力辦一個微型的圖書展覽館吧。我這樣訥訥的時候,心里則惴惴著:遇見那么一個人,該有多么難啊!可要是遇不見那么一個人,何老師的日子,目前看來過得也還不錯,被這個樸素的說西北方言會做面食的大姐像過日子一樣給照顧著衣食起居。他的視力雖然下降了,但她可以讀書給他聽,簡單的文字處理,她應該也是會的。其實,能遇見這樣的保姆,也是一種福分,不知何老師是否這樣理解。
最近一次和何老師通話,是在幾天前,我問他最近身體狀況如何,他說腰椎狹窄壓迫坐骨神經的問題已經經醫生做局部麻醉封閉治療后大為改觀,活動已經不再受限制,眼睛沒有什么變化,沒向好的方向發展但也沒變壞,臉上的高原紅還在,只是紅血絲不那么明顯了。聽他說到高原紅,我忽然控制不住自己地在電話的這一端大笑,笑他幾十年來心心念念一直想變回那個尚無高原紅的白面書生。他在電話的那一端說弄不明白我為什么會笑得如此無所顧忌,我打馬虎眼說,也許是和他通電話情緒放松,心里則在想,那讓何老師心心念念了那么多年的“高原紅”,已經成了他的一個符號。而他怎樣才能明白,相由心生,那經久不退的所謂高原紅,示現的,是他心里對文學經久不退的熱,是文學之酒,讓他始終微醺而不醉。
以上若干字,有那么點道理否?
責任編輯 張明暉
實習生 邱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