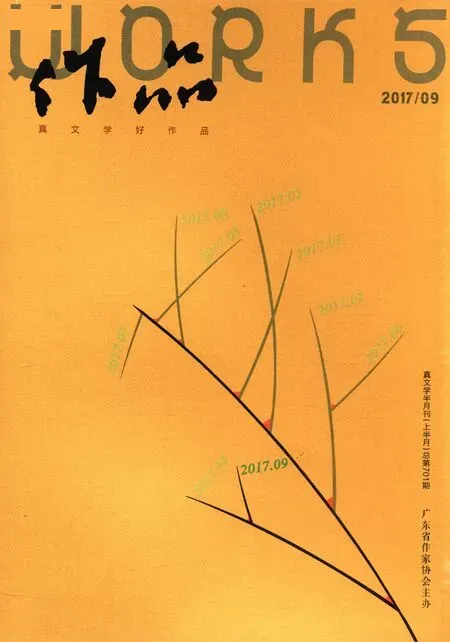少 年
文/葉延濱
少 年
文/葉延濱
葉延濱
葉延濱,當代詩人、散文雜文家、批評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曾先后任《星星》主編及《詩刊》主編。迄今已出版個人文學專著47部,作品自1980年以來先后被收入了國內外500余種選集以及大學、中學課本。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俄、意、德、日、韓、羅馬尼亞、波蘭、馬其頓文字。作品曾先后獲中國作家協會優秀中青年詩人詩歌獎,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新詩集獎(1985年—1986年),以及四川文學獎、十月文學獎、青年文學獎等50余種文學獎。
蟈蟈、骨牌和草蛇
我最早的自我游戲,有點像砌搭多米諾骨牌。那時,父親在大學任職,很大的房子,很空的家,很少的人,少到經常就我在家。平時,我不與父親住在一起,我上寄宿學校,周末回到母親那里,母親在城里的機關上班。只有放假了,我才到父親那里住一段時間。父親所在的學校,在成都西郊的光華村。五十年代初,就是建立在鄉間田野里的一所大學,連學校的圍墻都是竹籬笆。大部分的校舍都是平房,最初還有不少草舍,到了五六年和五七年,才變成了青瓦蓋頂。一九五七年那年夏天,到父親處度假,就像下鄉,住兩層的小樓,一出門,完全是鄉村景象。父親身邊一直配有警衛員,給大學校長配警衛,可見天下大定不久。警衛員姓張,名余祖,后兩年又改叫通訊員。下班沒事了,就帶著我們捉蟈蟈,抓知了。那時的蟈蟈真多,一早出去能抓幾十只回來,把蟈蟈放在玻璃窗和紗窗之間,那是最好的蟈蟈籠。蟈蟈愛叫,晚上一起叫,能壓過外面的蛤蟆聲浪。我就在窗戶上拴一個小棍,一頭捆上繩,繩的一頭引到床頭。晚上睡覺,被蟈蟈的百家爭鳴吵醒了,拉一下繩頭,咚地敲響了窗框,剎時萬馬齊喑,繼續睡太平覺。在鄉下度假,鳥啼蟬鳴,風清氣爽,常睡得三竿不覺曉,醒來,恨那大好時光昏昏然過去,不甘心。于是便在鬧鐘上下功夫,不僅要有響聲,還要有動靜。那時鬧鐘都是機械型,小鐵錘當當地敲鐘上的小鈴,叫“雙鈴馬蹄鬧鐘”。在鬧鐘小錘上系一根絲線,線的另一頭擺著一排骨牌,骨牌的另一頭,放個皮球。鈴聲一響起,絲線一抖動,骨牌一個接一個地倒,骨牌先是被動挨打,然后又去打擊下一張骨牌,傳遞著力量和不安,最后一張骨牌把力量傳給皮球,滾動的球最后砸在腦門上,起床了!這是孩子的游戲,我從這個游戲中發現我的智慧,我覺得我能當物理學家。那陣子,我愛讀蘇聯版的《十萬個為什么》。
張余祖這個通訊員的名字能叫我記住,實在是個奇怪的事。許多更熟的同學、同事和朋友,名字都忘了。他只是和我度過了兩個假期,竟然烙印一樣忘不了。他會捕蛇!晚上帶我出去散步,手里總是提著細竹棍,專門用來打草驚蛇。他說不小心踩上草叢里的蛇,會有危險。有一回,草叢中驚了的蛇不逃走,反而向張余祖撲過去。他手一揮,捏住了蛇的七寸,將那青蛇提起來,一揚臂遠遠地丟到小溪那頭去。后來,他告訴我,他父親是賣跌打刀槍藥的郎中,專門抓蛇、蝎、蜈蚣等毒蟲制藥。他從小就抓這些蟲豸,習慣了。
這本來是件不大的事,但對一個小孩,印象深刻。印象再深,能記住他的名字,還在于這個夏天不平常。那時,在校園里散步,看見教室里常發生激烈的爭論,爭得白熱化了,就會有人被架到講臺上,低頭聽別人的呵斥。
那個夏天,在我的記憶中,有兩點值得反思。一是我小小年紀,怎么就想到把所有的蟈蟈關進紗窗里呢?一面是玻璃窗,讓蟈蟈們感到風景如畫前途光明,另一面是紗窗,讓它們空氣清新自由呼吸,一旦蟈蟈們放聲歌唱自由爭鳴,我又給它們敲一棒子!二是我小小年紀,怎么也會玩骨牌游戲?看“令如山倒”,一倒都倒,被人打擊者,再去打擊別人,誰都是鏈條中的傳遞者,這不是在建造一種“機制”嗎?
那個夏天過后,我再也沒去這所郊外大學的校園里度假了。第二年,我的母親從省城下放到偏僻的大涼山“鍛煉改造”,一年后,留在了當地師范學校當語文老師。母親回不了省城,我也坐了三天的長途客車,去了大涼山,和母親做伴,在大山深處開始了底層少年的生活。
我童年生活最后一個夏天的記憶:蟈蟈,骨牌和一條草叢里的蛇。
涼山的邛海邊一排平房
在大涼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來里,有個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滬山的山,三十多年前,山下湖邊有一所學校——西昌師范學校,在這學校的一排平房中,有過我的家。那是“大躍進”后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的母親從成都下放到這個偏僻山區當一名教師。不久,我也從成都轉學到西昌,和母親一起生活。母親是“一二·九”時期的“老紅軍”,突然下放,成了一個教員,這中間沒有任何人作出說明。在下放以前,母親是省上一家刊物的副主編和某研究室的副處長,盡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過開除黨籍的處分,從某部長職務上降了職。她到西昌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員的“帶隊領導”,其他被下放者到基層勞動了,她呆在機關里閑得沒事干,又不愿去監督巡視下放人員,于是就要求到學校當老師。不知誰同意了,她就來到了這所師范學校。到學校后,她每月去領工資,發現自己的工資比校長的多得多。她想,我來鍛煉的,怎能這樣特殊?于是她交了兩份申請,重新入黨的申請和要求把工資降到低于校長水平的申請。入黨的申請沒批,工資很快降下來了。從此她在大涼山呆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母親的黨籍問題得到甄別平反,恢復了黨籍和職務,但她的下放問題和降工資問題“無法弄明白”。這二十年來她的檔案一直還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動下放和自動降級”二十年。
我從成都坐了三天的汽車,又讓一輛小馬車接到了這個家。
那時,這里真荒涼。學校沒有圍墻,野獸常在房前屋后竄。大涼山,社會治安也不太好,我到這里一星期后,就出了一起兇案。師范學校的旁邊是民族干校,那天民族干校的會計從城里領工資返校,就在師范學校下面的小路上被人劫殺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讀了艾蕪的《南行記》,如果你今天讀這本書,就可以了解我那時的心境。
比蠻荒更直接的是饑荒。我到這里后,正是全國的三年大饑荒。西昌是一個沒有大災的地方,除了夏天的泥石流,人們還沒有經歷天災的經驗。
在延安搞過大生產的母親,又在這里讓我體會到許多難忘的事。
我們在門前的空地上種上了包谷,長得挺好,但周圍都是高大的樹木,沒陽光,包谷稈就拼命地往上躥,老高老高的,夏天第一場暴雨,它們全倒了。我們在屋后種了南瓜。南瓜長得很大,二三十斤一個。
饑荒年月,冬天特別難熬。越冷越餓,越餓越怕冷。在學校里念書,一下課,大家就靠著太陽曬著的那面墻,此刻才特別覺得“萬物生長靠太陽”,“我們都是向陽花”真是唱到心坎兒上了。母親為了讓家里有些暖和氣兒,每天一大早,就到學校的大伙房去,用家里的舊臉盆,滿滿地裝一盆從灶坑里掏出來的紅炭灰。山區燒的是柴草。木炭渣和熱草灰,在盆里壓得嚴嚴實實,直到傍晚都還會有熱氣。
母親是紅軍時期參加革命的,在這饑荒年間,每月還能領到一斤肉和兩斤黃豆。母親把肥肉煉成油,把瘦肉切成末,煉在油里。這一斤肉就變成全家一個月菜湯里的油花兒了。黃豆也沒有吃過一顆整的,每回母親抓出一把,泡一夜,第二天用鐵臼搗成漿,漿汁當奶,豆渣煮菜。
在那個災年里,我開始了在大涼山里的生活。這三年我長高了兩公分。這三年我就讀于邛海另一側的一所初中——西昌川興中學。
現在,這地方是有名的航天城——西昌衛星發射基地。去年,我應邀去現場看亞太一號發射實況。我對主人說,我在邛海邊住過三年。“哎呀,那可是依山傍海最有名的風景區,著名的療養地。”是啊,我想起來了,那里確實風光美麗,只是住了三年,我都沒有注意到這山光,這水色,可惜了。還記得一件事,我是在這里學會游泳的。那年夏天,我抱著一根木頭,仰在水上玩。忽然,兩個大孩子搶走了這根木頭,我兩腳探不到底,心一驚,拼命向岸邊游去,于是沒有沉下去……
老 廟
中國的風景大致都一樣:河邊有山,山上有廟,廟里住著老和尚。一到這種風景地,就讓我想起我住過的一座老廟。這座老廟所在的地方,現在有許多人都知道——西昌。我在那老廟住的時候,西昌還是個無名的邊地小城,那城邊有個美麗的高原湖,名叫邛海。邛海的西南側,是一座風景山,叫滬山。滬山風水好,從山底到山頂有一脈,樹木特別的繁密,遠處望去,高大的樹冠起伏如浪。在這樹浪中,錯落有致地有大大小小十來座寺廟,從山腳到山頂,隱約可見,讓人想起仙山瓊閣這個詞。
我進廟不是出家。大躍進后,破除迷信,把老廟里的老和尚們遣散了,剩下個空廟,掛上一個牌子:西昌專科學校附屬中學。我和兩百個初一新生,接了老和尚們的位子。大躍進年代一切都那么敢想敢干,除了老和尚念的那本經與我們念的不一樣外,廟里其他的變化不大,所以在我前半生里,有了住廟的經歷。學的那些課本大都誠心誠意地忘了,留在記憶中的是一年多的廟里生活:簡槽、菩薩、臭蟲、花豹、老僧……
老廟生活最先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引水的簡槽。我從成都隨下放的母親到西昌,又從家里進了老廟。我個人的生活卻一下子退了八百年,也就生平頭一回知道簡槽這種東西。山泉在高山頂上,多年以來,人們把碗口粗的棕樹一剖為二,然后掏去樹心,形成一個長槽,槽與槽相接,水就越溝過坎,跳崖穿澗,流進老廟的灶房。簡槽是一槽搭在另一槽上的,如果其中一根被風吹落,被動物撞掉,老廟立刻就會斷水。我到廟里最早的勤務就是去查簡槽。全校師生飲水就靠簡槽引來的那股汩汩細流了,一天斷流好幾回,上山去查水是沒辦法的事。上山查槽,在槽的兩邊,因為常有水流滴注,所以樹草豐茂,苔厚路幽。那些簡槽不知是哪個朝代的物件,銹滿木菌和青苔,像百年老人的手。這使我感到一種恐懼,想起這原是一座老廟。
老廟里的和尚被遣散了,那些泥胎的菩薩還繼續留任。沒有了香火,就沒了神采。沒有人來頌經敲磬,就沒有了威嚴。文菩薩和武菩薩都一個個呆坐著,在我們的身邊,當留級生。聽不進三角代數,政治經濟,現在想起來,覺得真是如從第一線“退休”下來的一些人的神色。在位和不在位不一樣,在位有香火和沒香火也大不一樣。我覺得在老廟里上那些課沒算白上,就因為好好看了那些坐在身邊的菩薩面孔,想到了另一種菩薩心腸。
老廟在大山上,于是常和野物相遇。那時國家極其困難,每月定量配給二十一斤糧,三兩油,半斤肉,市場上買不到任何東西。每天都在饑餓狀態,只好上山挖山藥充饑。那地方山藥叫黏口苕,長在山間石縫里。我們下課帶上小鋤去挖。這小鋤,把兒只有手臂長,鋤口只有一寸寬,是山里人挖藥用的,在石縫里掏山藥比較順手。挖山藥會遇到野物,貓頭鷹、狼、麂子。開始怕,但餓起來,也就不覺得貓頭鷹的叫聲和狼的眼神兒恐怖了。有一天半夜里,一對金錢豹闖到老廟外,在通往廁所的后門叫了一夜。全校師生都被那叫聲嚇醒了。當時我和三個同學,就住在后門旁的一間小屋里,我們竟沒有一個人醒來。第二天早上,聽見大家對那種聲音的描繪,看見住房外十分清晰而碩大的爪子印,我們再也不敢上山挖山藥了。
在老廟沒有被花豹吃了,卻被臭蟲們飽餐了許多次,應該說,從生下來到現在為止,老廟的臭蟲我認為是最狡猾、最瘋狂和最可怕的了。剛進廟,不知廟里有臭蟲,在和尚們原先住的樓上,把地板掃干凈,打個地鋪就睡。半夜渾身火燒一樣地痛。點上煤油燈一看,身上已被咬腫了。掀開枕頭,還沒有來得及撤退的臭蟲就有十多個,用油燈照一下墻板,新開來的臭蟲大軍排成隊地前進著,用油燈一燎,燒得啪啪響……第二天我發高燒,打針吃藥一個星期才緩了過來。之后,就逃到后門旁的那間小屋,鬧豹子后,我也沒敢撤回到那老和尚們住過的樓上去。
這就是老廟留給我的印象:比和尚厲害的是趕不走的菩薩,比廟里菩薩厲害的是廟外的花豹,比花豹厲害的是真咬人的臭蟲,比臭蟲厲害的是不怕咬的老和尚……
故事在水波的底下
眼前是一派波光蕩漾的湖水,湖面不算寬闊,四周的高山環抱著它,我們站在山坡上,能清晰地看到這高山湖泊的邊緣。四周的高山,湖邊的壩子田野,構成奇絕有美景。說這湖不算大,走一圈也有百十里路,望山跑死馬,在高原這句話一定要記住,高原抬高了我們的視線,我們看得更遠,高原的空氣更加清澈,遠處的風光好像就在面前。連那天空的云也格外的美麗,高山氣流多變,云的姿態也豐富而多變,輪廓分明,有觀光者到這里,就是為了看云,叫做觀看高原云象。我站在這里,我看到的和同行人不一樣,他們是初來的客人,而我是重返少年的時光,也就是說,是四十多年前的歲月,那時,我的學校就在這座大廟里,現在大廟修葺一新,進門要收十元錢門票。而我在這所大廟讀書的時候,大廟破敗得只剩下幾個泥菩薩了。山腳下的西昌專科學校辦起了附屬中學,沒有校舍,就把我們這近兩百個初中一年級的孩子送進了大廟,不是出家,也不是習武,坐在菩薩的旁邊讀書。
不知道那些和我一起在大廟里與菩薩一起讀過書的孩子,還記得大廟里的故事嗎?我曾在一篇叫《老廟》的文章里寫過它,寫它的破敗與荒涼,寫它墻縫里厲害的臭蟲和山門外的花豹,當然,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讓我記住了一個饑餓的年月,站在這油漆一新的山門外,一陣饑餓的疼痛又咬住了我記憶的引線。怎么能體會到一個孩子曾有的饑餓感呢?好喲,講幾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細節吧。
半勺玉米粒。那是一個下午,我和兩位同學指派參加勤工儉學勞動,協助食堂管理員去城里拉一車糧食回來。從學校到城里有十五里路,人力板車空車去,一人拉兩人坐,不累。回來時拉上三四百斤大米,管理員在中間架轅,我們各在一側幫忙拉,也還行。不算累,但出了力,就更餓,傍晚回到學校,一人一碗菜湯,比平時不參加勞動的菜湯稠,有菜葉了。主食是煮玉米粒,一個四勺。打飯的大師傅后給我打,打第四勺時落下去幾粒,師傅又給我添了小半勺,大概就二三十粒。如果是大米就數不清了,玉米粒大,能數出來。大師傅把碗遞到我手里的時候,同行的那位同學突然放聲大哭。把在場的人嚇了一跳。“怎么了?”同學依然大哭,委屈得直抽搐。問了半天,他才說:“我,我為什么,少少了半勺!”也許今天的人聽了會覺得太小氣了,但那天管理員很認真地調查了此事,我們倆都沒有動筷子,用一桿小稱,把兩只碗里的玉米分別稱了。大師傅手真準,兩碗玉米竟然差不多一樣重!這才相信了大師傅解釋"破例"多加半勺的原因。那時所有的學生都在學校吃飯,八個人一桌,每天值班的同學負責分飯,分飯的工具是一桿自己做的小秤,像中藥房抓藥,把米飯分進八只形狀各異的碗里。這是一件很嚴肅的工作,如果一個人當值之時分飯不公,耍了小聰明多占了別人的便宜。這是最大的事情,他會沒有朋友:“這個人連分飯都要搞鬼!”
饑餓讓人變得小氣,也變得沒有尊嚴。這是一件讓我回憶起來都要臉紅的事情。大概是過國慶了,山下的專科學校領導上山來看望學校里的老師。老師也在大廟里住,老師也吃食堂。山下的領導給老師們帶了幾斤肉、干海帶和一些干菜。那天中午老師第一次不在大食堂打飯,而是在老師開會的小會議室聚餐。也就是三桌人,每桌有一碗肉,幾碗菜,主食是一碗米飯,分量比平時多一點。今天看來,這是太正常的小聚會了,過節嘛,領導來慰問嘛。但那天的情形完全出乎人意料。所有的同學,都不去食堂了,都圍住小會議室,里三層外三層。我也傻呆呆地站在會議室外的院子里。沒有人召集,把所有同學召到這小會議室前的是肉香味!是進了學校就沒有聞到過的肉味!都是十二三歲的孩子,聞到這肉味就傻傻地站在那里。1960年的國慶,在我一生中都不會忘記,從老師的會議室里飄出來的肉味。也許反差太大了,一座古廟,一群孩子聞到了肉味。也許今天的人永遠不會明白,其實,我可以說出當時孩子們的心情:“多香的肉味呀,為什么沒有我的,哪怕一片肉,哪怕一勺湯?為什么?”孩子們不會明白,坐在里邊老師們的心情。大家靜靜地站著,一分鐘又一分鐘過去了。會議室里的老師沒有一個人動筷子,會議室外的孩子沒有一個人說話。空氣都凝固了。最后是一位女教師忍不住了,她哭著從會議室跑出來,打破了這場可怕的沉寂,結束了“包圍會議室”事件,記得后來人們用這樣的話,講述肉香引出的安靜的“騷動”。
這就是我的初級中學,一座古廟給我的記憶。今天我站在這修整一新的“名勝古跡”面前,青山在后,碧水在前,而記憶就像面前湖水波浪下的魚,重新游進了我的生活,那半勺玉米和肉香味引出的“安靜騷動”,讓我再一次回到1960年:一個坐在泥菩薩旁讀書的孩子,他眼前的青山綠水都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在看從窗縫里投進來的那縷陽光,那陽光再挪兩寸,就可以吃午餐了……
細雨霏霏中的碉樓
往事像陰雨天里的蘑菇,一簇簇的,又分不清,于是你覺得你是一棵老樹了,老樹與細雨也許就是人生一種境遇?電視上正在播廣東省開平的碉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前年去廣州,專程到開平去看過碉樓,那是上世紀初年,在海外發了財的華僑,回到故鄉蓋的洋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絕大多數的人還在饑寒交迫中掙扎,“一個腳印里站三個賊”,富起來的華僑成了盜搶的對象,無奈之中,一幢幢富宅蓋成了碉堡與洋房的結合體。這是建筑中的怪胎,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一個畸形的文化產物。
與碉樓相似的建筑,我在童年時見過,那是在大涼山的西昌。我是1959年到西昌的,隨下放的母親從省城到了西昌。1959年,解放軍剛剛平息了大涼山彝族反動土司的暴亂,結束了奴隸制進行民主改革。關于這段歷史,老作家高纓寫過《達吉和她的父親》,當年還拍了電影,故事是說一個被彝族土司搶去當奴隸娃子的達吉,終于見到了自己的漢族父親。電影拍得美,與電影呼應的,是我在西昌處處都看得見高高的碉樓。西昌的碉樓與開平的碉樓無法相比,典型的“土樓”。西昌碉樓有三四層高,每層只有一間房的大小。碉樓緊依著老百姓平時生活的用房拔地而起。碉樓的地基是用石頭壘起來的,石頭地基上的墻體是土坯砌成的土墻。修建碉樓,就為了防止土匪和山上的彝族奴隸主、土匪搶物,彝族奴隸主搶人,搶去就當奴隸娃子。西昌現在是大涼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在我到西昌時,還是漢族聚居地區,漢人生活在平壩里,彝人生活在四周的高山上。民族之間的矛盾深淺與沖突大小,可以從村莊的碉樓數目顯現出來。童年時光,從大都市來到邊地,夜色朦朧中,那些高高站立在村莊之上的碉樓,讓我感到呼吸的空氣都充滿了恐懼。
這些石頭和土坯建成的碉樓,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新奇,也因為高原的風雨讓它們滿目瘡痍。自從西昌解放后,民族間的隔閡還沒有完全消除,但彝人土司下山搶劫的事情基本上沒有了。碉樓沒有槍炮留下的創傷,卻經不住風雨的剝蝕,像一個蒼老的守望者站在高原的陽光下。我常常著迷地望著碉樓,在陽光下,它褐紅的土墻凸凹不平,粗糙而又溝壑密布,讓人感到它已經站得飽經滄桑而不愿說出它的故事了。每一個碉樓都會有他的故事,雖然是土樓,又在窮鄉僻壤平凡得像這里的石頭和泥土,真的,就不過是一些石頭和一些泥土因為一個愿望聚集在一起而已。碉樓旁長滿高原的仙人掌和霸王鞭,這些熱帶植物,表明這里有漫長的干旱季節。旱季的大涼山河谷地區吹著燥烈的風,這些風把西昌吹得長滿了仙人掌和霸王鞭。這些風把大山也吹得兩副面孔,陽面迎風光禿禿的焦黃,陰面則被森林涂滿墨綠。不過,西昌除了旱季還有淫雨霏霏的漫長雨季。老百姓說了,西昌只有一場風,從大年初一刮到年三十。老百姓還說了,西昌無四季,下雨便是冬。
我是在一個雨季住過碉樓,那是秋天收割莊稼的日子。秋天,西昌的雨季把這里變成了最冷的日子,我所讀的初中,奉命下鄉去支援人民公社的秋收。住進村里,生產隊把我們安排在碉樓里,進入高高的碉樓,爬上扶梯,四周光線很暗,碉樓沒有我們通常的窗戶,只有五寸見方的“通氣孔”,從里面能看到外面的情景,但小得連頭也伸不出去。碉樓高也就不潮濕了。窗孔小,也就不冷了,鋪上一層干草,我們便打開被包,在碉樓里住下了。全國的災害造成糧食的恐慌。西昌這個西南高原腹地的壩子,沒有什么自然災害,但要向災區調撥糧食。糧要調走!這消息在農民中傳開,出現了瞞產和隱藏糧食的事件。派我們“支援秋收”,就是在各個要害位置監督生產隊“顆粒歸倉”。卻今難忘,我站在霏霏雨水中,頭上戴著一只斗笠,高高挽起褲腿,赤腳站在田埂上,看著農民在雨里收稻,脫粒,然后挑著一擔濕漉漉的新谷子,送到糧站去。在送到糧站的泥濘道路旁有我的同學,在糧站收谷的水泥曬場也有我的同學,在烘干濕谷子的現場還有我的同學,直到這些谷子裝上“支援災區”的大貨車。
這是一個最漫長的雨季,那些雨絲一直停留在我的記憶中。這也是一串最漫長的夜晚,那些日子,在碉樓里睡覺和休息,沒有電燈,昏黃的煤油燈也只在睡覺前點亮一會兒,滴滴答答的雨聲浸透夢境……
前兩年,我有機會再次回到大涼山,我認不得眼前的西昌城了,這座高原小城變得和內地的城市一樣。特別是那些石頭和土坯砌成的碉樓從眼前的風景中消失了,消失得像夢,也像云。比起高原的云,碉樓竟然更夢幻。云彩雖不是當年的云彩,但依舊有高原云彩的風貌,形態萬千,輪廓分明,變化無窮。而那些碉樓,卻好像從來沒有在這塊高原壩子上站立過,只是在細雨霏霏的夢里,才那么親切地成為記憶中的風景。
時間爬得比蝸牛還慢
在我的記憶里,饑餓不是一種肉體的感受,而是時間。肉體感受到的那種饑餓,是隨機產生的臨時的感受。啊,有點餓了,吃點什么好呢?是對這一類饑餓的應激反應。當然,這是來自身體正常健康的反應。現在,最流行相反的東西“厭食癥”,厭食癥的流行,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飽食終日正在侵占最可寶貴的每個人的內在空間。
那是并不遙遠的記憶,當饑餓成為一種常態,我也生活在這種常態中,我的肉體已經懶于或者說不能向我自己發出來自腸胃的信號了。這個時候,我關注到了另一個信號,時間爬行得比蝸牛還慢,時間因為饑餓,也走不動了。
饑餓的時間在哪兒?那是在教室窗上爬行的陽光。在“自然災害”的年月,我的記憶是小學高年級的早自習。小學高年級,再加早自習,這意味著充滿陽光,布滿清新空氣,空氣中飄散著露水浸潤后的花草氣味。是的,就是這樣,我的高中早自習也是如此,只是多了一個定語,那是饑餓的年月。饑餓的年月也有陽光,也不缺雨露滋潤花草,空氣清新透亮。只是陽光總是爬得那么慢。因為糧食緊張,我所在的那個地方,機關和學校都將一日三餐改為兩餐。早飯在兩節自習之后。第二節早自習的下半段,我的腦子里就是一碗稀粥。說腦子里是一盆糨糊,意思是什么都不清楚了。一碗稀飯同樣能達到忘掉一切的效果。一碗稀飯什么時候能到手上呢,陽光知道。我早就記住了陽光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告訴過我的那一刻,那一刻,陽光會爬到窗臺上一個細小殘縫。陽光爬到的時候,下課的電鈴就會像我的心房,高聲的歡叫:下課了!開飯了!今天的粥好啊!更稠!只是今天的陽光好像比昨天爬得更慢。不看!數一百再看!云彩快走開!……啊,真的,我無法告訴你饑餓的感受,但我可以對你講早上的陽光,講一講陽光怎么爬得比蝸牛更慢。
饑餓的時間在哪里?是在糧店前靜靜地排隊的小椅子。電影里演的在災荒年代,人們搶糧倉,場面如同打仗。我記得的不是這個樣子。我們是和平年代懂規矩的市民,大人告訴孩子,高鼻子的洋人逼我們還債,用火車拉走了白面、大米、豬肉和蘋果。我們懂道理,排隊就是懂道理的行為。排隊是因為糧店據說要出售紅薯,一斤糧票可以買五斤。這個消息讓糧店前的小椅子、小菜籃和報紙包著的磚頭排成長長的隊伍。排多久糧店會開門?不知道,聽說拉紅薯的汽車早就出城了。小椅子和小菜籃排成的長隊,像放學回家的小學生守規矩,一個跟著一個。只是小學生,會有說有笑地走著。而小椅子、小菜籃和大磚頭靜靜的呆立在隊伍中,一動也不動。我看著這長長的隊伍,心想,他們一定餓壞了,如果他們吃飽了,就會像變魔術一樣,變成一隊歡蹦亂跳的小人兒,唱著歌,跳著舞,讓這條街成為神話世界。也許,這是我最早的創作。只是饑餓打斷了我的念頭。我望著越來越下墜的夕陽,用雙手支著下巴:“看來今天是不行了,明天會來嗎?”我不想丟掉希望,沒有希望的話,我也許就會變成那把排隊里的小椅子。我看著小椅子,恍忽中,聽見小椅子向我打招呼:“您吃了嗎?”我一定神,四周看,沒人啊。
多年以后,讀到小說家賈平凹寫的一首詩。詩的題目是《題三中全會以前》。我看了題目想,這個賈平凹,外國人讀了,一定不知道他說的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再說了,題目像社論,這是詩的題目嗎?但當我讀到題目下面這幾行詩:
在中國
每一個人遇著
都在問:
“吃了?”
這四行詩,讓我的眼眶一下潮潤了,我相信,他和我一樣,知道為什么陽光爬得比蝸牛更慢啊!
望月獨行
中學同學來信,說是“西昌高中六六級三班同學會”,在國慶長假期間,想要聚會一下,問我能否回去。我沒有回去,新買了一套房子,忙著裝修搬家。西昌對我來說太遠了,三千里山水迢迢。西昌高中六六級三班也太遠了,三十年的歲月煙云。他們屬于少年的我。
我在西昌讀了三所中學,兩所初中,一所高中。第一所初中是西昌專科學校附中,中學設在邛海邊的一座大山的老廟里。第二所初中是川興中學,是所鄉村中學,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在這里讀書,同時學會了種菜,割草和打柴。最后考上了西昌高中,讀完高中后,又在學校度過了“文化革命”最初的幾年,然后到陜北延安插隊。幾乎十年的西昌,留給我最美的是什么?瞇上眼,腦海里浮動著一片銀色的月光:“空里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這是張若虛的詩句,也是我夢中常有的西昌月夜……
這是邛海湖濱的月色。剛到西昌時,曾任過宣傳部長和刊物主編的母親,是在一所師范學校當老師,那時正在流行《青春之歌》這本書,同學們都知道母親像林道靜參加過“一二·九”,因為受了處分下放到了西昌。學校在邛海邊上,離城還有二十里路。我記得最初幾個星期天母親會給我一元錢,讓我進城去看一場電影,那是我在省城星期天的休息方式。為一場電影,來回走四十里路,回家的路浸在月光里。西昌是個高原盆地,盆地中心是邛海這個高原湖,四周是環形群山。看完電影,出城時四周黑咕隆冬。夜幕中環立在四周的大山,崢嶸高聳,把天擠得很小。擠在一起的星斗,“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我常仰望這些晶亮的星子,叫自己忘卻黑暗壓過來的恐懼。高原的風把天擦拭得潔凈如鏡,好讓那輪月亮升起來。山真高,月亮緩緩地向上爬,先是一片乳色,然后月色勾出大山的輪廓。剎那間,一輪明月跳出山來,給人的喜悅真如孟郊的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好一個石上生出的月亮,又大又亮,叫黑暗中的高原一下子生機盎然。天上一個月亮,邛海的水中還有一個月亮。兩個月亮互相顧盼,“月下飛天鏡,云生結海樓”,銀色的光輝四處散逸,把歸程抹出一路詩意。
記得四川著名作家高纓當時出了一本散文集,名字就叫《西昌月》。也許西昌的月亮真會比別處的可愛,一是高原天空格外明凈,二是高原盆地地貌在月亮升起前后反差強烈,三是高原湖泊讓西昌有兩個月亮。然而對我來說,這月光,是我少年生活中,難得而可貴的亮色。月下獨行,這是我少年時代常有的事情。進城要走夜路,周末回家也要走夜路。在川興中學讀書,我是住校,我的學校與母親的學校相距三十多里路,剛好圍著邛海走半圈。星期六上完最后一節課,就是下午五點鐘了。歸家路上,先看日頭西墜,落天金鯉似的晚霞游進蒼茫的暮色,然后夜幕悄然低垂,讓我聽著自己的心跳,期待月亮升起來。在月光下,伴我獨行的還有那些美輪美奐的詩句。“白云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啊,千年以前的李白,也知道會有一個少年,在邊城湖泊的月下前行?“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樓半開壁斜白。”李賀的詩常讓少年的心傷感,其實,月光給我的是一種淡淡的溫馨,像回家路上另一端的母親目光,還像牽動我勇氣的自信。說實在的,離開省城去邊城西昌和母親作伴,我并不知道情勢的險峻。母親也許永遠被貶放于一個山區教師的講臺,而且日后連這謀生的職位也被剝奪。我去了西昌,也陷入四周阻隔的人生困境,像暮色四起而沒有月亮的時候,四周是高聳的黑暗,和黑暗中的群山!
在令人窒息的高壓中,我策劃了一次突圍和逃離。約上三個同學,半夜一點鐘在學校貼出一張大字報:“我們要步行長征去見毛主席。”算是告訴大家我們出逃的理由。然后,四個人背著行李背包、鋁鍋和臉盆,悄悄離開學校。那一夜,我們在又大又亮的月亮關照下,開始了人生第一次長途跋涉。四個半月后,我們行走了六千七百里路,在隆冬臘月到達北京。
出逃那一夜的月光真好。我記得,因為不是月下獨行,身邊還有三個同學,心底升起一種豪放之情,啊,“誰為天公洗眸子,應費銀河千斛水!”少年不知愁,說走也就走了。
月光下的邊城西昌和月光下的少年情懷,都成為夢中的清輝,遠遠的,飄逸的。
沒有回去參加同學會,收到西昌寄來的“同學錄”,上面有與我一起月夜出逃的三位同學的名字:張云洲、王守智、陶學燊。
吾愛吾師
收到高中同學邀同學會的電話。關上電話,卻想,都半個世紀了,這同學會大多數人還認識嗎?高中同學曾寄給我一本同學錄。初中的呢?說真的,初中同學的名都基本上忘記了,只記得一個姓侯的。老師呢,老師中有個何守模,二十年前還寫過一篇回憶他的文章。還有呢?真是奇怪了,又蹦出來三個名字,賴仁價,左惠蘭,李華強。這四位老師,只有何老師多年前與我有過書信聯系,沒有見過面。其它三位,不僅沒見過面,自從離開那所學校,再沒有聯系過。五十多年啦,他們的名字怎么像藏在石縫里的雞毛信,過了半個世紀,因為另一個無關的電話,破土冒出來。
一個何老師,扯出四個老師,四個老師拉出一個學校。這個學校叫西昌川興初級中學。在饑餓的“三年自然災害”,我剛考上的一所初中停辦了,中途轉入這所鄉村中學。一進了這所鄉村中學,有兩個非常深刻的印象:沒有圍墻和校門,四周都是稻田所圍的幾間用土坯壘起的教室。學校沒有電,上晚自習一人一個小墨水瓶改成的煤油燈。我就是在這里度過了我的初中和“三年自然災害”,因此,這四位老師的名字記錄了我人生中一段非常時期。
何守模。我寫過他一篇文章《何先生》。他是四川大學歷史系高材生,讀書當了大學生右派,畢業分到這偏僻的農村中學任教。學校規定,右派不能叫老師,他進教室上課,值日生就喊:“起立,何先生好!”何先生課教得好,脾氣也大,教鞭敲桌子是他的特色動作,真生氣時還罵人。因為出自名牌大學,會講課,反正都“先生”了,所以校領導也任其發飚。他對我很好。他除了上課,還管圖書館,我是他圖書館一號讀者,所有的新書先睹為快。為此還鬧出許多矛盾。《紅巖》剛出版時,學校分到一冊。語文老師去借:“為全校同學進行傳統教育需急用。”何先生說對不起借走了。冤家路窄,這個老師上課時發現這本書在我手里。怒不可遏向校長告狀。據說校長反問他:“你沒事惹那個右派干什么?你掙多少?他掙幾文?你上完課回家,他上完課管圖書館。換一下,行嗎?”出面替語文老師出頭的是教導主任,在全校大會上臭訓我一頓。初中畢業時,何老師送我一張書簽,是北京中央廣播電臺的照片,照片背后他寫上:“祝你順利考入高中,并有機會繼續深造……將來在這所雄偉的大廈播出你成功的消息,我會聽到的。何守模”多年后,我走進了這所大樓,在這里完成了我的大學畢業實習。我想到了何先生,他是我的“預言帝”。
賴仁價。學校的教務主任,但什么事情都管。替語文老師出氣訓人這件事,讓我記一輩子。期末全校大會,我統考得了第一。他代表學樣發獎狀,拿著獎狀先罵人:“葉延濱自以為聰明學習好,上自習看小說,自高自大,自大兩個字疊起來是什么?臭——”然后把獎狀遞給我。(此法絕殺,讓你不得不站在他面前,聽他講完。)他更高明的是按照人民公社管理社員的方式管學校。農村中學沒錢,困難時期饑荒,他竟然把這個又沒錢又饑荒的學校辦下去了。每個同學有一個工分本,好像規定一年要掙100個工分。學校所有的空地,全部分成一小塊一小塊的菜園,每小組一塊地,種出的菜,交食堂后換成工分。每個星期六是勞動課,到學校背后的高山上割茅草,交給食堂做燃料。茅草葉堅硬鋒利,山里人主要的燃料就是它。同鄉下同學去割草,手上全是血道道。割下草還要扎成小草把,把小草把再打成捆,才能從山上背回來。早出晚歸,背下山來,渾身都扎滿草刺。還有到糧站拉口糧,到河灘抬石頭筑圍墻,一切勞動都換算成工分。在那個饑餓年代,這所農村初中教會了我大多數的農活,也讓我像一個農村孩子一樣活著。衣縫里長著虱子,腳下穿著草鞋。進學校身高一米四九,畢業出學校身高一米五一。賴主任得過天花病,臉上留下麻子點。老師們開玩笑就說,“幸虧賴主任點子多”,讓學校熬過了饑荒年。
左惠蘭。我的班主任。李華強,學校分管少先隊和團委工作的老師。我在川興中學也經歷過“大起大落”的事情,我想與他們兩人有關。因為我是從城里轉到這里的學生,一年后,學習成績冒了尖,農村孩子能干的種菜、割草之類的勞動也能完成。那年城里開共青團代表會,我就成了“優秀少先隊員”代表,跟著李老師列席大會。這對我來說是頭一次見大世面:吃會議飯(饑荒年代也定量),聽大報告(還要記筆記),住招待所(四人一間還干凈)。開完會回校不久,出事了。農田中間的學校,夏天多昆蟲。我們宿舍的同學到野外抓了一種能飛的甲殼蟲,捉了幾十只。偷偷從窗戶縫,放進另一個宿舍,滿屋亂飛的甲殼蟲引出一陣騷亂。不幸被值日老師撞上,成了一件擾亂學校秩序的大事。值日老師的訓話有“施放害蟲”,“擾亂秩序”,“帝國主義分子才想得出的壞主意”。全校通報,對我的處分是取消三好生等榮譽稱號。過了些日子,班主任左老師來動員我寫入團申請,我納悶,不是剛處分過嗎?后來我聽說,我成了學校“正確對待青少年思想行為”的典型,上報的材料中,已經改正了錯誤。后來明白原因。初三馬上考高中了,那年頭全地區十個縣,只有一所重點高中。又窮又缺資歷的鄉村中學要保重點,也就保到我的頭上。我順利地被批準入團。對于發生在我身上的大起大落,左老師和李老師肯定是向上正能量。我也算爭氣,從這所鄉村中學考入全地區重點高中。
老師是什么?有人以為,老師就是給人熬燉心靈雞湯的烹調師。雞湯可口,過肚穿腸難入心。入心者是老話“良藥苦口”。回想我的初中,離開家后的第一個“社會熔爐”。不像熔爐那么熱烈,倒是像一罐湯藥,五味雜陳。吾愛吾師,他們的名字就像美妙的藥名:當歸、杜仲、生地、甘草、金銀花……
(責編:楊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