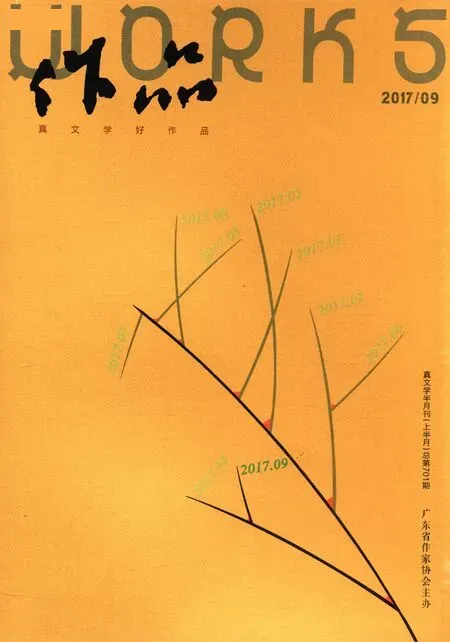守夜草
文/王魯湘
守夜草
文/王魯湘
王魯湘
男,漢族,1956年出生于湖南邵陽(yáng),1982年畢業(yè)于湘潭大學(xué)中文系,獲文學(xué)學(xué)士學(xué)位,1987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獲哲學(xué)碩士學(xué)位,曾任教于湘潭大學(xué)、首都師范大學(xué)、清華大學(xué),教授,博導(dǎo),中國(guó)國(guó)家畫院研究員, 中國(guó)文物學(xué)會(huì)會(huì)員,中國(guó)文物學(xué)會(huì)玉器專業(yè)委員會(huì)理事,清華大學(xué)張仃藝術(shù)研究中心理事,香港鳳凰衛(wèi)視高級(jí)策劃、評(píng)論員、主持人,李可染藝術(shù)基金會(huì)副理事長(zhǎng),李可染畫院副院長(zhǎng),中國(guó)畫學(xué)會(huì)創(chuàng)會(huì)理事,北京鳳凰嶺書院院長(zhǎng),中國(guó)國(guó)際書畫交流學(xué)會(huì)副會(huì)長(zhǎng)。
一、追日草
劉巨德有一方朱文印《追日草》,他還把這方印作為他的微信標(biāo)志,可見他喜歡。《追日草》也是他一幅大水墨畫的名字,畫很大,362cm×141cm,畫蒙古草原上一種野草,從泥地里使勁拔節(jié)沖上長(zhǎng),密密麻麻,望不到邊。開一種毛絨絨的花,有黑,有白,有紅,燦若星斗,不知何故叫追日草,太詩(shī)性的名字,誰(shuí)取的?
“《追日草》畫了我一種感覺,想象草追著太陽(yáng)。我的家鄉(xiāng)在內(nèi)蒙古后草地,我小時(shí)候,夏日經(jīng)常小裸體,什么也不穿,跑在花草叢、綠草地。那時(shí)候,我感覺草長(zhǎng)得特別高,比我高多了。我們小孩,一群群的,進(jìn)去掏鳥蛋啊,抓老鼠啊,采蘑菇啊,挖野菜啊,拾牛糞啊,割青草啊……草給我童年的印象特別深。”[1]
劉巨德畫的草,給我的印象也特別深。
還沒有哪個(gè)畫家,像他這般投入地畫草。古今中外,找不出的。
更沒有哪個(gè)畫家,把草畫得這般高大偉岸,頂天立地。人就像匍匐在草中,如蟲蟻,通過(guò)草的身軀,仰望蒼穹。
這是一個(gè)多么卑微的視角:趴在泥土上,讓野草肆意地?fù)u曳在你的頭頂。你看天,看天與地相交的地平線,都是野草的世界,一望無(wú)際,漫無(wú)邊際,芳草碧連天!
“《追日草》就是畫草在土里生長(zhǎng)的情景。它沒有邊界,自由蓬勃地生長(zhǎng),瘋長(zhǎng)。我經(jīng)常走在里面,有時(shí)候躺在里面,秋天會(huì)聽見草籽噼噼啪啪作響,像驚濤駭浪一樣轟鳴在心里,那是草籽降生土地的歡樂。”[2]
“草籽降生土地的歡樂”——有幾人知曉,幾人體驗(yàn)過(guò)?
草籽破殼,凌空降生,落入土地——這樣微小、卑弱的生命降生,誰(shuí)聆聽過(guò)?非常幸運(yùn),我聽過(guò),在山區(qū),而非草原。所以,陣勢(shì)與聲勢(shì)完全不可比擬。大草原如恒河沙數(shù)與宇宙星數(shù)的草籽同時(shí)破殼迸出——想象一下吧,難怪劉巨德會(huì)說(shuō)“像驚濤駭浪一樣轟鳴在心里”。要我說(shuō),從生命誕生的壯麗而言,可能堪比宇宙大爆炸。
所以,這卑微的小草,其實(shí)有我們懵然不知的能量。
這能量,見陽(yáng)光就瘋:
“看‘草’字,上邊兩棵草,中間一個(gè)日,下邊一棵草,草抱著太陽(yáng)。草的生活,草的生命,就是懷日追日。我們的生命呢?也是追趕光陰,追趕太陽(yáng),我感覺我在追趕藝術(shù)的‘太陽(yáng)’。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追不上。因?yàn)槊朗遣豢赡苤苯咏咏模阒荒苄蕾p她、仰望她、敬畏她,讓她照耀。《追日草》,就是在享受太陽(yáng)的光芒,享受美的光芒,這也是我心里的一種感覺。還有一層意思:夸父追日,道渴而亡,化為鄧林。他所有的毛發(fā)都變成了草,草是夸父的遺骸,夸父生命的再生,隱喻草里有夸父的靈魂。所以,草自然有追日的精神。” [3]
原來(lái),“追日草”是劉巨德起的名字,也是給他自己起的名字。草是夸父生命的再生,追日是草的宿命。
但草在地下也是瘋狂的:
“所有的草一直在地下自由地瘋跑著,草的根須一躥千里,不怕風(fēng)寒,不怕火燒,永生不滅,非常平凡而奇特。它們不獻(xiàn)媚,不爭(zhēng)艷,也不爭(zhēng)寵,什么都不爭(zhēng),只向往追日。你感覺它,好像離太陽(yáng)很遠(yuǎn),其實(shí)它的心,離太陽(yáng)很近。”[4]
這就是草的力量,卑微,但瘋狂,一根筋,一個(gè)目標(biāo),除了追日,別無(wú)他求。我感覺到劉巨德是在說(shuō)自己,他的草就是他自己,因?yàn)槲彝嘟幌嘧R(shí)三十年,我知道他對(duì)藝術(shù)這個(gè)太陽(yáng)的追逐,就像夸父;我還知道他對(duì)藝術(shù)的執(zhí)著,就像草根,“不獻(xiàn)媚,不爭(zhēng)艷,也不爭(zhēng)寵,什么都不爭(zhēng),只向往追日。”
這是怎樣的一棵“追日草”啊!
然而,在他謙卑的內(nèi)心深處,那些草,卻有著別樣的形象。2011年,他畫了一幅69cm×139cm的畫,還是草原上的野草,開滿黃白的花朵,就像天上的星星灑落在莽原上,照眼驚心。畫的名字就叫《英雄起步的地方》。2014年,他以同題又畫了一張194cm×503cm的大畫,各色野花,璨若星河,又如同節(jié)日焰火,盡情綻放!
“我體驗(yàn)這些草,都是高大的英雄。”[5]
驀地,我想起了兩個(gè)人,兩個(gè)畫家。一個(gè)叫齊白石,一個(gè)叫草間彌生。
齊白石有一方印,刻“草間偷活”四字,常鈐于有細(xì)工昆蟲的畫作之上,還以此為題,畫過(guò)一本精美的冊(cè)頁(yè),說(shuō)他可憐那些草間的小生命,既無(wú)野心,又無(wú)壯志,僅求偷活于世。他也有過(guò)趴在草叢里看蟲子而忘饑的童年。他的大愛通過(guò)“草間偷活”的昆蟲感動(dòng)全人類。
過(guò)去一直看不懂草間彌生,說(shuō)不清她那些大大小小的圓點(diǎn)點(diǎn)是什么意思。現(xiàn)在好像突然懂了,她的畫,就是圖釋她的名字:草間彌生。那些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紅紅粉粉的圓點(diǎn)點(diǎn),是歡樂地降生大地的草籽,是愉快地飄蕩空中的孢子,是水珠,是氣泡,是原子,是一切孕育生命的元素。
他和她,都是劉巨德的同道,他們都在草的世界看到真的生命,強(qiáng)的生命,韌的生命,繁的生命,美的生命,聽到澎湃如海的生命《歡樂頌》。
“在田野,我看見新長(zhǎng)出的胡麻花,一片片,藍(lán)瑩瑩,隨風(fēng)蕩漾。我蹲在他們面前,俯下去面對(duì)每一朵花,胡麻花有一種無(wú)法形容的嬌嫩,瑩潔和光明,好像嬰兒微笑一般喜人。旁邊田頭亂石叢中,一蓬蓬被踐踏過(guò)的草花,雖然干渴的枝葉已經(jīng)發(fā)黃,它也仍然昂首挺立,面朝太陽(yáng),笑口迎天。它們頑強(qiáng)、樂觀,長(zhǎng)得精致喜人,充滿道的精神。”[6]劉巨德對(duì)草的感情是發(fā)自靈府的。他畫了那么多以草為題的作品:
《家鄉(xiāng)草》 (紙本水墨設(shè)色137×69cm 2001年)
《守夜草》 (紙本水墨178×90cm 2010年)
《故鄉(xiāng)草》 (布面油彩90×60cm 2006年)
《家鄉(xiāng)秋色》 (紙本設(shè)色98×49cm 2005年)
《金蓮花》 (紙本設(shè)色141×362cm 2013年)
《霜降》 (布面油畫90×50cm 2009年)
《原上草》 (紙本水墨設(shè)色144×365cm 2010年)
《追日草》 (紙本水墨設(shè)色141×362cm 2011年)
《霜原》 (紙本水墨 141×366/2013年)
《英雄起步的地方》 (紙本水墨設(shè)色 194×503cm 2014年)
《星光草》 (紙本水墨 362×141cm 2012年)
《駱駝草》 (紙本水墨設(shè)色69×139cm 2015年)
《披霜草》 (水墨紙本 362×141cm 2012年)
《糜間草》 (水墨紙本設(shè)色138×69cm 2016年)
許多都是煌煌鉅制。古今中外,還真的沒有哪個(gè)畫家如此濃墨重彩地畫草。
“我家里擺的全是草,枯草,荒草,花草……都是我從家鄉(xiāng)帶回來(lái)的草。工作室,也供一蓬草。”[7]
我第一次看到野草被隆重地供在陶罐和瓷瓶里,是在張仃先生家。我當(dāng)時(shí)確實(shí)很驚訝,居然是野草,而且是枯草。陶罐是很講究的,4000年以上的彩陶罐當(dāng)然最好,最不濟(jì)也得是漢魏的灰陶罐,隱隱留著點(diǎn)紅白彩繪的痕跡。瓷瓶以晉唐的青瓷氣息最好,或者,一只磁州窯的黑白劃花大罐也不錯(cuò),穩(wěn)重又大氣。哪怕只有一只民間的黑釉耳罐,也特別給力。插上一蓬參差的野草,雜以說(shuō)不上名的野花,往書架上、窗臺(tái)上一擺,滿室生輝,原野的活力帶給書齋、客廳、畫室的氣息,無(wú)物可與倫比。那是一個(gè)冬日的下午,30年前,北京,紅廟,張仃先生介紹我去找劉巨德,為即將開拍的電視片《河殤》設(shè)計(jì)演播室,畫背景。
走到劉巨德家,一眼看到的,也是一蓬野草!
而他最喜歡讀的文學(xué)作品,竟也是魯迅的《野草》。先生塑造的那個(gè)黑夜中聽見前方聲音的召喚而執(zhí)意前行不肯息下來(lái)的“過(guò)客”,劉巨德引為同志。
二、守夜草
在劉巨德眾多《草》作中,我個(gè)人偏賞《守夜草》。這幅畫于2010年的作品,在他的紙本水墨中,尺寸不算大,178cm×90cm,一張六尺整宣。滿紙濃濃淡淡大大小小的墨點(diǎn),層層積墨,點(diǎn)染出草原幽深神秘的秋夜,一片漆黑。有朦朧的月光,透出黑夜的重圍,在天邊隱隱發(fā)光。黑夜中真正的精靈,是那些黑黢黢的野草的剪影,像穿了夜行服的忍者,露出鬼火一樣的眼睛,照亮深不見底的寂靜,飄蕩在無(wú)邊的原野;像幾千年逝去的草原英魂,被神秘的月光喚醒,仿佛聽到一個(gè)聲音在前方召喚,窸窸嗦嗦簇?fù)砬靶校幌裾诩Y(jié)的匈奴軍隊(duì)、鮮卑軍隊(duì)、突厥軍隊(duì)、蒙兀兒軍隊(duì),秋夜的草原正在聚集能量,匯成洪流,一旦蘇醒,地球震動(dòng),歐亞大地,不復(fù)寧?kù)o……
這幅杰作是如何產(chǎn)生的?我不知道。或許,草原上就有這類含有熒光素而可以在夜的黑暗中自體發(fā)光,從而招引趨光的飛蟲并吞噬它們的美麗如妖魅的花朵?
不管是來(lái)自草原生活的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還是源自他詩(shī)意的想象,劉巨德筆下的水墨野花是自體發(fā)光的,無(wú)論是插在室內(nèi)的瓶中,還是盛開在野外的大地,它們都從黑暗中放出光明。
你看2001年他畫的《家鄉(xiāng)草》,那只黑黑的只有剪影的罐子,那些黑黑的只有剪影的枯葉,映襯出上下前后一朵朵大放光明的野花。這可是剛剛從故鄉(xiāng)的草原捧回來(lái)的啊,輻射出故鄉(xiāng)灼熱的秋陽(yáng),溫暖異鄉(xiāng)游子的心房。
還有畫于2008年的紙本水墨《秋塘》,黑、灰、白,三個(gè)跳躍的色階,一路攀躋,從低沉渾厚的黑,到溫柔潤(rùn)澤的灰,到清脆嘹亮的白,以黑之濃厚為托,威嚴(yán)行進(jìn);以灰之溫潤(rùn)為襯,和之以柔;高潮處,捧出白之清亮,敲出一個(gè)響遏行云的高音,戛然而止,一朵潔白的蓮花,以其素雅高華的身影,肅立于秋日之朗朗乾坤。
還有畫于1999年的小畫《月季》,大墨點(diǎn)的葉子形成了光柵,被遮蔽的光從后面篩漏進(jìn)來(lái)。這種小心翼翼的留白,李可染謂之“擠白”,是對(duì)光的敬畏,所以畫面吝光。但畫面頂部一朵微粉的月季,恰如一輪皎月之行秋夜;那些畫面上的光斑,又似月光之透窗欞。如此這般的巧用“留白”,效果正如黃賓虹所謂的“靈光”:“一燭之光,通體皆靈。”
“靈光”這個(gè)黃賓虹常用來(lái)為中國(guó)畫辯護(hù)的詞,放在劉巨德的水墨畫甚至部分油畫中很合適。
劉巨德是一個(gè)“通靈”的藝術(shù)家。當(dāng)然,這里所說(shuō)的“通靈”不是西方所說(shuō)的“靈媒”,但又不可否認(rèn)劉巨德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正好在歐亞大陸通古斯薩滿教的核心地區(qū)。薩滿教作為一種原始宗教,主張萬(wàn)物有靈,而人可以通過(guò)薩滿與神靈相通。
與劉巨德交談,會(huì)發(fā)現(xiàn)他是主張萬(wàn)物相通的。我接下來(lái)會(huì)討論他的重要藝術(shù)觀,也是他的哲學(xué)觀,那就是“渾沌”論,在渾沌的世界里,萬(wàn)物齊同。這一思想雖然直接來(lái)自戰(zhàn)國(guó)杰出的思想家莊子,屬于道家哲學(xué),但劉巨德如此推崇“渾沌”論并視為自己藝術(shù)觀的完整表述,則不能不是受到自己母文化的“薩滿”教的影響。他的思想,尤其是藝術(shù)觀,毋寧說(shuō)就是道家與薩滿教的合一,我們會(huì)在他太多太多的作品里發(fā)現(xiàn)這種混合的世界觀。
劉巨德受過(guò)良好的西畫訓(xùn)練,對(duì)光與色的關(guān)系有過(guò)十分專業(yè)的研究,但他作畫時(shí),卻全然不受這些教條的影響。有趣的是,在他的畫中,無(wú)論油畫,還是水墨,光無(wú)處不在,但那確乎不是自然之光,而是“靈光”。
比如《秋紅》(紙本水墨設(shè)色/136cm×34cm/2011年),那些靈動(dòng)的似乎是隨機(jī)的有理無(wú)理的“留白”,讓一片枯敗之象的荷塘,煥發(fā)出神性的光輝。我們無(wú)法從科學(xué)和美學(xué)上來(lái)解釋清楚這樣的視象,只能說(shuō)是劉巨德心象的投放,他心中躍動(dòng)著這樣的“靈光”,于是就有了畫面上不可思議的“靈光”的躍動(dòng)。
作于2011年的《草原悲鳴》(紙本水墨/144cm×365cm)是一幅有濃厚象征主義旨趣的作品。八匹野馬似乎陷入了生存的絕境,在風(fēng)雨如磐的夜晚仰天長(zhǎng)嘶,眼看禿鷲咬嚙同伴的殘軀而悲鳴不已。畫面的筆墨中,沉重的墨色,蕪亂的點(diǎn)線,帶來(lái)強(qiáng)烈的不安,引發(fā)一種悲愴的壓抑;而草叢中像地光一樣閃爍的“靈光”,照亮馬群的輪廓,似乎又預(yù)示著一線生機(jī)。在這幅作品中,“靈光”顯然不僅僅只是作為語(yǔ)言,同墨色玩著主部主題和副部主題的旋律對(duì)位游戲,它直接就構(gòu)成了象征的“能指”,甚至“所指”——它就是拯救者的神光。
有意思的是,當(dāng)劉巨德用這樣的眼光來(lái)看世界的時(shí)候,他的心象就會(huì)投放到幾乎所有對(duì)象上。
一束神秘的光線會(huì)凌空直下,照亮《原上草》的一個(gè)區(qū)間。
一片神秘的光霧會(huì)照亮整片草原,讓所有的《金蓮花》都沐浴神光,歆享神福。
甚至連畫家工作室所在的九龍山,在他的筆下,那片蓊郁蔥蘢的林地,也會(huì)有一處山坡,被靈光照得雪亮。
蕭瑟寥落的《秋夜鳥》(紙本水墨/179cm×45cm/2013年),依偎枝頭的小鳥身后,是炫目的無(wú)法言狀的昊旻光網(wǎng);而《春雪》(紙本水墨設(shè)色/139cm×69cm/2014年)站立枝頭的群鳥,已然幻化為天使,以透明的白色的光的形象,降臨初春的人間。
《生命沒有告別》(紙本水墨/141cm×362cm/2012年),這靈光化為流星雨,掠過(guò)蒼穹,照亮大地,慰藉悲傷的人們。
在史詩(shī)般的巨制《生命之光》(紙本水墨設(shè)色/245cm×500cm/2015年)里,這靈光灑滿天地,化作繽紛的花雨,同心靈的鴿子一起,把哀思帶往彼岸和天堂。
對(duì)“靈光”的迷戀與追逐,來(lái)自于劉巨德的信仰。他雖然沒有確定地皈依某一宗教,但他有著虔誠(chéng)而至篤的宗教情感。他明確表示,“藝術(shù)就是照亮生命,點(diǎn)燃生命的光與火。”人性對(duì)光明的向往,就是夸父追日的情懷,也是藝術(shù)家的良知和使命。
“在寂靜中,前賢高人走進(jìn)宇宙生命的最深處,站在內(nèi)部反觀自然,內(nèi)觀生命,心照萬(wàn)物,發(fā)現(xiàn)光吞萬(wàn)象,萬(wàn)象皆空,‘渾沌里發(fā)出光明’,一切均是光的幻影。”[8]
記得20年前,我寫過(guò)一首歌,其中有兩句歌詞:“我的夢(mèng)就是我的馬/我的馬就是我的夢(mèng)/我是高原守夜的人。”
自比于草原上的野草,劉巨德白天追日,晚上守夜,全天候生活在他靈魂的棲息地。這正好組成他藝術(shù)生命的陰陽(yáng)太極。白天,他吸收陽(yáng)光,向著天空瘋長(zhǎng);晚上,他自體發(fā)光,根在地下狂躥。他被宇宙的光照亮,他的光也照亮宇宙;光既外灼于他,點(diǎn)燃他,他也寂靜內(nèi)觀,光吞萬(wàn)象。
“一切均是光的幻影。”
三、家鄉(xiāng)土
1991年,中國(guó)歷史博物館(今國(guó)家博物館)舉辦《吳冠中師生作品展》,劉巨德是第一次拿出較多作品參展,記得李澤厚也來(lái)了,他一邊看一邊說(shuō):“為什么請(qǐng)我來(lái)看這個(gè)展覽?”貴賓室的研討會(huì)上,吳冠中先生操著他尖而高亢的吳語(yǔ)激動(dòng)地說(shuō)了許多話,對(duì)他的愛徒們一個(gè)個(gè)加以點(diǎn)評(píng),場(chǎng)面感人。劉巨德一如既往地憨笑,寡言少語(yǔ)。他不是不能說(shuō),他很能說(shuō),但這種場(chǎng)合,他保持有禮貌的沉默。他聽。
我也應(yīng)邀去了,請(qǐng)柬是吳先生親筆所書,可我知道是劉巨德的意思,他想讓我看看他1989年以后的近作。而我,也剛獲自由不久。
這場(chǎng)展覽真正的明星是劉巨德。一條魚,幾穗金色的粟子,一堆土豆,幾根紅薯,一只黑釉碗,碗里一堆紅色的櫻桃,還有幾顆土梨與山桃……就是這些畫在宣紙上的家鄉(xiāng)的土產(chǎn),征服了所有的觀眾,無(wú)論老幼男女,專業(yè)業(yè)余。大家圍觀,議論,湊近去,又退后,如此往復(fù)幾遍,留連不去。
大家看什么呢?
首先,畫得真像。用中國(guó)的毛筆、墨,加點(diǎn)色,淡淡的,畫在宣紙上,竟能這么逼真,比油畫和水彩表現(xiàn)得還逼真,那土豆皮上的沙土,山桃皮上的絨毛,魚的鱗,粟的粒,好像用手能摳下來(lái)。所以觀眾總是湊得很近去看——近觀其質(zhì)。
其次,如此寫實(shí)逼真的一堆靜物,好像有極大的氣場(chǎng),能把人推得遠(yuǎn)遠(yuǎn)的,看它們?cè)谝粋€(gè)看似逼仄實(shí)則遼遠(yuǎn)無(wú)際的空間里無(wú)聲地講述關(guān)于生存,關(guān)于活著,關(guān)于父親母親,關(guān)于愛與奉獻(xiàn)的故事。所以,觀眾又總是不斷地退后,在這些靜物的背景中尋覓歷史的天空——遠(yuǎn)觀其境。
劉巨德肯定不是第一個(gè)畫這樣鄉(xiāng)土題材的畫家。法國(guó)19世紀(jì)的巴比松畫派,偉大的米勒,還有后來(lái)的梵·高,也都畫過(guò)類似的題材。在中國(guó)文人畫傳統(tǒng)中,甚至還專門有一個(gè)小傳統(tǒng),那就是總有人畫蔬圃,以提醒士大夫不忘其味,齊白石是這個(gè)小傳統(tǒng)的大師,他畫過(guò)一個(gè)湘潭農(nóng)民所知道的一切有關(guān)稼穡蔬圃的東西。他說(shuō)畫這些東西是因?yàn)檗r(nóng)夫知其味而不知其趣,士夫知其趣而不知其味,而他,一個(gè)從農(nóng)夫變成士夫的畫家,要味與趣兼而知之。他沒有說(shuō)對(duì)農(nóng)家蔬稼的土產(chǎn)為何要味趣兼而知之?
我們或許可以從幾個(gè)角度來(lái)理解齊白石的深意。
首先,從社會(huì)學(xué)上說(shuō),通過(guò)對(duì)蔬圃稼穡的味趣兼知,打通城市與鄉(xiāng)村、精英與民眾的隔閡,富不忘貧,上不忘下,士不忘農(nóng)。說(shuō)到底,不忘本,不忘所自。知趣者不驕,知味者不卑。
其次,從美學(xué)上說(shuō),雅之過(guò)于脫俗,高蹈絕塵,久之必導(dǎo)致空洞貧血,裝腔作勢(shì),其趣必墮頹唐萎靡,玩世不恭,不接地氣,難有擔(dān)當(dāng)。而俗之不能近雅,畫地為牢,久之必導(dǎo)致自甘平庸,胸襟狹促,其俗必墮積習(xí)難改,不思進(jìn)取,因循守舊,品質(zhì)退化。而雅俗相濟(jì),趣味互補(bǔ),高下相摩,天地相蕩,美學(xué)境界才能充實(shí)而有光輝。“充實(shí)之謂美,充實(shí)而有光輝之謂大”。味趣兼而知之,才能充實(shí)而有光輝。
劉巨德是從1989年以后,開始認(rèn)真地畫他這一批“家鄉(xiāng)土”的。
這個(gè)時(shí)間點(diǎn)很耐人尋味。
在此之前,他也同中國(guó)美術(shù)界大多數(shù)中青年藝術(shù)家一樣,投身到了“新潮美術(shù)”當(dāng)中,為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所迷醉,探討形式、語(yǔ)言、觀念,唯新是趨,認(rèn)為詩(shī)與哲學(xué)與藝術(shù),都在遠(yuǎn)方。
就在這一年,1989,一場(chǎng)社會(huì)大變動(dòng),暴烈地中止了這一切。
也就在這一年,1989,劉巨德畫了那條著名的《魚》(紙本水墨設(shè)色/50cm×55cm/1989年)。
說(shuō)不上這是一條活魚,還是死魚?但是,它的命運(yùn)已經(jīng)注定。它被放在盤子上,渾身濕漉漉的,唇微翕,鰭緊收,眼珠絕望。如果到此為止,我們會(huì)說(shuō),啊,劉巨德畫了一條將死的魚。但是,吊詭的是,劉巨德用濃淡相間的墨,從魚嘴往上,橫著刷了幾十道墨線。這抽象的不明所以的墨線畫在魚和盤子的后面,天曉得,我們一下子就聽到了江河湖海的濤聲!尤其是那幾道若隱若現(xiàn)的水線,那是潮?還是浪?那是岸?還是天際線?引人遐想。
于是,一張非常確定的靜物畫,就變了。那盤子本來(lái)決定了魚的空間邊際,它們應(yīng)該在桌上,案上;但現(xiàn)在變了,我們不能確定它們的空間,也就不能確定它們的存在了。劉巨德玩了一個(gè)戲法,他用幾近于超級(jí)寫實(shí)的手法畫了一條魚,用大寫意的筆法畫了一個(gè)所謂的盤,又用抽象的手法畫了一個(gè)背景,幾種手法的交錯(cuò),變出了一個(gè)意義無(wú)法確定的空間場(chǎng)境:這到底是一條將為盤中餐的魚呢?還是一條行將相忘于江湖的魚?它是將要成為犧牲呢?還是將要重返自由?它的目光是充滿恐懼和絕望呢?還是滿懷希冀與渴望?
面對(duì)這樣一個(gè)矛盾的場(chǎng)境,我們猶疑了。“生,還是死?這是一個(gè)問題。”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的自白又一次響起在我們耳邊。
這是一個(gè)永恒的考問。
劉巨德在那一年,1989,用這張《魚》考問自己,也考問他人。
沒有答案,但引人注目,招人喜歡。
后來(lái),他把這張《魚》送給了我,我懸掛于餐桌之側(cè),用以佐餐。有時(shí)候,也凝對(duì)出神,幻想一些江湖和遠(yuǎn)方的事情。
2001年,作為劉巨德的代表作,另一張同樣的《魚》入選百年中國(guó)畫展,并被中國(guó)美術(shù)館收藏,未返江湖,進(jìn)了廟堂。
我一直在想,為什么《魚》會(huì)成為劉巨德的代表作?還有什么更隱秘更深刻的潛意識(shí)有待解讀?
或許,《魚》代表了劉巨德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他確實(shí)用圖像描繪了一個(gè)困局。魚在盤中,那就是1989年當(dāng)下,劉巨德的自我感知。盤后的江河湖海,那可能就是魚的記憶和它要努力重返的世界。這個(gè)困局和困境是魚自己造成的呢?還是有魚所不能擺脫的力量?這個(gè)已經(jīng)不重要。重要的是,魚還能重返江湖嗎?
這似乎是一個(gè)比莊子在《秋水》篇里設(shè)置的“涸轍之鮒”更大的困境。
《魚》似乎隱隱地預(yù)示了劉巨德藝術(shù)生命的另一個(gè)方向,另一條出路。
這一年,1989,劉巨德回到故鄉(xiāng),內(nèi)蒙古的后草地。
接下來(lái)的幾年,他畫了一個(gè)系列的“家鄉(xiāng)土”。
我們看他不同年份畫的四張土豆:
《家鄉(xiāng)土》 (紙本水墨設(shè)色 50×69.5cm 1990年)《南沙坡》 (紙本水墨設(shè)色 55×69cm 1991年)《沙土地》 (紙本水墨設(shè)色 69×69cm 1992年)《土桃與土豆》 (紙本水墨設(shè)色 68×68cm 1995年)
這些土豆,讓我想起梵·高的《靴子》,以及海德格爾對(duì)《靴子》的著名的分析和解讀。這樣一雙丑陋不堪的沾滿泥濘的靴子,離開了它的主人,靜靜地呆在房中一隅。畫家憐憫的目光居高臨下注視著它,一筆一筆畫出了它的全部細(xì)節(jié)。靴子上的泥土,讓人想到它走過(guò)的土地和道路,它風(fēng)雨無(wú)阻行走過(guò)的那些日子和季節(jié)。能把靴子穿成這么一幅模樣,它的主人該是什么模樣呢?是什么樣的沉重的勞作,才能把一雙靴子折磨得如此丑陋呢?靴子不也曾美麗而周正的存在過(guò)嗎?它現(xiàn)在丑陋地敞著它的靴口,里面空空洞洞,卻裝著一個(gè)人的命運(yùn)。
這些家鄉(xiāng)的土豆,劉巨德沒有讓它們離開生長(zhǎng)的沙土地。它們被種下它們的人從土地里刨出來(lái),還堆放在生長(zhǎng)的沙土地上,挨挨擠擠,滿身灰色的沙粒,好像剛剛出生的嬰兒,閉著雙眼,卻嘟著小嘴尋找母親的奶頭。它們是有身體的,它們甚至還有朦朧未開的嘴臉和可愛的胖胖的屁股。它們也有溫度,有質(zhì)感,有重量。它們是一種生命,在劉巨德看來(lái),它們是一種特殊的生命:
“人們對(duì)童年的記憶都極為清晰,可能是小腦瓜還處于空白狀態(tài)的緣故,只要回到老家,我眼前的一切都會(huì)匯入心中童年無(wú)底的河。見到什么都想去畫,特別是畫土豆,梵·高畫過(guò),我也愛畫它,這不僅是因?yàn)槲曳N過(guò)土豆,并吃土豆長(zhǎng)大,更重要的是土豆的生命精神頑強(qiáng)感人。它土渾渾的面孔和變形的身軀,不管人們把它切成幾塊,到春天它總會(huì)發(fā)芽。因?yàn)樗砩嫌袕?fù)眼,多視角,多方位發(fā)芽生長(zhǎng),它的軀體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全息的整體的化身,所以它的成活率、繁殖率屬于塊莖植物之最。”
“老鄉(xiāng)常把土豆藏在深深的地窖里,終年不見太陽(yáng)。但是土豆心里明白外界的春天在何日,屆時(shí)它自動(dòng)長(zhǎng)出白芽和根須,并且越長(zhǎng)越長(zhǎng),直到把自己體內(nèi)的能量耗干,長(zhǎng)出新綠,又有了下一代為止。”
“從中你會(huì)感到有限的生命是‘道’的生滅,而‘道’的生滅是無(wú)限的。生命像一個(gè)流,一個(gè)同時(shí)生滅的續(xù)流,綿延不絕。”
“藝術(shù)生命也像土豆發(fā)芽,它不怕黑暗和孤寂,它懂得春天來(lái)臨時(shí)會(huì)勃然而發(fā)。它是春的使者,它默默誕生于地下”[9]
劉巨德在一篇訪談錄里坦言:“現(xiàn)在隨著年齡的增長(zhǎng),我的心逐漸往回走,往生長(zhǎng)和養(yǎng)育我的那塊土地走。”他不斷地畫家鄉(xiāng)的土豆,有一種想化生為土豆,鉆回家鄉(xiāng)的土地的生命沖動(dòng),這是一種“逆生”心理,回到自己生長(zhǎng)的土地,回到童年的故鄉(xiāng),甚至回到母親的子宮。
“我母親跟我說(shuō),我出生的時(shí)候是晚上,牛羊歸圈捻燈后,堂屋羊圈里的一只小羊羔和我同時(shí)降生。那是臘月,我母親坐在土炕上,坐在厚厚的、被太陽(yáng)暴曬過(guò)的、被火炕烘烤過(guò)的熱乎乎的沙土里,生下了我。胞衣啊,羊水啊,血液啊,都滲透在沙土里。……我生在土里,按陰陽(yáng)五行的話,也屬土。”[10]
生在土里,自覺五行屬土,而且覺著自己最像“一把土”的劉巨德,確實(shí)是在回到故鄉(xiāng)的土地后,找回了心中的寧?kù)o與祥和,安頓好了自己的靈魂,也找到了自己藝術(shù)的歸宿。自那年以后,從90年代至今,他經(jīng)常回故鄉(xiāng),畫畫故鄉(xiāng)院子里的大蔥,墻頭上擺著的向日葵,喝水的粗瓷碗。有時(shí)走出去,看到滿地的蓮針草,仿佛看到父親背著一大捆蓮針草回家當(dāng)柴燒,自己同小伙伴們?cè)谏忈槻莸那G棘里翻找蓮針莢莢,放在嘴里吹口哨。于是歡欣,便穿過(guò)蓮針草叢去往南河溝邊,那里有一條小路,通往鄉(xiāng)中心小學(xué),他在這路上走了五年。時(shí)光仿佛又回到11歲那年冬天,漫天鵝毛大雪,四野無(wú)人,白茫茫一片,只有他獨(dú)自走在厚厚的積雪里,在徹骨的寒冷和恐懼的孤獨(dú)中,強(qiáng)忍淚水,前往學(xué)校……
“童年的背影晃動(dòng)在這里,我畫了這條路。這條路夏日碧綠,冬日雪白,春天花開,秋天黃灰,四季都美麗。”[11]
這是一個(gè)同故鄉(xiāng)完全和解了的藝術(shù)家晚年的心境。歲月靜好,安心若素。
一切偉大的人物,都經(jīng)歷過(guò)奧德修斯的人生回環(huán)。童年時(shí)并不覺得故鄉(xiāng)有多好,青年時(shí)想法設(shè)法逃離故鄉(xiāng),在經(jīng)歷了中年的人生激蕩,并同這個(gè)世界搏斗了半輩子之后,突然有一天,他聽到故鄉(xiāng)的召喚。于是,他扔下所有掙來(lái)的功名利祿,以及一切他曾經(jīng)視為幸福的東西,義無(wú)反顧踏上回鄉(xiāng)的路。
在湘西鳳凰城沱江邊的沈從文墓地上,黃永玉為他的表叔刻寫了這樣一句墓志銘:“一個(gè)戰(zhàn)士,不是戰(zhàn)死沙場(chǎng),就是回到故鄉(xiāng)。”
回到故鄉(xiāng)的劉巨德,看什么都情滿于懷,意溢于胸。
“我看見故鄉(xiāng)那些高壽的大伯們,紫紅紫紅的臉膛,長(zhǎng)須眉下深深的、閃亮的眼光,蓬亂的胡須,凹凸不平的皺褶,好美啊。”
“我高興畫他們,他們也高興讓我畫。他們滿臉層層疊疊的溝壑,彎彎曲曲的波濤,令我激動(dòng)。我的手常下意識(shí)地跟隨著那漩流,或上或下,或急或緩,不停地運(yùn)動(dòng)于紙上,筆觸一下緊接一下,粗粗細(xì)細(xì),隨著波濤而起伏。……我只是在紙上求索,閱讀鄉(xiāng)親們臉上的風(fēng)景,撫摸他們臉上一道道曾經(jīng)流過(guò)汗水、雨水、雪水、淚水的溝岔和山梁,深感他們?nèi)巳擞凶约旱淖饑?yán),個(gè)個(gè)有獨(dú)特的奇美。”[12]
人生的閱歷,哲人的啟迪,生活的陶冶,讓劉巨德鉆過(guò)了曾經(jīng)橫亙?cè)谒凸枢l(xiāng)之間的“鐵壁”,也幫他鉆過(guò)了橫插在一個(gè)藝術(shù)家和他所感到的和所能做到的對(duì)象中間的那道“鐵壁”。劉巨德為此而興奮:
“手感的快慰和情感的釋放告訴我,這一定是藝術(shù)的種子已發(fā)芽。”“面對(duì)形象,我沒有片刻的用腦分析和比量,只是跟著感覺走,憑著手感畫,順勢(shì)而為,也可能畫得不準(zhǔn)確,或者已變形,但目中的所有人,全已化為‘韻’。抽象的律動(dòng)讓我把和諧盡收眼底,其間有難以言說(shuō)的笑口和傷口。形象,無(wú)論老人、婦女、兒童、田野、村莊、土豆,他們都有表情,有尊嚴(yán),有精神。與天地相連,有浩然之氣鼓蕩其間,或悲或喜、或憂或泣,或磅礴綿延,如彩云舒卷、江河奔騰、琴聲婉轉(zhuǎn)。她們讓我感動(dòng)和傷痛,也令我喜悅又迷茫。”[13]
2010年,劉巨德創(chuàng)作了一幅紙本設(shè)色的水墨畫:一只羽毛凌亂的鳥,勾著腦袋,全身趴在它的兩只雪白的鳥蛋上。黑黑的厚厚的土地,灰灰的渺渺的蒼天,天地之間,別無(wú)長(zhǎng)物,唯有它和它的即將出殼的孩子。畫家動(dòng)情地為這個(gè)“家”獻(xiàn)上了三枝百合花,一枝給母鳥,兩枝給即將誕生的孩子,并為此畫取名《后草地》——那是他的故鄉(xiāng)。
“藝術(shù)家都由故土養(yǎng)育。第一塊是子宮的故土,養(yǎng)育著藝術(shù)家的天性、秉性和血?dú)猓坏诙K是童年的故土,像人生的河床,布滿理想,鑄有藝術(shù)家的心范,相遇在自然深處;第三塊故土,是文化的故土,它是一個(gè)國(guó)家一個(gè)民族生機(jī)勃勃的文化傳統(tǒng),古圣先賢的智慧、骨氣、生命和精神。文化故土永不過(guò)時(shí),我們需要回到永恒的源頭;第四塊故土,是自然宇宙的故土,也是人類共同的故土。我們每一個(gè)人都和大自然大宇宙相連,和無(wú)限相連。只有我們進(jìn)入無(wú)限的時(shí)候,我們才能進(jìn)入藝術(shù)。”[14]
回歸故土,對(duì)于劉巨德,不是對(duì)世界的逃避,也不是策略性的權(quán)宜之計(jì),更不是走投無(wú)路的浪子回頭,而是出于他對(duì)藝術(shù)家與藝術(shù)的人類學(xué)思考,哲學(xué)思考,甚至源于他心靈深處澒洞浩渺的宇宙情懷。
故土于劉巨德,是所自,所來(lái),所由,所歸,所有。
四、裝飾
說(shuō)劉巨德,不能不提到他學(xué)習(xí)并工作的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及其前身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
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建于1956年11月,是新中國(guó)第一所設(shè)計(jì)藝術(shù)類高等學(xué)府。中央工藝美院匯集了一大批力圖發(fā)展中國(guó)現(xiàn)代工藝美術(shù)和設(shè)計(jì)藝術(shù)的大師,如張光宇、張仃、龐薰琹、雷圭元、祝大年、鄭可、高莊、吳冠中,還有一大批各專業(yè)的名師、名家,培養(yǎng)出了袁運(yùn)甫、常沙娜、喬十光、丁紹光、李鴻印、何山、劉紹薈等一批有影響力的藝術(shù)家,而像王懷慶、杜大愷、劉巨德、鐘蜀珩、王玉良等藝術(shù)家則是這個(gè)學(xué)院傳統(tǒng)的又一輪后來(lái)者。1999年11月,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并入清華大學(xué),成為“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劉巨德任副院長(zhǎng)兼院學(xué)術(shù)委員會(huì)主任。由于中央工藝美院在北京朝陽(yáng)區(qū)光華路辦校教學(xué)的時(shí)間最長(zhǎng),幾乎長(zhǎng)達(dá)30年,所以,學(xué)院師生的“光華路”情結(jié)特別濃重和強(qiáng)烈,以至于清華大學(xué)校園里通往美術(shù)學(xué)院的道路都被命名為“光華路”。
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并沒有設(shè)置繪畫系及相關(guān)的純藝術(shù)專業(yè),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則設(shè)置了繪畫系,有中國(guó)畫、油畫、版畫和公共藝術(shù)四個(gè)專業(yè)。
雖然純藝術(shù)的繪畫在中央工藝美院時(shí)代只是作為基礎(chǔ)課,正如杜大愷所說(shuō):“他們的學(xué)術(shù)思想和藝術(shù)成就不僅影響了這所學(xué)院的發(fā)展,亦同時(shí)影響了中國(guó)近現(xiàn)代藝術(shù)的歷史,中國(guó)近現(xiàn)代藝術(shù)如沒有他們的名字或會(huì)是另一種狀態(tài),而且這個(gè)影響沒有結(jié)束,有人把這個(gè)影響稱作清華學(xué)派。”[15]
其實(shí),早在中央工藝美院的時(shí)代,就有識(shí)者指出,中央工藝美院不同于中國(guó)其他幾所純藝術(shù)類美院的地方,不只是因?yàn)樗俏ㄒ灰凰O(shè)計(jì)藝術(shù)類學(xué)院,而在于其理念和風(fēng)格。她具有更開放更包容更現(xiàn)代的藝術(shù)理念,她打通生活和藝術(shù)的辦學(xué)方向,熔鑄中西的胸襟,平等對(duì)待精英藝術(shù)和民間藝術(shù)的氣度,不為古典繪畫門類所束縛的超脫,充分尊重藝術(shù)個(gè)性的寬容,還有,對(duì)藝術(shù)更高遠(yuǎn)的期許,以及使用藝術(shù)語(yǔ)言上更自由、更達(dá)觀的氣派,使得她更像一所20世紀(jì)的藝術(shù)大學(xué),更接近“大美術(shù)”的20世紀(jì)國(guó)際潮流和方向。因此,應(yīng)該特別提出,20世紀(jì)中國(guó)美術(shù)史,有一個(gè)“工美學(xué)派”或叫“光華學(xué)派”。
杜大愷在回望這一段院史的時(shí)候,不無(wú)感慨地發(fā)問:
“他們何以會(huì)在同一歷史時(shí)刻會(huì)聚于一所學(xué)院,他們各自的獨(dú)特性何以不被彼此遮蔽且因?yàn)橄嗷バ蕾p而彰著,他們竟能在成功地維系各自的獨(dú)立中凝聚相對(duì)同一的目的、同一的意志,這是一個(gè)奇跡。所以能有這樣的境界,得益于這所學(xué)院的開放與寬容,得益于這所學(xué)院能夠穿越古今、融匯中西的高瞻遠(yuǎn)矚,得益于這所學(xué)院超越時(shí)間和空間的情懷和識(shí)斷,得益于這所學(xué)院能夠集結(jié)人類的智慧與創(chuàng)造并以其為出發(fā)點(diǎn)的理性與情結(jié)。”[16]
劉巨德在很多場(chǎng)合都反復(fù)說(shuō)過(guò),他此生最大最大的幸運(yùn),是考進(jìn)了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
他的言下之意和話外音是什么呢?
其次,這個(gè)學(xué)院不偏食,中餐西餐小吃都有,葷素齊備,學(xué)生可根據(jù)胃口和偏好各取所需。
第三,這個(gè)學(xué)院的繪畫是要服務(wù)于設(shè)計(jì),服務(wù)于實(shí)用的,所以,沒有高高在上的“貴族感”,必須會(huì)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材料,適應(yīng)不同的空間和環(huán)境,當(dāng)然,也不可能嚴(yán)格劃分油畫、國(guó)畫、版畫,因此,劉巨德們被培養(yǎng)和訓(xùn)練得樣樣都能,拿起板刷能畫油畫,拿起毛筆能畫水墨,拿起刀子能刻板,拿起尺子能設(shè)計(jì),還能上墻畫壁畫,給書畫插圖,還能設(shè)計(jì)動(dòng)漫電影——他們衣缽傳自老師,張光宇、張仃、龐薰琹,就是美術(shù)界的多面手。
但是,不要認(rèn)為中央工藝美院只是消極地準(zhǔn)備了一桌“滿漢全席”,而對(duì)學(xué)生們沒有正面的藝術(shù)理念和方法的積極灌輸與訓(xùn)練。
劉巨德認(rèn)為,作為一個(gè)畫家,他從老師那兒獲得的終生受益的教誨有:
一、對(duì)線的強(qiáng)調(diào)。劉巨德反復(fù)同研究生講,“線描是我院各專業(yè)的看家本領(lǐng)。”把線放在繪畫藝術(shù)的本體位置之上,用線造型,并形成用線造型的思維習(xí)慣,把用線造型當(dāng)成激發(fā)潛在美感和造型能力的基本方法,甚至是唯一方法。西畫習(xí)慣以明暗光影的實(shí)體觀念畫對(duì)象,中國(guó)畫家完全不一樣,是從線組成的虛空的流動(dòng)去畫對(duì)象,線是氣之所聚,有流動(dòng)就有韻,所以不僅有虛空,還有節(jié)奏。無(wú)論什么對(duì)象,是人還是物,先從平面虛空抽象地去看,不作分別,構(gòu)成對(duì)象的都是虛空的線的流動(dòng),他(或它)都是線的氣韻和虛像。這涉及到對(duì)“真”的理解。西畫從明暗光影,把“真”看成“實(shí)”,所以有“真實(shí)”;中國(guó)畫從虛空的運(yùn)動(dòng),把“真”看成“氣韻”,所以有“生動(dòng)”,生動(dòng)即真。線是尚虛的,尚氣的,尚韻的,尚動(dòng)的。因此,劉巨德一生都在用線造型,一生都在錘煉畫線的功夫,不管拿什么工具,油畫的板刷,刻紙的刀片,鉛筆或木炭條,毛筆,都可以操起即畫,畫出渾沌圓融環(huán)轉(zhuǎn)的各種線條。
他現(xiàn)在帶研究生,第一堂課就講線,可能同學(xué)們一時(shí)還難以理解,尤其從西畫過(guò)來(lái)的,但不要緊,劉巨德會(huì)一次一次地示范,叫學(xué)生們?nèi)绾伟颜n堂上的模特“虛空”掉,抽象出線,然后如何讓線分出主次和隨輔,如何讓線隨著氣運(yùn)動(dòng),如何去用身體感覺毛筆和宣紙接觸時(shí)那種如撫摸嬰兒肌體一樣令人欣喜的微妙感覺,他告訴學(xué)生:
“任何有光影、明暗、體積的對(duì)象,都可以虛化成一種線的運(yùn)動(dòng),并把所有的特征化進(jìn)去。”[17]
有趣的是,劉巨德的線,既非達(dá)·芬奇、米開朗基羅、安格爾、羅丹、梵·高、畢加索、馬蒂斯、米羅、達(dá)利等西方繪畫大師的線,也非顧愷之、陸探微、李思訓(xùn)、吳道子、李公麟、趙孟頫、唐寅、徐渭、石濤、八大山人、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等中國(guó)畫大師的線。他的線沒有書法性,所以既無(wú)“高古游絲”般飄逸,也無(wú)“千年枯藤”般蒼勁,更無(wú)“生死剛正”的金石味;但也明顯不同于西畫之線,因?yàn)樗瞄L(zhǎng)鋒的中國(guó)毛筆,線的變化明顯多于西畫之線;又因?yàn)檎核谛埳线\(yùn)行,其速度之疾徐、力量之輕重,又同西畫線條的軌跡特征大異其趣。更何況,他的線條還有濃淡粗細(xì)枯潤(rùn)的變化。我們只能說(shuō),劉巨德所理解的線,是非中非西又中又西的,這恰好符合他的“渾沌”理論,即不作分別。從他執(zhí)筆作畫的身體姿態(tài),我們或許能夠理解這一點(diǎn):他作畫的姿態(tài)更像一個(gè)西畫家,宣紙像畫布一樣釘在畫板上,與地面垂直。他坐在椅子上,右手像拿油畫筆一樣,拿一根一米長(zhǎng)的中國(guó)長(zhǎng)鋒毛筆,蘸足墨水,伸臂向前,與垂直于地面的紙面正好成90°角,在兩米直徑的范圍內(nèi),他不用移動(dòng)身體,而直接掄出各種長(zhǎng)長(zhǎng)短短的線。他的這個(gè)身體姿式,好像古代的騎士。我想,這種作畫的經(jīng)驗(yàn),恐怕古今中外不會(huì)有第二個(gè)畫家了吧?因此,劉巨德的線條,在看似無(wú)個(gè)性中,反而呈現(xiàn)出辨識(shí)度極高的個(gè)性,因?yàn)椋倪@個(gè)握筆行筆的身體姿態(tài),是獨(dú)門功夫,江湖上無(wú)人能練。所有的中國(guó)書畫家執(zhí)的都是短筆,三指搦于管腰,垂直點(diǎn)厾,能懸腕已是其極,直徑不出一臂,也就是半米,所以,如用執(zhí)兵器比喻,他們都只是持匕。而劉巨德,是五指抓筆,掌心抵筆,直戳向前,直徑兩米,他這是真正的使筆如槍,是長(zhǎng)槍大戟的玩法。觀唐代墓室壁畫,那些動(dòng)輒長(zhǎng)達(dá)兩三米的長(zhǎng)線,恐怕也是用這樣的長(zhǎng)槍筆法掄出來(lái)的。
二、對(duì)裝飾的全新闡釋的理解。劉巨德說(shuō):
“我們學(xué)院有一個(gè)老傳統(tǒng),就是裝飾藝術(shù)的文脈,對(duì)我影響很大。我的老師龐薰琹先生,上個(gè)世紀(jì)30年代中國(guó)美術(shù)界決瀾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曾說(shuō)過(guò):裝,藏也。即看不見的真理,它藏在里面,特指宇宙之道,你是看不見的,它是中國(guó)人一直追尋、敬畏和體驗(yàn)的。飾,文采也。在古代,飾和拭通用,都是擦干凈的意思。擦掉你心靈上的銹蝕和污垢,心靈明亮,你才能接收到宇宙的光芒。所以,裝飾與中國(guó)畫論講的澄懷觀道是一個(gè)道理,同一個(gè)境界,澄懷觀道是裝飾的最好注釋。”“很多人誤讀、誤解裝飾藝術(shù),甚至認(rèn)為這是個(gè)貶義詞,或形式主義的代名詞。其實(shí)裝飾藝術(shù)是對(duì)中國(guó)乃至東方傳統(tǒng)藝術(shù)精神的總稱。”“因?yàn)檎`解它,就小看它,就不重視它,就會(huì)錯(cuò)怪它,就像錯(cuò)怪真理一樣。也有人把裝飾理解成一種形式語(yǔ)言。語(yǔ)言屬形而下,語(yǔ)言的背后,澄懷觀道是形而上,裝飾屬形而上,真正的藝術(shù)生長(zhǎng)于形而上世界。”“其實(shí),裝飾藝術(shù)是東方現(xiàn)代藝術(shù)之母,貴在替天行道。不懂裝飾藝術(shù),難以進(jìn)入藝術(shù)永恒的精神世界中。”[18]
劉巨德關(guān)于裝飾和裝飾藝術(shù)的這番話,真是大做翻案文章,可以視為裝飾藝術(shù)的宣言書。
裝是藏,飾是采,也是拭。裝飾合為一個(gè)復(fù)合詞,意思非常深刻和豐富。把某件東西裝起來(lái),實(shí)際上就是藏起來(lái);裝藏和隱藏不一樣,是隆重地、有儀式感和形式感地藏起來(lái),所以這裝的外表,就要有文采,要擦試干凈亮堂,這就是飾。什么東西或事物值得這樣去“裝飾”呢?這樣隆重而有文采地去“藏”一件東西,豈不是同“藏”的本意和目的相反,有“謾藏誨盜”或“欲蓋彌彰”的意思嘛!對(duì),就是這樣子的,因?yàn)橐把b飾”的不是什么見不得人的壞家伙、丑東西,而是大美、至善的道與真。裝飾藝術(shù)的本意,一是為了隆重其事,二是為了讓人們更加關(guān)注其事,三是為了道與真本身更光明更干凈更亮堂更美麗更輝煌,所以,裝飾一詞,內(nèi)含敬畏,外呈隆重。裝飾藝術(shù),顧名思義,當(dāng)然就是敬畏隆重道與真的美的藝術(shù)了。我們難道要對(duì)這樣敬畏和隆重道與真的美的藝術(shù)表示鄙夷嗎?歷史上,人類文明史上,大凡昌盛之世,禮儀之邦,裝飾藝術(shù)都大行其道;反之,衰落之世,野蠻之邦,裝飾藝術(shù)或打入冷宮,或遭受荼毒。龐薰琹先生打成右派的二十年里,恰好是裝飾藝術(shù)在中國(guó)遭受厄運(yùn)之時(shí),就證明了這一點(diǎn)。
“光華學(xué)派”或“清華學(xué)派”,作為一個(gè)美術(shù)學(xué)派,其60年傳承中一個(gè)顯著的特點(diǎn),就是“裝飾風(fēng)格”。張光宇、龐薰琹、祝大年、張仃,是這一學(xué)派的奠基者。在寫實(shí)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年代,他們的藝術(shù)被批為“形式主義”、“唯美主義”、“畢加索加城隍廟”。
其實(shí),按照“裝飾”的語(yǔ)詞本義,是要為了更好地彰顯真理,讓真理更直觀更鮮亮更透明地呈現(xiàn)出來(lái),所謂“形式感”,在這里就是內(nèi)容本身,因?yàn)檎胬肀缓?jiǎn)約化了,去蕪存菁,一切不必要的雜質(zhì)一旦滌除,真理本身就會(huì)形式感十足地呈現(xiàn)出來(lái),因?yàn)樗皇潜A袅俗畋举|(zhì)的結(jié)構(gòu),真理的最本質(zhì)的結(jié)構(gòu)一定是唯美的,和諧的,簡(jiǎn)約的,形式感十足的。所謂“飾”,也就是文采和擦拭,不是畫蛇添足的繁文縟節(jié),而是把“裝藏”的真理隆重地表達(dá)出來(lái),讓人們對(duì)她充滿敬畏和愛戴,心中一片澄明與歡欣。
自從三萬(wàn)年前人類有了原始藝術(shù),一直到今天的當(dāng)代藝術(shù),難道藝術(shù)史不就是這樣來(lái)揭示真理的本質(zhì)結(jié)構(gòu),并做最美的呈現(xiàn)嗎?
所以,劉巨德才說(shuō):“裝飾屬形而上,真正的藝術(shù)生長(zhǎng)于形而上世界。”“不懂裝飾藝術(shù),難以進(jìn)入藝術(shù)永恒的精神世界中。”
從進(jìn)入中央工藝美院那一天起,劉巨德就在努力理解“裝飾”和“裝飾藝術(shù)”的深刻含義,他也曾說(shuō)過(guò),中央工藝美院在中國(guó)是另一個(gè)“藝術(shù)星球”。現(xiàn)在,他的藝術(shù),已經(jīng)屬于這個(gè)裝飾藝術(shù)文脈,而他,也榮幸地成為了這個(gè)特別的“藝術(shù)星球”的居民。
五、渾沌
采訪劉巨德的記者問他最像哪種動(dòng)物,駱駝?牛?羊?劉巨德出人意表地說(shuō):“一把土。”
土,沒有形狀,又可以摶成各種形狀。據(jù)說(shuō)人、牛、豬、羊,都是女媧摶土所造。人又摶土造器,造各種形態(tài)的雕塑。
按中國(guó)五行學(xué)說(shuō),土居中央,中央之帝為渾沌。渾沌待人厚道善良,但囫囫圇圇沒有七竅。他有兩個(gè)鄰居,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兩個(gè)冒失鬼覺得人皆有七竅,眼可視,耳可聞,鼻可呼息,口能言能食,還有管排泄和性欲的,有七竅才有感覺,有感覺才有幸福。于是為了渾沌的幸福,倏和忽決定給渾沌開七竅。每天一竅,七天七竅成而渾沌卻死翹翹了!
莊子講這個(gè)寓言是帶著快感的,劉巨德聽了卻很傷感。他決定為渾沌招魂,用藝術(shù)。
首先,他認(rèn)為“渾沌是不可改造的。”藝術(shù)之所以可貴,就是藝術(shù)順應(yīng)和成全所有人的天性和志趣,絕不強(qiáng)求一律。批評(píng)家和觀眾不可以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要求藝術(shù)家和藝術(shù)品,藝術(shù)家自己也切記不可以別人的眼睛看世界,遮蔽自我的純真。“我之為我,自有我在。”
其次,“渾沌呈內(nèi)直覺。”什么是內(nèi)直覺?就是關(guān)閉導(dǎo)向五色、五音、五味、五能等現(xiàn)象界的感官窗口,不要讓現(xiàn)象界的龐雜紛亂擾亂心智,破壞了最自然之道的本質(zhì)體認(rèn)。超越現(xiàn)象界,用心靈的內(nèi)直覺去認(rèn)識(shí)世界的理、法、道、真。
第三,“渾沌無(wú)分別。” “渾”就是整體無(wú)分別,“沌”就是圓環(huán)無(wú)極,無(wú)始無(wú)終。渾沌強(qiáng)調(diào)整體思維,追求無(wú)差別的“無(wú)朕”境界,對(duì)事物不強(qiáng)起分別心,不用人為的概念和范疇去切割本來(lái)聯(lián)系為一體的整體,看世間萬(wàn)物總是看它們的同一性和內(nèi)在聯(lián)系,同氣相求,同氣相應(yīng),同氣共存。老子所言“大象無(wú)形,大音希聲”,莊子所說(shuō)“與天地相侔,萬(wàn)物齊一”,謝赫所倡“氣韻生動(dòng)”,都是從渾沌一氣來(lái)立論的。
第四,“混沌至善”。渾沌順其自然,無(wú)為而無(wú)不為,有大美而不言,保持自然的生命本性,寬容,博愛,平等,不妄作。
關(guān)于“渾沌”的這四個(gè)特性,劉巨德寫有《走向未知的美神》專文論述,文章收入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
熟識(shí)劉巨德的人都知道,他這個(gè)人就比較“渾沌”。不僅長(zhǎng)得渾沌,性格氣質(zhì)也渾沌。
他的畫也渾沌,圖底關(guān)系不太明確,意義含混,情感朦朧,光影迷離,線條圓融,形象豐滿,構(gòu)圖飽和。不可否認(rèn),他對(duì)圓乎乎的、胖嘟嘟的,土渾渾的形象,無(wú)論是人還是物,有著自己審美上的強(qiáng)烈偏愛,這可能也是出于他對(duì)渾沌的理解和追求吧。包括他對(duì)毛筆、水墨、宣紙這些中國(guó)畫工具材料的偏好,我認(rèn)為也是他的渾沌觀的工具性表達(dá)。因?yàn)樵谑澜缟纤械睦L畫工具和材料中,中國(guó)毛筆因其長(zhǎng)鋒、水墨因其含混、宣紙因其氤氳,而成為極難駕馭的柔性工具材料。它們對(duì)抗所有清晰、明確、精準(zhǔn)的剛性指揮,總是自由地“逸”出常規(guī)和理性,所以,中國(guó)水墨畫的最高境界,不是“神”,更不是“能”,而是“逸”。他對(duì)黑色和灰色的偏愛,也是這樣。這樣的工具,這樣的材料,這樣的色相,合到一起,以水融之,以水運(yùn)之,以水化之,就是老子所說(shuō)的“玄之又玄”,也是老子所說(shuō)的“恍惚”:“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尚水尚玄尚逸的“恍惚”之境,就是渾沌的另一種表述。劉巨德迷戀于其中,游于無(wú)朕,他甚至把大寫意的水墨畫法用于他的油畫。他非常自豪地宣稱,中國(guó)的哲學(xué)智慧所灌溉的中華民族的審美心靈,是可以受之無(wú)盡的文化滋養(yǎng)。一個(gè)藝術(shù)家應(yīng)該經(jīng)常“回到永恒的源頭”,回到永不過(guò)時(shí)的“文化的故土”。確實(shí),“文化故土”給他提供的渾沌智慧,給了他跳向玄默深淵的勇氣。
渾沌之所以為渾沌,就在于一團(tuán)元?dú)獍形撮_,故而天真存焉。清代桐城派領(lǐng)袖姚鼐說(shuō)泰山所以稱雄五岳,就在其元?dú)鉁喨谖磋彛蕴┥浇^不以巧示人。他實(shí)際上是在宣揚(yáng)他的古文理論。從泰山采氣,以壯其文。
劉巨德也主張畫家要采氣:
“采自然之氣,采古賢之氣,采大師之氣,以養(yǎng)我手氣、心氣,時(shí)間長(zhǎng)了,自己就有了膽氣,敢跳向深淵,在深淵里遇見了自己一團(tuán)渾沌的氣。”[19]
采自然之氣,劉巨德偏好北方,黃土高原,蒙古草原,有滿滿的土渾渾的元?dú)猓形磋彛黄煺妗?/p>
采古賢之氣,劉巨德偏愛霍去病墓石雕群,米開朗琪羅,八大山人。特別是霍墓石雕:
“在渾沌中雷霆萬(wàn)鈞之力凝于一瞬,英雄的力量和不朽,全然與天地相連,”“無(wú)名工匠天馬行空,神與物游,在荒野亂石中,利用天然的石頭形態(tài),稍加雕刻而成。一切惚兮,恍兮,其中有人,有物,有情,有神,卻無(wú)解剖結(jié)構(gòu)表現(xiàn)之顯現(xiàn),圓雕、浮雕、線刻渾然為一。”[20]
劉巨德對(duì)渾沌四特性的總結(jié),有點(diǎn)像夫子自道,其實(shí)說(shuō)的是他自己和他的藝術(shù)主張。
渾沌不可改造,尊重自己的天性,稟賦,血?dú)猓瑥牟桓L(fēng)。他對(duì)老師龐薰琹、吳冠中、祝大年、張仃非常尊敬,也從他們那兒學(xué)到許多,但“我自收我肺腑,我自揭我須眉。”對(duì)藝術(shù)潮流也能做到“八風(fēng)吹不動(dòng)”,我自做我的“天邊月”。甘于寂寞以求真。也從不要求學(xué)生學(xué)他,似他,在教學(xué)中尊重、啟發(fā)每一個(gè)學(xué)生的個(gè)性。
做畫,寫生,都非常強(qiáng)調(diào)內(nèi)直覺,以神遇,不以目視。他那些家鄉(xiāng)故土的作品,能超越寫生而直抵某種浩渺的宇宙情懷,就是他的內(nèi)直覺在觀察那些土豆、向日葵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洞穿童年的故土,而引向子宮的故土、文化的故土和宇宙的故土,所以才能擁有如此浩大深邃的意境,直擊每個(gè)人心靈深處的秘府。包括那條著名的《魚》,如果不是在觀察、寫生、創(chuàng)作時(shí)依靠和發(fā)揮內(nèi)直覺,又怎么能夠超越一幅單純的靜物畫而發(fā)人無(wú)限之思呢?我們看到劉巨德的畫,總覺得在眼前的這個(gè)視象之外,還有許多詩(shī)思把我們的心靈引向遠(yuǎn)方,大概就是這個(gè)道理。他用內(nèi)直覺把我們從現(xiàn)象界牽到渾沌世界,意義含藏不盡。
渾沌無(wú)分別,在劉巨德這里,首先表現(xiàn)為風(fēng)景、人物、靜物、花鳥無(wú)分別,油畫、水墨、雕塑、線描無(wú)分別,隨心所欲,隨感而興,隨緣即作,看山如看人,看人如看花,看花如看影,看影如看光,看光如看氣。宇宙萬(wàn)物一氣耳,氣韻生動(dòng),這就是一個(gè)藝術(shù)家心目中萬(wàn)物的統(tǒng)一性。他畫水墨如畫油彩(《向日葵》),畫油彩如畫水墨(《優(yōu)思鳥》);畫土豆如畫人(《家鄉(xiāng)土》),畫人如畫土豆(《女人體》);畫小草如畫世界(《原上草》),畫世界如畫小草(《黑白相知》)。在《生命之光》里,人、鳥、花、葉已全無(wú)分別,只是生命之歌的一個(gè)音符,一節(jié)旋律。
對(duì)于劉巨德來(lái)說(shuō),“渾沌至善”并不是一個(gè)世俗層面的道德命題,而是指在自由極至的藝術(shù)至高境界里,美與真相通所獲得的大解放,唯其大解放,才能順其自然,寬容博愛。落實(shí)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就是跟著感覺走,一筆生萬(wàn)筆,起于所起,行于所行,止于至善。看劉巨德作畫,真有這種妙感通貫全身。不管多大的畫,哪怕是丈二,哪怕是一壁墻,他都是從不起稿,只追隨胸中勃勃生意,一筆落紙,筆筆赴之,主線,結(jié)構(gòu)線,輔線,隨線,在他筆下反轉(zhuǎn)流動(dòng),節(jié)奏,動(dòng)勢(shì),體量,都從線條“流”出來(lái)。他站在一米開外,手握一米長(zhǎng)的特制毛筆,像金庸筆下的武俠高手,凌波微步,用他教學(xué)生示范時(shí)的話說(shuō):
“你是走在湖面的水上,用腳輕輕踩著水,做著氣功走,松、靜、自然。輕輕的,平靜的,撫摸式的,與神對(duì)話般的,舒服的,驚喜的……任何有光影、明暗、體積的對(duì)象,都可以虛化成一種線的運(yùn)動(dòng)。”[21]
劉巨德作畫的過(guò)程,其實(shí)是一個(gè)意識(shí)流的過(guò)程。對(duì)象早已裝進(jìn)了他的“心范”,這個(gè)“心范”是柔軟的,活潑潑的:
“所有生命的光、生命的色、生命的形、生命的氣流進(jìn)‘心范’的時(shí)候,‘心范’就會(huì)把紛雜的對(duì)象整合出一種詩(shī)意的意識(shí)流,鑄成藝術(shù)。”[22]
這時(shí)候,用筆就像長(zhǎng)江后浪推前浪,如水就下,如焰就上。這種狀態(tài),就像畢加索說(shuō)的:“不是我要畫畫,而是畫讓我畫。”美就在這種忘我意識(shí)流的狀態(tài)中順其自然而產(chǎn)生。而這,就是劉巨德所理解的“渾沌至善”。實(shí)際上,這是一個(gè)關(guān)于藝術(shù),關(guān)于自由,關(guān)于人和宇宙的終極目的的終極命題了。
有客問劉巨德:“中國(guó)畫,最本質(zhì)的精神是?”
劉巨德答:
“就是澄懷觀道、悟道、敬畏道、殉道。真正藝術(shù)的背后和最后都是天理和人性的最深處。至于每個(gè)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語(yǔ)言風(fēng)格,是澄懷觀道以后,自己自然而然長(zhǎng)出來(lái)的,千差萬(wàn)別,不需要人為去謀劃和設(shè)計(jì)。藝術(shù)需要自由地生長(zhǎng),像草一樣沒有疆界,根在地下默默地瘋狂蔓延。”[23]
注釋:
[1]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0.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2]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2.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3]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2-43.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4]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3.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5]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3.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6]劉巨德《面對(duì)形象》,見《名師名校寫生系列·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劉巨德》,P5.榮寶齋出版社。
[7]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2.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8]劉巨德《藝術(shù)點(diǎn)燃生命》,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81.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9]劉巨德《面對(duì)形象》,見《名師名校寫生系列·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劉巨德》,P5.榮寶齋出版社。
[10]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1-42.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11]劉巨德《面對(duì)形象》,見《名師名校寫生系列·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劉巨德》,P6.榮寶齋出版社。
[12]劉巨德《面對(duì)形象》,見《名師名校寫生系列·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劉巨德》,P6.榮寶齋出版社。
[13]劉巨德《面對(duì)形象》,見《名師名校寫生系列·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劉巨德》,P7.榮寶齋出版社。
[14]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50.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15]杜大愷《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序言,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16]杜大愷《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序言,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17]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70.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18]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8.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19]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44.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20]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7.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21]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70.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22]劉巨德《體驗(yàn)與冥想》,見《名作欣賞·靜若處子·劉巨德》,P19. 名作欣賞雜志社。
[23]劉巨德《追逐藝術(shù)的太陽(yáng)》,見《清華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繪畫系教師個(gè)案研究·劉巨德》,P50.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
(責(zé)編:楊 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