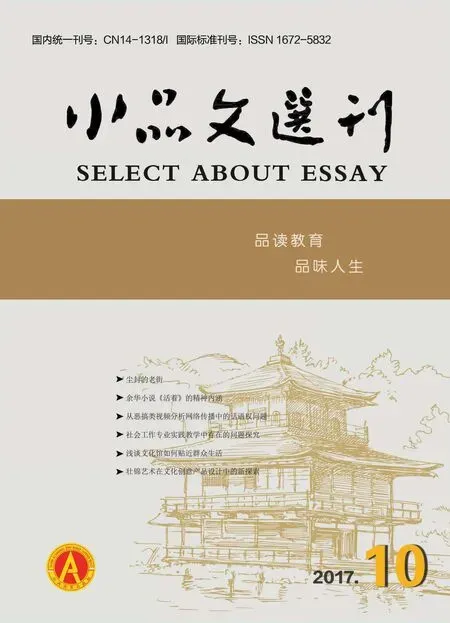潔凈、骯臟與分類秩序
——讀瑪麗·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
覃思思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與新聞傳播學院 廣西 桂林 541000)
潔凈、骯臟與分類秩序
——讀瑪麗·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
覃思思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與新聞傳播學院 廣西 桂林 541000)
瑪麗·道格拉斯是英國著名的象征人類學家、新結構主義的代表,其代表作 《潔凈與危險》 融合了象征人類學、結構人類學與宗教人類學的觀點和視角,被譽為人類學的扛鼎之作,對人文學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潔凈與危險》是“關于污穢和傳染觀念的論述”。該書包括序言、導言一共有十二個章節。從書目我們可大致看出作者的寫作思路:以小見大,用實際事實引出理論分析。并且開篇道格拉斯便交待了本書的寫作目的以及大致思路,有助于幫助讀者理解此書。在序言中,瑪麗·道格拉斯揭示了本書的兩大主題,一是“禁忌作為一個自發的手段,為的是保護宇宙中的清晰種類”,另一個是“對含混帶來的認知不適作出反思。含糊的事物看上去很有威脅感”。該書通過原始文化中禁忌與儀式的研究,引入了潔凈與骯臟這一對范疇,以此來揭示人類社會的分類體系與人的觀念之間的連帶關系,并對其象征意義提出了系統的看法。
本書十分強調“分類與秩序”,在序言中,道格拉斯便明確指出:“本書的中心論點之一是理性行為都離不開分類,分類為組織所固有,并不是自娛自樂的認知操演,組織需要分類,而分類又是人類協調的基礎。”書名便是對這一中心論點的點明與強調。
此外,書名其實也帶著濃重的象征主義色彩,即對事物“能指”與“所指”的巧妙運用。道格拉斯是少數對整個人文學科產生重大影響的人類學家之一,被大眾稱為象征主義人類學、新結構主義的主要代表學者之一。“象征人類學在本質上講就是把文化當成象征符號系統加以探討的人類學。”通過閱讀瑪麗·道格拉斯的《潔凈與危險》,我們不難發現,書名中“潔凈”能指的是“干凈與整潔”,而在這里所指的是一種“正常穩定的社會秩序”;“危險”本身指的是“有可能導致災難與不安全”,在書中它的“所指”則是“骯臟、失序的社會狀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象征人類學認為,文化符號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它之所以具有意識,都是人們根據自身文化需求賦予其上的。“象征符合是社會整合的意識形態工具,象征不具有全人類的一致性。”不同的民族文化有著不同的象征符號體系,這些象征體系是不同民族或者族群對其所處的世界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說,事物“能指”的情況可以只有一種,但“所指”的東西、意義卻可以是多種的,這是根據文化的具體需要而定的。正如格爾茨在《地方性知識》一書中提出的觀點一樣,每種文化都是“地方性”的,同一事物對不同的文化來說可以有不同的意義,并不存在什么全人類共同的文化。也正是因為文化的多樣性以及文化符號的多樣性,才出現了后來格爾茨所提出的“深描”的觀點。雖然象征人類學大致出現在20實際60年代之后,但縱觀整個人類學的發展歷史,其實也可以看到“象征”的影子。筆者認為,不論是對象征人類學也好,還是對其他人類學學派也罷,所有的文化都不可能擺脫符號與象征。比如,馬林諾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談到的“庫拉”交易模式,交易過程中所用到的“臂鐲”和“項圈”,它們“本身并無實際用途(非裝飾品、無經濟利益)”,但它們卻是布里恩德人身份、聲望與權力的象征;比如,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中提到的努爾人的“圣物”——牛,在傳統意義上,牛是一種耕作工具,但對努爾人來說,牛卻是他們標志性的文化特征;再比如格爾茨《文化的解釋》中描寫到的“斗雞”,巴厘島斗雞的深度不是為了在賭博中獲得金錢,而是為了獲得某種象征地位的“意義”,斗雞是象征,等級地位才是意義所在。
在英過社會人類學界中,道格拉斯是為數不多將結構主義容納進研究框架的學者之一。道格拉斯也提倡所謂的“二元對立”,并對社會觀念中的“異常物”十分關注,所謂的“異常物”“不是斯特勞斯所講的二元對立的東西,有點類似艾德蒙·利奇所說的‘第三元’”。例如,性別設置與性行為的秩序其實是存在著一定的沖突的。縱觀當今社會,我們會發現,在“男、女”二元性別關系之外,還有著“第三元”的存在——變性人。這類人介于男性與女性之間,便是道格拉斯口中的“異常物”,即違背社會戒律或超越社會所設立的事物之間界限的東西。而這種打破了社會正常秩序的存在,也就是道格拉斯在書中反復提到的“骯臟”、“危險”、“污穢”之物。變性人無法歸入傳統的性別結構之中,因而是具有潛在的危險,進而為社會大眾所排斥。“異常物”、“不純”、“危險”的概念明顯具有思維結構的含義,不過道格拉斯認為它們更重要的是具有社會功能,是維系社會自身秩序的手段,這點就不像斯特勞斯那樣提倡純思維結構了。
“分類排序”是道格拉斯潔凈觀中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個觀點。用道格拉斯的觀點來說,只有當事物處在分類框架的某個位置時,它的存在才有意義。不難理解,比如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鞋子”。鞋子放在地上通常是被認為是合理的,因為人們對日常生活用品的分類中,鞋子就應該處在玄關、鞋架的位置上,這個時候的鞋子我們可以說它是干凈的、安全的。但當我們把鞋子從鞋架上拿下來并放到飯桌上去時,鞋子便因逾越了生活用品的分類界限、破壞了生活用品擺放的正常秩序而變得骯臟、危險。這樣我們就很明顯能看出,同一雙鞋子,在不同的位置會得到不一樣的評價。鞋子本身并不是骯臟的,它之所以骯臟只是因為它本身的擺放不符合人們的分類框架。為了清除掉這種骯臟與危險,人們會將鞋子從桌子上再拿下來,把它放回到鞋架、玄關上去。這種行為其實也就是道格拉斯所謂的“排序”,將這種脫離正常秩序的存在進行重新歸位。此外,有一點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道格拉斯在書中提出“潔凈是相對的,骯臟也是相對的”,兩者并不是始終對立的,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相互轉化。仍舊以“鞋子”為例,放在玄關與鞋架處的鞋子是潔凈的,而放在飯桌上的鞋子則是骯臟的。因為骯臟,人們可能會將鞋子仍掉,歸為垃圾。一旦鞋子變成垃圾后,由于被歸于垃圾這一類別,這個時候它又變為潔凈的了。這一轉變實則也可以解釋原始宗教中模糊不清的禁忌食物。
C912.4
A
1672-5832(2017)10-0034-01
覃思思 (1993—),女,壯族,廣西柳州人,研究生在讀,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