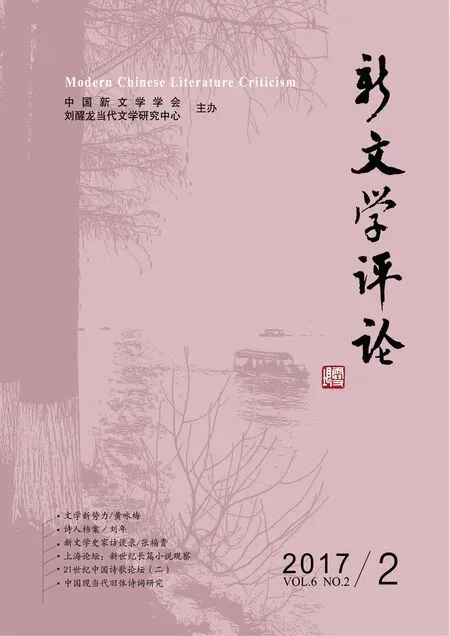汪劍釗詩(shī)歌的自然與生命主題解讀
◆ 徐 寧 吳投文
汪劍釗詩(shī)歌的自然與生命主題解讀
◆ 徐 寧 吳投文
用詩(shī)人泉子的說(shuō)法,汪劍釗是一只“食腐的金烏”。泉子說(shuō):“這是一個(gè)詩(shī)歌的烏鴉時(shí)代,但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新詩(shī)的‘詩(shī)經(jīng)’時(shí)代。”汪劍釗的詩(shī)歌多運(yùn)用隱喻手法,畫面感強(qiáng),聚合特征明顯,與莊子的齊物論思想似有某種精神上的關(guān)聯(lián)。在他的詩(shī)歌中,有一類以自然與生命為主題的詩(shī)歌值得注意,此類詩(shī)歌具有批判世俗物欲、重構(gòu)心靈世界與向往詩(shī)性人格的主題指向。汪劍釗的詩(shī)中有一種隱隱的焦慮,這種焦慮在很大程度上來(lái)自現(xiàn)代性的壓抑,同時(shí),他表達(dá)的又是一種詩(shī)性理想和愿景,渴求人類擺脫現(xiàn)實(shí)物質(zhì)的異化束縛,將自然化為生命的有機(jī)組成部分,進(jìn)而達(dá)到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使人類的世俗情感得到凈化。
在汪劍釗的詩(shī)中,《鹽水溝》表達(dá)了對(duì)人類浮華生活的否定,關(guān)注自然而暗含對(duì)生命本質(zhì)的思考,感情基調(diào)深沉、節(jié)制;《我的睡眠》表達(dá)了超越生命,平靜面對(duì)死亡的體驗(yàn),充滿著生與死的哲理思考,感情基調(diào)悠遠(yuǎn)、寧?kù)o。汪劍釗的詩(shī)歌往往專注于“生命與自然”主題,引發(fā)讀者對(duì)生命意義的思考。在他的詩(shī)中,對(duì)美的凝望正是出于對(duì)生命與自然的尊重,美是實(shí)現(xiàn)詩(shī)意生活的重要途徑,而美的實(shí)現(xiàn)則蘊(yùn)含于自然與生命的關(guān)系之中。回歸自然,不為物質(zhì)所累,在生命的夢(mèng)幻世界里,依靠美來(lái)超越生死,追求生命的永恒意義,這在汪劍釗的詩(shī)中可以找到比比皆是的例證。
一、 自然中的獨(dú)行者
汪劍釗有不少以自然為題材的詩(shī)歌,如《草》寫草叢中的玫瑰在日月之下發(fā)出耀眼的光芒,享受人們的贊嘆,而草卻因其樸素、平凡而被忽略,頗有童話寓言的風(fēng)味;如《樹葉如何劃破風(fēng)》,詩(shī)人在細(xì)致觀察的基礎(chǔ)上,充分發(fā)揮想象力,描述了在春節(jié)前夕一場(chǎng)晚來(lái)的風(fēng)雪中樹葉落下的情景,隱含了一種孤寂的生命體驗(yàn)。此類詩(shī)歌圍繞自然意象展開想象,對(duì)自然物象的情態(tài)描寫細(xì)致精微,畫面感極強(qiáng),詩(shī)中的中心意象往往折射出人類的當(dāng)代處境。汪劍釗有一首短詩(shī)《鹽水溝》,正是此類題材的佳作,也頗能代表他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全詩(shī)如下:
毀滅,另一種形式的拯救,
清風(fēng)拂過(guò)廢墟,
給虛假的歷史補(bǔ)上說(shuō)出真相的注釋:
一群人喧鬧地穿越海的風(fēng)暴,
折斷體內(nèi)的白帆;
一個(gè)人獨(dú)自回到自身,
在低處尋找高山的根須。
鹽水溝白光閃爍,
亮得令人心痛,
風(fēng)、云、霧的混合
構(gòu)成咸澀的地貌。
沙漠烘烤過(guò)的心臟
碎裂,墜進(jìn)無(wú)淚可流的溝壑,
血液給予最后的滋潤(rùn)……
詩(shī)中的鹽水溝是一條死水溝,骯臟、了無(wú)生機(jī)。只有在土地荒蕪的地方,才會(huì)出現(xiàn)鹽水溝,詩(shī)中點(diǎn)明了沙漠這一背景。“清風(fēng)”意味著對(duì)陰霾的吹拂,將陰郁、躁動(dòng)化為平靜。在沙漠中,清風(fēng)吹過(guò)曾經(jīng)繁榮而現(xiàn)在荒涼的廢墟;廢墟?zhèn)鬟_(dá)出了詩(shī)人內(nèi)心的荒蕪與凄涼。廢墟由繁榮的毀滅形式,這兩個(gè)意象照應(yīng)了詩(shī)歌開頭的“毀滅”一詞。“虛假”與“真相”,作為對(duì)歷史的描述,形成了鮮明對(duì)比。毀滅之前的繁榮是虛假的,而毀滅之后的廢墟才顯露出繁華下隱藏的虛假。詩(shī)中“折斷體內(nèi)的白帆”,后面用了一個(gè)分號(hào),分號(hào)之前的詩(shī)句是對(duì)全詩(shī)思想感情的一個(gè)概括,奠定了全詩(shī)荒涼的情感基調(diào)。
“一群人”意味著一個(gè)團(tuán)體克服艱難險(xiǎn)阻,穿越茫茫沙漠,然而在喧鬧中,詩(shī)人卻更加孤獨(dú)。穿越沙漠的過(guò)程,也是與沙漠交流、對(duì)話的過(guò)程。在此過(guò)程中,詩(shī)人體會(huì)到自然與宇宙的真實(shí),城市文明仿佛是一艘揚(yáng)帆遠(yuǎn)行的船舶,在沙漠中詩(shī)人發(fā)覺自己所追求的物質(zhì)功利是虛假與虛無(wú),此刻那顆功利的心冷卻下來(lái),好似白帆折斷。在脫離眾人之后,詩(shī)人進(jìn)入自己的內(nèi)心深處。“根須”既有根本之意,同時(shí)也具有重生、新生的暗示。“高山”巍峨,暗示人生思想的新高度,或人生的更高追求。“低處尋找高山的根須”,象征著此時(shí)“我”回到被自己所拋棄的純真、單純的內(nèi)心形態(tài);經(jīng)歷沙漠景色洗禮的“我”,在歷史時(shí)空中,感覺當(dāng)初的本心才是自己真正應(yīng)追求的“高山”。
詩(shī)人運(yùn)用“清風(fēng)”、“廢墟”、“歷史”等意象,表達(dá)了自己的心境——來(lái)到雄渾又荒涼的沙漠戈壁,面對(duì)自然之景,對(duì)比城市文明的繁榮,明白在時(shí)間與自然面前,自己在城市文明中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人生的廢墟。沙漠廢墟對(duì)自己原來(lái)的人生觀產(chǎn)生了毀滅性的沖擊,而這種沖擊讓“我”獲得了拯救,從原來(lái)對(duì)人生的虛假陶醉中清醒過(guò)來(lái)。詩(shī)歌開頭一句“毀滅,另一種形式的拯救”,流露出詩(shī)人的感嘆,實(shí)際上是生命狀態(tài)的覺醒。
鹽水溝了無(wú)生機(jī),與廢墟一樣荒蕪,暗喻生命的沉淀。白色的鹽在太陽(yáng)光下閃爍著耀眼的光芒,白色代表純潔,但也與死亡、空白、空虛相關(guān)。“鹽水溝白光閃爍”,白光是自然之象,卻也包含著情緒性的生命體驗(yàn)。在歷史與自然的沉淀中,詩(shī)人盡去心中浮華,對(duì)生命的虛無(wú)感到悲痛。“風(fēng)”、“云”、“霧”刻畫出沙漠地貌,即“構(gòu)成咸澀的地貌”,這兩句既是寫實(shí),同時(shí)也可以引發(fā)讀者對(duì)人生的解讀。詩(shī)中所描寫的地貌亦可設(shè)想為詩(shī)人心中的觀念形態(tài)以及對(duì)生命、人生的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心臟”在詩(shī)中似乎是指詩(shī)人的思想,通過(guò)“心臟”一詞可以見出沙漠之行對(duì)于詩(shī)人思想的強(qiáng)烈震撼,因?yàn)樾呐K是人類生命的關(guān)鍵所在。另一方面,心臟作為意象具有實(shí)寫與意指兩種功效,既可指詩(shī)人的思想,也可指自然的規(guī)律,照應(yīng)詩(shī)人在沙漠中的行走經(jīng)歷。心臟的碎裂是指詩(shī)人價(jià)值觀念的斷裂,“無(wú)淚可流的溝壑”,這里可做兩種解讀:一種“無(wú)淚”指沙漠少雨,而“溝壑”則是沙漠的淚槽;另一種,“無(wú)淚”實(shí)指詩(shī)人的眼淚,“溝壑”指詩(shī)人的淚槽。“血液”意味著生命,同時(shí)也意味著血腥、暴力的殺戮,“血液給予最后的滋潤(rùn)”,暗示詩(shī)人在失望與悲痛后,決定用生命的血液去滋潤(rùn)荒蕪的心靈世界,讓它重新煥發(fā)生機(jī)。此詩(shī)開頭的第一句已經(jīng)暗示了詩(shī)歌由毀滅到拯救的主題,詩(shī)中出現(xiàn)了大量對(duì)比性的意象,如“虛假”與“真相”,“一群人”與“一個(gè)人”,“低處”與“高山”等,在充滿悖論的語(yǔ)境下呈現(xiàn)詩(shī)人的情感與思想陣痛。
梳理《鹽水溝》中的意象,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意象特色鮮明,一種是抽象的具有人文色彩的意象,如“毀滅”、“拯救”、“歷史”、“真相”等;另一種是具體的自然意象,如“白帆”、“風(fēng)暴”、“鹽水溝”、“風(fēng)云霧”等。詩(shī)歌因?yàn)樽匀粚?shí)存的意象而有“地氣”,給人以現(xiàn)實(shí)之感;人文意象則使詩(shī)歌境界宏闊,脫離了風(fēng)花雪月的俗套,超越時(shí)空,承載著詩(shī)人對(duì)于生命、自然、時(shí)空的深刻思考。
在詩(shī)中,詩(shī)人的旅行是象征性的。詩(shī)中的表層結(jié)構(gòu)是敘事性的,詩(shī)人與同伴一起穿越沙漠;詩(shī)中的深層結(jié)構(gòu)則是隱喻性的,詩(shī)人在穿越沙漠的過(guò)程中,與沙漠進(jìn)行了一次思想與情感上的碰撞與交流,最終以詩(shī)人對(duì)自己思想的否定為結(jié)局,但引發(fā)了更深的人生思索。《鹽水溝》是一首短詩(shī),卻有相當(dāng)復(fù)雜的意蘊(yùn),大致包含著以下幾個(gè)層面:
其一,對(duì)世俗的叛逆。在《鹽水溝》中,隱含著詩(shī)人對(duì)自然萬(wàn)物承受苦難災(zāi)難這種博大胸懷與寧?kù)o心態(tài)的贊賞,詩(shī)人穿越沙漠的過(guò)程就是解讀自然的思想過(guò)程,同時(shí)對(duì)自己的人生進(jìn)行反思。詩(shī)人看到的鹽水溝是一片廢墟,卻也是純樸、純真的自然,寧?kù)o、坦蕩,按照自己的意志刻畫地形地貌,率性、自由,無(wú)絲毫的虛偽與浮華,與自己在城市中扮演的現(xiàn)代性人格判然有別。更重要的是,詩(shī)人認(rèn)識(shí)到一切都會(huì)像沙漠里的廢墟那樣,終歸將化為虛無(wú)。詩(shī)中隱含的主題頗有中國(guó)古代田園詩(shī)的意味,但有更深的發(fā)自現(xiàn)實(shí)的憂慮,實(shí)質(zhì)上是對(duì)世俗的叛逆,是另一種形式的歸隱山林。“以‘物’為鏡,當(dāng)代詩(shī)人將生活的‘在場(chǎng)’證據(jù)沉淀為具有文學(xué)性的異質(zhì)經(jīng)驗(yàn),其主體意識(shí)也在一個(gè)個(gè)日常生活的橫斷面中綿延不絕。其自我意識(shí)的傾注焦點(diǎn)完全轉(zhuǎn)向物化對(duì)象或現(xiàn)實(shí),以求觸碰到生存的感性氣息。同時(shí),他們盡量謀求精神與文化價(jià)值的雙重提升,參與并見證著當(dāng)代詩(shī)歌的世俗文化轉(zhuǎn)向。”詩(shī)人厭棄虛偽、壓抑的生活狀態(tài),對(duì)喧鬧與浮華持否定態(tài)度,則暗示著孤獨(dú)情愫的流露,詩(shī)人就像一個(gè)眾人沉睡我獨(dú)醒的孤獨(dú)者一樣。
其二,對(duì)心靈的重構(gòu)。汪劍釗將詩(shī)歌作為自己的夢(mèng)想,他的專業(yè)性寫作有極其深厚的功力,善于在有限的詩(shī)行中布置孤獨(dú)的生命情緒,由此引發(fā)對(duì)人生峻急情境的深刻思考。在《鹽水溝》中,詩(shī)人對(duì)景物的描寫看起來(lái)是寫實(shí)性的,實(shí)際上卻包含著隱喻的深度意向。如果詩(shī)中的意象側(cè)重寫實(shí),全詩(shī)就會(huì)顯得板滯而缺少靈動(dòng),詩(shī)歌的主旨也會(huì)隨之改變。對(duì)自然的毀滅是人類的惡行,毫無(wú)疑問,廢墟是人類自身的枯竭,也是詩(shī)人的思想和靈光的枯竭。這是詩(shī)人不可忍受的。詩(shī)人說(shuō):“給虛假的歷史補(bǔ)上說(shuō)出真相的注釋:/一群人喧鬧地穿越海的風(fēng)暴,/折斷體內(nèi)的白帆。”在此,“虛假”與“真相”的對(duì)立恰恰也是互證,虛假在真相面前現(xiàn)出原形,而真相則是心靈的棲息之處。“一個(gè)人獨(dú)自回到自身,/在低處尋找高山的根須”,這就是尋找心靈的真實(shí)和純度,是一種精神上的皈依。此時(shí),“折斷的白帆”、“回到自身”、“尋找高山的根須”,都是具有反思性內(nèi)涵的精神依托。人類在工業(yè)革命的幫助下,物質(zhì)文明取得高度繁榮,正如廢墟之上原來(lái)的綠洲文明一樣繁榮,但是由于對(duì)自然過(guò)度開發(fā),最后走向毀滅。那些所謂的繁榮也不過(guò)是“虛假的歷史”。鹽水溝亮得讓人心痛,因?yàn)樗纯萁撸G洲消失,溝中只剩下鹽粒,恰如一片心靈的荒漠。詩(shī)人痛心于人類對(duì)自然的破壞,更痛心于人類對(duì)自我心靈的戕害。“沙漠燒烤過(guò)的心臟”,這是多么酷烈的情景,詩(shī)人痛心于綠洲的消失,人類只能用自己所積累的血汗財(cái)富,用更大的代價(jià)來(lái)恢復(fù)綠洲。心靈的重構(gòu)更其困難,詩(shī)的主旨指向更深的一層,更促人深省。
其三,對(duì)詩(shī)性人格的護(hù)衛(wèi)。這首詩(shī)感情深沉、內(nèi)斂,實(shí)則暗含著思想的風(fēng)暴,里面有一種劇烈的情感的激蕩,而詩(shī)人將其節(jié)制在理性的可控范圍之內(nèi)。《鹽水溝》中所包含的隱喻,既指向個(gè)體的生存處境,“一個(gè)人獨(dú)自回到自身”,也包含著人與人之間互通聲氣的共同處境,“一群人喧鬧地穿越海的風(fēng)暴”,兩者是糾結(jié)并統(tǒng)一在一起的。詩(shī)中的自然有時(shí)是自然景觀,有時(shí)也指人的現(xiàn)實(shí),并無(wú)決然的界線,相互交融著某種共通的底色。“馬丁·海德格爾說(shuō):‘藝術(shù)的本性是詩(shī)’,而‘詩(shī)就是以語(yǔ)詞的方式確立存在’。一個(gè)真正的詩(shī)人不僅是一位詩(shī)歌的創(chuàng)作者,更是一位存在的思者。”人與自然,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矛盾以及由此所產(chǎn)生的孤獨(dú)與痛苦,是汪劍釗詩(shī)歌不懈表達(dá)與探索的主題,就是“一位存在的思者”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思考。在《鹽水溝》中,無(wú)論是詩(shī)人表達(dá)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及由此產(chǎn)生的對(duì)自然的崇敬之情,還是詩(shī)人為人類代言,表達(dá)對(duì)自然的懺悔,實(shí)際上都是對(duì)某種詩(shī)性人格的護(hù)衛(wèi)。詩(shī)的最后一句,“血液給予最后的滋潤(rùn)”,正是以血來(lái)滋潤(rùn)這種詩(shī)性人格。詩(shī)中有一種孤潔的情緒,與自然之景融為一體,又彌散在字里行間,讓人深思。表面的平靜之下,隱藏著深沉的感情。
二、 生命的思考者
自然景觀、現(xiàn)實(shí)情境固然是汪劍釗詩(shī)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對(duì)生命、靈魂與死亡的思考也是其詩(shī)歌的重要主題,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鹽水溝》、《草》、《頹廢的月亮》等詩(shī)帶著濃郁的自然氣息,而《睡眠》、《建設(shè)工地隨想曲》、《門》等詩(shī)歌則是關(guān)于生命活力、喧嘩與死亡的思考。“一切景語(yǔ)皆情語(yǔ)”,以自然為題材的詩(shī)歌都隱含著詩(shī)人對(duì)生命的思考;“一切情語(yǔ)皆景語(yǔ)”,關(guān)于生與死的思考,對(duì)人生的感喟,往往都寄托在自然景物、客觀事物之中,自然景物、客觀事物作為思想與情感的載體,不再只是一種自在的狀態(tài),而是包含著生命的情境和人類情感的內(nèi)核。汪劍釗的短詩(shī)《睡眠》值得品味,就在于其中的意義指向值得探究。全詩(shī)如下:
我的睡眠是一只美麗的瓶子,
比床小,比世界大。
悄悄刨開黑暗的沃土,
培植夢(mèng)幻的花。
翻身,按動(dòng)時(shí)間的遙控板,
調(diào)整音量,
讓喋喋不休的小鳥
學(xué)會(huì)
花朵的沉默。
那是輕到
不能再輕的聲音,
卻能穿透一切的喧嘩,
包容
整個(gè)死亡的平靜。
“睡眠”意味著夢(mèng),夢(mèng)是一個(gè)與現(xiàn)實(shí)迥然不同,有著荒誕色彩的虛擬世界。夢(mèng)只屬于個(gè)人,夢(mèng)的世界里所發(fā)生的一切都只與個(gè)人有關(guān),也只有個(gè)體自己才能窺探這個(gè)世界。在詩(shī)中,把夢(mèng)比喻為“一只美麗的瓶子”,是一處妙筆,可以引申到生命的幽暗體驗(yàn)之中。“瓶子”體積小,但是體積小并不意味著內(nèi)容貧瘠,正如“我”的夢(mèng)境一樣,這個(gè)世界就裝在“我”的大腦上,因此,它雖比床小,但它的豐富程度卻可能比現(xiàn)實(shí)世界更大。夜晚是“悄悄地刨開黑暗的沃土”的,而白天則是夢(mèng)的敵對(duì)形式,在眾人的喧鬧沉寂之后,只剩下詩(shī)人自己在悄然扇動(dòng)夢(mèng)幻的翅膀,此時(shí),詩(shī)人必然是孤獨(dú)的;黑暗意味著死亡與沉寂,而詩(shī)人卻把它當(dāng)作“沃土”,這也是一個(gè)恰當(dāng)?shù)谋扔鳎屓讼肫鹬熳郧濉逗商猎律分械摹盁狒[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這里有孤獨(dú),也有一種異乎白日的沉靜。“我”的夢(mèng)在夜晚來(lái)臨,在靜謐與黑暗之中,恰如一幅孤寂的畫卷展開。“培植夢(mèng)幻的花”,這是在詩(shī)人的想象中展開的,黑夜是培植夢(mèng)幻的土壤,也是詩(shī)人的心境的流露。在夜里,一切似乎都變得不確定,夢(mèng)幻像幼苗那樣,需要一個(gè)培植的過(guò)程。盡管如此,詩(shī)人還是愿意在黑暗中耐心看著它長(zhǎng)大,直到它開出花朵。這是詩(shī)人對(duì)睡眠狀態(tài)的描繪,給人安穩(wěn)的感覺。
讀者可以進(jìn)一步展開想象,詩(shī)人在似睡非睡之際,意識(shí)朦朧,突然他翻身醒來(lái),意識(shí)剎那間清醒,但隨即又模糊起來(lái),重新陷入夢(mèng)幻之中。在這模糊之中,詩(shī)人擁有掌控夢(mèng)幻世界的能力,按動(dòng)“時(shí)間的遙控板”,在此詩(shī)人讓畫面定格,以便擁有充足的時(shí)間,布置自己的夢(mèng)幻世界。在這里,詩(shī)人的時(shí)間意識(shí)再次突顯出來(lái),生命處于恍惚之中,但又清醒于時(shí)間的掌控。時(shí)間與生命密不可分,生命在時(shí)間中被賦予某種存在的限度。這就是此詩(shī)流露出來(lái)的生命意識(shí)。
讀者再往深處想象,似乎外界有某種雜音傳入了詩(shī)人的耳中。在朦朧中,詩(shī)人仿佛聽到了小鳥的啁啾,“小鳥”這一意象來(lái)得非常及時(shí),它的吟唱本身帶著一種美好。這只快樂的小鳥并不是詩(shī)人,因?yàn)樗淖杂墒窃?shī)人所不具有的,卻是詩(shī)人強(qiáng)烈向往的。另一方面,這只小鳥又是詩(shī)人的化身,因?yàn)檫@只小鳥的喋喋不休,正如詩(shī)人用詩(shī)歌來(lái)發(fā)言一樣,都是用來(lái)逃避孤獨(dú)的形式。盡管在世俗生活中,詩(shī)人有時(shí)不得不噤聲,但是詩(shī)人仍然相信自己即使沉默,也會(huì)像花朵一樣無(wú)言而美麗。
詩(shī)人希望進(jìn)入夢(mèng)境,他將注意力轉(zhuǎn)移到花朵上來(lái),此處可以想象小鳥休憩在花園中,像花朵一樣沉默。這是對(duì)睡眠狀態(tài)恰到好處的描繪,睡眠也有迷人的一面,“花朵的沉默”正是睡眠的理想狀態(tài),盡管并非易得。終于沉靜下來(lái)了,沉靜下來(lái)的不僅是喧鬧,還有詩(shī)人的心靈。現(xiàn)實(shí)中一切的瑣碎都已被夢(mèng)屏蔽,詩(shī)人厭惡的喧嘩不復(fù)存在,獲得了內(nèi)心的平靜。在詩(shī)人的內(nèi)心深處,有一種強(qiáng)烈的渴念,渴望穿透一切日常的阻隔,歸化于一種永久的安寧。這種安寧可能只與死亡隔著一層薄紗,詩(shī)人在想象中與之達(dá)成了最親密的接觸。這里面可能還包含著某種沉重的生命體驗(yàn),卻被詩(shī)人化解在超脫之中。
《睡眠》是一首非常細(xì)膩的詩(shī)歌,看似單純,意蘊(yùn)卻非常深刻,有沉重的一面,關(guān)涉到對(duì)生命與死亡的辯證理解。人的睡眠如死亡一樣,中國(guó)文化對(duì)此并不避諱,“長(zhǎng)眠于地下”這樣的婉轉(zhuǎn)之詞,是一種解脫的措辭,實(shí)際上也是一種詩(shī)意的描繪。與《鹽水溝》相比,此詩(shī)在平靜與節(jié)制之中,多了幾分輕快、悠遠(yuǎn),情感像溪流一樣緩緩流出,其中也有一種生命在寧?kù)o中變得豐富的體驗(yàn)。“整個(gè)死亡的平靜”是此詩(shī)的點(diǎn)睛之筆,里面包含著深刻的哲學(xué)思考,生命終究是短暫的,而死亡卻是永久的。生命無(wú)法獲得終極的平靜,終極的平靜只屬于死亡,生命與死亡相互完成,相互豐富,也相互對(duì)照,形成睡眠的外殼和哲理實(shí)質(zhì)。《睡眠》中可能縈繞著來(lái)自日常生活的憂煩和看破紅塵的曠達(dá),但更深的卻是對(duì)生命存在的沉思。在詩(shī)人平靜的語(yǔ)調(diào)中,同時(shí)也包含著非常復(fù)雜的情緒,人生作為一個(gè)過(guò)程,總是糾結(jié)著難以言傳的痛苦和憂煩,有時(shí)不得不通過(guò)做夢(mèng)來(lái)紓解,這樣才能得到些許平靜和安穩(wěn),才能抵達(dá)某種自由的幻境。但人生的自由哪能如此容易得到?況且,在自由和夢(mèng)境之間,只有虛擬的通道,而被現(xiàn)實(shí)所阻隔。《睡眠》寫得謹(jǐn)嚴(yán)精湛,經(jīng)得起反復(fù)推敲、回味,雖然詩(shī)的切口較小,但帶給讀者深長(zhǎng)的回味。
三、 情感的守望者
人要獲得自由,要詩(shī)意地生活,就必須敏感于生活的詩(shī)意,而生活的詩(shī)意則在人類審美情感的實(shí)現(xiàn)之中。人類審美情感的實(shí)現(xiàn)在于自然與生命的關(guān)系之中:摒棄浮華,回歸自然,擺脫對(duì)物質(zhì)生活的過(guò)分關(guān)注,追求內(nèi)心生活的平靜,經(jīng)營(yíng)一片屬于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情感的釋放意味著內(nèi)心的自由,隨心所欲,不為世俗所累,像在夢(mèng)中那樣無(wú)拘無(wú)束。藝術(shù)恰恰是人生的“白日夢(mèng)”,人生總是充滿缺陷,但可以在藝術(shù)中得到彌補(bǔ),在藝術(shù)中化解生存的危機(jī)。藝術(shù)是實(shí)現(xiàn)自由的途徑,詩(shī)歌似乎更能體現(xiàn)出藝術(shù)的這一功能。在汪劍釗的詩(shī)歌中,他反思自我的存在境況,抒發(fā)回歸自然的熱忱,尋求生命的價(jià)值與意義。在他的詩(shī)中,生命是一個(gè)極其重要的關(guān)鍵詞,他思考著生與死的關(guān)系,尋求超越時(shí)空的生命意義。無(wú)論是在自然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中,還是在生命的夢(mèng)幻世界里,生命都應(yīng)該遵循審美的情感,至少也不能回避審美對(duì)于生命的價(jià)值,只有在情感上得到回應(yīng),人類才會(huì)感受到生命的愉悅,才能體驗(yàn)到生命存在的價(jià)值。相反,人類的情感如果被壓抑、被扭曲,就會(huì)備感痛苦,即使物質(zhì)再豐富,生命也會(huì)變得毫無(wú)意義。
汪劍釗在創(chuàng)作于2000年的《建設(shè)工地隨想曲》中寫道:“推土機(jī)挺著肚子走過(guò)的時(shí)候,死人不得不再死一次”;在2004年的《門》中寫道,“我們意識(shí)中的美,不斷打磨,學(xué)習(xí)死亡的入門術(shù)”,都與死亡有關(guān),而又連結(jié)著生命的永恒。汪劍釗的詩(shī)歌在生命與自然的主題中,一直努力探討兩者之間的隱秘聯(lián)系,包括生命與死亡、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短暫與永恒的關(guān)系。他的詩(shī)歌富有哲思色彩,正是來(lái)源于對(duì)生命存在的某種深刻洞察。實(shí)際上,在他的詩(shī)歌中,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gè)核心視角,由此可以透視其創(chuàng)作中的復(fù)雜內(nèi)涵。
汪劍釗注重感情的自由抒發(fā),他的詩(shī)歌夢(mèng)想基于用詩(shī)歌達(dá)到對(duì)永恒的某種思索,他的創(chuàng)作野心大概也在這里,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留下幾道深刻的烙印。汪劍釗長(zhǎng)期以來(lái)不懈專注于兩個(gè)問題:以《鹽水溝》為代表的詩(shī)歌對(duì)現(xiàn)實(shí)虛華生活、世俗功利的否定;以《睡眠》為代表的詩(shī)歌則追求超越生命的自然限度,平靜面對(duì)死亡,并把這種審美體驗(yàn)轉(zhuǎn)化為一種內(nèi)斂的人生姿態(tài)。他在《詩(shī)歌是什么》一文中這樣自述寫作的緣由:“至于為什么要寫,一個(gè)原因是出自我喜好幻想的天性,由于寫作的存在,我經(jīng)常可以獲得在現(xiàn)實(shí)人生以外的另一種人生,那種超越時(shí)間和空間局限的體驗(yàn)讓我十分著迷;另外一個(gè)原因則跟對(duì)死亡的恐懼有關(guān),由于意識(shí)到生命的短暫,意識(shí)到肉體的必然性消亡,我渴盼給這個(gè)世界留下一點(diǎn)我存在過(guò)的痕跡。我的詩(shī)歌夢(mèng)想是什么?通過(guò)詞和詞的綴連,讓漢語(yǔ)的詩(shī)性可能盡可能得到發(fā)揮,在詩(shī)歌缺失的地方播下一些詩(shī)歌的種籽。我在文字領(lǐng)域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創(chuàng)作、翻譯和評(píng)論,都是邁向這一夢(mèng)想的試步。”這并非虛言,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對(duì)生命永恒的探索,通過(guò)詩(shī)性思維超脫有限的生命束縛,始終是一個(gè)值得注意的主題。

注釋
:①泉子主編:《詩(shī)建設(shè)》,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頁(yè)。
②中國(guó)文聯(lián)研究室編:《中青年文藝評(píng)論家文選》,當(dāng)代中國(guó)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yè)。
③張三夕主編:《華中學(xué)術(shù)》,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頁(yè)。
④劉翔:《來(lái)自南方:一只抒情的烏鴉——汪劍釗和他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文學(xué)界》2012年第2期。
湖南科技大學(xué)人文與傳播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