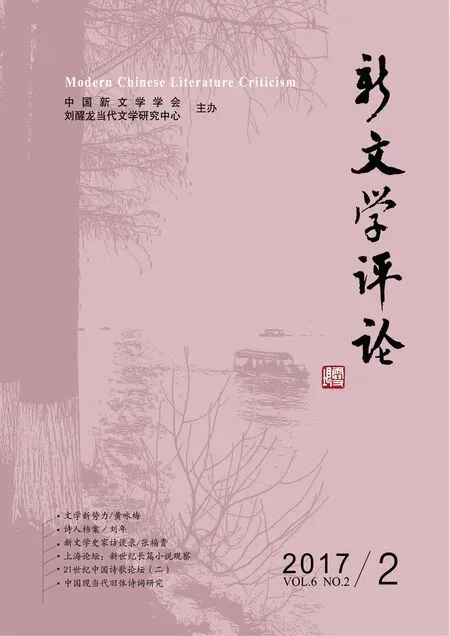曉蘇短篇小說的荒誕書寫
◆ 吳平安
曉蘇短篇小說的荒誕書寫
◆ 吳平安
在論及曉蘇的小說藝術時,荒誕書寫是評家的共識,然而即或以新時期文學論,荒誕書寫也并非自曉蘇始,在他前面已經有不少名家名作,業已沉淀在當代文學史的書頁中,僅以此并不足以將彼此區別開來,曉蘇處于這一鏈條的哪一個環節?他是否為荒誕書寫提供了某些新質呢?這才是衡估一個作家在一個或大或小的文學格局中所處地位的最關鍵的因素。
“荒誕”是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美學的核心概念,和幾乎處于西方美學源頭,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就已經進行了經典性論述的悲劇、喜劇比起來,這一概念及其依存的創作實踐的產生,不過是20世紀中葉的事情,這一美學概念的巨大意義,在我看來,是在悲劇、喜劇這一對基本的美學范疇之外,又開啟了藝術把握世界的第三種方式。
荒誕派小說有別于傳統小說最外在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情節的離奇。離奇不同于傳奇,也不同于神怪,后兩者的情節取戲劇化模式,其結構是完整的,情節是連貫的,是合乎邏輯的展開,其因果鏈條是環環相扣嚴絲合縫的,荒誕派小說的結構卻是破碎的,情節是“去戲劇化”的,即在看似平淡瑣碎的庸常形式中表達出反常的內容,其展開是不連貫的,非邏輯性的;與這一顯著特點密切相關的是小說的敘述語言,傳統小說的傳達語言是流暢的,明晰的,其明晰性來自能指與所指的一致性,荒誕派小說的語言往往是跳動的,晦澀的,能指與所指常常是分離的,這給閱讀趣味為傳統文學培養起來的讀者造成很大的不適感,就像習慣了欣賞古典美術“高貴的端莊和靜穆的偉大”(溫克爾曼語)的眼睛,突然接觸到畢加索、馬蒂斯受到的沖擊力那樣,反感和排斥幾乎是必然的反應。
然而,在天分很高的藝術家那里,情況發生了逆轉。正是這種不適感和沖擊力,給對新鮮藝術、另類藝術有超常敏感度的作家帶來了強烈的刺激,彼時正力圖沖破僵化的現實主義實則古典主義教條的先行者,提供了求新求變的武器。
1981年,高行健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出版,這本體量不大的小冊子在文學界引發的興奮卻是空前的。書名不難看出,西方的現代小說,最初是作為一種反叛傳統敘事方式的“技巧”引進中國的。技巧人人可學,然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1982年,蔣子龍的一篇微型小說《找帽子》開風氣之先,將荒誕作為反思“文革”的獨特視角,引入一統天下的寫實風中,一新讀者耳目。此番熱身之后,王蒙的《冬天的話題》、諶容的《減去十歲》等等紛至沓來,一時蔚為大觀。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和徐星的《無主題變奏》,成為而后被稱為“85新潮”時段中敘事文學里程碑式的作品。兩部小說中人物的躁動不安,落拓不羈,尤其是對生活荒誕感的體悟,概括了特定歷史階段青年群體的精神面貌,因而反響強烈,這表明荒誕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敘事技巧的存在,它已然和本土經驗漸漸融合了。而當人們認識到荒誕、異化這一對支撐西方現代派文學核心概念的確立過程,并非如形式主義批評所宣示的那樣,只不過是一種表達方式的變更,其深層動因是西方社會背景的巨大轉換時,十年浩劫便與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在心靈上的投影就有了較為深度的契合,激發了中國作家試圖穿透現實表層,進一步上升到對人類生存意義的整體性思考上來,殘雪以其變形的、詭異的小說世界,伴隨著激進的形式探索,將卡夫卡式的荒誕和詭譎推向了極致,也將漢語言的張力推到登峰造極的境地。
當中國的先鋒作家在新時期文壇上攻城略地時,初出茅廬的曉蘇剛開始在大學校園里回望他的精神故鄉,并且在寂寞中摸索“寫有意思的小說”這條文學之路。光怪陸離的現代派后現代派對一個來自鄂西北山區的后生,顯然存在過大的文化落差,還是生于斯長于斯的那片熱土,以及音容宛如目前的父老鄉親,因為空間距離的拉開,反倒更能觸動他寫作的欲望,這就是為什么,曉蘇的早期作品,全是以油菜坡為系列的,直到他逐漸融入了省城這座大都市,融入了這所著名的大學,身邊那個新儒林,那些每時每刻都在面前晃動的人和事,方才給與他別樣的刺激,讓他體會到荒誕的滋味,并逐漸進入他的文學視野。這使我想起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一向是視包括荒誕派在內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為異端的,然而在匈牙利事件中,卻被社會主義蘇聯老大哥的士兵押上囚車,如同禪師的機鋒棒喝,盧卡契在那一瞬間“開悟”了,因為他實實在在體會到了荒誕。這一非文學的文學掌故啟示我們,對荒誕的感知,不是僅憑教科書的詮釋就可以獲取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真正讓你覺悟的,還是伴隨著疼痛感的現實生活的教訓。在我看來,曉蘇對荒誕的體察有似于此。
曉蘇開始書寫學院生活的90年代,中國社會正經歷著急速的社會轉型,商品經濟大潮天風海雨般掃蕩著中國每一個角落,也席卷了昔日的象牙塔。社會價值取向與80年代形成巨大逆反,文學的啟蒙工程隨著自身的不斷邊緣化而徹底崩塌,隨之而來的是知識分子精神領路人的社會角色終歸消解。先鋒文學的語境已然不再,然而春風已度,必會花開草長,經受了現代主義、先鋒文學吹拂的現實主義文學,卻再也不是往日那副刻板的面貌了。
曉蘇的學院小說,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他用一系列短篇連綴而成的人物畫廊,讓我們清楚地直觀到這一特定歷史時期高校高級知識分子群體的變異。一言以蔽之,士農工商中“士”階層已不復往昔,再沒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自強精神,“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對真理的渴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定執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續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責任擔當,“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豪邁自信,更遑論那種為了捍衛道統不惜以身家性命相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了(“衛道士”一詞在古今漢語語境中的差異,最直觀地表征了時代精神的退化),這些千百年來受人崇敬的風骨和節操,在“五四”時期表現為啟蒙大眾的盜火精神,在革命戰爭年代表現為赴湯蹈火的獻身精神,在極左年代的政治高壓下表現為寧折不彎的獨立精神,這些皆可視為魯迅先生盛贊的民族脊梁的體現,已被謀取現實利益的蠅營狗茍取代。李澤厚先生告訴大眾:當今的讀書人已經放棄了知識分子的身份,從公共空間抽身而去,退回到書齋中做學問,他們只能成為各自狹小領域內的專門家,而不再可能對公共事務發言了,于是“思想家”淡出,而“學問家”增多,“知識分子”便退化為“知道分子”了。然而讀一讀曉蘇的學院小說,你會明白就連上述的精辟之論,也實在是高看他們了,因為倘能做一個名副其實的學問家,也需要具備馬克斯·韋伯所推崇的那種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發自內心地對學問獻身”的情懷,以及必不可少的勇氣和熱情,非此則耐不住青燈孤影的寂寞。且看曉蘇筆下的大學風景:“大學老師中喜歡打麻將的人并不少,比喜歡搞學問的人要多得多。”政治系老師大和就是一個麻將迷,“只要喊他打麻將,他可以從課堂上溜出來”;埋頭學術,大年初一還泡在省圖書館而被寫成新聞上了報紙的何日休,“專著和論文裝了滿滿一蛇皮袋”,也沒能評上教授,而“從來沒見過他讀過書,也沒見他正兒八經寫過什么文章,只見他一天到晚出沒于各種娛樂場所”的相公,卻“會玩,什么都玩得轉,把名和利都玩到了手”,年紀輕輕就當上了教授和博導,“還享受國務院的專家津貼呢”,此情此景,終于讓何日休“對做學問徹底心灰意冷了”,而后也進入了麻將圈(《打撈記》)……
曉蘇所發現的荒誕,并非是人作為一種形而上的類的存在面對的荒誕,而首先是學院現實生活中的悖謬。那個麻將迷大和,是“教思想品德課的”;教社會學的教授白夜,其專業素養體現在利用命題權在社會上獵艷的精明狡黠上(《電話亭》);研究“變態心理學”的教授韋敬一心理就有些變態(《粉絲》);倫理學教授林伯吹 “學問并不怎么樣,有點名不符實”,“課講得也不好,東扯西拉,浮光掠影,喜歡玩花拳繡腿”,更是一個將倫理道德棄如敝屣的人,他嗜錢如命,就講課酬金問題討價還價,一副商人嘴臉,沽名釣譽,在論文署名上做手腳,收買小報記者為自己虛假造勢,還涉足色情場所(《保衛老師》)……
古人治學,必先自修身始,若是個別人的行為不端,可歸咎于其真心誠意的欠缺,若蔚成風氣,就要檢查體制上的弊端了:大學學報這樣的學術機構中,一個“沒有正正規規讀過大學”的勤雜工許丹,居然當上了編輯部主任,而后竟升任副主編(《三年前的一個吻》),而學品與人品均無可挑剔的陳克己,卻帶著無法評上教授職稱的遺憾離開了人世,這些都給人帶來荒誕感,死于交通事故的結局表面上看來有些突兀,但偶然性中卻暗含了一種必然性:像陳克己這樣正直而“克己”的知識分子,在目前高校的生態環境中,已經沒有容身之地了(《我的丈夫陳克己》)。“眼下提倡標新立異,誰頭腦發熱了,誰心血來潮了,誰神經出毛病了,都可以創建一門學科,然后吆五喝六,出人頭地,爭名奪利”(《兩個研究生》)。那個一心想“弄個博導當當”的不學無術的人,竟然遇上了同樣不學無術的“想讀博士”的校領導的兒子,遂與領導達成“弄上了博導”、“第一個招他的兒子”的利益交換……
行文至此,便可以大致歸納出曉蘇學院小說中荒誕敘事的特點來,西方的荒誕敘事務虛,側重形而上,取全人類視角,其民族歷史文化背景是宗教信仰、彼岸情懷,它并不以某種具體的價值事物為否定對象,因而其否定是根本性質的,立足點是非理性的(虛無主義的);曉蘇的荒誕敘事務實,側重形而下,取中國視角,其民族歷史文化背景是世俗追求,此岸情懷,他以具體價值事物的異化為否定對象,其否定是建設性的,立足點是理性的(人文主義的)。
當言及“中國視角”和“民族歷史文化背景”時,很容易聯想起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來,莫非早在清代,吳敬梓就開始了荒誕敘事?換言之,曉蘇的系列學院小說,倘若連綴起來,與“雖云長篇,頗同短制”(魯迅語)的《儒林外史》究竟有無區別呢?
將《儒林外史》視作對“儒林”的諷刺批判已成定論,這固然不錯,至少并無大錯,但若細察,書中的“儒林”卻是一個成分復雜的“林子”,里面什么樣的鳥都有,有些是官僚子弟(即今之“官二代”),有些是江湖騙子,有些是市井無賴,這類人其實并非“真儒”;那些登第榮身之后即橫行鄉里的“儒”,其身份已然官僚或是劣紳了,諷刺矛頭所及,其實針對的是官場黑暗吏治腐敗;另有一類儒生(真儒),則或疏狂,或迂闊,或偏激,批判之余,同情之心卻也溢于言表;作者真正傾心折節的理想士人,是開篇描寫的淡泊功名利祿的市井隱士王冕那類高人雅士。
再看曉蘇筆下之“儒”,顯然更純粹,高學歷、高職稱,身份是高校教師,個個皆“真儒”是毫無疑問的,《儒林》之儒,在舊教育體制下,是個體化的存在,曉蘇之儒,則是現代教育體制的伴生物,是群體性的存在,有些荒誕之舉,甚至是高度組織化的活動(《唱歌比賽》)。這一區分的意義在于,曉蘇學院小說的荒誕敘事,是現代意義上的荒誕。
當曉蘇把目光轉移到油菜坡時,荒誕敘事又有了新的變化。曉蘇的小說敘事,秉持的是民間立場,在我看來,所謂民間,應該有一個特定的所指,鄉土(農村)即民間自不必說,城市的“民間”,恐怕應圈定在“市井”范圍內,一如鄧友梅、陳建功之寫皇城根,馮驥才之寫天津衛,陸文夫之寫姑蘇小巷,王安憶之寫上海弄堂,池莉、方方之寫吉慶街、中北路,如此等等。但大學原是象牙塔,是五湖四海精英薈萃之地,這就同民間敘事立場發生了某種程度的抵牾,例如在《我的導師路明之》中,將貪財、好色、淫邪、剽竊、猥瑣諸多劣跡集于路教授一身,活畫出當今“文化精英”的丑惡嘴臉來,其強烈的諷刺性在油菜坡小說中十分罕見。諷刺藝術固然離不開夸張、強烈、集中等等手法,但這些手段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是常常使作品多直露,少含蓄,擠壓了讀者含蘊想象的空間。這個兩難如何解決,也是這類小說留給我們的美學難題。還有一個最外在的呈現是小說語言,只需比較一下油菜坡小說,從敘述語言到人物語言,曉蘇操持的鄂西北方言與小說內容有高度的契合,因此他可以左右逢源得心應手,而將此挪用到大學題材小說中,顯然是萬萬不能的,就我個人的閱讀感受來說,覺得油菜坡小說比大學題材小說更有“意思”,更有滋有味,其深層次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以下這兩個短篇,便堪稱漢語荒誕小說的精品。
《推牛》(《天涯》2017年第1期),小說講的是一個老農為了救自家的老牛,被一輛裝有38人的客車撞死,旋即被主管宣傳的鎮領導打造成“英勇”、“悲壯”的“舍己救人的英雄”,并被追認為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甚至還“修了一個紀念塔”。而“笨嘴笨舌”、說話“結結巴巴”的兒子作為“英雄之子”,被指派專人調教成口吐蓮花的“講故事的高手”,“英模報告團”的主講,隨著宣傳力度的層層加大,上上下下一干參與其事的人物均沾光獲利,各有升遷,只有被推到風口浪尖的“英雄之子”,變成一塊村民人人想吃一口的唐僧肉,不僅家中錢物被以各種名義洗劫一空,連腎臟也被“捐出”以致病入膏肓。吃盡苦頭的“英雄之子”死前才給家人道出了“推牛”真相。然而荒誕之事還沒結束,當家人上上下下登門要求澄清真相還“英雄”本來面目,以免被人繼續敲詐時,卻受到官方嚴厲拒絕和嚴肅警告:“說法”要“始終跟鎮上和縣里保持一致”,“千萬不要亂來”……
這是一個深得荒誕精髓的故事,是喜劇因素、悲劇因素、黑色幽默合為一體的故事。它極具中國特色,因為它只能發生在中國這塊地域;它又超越了特定的地域,因為當我們試圖去尋找這一悲喜劇的源頭時,會發現僅僅歸之于參與運作的各級領導是遠遠不夠的,在這些當事人身后還有一種無形的、神秘的力量,像22條軍規那樣左右著他們的言行,小說也因此獲得了更大的涵蓋面。
《傳染記》(《天涯》2014年第2期),這是一篇精思傅會的上乘之作,說的是村婦傅彩霞得了“一種特殊的病毒性感冒”,百治不愈,后來從一個跑江湖的飼料販子那里,獲取了一個“找個男人睡一覺”的“偏方”,傅彩霞如法炮制,果真靈驗,把感冒傳給了發小鄔云的丈夫郝風,事敗后朋友反目,夫妻失和,郝風又把感冒傳染給了鄔云,而鄔云則瞄準了再次登門的飼料販子……
如果飼料販子患了感冒,誰又會是另一個下家呢?“傳染”是呈直現狀地延伸,還是呈圓環狀的循環?不見下文,小說到此戛然而止了。
簡單地勾勒故事情節是難盡其妙的,在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中,最能見出小說的功力:
鄔云是二十六中午回到油菜坡的。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發現沿路的油菜花都開了。花朵金燦燦的,像電焊時發出來的火光,讓人看了睜不開眼睛。鄔云感覺到油菜花是一夜之間開的。去娘家時,它們好像還沉睡著,回來時就開得這么刺眼了。鄔云認為花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它們總是在某個夜晚偷偷綻放。
這是一處神來之筆,寫出了鄔云回娘家探母后心情的愉悅;透過鄔云的主觀視角,又描畫了鄉村早春樸素的美景;而“花”在中國文化中,則有“性”的隱喻義,“在某個夜晚偷偷綻放”,則暗含或預敘了傅彩霞與郝風“傳染療法”的茍合,為下文的朋友反目、夫妻失和做了鋪墊,仿佛是在不經意間,曉蘇接續上了中國古典小說長于預敘的傳統。

武漢市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