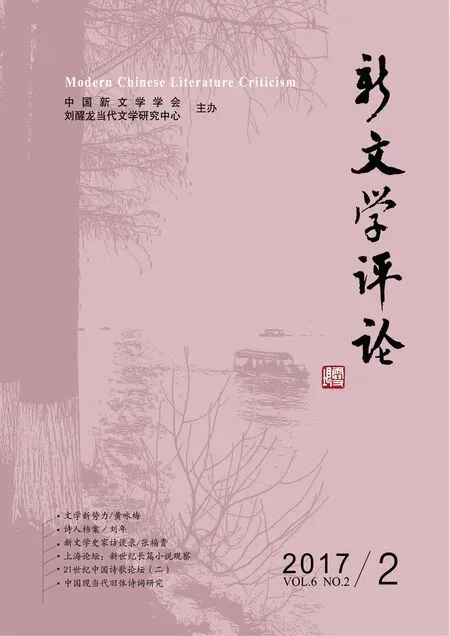夢語者的歸返、城市和他的詩
———邱華棟詩論
◆ 謝尚發
夢語者的歸返、城市和他的詩———邱華棟詩論
◆ 謝尚發
海德格爾在其著名的詩學文論《詩人何為?》中,借用詩人荷爾德林的一句詩來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進行追問:“……在貧困時代里詩人何為?”接著,他又對“貧困時代”進行了詳盡的解釋。“世界黑夜的貧困時代久矣。既已久長必會達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時代貧困。于是,這貧困時代甚至連自身的貧困也體會不到。這種無能為力便是時代最徹底的貧困,貧困者的貧困由此沉入暗冥之中。貧困完全沉入了暗冥,因為,貧困只是一味地渴求把自身掩蓋起來。……也許世界時代現在正成為完全的貧困時代。”這篇文章誕生的時間,離現在已經過去了整整七十年了,詩及其處境非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每況愈下,徑直是一種被視而不見的存在,被置若罔聞而不顧。一俟說到文學,所指幾乎都是小說的存在,或許還有散文,詩歌則幾乎被遺忘。那么,在這樣的“貧困時代”里,解讀詩無疑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冒險。但是我確信,詩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冒險,也因此,寫詩、讀詩、解詩更是這一冒險事業中最孤注一擲的冒險,這冒險本身中所充滿著的驚喜、神奇和偶遇,恰構成了最值得期待的詩情和沉思。閱讀邱華棟的詩歌,便是這樣一種冒險中的偶遇,充滿了值得期待的種種。不管是夢語者的自言自語,還是在夢語者的自言自語中彰顯的歸返的情愫訴求,抑或是對愛的禮贊與對城市的質問,都指向了這樣一種難得一見的精神偶遇。
一 夢語者和他的詩
在邱華棟的詩作中,時常聆聽到的乃是在午夜吟唱著的夢囈,那其中充滿了智性的思索與直面現實的勇氣,不管展眼望去所見的是黑夜還是燈火,都在一種詩情的感染下,被睡眠和夢境帶著,走向更遠的地方。至于那更遠的地方到底是故鄉還是他鄉,則構成了邱華棟詩歌的另一層內涵。邱華棟的作品仿佛并不是詩語,而徑直就是一個在黑夜里徘徊著的靈魂,唱出的夢中話語。因此,稱邱華棟的詩是“夢語者和他的歌”,一點都不為過。詩人仿佛在不停地做夢,夢見各種各樣的存在物與景觀,那其中充滿了記憶、執念和沉思,充滿了惦戀、情愫與寄托。這夢既可以是一個場景,比如:
我果然夢見你了
夢見了你家門外的一棵樹
和你全家的親戚
他們都在歡迎你
(《我果然夢見你了》)
也可以在夢中重構另一層的夢,從而在“夢的夢中”,看見時間的流逝、記憶的鮮活與生命的永恒、愛情的如斯不變。
我經常夢見你的夢
那時候你還小
是一個小姑娘 在一棵樹下睡眠
那么安甜 沒有人來打擾
在你生長過的地方
我看到了你已見過的風景
(《夏天本身所開的花》)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詩被作為和夢關聯的存在,有詩才有睡眠,才有夢境,竟至于難以分辨到底沉睡者所進入的是自己的夢境,還是詩所營造的夢境。
我是一個合格的朗讀者
就是為了幫助你解脫緊張
進入安閑的夢
我也愿意扮演這樣的朗誦者
和你一起在時光中飄浮
(《朗誦催眠》)
如此,詩仿佛并非是詩人寫下的話語,勾連著個人的情緒、感覺和認知,而是像一位姑娘手中,正在編織著的圍巾。那么,詩人并非是詩人,而是一個手藝人;詩也并非是詩,而是一個編織物。日常與詩意同構,夢境與現實相連,邱華棟的詩歌中這種面向現實的寫作,呈現出其作為“非詩之詩”的面貌的同時,也彰顯了一種對詩意的獨特理解。
編織藍色音符的,是你
你這個織夢者,帶著童年的瞳孔走來
(《圍巾》)
與此同時,作為私人生活中的夢逐漸被擴大,成為“整個時代的夢”(《博爾赫斯》),隨著白晝的到來而慢慢遠逝。在這樣的“夢的時代”中,“如果你是夢/那么我就是馬,順著你的頭發以吃草的方式圍困你”(《反修辭》),并進而“逃離傷口,迷入甜美的河流/我們命中注定一起在夢中飛翔”(《骷髏花》),因為這個“夢語者”從原初就是一個“從夢境中撈起”的詩人,所以他會說:
我剛剛被黑夜從夢境中撈起
感到列車異常平穩
就像一把刀子,在進入一個軀體
鋼鐵鏗鏘
(《1992年8月24日深夜2時,經過石家莊》)
如此一個“在睡夢中跌倒的人”(《北京,大城飄浮》),只能“我臉上帶著奇異的夢境/我躍動四蹄 在城市中狂奔”(《驚馬逃奔》),注定成為一匹“剛從美夢中驚醒的馬”(《城市中的馬群》),詩是夢中語,而夢則是安詳的寄托——“讓香草鋪滿你的夢境”(《甜蜜的星空》)。
天然地,夢語者自然和睡眠關聯,睡眠又自然地和黑夜關聯。于是,在邱華棟的詩作中,圍繞著“夢”打造出一個完整的“意象群”,包括睡眠、黑夜、黑色、白晝等。連夢語者自己都知道,“而你自然和黑夜共生,如同夢境中的樹枝/從陽光的背面伸進白晝”(《黑天鵝》),他的詩作就是“把黑暗鍛成布匹/就都是新娘和新郎/在天鵝的邊上梳妝”(《哎呀》)。因此,夢語者陶醉于黑夜,而拒絕白晝的到來,試圖“在空氣里把黑暗圍攏”,還宣稱:
十個死者站起來向你說話:
不要站起來去看天黑了
沒有白晝,你就是白晝
讓最后一枚種子在我的口中發芽
(《十個死者站起來向你說話》)
天黑了,幾乎成為夢語者的假象,因為天根本不曾存在過白晝,在他的世界里,只存在著“黑夜已經降落下來,大地荒涼的氣息上升”(《大海中的島嶼》),因此上,“黑夜比空氣純凈/我的語言烈焰熊熊”(《星光》)。夢語者的詩,只不過是黑夜中燃燒著的語言罷了,它總糾纏著黑色的氣質,縈繞著死亡的氣息。“這夜晚真黑,星星開始了它們的聚會/像死亡的聚會,而你為什么把我抓得那么緊”(《年復一年》)。在這一聲質問中,黑夜里的夢語者,以睡夢作最清醒的思考,用黑夜作為眼睛來思考關于人世的種種——終有一死者的忙碌奔波、生和死的歡愉與悲傷、戀人的絮語與故鄉的草、樹、風,以及茅屋、母親和大地。夢語者的黑夜,情到深處,往往只剩下了白晝,那代表著生的世界,雖然這生的世界也只不過是“向死而生”的悲劇罷了。
我留下的白晝比黃金更深沉
比泥土更黑
比太陽更幽暗
比人心更輕
更多的白晝被我的雙手從血管里擠出
(《更多的白晝》)
夢語者天然地是屬于黑夜的,那白晝的假象只不過是“從血管里擠出”的痛苦,寫滿了他的哀傷、悲戚與孤獨。或者,這白晝只不過是一束光——“黑夜的馬車拉著我/在海面上疾馳成一束光”(《我自己》)。夢語者和白晝終究無緣,在黑夜的夢境里,言說著自我的存在,“黑暗的顏色,黑色的鳥,適合于水底的飛行”,“黑暗的鳥,同樣是黑色的玫瑰”,“那樣黑色甜美的氣息讓我沉醉”(《黑天鵝》)。夢語者就在這“黑色甜美的氣息”里,寫下他的詩,他的歌。所以夢語者宣稱,他只不過是一個“午夜的孩子”:
午夜的孩子在大地的流浪中醒來
他聽見了美代表黑夜向他說話
午夜的孩子,在恐懼中領受著戰栗
單一的寧靜已使他發瘋
午夜的孩子,向半空拋擲銀幣
正面和反面都不是他的期待
那是孤獨,那是深入他肌體的針管
正在向他的身軀注入迷亂的淚水
而重建星空,還遠沒有開始
午夜的孩子醒著
或者他是在一個醒著的睡夢中
在兩個夢的疊壓下成為影子
在空蕩蕩的城市中游蕩 像紙一樣飄飛
(《午夜的孩子》)
作為“午夜的孩子”,夢語者的詩句中透露著詩人的糾結、痛苦和神經的不安,那焦躁的不是黑夜的恐怖,也不是白晝終將到來的痛楚,而是在“單一的寧靜”中所體驗到的痛入骨髓的孤獨。午夜的黑色中,純凈的單一,并未給夢語者帶來安慰,他痛苦的魂靈一如暗夜的流動,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由此,邱華棟的詩歌提供了一種時代的鏡像,躲避白晝的夢語者,只不過是無數人黑夜里的夢囈罷了。但這夢囈,難道不是夢魘?難道不是夢魘里,那痛苦的呼喊與嚎叫?充滿了靈魂的撕扯,以及詞語的破碎感?
二 歸返,從離去開始
夢語者的痛苦,也并非只是來自于黑夜的深處,從單一的黑色之寧靜中侵入骨髓,因為那孤獨的到來,和“遠離”密不可分。他孑然一身,佇立在黑夜中,在別人的沉睡里書寫自己的夢語,郁郁寡歡又自得其樂,纏綿悱惻也痛徹心扉。從夢語者的詩句中,讀出歸返的意思,恰恰也牽涉著別離與記憶。在邱華棟的詩歌中,夢語者喋喋不休地沉吟著的,就是這因別離而帶來的思念,因記憶而難以磨滅的牽掛,以及因歸返而愈發痛楚的靈魂。仿佛存在著一個“原鄉”,在夢語者的言說里,不停地作為歸返的動力,召喚著異鄉的游子,在暮鼓敲響之前,風塵仆仆地到達。
你是一種聲音
在暗影中呼喚我
又像一只鳥
用風拍打我的肩膀
你的目光中深藏著一個秘密
你透明,華美,敏銳,真摯
你的周圍,是美的河山
河山上盛產麥子、牛奶和大米
(《一種聲音》)
歸返仿佛正是對這樣“一種聲音”的應和,因為在記憶深處的原鄉,不斷地以清晰的面孔出現,那詩意的故居與想象。“你有一張光明的面孔/使出門的我,不斷地在月光下思家”(《獻詩》)。那是因為,“在大地上 我當然覺得你最美/你使我寒冷的雙手 始終可以摸到火柴/并且扎下根來/無論我跑了多遠 我知道/我么都要在天黑之前 雷雨之后/一起回家”。夢語者的深深執念中,“故家”的存在是縈繞不開的夢魘,而此刻身處的世界——城市及其不堪的生活,則是夢得以形成的基礎,也是歸返的動因。因著這樣的思念,才會有歸返:
黃昏中歸家的路上
透過車窗玻璃
我數著路邊向后飛快退卻的樹上的鳥巢
(《二十六個鳥巢》)
然而可悲的是,“在樹枝上,巢中經常沒有鳥/只有空虛,被懸置于春色之上”(《雪的暴力》)。別離也仿佛是夢語者的宿命,“我想起了養蜂人昨天告訴我的:/瞇縫知道自己要死了/總是要離開它供養的蜂王,離開它的家,它的花”(《一只瀕臨死亡的蜜蜂》)。在別離之后,心心念念的歸返執拗中,深藏著眷戀與牽掛,那里才是詩意棲居之地,無論這其中包含著多少想象的成分。
而美麗的風景鑲嵌在
人民勞動的畫框中
插秧人直起腰來,太遠了
我根本看不見他的臉,他的辛酸
(《江西的白鷺》)
別離實在是“太遠了”,才有歸返的切近之思。只有歸返,才能讓生命進入寧靜之中。“我回家了,這一刻總是那么的溫馨/總是,進入到片刻的寧靜”(《門外的燈》),這仿佛也是“遠與近”對比的另一重意味:喧囂與寧靜,漂泊與歸返。只有在切近中,原鄉的圖景才會清晰:“水稻田邊,蛙鳴陣陣/南方的景物啊,生機勃勃/讓我喜歡上了這美好的萬物”(《南方的植物》)。這就是原鄉的意味,那里有出發點,有一生中為之永難忘記的情思。然后,就有了遠離,就才會在遠離中,以夢的方式,看見原鄉的一切。夢語者不禁深思:
你和我像逃離湖水的魚,來到了空氣中
只有風掠過樹梢
人魚能跑到哪里,我們能離開水多久
沒有人告訴我們答案
(《羅馬湖》)
用了魚和水的譬喻,夢語者終于明確了他在“遠與近”、“別離與歸返”的邏輯中,所領悟到的真諦,也和盤托出了歸返的全部理由之所在。夢語者于此,才一遍遍地言說著:
還是轉身離去吧
回去,走回去
離開那些烏鴉,離開
那空茫茫的大地墳塋
(《冷靜色》)
夢語者的“空間辯證法”也恰好出現:離別與歸返的性質,差異十分遙遠,卻內涵又十分切近。對于夢語者而言,“空間辯證法”所言說的,正是:
出發就離開了家,而抵達則是另一次出發
沒有目的的旅途已經開始
家中的女人在啃食月餅
今天的月亮一定是最圓的
在這個夜晚我想念她
我們剛剛相聚,就要立即分離
(《2002年中秋,9月21日》)
然后,才有他的痛楚,才有他的思念,才有了永遠無法拋棄的“訣別”:“在田野里你被暮色運走/這訣別比淚水更重 更深!”(《訣別》)也才有了“遠行”和“飛走”:“我要去遠行”,“沿著夏天的跑道飛走”,“五月,最終我和兄弟們交互擁抱/隨即分手。在我們身后大片草莓熟透/一直走。/一只黑鷹,銜我影子向大荒漠悄然游走”(《黑蝴蝶》)。夢游者無法不去正視他的身份:“我乃遠行的游子,無戀人伴行”(《云境·心境》)。
在別離與歸返之間,夢語者執念著的原鄉,更存在于他的記憶之中,并且這記憶朝著時間和空間兩個方向前進:對于時間而言,原鄉的記憶意味著童年的須臾不可離之,以及離別之后渴望重新歸返的熱烈;對于空間而言,原鄉的記憶意味著故鄉的種種人、事、物,包括對于母親的思念,對于大地的沉思。靠著記憶構建起來的原鄉,總是夢語者最為珍貴的財富:
今天的螃蟹格外地好吃
雖然很貴,但是仍貴不過
我們的記憶,貴不過
你對自己家庭的守護,兒女雙全
父母雙全,你是一個喜興人
(《十一月一日得張小波送來大閘蟹》)
記憶之珍貴,勝過世間的一切,因為那里隱藏著原鄉最為深沉的執念和牽掛,仿佛是簡單的“兒女雙全”和“父母雙全”,但那其中所飽含著的,卻是對于“團圓”的渴望。夢語者寧愿就如此:“這是一個時間的截面,一個記憶的瞬間/在這個時間段里我們安靜地彼此凝視”(《羅馬湖》)。在凝視中,歸返發生,借著想象的翅膀,踏上歸途,朝著童年的方向,朝著故家的方向。
在井中我們下沉
下降到記憶和少年的深度
(《身在井中》)
年復一年 嘴唇上覆滅著春天
在懸鈴木下你蘇醒在童年的邊緣
蘇醒在你自己的身體里的哀憐
(《年復一年》)
這言說的,是少年和童年的種種;
母親老了
她的衰朽不止起始于血液
而是很多細胞的背叛
它們一點點地改變她的面貌
就像風蝕洼地
和風的關系
南方傳來妹妹懷孕的消息
另一個小生命
將在龍年誕生
(《母親》)
我想念我的母親
在早晨醒來的時候
沒有看見兒子
眼睛總是落下來
幾滴透明的憂傷
(《媽媽》)
我無法走出你的血液,父親
每一次遠行,我都知道
會有更多的聲音在你臉上老去
(《詞根:父》)
這說的則是故家,以及故家里的父親和母親,大地一樣的存在。然而對于夢語者而言,任何一次歸返都存在著無法規避的風險——
我從遙遠的地方歸來
見到你忽然就凄涼
(《舊房子》)
因此,回不去的故鄉和歲月,在夢語者的詩句中,就只得以“鏡像”的方式存在,宣稱了任何一次“歸返”都只不過是自我的一番想象罷了。這種歸返,似乎成了夢語者的宣言:
重回鏡中
我們是一對童男童女
像天使,在過去一年飛翔在上帝身邊
如今歲月之河滾滾而過
我們經歷的比預想的要多
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
我們擁有的一切嘆噓,一切幻想
而今復雜得像機械時代的儀器
自身都無法辨識
是什么叫我們心中充滿淤泥
和生活的每一片灰燼
生存就是無止境的下墜嗎
我多么向往重回鏡中
在那里我們黑發似夜
純凈如一張白紙
沒有一個字 曾經占據過我們的心
三 城市物語及其相狀
“重回鏡中”,代表著夢語者歸返的無可奈何的處境,也彰顯出了“現代人的悲哀”,以至于詩人徑直發問道:“是什么叫我們心中充滿淤泥”,“生存就是無止境的下墜嗎”。這種種發問與思索,都來自于夢語者對城市的觀察,來自于他對城市物語的描摹與城市生活相狀的體認。也因此,在邱華棟的詩歌中,一俟涉及城市的書寫,永遠牽涉著兩個方面:其一,對城市器物的描繪,以及附著于器物之上的種種情感;其二,對城市相狀的刻摹,以事件和經歷的方式呈現出都市生活的種種不堪。很顯然,相比較于波德萊爾在書寫城市的時候所使用的“象征的森林”,邱華棟更愿意直面都市的器物與事情,謂之為現實主義有失偏頗于刻板印象,謂之為“印象主義”則失之于走馬觀花的閱讀感覺,稱之為“城市的素描者”或者更為準確——一方面是寫實的精神記錄下城市的種種,另一方面則是用了情感的調色將之暈染、變形、扭曲,以映襯著夢語者的歸返和黑夜的沉思,因為城市幾乎是夢語者逃離的地方,又是必須棲身其間的場所。邱華棟在詩歌中,讓夢語者以“看見”的方式,來呈現城市的種種:
我看見了水泥廠的煙囪和煙,計劃生育的標語,廣告
看見了丑陋的紅磚簡易樓房
看見了高壓線和細線一樣發亮的水渠
而一排排樹影分割地平線
把白云的步伐和綠色大地分開
(《2002年中秋,9月21日》)
這還是靜止的城市存在物,它們充斥著城市的生活,擁塞著日常起居,幾乎構成了城市存在的全部。同樣地,在另一首詩中,邱華棟讓他筆下的夢語者,直接站在樓宇之上,觀看“上海的早晨”:
我從上海錦滄文華酒店12層的窗戶望出去
波特曼酒店、恒隆時代廣場和上海展覽館把時間扭曲在一起
這個早晨悶熱而華麗,我以外來者的眼光
對她漫不經心地一瞥,看見了上海的心臟地帶
在潮濕的8月里謹慎地涌動,并成為這個時代的腳注
為了她變得更高,更富麗堂皇,更輝煌,也更糜爛
(《上海的早晨》)
在觀看城市的時候,夢語者幾乎將他的夢言夢語糾結在一起,讓幾個主題同時出現,形成一個結點,輻射成巨大的圓環,充滿了話語的張力。這其中,外來者的身份讓夢語者連接起了他的歸返和他的離別,把故鄉作為參照物來觀看城市的存在物,領略城市生活的不堪;在夢語者的觀看中,“糜爛”則映襯著“原鄉生活”的一切美好,稻田、母親、老屋、田野等等,充滿著趣味的童年和少年;在白晝觀看的夢語者,顯然并沒有脫離黑夜的召喚,他始終“在黑夜中”,以黑夜之眼來領略白晝。如此而來,與其說城市是城市,不如說城市是白晝的象征,她越是不堪,就越證明了夢語者和白晝的距離,與黑夜的親近。所以在他的執念中,容忍不了城市的這一切:
還要吃掉路燈 和高速公路
吃掉牙膏和飛機場
吃掉加油站 和傘兵營地
吃掉沙發滅蠅器和古城墻
吃掉所有的鏡子
(《詩》)
可是對于夢語者而言,妄圖“吃掉”城市的這一切,無異于癡人說夢。城市用了一整套自我的方式,構建了自己的軀體和生活。
這就是大城,它用立交橋,高速公路,
用假面舞會、卡拉OK酒吧、發廊來交換內臟
(《北京,大城飄浮》)
城市腫瘤因為高速公路的輸血
日益變得茁壯,變得心動過速
(《高速公路》)
城市組建自我的軀體,并且用了各種方式防止蛻化、衰老和死亡,不管身處其中的普通人和夢語者如何對她作出反應,她總依然故我地強化著自己的存在,在強化中收編一切,順從者和逃離者,以及叛逆者。連夢語者都不得不躲在黑夜里,躲在自己的夢里,靠著想象而來的歸返去了解自己的“城市生活病”,卻并不見他逃離這樣一個不堪的所在。只能一個人,哀憐著自己,痛恨著城市,又寄生于城市。
從城市器物中看見糜爛、墮落,更可以看見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地圖里,描繪下自己的橫豎撇捺。夢語者仍舊是一個“外來者”,他仿佛只是靜悄悄地觀看城市,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物,他們的日常,他們的庸俗,以及他們的可憐可悲之處。
而大地上到處都是人
這使我擔心,哪里使它可以安身?
瀝青已經代替了泥土,我們代替了它們
(《京東偏北,空港城,一只松鼠》)
以動物的處境,反襯城市生活的不堪,夢語者總還是對城市抱著絕望的態度,認為“這絕對是末日的感覺”(《2009年7月24日,下午大雨,我驅車奔向石家莊》),也是他應該逃離的地方。然而許多人生活于其中,卻并不自覺:
有多少人,踩著一致的步伐
出入地鐵、公共汽車、飯店、商場和樓廈
買賣夢想,然后在物質中消耗自身
成為更為簡單的物質
(《北京,大城飄浮》)
這種簡直是失去了“詩味”的詩句,幾乎是一種發牢騷式的噴薄,如同一個人喋喋不休的抱怨。然而這不得不讓人同時也警醒:我們的詩歌觀念,是不是應該更新了呢?是不是應該拋卻那種朦朧的象征、巧妙的譬喻與指東打西的故作刁難,而是直指人心,一針見血,痛處撒把鹽,癢處偏不撓?畢竟,邱華棟在這種“非詩之詩”的語境中所要言說的,恰是要對著當下的生活,對著城市的種種不堪,刺下猛烈的一劍,因為他知道,對于如此現實,非用如此的“非詩之詩”不能描摹,不能盡意,不能狀其形態與心魂。然而,夢語者有夢語者的悲哀,他簡單處,可以直接一語道破,又在道破城市的弊病之后,看到城市的“偉力”:
我猛然向自己跪下
看見電車的辮子脫離軌道
我想死去 我聽見大地在微微顫抖
城市在嘲笑什么
在凝視中痙攣它龐大的身體
碾過花朵和少女
(《可以死去也不要死》)
城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不但吞噬著生活于其中的個人,還在震顫著大地。因此可以說,邱華棟對城市的觀察與深思,絕不是輕輕地滑過式的牢騷和抱怨,而是揪著一個問題不放,顛來倒去地進行質問。夢語者由個人而向著大地的追問,最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如果要給城市的器物描寫作為一個終結,為城市的事情做一個預熱,那么莫過于夢語者眼中的城市人及其生活狀態:
她害怕櫥柜、洗手間
害怕椅子、床頭柜、臺燈
她害怕窗簾、中央空調
和各種聲音
(《她和黑夜》)
和器物打交道,城市人開始變得焦躁不安、恐懼,以至于他們的生活中充斥著死亡的陰影。那些巨大的物體,不但帶來生活的便利,同時以無可爭辯的方式宣示著對生活的擠壓。夢語者經由城市器物的通道所看見的死亡比比皆是:
7月13日,一個不祥的日子
這一天我在東八里莊
看見了很多人圍觀
一輛停靠在僻靜地方的轎車里
一具腐爛發黑的尸體
臭味已經彌漫了三天
7月13日,晚報上還報道一個
無法證明其身份的人
從西單的中友百貨五樓上跳了下來
掉在了消防氣墊上,可仍舊死了
是個討要薪水的民工
7月13日,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
在通惠河四惠橋的河面上
有一具浮尸,脖子上有一道傷口
腰間綁著一塊磚
是誰干的?
我不知道殺人的是燥熱的心,還是空氣!
(《死人》)
這類似于流水賬的詩歌,確實了無詩意,并非是抒情的調子,也非吶喊的節奏,更不是控訴的激情,而這確是夢語者眼中的城市生活。橫死的新聞到處流傳,而尸體充斥其間的日子,也已經稀松平常。那末尾的一問,與其說是發問,不如說是指責,對整個城市的咒罵。不啻此,夢語者還在城市中,用了一只貓的死來隱喻人的死:
我看見有一只貓,在馬路中間
它感到無比驚懼,它無法逃走
因為車來車往
巨大的汽車在它頭頂碾過
它根本就不敢動
一直在無助地喵喵叫
第二天,我再次路過那里
發現那只貓已經變成了一堆凸起物
被壓扁在地面上
皮毛包裹著內臟,成為餅狀物體
又過了一天,一場大雨清洗了一切
我路過那里,看見貓的尸體沒有了
環衛工人打掃了它
連血跡都被沖刷干凈了
那里是一片空無
(《公路上的一只貓的死》)
在對城市進行刻摹的時候,邱華棟總是如此,把詩的詩意降到最低點,讓詩本身成為一種說話的方式,將簡單的敘述加以巧妙處理,用了分行、節奏變化等來調控這種說話的方式,從而達到書寫的目的。因此在夢語者的眼中,一只貓的死去,成了一個小事兒的書寫,卻無意之中關涉著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和他們的命運:背著死亡的黑影前行。對城市“事情”的書寫,集中地落在“死亡”之上,夢語者的歸返就顯然成了不可避免的生命之必然,那關于原鄉的種種想象,也愈發顯示出一種詩意的光明來。對于這位懷鄉的游子而言,此身在此,此心遠去,仍舊是逃不開的宿命,那“午夜的孩子”必須在黑暗中,觀看自己和蕓蕓眾生,用了夢囈的方式,寫下生活的種種:
午夜的孩子 城市夜晚的不明飛行物
樓廈間的一聲嚎叫
燈光背后的蝙蝠
一個人被汽車咬了一口,火光一閃
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城市尸布上的一道擦痕

2016.11.30-12.1北京·逸遠齋
2016.12.8改畢
注釋
:①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海德格爾選集》(上冊),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409頁。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