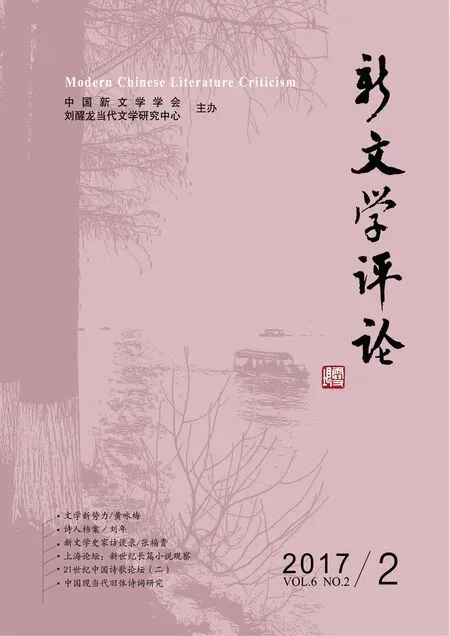包容的思想與獨到的創造
———張福貴先生訪談錄
◆ 張福貴 劉帥池 戚萌 包恩奇
包容的思想與獨到的創造———張福貴先生訪談錄
◆ 張福貴 劉帥池 戚萌 包恩奇
劉帥池
:張老師您好!作為國內文學界的知名學者,您的研究領域從文學到文化、從歷史到社會,包羅融匯、全面深刻。而作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您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時代的文化屬性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和清晰的預見性。那么縱觀歷史,歷代中國學者治學、為學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因為其各自所處時代的不同而精彩紛呈,秦漢的大氣恢宏凝結成微言大義、宋明的重儒取士衍生出理學文章。作為您的學生,大家對您的教學有一個共同的評價,就是知識的淵博和學術視界的開闊。我想請問您,那么,作為當代的學者、人文知識分子,處在我們當下這樣一個轉型劇烈日新月異的時代,您是如何考慮您的治學和教學的路徑的?張福貴
:可能對于我而言所謂的治學路子寬,并不是我自身的有意為之。因為在我們當下的社會氛圍與學術氛圍下,無論是我們社會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還是我們學科所要解決的問題,抑或是我們知識分子所應該和能夠承擔的責任,都決定了一個在高校從事教學和研究的知識分子必須要有開闊的視野,要用多元的角度和包容的心態來面對當下我們自身和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因為在當今這樣一個時代,任何問題都不是孤立的,它具有一種普遍性和關聯性,這種普遍性、相關性和多樣化,決定了我們任何一個領域的專業學者都不可能僅以本專業為對象進行研究,要有博大的胸襟、寬闊的視野、多元的思維和廣博的知識,才能真正適應我們這個時代和我們所從事的教育。所以我說一個學者治學領域的廣泛性是來自于我們社會問題存在的普遍性和相關性。而我們該如何面對和解決好專業領域中的問題呢?當然,它不是單純憑借單一專業基礎和專業領域標準去看待和完成的,而必須通過不同的視域才能更好地去解決和解釋這個問題,它需要在中國文化這樣一個宏觀的整體的理論框架下,關照本學科本領域的學術研究,培養跨學科跨專業的大視野,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學術進入更高的境界。所以這可能是所謂的治學路子很寬廣的本質原因和基本追求。至于今天我們怎樣去做一個專業的知識分子,我認為就是要追求學術領域的寬闊性及研究問題的多樣性和廣泛性,這三方面共同構成了當代知識分子在從事學術研究時應該具有的基本素養。因為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和過去不一樣,過去一個老師可能講《說文解字》,講幾個漢字可以講一學期;講《詩經》,講一首詩也可以講一學期,我們說這是有學問。但今天的學問和文化不是一個概念,所以今天的知識分子應當是現代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特征就是視野的開闊性、知識的廣泛性以及思考的多樣性,也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我們這個時代。所以所謂的治學道路和知識分子的使命也是休戚相關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為一個合格的現代知識分子,要面對社會現實,要專注于多種問題。而作為學術問題的多角度的解決方式,其本身又反映了知識分子的多種責任。過去,我也寫過很多文學專業之外的東西,這些寫作可能亦是不知不覺的在踐行著這樣一個使命和這樣一個標準吧。
劉帥池
:老師,正如您所說的,作為當代知識分子,在當下社會中尤其在大學這樣的平臺上,一方面我們是在育人,另一方面也是在修身,在修身中又不知不覺的承擔社會責任,回饋我們整個社會。那么可能按您剛才所說,就整體而言,一方面要明確我們的精神和傳承,明確整個學科發展的脈絡,明確我們社會發展的脈絡并與之貼合,明確我們文化發展的脈絡亦與之貼合;另一方面在此之后要完成我們自身的塑造和定位,用更多的學科知識來武裝自己,用自己的學科來進行表達,在這之后再用我們的成果和表述來完成整體的提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發展到今天,一方面我們是在梳理自己的歷史,一方面也是在創造自己的歷史。就如同您在《文學史寫作的四種制約》中提到:我們要淡化機制性的制約、觀念性的制約、知識性的制約和方法性的制約,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該如何回避我們的線性歷史觀或者說如何來梳理自己的歷史呢?張福貴
:先說你的第一個問題。其實你提到的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好,因為作為一個大學的教師,作為一個學院派學者,我們一方面的責任確實是育人,但其實也是育己,這個說法我是十分贊成的。也就是說,在我們傳給別人知識與啟迪學生思想的時候,其實也是我們自身思想的一個結果。因為大學教育和中學教育,或者說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最大的差別,就在于基礎教育以傳授知識為主,大學教育以啟迪思想為主,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要培養一個完整的、具有真知灼見和個性的人。那么你該如何培養這樣的人?首先我們應該贊同這樣一種現代的價值觀,而且具備這樣一種完整的知識結構、健康的思想和理智的情緒,有這樣一種抵達思想高度和把握前沿知識的能力。作為一個大學教師,必須要鼓勵思想個性、保護學術“叛逆”,因此大學老師要做的是把思想傳授給學生,把知識傳授給學生。那么你首先也應該是具有這樣一種思想、知識和能力的人。所以在大學教育的過程中,其實我們也是在不斷發現自己、改變自己、完善自己。我們在大學這樣的平臺上,治學方法和教育方法的核心也應該是讓學生如何在政治正確和思想健康的前提下,做到基礎知識標準化、核心知識個性化以及背景知識多元化。學生應該靠自己的思想而思想,而不是簡單地去重復別人的思想。我們應該在包容中保護個性,同時創造個性。當然,我們也不能刻意的為了個性而個性,如果那樣就是偏執了。我們要做的是在包容和寬容中去創造個性,這種個性的前提和結果并不是否定他人,而是內在發生的、以不傷害他人和社會為前提的個性。說到底,也就是一種包容的個性、健康的個性。那么之后再說第二個問題。對于我們學科而言,其實我們先要知道現當代文學和古典文學等學科的差異。和其他成熟的學科相比,現當代文學的學科性是先天不足的。我在一些文章和講座里,多次說到這個問題。因為任何一個學科的成熟,首先是通過學科的時間積累而最后形成的學術成果的積累,即可以說是積累的時間越長,成果就越豐富,這個學科也相對就越成熟。那我們現當代文學呢?必須承認在時間上是先天不足的,只有百年的發展歷史。這個時間和古代文學幾千年的歷史相比,可以說是歷史的須臾之間了;而與此同時,我們現當代文學又是一個最具當下性的學科之一,它受當下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心理的,也包括經濟的影響,它比古代文學等古老學科更多的受制于這些因素,這些因素也不斷地影響著我們這個學科的評價與判斷,甚至其中許多元素即構成了學科內容和屬性本身。所以我們這個學科與時代息息相關,往往具有不確定性,這可能是理工科,甚至是語言學、古典文學這些比較成熟的學科,有時候看輕我們的原因。但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任何學科都是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都是由不確定走向確定的,都是在不斷的研究與發展中完成了由一種個人理解到一個整體理解的過程。所以這個學科的不確定性也正是我們去多方探討這個學科,從不同角度去研究這個學科和完善這個學科的必然過程。經歷了這樣一種從不確定到確定,也就是最終確立了我們這個學科的基本定位。我想,這個學科的不確定,過去我們對于它給予的負面的評價過多,曾經使我們更多看到這個學科存在的不成熟性,但是要知道,學科和人一樣,一旦過于成熟了,可能就會走向僵化。正是由于它的不成熟,才擁有未來無限發展的空間。我們過去往往會把現當代文學這樣的不成熟看做是它的一個弊端,一個不足,但忽略了它未來發展的廣闊的空間。所以歸根結底,我們看到的學科的不確定性,其實是學科在探索、在逐漸發展過程中必有的一個過程,它最終是會走向成熟的。
當然了,這個不確定是如何來的?如何面對這些不確定性或者說如何面對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倒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堅守底線:歷史的底線、學理的底線、倫理的底線,當然也必須有政治的底線,政治正確就是政治安全。我們可以對這段文學史做出各種各樣的自我解釋,這是每個人的權利,因為歷史總是一個不斷被闡釋的過程,因此對于不同時段的人來說,歷史可能就具有不同的價值。而且,它也天然的決定了不同時段的人有無參與歷史的機會:作為后來人,當那段歷史已經過去,你就天生沒有參與的機會;但是評價歷史卻是每個人的權利,對歷史的個性化解釋就是對歷史的個人性評價,而個人的評價是五花八門的,也是包羅萬象的。文學史不能只有一種文學史文本和一種文學史解讀。它應該是多種多樣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和書寫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文學的歷史。但同時也要明確一個底線,即可以對文學史本身、對文學史事實做出不同的理解和闡釋,但不能無視歷史事實的存在。舉例而言,比如說面對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由于我們過去用單一的文學史觀進行評價,我們好像認為三十年代只有左翼文學,好像在左翼文學之外,其他文學都不存在了,這其實在不知不覺中,我們是曲解了歷史。前面說過,一切歷史都是個人史,所以必然帶有修史者個人的印記,但關鍵是我們是否脫離了歷史的真實本身。要知道三十年代初除了左翼文學,還有自由主義文學,甚至還有一些相當有成就的非左翼的文學。與此同時,我們過去無論是文學史教科書還是文學史研究論著,都認為當時“革命小說”存在著“革命加戀愛”的公式化創作模式,以此對其進行藝術描寫上的否定。但是,從作者的處境和文學觀的影響來看,這種藝術上的模式化來自于人生境遇和感受的共同性,所以不是單純作為藝術缺欠而進行否定那么簡單。因此我認為,無論哪一種文學史文本,都不能忽略這些歷史事實的存在。經驗告訴我們,歷史書寫中最難實現的往往就是真實地書寫歷史事實本身。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評價從來就不只是一種學術史和藝術史的評價,它同時也是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評價。所以今天我們談到文學史如何的發展,我之前說過像你剛才提到的四種限制、四種制約,這種制約是什么呢,其實它有的是必然的,是必然要形成制約,特別是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政治的結緣關系、親緣關系的分析。不管愿意與否,不管有沒有意識到,政治都是時時刻刻在對學科產生著影響的,因為現當代的時間范疇和政治的聯系太緊密了。我們現在可以期望有一部文學史和政治更少關聯,但這樣的文學史其實不是真的文學史,它就是我前面所說到的喪失了歷史真實的底線。只有把文學和政治放在一起來看待現當代這段文學史,才真正符合文學史的本質。因為從傳統文學觀和文人的人生實踐來看,中國的作家作品就是這樣的和政治、時代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所以我們說這種制約有的是先天形成的,因為歷史存在本身就是在如此的情況之下形成的,就像水乳交融一樣,你不能把乳從水中重新分離出來。
另外個人因素也決定了我們在觀察文學史的時候會產生不同的視角和結果,即使同一段歷史也不能用一個完全同一的文學史觀、學術史觀去看待它,因為文學史觀也是眾多個人判斷綜合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不斷成熟的過程。比如有的判斷,可能現在看起來很幼稚,但久而久之發展起來,它可能會成為很完整、很科學的文學史觀。所以我說,我們渴望著歷史有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但歷史恰恰是不斷的粉碎著人們的這種期待,歷史就是循環往復的,就是一種非線性的發展,歷史不止有前進,也有倒退或者說歷史有著自己的重復和回溯。所以在今天,無論未來我們的文學史怎么發展,在時代精神的指引下,我們都要持有一種學術的良知和底線——歷史的底線以及道德的底線,用一種開放的文學史觀去看待歷史上發生的一系列文學現象。我想,這樣的文學史,無論到了哪一天,也不會離本質太遠。
劉帥池
:老師您剛才提到的在文學史觀上我們要堅守的底線,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說是感同身受的。無論是學術的、道德的還是歷史的,可能時代在發展、科技在革新,我們人們的生活方式在日新月異,但無論如何,人類的基本道德底線和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應該是一脈相承的。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只要我們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那么接著上面的討論,當我們具體到文學本身來說,就像剛才我們所說的,我們在思想的交流、思想的融合中達成整體的研究成果。那么當針對具體的文學,比方說針對具體的一部當代小說:一部小說,一方面基于它的底線,在它的具體發展中,必然會存在著它的歷史定位、時代定位與文學定位;同時,在今天我們的生活環境里,小說也會更多的被體現或者被替代于戲曲、呈現于熒屏甚至發展于網絡。之前美國批評家希利斯·米勒在《論文學》中,對文學的命運作了如下表達:“文學的終結就在眼前,文學的時代幾近尾聲。該是時候了,這就是說,該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紀元了。”但對于關于文學命運的這種說法,我是持有否定態度的。媒介本身也是文學呈現的方式,是文學張力的體現和感染力的表達。您剛才已經說過了,在這樣的時代里,我們應該先堅守什么,我們的底線應該是什么,那進一步我想向您請教的是,您又是如何看待文學在變革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些什么,發展些什么?張福貴
:在回答你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對原有的問題我們應該梳理一下,可能更好地談這個問題。剛才你所談到的問題,包括習總書記提到的民族的夢想、民族的復興,應該說民族的夢想與民族的復興已經不單純是對傳統的回歸,其實夢想的實現更是時代的進步使然。習總書記講要一代一代堅持下來,其實在堅持的過程中,本身就包含了一種創造和創新。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體系,這個時代過去了,其價值體系可能會改變。因此,文化的與時俱進、思想的與時俱進是必然的。那么我們民族復興或者民族承傳最重要的一點,我覺得是體現在民族創造力上,而創造力最集中的體現則是思想的創造。確實在今天,我們說中華民族對于人類的貢獻,可能我們更多的還停留在千百年以來的文化積淀上,或者說從歷史上所謂的諸子百家、孔子孟子、唐詩宋詞、李白杜甫等等所闡發的,而關于近代之后我們這個民族給人類提供了哪些能影響世界的思想呢,其實是乏善可陳的。所以我說,習總書記所談到的民族復興與民族傳承,應該包含了民族的創新與創造,你可以從他更多的一些論述中切實感受到,特別是他所談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其實就是一種新的“全球化”思想。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也可再繼續單獨探討。下面我回答你的問題。你說文學的發展在當下語境中,在這樣一個以媒介載體為主導的環境下應該注意哪些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多年來人們一直在探討同時也一直在困擾我們的問題。就像你說的,米勒所談到的關于文學的終結,這個觀點在八九十年代已經流傳很廣了,大家都非常非常認同,而且當時人們都有些驚慌,都在呼吁如何挽救文學。當時我就說今天純文學的這種衰落,并不是純文學本身的不足,而是隨著大眾文化和網絡傳媒的崛起,非純文學的發達所致:不是純文學衰落了,而是通俗文學、網絡文學、影視文學更強了。就像在一個月光明亮的夜晚,星星就不發光、就不亮了;而沒有月亮的夜晚,才顯得星光熣璨。所以說時至今日,在文學的夜空之中,我們的文學之星好像暗淡了,但它并沒有改變,它仍然透過藍天,在我們頭頂閃耀著,依舊是熠熠生輝,甚至是整體光明,只不過我們就好像是由初一趕上了十五,月亮升起來了,而月亮的明光暗淡了群星的燦爛,所以我們才覺得群星已經要消逝了,我們才會恐懼。但豈不知,十五之后月亮還會消沉、還會暗淡,星星的光彩還會再一次出現。其實歷史本身的存在就定義了文化是一種自在的而非自為的,你不論如何驚呼,它其實就在那里。而且文化的接受也是自然選擇的過程,不是說我們說的哪好就要保留,哪不好就要去除,這只是一個人為的選擇。文化的傳承和選擇是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對人類有益處的東西總是不會消失的,也就如同我們今天吃飯所使用的飯碗一樣,從古到今人們一直在使用著,如果飯碗沒用的話早就已經被人們拋棄了,但人們只要吃飯,就需要用到飯碗。同樣,一種文化只要對人類有益,就一定能保留下來,有時候可能暫時的被弱化了、消逝了,但人們一旦重新意識到了,也就馬上可以恢復,這方面我覺得其實不用擔憂。歸根結底,我們過去所產生的文化憂慮癥太強烈,所以當我們看到通俗文學、影視文學的興起,才會有最初的一系列迷茫。但首先要看到影視文學等很多方面內容本身也是來自于傳統文學的,是來自于小說、散文的,只不過是轉變了一下載體而已,母體仍然是文學。我們也應該看到,今天的網絡、影視等新媒介平臺的文藝作品越來越多,其實這也說明了過去此類文學樣式的不足,因為影視是在百年前才產生的新的媒體形式,網絡更是二三十年前才產生的新媒體。新產生的自然一定要奪人眼球也一定要引人注意。而當它的新鮮感逐漸消失,逐漸成為一種常態之后,我覺得它也會進入我們正常接受的領域并完成接受的過程,人們也不再去驚呼了,哪怕是在之前驚呼的過程之中。就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發展來看,以歐美國家為例,當前他們的媒介市場相對于我們要更加發達完善,但純文學也依然存在著并未消亡。所以在今天,好像是網絡平臺上通俗文學“甚囂塵上”,但豈不知一切都是在變化的,網絡文學本身可能也會成為一種純文學。
那么我們今天的文學發展應該注意一些什么問題呢?這就要說回到我們一直所談到的:任何一種文學創作、文學現象,都要有經典化的過程,人們最后接受和留下的就是經典,而不會是全部作品。當下中國的文學創作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但是那種娛樂至死、本能放縱、宮闈權斗和一夜升天的流行模式,根本上就是因為缺少一種追求正義直面現實的人文關懷。一個全面娛樂的文化絕不大可能是一個昂揚向上的文化。迫切需要的是改善社會,推進文化建設取得新成就。當我們站在當下去縱觀歷史的發展,幾千年來傳統文學留存至今的也就是鳳毛麟角,如百家論著、秦漢文章、唐詩宋詞、明清小說等等,這些與幾千年的文學史比較而言,本身就已經足夠稀少了。所以今后我們的網絡文學、通俗文學的發展可能也是如此,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它現在動輒幾千萬的文字,去蕪存菁后就只剩下了幾萬字的容量;或者說現在活躍的數以萬計甚至數以百萬計的寫手,最后留在歷史中的也不過就那么幾個、十幾個,這都是不足為奇的,也是可以在文學的發展中找到證據的。所以我覺得,我們面對于大眾文化的繁興,先不要急躁,不要過于憂慮,就像我們說了文化是自在的不是自為的一樣,要相信讀者、相信時代。而且文化本身是有生命力的,一旦被創造出來,它還可以有自我選擇、自我更新和自我發展的過程,對于這樣的一個過程,等不迭的、看不慣的可能恰恰是我們自身。
戚萌
:就像您曾經在一篇關于文學時代的論文中提到過的那樣,我們的文學史文本會越來越薄的,這就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因為歷史本身就是一個淘汰和精粹的過程。包恩奇
:我覺得經典化建構的過程,本身就不是單一靜止的,它必然要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經典化應該是一種手段,而通過這種手段和途徑,會留下真正的文學經典。當然,經典化過程不是完全被動的,需要讀者和觀眾的參與。張福貴
:沒錯,說得很好。我們說文學時代也好,經典本身也好,其實都是相對而言的。我們還需要打破另一種觀念:不能以為建構了經典,就會被所有人所認同;也不能以為建構了經典,就能被一代一代所承傳,這本身就是有點幼稚的、不現實的看法。在歷史演化進程中,一種文化思想本來具有多種內在的價值能量,文化在歷史上的價值能量,會逐漸顯現在新的環境中,可能最終會成為另一種價值能量。因此,一成不變的傳統即使存在,也不應該或者說不可能還保持原有的樣態。其實,回歸和重復,是中華文化最為輕車熟路的取向之一。我們就當下經典而言,也是被很多人所不認同的,經典不過是我們相對尋找到的一個最大的公約數而已。認同的多、不認同的少就是經典了;認同的少、不認同的多就是非經典。所以經典的概念本身也應該是一個流動的概念和歷史性的概念,我們不能先排除非經典去建立經典,然后又把經典凝固化了,這本身也不符合文學經典的歷史化的過程和規律。包恩奇:還有就是可能今天的“新”轉眼就會成為明天的“舊”,新舊本身就存在一個轉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典可能會在今天得到了承認,但在未來又被推翻了,這本就是一個相對變化的過程。這可能就是您說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體系,這個時代結束了,價值體系就解體了。文學史觀、文學審美觀也是這樣一種價值體系。
張福貴
:是的,有可能某一部作品今天是經典,可明天就不是了。相反,有的今天不是經典,但明天可能就是經典了。《水滸傳》剛剛出現的時候很多人抨擊,被視為誨盜小說;《紅樓夢》也一度被列為禁書,被視為誨淫小說,但最后它們都成為四大名著中的一個,都被我們看做經典中的經典,都已經登堂入室,得到了肯定。戚萌
:那老師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您對于經典和非經典,對于“新”和“舊”又是怎么具體看待的呢?因為就以時下而言,我們剛剛跨入2017年,距離1917年的新文學革命剛好走過了百年的時光。遙想當年,以胡適陳獨秀等人為代表的啟蒙先驅們振臂一呼之后,那一代文化人遂扛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對雕琢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艱澀的山林文學進行猛烈的抨擊。自此之后中國文學進入到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全新時代,拋棄“舊”文學,進入到了“現代”文學的領域。那么對于“新”與“舊”您是如何理解的呢?您能從思想到形式對“新”與“舊”進行一下辨析嗎。張福貴
:客觀來說“新”與“舊”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我們該怎樣判斷“新”?首先那就不是往前看而是向后看,也就是說我們去判斷一個新事物一種新思想是否是“新”的,不是根據它未來的發展,因為未來無可判斷。任何所謂的預測未來或者對策之類其實大都是有些徒勞的,是費力不討好的,我們能判斷的只是在這個觀點、這種思想提出之后,比較起前人來,它存在哪些優越之處,具備了哪些創新,填補了哪些空白,又有哪些是可以稱作前所未有的,這才是“新”。所以“新”的標準永遠是向后看,或者說是以過去為參照來作為對“新”的判斷的依據;另外,“新”往往不是一個共識性概念,因為“新”首先往往是少數,少數會被視為“叛逆”,“叛逆”會成為“反動”,而“反動”是要被否定的。“五四”新文學最初就是這樣一種處境。因此在看待新文學的時候,我們要有一個寬泛的概念,要有一個時間周期,給新的事物一個更長的周期,給予它更多的理解,我們給它一段時間讓它自行成長,然后再去看它到底是一個畸形兒還是一個健康向上的人。當然,我們也有更多的手段,也不可能會是像判斷妊娠期間到底是男是女一樣就能直接解決,同時我們在文化的角度其實也可以看到,即使是畸形兒也是具有它生存的權力的,誰也沒有直接規定文學史必須是一個精品文學史,文學史本身也就是由精品和非精品構成的。我們現在來看,中國古已有之的傳統中,往往有一種對于人物形象的倫理和審美判斷:如果是好人那就不包含任何缺點和弱點,就好像我們寫英雄一定是君子,如果政治上反動那道德上也一定要是墮落的。但其實我們這樣的簡單的一元化觀點,是不符合事物及人性本身的,高大全的倫理觀本質上也還應該是人類的一種基本倫理,但是不應該排斥人性的邏輯,否則就很難具有真實性和感召力。人性本身就是復雜的,就像我們評價魯迅一樣,魯迅存不存在弱點呢?當然存在,性格的弱點、思想的弱點、道德的弱點也都是有過的啊,這些也可以共同稱作人性的弱點。但我們也并不是要因為魯迅有人性的弱點,就去否定他人性的優點和思想的先鋒性,我們要先去進行弱點和優點大小的比較,去看看哪個對于我們的文化和我們人類更有價值,然后再去選取、再去普及,否則的話那就只是把魯迅當作一個平常人看待了,那魯迅的價值也就失去了。戚萌
:那么老師您剛才所說的新文學概念主要是在講文學的意義價值,和您之前的民國文學作為時間概念的主張有無沖突呢?那么,民國文學和新文學是否都有還原歷史、還原到真相的意義呢?張福貴
:針對民國文學這樣一個概念,我還是堅持它是一個時間概念,具體說來,就是指民國時期的文學。從時間上來講,我們并不一定就是說要判定哪些是要還原到原來真相的,只是說我們提供了可能存在真相的一些邊界,或者說我們知道這座礦山里有鉆石或者是這片河灘上有沙金。但我們并不知道具體哪個地方有,而只能告訴大家從這一段到那一段之間是肯定存在的,這也是民國文學概念的這樣一個邊界,新文學就是其中一塊最大的金塊。具體說究竟哪些是真金,第一就要憑借研究者自身的能力去發現了,第二則是不同個體之間對真金的認定也是存在差異的。所以如果做一個類比的話,那么其中的金子是構成文學史的材料,而我們的沙灘則只是作為一個邊界,所以文學史中民國文學的概念本就是一個邊界的概念。我們說用民國的視角,是指用民國時期的時間概念,不是用民國的價值觀,這也是文學史觀存在的邏輯基礎。而如果我們把民國文學作為一種價值觀了,那其文學史觀的正確性便有待考察。因此說民國文學是個時間概念,是文學史觀中的文學史邊界,是文學史寫作的起點和終點。我們是劃定“沙灘”的人,至于怎么找“金子”,那可以衍生出各種各樣的文學史文本來,只不過是過去我們可能片面地認定這段沙灘是,那段沙灘不是,因而顯得有些局限,我們應該擴大沙灘的范圍,僅此而已。如果從我們學科的角度出發,可能也正像我之前寫到過的:文學史文本實質上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教科書文學史,一種是學術文學史,不能用前者代替后者,也不能用前者的尺度作為后者的尺度。教科書文學史注重基礎性和知識性,強調評價的穩妥性和普適性;學術文學史注重創新性和思想性,強調評價的個人化和獨異性。而當我們從事修史的工作時,就必須要有自己的歷史觀,而獨特的、深刻的歷史觀必然是具備獨立思想能力的人才能具備的。
劉帥池
:非常感謝老師,就像剛才您從文學性、思想性直到文學史觀和價值觀這樣一個整體上去觀照文學史,然后再具體的討論我們的學科那樣,思考我們的治學、為學,甚至是我們的為人。我記得您曾經也說過:大學作為思想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搖籃,首先要為時代和人類提供前沿性的思想。這不僅要為現實社會提供肯定性的科學依據,更要具有社會批判功能。張福貴
:無論世俗社會如何變幻,大學總要保留一些精神的清高。大學教師不僅是一個時代最尖端的知識者,也是一個社會最前沿的思想者。如果這個民族最精華的群體不去思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那還有誰去關心?大學的文學教育首先要強化學生的這種使命意識,使文學教育成為一種完美人性的教育:鍛煉人的表達能力,培養人的審美趣味,陶冶人的思想情操,提高人的文化品位。這些過程可能在其他學科專業中都有涉及,但是對于文學教育來說,可能更為重要。文學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的一種激情一種浪漫,這是人類的初心。人如果沒有了這種初心就會沉寂,社會沒有了這種初心就會失去色彩與活力。我曾經多次和剛入學的學生說,如果你到中文系渴望做一個作家,或者渴望像理工科那樣具體掌握一門學問,那么可能就會失望,文學教育是在不學而學、不用之用之中。過了四年,也許你覺得自己并無可圈可點的收效,但是回過頭來和四年前的你相比,你會感到這其中的變化有多大。你再回到中小學同學之中,大家會感到你的變化很大。大學的文學教育在不知不覺地改變著人的境界、情懷和氣質。我覺得這才是大學文學教育最動人之處。因此,從全民素質提升來說,我一直贊成大學盡可能的擴招。說到這里,我想用當年面對一位經濟學教授質疑文學的作用時的話,來回答開篇的問題。那位教授很不理解文學教育的功能,他認為學文學使人變得不實際、不實用,一切不適應市場需要的專業都可以停辦。他嘲諷道,談個戀愛整天藍天白云小花小草的有什么用?兩個人好鉆苞米地就得了。我告訴他文學有什么用:你讀了一首詩、看了一部電影,遇到危難和險惡你敢于沖上去,自己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這,就是文學的作用。這可以從當年部隊上演《白毛女》和流傳《誰是最可愛的人》的影響力來證明。毋庸置疑,這種影響力在當下人的精神生活中,已經變得十分有限了。如果大學培養的人最終仍然與游走于市場和夜店的人毫無二致,這四年時光是否是一種浪費?通俗化不是市俗化,“接地氣”是不忘初心,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關注現實而改造現實,而不是在市俗化的浪潮中隨波逐流,成為精明的功利主義者。我多次說過,我希望我的學生多保留一點天真和單純,盡可能地不要過早成熟。青春時光就是浪漫的年代,文學青年就是做夢的人。因為天真和浪漫最容易產生最美麗的詩。
當下中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在網絡時代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網絡不僅成為人們一種新的傳播媒介,而且成為普遍的生存方式,極大地豐富和改變了人們的文化生活。特別是自媒體的勃興使人人都有了表達權利和表達的空間,當人人都是寫手的時候,傳統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便會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于是,文學還有什么用?文學教育向何處去?并非是一個無須探討的偽命題。我一直認為,大學的文學教育不排斥對于大眾文化的關注和肯定,但是更應該是對精英文化的一種堅守,這不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別,而是大學文化和非大學文化的區別。大學的主要屬性決定了其對于精英文化的執著,這是民族進步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毫無疑問,當下中國正處于一個大時代,大時代需要有能表征這個時代的高尚文化,而代表當代中國文化形象的不會是那種娛樂至死、本能放縱、玄幻穿越、宮闈權斗和一夜升天的流行文化產品。這種低俗文學不僅缺少生活經驗也缺少生活邏輯,愚弄讀者和觀眾,其泛濫的最終結果就是降低民眾的智商和審美情趣。低俗文學泛濫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一種追求正義直面現實的人文關懷,缺少對文學創作的敬畏之心。一個全民娛樂的時代絕不是一個昂揚向上的時代,一個缺少深刻思想和美好情感的人也不是一個完整的現代人。而在此中,大學與大學的文學教育應該承擔起培育完美人性的責任。大學的文學教育不應僅是著眼于服務現實與地方,它更應立足高遠,發揮出自身的社會影響力,來為人類和未來服務。大學并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通過一種氛圍提升年輕人的思想境界,改變人的精神氣質。然而,這種風尚及境界恰是目前大學文化建設中所缺乏的。一句話,大學要有“文化”,大學不培養土豪,而應該培養有教養、有擔當、有品格、有個性、有終極人生關懷的精神貴族。這種精神貴族不是脫離甚而輕視大眾生活和大眾文化,而是引領大眾文化成為時代優秀文化和優美文學的先行者,實現“文學生活”。當下社會心理戾氣過重,缺少優雅和從容。
在文化生活不豐富,閱讀對象缺少選擇的時代,文學青年曾經是一種文明和才華的標志,業余寫作成為一種文化時尚,就連當時的征婚廣告中都以此為看點:“本人小學文化,酷愛文學。”而今天,文學青年已經消退了往日的光彩,變成了似乎很“二”的青年的代名詞。當文學被神化或者泛化,都不是文學最真實價值。相對而言,我堅持認為大學的文學教育是一種精英教育和高雅文化培養,這是有別于世俗社會一般訴求的大學精神。大學的文學教育不應僅是著眼于服務現實的地方,它更應立足高遠,發揮出自身的社會影響力,來為人類和未來服務。我認為,嚴格來說任何大學都是人文大學。
劉帥池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整個現當代文學學科和文學史觀以及于此之中我們思想的具體體現,那么您之前還提到了魯迅的精神、魯迅的批判性,我們最后不妨以魯迅的精神和魯迅的價值來收尾吧,記得孟繁華先生曾經說過:“學界討論什么問題,就是對什么問題表示焦慮的一種形式。”在您之前的諸多文章中,也都表達過當下關于魯迅的一種被輕看、被否定甚至是被反攻倒算乃至故意抹黑的過程,那么我也想請問您,在今天,面對魯迅,面對我們這個時代,魯迅精神可能具有不同的時代意義,但他一定擁有同一的時代價值,這個價值我們應該如何體現呢?張福貴
:其實你這里是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又談到了大學的教育和思想形成的關系,那么我們不妨從方法學的角度說回來,應該這樣說,我曾經一直堅持的一個觀念就是思想的重復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思想的價值在于創新,在于產生思想本身,不產生思想的大學不是真正的大學,所以從這樣的意義來說,任何一個大學都應該有利于新的思想的生成,這樣人類的文明和文化,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才可能進一步的提高和前進。那么由此我們也要看到,大學究竟要培養人什么東西呢?關于這個問題的相關性我一直在考慮,就比如說現在,習近平總書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所談到的如何培養人才,“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教育強則國家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視。我們對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對科學知識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我國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決定了我國必須走自己的高等教育發展道路,扎實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只有培養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夠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其實我們也應該看到,人才不只是知識性的人才,它應該更是一個全方位的人才概念,而對于大學來說,作為中國最尖端的教育模式,除了去傳授最尖端的知識,還應該具備最前沿的思想,如果說我們的大學不能提供那些具有民族意識,具有人類意識的前沿思想形態的話,那么大學其實是沒有盡到責任的,因為大學存在的意義畢竟不同于中學或者技術學院,大學是要去更多蘊養一個完整的人才。這也像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樣,我們一方面要用思想政治理論去教育學生,另一方面我們更應該生產新思想,以豐富思想政治理論本身,更加完善國家的政策方針。所以我才說,大學是產生思想的地方,我們應該保護那些具有學術叛逆性的思想,因為很多新的思想也就產生于這種叛逆之中。我想,無論是作為一個大學教師,還是擴展到一個大學校園,它對于我們民族和整個人類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就在于提供前所未有的新的知識和新的思想,而使之成為推動我們的社會、進而推動人類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力量。由此我覺得對于大學的界定,關于大學教師的職責等,都是不容忽略的。
那么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所談到的關于我們現在對魯迅的評價問題,這是一個老話題,但也是一個常說常新的問題,我們大家都愿意說“說不完的魯迅”,我也曾說過要借魯迅去言說我們自己和我們這個時代,這本身就是魯迅的價值所在。應該說任何歷史的產物,都具有它的歷史局限性,沒有歷史局限性的產物是不存在的,所以魯迅作為一個偉大的人物,與他相關命題的產生也必然會具有其局限性。但也如我之前所言,我們究竟是要關注這個偉大人物的局限性,還是更多關注這個偉大人物的創造性;我們應該考慮,我們不是將魯迅作為一個常人來看待的,如果僅僅作為一個常人去研究,那也絕不會有這么多的研究者研究了這么多年,魯迅的某些相關問題也不會引起全社會的爭論和討論,所以由此可見其實魯迅不是常人,那既然不是常人,我們也就不該用常人的屬性和觀點去評價他。如果說魯迅思想對于過去、現在和未來一以貫之有著太多的可取之處的話,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必然是他的超越性的思想,這個超越性的思想正是前面提到的人類前沿的思想體系。例如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社會政治革命還沒有開始,更沒有完成的時候,魯迅已經提出要如何去進一步完成思想革命,即在當時的革命黨人努力要去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治、議會政治的時候,魯迅卻是超前的認為這種所謂議會政治所帶來的壓迫可能會尤烈于暴君。這其實是我們難以想象的,而且當時的革命黨人拋頭顱灑熱血也就是為了建立一個以議會民主為核心的共和政治,但在魯迅的認知里這種政治的壓迫可能是比暴君獨裁更值得警惕的。在這里似乎魯迅與傳統的封建王道站在一起了,但豈不知,魯迅并不是因為落后而與當時革命黨人的方向產生了差異,而是因為魯迅的過于超前。當魯迅的思想已經前進到第二步、第三步的時候,也就自然把別人的第一步看成是落后的了。這其實也說明了魯迅是一個追求完整人性,追求絕對個性的人。因為議會政治是一個多數法則,而就像毛澤東所說過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在多數法則存在的過程中,多數人會不會成為庸眾呢?會不會去盲從呢?可能只有少數人是清醒的,可是由于利用議會的多數法則,就會否定少數人的意見,所以魯迅才會說“壓迫乃尤烈于暴君”。這其中魯迅對于個性的強調已經是具有絕對性和超前性了。所以我們說魯迅的這種思想是超越的。無論到什么時代,我們都不能忽略對于個性化的肯定,因為對于個人來說,它是創造、生存和發展的關鍵;對于一個民族來說,更是應對未來國際挑戰的關鍵;甚至對于人類來說,
它也是不斷的完善自我的過程,甚至是新的文化創生的關鍵所在。所以我才說,就此而言,魯迅就是創造性、超越性的。而且魯迅的幼者本位的思想,他對于傳統和習慣的評價,對于青年人和老年人的評價等等,都是不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改變的。所以才說魯迅是具有超越性價值的。同時,一個偉大的人物,也一定是具有超越性的思想的人物,否則他也就只是一個歷史人物而已,而不能成就其偉大。

注釋
:①引自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開班式的講話。
②引自2001年4月17日米勒教授在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英語系講座。J.希利斯·米勒,美國加州大學厄灣分校英文和比較文學教授。
③孟繁華:《新世紀:文學經典的終結》,《文藝爭鳴》2005年第5期。
④新華社:《習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2016年12月0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