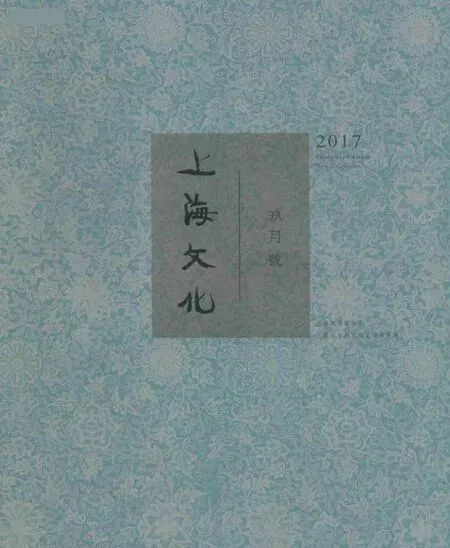你們必曉得真理
庫切的 《好故事》
文 敏
你們必曉得真理
庫切的 《好故事》
文 敏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John 8:32
我接到這本庫切最新著作的翻譯委托之前對它一無所知,亞馬遜網(wǎng)上只掛著最基本的簡介,與書上扉頁無異。我還以為這是一部造型別致的心理學小說,當然不可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或東野圭吾那種,但說不定是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致敬之作——畢竟庫切那樣推崇陀氏。再不好看也得是哲思與心理分析治療情節(jié)的混搭?……反正最后讀下來證明我錯得一塌胡涂。如果你也跟我一樣打算在《好故事》中搜尋到通常意義上的“好故事”,趁早死了這條心。但如果你想了解作家與心理學家尋求的哲學意義上的“好故事”,那不妨來與作者一起把何為“真”(truth)攪它一通。
文學意義上的好故事是什么?開篇時,庫切問心理學家:“好故事(似乎合理的,甚至引人入勝)的素質(zhì)是什么?當我把自己的生活故事說給他人聽時——或者更進一步來說,當我把自己的生活故事說給自己聽時——我應該迅速跳過那些沒發(fā)生什么故事的時間段,而增強那些發(fā)生許多故事時間段的戲劇效果,使敘事更為有型,并營造一種期待和懸念呢,抑或相反,我應該以一種中立、客觀的態(tài)度說出某種達到法庭標準的真相:真正的事實,整個事實,真相至上?
如果你想了解作家與心理學家尋求的哲學意義上的“好故事”,那不妨來與作者一起把何為“真”(truth)攪它一通
如果我沒理解錯的話,他是指某些特定的人生中“有故事”的那些部分,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講述的故事。而那一部分是否真實,是他需要與心理學家討論的問題。要命的問題就是,“真相”是什么?同樣的一件事發(fā)生了,不同的視角與不同的敘述者對此有不同的表達。那么哪一個是“真相”?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年幼時與年老時的回顧也會大相庭徑。于是作為一個敘述者,庫切再次向心理學家發(fā)問:“我和我的生活歷程之間是什么關(guān)系?我是我生活歷程有意識的作者呢,還是我應該把自己僅僅置于發(fā)聲的角色,盡可能不干預從我內(nèi)心流淌出來的詞語細流?最重要的問題在于,鑒于我保持在記憶中的豐富素材,一生的素材,哪些是我應該,或必須略去的?弗洛伊德的警告卻是,那些未經(jīng)思索刪除的記憶(例如,無意識的思考),也許竟是抵達有關(guān)我的至深真相的關(guān)鍵所在?但是,從邏輯上來看,如何確定哪些是我未經(jīng)思索而刪除的記憶?”
好問題!它引出了閱讀者另一個方向的問題:一個小說家,而不是新聞記者或傳記作家來追尋敘事的“真相”?抑或是作為自己生平回顧文本的真相?如果我們認為通常意義上作家隱藏在作品背后,那么作品的真相豈不就是作家想要表達的真相?再說,小說的“真相”,它指的是什么?
與庫切對話的心理學家阿拉貝拉·柯茲是心理學門診心理咨詢師,也是塔維斯多克心理診所頗具影響的心理分析與治療的訓練師。她在英國國民保健服務(wù)體制內(nèi)成年人及司法精神健康部門擔任過多種職務(wù),目前為蘭塞斯特大學心理學訓練課程的高級心理學導師。還需要補充一點:她是個文青。她的第一個回答大致意思是:可能只有精神分析才能抵達至深真相,或者,更審慎更確切的說法是,分析對象敘述當中的阻力,一個真實故事的同樣經(jīng)歷,在孩童、青少年及成年人等不同年齡的敘述是不一樣的。弗洛伊德認為,自由聯(lián)想法是診療室中能夠達到無意識經(jīng)歷呈現(xiàn)的最佳方式,但在心理醫(yī)生的經(jīng)驗中,它卻未如人所期待的那般奏效。病人被要求盡可能隨意地說話,不必考慮通常的社會規(guī)則以及是否精確,但他/她通常會發(fā)現(xiàn),自由表達能夠到何種程度其實是受到限制的——即使是在自己意識的私密之處。這確使我們看到心理防衛(wèi)對于個體的作用,以及作用于抗拒的分析,這是大部分治療中的實質(zhì)性挑戰(zhàn)。
心理學在庫切是被用來表達的工具,而在心理學家,那是她的專業(yè)所長,是用來研究的工具。所以在我看來,兩人的對話表面上互有呼應,實際上,通篇翻譯下來,我真的認為他們在各說各話
其中涉及相當多專業(yè)術(shù)語如:心理防衛(wèi)、抗拒,在本書后面附有專業(yè)術(shù)語表加以解釋。好了,這兩段對話奠定了本書基調(diào):心理學在庫切是被用來表達的工具,而在心理學家,那是她的專業(yè)所長,是用來研究的工具。所以在我看來,兩人的對話表面上互有呼應,實際上,通篇翻譯下來,我真的認為他們在各說各話。
庫切借心理分析這一工具來表述自己對真相與文學藝術(shù)、群體與個體、歷史與當下關(guān)系的思索。至于心理分析與文學的關(guān)系,庫切在此書中有說明:“我們要創(chuàng)作一部有關(guān)某人自始至終的生活的完全由虛構(gòu)組成的小說,那是很困難的,也許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讓人看出其中虛構(gòu)的成份才能創(chuàng)作一部小說。作為一種類型,小說似乎在其主張中具有某種本質(zhì)性的東西,即事情并非表面呈現(xiàn)那樣,我們表面上的生活其實并非真實的生活。至于心理分析學,我得說,它與小說在這方面有某種相似之處。”
他的意思是“真正的虛構(gòu)”不可能存在,虛構(gòu)的真實倒有可能是更高層次的“真”,文學理應是更高層次的“真”。鑒于人們總是把他的(《男孩》、《青春》、《夏日》)稱作“自傳三部曲”,他自己則一再堅持這是“外省生活場景”描述。他特意為浙江文藝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三部曲寫了中文版前言:“這個三部曲的誕生受到列夫·托爾斯泰《童年》、《少年》、《青年》模式的影響。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97年,當時有兩個稍有差異的版本:一個是全球版,另一個面向南非市場,在后一個版本里,隱去了某些人名并刪節(jié)了若干段落。在南非發(fā)行的版本之所以作了刪削,并非礙于檢查制度,而是避免對某些人的冒犯……‘外省生活三部曲’大致勾勒我本人三十五歲之前的生活輪廓。許多細節(jié)是虛構(gòu)的。就這點而言,我并非遵循某種特定的套路。作為作者,我很樂意讀者能將它們當作虛構(gòu)作品來閱讀。”可是,三部曲的扉頁照片都出自他本人:《男孩》中,是母親維拉,與年幼的他和弟弟大衛(wèi)在一起;《青春》中就是青春飛揚的他屈起一腿蹬在欄桿上的瀟灑留影;《夏日》的照片更是廣為人知的那張已經(jīng)發(fā)表了成名作的成年照了,明喻了他個人生活歷程與作品之間的關(guān)系,母親維拉,在《男孩》中就叫維拉,兩兄弟,他是長子。《青春》也差不多就重合了他離開南非之后在英國的生活場景。到了《夏日》,庫切將《男孩》、《青春》那種虛實相間、撲溯迷離的回憶錄風格更推進一步:采用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寫法,把自己作為死者。虛構(gòu)出另一位傳記作家來追尋他自己迷霧一團的中年生涯。小說中的傳記作者從他殘存的日記中選定了五位相關(guān)的人物進行采訪,他們分別是:庫切的一度情人朱莉亞、庫切的表姐瑪戈特、庫切曾經(jīng)追求過的舞蹈老師阿德瑞娜、庫切在開普敦大學教書時的好友和同事馬丁以及另一位同事兼情人蘇菲。我們知道小說中傳記作者要寫一本作家?guī)烨械膫饔洠撬讶∽骷业馁Y料的方式有很多種,為什么要用訪談的形式呢?作家的信件、日記和筆記完全也可以作為撰寫傳記的資料。對此的解釋是:“庫切自己寫下的東西不能被采用,不能作為一個事實記錄——并非因為他是一個撒謊者,而是因為他是一個虛構(gòu)作品的寫作者。在他的信中,他給他的通信者虛構(gòu)了一個自己。在他的日記里,他為了自己或是為了后代的緣故,同樣有許多的虛構(gòu)。作為文件,這些材料是有價值的,但如果你想在精心編織的虛構(gòu)背后看到真相,你就得去找那些跟他直接有過接觸的,還活著的人。”沒有比這個回答更為巧妙地解釋同為“虛構(gòu)作品的寫作者”寫下的《夏日》了。但是,如果作者虛構(gòu)了自己的一切,那么那些與作者有過真實接觸的人就能保證他們所見與敘述的真實性么?至少在訪談中,他們談到的作家面目都各不相同,各人分別看到的是作家生活、愛情、寫作、政治等不同側(cè)面的印象,把這些不同的印象組合到一起,能在多大程度上還原作家的真實面目呢?他們的回憶一定真實嗎?如果說謊言也是構(gòu)成真相的一部分,那就要看你對“真實”與“謊言”的理解了。
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2016年完成的《時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描寫蘇聯(lián)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的一生。開頭的場景是1937年站在電梯口等著被逮捕的肖斯塔科維奇。事情的起因是1936年,斯大林去看他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的演出,中途退場,之后《真理報》發(fā)表《是混亂不是音樂》的社論,他被當局招去審問,加上許多音樂家、藝術(shù)家在那個時代莫名其妙地消失,所以,他斷定自己要被逮捕。他不想讓妻子和不到一歲的女兒目睹他的被抓,所以,他每天晚上都拎著箱子在電梯口抽煙,等著人來抓他。這是許多人都認可的關(guān)于肖斯塔科維奇的一個場境。但是,肖斯塔科維奇生前從來沒有自己提起過此事,是他去世后家人朋友說起的,所以,這件事沒有經(jīng)過史學家的考證或得到完全的證明。如果寫歷史或傳記,作者至少得注明此事是不確定的,但是在小說中,巴恩斯認為可以當作歷史事實來寫。在一個專制獨裁統(tǒng)治下的國家里,歷史真實是很難得到確切梳理或確認。例如,審訊肖斯塔科維奇的人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根據(jù)不同的材料,有三種不同的拼法,巴恩斯在后記中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并把三個名字都列了出來。其后《倫敦書評》上刊登了一位歷史學家對此書的評論,文章題目用的就是這三個名字,她把小說家和歷史學家對比,抱怨小說家太多臆想杜撰的自由,又說她知道準確的名字是什么,如果是評論一本歷史著作,她是會說出來的,但因為是評論一本小說,所以就不屑于把這個信息告訴小說家了。但是“傳記和歷史結(jié)束的地方,就是小說的開始”,在歷史研究與傳記難以觸及之處,恰是小說能夠前往的地方。
那么以真實為其標簽的歷史研究與傳記作品一定是“真實的”嗎?1979年,一本題為《見證》的書出版了,此書是肖斯塔科維奇口述、伏爾科夫整理的肖氏回憶錄。這本書一出版就充滿爭議,尤其集中在它的真實程度。另有,《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lián)的私人生活》出版后,同樣引發(fā)了不小的爭議。肯定者認為《耳語者》代表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寫作,借用解凍之后的無數(shù)普通人的檔案和日記,還有幸存者的敘述,“第一次將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蘇維埃公民的內(nèi)心世界公之于眾。很多書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審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殺——但《耳語者》首次詳盡探討了它對個人和家庭刻骨銘心的影響”。但恰恰因其來源于真實檔案、日記、采訪,結(jié)果召至很多評論者以他捏造或者篡改幸存者的回憶為理由的指責,“書中俯拾即是的史實錯誤,比瓦隆布羅薩秋天的落葉還要多。” 關(guān)于納塔利婭·丹尼洛娃(Natalia Danilova),“費吉斯歪曲了她的家族史,并捏造了她的言辭,很明顯是想證明他著作的題目:除了一位姨媽外,‘其他人如想要表示異議,只得竊竊私語。’”費吉斯篡改了狄娜·延爾遜-格羅佐恩卡婭(Dina Ioelson-Grodzianskaia)的經(jīng)歷,她是一位在古拉格呆了八年的幸存者。費吉斯弄錯了她所呆的集中營后,說她是“古拉格系統(tǒng)中的‘模范囚犯’,擔任專家工作,與勞改營當局合作,以換取小小的好處,但在勞改營卻是生死攸關(guān)的”(中文版第380頁)。從費吉斯的采訪中并不能看出延爾遜-格羅佐恩卡婭曾是個“模范囚犯”以及曾享受過的特權(quán)。可是一名古拉格紀念協(xié)會的研究員說,費吉斯的敘述簡直就是在“赤裸裸地侮辱一個囚犯的記憶”……
照此看來,就算你有時間把所有能夠獲取的相關(guān)圖書文件全拿來讀一遍,真相并非向你展示,反倒讓你油然生出歷史不可知的困惑,即便有照片影音都不一定是真,何況采訪記錄。歷史的真相,或者干脆就說“真相”,在絕對的虛無主義者看來可能就是“明鏡本無臺”的文字游戲。就像那只“薛定諤的貓”,你不去觀察它時,它處于“死-活”疊加態(tài),一旦啟動追究程序,它就因你“觀察”這個動作而塌縮為一種狀態(tài)了。
好吧,我們確實不能夠原原本本地還原歷史,就如我們不能制造出包治百病的藥,可是,這也不能成為黑心工廠造假藥的理由吧?
話說到這里,我倒想知道以“好故事”的名目來追尋“真”,究竟意欲何為?讀者可以看到庫切把回溯真相這一話題討論到無話可說時話鋒一轉(zhuǎn)直指心理學治療的核心意義:通過回溯過往來修復心理中的黑暗陰影,從此以后可以坦然面向未來,重新建設(shè)生活了。真的可以這樣嗎?庫切問心理學家,你現(xiàn)在讓病人回憶一個真實的故事,試圖教導的卻是相反的道德:我們的生活是可以隨心所欲編造修改的,過去只是過去,秘密可以被自由地埋葬遺忘。這樣一個故事可以成立為一個故事嗎?我們是否可以用這樣的句子給這故事結(jié)尾,“他的秘密被遺忘了,他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真正的秘密,不被承認的秘密,關(guān)于秘密的秘密,確實被埋葬了,而我們從此真的可以過上幸福生活了,那便如何?如果試圖埋葬的是俄狄甫斯式的大秘密呢?換言之,如果我們的文化,甚至總體而言的人類文化,形成了這樣的敘述模式,即表面上不鼓勵隱藏秘密,但私底下卻希望埋葬不能令人滿意的秘密:秘密可以被埋葬,過往歷史可以被抹去,公義不能占據(jù)首位,那便如何?我希望相信宇宙有正義,有著某一雙不確定的眼睛在看著萬事萬物,違反道德律最終不能逃脫懲罰。
比如:“我父母睡覺時我把小弟弟悶死在嬰兒小床上,驗尸官稱他死于呼吸暫停,而我則成了城堡之王。這個被壓抑的記憶毒害著我生命的每一天,直至我坦白出來(向法律屈服)懺悔贖罪才得赦免;抑或相反,我能夠成功地忘卻所有,過著心滿意足沒有良心責備的生活?”
問題一:一個三歲孩子的所為,在這種行為中是有罪的還是無罪的?問題二:(真問題)假如只有我自己才能證明這種行為,誰能夠成功地壓抑我自己對此的記憶?
庫切與心理學家著重討論了W·G·澤巴爾德的小說《奧斯特里茨》。如果說所有那些有理由思索靈魂拷問的潛在復雜性的讀者都應該讀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澤巴爾德則適用于所有讀者,它關(guān)系此書的主要議題:人與歷史的真實。這個奧斯特里茨(結(jié)果并非他的真名實姓),他是神秘的,未知的,不可知的——他對自己的了解與他人一樣多。我們確實了解他以及他的個人歷史(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緊密相關(guān)),我們通過他的遭遇以及和一個敘述者的對話了解這一切,關(guān)于那位敘述者,我們基本一無所知。在閱讀這樣一本書時你會有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你在逐步地慢慢地開始了解這個人物奧斯特里茨。當然奧斯特里茨總是通過那位敘述者的中介呈現(xiàn)的,敘述者把我們的注意力拉到他們的主題研究上,例如,在長長的對話之后的那些筆記,以盡可能不致讓人忘記,但事實上奧斯特里茨只是在最后才作為精心構(gòu)建(澤巴爾德構(gòu)建的,敘述者構(gòu)建的,讀者構(gòu)建的)的人物出場,它告訴我們,一個在20世紀中期中部歐洲男人被裹挾進那種劇烈動蕩的大事變中的命運。我們被奧斯特里茨告知(通過敘述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的父母親把五歲的他從捷克斯洛伐克帶出來。他在威爾士,由一對加爾文派教徒夫婦撫養(yǎng)成長,他們叫他戴維·艾里亞斯,對他之前的生活守口如瓶。這是奧斯特里茨向敘述者講述的故事,而那位敘述者對于檢索他離開捷克斯洛伐克前后的童年經(jīng)歷極有興趣,他們對于這個過程的研究與檢索相當于對歷史內(nèi)容的回顧。小說的情節(jié)并非始于捷克斯洛伐克(那是艾利亞斯/奧斯特里茨/艾契瓦爾德的出生之地)而是威爾士,因為這個男孩就在那里開始遺忘,或讓他自己開始遺忘捷克斯洛伐克了。他直至三十多歲都沒想起自己的出處,這時發(fā)生了一個奇怪的危機:他似乎看到一個異象,一個孩子坐在倫敦火車站的候車室里,后來意識到這孩子就是他自己。這個異象導致了包括記憶喪失的精神崩潰。他為此就醫(yī)很長一段時間,只為了在園藝植物的診療室里一再重復的鎮(zhèn)靜安撫之后再次“成為他真實的自己”。
庫切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果被壓抑的意象并不回歸那便如何?如果,對于每一個年輕的戴菲德/雅克,在他們的腳下,這些故事支撐著他們免于崩潰,而還有另外的戴菲德/雅克卻從來不為自己是誰這個問題而糾結(jié),舒舒服服地過著隨大流生活,卻被裹進那些據(jù)說是他們自己的故事里了,那便怎樣?我們聽到的許多案例可以證明被壓抑的記憶會回歸縈繞于心,要爭辯此說是否正確沒有必要,因為我們沒聽說過的案例,就不存在回歸之說。
當年南非的真相委員會努力尋求歷史真相,為要承擔起和解的重任。與歷史和解,遠遠不止說出真相那么簡單。但說出真相,卻是重建寬容、多元社會最重要的第一步。獲得赦免,有兩個條件:申請人需對其曾參與的罪行進行全面的供述和懺悔;同時,要證明他們最初的行為是出于政治目的。赦免委員會將考慮一系列因素,以最終決定申請者是否滿足這兩個條件。委員會會考慮客觀上的具體行為、主觀上的過失或故意,與其聲稱的政治目的之間的關(guān)系,尤其是為達成所謂目的所采取的行動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任何出于個人私利、私人恩怨而犯下的罪行,則不得被赦免。那些最殘忍的罪行要獲得赦免,大量塵封的細節(jié)就必然要曝光,因而選擇”以真相換赦免“的人,必然是有足夠的理由擔心被起訴的人。早期幾個針對種族隔離時期罪行的司法審判備受關(guān)注,被告人被定罪,且面臨長期徒刑,這直接導致赦免申請數(shù)量的激增。然而,當另一個極其重要的審判——前國防部長馬格努斯·馬蘭與其十九個同僚最終被判無罪時,被公訴的威脅就顯然不足以迫使那些高級別的責任人訴諸赦免之路。
說出真相,卻是重建寬容、多元社會最重要的第一步
既是人間的真相與赦免無法避免欺騙枉法,那只有求諸“天理良心”了。庫切在《兇年紀事》中,專門有一章“論詛咒”令我印象深刻:“詛咒就是在那一刻突然降臨的:有權(quán)勢的人猶豫了一下,對自己說,人們說,如果我干這種事兒,我和我的家庭就會受到詛咒——我還要這么干下去嗎?然后自己回答說,呸!根本沒什么神靈,不會有帶來什么詛咒的東西!不敬神的人把詛咒帶給了他的后代;反過來,他的后代則詛咒他的名字。”
我想知道這詛咒是在對真相絕望之前,還是之后?
這就是來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領(lǐng)域:如果沒有上帝,沒有一位絕對位格的存在,一切真?zhèn)蔚呐袛啵胁话驳母杏X,都來自何處?天主教的告解與心理治療中的傾訴區(qū)別在于傾訴對象的無限性與有限性。善有善報,惡有救贖,人間有慈悲,金庸的武俠世界會讓人心存如此美好,但庫切不是,他絕不安慰失意者,天真者也無法從他那里得到鼓勵,他帶著讀者走到真相的懸崖邊自己抽身離去了。
但愿我能夠憑借作品來解讀庫切為真相而寫的“好故事”,但是我不能——
編輯/張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