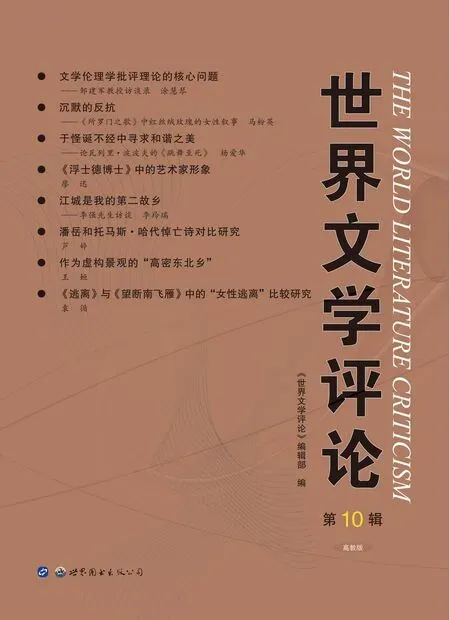哈羅德 ? 布魯姆的影響詩學與比較文學影響研究
楊 龍
哈羅德 ? 布魯姆的影響詩學與比較文學影響研究
楊 龍
當代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的影響詩學形成了影響的事實性、影響的生產性和影響的詩史重構三個層面相遞進的論述,用以鑒照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則可顯現這樣一種學術進路: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發端于研究跨國文學影響的事實,但在研究視角上經歷了從影響者向接受者的重心轉移,從而也引發了對影響的生產性的熱切關注和思考,并在構建影響的文學史方面提供了國際文學史等富有價值的設想。對二者作此種平行考察,能夠深化對各自研究范式的價值體認,并推進我們對文學影響的認知和研究。
影響詩學 影響研究 事實性 生產性 文學史
當代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被普遍認為是研究文學影響而卓有成就的杰出批評家,他發表于上個世紀70年代的詩學名著《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 1973)是他從長期的浪漫主義詩歌批評實踐轉向詩學理論建構的奠基性著作。繼其后,布魯姆井噴式地接連拋出了《誤讀圖示》(A Map of Misreading
, 1975)、《卡巴拉與批評》(Kabbalah and Criticism
, 1976)、《詩歌與壓抑》(Poetry and Repression
, 1976),這些相連續的著作以四部曲形式建立起他堪稱獨創的影響詩學,這也是他始終堅持并不斷豐富完善的唯一理論。像布魯姆這般專一而強烈地關注文學影響,舉觀近現代學術群落,實罕有其匹,細察之,恐怕唯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可相并論。影響研究是比較文學的最早范式,由法國學派倡導,堅持對跨國文學影響的實證考察,有力地奠定了比較文學學科建制的科學基礎。作為19世紀的產物,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與生俱來地強調研究對象的歷史性,與20世紀上半葉轉而注重文學性的研究范式相捍格,故一度被大加撻伐,備受冷遇。然而,從歷史性向文學性的遷移,一定程度地割裂了文學的歷史與形式,是對豐富復雜的文學場的繩削斧斫。文學影響所涉及的,應當是某種總體性關聯視角下的文學場呈現。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固然有愈來愈淪為影響的歷史考據學之弊,但斷然判定其所研究的影響并非“文學的”影響,或許也未必中肯,歸根結底恐怕要溯源于文學理解上的寬泛與純化之間的分歧。然而亦無可否認,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確實顯示出,在偏重于影響的事實材料堆砌下,其文學性維度至少是變得模糊不清。有關文學影響的研究,理所當然應著力發掘和闡釋“文學”在影響過程中是怎樣地發揮著真正的核心作用,就這一點而言,布魯姆的影響詩學提供了具有深刻乃至典范意義的入思模式,而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在當代也經歷了反思,愈益調整和深化了研究思路,不再囿于片面單一的影響關系考察。于此,將布魯姆的影響詩學與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做平行考察,應當更能深化對各自研究范式的價值體認,并推進對文學影響的認知和研究。
一、影響的事實性
布魯姆以研究浪漫主義詩歌起家,在彼時,T·S·艾略特的名文《傳統與個人才能》以其反浪漫主義的面目,盡管與他格格不入,卻最為深刻地刺激了他的詩學思維。他一方面旗幟鮮明地對抗艾略特的詩歌傳統觀,另一方面又從艾略特那里獲得了某種啟悟,將自己的詩學起點選定在對詩歌傳統的關切與思考,在此過程中他捕捉到了他的詩學關鍵詞——“影響”。
然而布魯姆并非將“傳統”理解為詩歌影響的代際承遞,以此成立什么統緒或譜系,他明確指出,“我所說的‘詩的影響’并不是指早期詩人把觀念和意象傳遞給后來的詩人。”“我所稱的‘影響’乃是一種對詩本身的比喻表達;不是作為產品與來源的關系,或效果與原因的關系,而是作為后來的詩人同前驅者的更重大的關系,或者是讀者與文本、詩歌與想象、想象與我們生活整體的關系。”因此,布魯姆對于影響與傳統之間關系的考論,絕非著眼于淵源批評或因果推理,而是將傳統所牽涉的先在者與遲來者的關系列為詩歌影響的赫然見證,以此奠定自己的詩學前提,即影響的事實性。
為了闡明自己獨特的理論意圖,布魯姆自創了“facticity”(事實性)一詞:“‘事實性’意指著某一事實的狀態,比如說,一個不可回避和不可變更的事實。陷入事實性,也就是陷入不可回避和不可變更之中。”詩歌影響的事實性,并不在于后來詩人的遲來者身份,遲來是一種姿態,甚至包含著一定程度的闡釋自由,而事實性是一種狀態,一種遲來者必須去直面的先在事實,即源自前驅詩人的先在性。“任何一位詩人,我修改為任何一位強勁有力度的詩人,像任何人不能選擇他的父親一樣,不能選擇他的前驅。……詩人們……最深層的欲望是變成影響,而不是受別人影響,然而,甚至在志得意滿的最強勁有力度的詩人中間,仍然保持著那種被影響的焦慮。”據此,布魯姆確定了“父親蔭庇下”的、不可逆轉的事實性,“文學影響的最大真實性在于它是一種無法抵制的焦慮。”
面對詩歌影響的事實性,布魯姆的詩學傾向表現得既微妙,又明晰,他所要求的是在對事實性的承認與反抗的雙重行動中尋得詩歌創造的真相。在布魯姆看來,詩歌影響的事實性的終極價值,唯在于激起對事實性的抵抗行動,展開強力誤讀或強力批評。因此,在事實性前提下,布魯姆始終寄望于主體性力量,恰如有論者所設問作答的:“布魯姆所期待于詩人和批評家的強力來自何處呢?與事實性形成對質、同焦慮作頑固抗爭的‘強力’只能來自人的精神。可是后現代文化處處把‘精神’置于表示不信任的引號中,精神成為在事實性的悲哀和衰敗中一道過時的景象。”后現代思想文化對主體性的百般拷問和質疑,一面奏響了主體性精神的哀歌,一面也宣告了事實性的凱旋。于是乎,從浪漫主義經由現代主義而至后現代主義的文化語境移位,仿佛便注定了布魯姆的不合時宜。然而,沒有對事實性的反抗,就沒有詩的創造,事實性也就一無用處,事實性的無往不勝恰恰是事實性的真正悲哀。
將布魯姆對詩歌影響的事實性的價值解剖,借以燭照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其義理辨析興許會更加彰明。如果說布魯姆影響詩學將影響的事實性視為審美創造無可回避的前提、但又必須努力穿透的壁障的話,相對而言,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則基于歷史主義的、科學主義的觀念統緒,毫不含糊地將影響的事實性作為確保其研究對象之科學性的最有力基石,而且,影響的事實即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的全部內容,而不止是前提。當然,比較文學所研究的影響事實是超國界的。1951年,法國比較文學學者伽列在給本國學者基亞《比較文學》所作的序言中寫下著名的一段話:“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的精神聯系,研究拜倫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萊爾、瓦爾特·司各特和維尼之間的事實聯系,研究不同文學的作家之間在作品、靈感、甚至生活方面的事實聯系。”在此,伽列盡管一仍其舊,堅持將比較文學歸屬于文學史學科這一法國學派立場,可是也漸漸感到了法國學派過去的影響研究所顯露出的自我中心缺陷,授人以柄,以致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范式在“二戰”后遭遇種種詰難,而罪責之很大部分源于“影響”一詞本身所預設的主體與客體的不平等角色情境:總有一方是影響者,而另一方是被影響者。于是,伽列的表述,有意用“聯系”替換了“影響”。這種一定程度上的自廢武功之舉,恐怕也是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對“二戰”后西方先后占據話語主流的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一系列反主體主義思潮作出的某種回應,當然亦可以說是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破關而出、自我否定而產生的認識飛躍。然而,較其更深更切近地處在西方后現代語境下的布魯姆,反而一定對此大不以為然,他是極其看重“影響”對于主體性反抗(實即創造)力量的激發作用的。
究其根底,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之所以熱衷于探討文學的跨國影響,其中對事實性的文學史真相不懈追蹤的熱情遠甚于對主體性的審美創造的關切,在其研究論域中,主體性精神標記始終顯得若有若無、毫不著意,似乎有跡可循,又頓覺消解無痕。在事實性的后果層面上,布魯姆將事實性的價值定位于對事實性的反抗,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關注的重心則是影響在異國的際遇,早在1931年,法國比較文學學者梵第根就明確指出:“比較文學家應該考察的,不是他們實在是怎樣,卻是他們被別人認為怎樣;他們應該從這被傳說所改變了的面目出發。”比較文學所致力于研究的,是真正的影響的事實,是跨國文學間影響功能發揮所造成的事實。固然,這與文學創造并非毫不相干,德國比較文學學者就將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命名為“發生學比較”,“‘發生學’這個稱謂也表明,要具體地理解某個特定文本的形成(Genese),除了總是成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及民族語言形成環境外,還必須考慮到外國作品對文本生產所施加的影響。”可是,這里所說的影響,無疑是居高臨下的賦予者,這種影響研究在布魯姆看來定然是與地地道道的事實性崇拜聯系在一起的,它甚至無意于與所謂審美原創建立任何瓜葛。針對那些基于藝術獨創而固守天才論、從而質疑比較文學忽視作家個性的反對意見,梵第根就曾表示:“比較文學家把深切貫通作家和作品的獨有之處和不可溝通之點這任務交給了傳記和心理學的與美學的批評。他只研究這件作品在那一方面和別一些作品有連帶關系,在語感上,內容上,形式上,文體上。他往往證明作者的氣質(這氣質并不是像人們所說那樣,是那么孤立,那么嚴密地不可貫通的)是因為和某一些外國因子接觸而豐富了,擴大了,改善了。”
雖然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志在探索所謂的那些“連帶關系”,但亦無可否認,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決非絲毫未嘗觸及審美創造的某些“冰山之角”,這可以從上面引述的梵第根最后一句話得到確證。審美創造之復雜異常,亙古未解,遠非僅僅依據主體的創造力可以達成。“世界文學研究一部作品的質量,不是完全取決于作品的創作者的天才:它與其原有的廣泛性聯系在一起。”影響的事實性并不總是意味著壓抑性,它時常也參與和推動著審美創造過程,更遑論壓抑性之中本來亦包含著隱蔽的生產性,對此布魯姆也深諳之,故其有“影響即誤讀”的著名命題。只是布魯姆面對傳統,面對影響的事實性,到底意難平,總是力圖以主體性的審美競爭為遲來者尋得立足之地,因此布魯姆的影響詩學實際上是某種“反影響”詩學,始終關注的是影響的焦慮在遲來詩人身上迸發出的修正沖動。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側重探尋影響的際遇,本已內在地包含了雙重視角:一者是影響的視角,另一者是接受的視角。因此,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也并非純粹的“影響”研究,而是容納了“接受”研究于其中,而且這樣一種對“影響”之“接受”的研究,在影響研究應對抨擊責難而致力于矯弊補偏的過程中日益得到凸顯。影響的接受者即審美創造者,按照布魯姆的概念邏輯來理解,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的這一重心調整,預示著或多或少地削弱了事實性崇拜。這樣,在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和布魯姆的影響詩學那里,影響的事實性力量都不是牢不可破的;領悟到這一點,二者便都主要地走向了對影響的生產性的揭示和闡揚。
二、影響的生產性
1997年,《影響的焦慮》在美國再版,布魯姆撰寫長文作為前言,重申:“‘影響’乃是一個隱喻,暗示著一個關系矩陣——意象關系、時間關系、精神關系、心理關系,它們在本質上歸根結底是自衛性的。”布魯姆以“關系”一詞來解釋“影響”,一方面,確實如同伽列等法國比較文學學者一樣力圖扭轉“影響”明顯的單向性,所謂“關系矩陣”即是為“影響”擴容,揭露更為廣闊豐富的、雙向多邊的影響關系;但另一方面,事實上他的用意著重在于顛倒某種習以為常的視角,影響不是順勢的,不是從影響者到被影響者,影響唯獨在后者的自我防御中方才顯形,是焦慮產生影響,而不是相反。在布魯姆看來,“詩的影響并非一定會影響詩人的獨創力;相反,詩的影響往往使詩人更加富有獨創精神。”進一步說,“影響的焦慮來自一種復雜的強烈誤讀行為,一種我名之為‘詩的誤釋’的創造性解讀。”此即意味著著影響的生產性。影響即焦慮即誤讀,實際乃三位一體的過程,影響的生產性就落實在強者詩人的創造性誤讀上。詩歌創造之所以可能,最終依賴的是詩人自我的強力意志。
故此,正如前文所論,布魯姆極力抨擊事實性崇拜,而大張主體性旗幟。根據他的判斷,“影響造成的悲哀,尤其是新的詩人因對留給自己去做的事情太少而感到的恐懼”,并非立即成為一種完全抹殺和否定的力量,驅使詩人陷入絕境,“事實上,一切都尚待思考和歌唱,只要詩人能獲得個人的聲音。”由此,布魯姆深富識見地評論道:“僅僅通過壓抑的創造性的自由,通過最早對影響的關注,一個人才能重生為一個詩人。也只有通過修正,詩人才能變得并保持得越來越強大。”亦可見,布魯姆時刻念茲在茲的創造性,實際強調的并不是全然的“新”,而是“強”,前者絕不可期,后者則真正標志著影響的生產性,這是“一種必然與歷史傳統和影響的焦慮相結合的原創性”。
于是,在布魯姆的影響詩學視野下,遲來詩人無不充滿追求自我不朽的渴望,紛紛挑起自我與先輩他者的審美競爭,文學場內爭強角力,戰火連綿。在遲來詩人與前驅詩人的對抗中,布魯姆熱切地稱贊遲來詩人對時間的撒謊行為,因為這關系到對詩歌優先權或強力地位的爭奪,在當中他看到了遲來詩人得以獲致原創性的唯一契機,這也是影響的生產性憑借所謂“詩學誤讀”而達到最終目標的唯一契機:“通過誤讀,我所說的影響,不是善意的傳遞,而是有意的、荒謬的誤讀,其目的就是清除前輩,為自我騰出空間。”
至此,布魯姆關于影響的生產性的論述,已然呈現出至少兩種鮮明的維度,即個體維度與時間維度,而這兩個維度交織在一起又構成激烈的對抗。在個體與時間的對抗中,即發生著遲來詩人對先驅詩人的轉義或修正式誤讀行為。布魯姆由此認定,影響的生產性之啟動力量在于遲來的個體。
與布魯姆類似,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出于對影響的價值后果的強烈關注,逐漸愈來愈多地注意到,被影響者的接受姿態和活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這也便促使比較文學學者認識到影響的生產性,最早當屬伽列。正如一位比較文學理論史家所云:“比較文學發展到加雷(即伽列——引者)那個時代,對影響和淵源的探索已經將比較文學引入悲涼的境地。也就在這種情勢下,人們重新認識到一個事實,這也是當時的首要認識,即沒有一種影響研究可以拋開與之相對應的接受研究來進行。”伽列在為基亞的《比較文學》1951年第一版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從根本上說,比較文學不是在作品原有價值的基礎上考察作品,而主要注重每個民族、每個作家被借用以后所產生的變化。運用‘影響’一詞的人,經常是指解釋、反應、抵制、抗爭。”這種帶有轉型特征的認知日益得到其他學者的共鳴。譬如法國學者布律內爾援引紀德的話作出論定:“影響是‘通過對抗’形成的。”奧地利學者齊馬甚至對以往的影響研究提出批判:“梵·第根提及的‘所接受的影響和所施加的影響’一樣是被建構的甚或事前就被建構好的,而老套實證主義的問題之一恰在于不能反思建構過程本身。”同樣地,美國學者亨利·雷馬克也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不滿:“在大量影響研究中,人們過度地強調對出處來源的證明,而不是問:什么被接受了,什么被拋棄了以及為什么。”此外,法國的文學史家朗松闡發得似乎更精妙:“發生影響的笛卡爾和盧梭既不是笛卡爾也不是盧梭本人,而是讀者在他們兩人的書中讀到的、用他們的名字所標識的東西;這取決于讀者并且隨讀者一起改變。每一代人都在笛卡爾和盧梭那里讀到他們自己,以自身做比喻,為了自身需要來塑造一個笛卡爾和盧梭。因此書籍乃是一種社會現象,它自身也在發展之中。”在尤其經歷了后現代思想洗禮的當下看來,這些學者的議論仿佛早已成了人所共識的尋常見解,但是,不可否認,其中共同蘊含的“英雄所見”,確實拓展了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境界,通過從影響者視角向接受者視角的焦點轉移,不僅消除了以往單向視角之弊,而且,重要的是更深入徹底地體現比較文學的“比較”思維,切實有利于建構比較文學所期許的文學對話。在此需提請注意的是,這種逆反地考察影響的思路,與布魯姆如出一轍。
同時,比較文學學者也越來越豐富地作出了一些正面論述,以奧地利學者齊馬為例,他在他的《比較文學導論》中就反復申明:“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有生產性特征,它不應被理解為機械的模仿,而是由一個或多個作家所做的對外來語詞的創造性加工。”“影響證明是一種選擇和生產過程,讓新的意義得以形成。”影響的生產性在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中日益得到確認和重視。但是,由于比較文學秉有的跨越傾向,它有關影響的生產性問題的思路,又顯然與布魯姆迥然相異。
如前所述,布魯姆的影響詩學所包含的是個體與時間的對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個體維度和時間維度都是被高度抽象了的,即,他所謂的詩人個體更多地只是一個遲來的身份,或者強力意志,而時間也是一個比喻,僅僅關涉著優先權的歸屬與篡奪。在個體與時間的對抗當中,所有語境性的東西都通約掉了,唯剩下無關利害的審美,供布魯姆頂禮膜拜。這樣一來,在布魯姆那里,影響的生產性嬗變成審美原創性,并且只能通過所謂詩人個體的強力意志來推動達成。
布魯姆的唯我主義和審美主義在很多情況下是不免抽象偏執的,使其喪失了語境主義所能觸及的豐富多樣的問題域。而當下的比較文學卻能敞開視野,在探討影響的生產性時努力剖析更多相關因素,揭露更多問題層面。在這一點上,布魯姆恐怕就頗不明智地縮削了自己的視域,他只認可審美意義上的個體化的誤讀。而在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視野下:
一旦能確定一位作家或一個作家群受到一位不同語種的作家的影響,類型學問題就出現了,它追問這樣一種接觸所牽涉的各種文化語境的歷史、社會和語言特性:是否能揭示出平行的發展演變,這種平行發展能夠解釋為什么不只是一種倉促而無結果的接觸,而是一位作家的作品對另一位作家的作品產生了內在影響?或者是否涉及一種創造性的誤解,一般是當一位作家對另一位作家的作品作出反應,卻并不理解所接受的作品形成于何種政治和文化語境下,作家又想通過作品達到什么目的時會發生這種情形。大多數場合中,我們遇到的都是這兩種反應的混合:在陌生語境中被閱讀的作品得到的理解從來不會和在它所誕生的社會中相同。它接納了新意義并且經常被無禮地簡化或‘誤解’……這類由語言、文化和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誤解,盡管產生了大量的——常常是令人愉悅的——歪曲,仍然值得歡迎,因為它們常常使原來的(‘民族的’)接受變得相對化,能夠激活文本的多義性或開放性,而文本在它固有的生成環境中有時會淪落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或商業的陳詞濫調。
在此,還應注意到,比較文學關注的是影響在異國的際遇,是異質空間下的影響關系,因此所論涉的影響的生產性必然源于空間跨越導致的諸多差異,如文化、語言、意識形態等層面。然而,布魯姆所入思的是時間維度上的影響關系,其空間基本是同質的,故此對影響的生產性的探究便落定在詩人的個體審美差異之上。總而言之,二者對文學影響的研究向度,一者是空間,另一者是時間,各自展開的有關影響的生產性的言說,無疑是可以互為補益的。
三、影響的文學史構圖
作為一位強力批評家,布魯姆一直懷有重構詩史的雄心,他確信:“詩的歷史是無法和詩的影響截然區分開的。因為,一部詩的歷史就是詩人中的強者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間而相互‘誤讀’對方的詩的歷史。”
然而,布魯姆的影響詩學給他提供的歷史敘述框架,卻或多或少是反歷史的。他從個人主義和審美主義立場出發,刻意縮削歷史,乃至將其化約為純粹的時間范疇,僅僅意味著時間上的先在性。他甚至坦言:“我感到,后來者地位根本不是什么歷史身份,而是屬于文學坐標上的這么一個位置。”以布魯姆對社會歷史批評的反感,他最終放逐了歷史的觀念意識形態,而只保留了純粹時間層面的歷史措辭,而且在較多情況下干脆回避這類措辭。他對于詩歌影響的歷史的論述,很快就轉換為對于詩歌影響關系的論述。這樣一來,盡管他所論述的詩歌影響關系主要是一種歷時的關系,可是最大限度地刪削了歷史超乎個體審美之外的種種意涵。
布魯姆之所以對歷史抱有疑忌,除了反感歷史決定論之外,恐怕原因還在于他有意排斥一種長期積習造成的自上而下的歷史思維。這種歷史思維肯定了歷史的壓抑,導致某種事實性崇拜,慣于將詩歌影響描述成代代相襲、陳陳相因的過程。布魯姆的影響詩學在事實性與修正之間建構了辯證的雙向視角,并且著重強調詩歌影響關系的逆向度和對抗性,因此在否定歷史壓抑的同時解構了歷史。進而,布魯姆通過他的影響詩學對詩史做了改寫,在他眼里,詩史毋寧只是詩的集合,而且是詩之間相互沖突的集合,是充滿強力誤讀和審美競爭的詩歌戰場。他甚至指出:“影響意味著,壓根兒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則取決于一種批評行為,即取決于誤讀或誤解——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所作的批評、誤讀和誤解。”對布魯姆這番話,有論者進一步闡釋道:“所以不存在文本性,而只存在‘互文性’,……據此,雖然文本出現的時間有早有遲,但早出的文本不一定就是影響者,晚出的文本不一定就是被影響者。因為晚出者對早出者的誤讀或修改,實際上就是對早出者的影響。……既然影響意味著‘互文性’,也即意味著詩人間的關系,那么,這種關系的實質也就是詩人間互相閱讀,更確切地說是誤讀的關系。”布魯姆所揭示的這種誤讀的互文性,真正發揚了“影響即誤讀”的意義,甚而一定程度地逆轉了時間向度,呈現出更具活力的自由交錯的詩歌影響關系。
但是,布魯姆在以互文性來重新闡釋他的“影響”概念乃至詩史構圖時,依然是在審美與歷史之間做了一種十分偏頗、非此即彼的取舍,他所認可和利用的只是詩歌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影響,對于詩史闡釋而言,這遠遠不夠。有比較文學學者深切認識到:“要區別開互文過程的兩方面:一面是作為主體回應過去或現在的其他文學文本的內部互文性;另一方面是外部互文性,意味著通過主體對非文學的文本和話語進行加工。……內外部互文性在共同作用,文學不能單由自治的角度,由文學演進內部的生產來解釋,它還是社會性事實并且因此成為社會學的對象:作為對政治、法律、科學、哲學和商業的社會方言和話語的反應。‘作品內部的闡釋’和任何一種文學自治美學的根本缺陷都在于抹去了整個非文學的語境。”若以這段話觀照布魯姆,則不僅可見布魯姆固守內部互文性這一明顯的偏失,而且也再一次暴露了布魯姆影響詩學的理論硬傷,即其看似純粹、實則狹隘的個人主義和審美主義。在他的母國,“研究影響問題的美國文學界學者雖然都在運用布魯姆的理論,但卻從兩個方面抵制了他的學說。其一,布魯姆持‘內在影響論’,只關注作者對作者,及作品對作品的影響,忽視文化(‘高雅’文化和‘低級’文化皆然)、歷史和思想等‘外在’影響。對此,他們基本上都加以抵制。其二,他們抵制布魯姆影響論中的直線性單一影響觀,傾向于新的歷史相對影響論,即認為影響具有多重性、異源性和復調性。這種研究將考察對象延伸到了傳統歐美高雅文化以外的影響因素,去關注宗教、哲學、文學、文化和思想諸影響之間的重疊部分。”
毋庸置疑,布魯姆的美國批判者們通過抵制和克服布魯姆的詩學缺陷,表明了一種為影響的文學史構圖填補更多空白的努力。盡管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并不曾與布魯姆短兵相接,可是以其特有的比較視域,對影響的文學史構建確乎別有創見,同樣足以裨補布魯姆。
有比較文學學者通過分析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發現“文學不僅是互文性的,也是跨文化的因此是比較文學的試驗。……不同文化疆域的無論文學還是非文學的話語都滲入其中。比較文學經常探究的影響在此表現為一種互文過程,表現為從事書寫的主體對外來語言形式的掌握。不言而喻,這種掌握對于自身的話語形式和由這種話語形式所塑造的自身的主體性都會發生影響”。而對這樣一些跨越國界和文化的文學影響的追蹤,正是促使比較文學真正興起的根本動因。那句“世界文學時代已經來臨”的著名呼召,如今看來,的確直接見證了西方學者的文學史觀念和視野在那一時期面臨前所未有的更新拓展。譬如,法國比較文學學者梵第根尤是如此,他不但劃出一個由影響的放送者、傳遞者和接受者組成的完整的影響路線圖,還進一步提出要“去劃出那形成國際文學史的經緯的,影響之網線。”在他看來,跨國文學影響交織的圖景,構成了所謂的國際文學史。他的《比較文學論》最末一章即題為“向國際文學史去的路”,其中寫道:“每一個國家,每一位作家都輪流著到這舞臺包括全人類的戲劇中來演他們的角色,表現他們的思想,做他們的夢。”并援引第爾克·高思特爾(Dirk Coster)的話:“各國偉大的文學互相補充著。為要恢復人的形象起見,它們應該互相借貸著它們所缺少的東西。”
雖然這些設想,時至今日,很大程度上仍然還只是設想,而且由于總體化敘事在后現代語境下的消解,更使得人們因這些設想明顯的總體化期求而對它們了無興趣,但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聯系日益空前緊密,諸如世界文學、總體文學乃至國際文學史等曾被拋棄的所謂空洞概念,又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重新拾起,甚至繼踵其后,全球文學、人類文學等概念也被發明出來,競相闡述。其實,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已有學者睿智地洞察到:“在各國文學史和比較文學為一方,世界文學的綜合為另一方之間存在著對雙方有利的來回擺動。”如今,這個擺動正擺向誰方呢?無論如何,在擺動的途中,在早已結成地球村的當下人類世界,文學空間無限敞開,彼此錯雜,交互影響,萬象紛呈,對此,影響的文學史恐怕正切其時,尚待我們去努力建構。
注解【Notes】
①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諾斯替主義影響下的哈羅德·布魯姆詩學創造及運用研究》(項目編號:15YJC752038)的階段性成果。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 [美] 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增訂版),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
[2] [美] 哈羅德·布魯姆:《誤讀圖示》,朱立元、陳克明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1頁。
[3] [美] 哈羅德·布魯姆:《批評·正典結構與預言》,吳瓊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頁。
[4] [美] 哈羅德·布魯姆:《誤讀圖示》,朱立元、陳克明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頁。
[5] 張龍海:《哈羅德·布魯姆教授訪談錄》,載《外國文學》2004年第4期,第32頁。
[6] 胡繼華:《抵抗蒙哀的事實性——談布魯姆的〈批評、正典結構與預言〉》,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6月27日第8版。
[7] [德]胡戈·狄澤林克:《比較文學導論》,方維規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8] [法]梵第根:《比較文學論》,戴望舒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45頁。
[9][奧地利]彼得·V·齊馬:《比較文學導論》,范勁等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頁。
[10] [法]梵第根:《比較文學論》,戴望舒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25頁。
[11] [法]皮埃爾·布律內爾等:《何謂比較文學》,黃慧珍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頁。
[12] [美]哈羅德·布魯姆:《再版前言:玷污的煩惱》,載《影響的焦慮》(增訂版),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
[13] [美]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增訂版),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14] [美]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增訂版),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
[15] [美]哈羅德·布魯姆:《讀詩的藝術》,王敖譯,《新詩評論》2007年第1輯(總第五輯),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235頁。
[16] Harold Bloom.Poetry and Repression
. 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6.[17] [美]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
[18] Harold Bloom. Ag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 New York: Oxford UP, 1982, p.64.
[19] [德]胡戈·狄澤林克:《比較文學導論》,方維規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頁。
[20] [德]胡戈·狄澤林克:《比較文學導論》,方維規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21] [法]皮埃爾·布律內爾等:《何謂比較文學》,黃慧珍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頁。
[22] [法]梵第根:《比較文學論》,戴望舒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19頁。
[23] [美]亨利·雷馬克:《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能》,載干永昌等選編《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頁。
[24] [法]G·朗松:《文學史和社會學》,轉引自[法]梵第根:《比較文學論》,戴望舒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20頁。
[25] [奧地利]彼得·V·齊馬:《比較文學導論》,范勁等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頁。
[26] [奧地利]彼得·V·齊馬:《比較文學導論》,范勁等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頁。
[27] [奧地利]彼得·V·齊馬:《比較文學導論》,范勁等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頁。
[28] [美]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增訂版),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29] [美]哈羅德·布魯姆:《再版前言:玷污的煩惱》,載《影響的焦慮》(增訂版),徐文博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
[30] [美]哈羅德·布魯姆:《誤讀圖示》,朱立元、陳克明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31] [美]哈羅德·布魯姆:《誤讀圖示》,朱立元、陳克明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32] [奧地利]彼得·V·齊馬:《比較文學導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頁。
[33] [美]埃默里·埃利奧特、克萊格·薩旺金:《美國文學研究新方向:1980—2002》,王祖友譯,舒程校,載《當代外國文學》2007年第4期,第56頁。
[34] [奧地利]彼得·V·齊馬:《比較文學導論》,范勁等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頁。
[35] [法]梵第根:《比較文學論》,戴望舒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139頁。
[36] [法]梵第根:《比較文學論》,戴望舒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173頁。
[37] [法]皮埃爾·布律內爾等:《何謂比較文學》,黃慧珍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頁。
Title: A Parallel Investigation of Harold Bloom's Poetics of In fl uence and the in fl uence Stud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uthor: Yang Long is from the College of humanity scienc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Harold Bloom's poetics of in fl uence, mainly accounting for the facticity of in fl uence, the productivity of in fl ue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 fl uential poetic history, could be appropriated to illuminate the study of in fl uenc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rough such a mirror, a route of academical evolvement would be seen clearly: the study of in fl uence begins with the research of fa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in fl uence; however, its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has transferred from the in fl uencer to the recipient, which causes the scholar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ductivity of in fl uence and deeply probe into it, and gives rise to a certain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y of in fl uence to the one of "accept"; and it always insists on connecting the literature with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refore provides such valuable idea as international literary history in the aspect of constructing in fl uential literary history. Therefore, such a parallel investigation could bring some deeper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both researching paradigms respectiv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push forward our cognition and study of literary in fl uence.
Poetics of in fl uence Study of in fl uence facticity productivity literary history
楊龍,華東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研究方向為中西詩學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