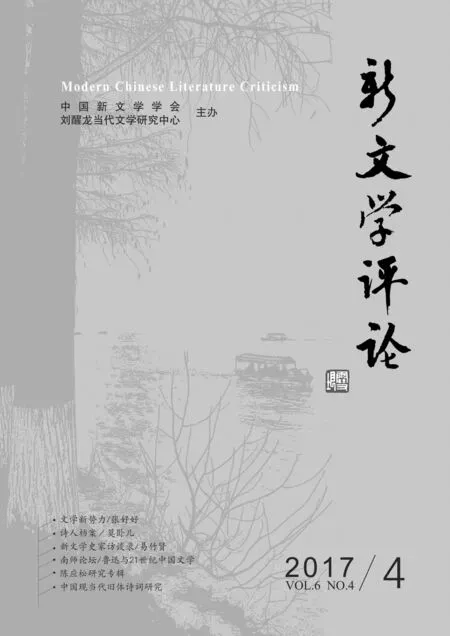貓與妖鳥:超越道德的悲懺
———評張好好的長篇小說《禾木》
◆ 桫 欏
“我想說的是,我并不想把隱匿、隱瞞、遺忘了好幾個世紀或好幾千年的事物顯現出來,也不想重新在其他人所說的話的背后找到他們意欲隱藏起來的秘密。我并不試圖去揭示掩蓋于事物或言說之中的另一層含義。不,我并不只想讓即時即刻存在的,同時卻又不可見的東西顯現出來。我的言說規劃是遠視者的規劃。我想讓距我們的目光極近的東西顯露出來,好讓我們都能看見它,它離我們太近,但透過我們所見之物,我們就能看見另一樣事物。讓這樣的密度成為一種氛圍,讓這種氛圍環繞于我們周身,確保我們能看見離我們很遠的東西,讓這種密度和厚度成為像透明度那樣我們沒有體驗過的東西,而這就是我們無時無刻不想著的其中的一個規劃,其中的一個主題。”
——米歇爾·福柯
一
讀張好好的《禾木》,不免令我想起兩個人,福克納和金宇澄。我不是說《禾木》能比肩《喧嘩與躁動》或者《繁花》,而在于這些作品中共同充斥著強烈的形式感,它們之間具有某種形式上的相近。為什么要談到形式感,是因為閱讀一部作品,我們首先要接觸到的就是它的形式而非內容。形式就像一塊篷布,我只有揭開這塊篷布,哪怕是撩開一條縫隙,才能看到它之下覆蓋的東西。對一部小說來講,形式是先于內容的,我們通過閱讀觸摸到它的語言形式和敘述的表達方式,之后才可能進入它的意象和情節之中。——形式感!在我的文學觀念里,談到形式,就會產生某種恐懼感,因為緊接形式感的就將是“為藝術而藝術”、“形式大于內容”這樣的說法。在并不算久遠的時代里,這些觀念因為違背或弱化了文學作品被賦予的某種功能而被定罪。在這些觀點的角度上,《禾木》就是“有罪”的——它選擇了第二人稱敘述方式,這顯然是一個不常見的寫法。關于第二人稱,有人認為這并不存在,我也一直沒有在各種文學理論詞典中找到它的定義,大名鼎鼎的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典》中它也是缺失的,以至于需要有人通過理論文章證明第二人稱的客觀存在。這是閱讀《禾木》遇到的首要問題,“你”是誰?而又是誰在稱呼“你”?是作者在說,還是文中的某個人在說?他們又分別說給誰?
帶著這些疑問進入《禾木》,我不得不說作者是個勇敢的小說家。放眼望去,以第二人稱書寫并進入文學史的作品為數并不多,很著名的一部是法國作家米歇爾·布托爾的《變》。布托爾出身哲學家,所以他選擇第二人稱敘事與其說是在寫一部小說,毋寧說是在進行一種文學試驗,來驗證文學之中各種不同人稱交替寫法的可行性。他自認第二人稱代表的是讀者,用“你”在敘述,是在與主人公交心,對主人公規勸,表達自己的倫理。在華語寫作中,高行健的《靈山》也是一個非常少有的第二人稱敘事的例子。第二人稱敘事的難度可想而知。而我們當下的寫作,一貫在追捧順暢和容易,使用通俗的語言形成平滑、圓潤的效果。《禾木》是反潮流的,它的情感基調是出自內心最純樸的流淌,甚至其“創作感”都不明顯,與各種技術流派缺乏必要的關聯;它的人稱選擇則更是一個異類,帶給我的就是滯澀和陌生化,輔以綿密的回憶性敘事,整部作品就像一個質量巨大的球體,內里結體緊湊而外形樸拙渾厚。這種特殊的形式選擇,決定了這部作品在當下長篇小說寫作中的可談論性。
《禾木》的第二人稱寫法顯然給讀者和作者都造成了困難,作者在實施一種“有難度的寫作”。作為讀者遇到的困難,我首先感覺到無法在閱讀中擺位,時刻在與作品本身以及作者和人物發生揪扯:我是誰?我是讀者還是作者?我如果是讀者,“你”顯然來自作者的定名,我一面要閱讀文本,一面要時時提醒自己,稱呼主人公為“你”不是我的意見,而是作者的自作主張。而我如果承認“你”的合法性,則就會成為作者的“同謀”,但作者又有什么權力將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稱謂與閱讀者聯系起來,又代替讀者對人物施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而我揣摩作者在創作中和在文本中的境遇,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作者要克服的首先是作者與隱含的敘述者之間的關系難題,稱呼“你”的那個人究竟是作者本人還是敘述者?假如是作者本人,作者就會完全取代敘述者,這是不妥當的,但“你”的稱呼則時時讓作者陷入身份的迷亂中。作品就在這樣的紛亂復雜的倫理關系中被創作和被閱讀。我因此有理由相信,作者之所以選擇這樣的寫法,在于她在進行自我的“設難”:在有可能以傳統方式書寫的情況下自我設定難度并超越它,從而實現主題的深化——這種深化來自作者本人附身于敘述者對經驗進行的獨立批判,而并不與依靠經驗成長起來的人物面對經驗持有相同的態度。
由此可見,是作者的敘事視角決定了文本形式的選擇,包括人稱問題,也包括講述和禱告式的敘述語言風格,甚至這種敘述形式本身就接近宗教懺悔儀式的調子。看起來作者置身事外,以一個見證者和“過來人”的角色向一個遺忘了身份的人講述她過去的經歷,但實質上作者的情感態度、道德堅持和審美取向無不體現在每一個詞匯和句子中。“設難”的另一個含義是作者對所針對的事物了然于胸,并明白讀者的期待,所以敢于獨辟蹊徑和知難而進。相對于慣常使用的小說表達方式,敢于為自己“出題”,敢于突破自我,《禾木》的選擇是一種非常值得稱道和討論的方法。應當說,這種創作的勇氣在“先鋒文學”以來的小說創作中是缺乏的,作家太過于沉迷于自我修筑的金光大道了,可能創新的荊棘之路上人煙稀少。
二
《禾木》從現實入手,講述了一個尋找和揭秘的故事。“你”通過回憶一個家庭的經歷來尋找一個叫“娜仁花”的女人和一個叫“巴特爾”的少年,揭開了縈繞在父母身上隱秘的歷史。敘事的重點并不在尋找的過程和結果上,而是用“你”這一代的人生與上一代做對比,反映人性、情感和道德的嬗變。——假如“尋找”的過程用傳統的方式當作通俗故事來講,它再俗套不過:這只不過是一次成功的婚外情。但是,《禾木》在沉靜、哀惋和隱忍的氤氳之下,透射出人生對情感的渴望以及對罪感真誠的寬宥和懺悔。這樣“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既來自敘事方式的選擇對俗世經驗的文學性提升,更來自作者所秉持的觀念立場。
在我們當下的敘事中,婚外情的出現習慣用來表示人物道德的敗壞,或者作為價值多元化、生活庸俗化的證據,但是《禾木》里的婚外情呈現為人性、情感和欲望的自然表達,盡管它應當受到道德的約束,但這種源自本能的情感優先于道德的存在,這是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事實上作者通過“你”的講述觸及了言說的禁忌,即談論父母一輩的情感問題,何況牽涉并不光彩的婚外感情。在傳統小說的倫理建構中,這是一個“雷區”,無論持何種態度,都將使寫作陷入兩難境地。作者煞費苦心地選擇人稱和敘事方式與此有直接關系,她的機敏之處在于,將自我的道德意見具體化為某些意象,以此作為自己的代言者,委婉地表達自己對世俗生活的意見,并以悲憫和懺悔替代情感和道德的批判。
《禾木》多次寫到動物,實有其物并只作為自然的代言者出現的是真正的動物,但有兩種動物的形象超出了作為動物的本身,一是貓,一是虛構的妖鳥。溫暖的身體、靈巧的姿態和蔑視一切的神情,貓最大限度地代表著人對情感的向往,而它們對人類無時無刻的陪伴更讓走出布爾津的“你”體驗到世界的善良和關懷,所以當“你”將貓托運到母親處,自己回到孤單的現實中時,“你幾乎要失聲痛哭,你想起十來年的流離輾轉,它們一只一只地到來,讓你無暇愁苦,讓你安然抵達彼岸”。“你”收養流浪貓,一遍遍回憶如何遇見幼小的“六寶”并收留它的過程,它們作為人類感情的代償者而出現在“你”的身邊,它們是“你”情感的寄托。順著這個思路,我就看到“你”眼里父親的情感:“如果不是因為愛情,因為一個別的女人慰藉了他的心,他不會成為一個快樂的人。”擁有過苦難和輝煌歲月的父親因為承包工程而前往禾木,并在那里結識了圖瓦女人娜仁花。“父親”是善良的,愛家庭、愛孩子,所以他不能選擇離婚,而因為同樣的原因,他也不能選擇離開娜仁花,就在那樣的牽扯中走完他的一生。“你”對父親的評判是“小平原上的父親,他從來不夠狠。他若狠點,命運一定會好很多”。顯然,作為女兒,對父親背叛母親的行為是寬容的,“你”也不斷說出“誰不熱愛自己的父母?”這樣的話來表達對父親的感情。在血脈親情面前,道德批判退居其次,情感具有優先權。
人不是貓,世界也并非只被美化為浪漫的情感,作者也不是一個幻想家,因此妖鳥這個意象顯示出特殊的意義。妖鳥呈現“鳥”的形象,并被加上了“妖”的屬性限制。日常生活中我們對貓頭鷹和烏鴉有偏見的態度,覺得它們是不祥之鳥,而妖鳥的意象或許從此生發,它被用來被指代欲望。作者數次強調,妖鳥憑借無聲的咒語讓溫良的女性產生邪惡的墮落。一旦被這種咒語擊中,“那有獲取之心的婦人”就將在劫難逃。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與這個小平原上一個著名的小流氓做了那樣的事而退學,成了一個壞女孩,連“唇邊笑意里”都“含著毒”;“妖鳥橫空飛過”時,“他(父親)對他的妻說白日里撞見的事。一個妖媚的婦人坐在某個男人的腿上”,“他還說起某年石灰窯里鉆進去一個男人,后來另一個女人也鉆了進去”。縱然“你”對父親的感情優先于對他的道德評價,但“妖鳥”這個形象則顯示出了作者的道德立場。作者借由妖鳥對傳統道德的敗落展開了批判,而“世風日下”的社會情境成為父親情感轉移的借口之一,從這個角度上看,妖鳥的背后隱藏的是對“父親”出軌行為的譴責——但這種譴責因為親情的存在而很快化作心底的理解,從而獲得對父親的諒解和寬恕——盡管這種理解充滿無奈。
妖鳥的形象所蘊含的意義在貓的形象中得到清晰的對照,對溫暖的渴望并不等同于現實可行的法則,我因此看到《禾木》并不是一部鼓勵或宣揚非道德情感的小說,而是一部懺悔與寬恕之書。妖鳥作為貓的對等意象出現,雖然次數并不多,但其力量足以抗衡故事中非理性情感的蔓延。敘事顯然在這里故意走了一段彎路,以隱晦地表達以“你”為代表的作者的態度。如此繁復的書寫令人費解,但將“你”放置在傳統家庭倫理的位置考量,就看到了“彎路”的必要性。
三
小說應當是一個自足的世界,它僅靠文本力量就能通達到現實世界里看不見的隱秘之所,以“發現那些只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作家作為創世者,會站在高遠之處為小說選擇懸浮運轉的宇宙以及它內在封閉的運行規律。所以一個小說世界的品性和溫度,比如它是粗獷的蒼涼還是精巧的繁密,是感人的溫暖還是寂寞的荒寒,取決于它的創世者即作者自身對世界的感覺經驗和愿望期待。《禾木》的開頭寫著三句話:“人類對大自然的悔罪;男人對女人的悔罪;女人對罪惡的悔罪。”我將其看作作者對《禾木》的主題定位。人分男女,作家似乎不應該以性別區分身份,但是能夠以懺悔的姿態面對這個世界,女性寫作者一定優于男性,男性往往將“無怨無悔”當作自己的座右銘。關于人生罪感和懺悔的書寫,這兩年最好的作品一是喬葉的《認罪書》,另一個就是張好好的《禾木》了。《禾木》是溫暖的,而且溫暖的生發是無條件和無界限的。能夠將歷史的僵硬以情感之火淬煉為溫潤之珠,甚至將欲望的原罪消解為羞慚的寬宥,這背后作者的女性身份時隱時現——但是誠如陳曉明在論及新時期女性主義寫作表征的文化與美學意象時所說:“很顯然,父權制設定的歷史動機和目的輕而易舉就統合了女性話語。新時期的女性寫作可能一開始就試圖表現女性自身的感情(例如張抗抗、鐵凝等),但是宏大的歷史敘事所給定的意義改變了女性初始的意向,那些本來也許是女性非常個人化的情感記憶,被劃歸到歷史化的語境中重新指認現實意義。”《禾木》也深陷這種統合和改變當中。
《禾木》是一部女性之書,首先主角“你”是一位女性,所生活的家庭是女性主導的家庭。做裁縫的媽媽帶著三個女兒生活在布爾津,唯一的男性是父親,但是父親在家庭生活中近乎缺失。計劃經濟時代,父親是手工業聯合社里的木匠,曾經與母親同甘共苦,那時的家庭是完整的;市場經濟了,手工業聯合社解散后父親去了禾木包工程。工程完工,父親不回家,借口還有另外的工程,事實上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了圖瓦女人娜仁花。接下來,“你”的家庭就成為一個“母系社會”。在小說中,“你”觀察歷史和現實的目光呈現出的女性特征,主要在對待父親和母親的態度上。敘事焦點對準的是父親,而將要被原諒的也是父親,這是一個女兒因女性的本能而對男性父親保有的無條件的親切感。相對來說,母親就成為一個特殊的存在。“你”看到母親在有關父親的傳聞中一夜老去:“她四十歲開始生白發,不是一根根慢慢生,是百根千根,一夜,她就老去了。”盡管這樣,“你”看父親時還是覺得“不會認為自己的父親就是敗壞的”,而看母親時則變成“母親的壞脾氣,抱怨語言”。事實上母親是這場變故的最大受害者,但“你”對此視而不見,對父親的寬恕是以對母親的忽視(盡管也多次寫到母親的吃苦耐勞和忍辱負重)或誤解為代價的。而對父親沒有離婚的事實,“你”也歸因于父親“不夠狠”,而未從母親的角度做一點考慮。甚至那個因為父親不倫之愛而被談論的孩子也被以“巴特爾”——蒙語里英雄或神的名字命名,并視作生命的牽掛,可見對父親無限度的寬容已近極致,母親的感覺再次被忽略。
顯然,母女間的這種微妙關系明顯區別于與父親的關系,這樣的倫理結構創設形成了文章內在的矛盾,甚至導致與作者所宣稱的觀念的偏離,與“男人對女人的悔罪”這一被宣稱的主題相左——父親對家庭的懺悔表現在這樣一句話中:“所以你對他說,父親的一生不圓滿,在最后的時刻,他無人深情致謝,也無人對他深情致謝。”僅此而已——它只是人世間女兒與父親的正常關系——那仍然是男權社會里的倫理。作者依舊贊同男人的社會地位,男人是家庭的支柱,以至于父親離家多年及至故去后,女兒仍要尋找母親之外的那個女人以及可能是他們生育的兒子,事實上是對父親的牽掛和行為的認同。甚至對娜仁花,“你”也沒有絲毫的怨言,仍然設身處地地從她的角度為父親愛上她尋找理由,“五十多歲的男人也可以是內心脆弱的,是需要人痛惜的”。由此而往,《禾木》中男性是被女性美化的對象,老沖大爺、小曾和布克賽爾的蒙古男人、北戴河遇到的男編輯,“你”的前夫,他們是那么善良,淳樸,寬容,不計較一切得失,甘愿做“你”傾訴的對象,幫助“你”,在“你”想要時給“你”依靠,唯一有污點的男人是父親——而且他也獲得徹底的、宗教般的寬恕。“你”的彈吉他的丈夫與“你”和平離婚并保持友好的關系,這一情節成為父親與母親關系的反向對照:徒有虛名的婚姻悲劇沒有在“你”的身上上演,這種自我的解放返照的是社會的發展對人性的促進,結束意識形態的禁錮,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感意愿生活的。
我一直在想“你”對待父親與母親的態度,假如“男人對女人的悔罪”得以成立的話,那么只有一種可能:“你”站在母親的對立面,與父親構成了命運共同體,共同向以母親為代表的女人懺悔。但是因為“你”并不能認同母親的生活,所以這種懺悔就變得很可疑。“你”這樣評價母親:“她是多么好的妻子,無人能做到。如是你,你會怎樣?你說,會離婚。”——“你”已離婚流落四方,而“他”并沒有責怪你,在這場分離中“你”對他是心懷歉疚的。從另一個角度講,父親、母親的情感遭遇也成了“你”為自我辯解的方式。作為自足的敘事,我看到其中存在的這些矛盾,但仿佛這些矛盾恰恰才是俗世生活的本來面目,正如福柯所說:“我想讓距我們的目光極近的東西顯露出來,好讓我們都能看見它,它離我們太近,但透過我們所見之物,我們就能看見另一樣事物。”張好好在《禾木》之中顯然站在現實的遠方,與經驗形成距離,才得以窺破屋檐下天天發生的無可言表的感情故事,這樣由遠知近的方法也許對于女性寫作者而言是一種特殊的才能。
四
家庭生活和個人成長經歷是張好好喜歡的題材,她的前兩部長篇作品《布爾津的懷抱》和《布爾津光譜》也在處理發生在阿勒泰布爾津這個地域的歷史和現實經驗。《禾木》出現之后,這一組“布爾津三部曲”在反映時代與人的關系,人生成長經歷,書寫邊地童年、少年和青年生活等方面形成了同題異構。關于布爾津的書寫也成為辨識張好好作品的重要標志。在當下的生活中反顧歷史,通過拉開現實生活與歷史的時間距離和生活地理的空間距離,形成對成長經驗的再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對經驗進行解構和重建,是小說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責任,也是張好好極為擅長的書寫方式。布爾津地處新疆北部邊陲,《布爾津光譜》就曾經將小說展開的背景放置在邊地開發的歷史大幕下,將個人史與民族史和西部的發展史結合在了一起,使得與作者人生經驗有著緊密聯系的私人化敘事具有了宏大的氣象。而在《禾木》中,作者的視野進一步擴大,伴隨“你”的成長與遷徙和父母情感變化過程的,是看到道德敗壞和自然環境被破壞后對人類終極命運的思索。所以《禾木》整體上呈現了人類道德進化和生存發展的困境,其中的“尋找”主題則在困境下深化為回歸的理想,但似乎小說中這些主題之間存在著矛盾。
在對社會生活的描寫中,作者表現出博大的胸懷和博愛的情感,小說中的“你”對男性懷有美好的憧憬,而對同性也保持了足夠的憐惜和仁厚。這一切有一個基礎性前提,即在作者看來,發自人類本能的情感和意志大于以道德和法律為基礎的社會規約,這在本文中已有論述。這是一種超越性的大膽的思想,并不符合傳統道德觀念和政治影響下的社會習俗,這也是《禾木》的特殊之處。在最為基礎的傳統啟蒙讀物《三字經》中,開篇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就已經在使用道德標準評判人性,認為人性最初應該是善的。但是人作為自然物之一種,假如不是后世的道德標準,其行為就將無所謂善惡。在人類的進化發展意義上,自然性先于道德性出現,因而人作為自然物的最本能的權利應當首先得到保護,雖然人性應當遵守道德和法律的約束,但后世的道德和法律并不應該以違反人性為前提。從這個角度上看《禾木》中父親的情感生活,它是一種天然生發的感情,如果不用道德律條去框定,則它沒有罪惡,沒有譴責,它甚至是男女之間必要的情感——作者已經在文本中為這種情感的合理性提供了周到的解釋——也正基于此,作者才可能以寬恕和懺悔來對待“你”父親的這段感情,而小說中所有道德視角下不倫的愛情都帶有浪漫唯美的一面,甚至全部都是唯美的。在這種觀念之下,符合道德要求但是卻違反人性的婚姻就成為罪孽,所以“你”的離婚就有了合法性。所以,當父親和母親為了孩子和一個形式上圓滿的家庭的存在,彼此苦守著一紙名存實亡的婚約,時過境遷之后的“你”重新審視父母之間名存實亡的婚姻關系時,產生替父親辯護、替男人向女人賠罪的想法就不足為怪了。
張好好將情感置于道德之上的嘗試并非空穴來風,而得自她自童年到青年時代就深受到的自然的影響,自然世界里的客觀規律才是作者思想中的律令。從自然地理上看,布爾津仿佛是一個世外桃源,游牧民族信仰中的自然崇拜深刻地影響了作者文化心理結構的形成,所以在作者的筆下,自然永遠是美的,而人類成為丑陋的化身。當“你”離開布爾津到內地闖生活,滿目所及都是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卡萊爾說:“我想我有必要再次說明,自然法是永恒之法:人們決不敢不予理睬這來自我們內心深處的自然法的和平之聲,否則將會受到可怕的懲罰。”但似乎人類已經忘記了這樣的警示。這引發了作者深深的憂慮,很多時候小說就在環境被毀壞、草木被破敗、動物被虐待和屠戮所引起的作者的悲憤中展開。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作者通過不同的角度表達對自然法的尊崇和對當下人類生活的質疑。首先是動植物遭遇滅絕性屠殺和砍伐,“黃羊票”,喬爾泰魚的洄游遭難,長江野生游魚減少,圈養黑熊活取熊膽的殘忍,對刺猬、青蛙的餐食;“如果有一天大樹全毀,即使有大樹,但大樹頂端全部鋸齊,鳥兒無處落足”,“人的心可以壞到見了生靈就殺害”。之后是對物欲橫流的人類發展現狀的反思,作者說:“人類進程的關鍵的一百年,文明到來得這樣迅疾,大地的腐爛來得太快了”,而“人把九色鹿出賣后,這個世界的靈獸就絕跡了”,隨后作者將西天山的美景自然和中原城市做對比,“大家生活在概念里,一句宣言,就糊住了所有的不潔凈,黏稠”。而比這更可怕的,是人類對自我的放縱和對自身責任的逃避,人類的狹隘和自私由此可見一斑:“人們把信任交給了城市的創造者,這個‘者’是誰呢?反正掉下去的不是你,不是他,不是她。反正別人的事,永遠都是另一個星球的事。”“大家都認為自己是無辜的,善良的,只是觀眾,‘者’究竟是誰?”在所有的生態文學中,這樣直接深刻反思自身,拷問人類道德上的“平庸的惡”泛濫的作品,《禾木》是我僅見。
從自然法到人間法,《禾木》宣揚一種“天賦之權”的自然法則,所以作者引用印第安人的古老歌謠來表達對人類終極命運的擔憂:“人類啊,最后你只剩下銀子,而世界的美好全部消失,這錢你能塞進嘴巴里當食物嗎?”但作者所沒有解決的,是如何調節人性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從娜仁花到紡織女工,從鉆進磚窯里的女人到坐到男人腿上的女人,甚至到妖鳥的咒語對“你”的引誘,在作者看來,天然人性的舒張是以俗世生活中的道德敗落為代價的。這是不能簡單地用向往“自由”來解釋的,因為按照斯賓諾莎的說法,“自由人,即只遵循理性指引生活的人”,顯然,他們談不到理性指引,而是受到了“妖鳥的咒語”——欲望的引誘,這恰恰是道德所反對的。只有確證了對道德約束的認同,“你”的懺悔和贖罪才有存在的道理;但假如承認情感的超越是道德衰落的表現,對待父親情感的態度和對父親的寬恕就顯出了悖謬。《禾木》的寫作顯然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所以通過“尋找”而“回歸”的企望變得無所適從。
五

透過《禾木》,連同《布爾津的懷抱》和《布爾津光譜》,我看到了張好好溫婉、澄澈又飽含關懷與悲憫的敘事風格。而這種效果的出現,則來自閱讀《禾木》的另外一個感受:小說仿佛是自作者心底流淌出來的,沒有造作與矯揉,是完全起自自然狀態的心靈表達,它或許是詮釋人生經驗如何升華為文學作品的非常好的例子。盡管第二人稱的寫法令閱讀產生滯澀和陌生的感覺,但私語化的語言又能夠對此有所減弱。而作為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它的故事性并不強,單從“尋找”這個情節本身來看,甚至都不足以構成一個故事,尋找對象的模糊性使這一行動的完整性受到損害。或者尋找本身只是一個框架,懸掛在這個框架上的部分是父母與下一代彼此不同的人生選擇。在作者、敘述者、主人公和讀者之間復雜的倫理結構之內,《禾木》開始從人性和道德的角度展開經驗的批判性審美,因為當中牽涉進大量的成長經歷,尤其是對幽微的內心世界的描寫,使得作品與作者的關系發生無可分離的貼近感,作者在其中借助“你”的身影而顯形。盡管某些觀念的混亂使得敘事邏輯稍有亂象,但保證了小說的客觀真實感。在真實性的平臺上,兩代人無法理清、混沌囫圇的人生被小說濃縮并延展。

注釋
:①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kAY1crWkRVjiWo 9OuQzqHztAaDysI1XRidPB_zes8EUIZ9zMk4K_oqMthkaKPrQ2kqVwyTtededCGIA4YmPn_.
②M.H.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爾特·哈珀姆著,吳松江等譯:《文學術語詞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③王學勤:《論第二人稱敘述存在的客觀性》,《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④鄭克魯、董衡巽主編:《新編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3編,學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頁。
⑤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頁。
⑥福柯:《大師之聲》第1卷,譯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頁。
⑦張好好:《布爾津的懷抱》,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新疆電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版。
⑧張好好:《布爾津光譜》,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⑨卡萊爾著,郭鳳彩譯:《文明的憂思》,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
⑩哈耶克著,馮克利譯:《哈耶克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