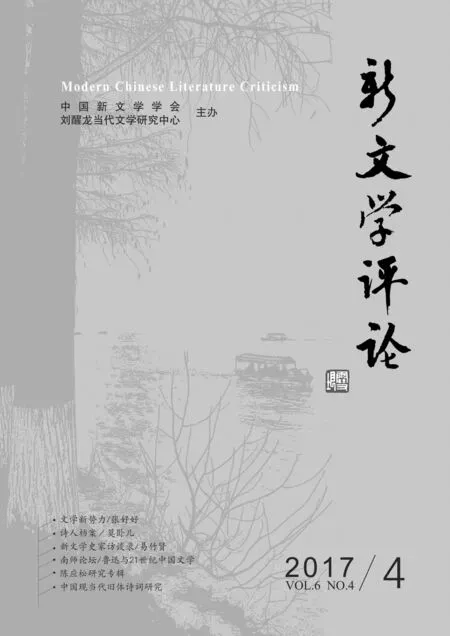創(chuàng)作談:可以撫慰
◆ 張好好
赫拉巴爾在他的自傳意味的長篇小說《甜甜的憂傷》里,興致盎然地寫他童年家庭里的兩只大貓兒、他的大伯父,還有啤酒廠里的許多故事。我在老漢口地鐵的來回里讀來讀去,愛不釋手,后來給最親密的幾個人都買了,仿佛硬塞給了他們。
我把這種閱讀心情叫做生活的況味。因為怕現(xiàn)今的我們沉溺于復(fù)制粘貼的雷同分秒,所以一定要返身去閱讀,上至三皇五帝風(fēng)里遺留的話,下至滴答眉前出現(xiàn)的好作家寫下的字——捉回真誠和美,躍動的空靈能夠輔佐我們不要丟失想象和超然。這樣的撫慰,心靈需要。
一種貴族式的心靈享用。生命難道不是用來享用的么?停佇下來,在山雨欲來風(fēng)滿樓的樓中,在一壺油綠的日照綠茶前,在一尊端莊的玉像前,在三只貓的溫柔審視里,在前半生的輾轉(zhuǎn)和韌性里,在腦海里能夠記憶起來的所有善良人的面影里,一個寫作的人,她是否不茍且寄生和虛榮——她能夠為偌大宇宙、月亮、人世奉上什么呢?
我曾經(jīng)在一首詩里寫下這些個句子:
宇宙的幼牙,星星們——彼此無言——誰能辨識清楚何為永在?
大歡喜和大悲傷——你們無憑無據(jù)!
只默然遴選了三樣活著的依據(jù):真、善、美。
我捉筆為刀,為人世奉上的正是它們?nèi)唬妗⑸啤⒚馈?/p>
然而只有真善美,并不構(gòu)成文學(xué)所必須加持在身的經(jīng)典性。還需:常習(xí)舊莊嚴。
這是佛經(jīng)用語。文學(xué)是藝術(shù)眾多門類中的之一。藝術(shù)最大的特征是雋永,也就是耐品。世界上所有尊貴的事物都是純真、堅韌并莊嚴的。比如天空和星子。比如樹木和眾鳥。比如小獸的心靈和眸子。
人類心靈一旦被物化,即使作為作家,也是物化的作家了。物化的作家最大的特征就是以會講故事、奪消費群體的關(guān)注為榮。以文學(xué)作品最終能夠產(chǎn)生諸多衍生機遇為目的的講述,一步一微瀾,三步一跌宕,十步一高潮。技術(shù)、機巧充斥人心的時候,百泉廢殆。吃著薯片津津有味看書、看電視、看電影、打游戲的人類的烏泱泱,心靈已被物化的作家對此應(yīng)該有羞愧心。
據(jù)統(tǒng)計,藝術(shù)家在整個人類中的比例,可以用稀世這個詞語來描述。惶惶然如喪家犬。當年的孔子在城門的黃昏中不停地徘徊,抑或是傻傻的安靜。不單單是等學(xué)生把他找到,帶他去一席溫暖的地方休憩,更是他在內(nèi)心里想:吾一介書生對于全人類究竟有何用呢?
我們這些進入可以掌控自己命運的時段里就開始以碼字為一刻不息之己任的人,內(nèi)心里何嘗不常常想,吾這么寫啊寫,肩不挑手不提,孱弱如蟲,傲嬌如貓,何等惴惴啊,去那黃昏中徘徊吧,若喪家犬吧。
木心的詩歌:尤其靜夜我的情欲大紛紛飄下綴滿樹枝窗欞……因為第二天又紛紛飄下更靜更大我的情欲。
其實不是情欲大,是情感大。“我的心略大于整個宇宙。”佩索阿的感慨。
如此豐沛旺盛的情感,思索復(fù)思索,化成奶、化成血,變成字,一行行、一頁頁、一本本地條分縷析,把正確的生命滋味端上來。蕭紅的呼蘭河和生死場,她的文學(xué)態(tài)度是不服務(wù),不迎合,不投機,不蹩腳,不假裝。
她說過:黃瓜愿意開一個黃花,就開一個黃花;愿意結(jié)一個黃瓜,就結(jié)一個黃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jié),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愿意長多高就長多高,它若愿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地飛,一會從墻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墻頭上飛走了一只白蝴蝶。它們是從誰家來的,又飛到誰家去?太陽也不知道這個。只是天空藍悠悠的,又高又遠……
生命本來的樣子、真善美本來的樣子、一個寫作者拙樸的慧心理解的人世的本來樣子。如同一個每天早上起來就灑掃、劈柴、挑水、煮粥的小沙彌,他在寂然的山林古寺里如此修行,這本身就是對全人類的超度。你聽木魚聲,清越激昂,上達宇宙的天心,下通人心。一切無為皆為有為。這句話我們聽懂了么?
在物欲這潘多拉魔盒中迷失的全人類,那稀世的巋然不動者,不可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