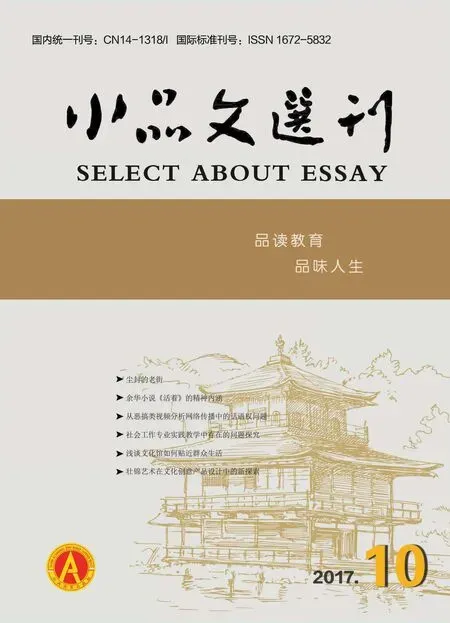西方知識人眼中的東方藝術
——蘇立文的三部藝術史的三個觀念
姚紹將 陳明春
(貴州凱里學院 貴州 凱里 556000)
西方知識人眼中的東方藝術
——蘇立文的三部藝術史的三個觀念
姚紹將 陳明春
(貴州凱里學院 貴州 凱里 556000)
“藝術界的馬可·波羅”邁克爾·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的《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國藝術史》、《東西方藝術的交會》相繼被介紹到國內,蘇立文以西方學人的眼光讓國人享受了到東方(主要是中國和日本)視覺藝術盛宴。中譯本除了有著流暢的譯筆,精致的封面與裝幀設計,以及許多新的翔實考古材料的運用外,還有如下幾個藝術史觀。
1 沒有中心的藝術史觀念

世界藝術史都是有著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貢布里希著名的《藝術的故事》,把絕大多數的篇幅都留給了對歐洲藝術的描述,在亞洲藝術方面只是寥寥幾筆、惜墨如金;詹森《詹森藝術史》全史就沒有東方藝術的容身之地。這些著名藝術史家對藝術的觀點幾乎代表了西方學者眼中的東方藝術、中國藝術的主流觀點。因此,他們的藝術史都顯得美中不足,僅僅是“粗暴專橫”的“殘篇”。而蘇立文并沒有表現這種西方或歐洲中心的藝術觀念,他相信中國古代藝術依據中國思想文化觀念長久發展,譬如他講到“和諧感是中國思想的基礎”(《中國藝術史》,第4頁),逐步展開中國藝術史,將發現“其特性和獨具之美就在于和諧感的表達”(同上);蘇也指出東西方藝術存在著一個相互交流的過程。而發展到現代的藝術事實表明日本、中國都有一段時間如饑似渴地學習效仿西方,蘇立文也貢獻了描述西方藝術工作者十分狂熱地搜集中國與日本的藝術作品資料。指出東方藝術家很快轉化、創生為表現中國人、日本人、東方人情感的本土藝術。蘇立文在描述中習慣把中西藝術進行比較,然而他并不作如其他藝術史家那樣明顯的價值判斷:西方藝術是優秀的杰作,而中國藝術可有可無。在談到1990年代以來中國藝術表現出的活力時,蘇立文稱那似乎預示著中國將在21世紀的世界發揮主導作用。
蘇立文是一位藝術史家,漢學家,但也同時是一位著名的人道主義的和平使者。最初到中國,年輕的蘇立文是作為一名為國際紅十字會工作的使者,在戰亂中“駕駛著卡車,載著醫藥用品”穿梭來往于大西南的各家醫院。其妻子吳環當時也在為紅十字會工作。隨著蘇立文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文化,并于國內很多藝術家成為好朋友。他藝術史就是以一種“角色換位”來看待中國藝術的,國內對中國藝術的研究可能是當局者迷,而當與“事發地點”拉開一定距離,轉變角色來思考,那么看待的問題會是另一種局面。蘇立文尊重中國人按王朝更替序列認識自身歷史的習慣,把握中國人自身哲學文化基礎與對于中國歷史的認識方式,譬如中國人深厚的歷史感,人與自然順應關系等。這就是一種內在邏輯生發機制來看待中國藝術發展史。而不是其他西方藝術史以西方正統藝術理念來觀照中國幾千年的藝術。他認為,中國的藝術形式因為身處最廣泛、最深刻的和諧感之中而極度妍美,我們之所以能欣賞它們是因為我們也能感覺到自身周圍的韻律,并且能夠本能地回應它們。這是一種中國藝術的生命體驗與生命精神,蘇立文已經能夠體驗到了,這也正是他非西方中心的藝術經驗。在蘇的藝術史描述與闡釋過程,也是他生命體驗過程,在精彩之處,贊嘆不已,感嘆號就是其情感之顯山露水。如談到兩宋禪畫時,驚嘆道“所有杰出的禪宗畫的共同特點是畫家通過細致地描繪某些關鍵細節,虛化其他不重要的部分的方式吸引觀眾的注意力,這不正是冥想本身嗎!”(《中國藝術史》,第204頁)在主張以沈括評論宋代花鳥畫“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徐熙以筆墨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氣。”蘇立文說“這真是真知灼見啊!”能夠體驗到中國藝術神韻,并非就是西方藝術作品的那種觀看邏輯。

在東西藝術交流中,研究者越來越相信,亞洲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是世界歷史上自文藝復興以來意義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蘇立文認為東西藝術交流是自然而然的事,這是所有事物發展都必然經歷的過程。歐洲藝術對東方藝術的影響不一定就是積極的,可能是破壞的而非建設的。并非每一位藝術家汲取了西方影響,就變得有活力。比如傅抱石現代文人畫比徐悲鴻畫得更好,但是傅幾乎沒有留下什么西方藝術的影響痕跡。在視覺藝術方面除了電影,“真正的、富有成效的相互借鑒的時代還沒有到來。”例如,他比較中國與日本接受西方藝術影響的不同態度,將其歸因于中日兩國不同的文化傳統。內在邏輯的傳統猶如無法選擇的出身,即使是“傳統的發明”也深受其影響。在三部著作中蘇立文都把藝術放置在宏大的國際視野來看待,那么比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方法。《中國藝術史》中,也經常比較研究中國藝術與印度、日本及西方藝術的類似與差異,在比較中凸顯中國藝術的特色。《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對中國藝術接受西方寫實主義和現代藝術影響的分析。他說明:“本書的主題是有關在西方文化和藝術的影響之下,中國藝術在20世紀的新生。兩種偉大傳統的相遇,已經為中國藝術帶來了難以估量的震動。”在《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中蘇立文以詳細的圖像資料與文字材料比較研究了從16世紀到20世紀西方藝術與東方藝術(主要是中國和日本)的交互交流。蘇認為中西交流是相互的,但是中國、日本與西方思想文化有著自己內在思想根基,日本藝術很快適應西方藝術的節奏與改造,而中國藝術并沒有,至今也是存在著平行的兩條發展線。這是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根基有關的,在西方的日本藝術家很快就完全西化,但是中國藝術家并沒有,而是在心里依然固守著中國藝術的某種“精華”。蘇立文以自己親自接觸的劉國樞等藝術家來證實了這些趨勢,而形成這樣的看法又是那么的精辟。并且指出這只是時間問題,西方人在鑒賞、模仿與汲取中國藝術,尤其是傳統藝術時,需要一定時間。蘇立文并不認為西方或歐洲藝術的中心,而是以平視的眼光,一視同仁。
2 沒有理論的藝術史寫作
20世紀是一個“批評的世紀”,而批評的你來我往皆以建造或套用各種理論話語,再則隨著西方各種哲學思潮風起云涌,20世紀更是一個理論與概念帝國的時代。蘇立文曾說道,當他被質問是從什么理論角度看待中國現代藝術?他說他沒有理論。“我懷著最深的信念相信,如果是在人文學科中而不是在精確的科學中,理論,遠離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發現真相的障礙。它們無法被檢驗。藝術中的理論如同一連串的有色鏡,我們手持著有色鏡去看現實,不會看到我們原本看不到的東西。它們模糊了許多東西,以至無法看清楚整幅畫卷。”(北大演講)并建議年輕藝術史家,僅僅把理論作為幫助理解藝術史概念的一個援手。蘇立文把這樣的觀念執行在了他的藝術史寫作與研究中。除了他對中國藝術的喜愛和中國藝術家的深厚友誼之外,我們沒有看到藝術理論或美學思潮對藝術及藝術史的操控。
蘇立文的幾部著作都有著圖文并茂、樸實敘事的特點。從歷史文明的曙光到21世紀的視覺經驗,從歐洲文明到東方文化,上萬年的歷史圖像故事,都猶如傾聽一位飽經風霜、無比睿智的老者把那人類的故事,圖文協和,相得益彰,生動形象地娓娓道來。一種理論亦如一副眼鏡,帶上不同的眼鏡影響著主體(講故事的人或敘事者)對對象或被敘事者的觀看。人們直觀地發現,蘇立文基本上采用了實證、描述、陳述的方法,并非擺先驗形而上學的理論思辨或假設的固定模式,三大部藝術史模式都以搜集經驗材料,通過觀察、調查、訪問、文獻梳理等方法獲取經驗證據,對事實加以分類、比較和歸納,以求得客觀的認識和科學的結論。圖片資料與參考文獻有的來自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的博物館,有的來自美國的博物館、英國的博物館、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俄羅斯、德國、法國、瑞士、日本的相關博物館,另有些圖片甚至來自于收藏家、經紀人,及他自己的收藏。蘇立文對文獻資料處理就顯示一種扎實的功夫,值得尊重。“史料即史論”,在宏大敘事、國際比較視野與作品細部解析中,蘇立文幾乎都沒有對美學理論或藝術理論思潮花過筆墨,只是順便帶過。那也就意味著不可能陷入美學理論的沼澤地中。蘇立文這種“沒有理論的藝術史”的寫作,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國內都是一盞指路明燈。理論常常也是一種“行業黑話”,其抽象、思辨的特點往往拉開了與閱讀者的距離,而蘇立文采取這種質樸、材料經驗的藝術史,通俗易懂,而且令人信服。
值得一提的是,蘇立文以大家氣度尊重中西方思想文化傳統的大模式范式,這是中西方藝術產生的根底,而藝術交流與發展,蘇立文并沒有生搬硬套上各種歷史哲學理論與美學理論思潮。他認為東西藝術的相互作用,或許是藝術自身的,偶然的或政治、經濟、宗教壓力的副產品,而闡釋僅僅運用“沖擊—回應”的幾乎生物生理學的模式。當然,肯定不能臆斷蘇立文對各種哲學美學思潮一無所知或不甚了解。反之,他是深諳理論的,并指出理論可能遠離真相,產生偏見。他懷著一種強烈的求知欲和對理解的渴望來理解東方藝術和中國藝術。理解是一種高貴的語言,是心靈寬恕的珍貴精神。離開了理論的拐杖并非無法行走,蘇立文的三部藝術史著作給了我們一種答案:沒有理論反而行走的更踏實,獲得更多的理解。他強調自己是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東方藝術,誤解難免,要完全克服民族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個人好惡的偏見,幾乎不可能,所以只能迫近真相或真理。他也以文獻材料為核心保持價值中立,盡量避免意識形態的偏見,但不缺失人道主義的情懷。他藝術史以最習以為常的歷史時間和精確的文獻資料來呈現客觀藝術事實史,遠遠跨越了以某種理論觀念來選擇材料與圖像進行分析敘事方式。沒有理論的“眼鏡”,蘇的藝術史評估也展現了客觀性。如盡管他對“文革”時期破壞文物的現象深感痛心,但是也指出毛澤東時代對文化遺產發掘與保護,做得比過去更多;關注藝術家的不幸遭遇,如石魯、吳大羽等;也批判西方對中國現代藝術深刻的偏見,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術界才把中國現代藝術列為嚴肅對待的研究課題。另外,他對中國傳統繪畫、藝術革命、日本藝術在歐洲的接受、對大藝術家等等均給以比較客觀的評述;如評價徐悲鴻,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一個理想主義者和一個浪漫主義者,在藝術技巧和目的的嚴肅性方面,為學生們樹立了崇高的典范。“他真誠地相信他的學生所需要的不是根基膚淺的現代派,而是西方技巧的堅實基礎。”這種態度是比較公允。
3 沒有斷裂的藝術發展史
蘇立文并不承認歷史經驗存在絕對斷裂。西方現代藝術研究的學者基于現代工業與技術革命的特點:在物質生產中體現為現代化,在思想觀念心性結構體現為現代性,而提出人類歷史的斷裂,現代藝術與古代藝術是急劇斷裂的,并且提出“新藝術史”。蘇的藝術史是時間連續的,空間上交互的。藝術是在內在與外在,過去與現在的交流、碰撞、沖擊與反應中不斷發展,藝術發展與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宗教密切相關,這樣才構成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藝術史。
《中國藝術史》材料豐富,恪守政治王朝的分期序列,一氣呵成。蘇立文呈現給我們一部從石器時代、夏商周到秦漢到21世紀初,包括瓷器、青銅器、書法、繪畫、建筑、園林、雕塑、瓷器、漆器、絲織品、服裝等豐富多彩的視覺藝術史。歷史沒有如刀切般斷裂,是以多條線索交互,曲線連續地發展著歷史。中國與日本的藝術都離不開社會各方面的綜合因子。比如說中國畫,蘇在幾乎中國畫產生后每個時期都曾講到這個問題。即使是20世紀現代藝術風起云涌中,中國畫畫家始終在進行著創作,國畫依然大量存在。而且那種中國傳統根據性的東西依然在創生在保持著生命力。一逢相對的時機又可能蓬勃發展。20世紀80年現代藝術飛速發展,國畫也出現再生。蘇立文在描述20世紀中國藝術的時候也以“傳統的繪畫”起始的。雖然在國內因落后的緣故,一浪又一浪地激起向西方學習,提出全盤西化的熱潮,但是蘇立文從西方外圍或許看得更清楚:即使在內憂外患之際,中國人有某種透在骨子里的看法,中國從不認為歐洲藝術有助于現代化,如果他們對西方文化有認知的話,西方文化和西方槍炮一樣,都應遭受到敵視和否定,文化摩擦和沖撞問題因因而凸顯出來。而蘇立文認為傳統與現代,國畫與西畫之間古老的辨爭并沒有解決,或許根本就無法解決。他在北大演講道“20世紀的中國藝術家用各種風格和媒材工作,本土的和進口的,只是選擇對他們最合適的。如果他們表達的是中國人的思想和情感,不論他們用什么風格或技術,他們的作品都是中國藝術,他們的藝術是否是‘中國的’或‘西方的’,不再是個問題。”或許是一個理解之法。一旦中西藝術達成綜合,那絕不是一個不同技法相結合的問題,而是藝術家雙重經驗內心化之后的一種處于自然和自發的自我表現的形式。(《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序言)

不作飛躍的、連續的藝術史也是西方傳統的藝術史觀。在各個時代歐洲公眾視野中中國畫是他們最為常見的,而國畫之外中國現代藝術是不被認同,那也似乎在暗示中國藝術史并沒有發展,現代藝術不值得一提。而蘇立文的沒有斷裂的藝術史觀,以結合中國或日本現代化社會進程進行敘事,現代是對傳統的賡續與銜接,那是自然而然形成過程。由此觀之,蘇立文的幾部著作其實已經證明了他從未相信存在無歷史之事物,人類思想文化的結晶無不來自前人十整、百整的累積。東西方的現代藝術也更不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怪胎,它肯定生長于傳統積累與現代境況的歷史中。任何歷史都是一種綿延不絕的流動,而蘇立文采用分期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以便把握中國人自身對于中國歷史的感覺。而《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也依然遵循的是一種連續性的東西交互敘事,以新穎而詳細材料按線性描繪了西方藝術與東方藝術的交會始于宗教傳播、商品交流等等的歷史。
J0-03
A
1672-5832(2017)10-0185-03
姚紹將(1987-),男,苗族,貴州天柱人,凱里學院藝術學院教師,2016年畢業于南京大學,獲藝術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視覺文化、民族民間藝術研究;陳明春(1987-),男,侗族,貴州榕江人,凱里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教授,民族藝術家,研究方向:民族民間視覺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