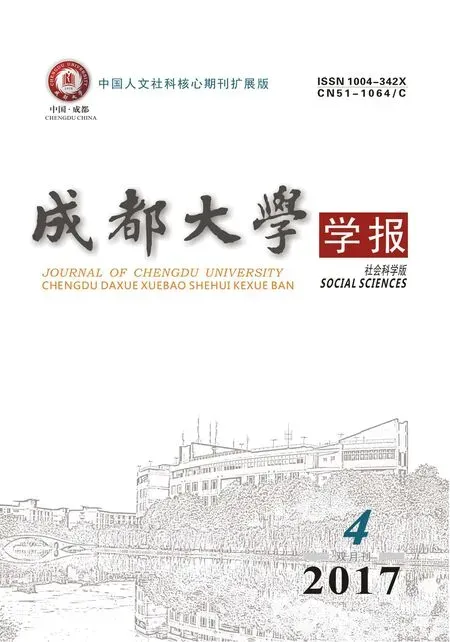宋元之際詩論家的陶淵明論
薛寶生
(成都大學 師范學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文藝論叢·
宋元之際詩論家的陶淵明論
薛寶生
(成都大學 師范學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與宋金諸人相較,宋元之際諸論家對陶淵明的討論,在沿襲的基礎上又有所拓展延伸。其一,在肯定其氣節時,流露出深閔其志的心態。其二,綜合前人之言而稱道其知道任真的生活態度及高逸情趣。其三,與前人相較,進行了一個新話題的討論,即對后世詩人“和陶詩”的討論。此外,諸人也肯定其對后世詩歌創作的開枝散葉之功。
宋元之際;陶淵明;和陶詩
宋元之際論家言陶淵明,于其人其詩多所推重。觀其所推重的內容,則淵源要追溯到北宋,歐陽修、黃庭堅、東坡、王安石,①以上諸公皆就其詩而論。特別是王安石論陶,許之以“晉、宋之間,一人而已”。南宋理宗端平以前(即本文所謂“宋元之際”以前),葛立方、朱熹、真德秀等人也對陶淵明其人其詩作了評價。葛氏稱許淵明不事二姓的志節②,朱熹以“豪放”定位陶氏其人及其詩,也盛稱其氣節③,真德秀則對其人風度志節及其詩中經書之旨作了探討④。金代論家對陶淵明的稱詠主要在于兩點:一是其不事二姓的氣節,二是其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及高逸情趣。⑤大抵北宋諸人多重其詩,南宋前期諸人多稱其節復贊其詩,金代諸人多嘉其氣節、道趣。而宋元之際諸論家對陶淵明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匡晉之志、拒宋(劉宋)之節,知道任真、悠然之趣,和陶之難、東坡尚可等方面。
一、既高其節,復閔其志
宋元之際諸人對陶淵明的討論,傾向之一便是“既高其節,復閔其志”。
其一,對其氣節的肯定。宋亡之前,士人對淵明氣節的肯定多沿世之常談,稱其“恥事二姓”、“不書宋帝年號”等。如:劉克莊《趙寺丞和陶詩》云:“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1](卷九四)宋亡以后,士人對陶淵明氣節的肯定則富于現實意義。以往只是在心理上崇拜,宋亡后卻要在實際行動上效法陶淵明而不事新朝,其對陶的褒獎也是對自己的鼓勵和褒獎。如方夔《九日讀陶淵明詩》云:“晉有靖節翁,古昔稱高士。自陳簪組后,為義不兩仕。……醉余灑新詩,題自庚子始。托此明大閑,言外有余旨。”[2]369


而鼎革之際,陶淵明也確是士大夫靈魂的寄托處。舒岳祥《四月六日絕糧用銀盞易谷作詩別之》云:“已悟興亡理,空留物我情。不知陶靖節,何物了平生。”[5]375舒氏對歷史興亡之理已看淡,而內心深處對大宋的眷戀之情卻未泯,而此處借對“銀盞”的惜愛之情出之。“不知”之句,則明確說明如果不知道晉宋易代之際尚有陶淵明的活法,則自己漫長的生涯便無所寄托。

宋末番陽湯漢《陶靖節詩集自注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于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荊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于后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嘆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亦并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7]473湯氏與前面諸人盛稱淵明節操略有不同,不僅肯定其不事二姓的高節,亦能深挖其志(即“深懷”),他認為陶氏既不能像張良招勇士擊秦皇那樣去為晉室報仇,也沒有像張良遇漢高祖那樣遇到雄主,故其志向不得伸展,因而輾轉詩中,以吟詠歷史人物來寄托自己的深懷。湯氏并為其志業不得伸展、空有匡時之志而感到惋惜。
后來劉岳申、吳澄又對湯氏的說法進行了拓展,對比對象由張良延及屈原、諸葛亮。
劉岳申云:陶淵明本志不在子房、孔明下,而終身不遇漢高皇、蜀昭烈,徒賦詩飲酒,時時微見其意,而托于放曠,任其真率,若多無所事者。[8]180-181(《張文先詩序》)吳澄云: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征士,是四君子也。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略伸志愿者,其事業見于世。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托之空言以泄忠憤。……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復仇,無可以伸其志愿而寓于詩,倘使后之觀之者,又昧昧焉,豈不重可悲也哉![9]227(《陶淵明集補注序》)
劉岳申徑直言“陶淵明本志不在子房、孔明下”,較之湯漢則直接坐實了陶淵明有匡扶晉室的志向,指明其有是志,只是苦于不遇漢高祖、漢昭烈那樣的雄主而已,所以才“托于放曠任其真率,若多無所事者”。將雄深之志寄于看似淡泊的言辭中,這樣是為了掩蓋其志。吳氏在發明陶氏之志時,又加入屈原。認為此四人“明君臣之義”,不事二姓之心是一致的。且屈原、淵明為“末如之何者”(即不得伸志愿者),并認為屈原死宗國,與淵明歸隱其意實同,均是無可奈何者。故“不得不托之空言以泄忠憤”,言語之中流露出了無限的同情意味,也流露出了對其壯志不得伸展的惋惜之意。
二、知道任真,悠然之趣
北宋時,東坡就曾指淵明詩為知道之言。⑥而南宋中葉魏了翁則發陶詩悠然之趣,認為其“以物觀物而不牽于物,吟詠情性而不累于情”。⑦宋元之際論家在討論陶淵明時則并有兩者,多以“知道者”目之,謂其能安貧樂道,與世無競,有悠然自得之趣。

“知道”則任真,“真”有順其自然之義,亦有忠義之情。宋末王應麟《評詩》云:“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遠則遠,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于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12]1892王氏先引淵明詩中標舉“真”的詩句,次引東坡言,以證明陶淵明確實“知道”而能任真。后又提及諸人對陶詩的苛責,也就是說,諸人以人事責之淵明,而不能察淵明之“真”。“韓子蒼知之”,則是云韓子蒼能識得淵明“忠義”之“真”。⑧也即是說,王氏認同韓子蒼關于陶詩“真”含“忠義”之說法。

可見,宋元之際諸人能兼取前人之言,而稱道陶氏知道任真,并認同其有順其自然之“真”,亦有忠義之“真”;稱道其悠然之趣,并發明此趣直與莊周幾同。
三、和陶實難,且饒東坡
宋代“和陶詩”當起于蘇軾兄弟,郝經《和陶詩序》云:“獨東坡先生遷謫嶺海,盡和淵明詩,既和其意,復和其韻,追和之作,自此始。”[13]62此后和陶者多矣。高才如蘇軾“遍用其韻”,下者也有斤斤和得一兩篇者。較之宋元之際以前的論陶,宋元之際諸人于“和陶詩”的討論可以看做是論陶的一個新方向。而論“和陶詩”主要集中在“東坡和陶”及和陶的條件探討,且諸人多稱許東坡和陶,鮮有論“和陶詩”而不及東坡者。



又柴望《和歸去來辭》云:“陶靖節辭豈易和哉!《歸去》一篇,悠然自得之趣也。無其趣,和其辭,辭而已。坡仙之作皆寓所寓,各適其適,有趣焉,不為辭也。余動心忍性,于歸田之后,視得喪榮辱,若將脫焉。暇日趺坐柳蔭,吟詠陶作,與灘聲、風籟互相應答,知山水之樂,不知聲利之為役也,悟而得焉,遂和其韻。”[14]487柴望認為和陶詩不易,和陶詩的關鍵在于識得淵明悠然自得之趣,不識此趣,只能得其文字之表。而東坡的和詩和淵明詩中表現出悠然情趣一致,人、物皆有寄托,皆能安于自然的生命狀態。最后他描述了自己的修養狀態,能擺脫榮辱得喪,不為聲名利益左右,所以也和得陶詩。柴氏所論,亦如劉克莊所指出的一般,和陶必須修養境界要及淵明才行。
事實上,陶氏已矣,陶意已遠。和陶終究是有心為之,不似陶氏一任悠然。和陶也不過自寄其趣,借他人酒杯澆己之塊壘。如黃震云:“陶詩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真機自然,直與天地上下同流。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15]551又劉岳申《張文先詩序》云:“而和陶效韋,高者不過自道,下者乃為效顰。”[8]180-181
四、結語
綜上,宋元之際論家的陶淵明論主要集中在志節、道趣、和陶三方面,且較之前人多有延伸拓展。除此之外,論家也多言及陶淵明對于后世創作的開枝散葉之功。如劉克莊《趙寺丞和陶詩》云:“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得其遺意。”[1](卷九四)又舒岳祥《劉正仲和陶集序》云:“自唐以來,效淵明為詩者,皆大家數。王摩詰得其清妍,韋蘇州得其散遠,柳子厚得其幽潔,白樂天得其平淡。正如屈原之騷,自宋玉、景差、賈誼、相如、子云、退之而下,各得其一體耳。”[5]425劉氏、舒氏明確地指出陶淵明的開枝散葉之功,認為王維、韋應物等各得陶氏之一支脈。
注釋:
①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錄北宋范正敏《遁齋閉覽》之語,廖德明校點,前集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18頁。
②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五云:“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邪!” 見何文煥:《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第530頁。
③朱熹云:“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又朱熹《向薌林文集后序》云:“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后代,雖事業不概見,而高情逸想播之聲詩者,后世皆自以為莫及也。”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六,四部叢刊本。


⑥葛立方《韻語陽秋》云:“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摘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睹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見何文煥:《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第507頁。
⑦魏了翁《費元甫注陶靖節詩序》云:“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于物,吟詠情性而不累于情,孰有能如公者乎?”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四部叢刊本。
⑧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后》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所為也。’余反復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嘆,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廖德明校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第19頁。
⑨《孟子·告子下》云:“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茍去。”見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30頁。
[1]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M]//四部叢刊本初編本.
[2]方夔.富山遺稿[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89冊.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4]鄭思肖.鄭思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舒岳祥.閬風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87冊.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6]真德秀.西山文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74冊.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7]陶淵明.陶淵明集[M].龔斌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8]劉岳申.申齋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04冊.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9]吳澄.吳文正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7冊.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1]羅大經.鶴林玉露[M].王瑞來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王應麟.困學紀聞[M].翁元圻注,樂保群等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郝經.陵川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2冊.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4]柴望.秋堂集[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87冊.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5]黃震.黃氏日抄[M]//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08冊.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責任編輯:劉曉紅)
2017-02-15
薛寶生(1984-),男,成都大學助理研究員,博士。
I207.22
:A
:1004-342(2017)04-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