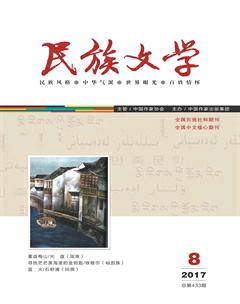光棍的房子
韓靜慧
一
村民們都說,蒿子溝最有福的光棍就是老甘圖。
因為蒿子溝老少加起來就三個光棍,唯獨老甘圖今年住上了政府給蓋的免費房子。
甘圖的房子蓋在村西口,在村子中間那條主路的邊上,因為沒有圍墻的遮擋就格外顯眼,每個進村子的人第一眼都能看見這兩間漂亮的房子:白瓷磚墻,紅瓦屋頂,白色塑鋼窗子,里里外外四白落地,亮亮堂堂。
于是村里就有人生氣:
“他炕頭上睡著女人,憑啥算光棍?”
“蓋了房子也不住,這房子純粹是給那‘爛板凳蓋的。”
“這不是騙取國家資金嗎?”
村民劉三也羨慕嫉妒恨,但他的恨只在心里裝著,從不用嘴巴表達,誰也看不出他真正的心思。他見著老甘圖照樣點頭哈腰地招呼二哥,一臉謙卑的微笑。他歷來認為自己在蒿子溝三組是最有品的人,不能跟一般的村民那樣沒事罵大街。
劉三有自己恨人的文明方式——告狀。他三天兩頭去代理村長(村民對村主任都稱村長)陳波那兒告狀,但一回來就裝作啥事都沒發生。
陳波為什么是代理村長?因為這個村的村長甘文只干了一年就被村民劉三拉下了馬。劉三當初也想當村長,但他的實力不如甘文,人家甘文競選那天給每個村民補助誤工費二百元,而劉三只拿出了區區一百元!更讓劉三始料未及的是,競選那天甘文把所有去外地打工但戶口仍在蒿子村的村里人都一一請了回來,連跟隨兒女住在城里的那些耳聾眼瞎的八九十歲老婆子、老頭子也都用小轎車像接祖宗一樣恭恭敬敬地接回了蒿子村,甚至兩個中風癱瘓的病人也用擔架抬了回來!這小子真是賊呀,一票都不想放過,還美其名曰:要尊重所有村民的選舉權!盡管劉三在會上把蒿子村的未來藍圖描繪得比玉皇大帝住的天宮還美好,還唾沫飛濺地許了一大卡車愿,承諾出去招商引資把蒿子村那滿山坡的蒿子都兌換成金條……但仍沒有幾個人相信他的那些狗屁蒿子夢想,村民們把票都投給了那個在城里發了點小財的甘文,甚至幾個劉姓家族里的人也見錢眼開臨陣當了叛徒!甘文高票當選,劉三損失了不少錢,把氣都撒到甘文身上,選舉結束后他不但處處給甘文找麻煩,還天天去鎮長辦公室上班,告甘文賄選。
2015這一年鎮政府辦公室的門檻都讓劉三給踏平了,搞得鎮長不勝其煩,只好派了個工作組去蒿子村調查甘文的賄選情況,這一調查還真調查出甘文給村民二百元錢的事情,雖然錢不多,但畢竟也是錢,所以鎮長大巴掌一揮,就把甘文給揮下臺去了。甘文本想回家鄉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干,但經過這一折騰,對生他養他這塊土地上的人很失望,又回城里掙自己的省心錢去了。甘文下去了,讓誰去當這個村長?總不能讓這個一肚子小算盤的劉三干吧?何況你告人家賄選,你自己不是也參與賄選了嗎?
鎮政府為蒿子村琢磨了半年村長也沒琢磨出來,像樣能干一點的中青年都去城里打工了,誰也不回這個地處高原的塞外小村子,剩下的不是有這個缺點就是有那個毛病,稍微聰明一點的也都自己搞點養殖,有的村民還公開跳出來瞎嚷嚷:今年中央管得嚴了,不允許隨便征地了,沒好處誰愿意去操那些閑心,不如自己掙點省心錢……
就這樣蒿子村的村長位置空缺了半年,鎮政府非常著急,于是就派街道司法所的所長陳波到蒿子村臨時兼任村長。
陳波戴著一副白邊的眼鏡,白白瘦瘦的身材,文文弱弱的氣質,一看就是個長期坐辦公室的,沒在農村牧區摸爬滾打過。
這陳村長聽了劉三告的狀,就悄悄地跑到蒿子村微服私訪,他把臉貼在老光棍甘圖小房窗玻璃上往屋里窺視,想看看里邊到底有沒有女人。這時辰正是農牧民們在家吃晌午飯的時候,村長是專門挑這個時間來的。因為他覺得如果這個房子里住著人,這個時候就能一目了然。
村長這一看不得了,里邊不但沒有女人,連男人都沒有。共計兩間屋子,一間堆滿了鎬頭鐵锨鐮刀馬鞭馬鞍子等農具,另外一間屋關著一匹馬,那馬本來正安靜地低頭吃草,聽見動靜警覺地抬起頭來,將那傲慢冷漠的大馬眼投射過來,也許它以為這個自己從沒見過的白面書生要侵犯自己的領土,是的,這房子從一蓋好主人就把它從那個四處漏風漏雨的臭棚子領了出來,領進了這個亮亮堂堂的新房子里,這是它的島嶼,主權歸它,除了它的主人能進這個領地,別人都無權進來,即使是臉蛋子貼在玻璃上張望也具有偷窺的可恥企圖。是可忍孰不可忍,維護領土完整是自己的責任,大白馬瞪圓兩只鼓鼓的馬眼用鼻子憤怒地向外噴氣:“噗噗噗——噗噗噗”,大白馬噴出來的氣將馬槽里的草吹得飛起來,也把本來很干凈的窗玻璃弄得霧氣蒙蒙的。
陳村長心里的憤怒也不比大白馬的憤怒小到哪里,好呀,政府給光棍蓋的亮亮堂堂的好房子現在成了馬棚,怪不得這劉三盯著這件事沒完沒了!人家就是告得在理!這還了得,如果這事自己不解決,將來真查下來,自己吃不了也得兜著走。
陳村長氣沖沖地找來這個村的村民小組長,劈頭蓋臉的就是一頓大罵:“政府給錢蓋的房子是給人光棍住的,不是給馬光棍住的,你們村的馬怎么他媽的這么金貴,那個什么甘圖老光棍既然有住處,既然有女人,你們為啥還要打報告把他當成光棍讓政府拿專項基金給他蓋房子?他現在在哪里?如果他真不需要那房子就立刻沒收給村子里其他的光棍住。”
陳村長劈頭蓋臉的一頓大吼把蒿子村三組組長嚇得膀子都斜了,這代理村長別看長得文文弱弱的很奶油,脾氣還真不小。
三組的組長平日說話本來就結巴,這回更結巴了,好在人還算聰明,說話咬骨頭,他結結巴巴地說:“陳村長,村里……村里老老少少……就……就三個光棍,一個……一個是甘圖的哥哥甘鋼,他在石灰廠打工得了矽肺病幾年前就死了。”
結巴組長結結巴巴地說,陳村長聽得很費勁,他不耐煩地擺擺手,心想這蒿子村的人都死光了?怎么選出這么一個結巴當村民組長,下一步我就把這家伙給換掉。
陳村長厲聲呵斥道:“那另外一個光棍呢?給他蓋房子了嗎?”
結巴組長被陳村長一吼立刻不結巴了:“另外一個姓劉,上個月政府剛要給他蓋房子,可他一時想不開在果園的一棵果樹上吊死了。你說這小子,四十多歲了,怎么就想不開呢?”
陳村長問:“他有什么想不開的,國家要拿錢給他蓋房子,他還有什么想不開的。”
結巴組長立刻解釋:“唉,可憐呀,四十六歲了還沒討到老婆,又生了鼻癌,咱政府還真沒少管他,現在看病住院有新農合,出院就給報銷。但他那病不是三兩個錢能治好的,就是報銷自己也得先拿錢交上呀,一次一次地跑醫院,那藥忒貴了,一個光棍老農民實在承受不住,也受不起那個罪呀,就一時想不開跑到僻靜地方上吊了!這不是嗎,我剛給他老娘送殯出來。這幾天可忙壞我了,連抬棺材的人都沒有,村里的年輕人都走沒了,半個村子都空著,上哪里去找抬棺材的人,最后沒辦法還是求人找輛卡車送到墳地的。唉,這村子不大,啥……啥事都靠……靠我張羅。”
陳村長被這結巴組長給搞蒙了,這叫啥事,不是光棍上吊了嗎?怎么這又出了一個給什么老娘送殯!
結巴這才解釋:“這不是光棍上吊死了嗎?他老娘昨天去給他燒頭七,竟然在墳頭前哭死了,一起上墳的人以為她哭暈過去了,就又拉又打核勒(用手拍肋骨處)的,等發現身上涼了才往醫院送,送到半路人都僵硬了,只好又拉了回來,七天工夫死了兩口,陰陽先生說老光棍死的時辰不對,犯內乎,乎死自己親娘了。”
陳村長覺得這組長實在不像話,怎么還相信陰陽先生什么犯內乎外乎的,都是不懂科學的狗屁話,你說這個蒿子村還有好?村組長不但是個結巴還是個啥文化都沒有的老迷信,蒿子村蒿子村,就出結巴這樣的蒿子,連小組長這樣最小級別的村組干部都扒拉不出來像樣一點的人才。
陳村長和結巴這一扯,腦袋里全是“內乎外乎”的事情了,差點就忘記了身邊那亮堂堂的兩間房子,多虧房子里邊的大白馬響亮地打了一個響鼻才使他轉過神來:“聽說你們村的甘圖是有女人的,不算光棍,你們為什么謊報他是光棍?騙國家的錢給他蓋房子?”
這大帽子可是太大了,結巴嚇得一哆嗦,這回一點都不結巴了:“那女人是人家的,不是他的女人呀,他只是在人家家里睡覺。”
“啊,什么?睡人家的女人?”
“啊,就是,就是,就是人家的女人。”
結巴手往那兩間房子下邊一指:“他就睡在這家。”
陳村長順著結巴的手指向下一看,一個方方正正的磚墻院子里,四間白墻紅瓦的大房子矗立在老光棍的兩間房子下方,院子的南邊是菜園子,菜園子里綠油油的,還種著幾棵果樹。院子的東邊有一個羊圈,圈里并沒有羊,是空的。房子的前邊已經都被水泥硬化,水泥地上曬著一些粉紅色的肉蘑菇,墻上掛著一些用線穿起來的瓜條子和紅辣椒,整個院子干干凈凈的,一看就知道主人是個整潔利索的人。這是蒙東地區特有的農牧結合的院子,既有農家的菜園子,又有草原特色的牲口棚子。因為這個村子自古以來就是漢蒙滿人雜居的地方,蒙古人滿人和漢人的生活方式早已經水乳交融,無論是從表面上還是生活習慣和語言上根本就分辨不出戶口本和身份證上所標注的民族身份。
“這家的女人叫啥?多大歲數?她男人叫啥?”
陳村長又好奇又生氣地問結巴。
結巴組長立刻回答:“這是爛板凳的家。”
陳村長皺了一下眉:“什么叫爛板凳?哪有爛這個姓?”
結巴組長立刻解釋:“嘿嘿……我……我說順口了,爛……爛板凳是蒿子村的人對白琴琴的稱呼,意思是……是白琴琴這個女人像……像一條爛板凳一樣,誰都可以坐。”
陳村長問:“她多大年齡?”
結巴說:“都六十七八歲——歲了。”
陳村長冷笑一聲:“六十多歲的老婆子還有人坐?你們這村沒女人了?”
結巴立刻解釋:“這爛板凳的名是……是從她年輕的時候叫……叫起來的,再說……說了,你別……別看她六十多歲了,臉上還像桃……桃花一樣粉……粉呢,想……想當年是這個村最漂亮的媳……媳婦,和演員劉曉慶一樣好看呢。”
陳村長聽結巴一說,立刻對這個老女人有了興趣,他又掃射了一遍院子,希望那個快七十歲還粉面如桃的女人忽然出現在院子里,但他等了半天院里還是靜悄悄的,于是他又轉頭問結巴:“她的男人怎么樣?”
結巴說:“她男人是這個村最帥氣……最好看,個子最……最大的男人,但也是這個村最窩囊,最沒能力,一分錢也掙不來的囊貨,窩囊到……到啥程度你知道不?”
陳村長說:“我不知道!”
結巴說:“嗯,不知道我告訴你,她男人窩囊到能和另外的一個男人與自己的女人睡在一鋪炕上,怕打擾老婆和別人親熱還得轉過身去臉貼在墻上大氣不敢出。”
啊,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男人?
陳村長一聲驚嘆,結巴看看陳村長那一臉的驚愕,撇了一下嘴巴,心里冷笑:哼,世界上的事你不知道的多著呢,別以為你這小白臉比我多讀幾年書,農村的事你知道個屁。甘文能耐吧?在城里跑了十年掙了點錢跑回來說什么治理家鄉,競選村長,剛當了一年,還沒等施展他的那些宏偉計劃就被劉三拉下馬了,沒進監獄就算便宜他了。就你這只讀過幾本法律書的小白臉,還來給我們當村長!嘿嘿,等著瞧好戲吧。
這個時候,一群羊咩咩叫著從馬路的南側走了過來,大概有三十多只,那羊全是黑腦袋白身子,這種羊叫杜蒙羊,是內蒙古本地的羊和澳大利亞引進的種羊繁殖的后代,這種羊不但耐寒性強繁殖能力也特別快,非常適合蒙東地區冬長夏短的寒冷氣候。
羊群的后邊跟著一個看起來像五十多歲的女人,女人穿著一件白底粉花的上衣,褐色的褲子,梳著齊耳短發,整個人給人一種干凈整潔的印象。
羊群走近了陳村長又從陳村長的身邊繞過去走進了陳村長剛才端詳的大院子,陳村長看見羊走進院子才回過神來:哦,這個人一定是那條爛板凳……不,是那個白琴琴。
陳村長將目光飛速地定格在白琴琴的臉上:只見那臉雖然在眼角處有幾條皺紋,但那皮膚還真的是白里透紅,粉面如桃,兩只黑黑的眼睛雖然很小,但天生就夾帶著微笑,且黑白分明,看不出這個年齡本該擁有的渾濁,臉部輪廓也像年輕人一般清秀,一點多余的贅肉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