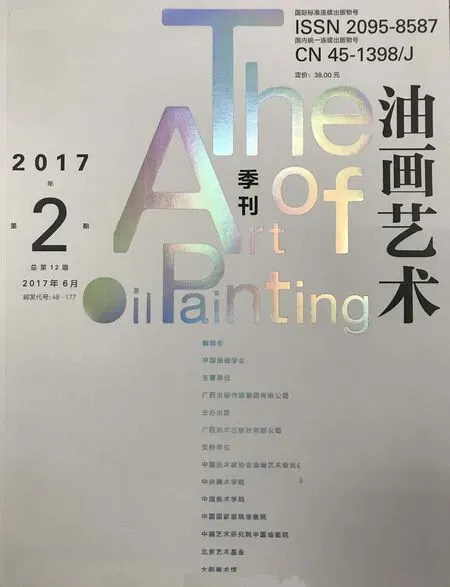圖像繪畫的變體與潮流化的新面孔—西南當代藝術中“硬邊”繪畫與“新萊比錫”繪畫的流行
在一個崇尚創造性與多元化的時代,潮流化或許是當代藝術創作中非常令人反感的現象。但在文章的開始,我必須首先澄清一個有關個人趣味與藝術潮流之間的關系問題。我的立場是,個人趣味不受他人指責,藝術趣味的形成受異常復雜的原因所決定,最終落實在個體的、獨一無二的“身體”層面。以自己的趣味和喜好為出發點所進行的藝術創作是無可挑剔的,哪怕是你仍然迷戀那些看似“老套”的題材和風格。民國初年,“四王”式山水的陳陳相因已經遭到普遍的詬病,從個體角度來看,傳統畫家們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繼續畫此“山水”,誰也無權去批評這種個人藝術趣味。此外,批評家們當然可以推崇更具創新意識的作品;他們也可以站在當時藝術界的宏觀角度對這種缺乏創造力的藝術狀態進行擔憂,并找到其背后的歷史、社會“病因”。所以,趣味無可指責,批評家卻可以對社會整體的創作狀態有所擔憂,有所批評。視角不同,得出的結論可能完全不同。本著這樣的視角來剖析、批評近些年來西南繪畫中的一些潮流化問題,其批評面就不至于擴大化,也不至于因此而誤解某些真誠的藝術趣味。
十年前,當批評界開始抨擊西南地區的圖像繪畫時,其原因也正在于圖像繪畫的泛濫已經壓制了藝術界的創造力。市場的瘋狂使得藝術家可以簡單地借用圖像、符號來玩一些和社會、政治相關的“圖文游戲”,對視覺豐富性的追求讓位于圖像、文字之間簡單、乏味的對應關系。批評界對圖像繪畫的批評仍然是站在宏觀語境角度來進行的,這里必須澄清兩個問題:第一,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當鐘飚、郭晉等人在當時的流行圖像中進行借鑒時,圖像繪畫還具有語言和社會的雙重前衛性。第二,個體藝術家若仍真誠地執著于此類型的創作,這無可厚非,批評是從宏觀層面對后十幾年來藝術界鋪天蓋地的圖像繪畫進行反思。西南地區圖像繪畫的出現或許和北京地區曾經流行的“政治波普”有一些聯系,隨后它在年輕一代的藝術創作中引起反響,并很快地成為一種較為主流的當代藝術創作潮流。它熱衷于挪用各種流行圖像和文化、政治符號,在繪畫語言上體現為“平涂”“揉擦”等筆法,對色相數量上則進行簡化,有別于傳統意義上油畫等繪畫門類中對色相豐富性的追求。到21世紀初,這種圖像繪畫又在更為年輕一代中演化為一種借鑒了卡通、漫畫圖像的“卡通繪畫”。為了與黃一瀚等老一代的卡通繪畫相區別,人們將其稱為“新卡通一代”。由于受到市場的追捧,“新卡通一代”也迅速地被后來者們競相模仿、追捧,迅速地成為一種在年輕藝術群體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創作潮流,這也正是鮑棟、盛葳等年輕批評家對其進行批評的藝術語境。
如上文所言,對潮流化的警惕與現代主義以來對創造性的推崇有關,人們總是希望不斷看到新的創作思路呈現出來,而不是千篇一律、人云亦云。批評的介入使得西南地區的圖像繪畫在2010年前后開始出現了表面上的偃旗息鼓。但實際上任何文化現象都難以被攔腰折斷,它們往往以其他方式被延續下來,產生各種各樣的變體。最近幾年,在西南尤其是重慶、四川等地年輕一代的作品中,有兩種新的繪畫風格開始大行其道,且又再次開始出現明顯的潮流化傾向,這毫無疑問應該引起人們的反思。
一種是以“抽象藝術”為名義出現的“硬邊”圖像繪畫。它的流行一方面與前些年批評界對中國抽象藝術的呼吁和推崇有關,另一方面又滿足了市場對于視覺愉悅性的需求。此外,對于繪畫積淀并不深厚的年輕藝術家們來說,其制作性有利于他們迅速“上手”,在藝術市場中獲得肯定。在表象上,這種“硬邊”繪畫有些類似于蒙德里安、里特維爾德等人在20世紀30年代所創作的風格派作品,以“花布格子”或“多棱鏡面”般的圖像呈現于畫面之中。但風格派的作品與“通神學”和歐洲北方新教的教義有著密切關系,而今天的“硬邊”圖像繪畫卻更多地體現為裝飾性、悅目性和符號性。同時,它們與20世紀60年代在歐美出現的帶有視覺實驗性的歐普藝術也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但毫無疑問卻較少具有視覺心理學層面的實驗性。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此類型創作,除了整幅純粹性的硬邊風格作品,也有在敘事性的具象繪畫中插入“硬邊”圖像的創作方式,以此作為畫面構圖的一部分。當然,此類創作未必完全從商業邏輯出發,也極有可能來自身邊藝術群體的影響或在市場上“已成功”藝術家的標榜作用。對于他們來說,商業上的“成功”表征著藝術上的正確性,或許眼界上的局限導致他們無法站在一個更高的視野來進行判斷。而有些人或許已經意識到了潮流化的危險,轉而采取了看似“聰明”的方式來進行“硬邊”創作,例如描繪體育場邊的菱形鐵絲網格,窗戶中密集交織的方格窗欞,電路板中錯綜復雜的電路線……其目的或許正在于有意回避直接的視覺雷同,但又通過這種隱晦的方式與“硬邊”繪畫建立起聯系,獲得商業上的認可。
另一種是受到新萊比錫畫派影響的繪畫風格及各種變體。以大衛·施萊爾、勞赫、艾德里安·格尼等人為代表性的藝術家及其風格近些年來在西南地區的藝術創作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力。萊比錫地處前東德,這一批藝術家對政治題材的興趣,對寫實性繪畫的延續,似乎都非常適合于“嫁接”到中國的當代繪畫之中。就這一點來看,它和前些年里希特繪畫在中國的盛行有類似的原因。
下面從幾個方面來闡述此類型作品流行的原因:第一,由于在作品中善于挪用各種政治、社會圖像,這對于藝術家來說似乎帶有很強的吸引力,所以我也將西南地區此類型的創作理解為前些年圖像繪畫的一種變體。后者作為曾經影響力巨大的繪畫潮流,因批評話語的介入而短暫地得到了抑制,卻需要以其他的方式、風格被延續了下來。他們對某些歷史圖像、政治圖像的挪用無疑讓西南的藝術家們找到了一些契合點,且非常有利于進行政治、文化層面的意義增值。在大衛·施萊爾等人的作品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硬邊”圖像的運用,這或許也有利于與上文提到的“硬邊”繪畫潮流進行呼應。第二,這種繪畫風格帶有非常強烈的兼容性,既熱衷于對各種圖像進行挪用,又善于運用各種新鮮的筆觸語言。今天西南地區的藝術家們一方面難以完全跳出之前圖像繪畫的創作模式,另一方面又需要盡快地進入“去平涂”的語言風格中去,以此對前者進行超越。由此新萊比錫畫派的這種兼容性無疑成為他們最便捷的模仿范本。在艾德里安·格尼等人的作品中,那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筆法和處理方式的確讓人大呼過癮。第三,新萊比錫畫派帶有很強烈的歐美視覺趣味,對于中國藝術家來說它似乎具有一種視覺上的前衛錯覺。例如,那些并不鮮艷的麥黃金、牛油果綠、懷舊的灰色……使得這樣的畫面看起來非常類似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廚房中的流行色彩搭配方式。此外那種獨特的黑灰色關系和看似斑駁的視覺效果隱約有一種懷舊感,它們有時會讓人聯想到褪色的老照片或老派的歐美電影畫面。

1何森《有玩偶的女人》200 cm×250 cm布面油畫2008年
從全國范圍內來看,西南的藝術家們并不保守,當代藝術在這里從來就不是一個禁忌。西南地區似乎沒有那么根深蒂固的傳統包袱,這里相對濃厚的市民文化與淡薄的等級觀念使得新的藝術觀念與風格很容易獲得藝術家們的接受。所以,無論是20世紀70年代末對美國照相寫實主義繪畫的模仿,“85美術新潮”時期西南藝術群體的“生命流”,20世紀90年代的圖像繪畫還是如今流行的這兩種繪畫潮流,對新東西的接受似乎一直都不是問題。西南地區在地理位置上看似邊緣,卻一直走在中國當代藝術的前沿,但問題卻在于受利益驅使而出現的“一窩蜂”現象。對潮流的迷戀使得藝術家們難以靜下心來去細細琢磨繪畫的本體問題,難以在個性層面展開較為深入的挖掘。潮流化與利益相關,也與資本的訴求相關。對于藝術資本來說,他們需要集中資本推高某種藝術潮流的市場價格,前些年的圖像繪畫、新卡通繪畫,近些年“硬邊”繪畫的流行和“新萊比錫”繪畫的熱潮或許與之都有著密切聯系。這一現象在今天的中國藝術界越來越明顯,如近些年來在理論界定上語焉不詳的“新水墨”,同樣與藝術資本的急切包裝和熱炒相關。當然,市場化在今天的藝術界并非無法接受,但它所帶來的潮流化后果無疑值得警惕,潮流化的存在是對創造性的壓制和文化多元性的抹殺。對于某些年輕藝術家來說,輕易地被潮流所淹沒也與其眼界與判斷力相關。在今天略顯保守的文化語境中,“影響的焦慮”仍有意義,個性仍值得推崇。“文化大革命”后,發時代之先聲的“傷痕油畫”“鄉土現實主義”的主要創作群體如高小華、羅中立、何多苓等畫家均來自四川美術學院。四川美術學院在新時期伊始所煥發出的蓬勃創作力引發了全國關注的目光,成為人們一時熱議的“四川美術學院現象”。四川美術學院之所以能夠培養出如此多的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青年畫家,是和其獨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式分不開的。自20世紀80年代之后,四川美術學院在面臨新的發展形勢時也在不斷地調整著教學的方式,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本期欄目特約幾位長期執教于四川美院的專家教授撰文敘述,梳理和探討四川美術學院的教學發展和革新的歷程,以及面對時代課題的思考,這可以讓更多的人進一步了解四川美術學院在歷史和現實中所形成的教學方式和教育經驗,對于進一步推動美術學院的藝術教學,提煉、積累經驗,討論現實教學問題,探索未來發展,意義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