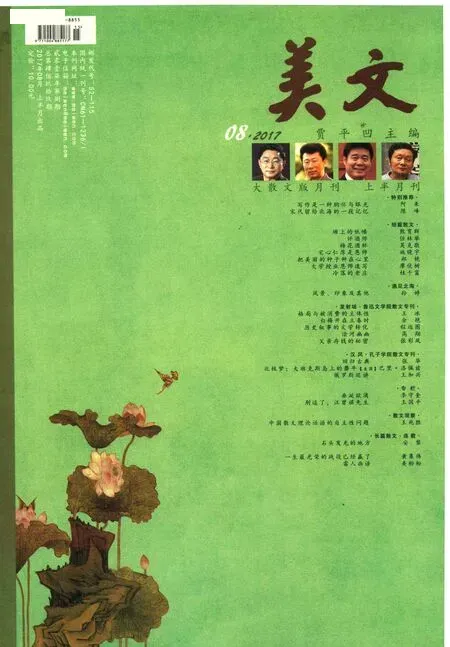中國散文理論話語的自主性問題
◎ 王兆勝
·散文觀察·
中國散文理論話語的自主性問題
◎ 王兆勝

我們通常用四分法來劃分文學,即小說、詩歌、戲劇和散文。比較而言,其他文體都有自己的較為成熟的理論,而散文則缺乏理論,甚至多從小說、詩歌、戲劇中借鑒所謂的理論,于是其理論的困境是相當突出的,而理論的自主性缺乏就更加明顯。我們認為,散文應確立自主性,建構屬于自己的理論話語。
一是不應將“創新性”作為散文唯一、絕對的衡量標準,而要強調繼承性,尤其是在繼承與創新的辯證關系中,考量散文理論話語的建構。
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理論一直強調創新性,有創新則活,無創新則死,這在散文理論上也有明顯表現。如黃浩在《從中興走向末路》(《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一文中,直言沒有創新的散文必然走向末路和死亡。其實,從“創新性”角度衡量散文只是一個維度,沒有創新也未必不是優秀散文,如中國歷代寫父母之愛的優秀作品,其創新性并不突出,但它們都非常感人。又如朱自清、俞平伯的同名散文《漿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如按創新性理論進行判斷,它們一定無多少價值,因為二者的重復性極高,基本可看成復制品;然而,若以自主性角度擺脫“唯創新性理論話語是從”的局限,也就容易獲得超越性,其價值就有了新解:創新性散文不一定好,守成的散文未必就差,關鍵是它能否以真誠動人,能否在情感和審美上激起讀者共鳴。
其實,“變”與“不變”是一個辯證關系。錢穆曾在《晚學盲言》中說過:“一陰一陽之變是常,無窮綿延則是道。有變有消失,有常而繼存。繼承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如果沒有“常”作為基礎,“變”就會走向消亡。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變數太多,而守常甚至守舊不足,因此,真正有真知灼見的人并不多,而能堅守己見者更少。用這一角度反思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發展,求“變”的創新成為唯一有價值的維度,而不變之守常就在被否定之列。這必然導致許多美好內容的喪失,包括我們的價值觀和審美趣味。因此,散文要想獲得理論的自主性,必須突破“創新”的單一向度,進入“繼承”與“創新”的辯證理解中。
二是要跳出“跨文體”散文寫作的羈絆,確立散文的體性及自主性,避免其異化狀態。
近現代以來,我們習慣于用西方的“散文”概念進行闡釋,甚至用它簡單地取舍中國古代的“文章”,其實“散文”與“文章”的區別很大。“散文”是一個現代學科概念,是與詩歌、小說等比較而言的;“文章”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散文”概念,是除了韻文以外的文學總稱。當然,還有另一種相反的情況,即用中國傳統的“文章”來破解當下的“散文”文體,否定“美文”和“純藝術散文”的價值,甚至簡單批評西方散文,那也是不可取的。
還有,用“散文詩”覆蓋“詩的散文”,將西方隨筆與中國古代筆記、小品文相混淆,都是缺乏自主性的表現。如一般人都熟悉“散文詩”,但對于“詩的散文”比較陌生。其實二者是有區別的:“散文詩”的中心詞是“詩”,“詩的散文”中心詞是“散文”。“詩的散文”盡管有詩味兒,但比“散文詩”的詩意淡得多,也比詩更加“無韻而冗長”,最重要的是它“不分行”。因此,將魯迅的《野草》稱為“散文詩”,是值得商討的,因為其中的不少作品是不分行的,是散文的形式,而不是詩的形式。所以,魯迅《野草》中像《雪》這樣的篇章就不是“散文詩”,而是“詩的散文”。
如果要確立中國散文理論話語的自主性,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擺脫中西傳統的束縛,并對二者進行比較、融通、再造,從而建立起具有當下性的新的散文理論話語。以“跨文體”散文寫作為例,現在不少作家追求以詩的筆法、小說的虛構,甚至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來寫散文,一方面帶來了散文創作的增殖,尤其是擴大了散文的視域和容量;但另一面,卻導致散文體性和自主性的異化甚至喪失。如楊朔當年就坦言自己是將散文當詩來寫的,這個長期以來被作者引為自豪的“跨文體”寫作,是被學界普遍贊同的。其實,從散文自主性角度觀之,楊朔的寫作方法在獲得詩意的同時,也給散文帶來一種做作之感。余光中更是如此,詩的大量摻入直接導致其散文的矯揉造作和濫情狀態。余光中有篇散文叫《老的好漂亮》,其題目本身就不自然,他在文中寫道:“津浦路伸三千里的鐵臂歡迎我去北方,母親伸兩尺半的手臂挽住了我,她的獨子。”如果這句話當詩讀,是可以的,但用在散文中就變味了,為什么呢?太過夸張,別扭,不自然,欠平實。另一段這樣寫蓮花:“蓮是神的一千只臂,自池底的淤泥中升起,向我招手。一座蓮池藏多少復瓣的謎?風自南來,掀多少頁古典主義?蓮在現代,蓮在唐代,蓮在江南,蓮在大貝湖畔。蓮在大貝湖等了我好幾番夏天,還沒有等老。”散文不能這么寫,散文這么寫就是“炫張”,給人的感覺是感情虛假。因為它的“詩性”太多了。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那是詩,若用在散文里就不自然。林語堂曾在《說本色之美》中表示:“文人稍有高見者,都看不起堆砌辭藻,都漸趨平淡,以平淡為文學最高境界;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運用之,便成天地間至文。”如果過分強調散文的“詩性”,那就變味了,余光中經常有這樣的問題。還有不少人用小說的形式寫散文,所以有虛假之感。因此,散文在追求“跨文體”寫作時,一定要有敬畏心,既掌握好文體的邊界,更要做到“適度”。
住院總費用構成包括藥品費、檢查費、材料費、手術費、治療費、床位費、輸血費和其他費用。2017取消加成后與2016取消藥品加成前次均藥品費、檢查費、材料費、治療費都有所下降,其中次均藥品費金額下降幅度最大,次均下降2100元,只有次均手術費上升較明顯,次均上升500元。在構成比重上取消加成變化幅度最明顯的是藥品費,所占次均總費用的比例下降6.59%,手術費所占比例上升3.14%,其余費用比例小幅上升(表2)。
三是要突破長期以來流行的“散文形散、神不散”理論,也要突破當下風行的“散文形散、神也散”模式,而要進入“散文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新的理論話語。
理解“散文”的關鍵在一個“散”字,但具體而言怎么個“散”法,卻少有人進行深入研究,更難擺脫習慣和流行看法。可以說,如果解決不了散文的“散”字所含的深意,那就不可能真正走進散文文體,也不可能克服時下散文的流行病和幼稚病。當然,散文文體的自主性也就無從談起。
1.散文大可隨便
魯迅曾說過:“散文大可隨便。”這是針對散文文體過于拘束,有時放不開而言的。然而,人們對于魯迅這個“隨便”的理解,往往是相當隨便的,認為可以不要束縛,隨意而為。尤其是對于“大可”二字,人們也加重了分量,認為散文就可以無拘無束地隨便寫開去。其實,這樣的理解和認識顯然是不正確的。
2.散文的形散、神不散
20世紀60年代,肖云儒提出“散文形散、神不散”的觀念,于是成為影響深遠的一種散文觀念。其核心意思是,散文的形體完全可以放開,使其成“散漫”狀態,但“精神”卻不能“散”,這就是所謂的“形散神聚”。這種散文觀的最大優點是給散文之“形”注入自由,同時又保持了散文“神”之凝聚。但其最大問題是,散文“形”散而不受約束,從而導致散文之形“散”無所歸依。
3.散文的形可以散,神也可以散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為散文“松綁”的呼聲越來越高,到后來集中在為散文之“神”松綁。較為突出的是劉燁園提出的“散文不僅要形散,其神韻也可飄忽不定”。還有學者進而強調,散文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愛怎么寫就怎么寫”“法無定法的自由上”。這是導致當下散文“形銷骨立”和“失魂落魄”的重要理論依據。當“形”“神”俱散后,今天的不少散文已變成“委地如泥”的“北癱”了:題目、結構、主旨、章法、語言等都可以沒有提煉和提升,散文寫作幾近成為一種“掃垃圾”狀態。
4.散文的形不散、神不散、心散
針對學界關于散文之過度解放,我在《“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觀及對當下散文的批評》(《南方文壇》2006年第4期)提出了“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散文觀。其核心詞是:無論是散文之“形”還是“神”,都不能“散”。這頗似一個人,如無骨架和神韻,他就會變成“非人”,至少是“脫形”和“失去風采”了。既然散文的“形”“神”都不能“散”,那么,散文之“散”應表現在哪里?我認為是“心散”,即心靈的自由、散淡、自然、超然,一種超越世俗性的形而上理解。因此,散文之“散”應打破以往的觀念,找回自己的主體性,將重心不是落在“形”與“神”上,而是放在“心靈”上。
以往對于散文之“散”的理解,都有些偏向,也不得要領。這是因為,只有“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才不至于失為散文本性,才能真正獲得散文理論話語的自主性,這包括處理好自由與限制、真實與虛構、中心與邊緣等的辯證關系。
四是從“人的文學”模式中解放出來,進入體察“萬物”尤其是關于“天地之道”的理解,這是散文獲得自主性理論話語的關鍵。
應該承認,“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有一個很大的觀念變化,那就是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學”,即由“非人的文學”轉變為“人的文學”。但后來,這種“人的文學”越走越窄,甚至走向以“個性解放”消解“集體”“群體”和“國家”的歧途。其實,文學表現的視野除了“人”,還不能離開天地萬物;在關注“人之道”時,不可忽略“天地大道”。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是以“天地之道”代替“人之道”;那么,中國現代以來的新文學則因為過分強調“人之道”,而忽略了“天地之道”。老子《道德經》有言:“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天地之偉大就在于,它可用其“大道”修正狹隘的“人之道”。這也是為什么,一陣風吹過之后,原來的坑凹會被填平;一個人年輕時可以以2.0的視力為自豪,但人到中年后眼卻比別人花得快。
具體表現在散文上,當下更多作家進入的是“人之道”的書寫,而更為廣大的“自然萬物”和“天地之道”卻被忽略了,作為散文理論研究也是如此。將“人是天地之主宰”“人是萬物的靈長”作為價值觀進行寫作和研究,勢必帶來散文理論話語的“窄化”與“異化”。就如魯迅在《狗·貓·鼠》一文中所言:“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可是嚕蘇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假使真有一位一視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對人類的這些小聰明,也許倒以為多事,正如我們在萬生園里,看見猴子翻筋斗,母象請安,雖然往往破顏一笑,但同時也覺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為這些多余的聰明,倒不如沒有的好罷。”魯迅筆下的萬物尤其是那兩棵棗樹,在現代性的“人的文學觀”之下,往往會被過度闡釋;其實,從物性與天地之道來看,可能更接近魯迅的創作實際,因為魯迅對于動植物并不都是遵循著“人之道”的理解。還有郁達夫散文《故都的秋》、關于閩地的游記,如從人的現代性來看,它們的確無甚可觀,但從物性和天地之道來看,卻寫得非常好,是天地至文。正因為對于“人的文學”觀的片面理解,今天的散文創作與散文理論才會失去自主性,進入一個被“人的文學”簡單過濾的困境。如葉靈鳳的香港風物描寫、陳從周的園林小品文、周建人的科學小品,還有黃裳、唐弢的書話等,在“人的文學”觀底下,往往都失去了重要價值。但在物性和天地之道中,它們卻會別開生面。這就是“人之道”散文觀的局限與困境。
理想的散文理論應將中國古代“物的文學”與中國現代“人的文學”辯證地統合起來,即將“人之道”與“天地之道”進行融通,然后再造,從而使散文理論獲得一種新的超越性。只有當散文理論話語由“人”而及“物”,并發掘出天地自然中“人”與“物”的靈光,散文理論話語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得以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