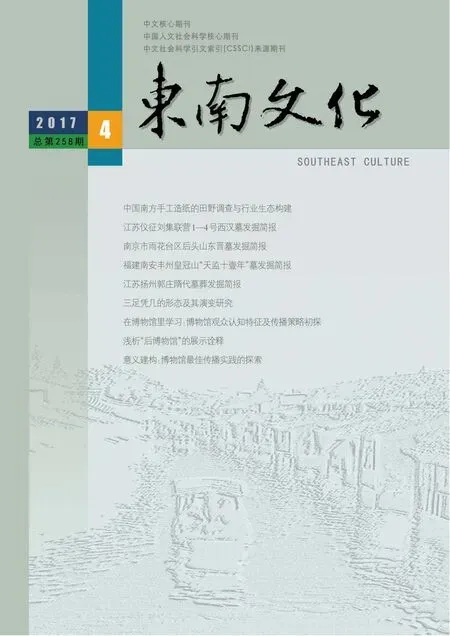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研究兼論楚系漆紗冠
王丹 李則斌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2.南京博物院 江蘇 南京 210016)
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研究兼論楚系漆紗冠
王丹1李則斌2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2.南京博物院 江蘇 南京 210016)
通過對江蘇盱眙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殘片的科學分析,可以得知該漆紗殘片內部的使用材料為桑蠶絲,其外再髹大漆;編織結構為典型經編纂組結構;其表面可裝飾紅色朱砂礦物顏料。楚、漢這一類漆紗冠情況概基本如此。同時,結合以往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可以推測漆紗冠這一形制,或起源于楚國,并沿用至漢及后世。
漆紗 纂組工藝 朱砂染料 楚文化
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的江蘇盱眙大云山漢墓是一座西漢早中期的諸侯王墓葬,墓主人為江都王劉非,陵園由主墓、陪葬墓、車馬坑、兵器坑及城墻、司馬道等部分組成,規模宏大,建制完整,被評為“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其出土的大量精美珍貴文物,更是令學界嘆為觀止。
在諸侯王主墓回廊上發現陪葬有鐵質髹漆鎧甲多套,是不可多得的保存完整、形制高級的漢代甲胄遺存,在送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實驗室考古過程中,在其中一套鎧甲的鐵質甲胄位置清理出一小塊漆紗遺存。工作人員對其提取檢測并進行了一系列綜合研究。
一、基本情況
漆紗殘片遺存,出土時折疊成一團,與泥土混雜一處。經小心清理揭展后,得到漆紗遺存面積約20平方厘米(圖一)。
漆紗整體呈亮黑色,質較硬,局部表面粘有紅色物質。孔洞呈方形或菱形,編制規整,均勻精巧。編織線投影寬度較均勻,約為0.28~0.42毫米,經緯向密度均約為10根/厘米。
二、分析檢測
1、組織結構:在顯微鏡下可見,漆紗內為編織物外部髹漆,其編織組織結構為經編織物的組帶形式(或可稱纂組結構)。具體為,兩組編織經線約呈垂直方向編織(為方便理解暫稱為經向編織線和緯向編織線)每根編織線均由2股線合股組成,其經緯向線相互交穿絞合,即在此組織點2股經向編織線捻合合股后夾于2股分股的緯向編織線中,之后經緯向編織線2股間分別相絞,于下一個組織點則呈現為2股捻合合股的緯向線夾于2股分股的經向線中,由此往復循環(圖二)。這種編織方式的優點為網格的可形變基數大,便于后續整形。

圖一//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殘片及細照

圖二//漆紗組織結構示意圖

圖四//漆紗殘片X射線電子能譜及元素分析表

圖三//漆紗橫截面切片掃描電鏡照片
2、鑒別:對漆紗碎塊進行提取檢測,其外層包裹物經傅里葉紅外光譜檢測,成分為大漆。漆紗內部織物纖維早已朽蝕不見,只有通過對漆紗殘片整體包埋切片,觀察其橫截面上纖維朽蝕后留下的孔洞形態而推測。在掃描電鏡下清晰可見,其單根纖維橫截面呈邊角圓潤的三角形(圖三),對照標準纖維圖譜可知,其內部主體纖維為桑蠶絲。
3、表面粘染物分析:漆紗出土時局部表面粘有一層紅色物質,略成粉末狀,分布不太均勻,且固著性差,很容易散落。對這種紅色物質提取,經X射線電子能譜分析可知,其中存在較高的汞元素(圖四);檢測漆紗表面無明顯紅色物處,知亦有汞元素存在。結合相應資料,可知其表面原紅色物質為硫化汞即朱砂。朱砂作為一種易得的礦物染料,在我國古代早期使用較為普遍。
4、由顯微鏡觀察可知表面髹漆是在編織定型后再進行的,也就是說先用柔軟的絲線編織整理成所需形狀,而后再髹漆定型,髹漆后其形狀即固定。
5、漆紗殘片恰好殘留較粗的幾根編織物位于原器物邊緣,發現時其尚保存著原本曲折的形狀,可能是對紗布起到支撐塑形作用。其具體屬性尚不明確。
三、分析研究
漆紗又稱為“纚”或“縰”,其結構為內部由絲、麻等物編織,再于表面髹漆而成,是古代一種較高級的材質。《釋名·釋首飾》:“纚以韜發者也,以纚為之,因以為名。”[1]
由于漆紗的有機質材料屬性,不易保存,歷來考古出土者并不多。有學者研究漆紗的保存“耐水解老化能力較差,在絲織物之下”[2],所以即使在有紡織品發現的墓葬中亦不易見到。目前考古出土的漆紗制品,主要器形為冠(注:考古另發現有外部髹漆的絲、麻編織履,此處暫不討論)。
已發現可知的早期(漢及以前)漆紗情況見表一。
大云山漢墓出土的這塊漆紗殘片,由于發現于鐵質鎧甲的胄處,且同出有或起支撐作用的邊緣,筆者推測其性質也是冠或與冠有關。對比以往出土漆紗情況,結合此次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殘片的檢測結果,可獲得以下幾點對古代漆紗及漆紗冠的深入認識。
1.使用材料
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殘片,經包埋切片檢測,知其內部編織物為蠶絲纖維,與常見漆紗內部所用纖維種類一致。是否可推知,內部用蠶絲編織作主體,外部髹大漆,為古代漆紗制作的常見方式。考古也見有麻纖維織物外髹漆的遺存發現,這種情況主要用于制作鞋履,如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麻鞋“表層用麻布,髹黑漆”[10],這種情況屬于普通麻布上髹漆,與編織物不同,應另外討論。使用麻纖維制作漆纚的,目前僅見于廣西羅泊灣漢墓,暫為孤例。
2.結構
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殘片內部編織物是一種經編織物,或可稱為“組”式織物。這種結構的編織方式極為復雜,其織物具有輕薄、美觀、伸縮性強的特點。考古發現這種編織方式主要用于帶子,如印綬、冠纓、甲胄系帶、鞋帶等,質地一般為蠶絲纖維。在湖北荊門包山楚墓、長沙楚墓、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河北滿城漢墓、北京豐臺大葆臺漢墓等遺址都曾發現過(圖五)。如滿城漢墓“發現用絲縷編制的窄幅織物……它可能是用于結連玉璧和束緊玉鞋的。該織物作網狀組織,拉伸時網眼能變成菱形”[12]。根據文獻記載,《說文·系部》:“組,綬屬也,其小者以為冠纓。”[13]《儀禮·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系于踵。”[14]《禮記·內則》:“偪屨,著綦。”鄭玄注:“綦,履系也。”[15]可知這種編織物在古代被稱為“組”或“綦”。

表一//考古發現漢及以前漆紗情況表

圖五//長沙楚墓中發現的編織組帶[11]
而纂組織物外再髹漆,便成了漆紗。顯微觀察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殘片清晰可見,漆皮僅分布于漆紗表面,其纖維間并不見,可知髹漆是在內部編織定型后再進行的。即先用柔軟的絲線編織纂組并整理成器物所需形狀。根據纂組的特點,髹漆前其經緯線的交織點是可以相對移動的,即通過抻拉改變每四個結點間菱形對角線的長度,從而可達到織物形狀的變化。而后用大漆封固表面,將經緯線間的結點固定,即可保持一定的立體效果。正是因為漆紗這種獨特的可塑形特性,這種材料常被用來制作漆紗冠(考古發現的漆紗材料也有內部僅為平紋組織紗而其外髹漆的例子,但為數極少)。
漆紗冠的制作方法,長沙馬王堆二、三號墓考古報告中認為:“當織物編好后,將此織物斜覆在冠子的模型上,碾壓出初具輪廓的帽型,再加嵌帽框的固定線,然后在經緯線上反復地涂刷生漆,這種碾壓出的弧形放射線更加固定牢實。”[16]
3.表面紅色裝飾物
大云山漢墓漆紗殘片出土時表面局部粘有紅色粉狀物質,牢固性較弱,輕觸則無。經X射線電子能譜檢測分析知其中含有大量汞元素,推測該紅色物質為礦物染料朱砂。因同時對殘片表面無明顯紅色物覆蓋處檢測亦顯示有較強汞元素存在,可知原紅色顏料覆蓋區域應比殘存面積更大。
殘片除紅色顏料覆蓋外,整體表現為亮黑色,具有漆器的天然光澤。這是目前考古已發現的漆紗遺物的普遍顏色,也是東周至漢代出土漆器的常見顏色。個別漆紗遺物顯示為棕黑色的情況,推測應是大漆在氧化后褪色而形成的。
以往考古發現中,也有漆紗表面還施有紅色顏料的例子,如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M62出土漆紗冠,“冠表面殘存紅色顆粒狀顏料殘跡”[17],從顏料呈顆粒狀分析,疑也是礦物染料朱砂。

圖六//大云山前室發現之紅色漆紗殘片

圖七//臨淄齊故城發現之漆紗(表面紅色)

圖八//漆紗冠形象
還有,根據南京博物院編寫的《長毋相忘:讀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一書記載,大云山漢墓主墓中除回廊甲胄箱發現此漆紗外,其前室也有漆紗遺跡出土,從發表的圖片可見,彼處漆紗的面積更大,根據該書對同出“桃葉形金飾片”的描述,“此類金飾片與紅色絲織品共出一處,出土時部分金飾片背面尚留有大量紅色漆紗殘片”[18](圖六),雖未發表紅色漆紗的具體報告,亦可以作為一例討論。
另有一處新近材料,中國社科院考古所2013年在山東臨淄齊故城遺址發現一處漆紗遺跡,漆紗表面整體覆蓋紅色,顏色保存極為鮮艷[19]。
后世使用的漆紗冠應多為黑色,因有所謂的“烏紗帽”之稱。而考古發現的早期絕大多數漆紗也都是黑色的,那么這三例表面涂朱的個案,雖然不能排除是埋葬時在墓葬中粘染上的可能性,但是至少可以帶給人們這樣一個啟示:或許這種漆紗織物表面原本是可以作紅色裝飾的。特別是齊故城的材料,從照片可顯見紅色物只存在于漆紗表面(圖七),其所附著的泥土中并未見,且漆紗孔洞內也并未見紅色,或可推測礦物顏料朱砂在髹飾時便已混合于大漆中。
另外的佐證可從實物與壁畫中描繪形象的比較中獲得。考古發現出土于馬王堆三號墓中的漆紗冠(北162-1),由于存放在油彩漆奩中,得以很好的保存[20](圖八‥1);其與磨咀子漢墓M62出土的漆紗質所謂“短耳屋形冠”[21](圖八‥2),形制略同;而1916—1924年間于河南洛陽八里臺出土,現藏于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的一副西漢晚期的壁畫中一人所戴之帽,其形制又與二者十分相似[22]。從壁畫可清楚看出,冠為朱紅色。雖無法肯定壁畫中人物頭戴之冠材質一定為漆紗,但或可作為這種形制漆紗冠可能有紅色的旁證(圖八‥3)。
對于紅色漆紗考古并不多見的現象,概是由于朱砂屬于礦物顏料,其裝飾時需借用膠類物質粘合,而在埋藏過程中隨著古代動物或植物膠類漸漸分解消逝,朱砂也就漸漸脫離漆紗表面混合于周圍泥土中了。這一推測能否被證實,需要等待日后更多的考古發現。

圖九//東漢畫像石中所見漆紗冠
4.支撐物
大云山漢墓漆紗殘片出土時,其附近另同出了幾根略粗的細繩狀物,表面亦髹黑漆,并形成一定的彎曲形狀,筆者推測它們的作用可能為漆紗的邊緣支撐物。支撐物的屬性目前尚不明。
《后漢書·輿服志》在談到“長冠”時有“促漆纚為之……以竹為裹”[23]的記載,似乎提示了東漢時某種漆紗冠,是以竹圈彎折制成冠形作為邊緣支撐的。
這種說法在磨咀子漢墓出土漆紗冠上得到了很好的實證。磨咀子漢墓M62出土“短耳屋形冠”即“邊緣裹竹圈”。其M49墓主男尸頭戴的“漆纚菱孔紋的冠”,也是“周圍一圈裹細竹筋,頭頂另設一竹圈架,上搭纚片一條,像是漢代的進賢冠”。這說明歷史上至少曾有兩種不同的“以竹為裹”的漆紗冠類型存在。
《后漢書·輿服志》亦載“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24]。目前,雖尚未有帶“鐵柱卷”的漆纚出土,但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曾出土過一件“絲帽”(M11‥71),帽上穿纏有鐵絲,“鐵絲按帽子形制所需而彎曲”[25]。或者可以說隨著時期、地域、式樣的變化,漆紗冠是曾有多種不同支撐物存在的。
5.源流研究
用漆紗做的冠具有其他材質無法比擬的優點:絲織物髹漆定型后變得硬挺,可達到所需立體效果;且相對于別的材質,漆紗輕薄,既不會有沉重感,又通風透氣,不會使頭部潮熱。
所以這種材質在后世依然被廣泛使用。《隋書·禮儀志》有:“弁……此通用烏漆紗而為之”[26],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服器·幞頭》:“幞頭,朝服也,北周武帝始用漆紗制之,至唐又有紗帽之制,逮今用之。”[27]李時珍的考據顯然有誤,這種漆紗冠至遲在兩漢魏晉已非常流行,考古發現漢代畫像石(圖九)[28]及魏晉時期的壁畫(圖一〇)[29]中均可見有很多漆紗冠的形象。
從考古發現看,早期出土這種漆紗冠的主要是東周的楚國和漢代的墓葬,或可推知這種漆紗冠大概首先由楚國發明并使用,而被漢代延續并推廣。
“冠”在中國服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歷代王朝均把制定冠服制度作為安邦興國的大事。《禮記·冠義》有:“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30]而東周時楚國冠服的特點即為“鮮冠組纓,縫衣博袍”[31],“組纓”的說法在包山楚墓竹簡中也有見到[32]。而楚冠具體形制如何呢?必是“冠切云之崔嵬”[33]。在考古發現的楚國漆畫中有很多描繪楚人戴冠的形象(圖一一)[34],其所配之冠均是高聳而形制奇特,大概只有這樣的冠,才能配合畫中婀娜起舞的飄逸效果。

圖一 //魏晉壁畫中所見漆紗冠

圖一一//漆畫及帛畫上的楚式高冠
楚文化一向是以精妙、奇幻的特點示人的。考古發現的楚國漆器、青銅器、紡織品等無不體現出楚文化這種神秘又獨特的氣質;而色彩艷麗、制作精巧又造型多變的衣冠,恰好能作為楚文化的最佳詮釋。
這種高聳的形制奇特的冠式,非一種延展性好、輕薄且容易塑形的材質而不可得。纂組結構,即具有“延展性好可形變能力強”的特點,《楚辭·招魂》中即有“纂組綺縞,結琦璜些”[35],推知纂組這種復雜的編織工藝,也可能產生于善于奇思妙想的楚人。大概為達到輕薄且容易塑形的效果,楚人又在纂組上髹漆,從而產生了漆紗冠。對這種神奇材料的發明,令人不得不佩服楚人的想象力和智慧。從楚國出土漆畫等形象看,那種冠有很多種形制,或高聳或鵲尾,可惜考古尚沒有發現完整的例子。漢代流行的漆纚冠,應是從楚系的漆紗冠流傳而來,漢文化根本上是沿襲了楚文化的風格,二者一脈相承。
根據考古發現,楚、漢文化都出土過紗質冠。長沙楚墓、云夢睡虎地秦墓和江陵鳳凰山漢墓,均有紗冠出土。冠分別由“黃褐色紗”[36]、“加捻組復絲編織”[37]或“冠面和冠里由兩種不同經緯密度的紗縫合成”[38]。尚沒有證據證明紗冠與漆紗冠產生的先后順序,是否楚人在已有的紗冠外又加髹漆從而發明了漆紗冠,還需考古材料證明。
本文通過對盱眙大云山漢墓出土漆紗殘片的科學分析,對其成分、結構、制作工藝、裝飾物性質等方面有了清晰的了解;并推導出對楚、漢這一類漆紗冠的一系列綜合認識。結合以往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筆者推測:漆紗冠這一形制,可能起源于楚國,并沿用至漢及后世。大云山漢墓出土的漆紗殘片為研究古代科技史、服飾史以及物質文化等多方面提供了珍貴的實物材料。
(致謝:本文的研究工作在掃描電鏡及X射線電子能譜檢測方面得到了故宮博物院實驗室王允麗、李媛等老師的無私幫助,特此向上述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1]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中華書局2008年,第158頁。
[2]王厲冰等:《髹漆絲織物的水解老化性能研究》,《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9年第2期。
[3][10]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3、24頁。
[4][19]周旸:《丹漆紗和素麻——臨淄齊故城出土紡織品的一些認識》,《絲綢》2015年第8期。
[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臺漢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8頁。
[6][16][20]湖南省博物館:《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田野考古發掘報告》(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26、226頁、彩版四三。
[7]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6頁。
[8]廣東省博物館等:《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38頁。
[9][17][21]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2期。
[11][36]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圖版四七、第415頁。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59頁。
[13]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53頁。
[14]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儀禮》,清嘉慶刊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2449頁。
[15][30]王夢鷗注譯:《禮記今注今譯》,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7、789頁。
[18]南京博物院:《長毋相忘:讀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293頁。
[22]中國墓室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墓室壁畫全集·漢魏晉南北朝》,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23][24]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補:《后漢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3664、3667頁。
[25][37]《云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云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9頁。
[26]唐·魏征等:《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第266頁。
[27]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74冊158頁。
[28]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畫像石全集2·山東漢畫像石》,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6頁。
[29]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一冊)》,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49頁。
[31]譚家健、孫中原注譯:《墨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89頁。
[32]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69頁。
[33][35]王泗原:《楚辭校釋》,中華書局2014年,第161、137頁。
[34](左)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中國漆器全集1·先秦》,福建美術出版社1997年,第105頁。(右)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彩版四八。
[38]陳振裕:《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考古學報》1993年第4期。
The Lacquered Fabric Remains Unearthed from the Dayunshan Han Tombs and the Lacquered Fabric Hats Originated from the Chu State
WANG Dan1LI Ze-bin2
(1.Institute of Archa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10; 2.Nanjing Museum,Nanjing,Jiangsu,210016)
The examination on the lacquered fabric remains unearthed from the Dayunshan Han tombs, which are located in Xuyi,Jiangsu province,indicates that the base fabric was silk made of threads woven with warp knitting technique and the lacquer coating was decorated with red pigment,as seen in most of the lacquered fabric hats from the Han and Chu.Referr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form of lacquered fabric hats may be originated from the Chu state and had been followed in the Han and other dynasties to come.
lacquered fabric;zuanzu(weaving technique);cinnabar pigment;Chu culture
K871.41
A
(責任編輯:張平鳳;校對:朱國平)
2017-01-03
王丹(1981—),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考古學、紡織服飾史、文化遺產保護。
李則斌(1963—),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漢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