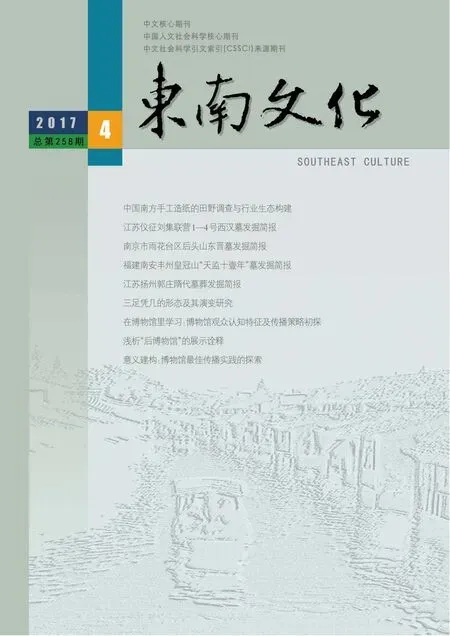“婦好墓展”與“海昏侯展”中所見“墓葬”展示的“他傳”難度
周高亮
(故宮博物院 北京 100009)
“婦好墓展”與“海昏侯展”中所見“墓葬”展示的“他傳”難度
周高亮
(故宮博物院 北京 100009)
婦好墓展與海昏侯展是以“他傳個人史”為視角展開相應(yīng)社會生活圖景的兩個典型展覽,這兩個展覽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人物生平展示介紹的一種展示結(jié)構(gòu)。在完全以出土“私人物品”為展示對象的展示中,信息殘缺嚴重的情況下,可以將墓主人的身份進行“模糊處理”,即仍需將其大致歸于一個人群,同時將能夠說明的問題進行細致分類。這是一種在個體認同無法確知的情況下,嘗試解決問題的新途徑,這一方法是對用考古資源展示“個體”過程中一般規(guī)律的探討。
展覽 考古學 婦好墓展 海昏侯展 “他傳”視角 策展
2016年3月首都博物館舉辦了《王后母親女將——紀念殷墟婦好墓考古發(fā)掘四十周年特展》(以下簡稱“婦好墓展”)和《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以下簡稱“海昏侯展”)。
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中最早的女將軍,她的事跡在殷墟甲骨卜辭中多有記載。殷墟作為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是中國眾多考古遺址中發(fā)掘次數(shù)最多、持續(xù)時間最長、揭露面積最大的遺址,被評為“20世紀中國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首。1976年在殷墟發(fā)現(xiàn)的婦好墓是目前已發(fā)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出土隨葬器物將近兩千余件,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此次的婦好墓展共展出411件(套)文物,包括青銅器、玉石器、甲骨器、陶器等。由“她是誰”、“她的時代”、“她的生活”、“她的故事”、“她的葬禮”等部分組成,展示婦好一生中“一國之后”、“王子的母親”、“巾幗英雄”三個不同角色,一位巾幗英雄不平凡的人生。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考古發(fā)掘取得了豐碩成果,此次展覽從中精選了符合展出條件并具有代表性的文物300余件,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了海昏侯國的考古發(fā)掘成果。展覽分四個部分,包括“驚現(xiàn)侯國”、“王侯威儀”、“劉賀其人”、“保護共享”等。歷時五年的考古發(fā)掘工作,所發(fā)現(xiàn)的多重證據(jù)最終確定海昏侯墓墓主為西漢第一代海昏侯劉賀。劉賀其人在文獻中多有記載,身為西漢皇室成員其經(jīng)歷了王、帝、侯的起伏跌宕,僅做了27天皇帝。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讓我們得以在史書之外,以物證的視角,重新審視劉賀其人其事及其時代特征。
從展示架構(gòu)上看,這次婦好墓展與海昏侯展是兩個墓葬出土物的一次聯(lián)合展覽。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展覽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人物生平展示介紹的一種展示結(jié)構(gòu),這一特征從其展示題目和展示對象就可以看出。我們比較熟悉的一類策展方式是人物生平歷史,尤其在對近現(xiàn)代革命人物的生平介紹中使用較為廣泛。對歷史人物的展示,通常采用較為固定的模式,本文通過對“個人史”[1]展示的一般規(guī)律進行分析,探討考古資源展示過程中對于“個體”描述方式的構(gòu)成問題。
一、“他傳”視角下的個體社會身份與個人歷史
這里所說的“社會身份”,實際上是指任何一個社會個體在社會中的存在特征[2],即他人如何認識他,通過哪些“標志物”來“辨識”[3]這樣一個人。社會身份是由社會地位決定的,通常我們將社會身份理解為權(quán)利、義務(wù)與特權(quán)所確定的一個人的地位,威望、權(quán)力、財產(chǎn)、工資收入等都是構(gòu)成社會個體的社會身份的要素。身份認同是個體對自我身份的確認和對所歸屬群體的認知以及所伴隨的情感體驗及行為模式進行整合的心路歷程。身份認同是心理學研究領(lǐng)域的重要理論范疇,包括人的各種社會屬性,這些屬性是個體在社會中的性質(zhì)分類和行事原則特征的總和。通常情況下,這種認同過程表現(xiàn)為對他人稱謂、社會職能、地位、權(quán)利、貢獻、政治角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認識過程;此外,也包括其在家庭等社會組織中的角色,如父親、母親、丈夫、妻子等。個體歷程中所出現(xiàn)的“行狀”、“事件”或“遺物”是支持這些基本特征的最有力證據(jù)。我們通常熟悉的個人歷程展示,如革命英雄人物事跡展,基本都是由這樣的一組內(nèi)容構(gòu)建而成,即由對英烈事跡的陳述、事件所留下遺物的展示等來“構(gòu)建”英烈的社會身份認同;其目的是通過對人物“可辨識”特征點的重構(gòu),在短時間內(nèi)明確人物形象,以便被參觀者記住。
考古學所觀察的對象內(nèi)容廣泛,但針對“個體”而言,其能說的話往往就較為有限。“普通”、“群體”、“大眾”這三個詞是考古學相比于其他歷史學科更加突出的特點,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考古學研究的對象一般多是古代建、構(gòu)筑物遺存,它們所能揭示的社會現(xiàn)象一般都是具有相當大“群體性”的,從各階段古代社會空間遺留的建筑遺存中所能夠復原出的“某一個體”的生活軌跡和社會身份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考古遺存中較為特殊的一類是固定場景中的個體的展示,多數(shù)是災難性場景中出現(xiàn)的“個體”,如龐貝古城所出火山灰“置換”的尸體、喇家遺址“母子”、南美洲安第斯山區(qū)祭祀“人牲”、阿爾卑斯山遇難個體遺址等,絕大多數(shù)遺址則完全不具備觀察古代個體本身的條件。其次,多年來考古學研究中,對于能夠反映“社會地位”或“等級”的“身份物品”(Prestige Goods)比較重視,而對于個體層面上的其他社會身份屬性細節(jié)是相對比較忽略的;同時,在統(tǒng)計學意義的層面上,性別、年齡、職業(yè)、疾病、信仰等因素基本是用于建構(gòu)某一時代“社會風貌”這類群體性特征的[4],個人歷史、家族史等這些層面的內(nèi)容則往往無法顧及。由于個體在自然和社會基本屬性很難與考古遺存建立廣泛而準確的對位聯(lián)系,考古遺存一般只能以物質(zhì)文化(器物組合)、空間平面(建筑遺存平面圖)以及生業(yè)面貌等形式進行展示利用,即社會群體性已經(jīng)構(gòu)成了一道考古遺存展示難以逾越的玻璃天花板。對于個體的歷史能夠揭示到什么地步,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遺存本身的存在方式、基本特征以及信息完整程度。在完全以出土“私人物品”為對象的展示中,能夠以“他傳個人史”為視角展開社會生活圖景幾乎是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二、對“婦好”和“劉賀”個人史的討論
所謂“婦好”,從名字、性別到身份地位,完全是通過考古學研究進行推測而獲得的,這一點與“劉賀”是完全不同的。劉賀,漢武帝劉徹之孫、昌邑哀王劉髆之子,其人生履歷主要來自于《漢書》等文獻的記載。也就是說,他的個人史是有跡可循、有章可查的,甚至可以說是記載翔實、條理清晰的。因此,與“婦好”完全不同,劉賀本人的歷史已經(jīng)有了確鑿的腳本。劉賀“個人身份”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次。其一,家族與政治身份認同。劉賀本人是漢武帝劉徹之孫、昌邑哀王劉髆之子,從血統(tǒng)上看是西漢王朝有條件擁有最高權(quán)力的人選。漢昭帝劉弗陵是漢武帝少子,本人無后,而劉賀在輩分上比昭帝晚一輩,這樣在血緣與輩分上都比較符合入嗣的要求。這里面家族身份認同、血緣認同、政治合法性認同是捆綁在一起的,對于這樣一系列身份的認同,最主要是通過劉賀本人的印信構(gòu)建起來的。通過印信(圖一),證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就是劉賀,從而牽引出其身份的全貌。其二,個人史記錄。這其實是貫穿海昏侯展示的一條主線,其人生軌跡根據(jù)史書記載主要可以分為昌邑王、皇帝、貶謫昌邑和貶謫海昏這幾個階段。墓葬本身雖然是在其貶謫海昏之后才出現(xiàn)的,但出土物中仍舊不乏載有“昌邑十年……造”等字樣的文物[5],這至少能夠證明其出身和前后貶謫的不同經(jīng)歷,與“信史”相互印證。其三,政治等級與喪葬級別。對于反映古代個體經(jīng)歷來說,政治身份和喪葬級別其實是最常見的被拿來作為歷史推論的因素。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古代文獻和歷年來該歷史年代的發(fā)掘物品所證明的墓葬形制、隨葬品豐富程度與社會等級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即墓葬形制及隨葬品本身就構(gòu)成對其社會地位的指證。其四,生前信仰。漢代以后,關(guān)于人對死后世界的信仰在墓葬里的體現(xiàn)已經(jīng)逐漸形式化。以上四點基本就是能夠通過墓葬材料構(gòu)建起來的反映一個人生前歷程的主要內(nèi)容。這四點在劉賀墓中都比較清晰,其地表的祭祀性建筑遺存也能較為深刻地體現(xiàn)出西漢時期王侯寢、廟(祠堂)、園的結(jié)構(gòu)特征。但是,劉賀墓這類能夠明確墓主人身份的情況畢竟是極少數(shù)。

圖一//海昏侯印信
相比之下,婦好墓則屬于墓葬考古發(fā)現(xiàn)中的絕大多數(shù)情況。具體說來,墓主人身份無法真正確知,甚至性別、死亡年齡、疾病等基本特征指標都無法完全明確。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去探討墓主人的生平,恐怕也只能是奢望了。但從認知層面來講,沒有墓主人身份的墓葬實際上是無法認知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無法認定這樣一個墓葬到底屬于誰。這個“誰”,其實就是墓葬的根本屬性。所謂“生有地,死有處”,僅有墓葬而無法確知墓主,這個墓葬也就失去了“處”的真正意義。那么,所謂的這個“誰”就是由“姓名、性別、社會地位、職業(yè)、社會關(guān)系、信仰、個人歷史”等因素構(gòu)成,如果這些要素不清楚,那么這個“誰”也就無法明確。為了緩解這個“身份危機”,婦好墓展示的策劃者從可被利用的研究中尋找信息。首先,研究者對于禮器及其他出土卜辭中“婦好”二字本身的含義并無異議[6],但確認“死者”本身確實就是“婦好”則仍存在證據(jù)上的不足[7],至少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并不是“身份”直接標志物(譬如印信)。其次,但有“婦好”其名,對于完整了解一個個體的個人史,仍顯得非常單薄。這就需要更多的“間接建構(gòu)”過程。對于墓主人女性身份的鑒定結(jié)果,除了以“世婦”之稱作為證據(jù)外,則最主要來自于出土物中的部分玉牙制品,如夔首玉笄等(圖二)。事實上,單就隨葬物品,根本無法推斷墓主性別是女性。墓葬內(nèi)由于有機物過于豐富,而導致埋藏環(huán)境酸性較強,最終尸骨無存,不可能有直接的性別鑒定出現(xiàn)。這樣,人們據(jù)以推斷其為女性的主要銘文證據(jù)“婦好”就基本上成了“孤證”。關(guān)于身份,研究與展示的重點都放在“武丁”的王后和所謂“女將”上,這個論定是完全建立在器物分期基礎(chǔ)之上的。即首先將晚商的器物分為四個大的階段,并附和到兩百多年的時間跨度中進行劃分,然后再與《史記》及甲骨文所構(gòu)架出來的商王世系進行對舉。在這個框架內(nèi)確定了年代之后,又進一步將所估測的性別以及隨葬品豐富程度等因素帶入,從而認定其為卜辭中所記載的武丁之妻,而非其他時期的“婦好”同名者[8]。

圖二//婦好墓展夔首玉笄
通過上述這些能夠在器物上辨識出來的信息,研究者建構(gòu)了一個特殊的女性社會身份——婦好。從思路上講,墓主人的身份與文獻的關(guān)聯(lián)性,特別是卜辭本身對于婦好身份認同的建構(gòu),都并不是可以確切認定的。對于單個墓葬的墓主人身份認同建構(gòu)來說,墓主人的明確性是關(guān)鍵。海昏侯展示與婦好墓展示雖然都是“個體”展示,但實際上存在著本質(zhì)區(qū)別。劉賀的社會身份是完全固定和清晰的,所有的墓葬材料是用來與此清晰的“人格”進行應(yīng)和的,這一點從展示的題目即可以明確看出:驚現(xiàn)侯國、王侯威儀、劉賀其人。而婦好墓則是通過墓葬材料去構(gòu)造這樣一個不可確知的“女性人格”。這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即便是在條件并不完全具備的情況下,人們?yōu)榱苏故镜目衫斫庑裕餐鶗蚓邆涿鞔_“出處”的情況靠攏。這樣,展示設(shè)計本身就成了一種對“展示對象”的“二度創(chuàng)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對個體的社會身份認同這一概念的認知結(jié)構(gòu)。如展覽策劃者所言:從展覽的題目“王后母親女將”,用三個名詞指稱一個人——婦好。之所以這樣做——其實我們所有策劃都是為了讓觀眾喜歡、易懂,用最通俗的語言把科研成果奉獻給觀眾,在語言的把握上非常重要。展覽的序廳,包括整個展覽的一級布題,全部用的是“她”,指的就是婦好[9]。這里明顯涉及了一個轉(zhuǎn)化過程,由展覽策劃者將考古研究的結(jié)果用觀眾能夠接受的語言來轉(zhuǎn)述出來。實際上,這個轉(zhuǎn)化難度顯然是不同的:就海昏侯的展示來說,并不需要做太多這樣的轉(zhuǎn)述工作;而婦好則完全不同,這個“她”完全是用考古材料構(gòu)建出來的“所指”。
三、墓葬展示的難度
在考古遺存類展示中,墓葬一直以來都是核心展示內(nèi)容之一。在我國,展示內(nèi)容一般包括三個類別。第一類是墓葬出土文物展示,也是最簡單的展示。這類展示一般囿于出土物背景的不確定性,而只能大致描述為“喪葬用品”。多數(shù)情況下,這類展品是出于其自身突出的藝術(shù)價值特征才得以被陳列展出,談不上對于墓葬主人的任何“人格”、“個人史”的建構(gòu)。第二類則是墓葬完整,但指稱墓主人的遺物或跡象并不確鑿,這類也是墓葬材料中的常見類型。第三類,則是如海昏侯這類,通過隨葬品、墓志銘等能夠指稱墓主人身份的材料可以明確墓主生前基本歷程的墓葬類別。準確地講,婦好墓為介于二、三類之間的一種特殊情況。前兩類由于材料限制很難談及墓主人的個體歷程,因此本來應(yīng)當采用其他的展示手段,而不應(yīng)當也沒有必要去向明確的個人信息分類結(jié)構(gòu)靠攏,也不應(yīng)當在考古材料無法完全印證墓主人身份信息的情況下,對其進行任何形式的建構(gòu),這并不客觀。
回避“不知名”墓葬與信息殘缺嚴重墓葬展示難度的有效方法,其實還是來自于考古學本身。在個體認同無法確知的情況下,應(yīng)當酌情考慮將墓主人的身份進行“模糊處理”,即仍需將其大致歸于一個人群;但同時可以將能夠說明的問題進行細致分類,這些基本的問題往往還是古人吃什么、用什么、怎樣居住、有何信仰等老問題。對于多數(shù)墓葬來說,用墓葬材料去拼湊一個“可靠”的人格,是墓葬展示的“玻璃天花板”。
四、結(jié)語
將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的結(jié)果(或階段性結(jié)論),通過大眾易于接受的形式展示歷史人物個人史,特別在考古材料指向性不強、考古材料主人身份不確定的情況下,具有相當難度。這種情況下,先將材料分類:一類是以物“說事兒”,說明功用、工藝等信息即可;另一類可先將展示主體的身份進行“模糊處理”,把個體歸入群體,用群體特征展現(xiàn)個體特點。以上是對用考古資源展示“個體”過程中一般規(guī)律的探討。
[1]錢茂偉:《公眾史學視角下的個人史書寫》,《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2]Brown R.,Social Identity Theory:Past Achievements,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European Journal Social Psychology,2000,30:745-778.
[3]韓靜:《社會認同理論研究綜述》,《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4]Carr.Mortuary Practices:Their Social,Philosophical Re?ligious,Circumstantial,and Physical Determinant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95,2:2.
[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館、南昌市新建區(qū)博物館:《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
[6]韓江蘇:《殷墟婦好墓主身份辨——與張素鳳、卜師霞商榷》,《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
[7]曹定云:《殷墟婦好墓銘文中人物關(guān)系綜考》,《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5期。
[8]王宇信等:《試論殷墟五號墓的“婦好”》,《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
[9]《首博副館長:海昏侯、婦好墓展是如何策劃的》,[EB/ OL][2016-11-12]http://news.163.com/16/1112/11/C5L STMPU000187VE.html.
The Challenge of Biographical Narratives of Exhibiting Ancient Burials as Seen in the Tomb of Fu Hao Exhibition and the Haihunhou Exhibition
ZHOU Gao-liang
(The Palace Museum,Beijing,10009)
The tomb of Fu Hao exhibition and the Haihunhou exhibition are two typical examples of ex?hibitions that depict the life scenes of the society that the subject lived in.In many ways,they are of the same narrative structure as those that focus on the lives of the subjects.For the exhibitions that entirely rely on the unearthed objects due to the severe lack of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one option is to implement a“fuzzy treatment”,which means to shift the focus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groups he or she belongs to and mak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group identities.This is a solution to the cases where the subject identification is insufficient,and can be regarded a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rules of presenting individuals through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exhibition;archaeology;the tomb of Fu Hao exhibition;the Haihunhou exhibition;bio?graphical perspective;curation
G265
A
(責任編輯:王霞;校對:張蕾)
2017-04-25
周高亮(1979—),男,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館學、陶瓷考古、遺產(chǎn)保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