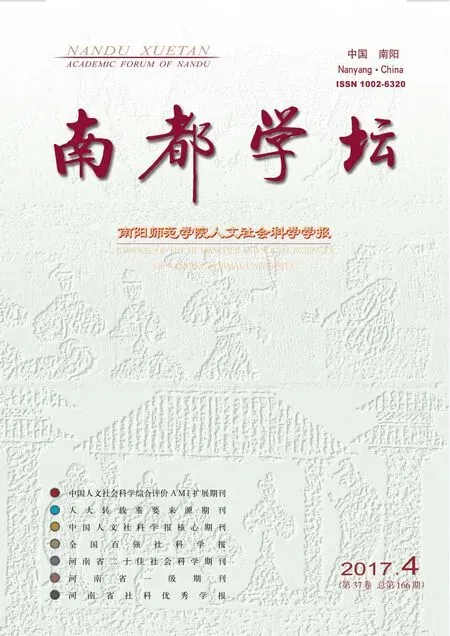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蔓延與新城鎮(zhèn)的興起
李 娟
(南陽(yáng)師范學(xué)院 文史學(xué)院,河南 南陽(yáng) 473061)
?
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蔓延與新城鎮(zhèn)的興起
李 娟
(南陽(yáng)師范學(xué)院 文史學(xué)院,河南 南陽(yáng) 473061)
自二戰(zhàn)結(jié)束以來(lái),美國(guó)郊區(qū)發(fā)展迅猛,人口數(shù)量急劇增加,經(jīng)濟(jì)產(chǎn)值比重大幅提高,深刻影響了美國(guó)城市和社會(huì)發(fā)展。然而,由于缺乏長(zhǎng)遠(yuǎn)規(guī)劃和總體規(guī)劃,廣大郊區(qū)在擴(kuò)展中逐漸形成蔓延之勢(shì),造成諸如資源浪費(fèi)、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種族和階層居住隔離加劇等問(wèn)題。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美國(guó)新城鎮(zhèn)興起。它們大都位于大都市區(qū)的郊區(qū),且以西部和南部“陽(yáng)光帶”居多。這些新城鎮(zhèn)擁有總體規(guī)劃,試圖滿足人們居住、就業(yè)、購(gòu)物、醫(yī)療、教育、休閑娛樂(lè)等全方位的要求,而且提供大量的開(kāi)放空間,倡導(dǎo)以休閑為導(dǎo)向的生活,為遏制郊區(qū)蔓延、實(shí)現(xiàn)城市健康有序地發(fā)展提供了新途徑。
郊區(qū)蔓延;總體規(guī)劃;開(kāi)放空間
美國(guó)著名城市史學(xué)者羅伯特·菲什曼(Robert Fishman)曾指出,“如果說(shuō)19世紀(jì)是(美國(guó)的)偉大城市時(shí)代,那么1945年之后則是其偉大郊區(qū)時(shí)代”[1]182。二戰(zhàn)結(jié)束后,美國(guó)郊區(qū)發(fā)展迅猛,郊區(qū)居住人口逐漸超過(guò)中心城市和非大都市區(qū),在全國(guó)人口總數(shù)中占據(jù)主體。到20世紀(jì)70年代,美國(guó)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郊區(qū)國(guó)家[2]60。“郊區(qū)是當(dāng)代美國(guó)文化最直接、最典型的代表,它在很大程度上比轎車、高層建筑或職業(yè)橄欖球更能代表美國(guó)文化,郊區(qū)是美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物質(zhì)成就。”[3]4然而,美國(guó)大多數(shù)郊區(qū)在發(fā)展中缺乏整體和長(zhǎng)遠(yuǎn)規(guī)劃,其迅猛擴(kuò)展之勢(shì)更直觀地體現(xiàn)為郊區(qū)低密度無(wú)序蔓延(sprawl),由此產(chǎn)生和引發(fā)了一系列城市與社會(huì)問(wèn)題。“美國(guó)郊區(qū)所體現(xiàn)的社會(huì)本質(zhì)特征是過(guò)度浪費(fèi)、嚴(yán)重依賴汽車、人口向上流動(dòng)、家庭分解為核心單元、工作與娛樂(lè)廣泛分離,以及種族、階層隔離。”[3]4在此背景下,美國(guó)新城鎮(zhèn)順勢(shì)而起,并逐漸受到美國(guó)社會(huì)的廣泛關(guān)注。本文擬從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蔓延的角度探討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新城鎮(zhèn)在美國(guó)興起的原因。
一、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的迅猛擴(kuò)展
(一)郊區(qū)人口數(shù)量激增
二戰(zhàn)后美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出現(xiàn)了繁榮局面,全國(guó)城市人口增長(zhǎng)也隨之迎來(lái)一個(gè)新的發(fā)展高峰,其中郊區(qū)逐漸成為重要的人口增長(zhǎng)極,與此同時(shí),郊區(qū)與中心城市共同構(gòu)成的大都市區(qū)日益成為美國(guó)城市發(fā)展的新模式①關(guān)于美國(guó)郊區(qū)與大都市區(qū)的關(guān)系可參閱孫群郎:《郊區(qū)化對(duì)美國(guó)社會(huì)的影響》,載《美國(guó)研究》1999年第3期。。
二戰(zhàn)前,中心城市是美國(guó)大都市區(qū)人口和產(chǎn)業(yè)的重心所在,這種空間格局在戰(zhàn)后二三十年的時(shí)間里逐漸被改變。如表1所示,1950年,美國(guó)大都市區(qū)人口所占比例為56.1%,超過(guò)非大都市人口(43.9%),成為美國(guó)城市發(fā)展的新模式,其中,中心城市和郊區(qū)分別占32.8%和23.3%,這一數(shù)字到1970年,分別被改寫為31.4%和37.2%,表明郊區(qū)已經(jīng)超過(guò)中心城市,成為美國(guó)大都市區(qū)人口增長(zhǎng)的主體。
(二)郊區(qū)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大增
美國(guó)郊區(qū)在發(fā)展之初,嚴(yán)重依賴城市中心,特別是在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和就業(yè)等方面,郊區(qū)實(shí)際上是中心城市的“臥城”或工業(yè)衛(wèi)星城,郊區(qū)功能非常單一。因此,城市在空間布局上呈現(xiàn)出單一中心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到了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這一格局逐漸被改變,郊區(qū)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獲得迅猛發(fā)展,就業(yè)崗位也大量增加,美國(guó)城市空間結(jié)構(gòu)的多中心化發(fā)展趨勢(shì)日益明顯。許多工廠業(yè)主為了減少地租、稅收等成本支出,在廉價(jià)的土地上建立大規(guī)模的流水線生產(chǎn)模式,紛紛從中心城市遷往郊區(qū),工業(yè)園如雨后春筍般在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涌現(xiàn)。有研究者估計(jì),到1963年,美國(guó)郊區(qū)大約聚集了“全國(guó)一半以上的制造業(yè)”[3]267。制造業(yè)的郊區(qū)化帶動(dòng)了商業(yè)、服務(wù)業(yè)以及政府機(jī)構(gòu)向郊區(qū)遷移,郊區(qū)購(gòu)物中心、辦公園數(shù)量不斷增加,極大地促進(jìn)了郊區(qū)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郊區(qū)就業(yè)機(jī)會(huì)也隨之大量增加。據(jù)估算,1950—1970年間,美國(guó)郊區(qū)在所有新的制造業(yè)和零售業(yè)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崗位中,所占比例至少為四分之三[1]182。

表1 美國(guó)人口數(shù)量及空間分布統(tǒng)計(jì)表(1940—1970年)
資料來(lái)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AbstractoftheUnitedStates: 1990(110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p.7;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PopulationDeconcentrationintheUnitedStates:SpecialDemographicAnalysi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65.
二、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的無(wú)序蔓延
郊區(qū)人口數(shù)量的激增以及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凸顯是戰(zhàn)后美國(guó)城市和社會(huì)發(fā)展與進(jìn)步的重要體現(xiàn)。然而,大多數(shù)郊區(qū)在開(kāi)發(fā)過(guò)程中都缺乏整體和長(zhǎng)遠(yuǎn)規(guī)劃,由此造成的資源浪費(fèi)、生態(tài)環(huán)境和景觀破壞、種族和階層隔離等問(wèn)題*相關(guān)問(wèn)題可參閱孫群郎:《當(dāng)代美國(guó)郊區(qū)的蔓延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危害》,載《世界歷史》2006年第5期;《美國(guó)郊區(qū)化進(jìn)程中的黑人種族隔離》,載《歷史研究》2012年第6期。不斷加劇,而且呈現(xiàn)出蔓延加劇之勢(shì),使美國(guó)城市和社會(huì)發(fā)展面臨嚴(yán)峻考驗(yàn)。
按照美國(guó)當(dāng)代學(xué)者的觀點(diǎn),城市生長(zhǎng)主要有兩種方式:傳統(tǒng)的鄰里社區(qū)式和郊區(qū)蔓延式。傳統(tǒng)的鄰里社區(qū)式是城市生長(zhǎng)的“自然方式”,它是二戰(zhàn)前美國(guó)城市發(fā)展的主要形式。按照這種方式形成的城市充滿了人文關(guān)懷,功能多樣,日常生活所需都在步行可達(dá)的范圍之內(nèi)。而郊區(qū)蔓延式則是一種“人為方式”,是建筑師、工程師和規(guī)劃師設(shè)計(jì)和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該方式在二戰(zhàn)后逐漸成為一種城市發(fā)展的“理想化模式”和標(biāo)準(zhǔn)方式。
通常說(shuō)來(lái),郊區(qū)蔓延主要由五個(gè)要素構(gòu)成。第一,只有居住功能的住宅區(qū)(housing subdivisions),又稱集合式住宅區(qū)(clusters);第二,帶狀或大型購(gòu)物中心,它們大都沿公路分布,遠(yuǎn)離住宅區(qū),以單層建筑為主,擁有大片的停車場(chǎng);第三,工業(yè)園、商業(yè)區(qū)和辦公園,它們僅提供工作的場(chǎng)所;第四,公共機(jī)構(gòu),如學(xué)校、教堂、市政廳等,它們提供文化交流和溝通的場(chǎng)所;第五,將上述四個(gè)彼此孤立的要素連接在一起的公路[4]。
對(duì)美國(guó)而言,戰(zhàn)后郊區(qū)蔓延之勢(shì)的形成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第一,人口和住房低密度擴(kuò)張,人口居住的凈密度從每英畝10戶下降到6戶,后來(lái)又降到每英畝只有1~4戶。萊維敦作為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的典型代表,其人口密度比半個(gè)世紀(jì)以前街車郊區(qū)的人口密度低一半以上。街車時(shí)代郊區(qū)的宅地面積平均為3000平方英尺,而汽車郊區(qū)的宅地面積平均為5000平方英尺[3]185,239。第二,嚴(yán)重依賴汽車。由于居住區(qū)、工業(yè)園、商業(yè)區(qū)與公共機(jī)構(gòu)處于不同的分區(qū),相互之間距離較遠(yuǎn),步行難以到達(dá),所以人們?cè)絹?lái)越依靠汽車出行。“在郊區(qū)只有一種生活方式,即擁有一輛汽車,并依靠它獲取每種需求。”在郊區(qū)擴(kuò)張的過(guò)程中,各社區(qū)沿高速公路呈帶狀分布,尤其是那些產(chǎn)業(yè)郊區(qū),如工業(yè)園區(qū)、購(gòu)物中心和辦公園區(qū)等,在公路兩側(cè)形成長(zhǎng)廊。第三,社區(qū)具有強(qiáng)烈的同質(zhì)性。廣大郊區(qū)都實(shí)行嚴(yán)格的分區(qū)制,對(duì)郊區(qū)的住宅面積、街道的寬度等都做了明確的規(guī)定,而且逐漸形成了將少數(shù)種族和社會(huì)下層階級(jí)排斥在外的居住隔離,使郊區(qū)具有強(qiáng)烈的同質(zhì)性和排他性。
在20世紀(jì)中期以前,盡管美國(guó)郊區(qū)擴(kuò)張也引起了許多社會(huì)和環(huán)境問(wèn)題,但由于規(guī)模較小,其破壞性影響尚不明顯。美國(guó)城市史學(xué)家劉易斯·芒福德指出,當(dāng)郊區(qū)只是“少數(shù)人的喜好”時(shí),它既沒(méi)有破壞鄉(xiāng)村也沒(méi)有威脅城市。但當(dāng)郊區(qū)化成為“大眾化的運(yùn)動(dòng)”時(shí),它對(duì)鄉(xiāng)村和城市環(huán)境所造成的破壞,將剝奪郊區(qū)“最本質(zhì)的價(jià)值”[5]。
總之,美國(guó)城市在二戰(zhàn)結(jié)束后進(jìn)入新的發(fā)展階段,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生調(diào)整,大都市區(qū)空間組織結(jié)構(gòu)隨之發(fā)生變化。盡管聯(lián)邦政府自戰(zhàn)后實(shí)施的城市更新計(jì)劃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了應(yīng)有的成效,但無(wú)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心城市的衰落之勢(shì)。郊區(qū)在大都市區(qū)中的地位和影響日新月異,但又普遍缺乏規(guī)劃,導(dǎo)致城市在景觀、功能、環(huán)境和社會(huì)等方面出現(xiàn)越來(lái)越多的問(wèn)題,許多城市規(guī)劃師、建筑師、社會(huì)改革者以及政府官員開(kāi)始將目光投向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將新城鎮(zhèn)視為改革郊區(qū)蔓延的一種方式。
三、美國(guó)新城鎮(zhèn)的興起
美國(guó)新城鎮(zhèn)是由私人開(kāi)發(fā)商發(fā)起和主導(dǎo)開(kāi)發(fā)的,即使是聯(lián)邦政府參與或支持的新城鎮(zhèn)項(xiàng)目,也是由私人開(kāi)發(fā)商主導(dǎo)的。這些開(kāi)發(fā)商各自有著不同的目標(biāo)和規(guī)劃,他們所開(kāi)發(fā)的新城鎮(zhèn)在特征上呈現(xiàn)出很多差異性。但總體而言,它們?cè)诤芏喾矫嬗执嬖谥嗨菩裕哂性S多共同特征。概括說(shuō)來(lái),美國(guó)新城鎮(zhèn)在興起過(guò)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共同特征。
2010~2015年,山東省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機(jī)構(gòu)醫(yī)生的工作量變化穩(wěn)定,但是從診療人才看,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wù)中心的診療人次明顯增加,住院人次變化不明顯,與我國(guó)整體的變化趨勢(shì)相同。目前基層醫(yī)療衛(wèi)生機(jī)構(gòu)承擔(dān)的入院量較小,很多即使初診于基層醫(yī)療機(jī)構(gòu),但后期住院服務(wù)會(huì)選擇上一級(jí)別的醫(yī)療機(jī)構(gòu),居民對(duì)基層醫(yī)療機(jī)構(gòu)的信任水平?jīng)]有建立,需要進(jìn)一步加大基層醫(yī)療機(jī)構(gòu)建設(shè)的力度,保證首診基層,實(shí)現(xiàn)合理分級(jí)診療的目的[7-9]。
(一)空間分布以“陽(yáng)光帶”為主
新城鎮(zhèn)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它的空間地理分布是與戰(zhàn)后美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布局調(diào)整相一致的。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以西部和南部為主的“陽(yáng)光帶”城市獲得迅猛發(fā)展,許多城市逐漸脫穎而出,與東北部和中西部“冰雪帶”的傳統(tǒng)工業(yè)城市形成鮮明對(duì)比。據(jù)統(tǒng)計(jì),1940—1970年間,在全美61個(gè)增長(zhǎng)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大都市區(qū)中,有44個(gè)位于西部和東南部的“陽(yáng)光帶”[2]17。這些地區(qū)城市發(fā)展的顯著特點(diǎn)是產(chǎn)業(yè)與人口同步郊區(qū)化,這與東北部和中西部城市所經(jīng)歷的人口郊區(qū)化在先、產(chǎn)業(yè)郊區(qū)化在后的發(fā)展道路是不相同的,西部和南部廣袤的土地資源使其城市布局從一開(kāi)始就可以借助新城鎮(zhèn)規(guī)劃來(lái)避免無(wú)序擴(kuò)張的城市發(fā)展模式。因此,新城鎮(zhèn)在空間地理分布上以“陽(yáng)光帶”為主。據(jù)統(tǒng)計(jì),到20世紀(jì)70年代中期,在全美141個(gè)新社區(qū)開(kāi)發(fā)項(xiàng)目(包括普通的大規(guī)模開(kāi)發(fā)項(xiàng)目)中,西部和南部城市占68%[6]。另有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加利福尼亞新城鎮(zhèn)數(shù)量占全國(guó)新城鎮(zhèn)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國(guó)超過(guò)一半的新城鎮(zhèn)集中在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和佛羅里達(dá)三個(gè)州。
對(duì)絕大多數(shù)美國(guó)新城鎮(zhèn)而言,它們基本上都位于或靠近大都市區(qū),主要是大都市區(qū)的郊區(qū)。這些新城鎮(zhèn)倡導(dǎo)自足獨(dú)立,致力于發(fā)展成為融居住、就業(yè)、生活、休閑、娛樂(lè)等城市功能于一體的新型城市,因而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衛(wèi)星城或臥城相比,功能更加多元,獨(dú)立性更加突出。這種類型的新城鎮(zhèn)是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美國(guó)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的主要類型。據(jù)統(tǒng)計(jì),在當(dāng)時(shí)全美58個(gè)新城鎮(zhèn)中,與中心城市距離在30英里之內(nèi)的有46個(gè),約占總數(shù)的4/5。其中,距離在0~10英里范圍內(nèi)的有7個(gè),占12.5%;11~20英里的有21個(gè),占36.2%;21~30英里的有18個(gè),占31%[7]。這些新城鎮(zhèn)主要集中于洛杉磯、休斯頓、巴爾的摩——華盛頓等大都市區(qū)。僅在華盛頓大都市區(qū)30英里輻射范圍內(nèi)就有4個(gè)新城鎮(zhèn),即弗吉尼亞的雷斯頓、馬里蘭的哥倫比亞、馬里蘭的圣查爾斯和華盛頓特區(qū)的林肯堡(Fort Lincoln)。除此之外,還有少數(shù)幾個(gè)獨(dú)立性更強(qiáng)的新城鎮(zhèn),它們建在非大都市區(qū)或農(nóng)村地區(qū),例如,北卡羅來(lái)納州的蘇爾城(Soul City)。它們后來(lái)的開(kāi)發(fā)歷程可以說(shuō)是舉步維艱,困難重重,不得不宣告失敗。與之相反,也有一些新城建在百萬(wàn)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形成所謂的城中新城(new town-in town),如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錫達(dá)河濱(Cedar-Riverside)、紐約的羅斯福島(Roosevelt Island)等。這些城中新城在實(shí)際的開(kāi)發(fā)過(guò)程中受到復(fù)雜環(huán)境和因素的制約,逐漸偏離了最初的規(guī)劃目標(biāo),變得與普通社區(qū)并無(wú)實(shí)質(zhì)區(qū)別,有的甚至成為富人社區(qū)或高級(jí)公寓。
(二)總體規(guī)劃以田園城市、雷德本體系和鄰里單位概念有機(jī)融合為原則
總體規(guī)劃(master plan)是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的重要步驟,也是新城鎮(zhèn)的顯著特征和“新意”所在。自20世紀(jì)20年代,美國(guó)城市社區(qū)規(guī)劃普遍遵循的是功能分區(qū)原則,對(duì)土地實(shí)行單一規(guī)劃和開(kāi)發(fā),因而開(kāi)發(fā)商或組織實(shí)行的是零散規(guī)劃(piecemeal plan)。1916年,紐約市通過(guò)了第一個(gè)綜合性分區(qū)制法規(guī),對(duì)土地利用類型、建筑物的容積率等進(jìn)行了全方位規(guī)范和限制。就土地利用類型而言,首先是居住或住宅用地屬于最高級(jí)別,擁有優(yōu)先權(quán),其次是商業(yè)用地,最后是工業(yè)用地。較高級(jí)別的土地利用模式可以出現(xiàn)在較低級(jí)別的土地分區(qū)內(nèi),即住宅特別是獨(dú)戶住宅可以建在任何地方,而工業(yè)用地只能建在工業(yè)分區(qū)內(nèi),形成累進(jìn)制分區(qū)[8]。分區(qū)制的初衷是為了保護(hù)人們的健康、安全等合法權(quán)益,但在實(shí)踐過(guò)程中卻成為郊區(qū)地方政府實(shí)施居住排他性和種族及階層隔離的重要依據(jù)。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也大都是采用這種模式開(kāi)發(fā)和發(fā)展起來(lái)的。
與傳統(tǒng)郊區(qū)的零散規(guī)劃不同,新城鎮(zhèn)實(shí)行的是總體規(guī)劃。在項(xiàng)目開(kāi)始之前,開(kāi)發(fā)商召集規(guī)劃師、建筑師、社會(huì)學(xué)家、景觀設(shè)計(jì)師、心理學(xué)家等組成規(guī)劃小組,通過(guò)反復(fù)討論與協(xié)商,制訂既符合居民多樣化需求又能實(shí)現(xiàn)社區(qū)合理有序發(fā)展的長(zhǎng)遠(yuǎn)規(guī)劃。這不僅反映了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美國(guó)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對(duì)人們居住模式的影響,即要求打破由傳統(tǒng)分區(qū)制人為演化而成的各種隔離,而且體現(xiàn)了人們保護(hù)土地、森林等自然資源開(kāi)發(fā)的環(huán)保思想的進(jìn)步。美國(guó)新城鎮(zhèn)開(kāi)拓者羅伯特·西蒙(Robert E. Simon)在對(duì)雷斯頓(Reston)新城鎮(zhèn)進(jìn)行規(guī)劃時(shí)指出:“我們開(kāi)始的是一項(xiàng)程序,而非規(guī)劃。我們要問(wèn)自己可以為人們提供什么,而不是處理土地。這就像圣誕節(jié)為人們提供禮物一樣。”[9]為此,西蒙不僅聘請(qǐng)了紐約著名的建筑規(guī)劃公司——懷特康克林(Whittlesey and Conklin),而且還聘請(qǐng)了心理學(xué)家、社會(huì)學(xué)家、休閑和宗教專家,共同商討制訂總體規(guī)劃,將教育、文化、居住和工業(yè)設(shè)施有機(jī)地融合在一起。按照總體規(guī)劃,雷斯頓將被建成一個(gè)城市化的郊區(qū)社區(qū)。哥倫比亞新城鎮(zhèn)的創(chuàng)建者詹姆斯·羅斯也提出,城市規(guī)劃應(yīng)當(dāng)與社會(huì)科學(xué)相結(jié)合。他在組建公司工作團(tuán)隊(duì)時(shí),專門聘請(qǐng)了政府、家庭生活、休閑、社會(huì)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教育、醫(yī)療、心理學(xué)、住房、交通和通訊等領(lǐng)域的專家,目的是為建立一個(gè)好的城市——“下一個(gè)美國(guó)”(The Next America)集思廣益。
按照總體規(guī)劃設(shè)計(jì)的新城鎮(zhèn)在規(guī)模方面要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傳統(tǒng)的郊區(qū)社區(qū)。盡管沒(méi)有關(guān)于新城鎮(zhèn)規(guī)模的明確規(guī)定,但除城中新城鎮(zhèn)的土地較小,大約只有數(shù)百英畝外,絕大多數(shù)新城鎮(zhèn)的規(guī)模都在數(shù)千英畝以上。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顯示,最小的新城鎮(zhèn)占地2700英畝,其人口數(shù)量在8000人左右[11],比較成功的新城鎮(zhèn)占地一般接近或超過(guò)一萬(wàn)英畝,計(jì)劃容納10萬(wàn)~40萬(wàn)人。如哥倫比亞新城鎮(zhèn)最初規(guī)劃占地14272英畝,目標(biāo)人口11萬(wàn),到2000年,其土地?cái)U(kuò)展到17705英畝,但居民人口只有88254人。歐文新城鎮(zhèn)最初占地29376英畝,目標(biāo)人口40萬(wàn),到2000年,土地增到29758英畝,實(shí)際居民只有20萬(wàn)[12]。如此大規(guī)模的開(kāi)發(fā)需要開(kāi)發(fā)商在開(kāi)發(fā)之前制定目標(biāo)長(zhǎng)遠(yuǎn)、通盤考慮的總體規(guī)劃,開(kāi)發(fā)周期一般為15~20年。
(三)城市功能以平衡與自足為發(fā)展目標(biāo)
城市功能,簡(jiǎn)單說(shuō)來(lái)就是城市的用途,它是由人們的各種活動(dòng)決定的。因此,城市實(shí)際是人們活動(dòng)的空間場(chǎng)所和載體。《雅典憲章》指明城市具有四大活動(dòng)職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美國(guó)郊區(qū)在發(fā)展之初主要是城市功能的外延,分擔(dān)城市人口和主要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因而很多郊區(qū)只是功能非常單一的“臥城”或工業(yè)衛(wèi)星城、公司城鎮(zhèn)等,郊區(qū)的基本特征是居住與工業(yè)分離。然而,隨著郊區(qū)人口的大量增加,郊區(qū)產(chǎn)業(yè)和就業(yè)機(jī)會(huì)也不斷增多,逐漸與城市中心形成鼎足而立之勢(shì)。
針對(duì)大多數(shù)郊區(qū)存在的功能單一、發(fā)展失衡等問(wèn)題,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商提出了平衡與自足的發(fā)展目標(biāo),目的是要在郊區(qū)建立一種自足與平衡的城市化社區(qū)。新城鎮(zhèn)所要提供的正是傳統(tǒng)郊區(qū)忽略和缺乏的,如便利的公共交通、完備的公共設(shè)施、完善的公園綠地等。總之,新城鎮(zhèn)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土地。這主要包含兩大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指社區(qū)居民,他們有不同的種族、收入、宗教、年齡、教育和職業(yè)等背景,新城鎮(zhèn)居民中既有白人,又有黑人;既有富人,也有窮人;既有年輕人,也有老年人。二是指社區(qū)功能,不是局限于單一的居住或工業(yè)功能,而是既有住宅,又有工廠企業(yè)、購(gòu)物中心、學(xué)校、教堂等機(jī)構(gòu)設(shè)施,能夠滿足人們居住、就業(yè)、購(gòu)物、休閑娛樂(lè)等設(shè)施。許多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商認(rèn)識(shí)到,美國(guó)城市發(fā)展的趨勢(shì)是為郊區(qū)工業(yè)的發(fā)展做出規(guī)劃,而不是禁止工業(yè)的發(fā)展。
為此,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商在規(guī)劃中試圖引入許多高科技工業(yè)園、輕工業(yè)企業(yè)等,一方面可以為社區(qū)居民提供更廣泛的就業(yè)選擇,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社區(qū)稅收來(lái)源,有利于社區(qū)的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在此過(guò)程中,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商將社區(qū)規(guī)劃與其所在地區(qū)的整體規(guī)劃相結(jié)合,試圖創(chuàng)造豐富多樣的社區(qū)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按照雷斯頓的總體規(guī)劃,其土地實(shí)行混合利用,土地的主要用途被分為8類:低、中和高密度居住區(qū);商業(yè)區(qū);就業(yè)中心;永久空地;汽車場(chǎng)地;道路、公共設(shè)施及其他[13]。
(四)開(kāi)發(fā)模式可為居民提供大量開(kāi)放空間
城市開(kāi)放空間理論(Open Space)源自19世紀(jì)下半葉快速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所導(dǎo)致的嚴(yán)重公共衛(wèi)生、環(huán)境問(wèn)題、城市公共用地不足等問(wèn)題。1877年,英國(guó)《大都市開(kāi)發(fā)空間法》(MetropolitanOpenSpaceAct)將城市開(kāi)放空間定義為:不圍合、無(wú)建筑,或是少于1/20的城市土地有建筑物,其他土地用來(lái)興建公園或娛樂(lè)設(shè)施,或閑置。20世紀(jì)60年代,許多城市規(guī)劃學(xué)家、生態(tài)學(xué)家、環(huán)境學(xué)家等進(jìn)一步發(fā)展和豐富了這一理論。總之,城市開(kāi)放空間是指城市內(nèi)部及周邊具有較高生態(tài)保護(hù)、景觀美學(xué)、休閑游憩、防震減災(zāi)、歷史文化保護(hù)等生態(tài)、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非建筑或少于建筑用地的空間形式,包括綠地、水域和廣場(chǎng),承擔(dān)著城市形態(tài)建構(gòu)、社會(huì)空間融合、城市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維護(hù)的重要功能[14]。
美國(guó)郊區(qū)社區(qū)的傳統(tǒng)開(kāi)發(fā)模式致使開(kāi)放空間普遍缺乏,為此,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商提出將為居民提供大量的開(kāi)放空間。例如,哥倫比亞新城鎮(zhèn)在總體規(guī)劃中預(yù)留了3200英畝土地免于開(kāi)發(fā)——占項(xiàng)目總面積的20%。在雷斯頓,公園占地大約3000英畝,還有多個(gè)人工湖和自然湖[10]32。新城鎮(zhèn)倡導(dǎo)以休閑為導(dǎo)向的生活,它們通過(guò)利用河流、湖泊、森林等自然風(fēng)光,為廣大居民提供休閑、游憩的場(chǎng)所,以實(shí)現(xiàn)許多新城鎮(zhèn)在銷售手冊(cè)中所強(qiáng)調(diào)的“陽(yáng)光下的快樂(lè)”。雷斯頓的每個(gè)村都有不同的主題,如騎馬愛(ài)好者的馬場(chǎng)、水上運(yùn)動(dòng)愛(ài)好者的人工湖以及高爾夫球場(chǎng)等。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商相信,新城鎮(zhèn)將是一個(gè)父母自愿工作的地方,一個(gè)孩子們可以盡情玩耍的地方,在操場(chǎng)上、游泳池里、球類場(chǎng)地上都可以聽(tīng)到他們縱情的歡笑聲。
四、結(jié)語(yǔ)
戰(zhàn)后美國(guó)郊區(qū)發(fā)展勢(shì)頭迅猛,不僅郊區(qū)人口急劇增加,在大都市區(qū)中所占的比重逐漸趕上并超過(guò)中心城市,成為大都市區(qū)發(fā)展的主導(dǎo),而且郊區(qū)經(jīng)濟(jì)產(chǎn)值所占比重也大幅提高,郊區(qū)工業(yè)園、購(gòu)物中心、辦公園等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一方面,這是美國(guó)城市和社會(huì)發(fā)展的重要成就;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數(shù)郊區(qū)都缺乏長(zhǎng)遠(yuǎn)規(guī)劃和總體規(guī)劃,在迅速擴(kuò)展中逐漸形成蔓延之勢(shì),造成諸如資源浪費(fèi)、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種族和階級(jí)居住隔離加劇等問(wèn)題。到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美國(guó)新城鎮(zhèn)順勢(shì)興起。它們大都位于大都市區(qū)的郊區(qū),且以西部和南部“陽(yáng)光帶”居多,突破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衛(wèi)星城或臥城的發(fā)展模式,功能更加多元,獨(dú)立性更加突出。這些新城鎮(zhèn)不同于傳統(tǒng)郊區(qū)的零散規(guī)劃,而實(shí)行總體規(guī)劃,將田園城市、雷德本體系和鄰里單元有機(jī)融合,試圖在郊區(qū)建立一種自足與平衡的城市化社區(qū),以滿足人們居住、就業(yè)、購(gòu)物、醫(yī)療、教育、休閑娛樂(lè)等全方位的要求,而且提供大量的開(kāi)放空間,以實(shí)現(xiàn)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所強(qiáng)調(diào)的“陽(yáng)光下的快樂(lè)”,從而為遏制郊區(qū)蔓延、實(shí)現(xiàn)城市健康有序的發(fā)展提供了新途徑。
[1]ROBERT FISHMAN. 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ia[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7:182.
[2]CARL ABBOTT. The New Urban America: Growth and Politics in Sunbelt Cities[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3]KENNETH T.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ANDRES DUANY. Elizabeth Plater-Zyberk and Jeff Speck, Suburban Nation: The Rise of Spraw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M]. New York: North Point Press, 2000:3-7.
[5]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32.
[6]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New Towns: National Reports of the U.S. and the U.S.S.R.[A]. 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1981:6,7,
[7]REID EWING. Developing Successful New Communities[A]. Washington: The Urban Land Institute, 1991:9.
[8]孫群郎. 美國(guó)地方土地利用分區(qū)制與大都市區(qū)的低密度蔓延[J].鄭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6):161.
[9]NICHOLAS DAGEN BLOOM. Suburban Alchemy: 1960s New Tow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M].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18.
[10]CARLOS C. CAMPBELL. New Towns: Another Way to Live[M]. Reston: Res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11]RICHARD W.HELBOCK. New Towns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68, 20(4):244-245.
[12]ANN FORSYTH. Planning Lessons from Three U.S. New Towns of the 1960s and 1970s: Irvine, Columbia, and The Woodland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2, 68(4):388.
[13]CAROL A. CHRISTENSEN. The American Garden City and the New Towns Movement[M].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6:109.
[14]邵大偉.城市開(kāi)放空間格局的演變、機(jī)制及優(yōu)化研究——以南京主城區(qū)為例[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2011:1-3.
[責(zé)任編輯:岳 嶺]
2017-03-20
2014年河南省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項(xiàng)目“美國(guó)新城鎮(zhèn)開(kāi)發(fā)的歷史考察(1960—1980)”,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4CLS011;2014年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xiàng)目“美國(guó)聯(lián)邦政府的新鎮(zhèn)政策與啟示”,項(xiàng)目編號(hào):2014-qn-319。
李娟(1980— ),女,山東省萊蕪市人,歷史學(xué)博士,講師,主要從事美國(guó)城市史研究。
K712
A
1002-6320(2017)04-0029-05
- 南都學(xué)壇的其它文章
- 有限理性條件下小微企業(yè)集群融資道德風(fēng)險(xiǎn)的演化博弈
- 互聯(lián)網(wǎng)與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研究
——基于我國(guó)31個(gè)省份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檢驗(yàn) - 從社會(huì)管理到社會(huì)治理:創(chuàng)新的經(jīng)驗(yàn)、反思與新常態(tài)
——對(duì)38個(gè)社會(huì)管理創(chuàng)新綜合試點(diǎn)的分析 - 開(kāi)發(fā)區(qū)管委會(huì)規(guī)范性文件的行政訴訟附帶審查問(wèn)題
——從上海自貿(mào)區(qū)“行政異議審查”談起 - 中國(guó)反腐敗追贓執(zhí)法合作的困境及其破解
- 北周以降開(kāi)封興衰與城市空間規(guī)模盈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