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華文化的燃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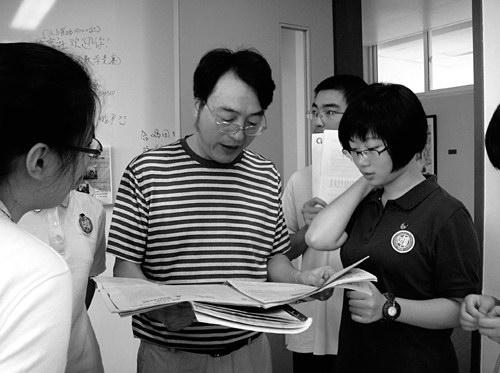
作者簡介:
黃榮華,特級教師,復(fù)旦大學(xué)附屬中學(xué)語文教研組長,國家級教學(xué)成果獎一等獎獲得者,國家“萬人計劃”領(lǐng)軍人才。長期探索并踐行“‘生命體驗與‘文化貫通相融相生的語文教學(xué)”撰有《生命體驗與語文學(xué)習(xí)》等10余部著作。
什么是“具有中國心的現(xiàn)代文明人”?我認為是一個基座和三個支點:一個基座是“中國立場”;三個支點是“世界眼光”“宇宙意識”和“人類情懷”倘若沒有“中國立場”,這個基座,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的三個支點就都無處可立。
“大”就是站立在天地間的“人”
小時候跟父親挖紅薯,挖到一個很大很大的,看了半天,突然問:“爹,‘大字為什么是‘人字上面加一橫?”
父親愣了一下,緩緩地伸直腰,站定,張開雙臂,說:“看我,這就是‘大。‘大就是站立在天地間的‘人。‘大就是‘人,‘人就是‘大。”
至今想不起來,為什么看到大紅薯,會追問父親“大”的寫法。但追問這件事我記下了,“‘大就是站立在天地間的‘人”這句話我記下來了。
應(yīng)當是長大一點了,哥哥不知從哪里弄來一本翻破了的書。我跑過去搶在手里,一看叫《四角號碼新詞典》。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詞典。隨手一翻,竟翻到這個詞語——“伸手不見五指”。我激動得不行,因為頭天晚上要跑到山上去與小伙伴野,母親說:不能去,伸手不見五指。沒有想到,這詞典里會有母親說的話!哥哥告訴我,這個詞典里不僅有母親說的話,還有父親說的話,還有很多人說的話。你讀了,就會說很多很多以前不會說的話。
不用說,我很快愛上了這本詞典,通過自學(xué)也很快學(xué)會了四角號碼查字法,經(jīng)常很神氣地對小伙伴說,報出你想查的字,我馬上可以翻到它在哪一頁。百發(fā)百中,讓小伙伴羨慕不已。在根本沒有書可讀的年代,在連得到任何一張字紙也要從頭看到尾的年代,這本詞典無疑將我?guī)нM了另一個天地。后來我得到的第一個有點“學(xué)術(shù)”含量的獎,就是1981年讀師專時查字典比賽獲得的二等獎。再后來,買辭書成了習(xí)慣,現(xiàn)在書柜里這類圖書已是滿滿兩大排。
說起字典詞典,就必定想起哥哥。他不只帶來了那本翻破了的《四角號碼新詞典》。1978年的冬天,我正準備跟大伯父去山里采藥,出發(fā)時哥哥過來問我:現(xiàn)在征訂新出版的《辭源》,你要不要?我點點頭。第二年冬天,哥哥給我拿來了《辭源》第一冊。我捧著它,不知說什么好。等哥哥走了,看到定價是5.7元,我哭了!哥哥那時是民辦教師,一個月掙300多工分,1個工分約值2分錢。這是哥哥將近一月的工資啊!而哥哥這時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1984年,我買齊了全部四冊《辭源》。讓我遺恨終生的是,1985年暑假,也就是我當教師一年后,小偷鉆到我的寢室,偷走了我的大部分圖書,其中就有哥哥送的那本《辭源》。現(xiàn)在書櫥里的兩部《辭源》,一部是1989年夏天在開封禹王臺附近的一個小書店買到的新版,一部是岳父贈送的民國四年出版的由鄭孝胥署檢的老版。
與漢字相關(guān)的書,現(xiàn)在最讓我不忍釋手的,是在北京王府丼新華書店買到的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xué)概要》和臧克和先生的《說文解字的文化說解》。那是1997年暑假,和妻子一起帶孩子去北京醫(yī)眼,抽空跑了幾家大書店,買了一大堆書。臨回時,還戀戀不舍,又跑了一趟王府丼書店,竟一下就撞上這兩本大著。正是這兩本大著,將我對漢字的喜愛一下子激發(fā)出來,回到家里,我就冒昧地給在上海的臧克和先生寫了求學(xué)信。臧先生很快復(fù)信,并寄贈了大著《漢字單位觀念史考述》。這年冬天,我赴上海拜訪了臧先生,臧先生對我已開始寫作的“漢字與民族美意識”100題給予了肯定、支持與指導(dǎo)。至2004年,我完成了100題的寫作,結(jié)集為《穿行在漢字中》,作為復(fù)旦附中校本教材“大視野教育書系”的一本于2008年出版。在書的后記中我寫道:
漢字對我們的影響,超過了任何別的力量。為什么?……我們每個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就生活在這樣的漢字文化中。我們的言行,我們的生存方式,我們的一切,都注釋著漢字;也可以反過來說,漢字在注釋著我們的一切——漢字是我們的命根!
正是有了對漢字的這種認識與理解,我不僅有意識地將漢字文化融進曰常的教學(xué),還開設(shè)“漢字單元文化”選修課,于2000年完成了對自己來說非常重要的三篇文章——《語文學(xué)習(xí)的第一要素是生命體驗》《中學(xué)語文建立“漢字單元文化”概念的探討》和《全球化時代漢語詩性特征的價值想象》;作為復(fù)旦附中人文實驗班的學(xué)習(xí)匯報,于2003年編輯了《復(fù)旦附中學(xué)報》專輯《穿行在漢字中》;于2005年完成了《“中學(xué)語文建立‘漢字單元文化概念”研究報告》并獲區(qū)級科研成果獎;2015年完成了“上海市民健康與人文系列讀本”之《漢字的故事》。現(xiàn)在回頭檢視2000年以來10多年的語文教育實踐,我確實是以漢字及其文化的認知、理解與欣賞作為核心展開的。
生活言語中的先袓氣韻與生活古意
“誰能歌祖詩章?”是我們黃家正月初一聚集祠堂祭祖時齊誦祭文的最后一句。
我第一次參加祭祖是1979年正月初一。也是那年春節(jié),第一次參加了玩龍燈、唱菩薩戲。這些第一次也應(yīng)當都是“文革”結(jié)束后的第一次。現(xiàn)在,老家的龍燈和菩薩戲都早已淡下去了,祭祖卻還一直保持著。
起初我不明白祭文為什么這樣結(jié)尾,后來慢慢明白了,它是對先祖黃庭堅的深切緬懷,是對黃氏家族后無來者的無限痛惜,是對黃氏家族中興的拳拳期盼。
據(jù)家譜,我們屬黃庭堅長孫黃黔后代,所居地古藤源,自黃黔遷居至此至今已有800多年了。也就是說,我們居住的村子可上溯至南宋后期。不知經(jīng)歷了多少天災(zāi)與變亂,除了明末重修的祠堂,這里現(xiàn)在已找不到什么歷史遺痕,只是從老人講述的故事和他們的生活言語中還能約略感知到些許先祖氣韻與生活古意。
夏天乘涼或冬天烤火,許多人聚在一起時,老人總會津津樂道黃庭堅“一石二丼”“知難發(fā)憤”“滌親溺器”“蘇黃譏書”“十日誦春秋”“舉進士修實錄”等故事。應(yīng)當是受到這些故事的影響,后來我愛上了黃庭堅,走訪了他當年讀書的一些地方,也買了不少相關(guān)的圖書。隨著閱讀的加深,我也慢慢感到近幾十年的文學(xué)史和文化史研究對黃庭堅有很大的偏見。宋明清三代,學(xué)習(xí)黃庭堅的詩與書是全社會的文化風尚。這里當然有很復(fù)雜的因素,但一定是與他詩書的高品質(zhì)緊密相連的。而今天,能識得黃庭堅的人卻極少極少。
2011年我?guī)W(xué)生游學(xué)臺灣,站在黃庭堅最負盛名的《松風閣》前久久不愿離開,待到再也不能忍受一批又一批無知的臺灣或大陸導(dǎo)游與游客的無知評說才悲傷地離去。2013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黃庭堅自己最得意、對現(xiàn)代印象派多有啟發(fā)的草書巨卷《廉頗藺相如列傳》在上海博物館展出,我?guī)W(xué)生去觀瞻發(fā)現(xiàn),除了我的學(xué)生,愿意在此作較多停留的參觀者真的很少,這幅草書巨卷顯得那樣的高冷與孤寂。
倒是家里老人的生活言語更給我一些安慰。如看到我和哥哥到山上去祭拜祖墳時,他們會說:“昆弟倆清敬祖塋,慎終追遠,善也。”如老人看到哪個小孩特別搗蛋時,他們會感嘆:“性相近,習(xí)相遠,莫怪莫怪。”起初我并不明白這些話的全部意思,后來讀了點書,知道這些話來自幾千年前的《論語》。來自《論語》的話,還有我一字不識的母親常說的話:“前半夜幫自己想,后半夜幫別人想。己所不欲,莫加于人。”母親這話,《論語》的原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母親還有兩句常說的話“走路莫急,欲速不濟”“過橋莫擠,小舟不濟”。因此,我在讀書時,常常會不期然與村里的曰常言語相遇,心中總會生出無限感慨。
但母親是我至今還想不明白的人。她3歲沒有了母親,7歲做了童養(yǎng)媳,新中國成立廢除童養(yǎng)媳,她回到自己家,那年12歲,17歲嫁給我父親,1977年時已在重病中掙扎了4年,那年端午后4天扔下我們走了。母親38年人生完全浸泡在苦水中,卻沒有聽到過她一聲嘆氣;她目不識丁,卻堅信讀書的價值。
我們村有位私塾先生,文化大革命中常被拉去批斗。記得有一次是大熱天,哥哥負責解押他。母親悄悄對哥哥說:系得松一點,系活扣。待大隊五六個四類分子都被反手捆綁著解押到舞臺上低頭跪著后,母親悄悄對我說:從舞臺后面爬過去,把他的活扣拉掉。那年我5歲。這是我能想得起來的第一次清晰的記憶。按一種說法,人生是從第一次記憶開始的,那我的人生就是從這次拉活扣開始的。
就是這次批斗會后不久,大隊組織民兵到我們家抄家,抄出了兩箱古書。這些書多數(shù)都是曾祖父留下來的,曾祖父是前清秀才。大家都知道我們家有古書,就藏在二伯父的床頂上。當民兵打開箱子一本一本將這些書燒掉時,二伯父搶出了一個羅盤,母親搶出了兩冊書。這兩冊書我在1979年還讀過,已燒掉了一個很大的角,記得其中有晁錯的《論貴粟疏》和賈誼的《治安策》。這兩冊書和那本《四角號碼新詞典》連同我自己買的一些不太常用的書,1988年我從江西調(diào)到河南工作時,都交給父親保管,1996年暑假有人趁父親不在家時取走了這三本書,也沒有留下借條,繼母也說不清是誰取走了。這已是我丟的第三批書了。
1974年9月,我還不滿12歲,到石坳街上讀初中,寄宿。去了三天,怎么也不愿去了。此時母親已病倒,但母親一定要我讀書,想盡各種辦法勸我。最后我提出一個條件,除非買一副象棋。母親當即就在大伯母家借了1角錢,讓姐姐買回來了一副7分錢的象棋。雖然是最小的象棋,但看到母親的樣子,我沒有了退路,就又去學(xué)校了。現(xiàn)在回過頭看一看,我們村子里只有我這一字不識的母親的三個孩子在那個生活極其艱難的年代,在那個根本不要讀書的年代,在湘鄂贛三省交界的那個窮鄉(xiāng)僻壤,全讀了書:哥哥是村子里第二個高中畢業(yè)生,姐姐是村里第一個初中畢業(yè)生,我是村里第一個大學(xué)生。
我不知道母親是不是因一字不識受到過什么大的打擊或羞辱,反正她敬惜字紙,非常虔誠;敬愛他人,極其真誠。或許是因此,她勉力做自己能做的一切。她從來不許我在祖母未落座動筷子前動筷子,她對我說的每一句假話都很認真糾正,她總是將家里最好的東西用在招待客人和其他人情世故上。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她重病在床,開追悼會那天,父親、哥哥、姐姐都去了大隊部現(xiàn)場,留我在家照顧母親,母親流著淚說:你也去開追悼會吧,毛主席沒有了啊。后來每當讀《論語》讀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xué),吾必謂之學(xué)矣”時,就會涌出淚水。我覺得這句幾千年前子夏說的話,就是寫給母親這一類人的碑文。
如果一定要問我為什么對中華古代文明如此依戀,我想說,家族的先祖崇拜、村里老人們的生活與言語方式,家里特別是母親對(讀)書的信仰,一定在我的心靈深處撒下了能發(fā)芽生根的種子。
有子司馬牛牧之東坡黃山谷
1980年春節(jié),到三伯父家拜年,做大隊支書(現(xiàn)在叫村支書)的堂兄說縣里年前配送了一批書,允我先借。我挑了《朝花夕拾》《吶喊》《中國小說史略》《家》《春》《駱駝祥子》《紅樓夢》《李白詩選注》《詩詞格律》《中國歷代文學(xué)作品選》(前三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巴黎圣母院》《復(fù)活》等。那年我17歲,此前從沒有見到過這么多書,也沒有讀到過任何一部名著。
這次能借到這么多好書,是托上海知青的福。我老家來過多批上海知青,堂兄所在的村是模范知青點,設(shè)有文化站,圖書由上面配送。堂兄說這是所有配送圖書中最好的一批圖書。1979年上海知青陸續(xù)返城,所以這也是文化站接到的最后一批圖書。大概是1980年底文化站撤銷,所有的書又被運走了。據(jù)說現(xiàn)在農(nóng)村又開始建類似的文化站了。如果從1980年撤消文化站算起,老家已近40年沒有類似的文化建設(shè)了。寫下這句話時,我感覺有一種非常沉重的東西在心中攪動。我借的這些書,《中國歷代文學(xué)作品選》沒能讀完,其他我都至少讀過一遍。現(xiàn)在想來,真的是非常感謝這一次不尋常的閱讀,一直領(lǐng)著我走到今天。
1981年,幾經(jīng)折騰后我考入九江師專中文系,教我們古代文學(xué)和寫作的是周萍迅老師。遇到周老師是我們的幸運。周老師是1948年隨軍入川的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畢業(yè)生。周老師的課堂內(nèi)容豐富、信息量大,對我最有觸動的是他隨時帶入課堂的有關(guān)文字、對聯(lián)和他自己創(chuàng)作的古體詩方面的內(nèi)容。那次講駱賓王的《為徐敬業(yè)討武瞾檄》,他插入少年才子,隨即帶進了他的鄉(xiāng)賢余心樂先生。他說余先生6歲時拜塾師,塾師一見很開心,脫口而出上聯(lián)“余見余心樂余心樂”。6歲的余心樂迅即對以“史載史可法史可法”。那次講到黃山谷的《登快閣》,他就帶入“有子司馬牛牧之東坡黃山谷”這個沒有下聯(lián)的絕句。開始同學(xué)們不能完全明白,周老師說:這全是名人啊。大家一下子明白了:有子、司馬牛是孔子的高足,有子還位列孔門十哲;牧之、東坡、黃山谷,都是文學(xué)史上的大家。這些名字巧妙地聯(lián)系在一起,即是說:有個小孩子在東坡上牧牛馬。有多少牛馬?整個山谷都黃了,就是說漫山遍野。這確實是很難對出下聯(lián)的。但它一直激勵著我們許多同學(xué)于此永不疲憊、永不停歇地在漢語這種特有的文學(xué)樣式中徜徉。且于個人而言,我一直以為,這個沒有下聯(lián)的絕句,其實就是中華幾千年古代文明的某種象征: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完美統(tǒng)一;或者說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化的自然。
其實,九江師專的三年,一大批老師的濟世大情至今對我們有著強力牽引的意義。班主任王珂魯先生、現(xiàn)代文學(xué)李彪先生、古代漢語劉琪先生、文學(xué)概論申家仁先生、歷史方良先生、邏輯學(xué)于德禮先生……無不讓我們常常在回望中幸福如沐春陽,產(chǎn)生永遠的光合作用。
“因為我抗拒黃老師”
斗轉(zhuǎn)星移。1999年,我從河南調(diào)入上海,來到浦東香山中學(xué)。上海是一個令人向往的現(xiàn)代大都市,這里有著人們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自己可以用心去經(jīng)營的空間。2000年,我以自薦的方式進入陳文高語文教師培養(yǎng)基地學(xué)習(xí);2002年,黃玉峰先生將我領(lǐng)進復(fù)旦附中;2006年,我進入于漪語文名師培養(yǎng)基地學(xué)習(xí)。
復(fù)旦附中是一塊神奇的土地。
這里曾涌現(xiàn)了一批聲譽卓著的特級教師,語文組就先后產(chǎn)生了盧元老師、過傳忠老師、張大文老師、黃玉峰老師等上海語文界的旗幟性人物。來到這樣一個傳統(tǒng)深厚、久負盛譽的語文組,我始終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真的害怕在這里求學(xué)的英才被我給掐沒了!因此,我始終在思考:怎樣才能最大可能實現(xiàn)作為語文教師的教育意義?怎樣才能真正實現(xiàn)教育的本質(zhì)意義——長善救失?
2005年,于漪老師主持的上海“兩綱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綱要和生命教育綱要)課題進入課堂實踐階段。市教委教研室譚軼斌老師推薦我去上一節(jié)課,我上了柳宗元的《愚溪詩序》。觀課后,于漪老師覺得我可以打磨打磨,第二年就破格錄取我到她主持的名師培養(yǎng)基地。在近距離學(xué)習(xí)于漪老師的十多年中,我收獲非常多。尤其是她提出的“培育具有中國心的現(xiàn)代文明人的教育主張,我以為具有極強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所以不僅一直奉為自己為之努力的教育目標,而且只要有可能就盡力宣講這一教育主張。
什么是“具有中國心的現(xiàn)代文明人”?我認為是一個基座和三個支點:一個基座是“中國立場”;三個支點是“世界眼光”“宇宙意識”和“人類情懷”。倘若沒有“中國立場”這個基座,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的三個支點就都無處可立。而“中國立場”的堅定與穩(wěn)定,一定根植于幾千年中華文化的深處。但現(xiàn)實的情況卻是,對中華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的深處,我們?nèi)狈φJ識、理解,以至于忽視,漠視,甚至于仇視。
如果說,以前隱隱約約感覺到學(xué)生缺失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那么到上海生活幾年后,我就更清晰地看到了全社會的這種缺失是多么可怕。如一些教師和學(xué)生以朝拜的姿態(tài)奔赴海外,去過港澳臺,去過曰韓美英法德意,但他們可能沒有到過中國的中西部,甚至沒有到過北京,沒有到過大陸其他任何一個省份,更極少有人會以朝圣的虔心去泰山、去孔廟、去黃帝陵、去壺口瀑布。再放眼看現(xiàn)今的中國人,有多少人知道杜甫死在何地,身葬何處?恐怕更極少有人去這位中國文學(xué)史上極憂國憂民的詩圣墓前祭拜吧。我有時在語文組開玩笑說:沒有到過北京的人不能教語文,不知道杜甫身葬何處的人不能教語文。這句玩笑話的背后,其實也是我對教育意義的一種思考與詮釋。
一方面,我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著極大的熱愛,另一方面我所處的教育環(huán)境對此又異常隔膜。這無論于語文學(xué)習(xí)的當下成效而言,還是對語文教育的終極意義而言,都不能很好地落實。于是,根據(jù)“長善救失”的教育原則,我從2002年開始就將含有“儒家的理想人“道家的理想人“墨家的理想人“魏晉覺醒的人等內(nèi)容的“中國人”課程和《論語》《古文觀止》《詩經(jīng)》“李白”“杜甫”等引入課堂。2006年主持學(xué)校語文教研組工作后,就將全組教師逐步引向“中國人”概念的理解與落實之中。于是,就有了語文組集體編寫的《中國人》(由《穿行在漢字中》第一節(jié)“中國‘人”擴展而成)、《中華古詩文閱讀》、《中華根文化·中學(xué)生讀本》等校本教材。這也是復(fù)旦附中2014年榮獲國家級教學(xué)成果獎一等獎的教材部分的基本組成。
于是,在我設(shè)計的游學(xué)課程中,探訪、拜謁中華古代文明自然就成了重要的主題,如2014屆同學(xué)的4次游學(xué)分別為——江西“唐宋明文化尋蹤”、“中華元文化齊魯尋根”、“徽文化徽杭古道探訪”、“陜西內(nèi)蒙‘追遠'拜渴”。
我是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的受惠者、見證者,我從來都認為我們必須以開放的胸懷擁抱整個世界,但我也一直認為,失去了來自傳統(tǒng)的力量,我們將無法真正繼續(xù)向前。所以,我在推進課堂教學(xué)時總是“中國人”與“外國人”并置的,只因為別人沒有將幾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國人”及其文化精神與“外國人”并置,我的做法也就凸顯了我對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重視。
毋庸諱言,在探究、落實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進程中,確實也是阻力重重的。學(xué)生、家長,甚至教師,都會有一些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甚至拒絕。我曾兩次收到過家長的“忠告”信,無數(shù)次回答學(xué)生的質(zhì)疑,許多次回答校內(nèi)外教師的質(zhì)疑。幾年前還有一位其他學(xué)科的老教師在我前腳走出教室時,他后腳走進教室,對班里的學(xué)生說:你們可以把《論語》扔掉了!《論語》有什么好學(xué)的?!
“我抗拒黃老師”,這是復(fù)旦附中2017屆的一名學(xué)生在2015年寒假作業(yè)中反省語文學(xué)習(xí)時的直陳。在每屆學(xué)生進入高二第一學(xué)期的寒假時,我都會布置一篇反省高中一年半語文學(xué)習(xí)的文章,給2017屆布置的題目是“談?wù)務(wù)Z文學(xué)習(xí)中的‘先見之蔽”。這個學(xué)生還用了“論我知識吸收的選擇”這個副題。這里不妨摘錄這篇文章中的幾句:“為什么我抗拒語文課的部分內(nèi)容?因為我抗拒黃老師……我知道他是個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正統(tǒng)的儒家學(xué)問人,一個傳統(tǒng)中國農(nóng)村社會成長起來的中國人。他愛孔子,他愛魯迅,中國傳統(tǒng)儒家倫理對于他有種不可抗拒的魅力。然而,正是這些特質(zhì),令我對他的語文課堂有所抗拒。”“我從心底里不認同中國傳統(tǒng)儒家倫理……黃老師認為我太西方了,太不像中國人了,而我認為我的價值觀恰到好處。相反地,我認為黃老師太東方了,太儒家了,而他認為他的價值觀恰到好處。這就不可避免地導(dǎo)致了在語文課上我選擇性聽所有不太涉及中國傳統(tǒng)的內(nèi)容。”
像這樣與我的課堂如此尖銳對立的學(xué)生當然是極少見的,但或多或少有他這種想法的還是不少的,我估計在一半學(xué)生以上。窺一斑而知全豹。因此,在回答媒體問及今春全民古詩詞熱的看法時,我多次表達,這說明我們在這一塊有極大的缺失,也表明我們對古詩詞的認知與理解的深度缺失。
是什么使我們能在重重阻力中前行?除了我們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更有我們對教育本質(zhì)的熱愛。如果我們看到了受教育者的缺失而不去盡力補救,那我們是有罪的。我很幸福,在復(fù)旦附中這塊土地上,治校者始終保有對教育本質(zhì)的清醒認知與熱愛。如現(xiàn)任校長吳堅老師,十多年來他從教導(dǎo)主任到副校長到校長,不僅始終強力支持我和語文組有關(guān)傳統(tǒng)文化教育課程的開發(fā)與實施,而且很多時候是深度參與,出主意,出思想。這樣,我們作為語文老師的教育意義才可能在應(yīng)試教育的夾縫中有所實現(xiàn)。
在《穿行在漢字中》的“再版前言”中我寫下了這樣幾句話,想放在這篇文章的結(jié)尾,表達我作為一名語文教師的心愿:
“在天地之間,在日月之下,在四季之中,行走著幾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國人,他們穿行在漢字中,他們修仁德之美,彰歌舞之美,享吉福之美,抒玄妙之美,繪雅韻之美,鑄就著一個從遠古走進現(xiàn)代、從現(xiàn)代走向未來的長長的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