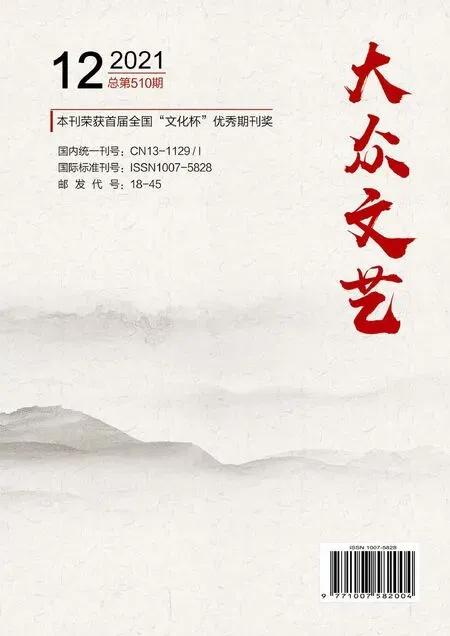活動變人形中的儒道分歧
劉 暢 (內蒙古民族大學 028000)
活動變人形中的儒道分歧
劉 暢 (內蒙古民族大學 028000)
在漫長的文化長河中,儒家思想久居正統地位不容挑戰。然而,五四運動爆發的強烈震感,動搖了“孔家店”的獨寵根基,也催生了道家思想在現當代文學中的復歸。本文旨在通過小說《活動變人形》中的多重矛盾碰撞,淺析儒道兩家的差異與分歧。
道家;儒家;儒道分歧
王蒙的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刻畫了一個舊式家庭中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倪吾誠,他對西方文明的狂熱追求,對現實人生的強烈控訴,貫穿著他苦悶彷徨又一事無成的一生,正如他名字的隱喻,“吾誠”即“無成”。如果粗暴的歸納小說的主要矛盾,就是倪吾誠只身面對來自封建家庭的傾巢討伐,倪吾誠的悲劇命運,究其文化根源,除了肆意成長中的新文化,新思想與傳統權威的正面對抗,更多的,還是復歸的道家思想與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的分歧與對立。
一、儒道分歧之節烈觀——勢如水火的“節婦”與“浪蕩子”
周姜氏靜珍十八歲成親,十九歲守寡。自此,便恪守“女子一生無非是貞節二字”的人生信條。守節之苦奪走了她青春的容顏,更剝奪了她生而為人的動力和樂趣,靜珍只能在一次次的為難自己,惡心別人中實現對其慘淡人生的惡意消耗。“靜珍們”的“固執”不需要選擇和討論,亦不需要尊重和鼓勵,這是從古綿延至今的儒家節烈傳統逼著女性養成的不自覺行為。
然而倪吾誠卻“不識趣”的提出了靜珍再嫁的可能性,他也由此成為了大姨子眼中的異獸和瘋子。那么倪吾誠緣何會講出如此“沒人性”的話?倪吾誠留學海外,自然受到了西方人道主義的影響,人道主義的精神內核當然是人,這與道家重視人的理念簡直是不謀而合。道家講求“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的人大說,這無疑是與壓抑人性,克己復禮的儒式傳統相悖。兩種思想的不可相容直接導致了靜珍將妹夫倪吾誠視為了假想敵,并在與母親和靜宜所結成的聯盟中充當了領袖的角色。
靜珍無疑是儒家節烈思想的衛道士,也最終淪為了它的殉道者。可悲的是,一生以守節為榮的靜珍在離開世界時,為她換壽衣的,卻是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
二、儒道分歧之女性觀——格不相入的“良婦”與“現代新人”
相比靜珍,靜宜對儒家思想的推崇與踐行也是伴隨其一生的。在胞姐靜珍的影響下,靜宜樂于做一個等待丈夫回心轉意的民國“王寶釧”。她可以像王寶釧一樣苦守寒窯十八年,甚至可以接受丈夫在出人頭地的前提下享受齊人之福。儒家之禮——五倫宣揚男女有別。作為女子的責任就是相夫教子,恪守本分,所以不論丈夫有多么混,多么壞,靜宜是多么委屈,多么苦,她仍會無條件的一次又一次的接納他。這種死心塌地的守候,一方面當然也源于初見時一瞥的甜蜜和生兒育女的情分,但更多的還是對女子當“從一而終”的儒家倫理道德的臣服。不同于靜宜的自輕自賤,倪吾誠的女性觀念顯然是偏向道家的主陰之說。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陰在前,陽在后。倪吾誠一生尊敬兩個人,一個是胡適,一個就是他母親。盡管母親差點毀了他,他仍對母親報以最大的深情和懷戀。倪吾誠認為女性可以騎馬,可以喝咖啡,可以像男人一樣享受現代文明。這在靜宜眼中,是大逆不道的,是對她代代讀書識禮的家風的褻瀆。倪吾誠對女性的崇拜也是一種生殖崇拜。靜宜只能是他一雙兒女的母親,除此之外,他無法給她任何的情感認同。
三、儒道分歧之性愛觀——兩性關系的壓抑與釋放
在對性的態度上,雙方也難以達成共識。儒家雖然也承認:“人之男女,飲食大欲存焉”,但確是羞于談性的。朱熹說:“圣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而道家對性十分支持,講究陰陽互補,更從玄學中推衍出一套性交養生術。
倪吾誠的留學經歷讓他接受了世界最前沿的性教育,也激發出其性格中潛藏的道家性觀念。他不止一次的“教育”靜宜要挺著胸走路,這種頗為大膽的性暗示讓靜宜又惶恐又憤怒。靜宜作為儒家思想的虔誠信徒,一向以正經人家的閨女自居,就算是結了婚面對丈夫仍常常羞紅著臉,一句囫圇話也說不出。她當然不能也不想成為丈夫所期盼的昂首挺胸的現代女性。
正如虹影《英國情人》中,女主人公閔所修煉的道家養生術不僅得不到施展,更受到來自傳統正派的知識分子丈夫的鄙棄一般,倪吾誠在家庭中所缺少的不僅一個精神愛人,還是一個旗鼓相當的性伴侶。
四、儒道分歧之人生觀——“入仕”與“出仕”夾縫中的異形人
倪吾誠與整個家庭的對抗看似是兩種文化的對弈,但倪吾誠體內的儒家血統非但沒有消亡,反而在悄無聲息中瘋狂生長,倪吾誠自身,就是一個儒道共存的矛盾體。共存卻難以和諧共生,在兩種對立文化的雙重夾擊下,倪吾誠必然會陷入痛苦的深淵,悲慘的度過一生。
倪吾誠的家中高懸著一條橫幅——難得糊涂。每當他既不敢投入戰爭,又疲于應對家庭中的紛擾,就會自覺的在這四個字中尋求庇護。道家遠離政治,遠離暴力,講求無為而治,糊涂正是其代表性的處世哲學。然而無為真的就是逃避責任,混沌度日嗎,顯然不是。正如小說作者王蒙所說,無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做那些無益,無效,無趣的事,更不是去做蠢事。
儒家主張出仕,主張建功立業,在倪吾誠的內心深處所根植的正是這樣的儒式人生理想。他幻想功成名就,渴望出人頭地,“難得糊涂”對他來說更像是一個幌子,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借以掩蓋他的郁郁不得志。他也并非真正的想要處江湖之遠,而是他根本沒有居廟堂之高的資格。當倪吾誠真的脫離了封建家庭的束縛,也并未過上寡欲脫俗的生活,反而更加熱衷于對權利的追逐,但可悲的仍是,有求實利之心卻無謀實利之術。
倪吾誠雖然高呼男女平等,女性當自強自尊自愛,但在對待兒女的態度上,卻暴露了他重男輕女的思想傾向,這是對儒家男尊女卑觀念的沿襲。而倪藻作為倪吾誠的兒子,雖然怨恨父親,不解父親,嫌棄父親,卻在不經意間與父親越來越相像。倪藻想要擺脫倪吾誠,卻成為了另一個倪吾誠。這樣無法逃脫的近乎復制的人生,也頗有些儒家“宿命論”的意味。
五、總結
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儒道文化的影響力都不容小覷,不論是小說開篇,史福岡一家在糊涂哲學的影響下,生活得平淡也怡然自得;還是小說結尾,西歐文化女代表對儒家傳統價值觀念的認同和向往。一首一尾的呼應中不難看出,一向被倪吾誠奉為天堂的西方現代國度,也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了民族前進的營養。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道德經》中也有“沖氣以為和”的記載。儒道兩家同根同源,源遠流長,和固然是萬事之基,但異卻是其精髓所在。儒道文化乃至多種文化傳統,文化個性正是在這種不休不止的博弈中相輔相成,共生共長,并且不斷地豐富中國人的文化內涵,更新中國社會的文化生態。
[1]王蒙.活動變人形[M].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2]魯迅.魯迅文集[M].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
[3]虹影.K-英國情人[M].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
劉暢(1993- ),女,內蒙古通遼人,內蒙古民族大學2015級碩士研究生 院系:文學院 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