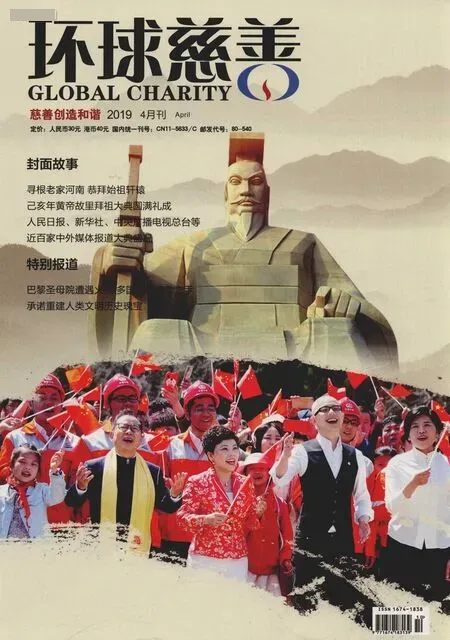并不只是黑人解放那么簡單
沈宇
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笑話:動物園游覽路徑的最后,佇立有一個籠子,邊上的指示牌寫著“世界上最兇狠、殘暴、丑惡的動物”,大人小孩無不好奇探頭張望,一瞅里面,原來是面鏡子。這是一個笑話,也是一則寓言。
科爾森·懷特黑德的這本《地下鐵道》,我就因擔心過于“政治正確”而差點錯過。小說的情節很簡單,講述了19世紀、內戰爆發前的美國,一名黑奴少女通過“地下鐵道”(U nderground Railroad)網絡從蓄奴的南方蓄奴州奔向北方追尋自由(小說并沒有指明故事發生的時間,但“地下鐵道”這一名詞最早出現大約是在1839年,出自一名年輕奴隸之口)。黑人、民權、自由這些關鍵詞,結合美國藝文界對特朗普當選總統表現出的反對及近年全世界范圍內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傾向,加之其在歐美屠榜,又蒙奧普拉、奧巴馬青眼,繼而獲得2016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最佳小說,未讀之前我自然略有擔心作品的成色,擔心獲獎是一種示威,文學被利用了。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在其獲得2015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最佳非虛構作品的《在世界與我之間》(Between the World and Me)中表現出來的深深被冒犯感和他支持以暴力回應不公的立場讓我受到極大的震撼,雖然一方面感受到當今美國看似公平的制度下仍存在許多不公,一方面擔心作者以對兒子娓娓道來的口吻將族群對立意識傳給下一代是否會將許多本不該由膚色族裔承擔的社會議題被簡單化和固定化;特朗普的當選顯然證明了國家確實面臨著撕裂的危險。
逃亡之路
《地下鐵道》的主角科拉非常平凡,自小生活在佐治亞州的種植園里,她守著外婆傳下來的三碼見方自留地沒有想逃走的意思。除了科拉銷聲匿跡已久的母親梅布爾——大家都說她是當地唯一成功逃到北方的黑奴,是一個傳奇,科拉的生命中沒有什么特別值得記掛的,可是外婆的地被后來的異族黑人盯上了要蓋狗屋,她又因為那么一滴濺到主人衣衫的葡萄酒而遭了暴打,想想當年狠心拋下她一人出逃的梅布爾估計在北方活得自在,孤女的心里有了波瀾。第二次,她答應了同為奴隸的西澤一同逃走的請求,就這樣踏上自由之路“地下鐵道”。懷特黑德的奇特設想就此展開,他將歷史上的近乎傳奇的地下鐵道網絡轉換為真實的火車在地下奔跑——當年媒體就曾調笑過“只要奴隸們從地板上的石頭暗門里穿過去,就能直接掉到地下鐵道的車廂里”——免省了路上的筆墨,達成了類似書信體小說讓劇情快速推進、壺中藏日月的效果,也更專注于實現自己的意圖:如果我們的主人公在美國的每一個州都如同置身于一個完全不同的另類美國。美國可以是一間間展示苦難的囚室,也可以是博物館一個個展室,更可以是呼嘯馳過的地鐵車站的車站風景、《雪國列車》里一路打怪經過的奇葩車廂。全書12個章節的一半就這樣成了櫥窗映射現實,偶數章節標題全為地名:出發地—佐治亞、第一站—南卡羅來納、第二站—北卡羅來納、第三站—田納西、第四站—印第安納、終點—北方。
看過科拉在佐治亞的悲慘遭遇,下面移步到達南卡羅來納,這里似乎非常文明,十二層高的摩天大廈——格里芬大樓成為本章的重要表征。科拉和西澤一方面對于逃亡路上的驚險仍有余悸——臨時加入的小可愛被逮,科拉錯手殺死一名追捕他們的白人小男孩;一方面積極地融入新生活中去,他們有了新身份、新工作,有宿舍住、有課上、有聯歡、有床睡——科拉有生頭一回睡到了床,比照在佐治亞州的遭遇,南卡簡直是天堂,誰能想象在這里學習認字不會被挖掉眼睛。不過醫生冷冰冰的檢查器械讓科拉想起了農場主的刑具,科拉幫傭那戶人家的先生就在格里芬大樓八樓辦公,十樓的公派醫生診察室卻讓她感覺迥異,聯歡時一個女人哭喊的“他們要奪走我的寶寶呀”,也讓人起疑,那聲聲尖叫招回了科拉當年被同為黑奴者輪奸的記憶幽魂……
科拉被調往自然奇觀博物館工作,她要在眾人的眼光和指戳下于玻璃櫥窗內表演黑奴的歷史與生活。歷史豈獨展科拉在櫥窗中:1865年12月18日,《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經美國國會通過、四分之三聯邦州認可正式生效;1906年,OtaBenga——一位黑人還在紐約的動物園籠子里跟猩猩一起展出,連《紐約時報》的社論都一度傾向于認為他可能更接近類人猿。經過全國范圍內的抗議活動——南方人都嘲笑這“北方的暴行”,OtaBenga終被視為人,但1916年3月19日晚,離開囚籠已近十年的他悄悄用槍對準了自己的心臟,似乎唯如此才是自由與平靜……要再過上將近百年的時間,2013年2月密西西比州才最終完成了批準此修正案的法律程序。
日復一日的被圍觀讓科拉開始思考這個展覽、這個國家、這片土地的過去與現在:白人屠殺印第安人,又運來黑奴……她也變得能狠下心“報復”觀眾:隔一個小時選一位看客,投去狠毒的目光,她對此愈來愈擅長,直到兇惡眼神盯視上原先照顧過的小女孩。孩子被嚇跑了,“勝利”的科拉羞愧難當。
而醫生非常柔和的詢問漸漸顯露出背后的意圖:“你已經發生過男女關系了。有沒有考慮過節育?”懷特黑德這般不動聲色寫出這殘酷的故事不是無來由: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美國政府在亞拉巴馬州,替黑人男性提供醫療服務實為研究梅毒。作家將它提前、與奴隸制并置,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再展現出權力者對其余人的看法。中澤啟治創作、連載于《周刊少年Jum p》的國民漫畫《赤腳阿元》里,漫畫家以自己原爆受害者親身經歷揭露美軍曾在廣島藉醫療救護為名實則進行核輻射研究、搜集數據;馬紹爾群島的原住民也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變成了美軍核爆的小白鼠,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不見血光的南卡羅來納如此懷柔,西澤和科拉就這么羈縻于途,錯過了四趟列車,直到奴隸主派出的獵奴者循跡追到。一場大火燒毀了他們的希望……
僥幸逃過劫難的科拉從此一人上路,下一站是北卡羅來納。這里的最新法律正在彰顯著主張:在北卡羅來納,黑人種族是不存在的,除非吊在繩子上。“自由小道”旁樹上滿是懸掛著備受侮辱的黑人尸身,南卡般黑人白人交混之情景已不復見;誰敢幫助黑人逃奴,等待著的是一樣下場。科拉被迫藏身于接應人馬丁家的閣樓,屏息匿跡,只有一個窺視小孔讓她勉強知曉些外界情況。北卡羅來納引入窮困落魄背井離鄉的愛爾蘭人、德意志人作為黑人的替代,他們自豪地聲稱,“我們廢除了黑鬼”,黑人的存在被湮沒了、驅逐了、掩蓋了。
直面痛苦
愛爾蘭人在舊世界一直是與猶太人一樣備受歧視的民族。英諺有云:寧可在英格蘭被絞死,也不在愛爾蘭壽終。在新大陸,愛爾蘭人發現了社會構成的不同——膚色,而這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狹縫窄門。NoelIgnatiev的《愛爾蘭人是如何變成白人的》專題研究了愛爾蘭人地位的提升。馬丁家的傭人菲奧娜便是一口愛爾蘭鄉音,正是她的告密,馬丁夫婦落得被懸樹上、眾人砸石,科拉則被獵奴者里奇韋所虜。
這是她第一次沒有通過地下鐵道穿州過省。里奇韋一行人并沒有南返,向西進入了充滿火災和疫病的田納西,準備去密蘇里捉拿另一個逃奴。在里奇韋的眼中,這場黃熱病是黑非洲搭船而來的、進步過程中繳的人命稅,在科拉看來,田納西和白人是受了詛咒,正義得到了伸張。在田納西,里奇韋還答應將一個名叫賈斯珀的逃奴送回主人處。當里奇韋發覺這趟先西后東的路程不劃算,抵不上押解賈斯珀的酬勞,賈斯珀的命途就此了結。
里奇韋對科拉的仇恨非同一般,科拉母親梅布爾的逃跑簡直是他職業生涯的最大恥辱;他不知道科拉同樣恨著梅布爾。她在閣樓幽閉時只有思緒可肆意,幻想著自己今后的幸福生活和路遇沒有替她攢過一分贖身錢、自己逃走的母親:“一個糟老婆子,窮困潦倒,渾身是病,沿街乞討,腰背佝僂,真是惡有惡報。梅布爾抬起頭,卻沒認出自己的女兒。”
里奇韋的隊伍里有一個黑人小男孩霍默,科拉總不明白為什么他會這么忠心耿耿自愿替白人趕車、養護、管賬。僥幸得救時——救人的里面也有一個愛爾蘭人,她想不好如何處置獵奴者。霍默反正在爭斗中跑了,科拉只是朝被拷在馬車上的里奇韋蹬了三腳,說是為了小可愛、西澤和賈斯珀,其實是為了自己。這寬宏為日后的她帶來了巨大的不幸:逃奴和自由黑人棲身的印第安納州瓦倫丁農場在兩派黑人的激辯中——有些攢錢贖身的自由黑人認為農場不該收容逃奴尤其是背負了人命的科拉——被屠戮。會場里人頭攢動,科拉入場時沒認出那個一見到她便沖她眨眼的淘氣小男孩,那是霍默。
科拉的主人已經死了,賞格無人兌現,但里奇韋一心要偵破這地下鐵道的真面目,命她打開隧道的活板們,扭打中,他倆跌落黑暗里……
故事主線就此結束,僅靠跟隨科拉的旅程所能展現的故事著實有限,懷特黑德通過奇數章節調度了更多的視角供我們回味,全書的敘事因而如拉鏈般緊實。在一次次前往下一站的隧道黑暗中,他通過阿賈里、里奇韋、史蒂文斯、埃塞爾、西澤、梅布爾補全了故事的細節,一個個次要人物的面目得以清晰、豐滿:科拉的外婆阿賈里帶出族人的歷史和早年種植園的細節,里奇韋是如何成為獵奴者帶著何種心情出發追捕科拉,看似溫柔的醫生史蒂文斯是如何盜尸做研究,馬丁的太太埃塞爾為何與黑人相處欲進又退冷面熱心,西澤沖著梅布爾成功逃走的經歷選中科拉作為自己的護身符,最悲慘的是梅布爾其實從未拋下過自己的女兒在北地獨活,她從自留地里采完菜,心心念念著科拉往家趕,不料遭蛇咬了一口;沼澤無聲無息地吞沒了她……這是整部小說最讓人心痛的一刻,科拉能夠踏出逃亡的第一步,與其說是出于對自由的向往,不如說是母親拋棄自己的恨意使然。命運卻開了天大的玩笑,母親不在紐約,不在奴隸主鞭長莫及的加拿大,而是葬身家園近側。
燭照人性
懷特黑德沒有給科拉的這趟旅程安排多么高大上的理念先行,科拉也曾退縮、迷惘過,一路上支持和幫助她的人全都逝去,前途似乎一片晦暗,但是堅持和命運讓她一步步捱到了終點。黑人和白人在作者筆下沒有千人一面,許多人的故事盡管始終沒展開,但一筆帶過更讓人覺得辛酸苦楚:科拉的父親格雷森躊躇滿志想要賣力干活贖出自由,結果發燒死了,都不知道妻子肚子里有了孩子;當年帶頭欺負科拉、搶地蓋狗屋的黑奴逃跑,被自己那條狗的吠叫暴露了行跡;農場主“喜歡品嘗黑李子”,在成排的木屋間悄然巡行,于“奴隸的新婚之夜登門拜訪,給那做丈夫的演示一番履行婚姻義務的恰當方式。他品嘗他的黑李子,就手把李子皮兒也弄破,留下自己的痕跡”。——《費加羅的婚禮》中,阿爾馬維瓦伯爵也對曾為他出謀劃策抱得美人歸的仆人費加羅未過門的妻子蘇珊娜打這個初夜權的主意;費加羅可不是黑人,又是一個權力者以外皆非人的例證。
懷特黑德的筆墨相當克制隱忍,歷史上真實的逃奴自述文本在美國已是家喻戶曉,如遭受主人多年性侵又委身其他有婦白人以求贖身的哈麗雅特·雅各布斯記錄下的《女奴生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曾是地下鐵道羅徹斯特轉運站的“鐵道員”、后來擔任過美國駐海地的公使——的《道格拉斯自述》,以情節而論均是凄慘更甚,兩位作者都是白人奴隸主與黑人女性的后代,敘述中涉及了更多被辱的黑人女奴和混血兒的多舛命途:同一個父親的異母兄弟,一個變成老爺,一個仍是奴隸,往往借不忍見兄弟/兄妹相殘或讓主母眼不見為凈為名,母親和孩子被賣得遠遠的;老主人即使宅心仁厚,許諾身后開釋其奴,繼承者往往毀約;科拉只是在閣樓里躲了幾個月,哈麗雅特竟躲了七年,連親生的孩子都得瞞過;有國會議員主張廢奴,倒與黑人女性生下子嗣,把女孩兒賣去當傭人;哈麗雅特接到過不少主人花言巧語哄騙她回去的書信,主人還偽造她的悔過信送給她的親戚,而《地下鐵道》最后一章“北方”的開頭,逃奴告示對于科拉的描述“她已非家奴”,也并不預示著她至此可以就地幸福。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因各地廢奴演講需要,時常在臺上露出背后的累累傷痕,懷特黑德的鏡頭始終尾隨科拉,不是絕地逃生就是生離死別漸漸遠去,省去了過多鮮血淋漓的直面。本來靠慘痛來博得的只能是同情,此書的重點也不僅僅在于黑人的解放和民權的平等,既然各州已經像《西游記》、《鏡花緣》和《格列佛游記》——西澤一生最在意的那本書,顯然也是作者懷特黑德致敬的對象,美國的五個州隱隱對位了格列佛出身、游歷的五國——那樣照出了我們的本性,為什么為何還要昧著良心、畫地為牢以為它們只是個笑話或少兒讀物呢?
本刊整理自《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