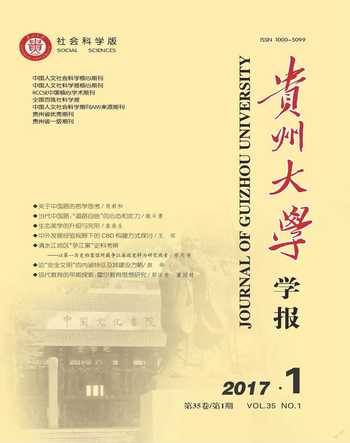梭羅的自然寫作
何云燕
摘 要:“自然寫作”是梭羅在《瓦爾登湖》之后進入的另一個寫作階段,標志著梭羅逐漸跨越了超驗主義的藩籬,進入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現(xiàn)象世界的觀察與言說,最后到達對自然進行詩性的描述。在這一過程中,梭羅確立了以自然為宗旨的信仰,并由此完成了完整自我的塑造。這是一個作家對人與生境潛能互動的從外到內(nèi)、從內(nèi)到外并循環(huán)上升的體悟之心路,展現(xiàn)了生態(tài)文學作品生發(fā)的機制。
關鍵詞:梭羅;自然寫作
中圖分類號:B83-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7)01-0051-06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shb.2017.01.09
一、引言:瓦爾登湖畔的實驗
在19世紀美國文學經(jīng)典之中,梭羅的作品被認為對美國的思想與文學貢獻最大。梭羅的寫作歷程不僅深刻地反映了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轉(zhuǎn)型中文學的命運和意義,而且還提示了一種日趨生態(tài)審美化的生活方式的美好愿景。在《重塑梭羅》一書中,米爾德指出,梭羅在其創(chuàng)作后期的自然歷史散文中擴大了自己“興趣的范圍和廣度,以一個新的形象出現(xiàn)在大眾面前”,然而這不但沒有被重視反而被認為是其創(chuàng)作的“衰退”。他認為有必要“重新勾勒梭羅事業(yè)的輪廓,它不是一條頂點在《瓦爾登湖》的拋物線,也不是一條綿延不斷的直線,而是一條上升的弧線,有周期性的斷裂,也有重新開始,不變的是其上升的動力。”[1]2-3這個動力就是梭羅對超驗主義價值觀的不懈實驗,也是他的終身事業(yè)。[2]697但是到了創(chuàng)作的后一階段,他則以更理性的角度、用更多方式去反思其正確性與合理性。在《瓦爾登湖》的結(jié)束篇里,梭羅是這樣總結(jié)過往、展望未來的:
我離開森林,就跟我進入森林,有同樣的好理由。我覺得也許還有好幾個生命可過,我不必把更多時間來交給這一種生命了。驚人的是我們很容易糊里糊涂習慣于一種生活,踏出一條自己的一定軌跡……想人世的公路如何給踐踏得塵埃蔽天,傳統(tǒng)和習俗形成了何等深的車轍!我不愿坐在房艙里,寧肯站在世界的桅桿前與甲板上,因為從那里我更能看清群峰中的皓月。我再也不愿意下到艙底去了。[3]283-284
這段話和開篇《經(jīng)濟篇》是首尾呼應的。從一開始,梭羅清楚地表明,湖畔生活只是一個實驗、一種生活的嘗試,在這里他再次重申不會把時間僅僅交給一種生活方式,因為他生活是豐富的,他“還有好幾個生命可過”。而且他再次呼吁:大地和心靈一樣都是柔軟的,可以開辟出千千萬萬條路,人人都要走自己的路,要“會取其適用的”,不要“削足適履”,不要去重復別人的模式。[3]2這應該是他超驗主義“自立”思想的一個很重要內(nèi)涵,構(gòu)成了美國個人主義發(fā)展的基石。
另外,他用了艙底的形象比喻闡述了自己瓦爾登湖畔實驗的本質(zhì)是探究事物尤其是心靈的深度,現(xiàn)在他要從這里出發(fā),回到世界的桅桿前和甲板上,即將準備開啟探究世界廣度的旅行。梭羅文學創(chuàng)作的后期開始在超驗主義詩學觀念的統(tǒng)攝之下,跨越了超驗主義的藩籬,進入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現(xiàn)象世界的觀察和言說,最后到達對自然進行詩性的描述,在認識論上形成了對世界和生命之整體形態(tài)初步的探索。這是一個從外到內(nèi),又從內(nèi)到外,循環(huán)往復,不斷上升的旅行,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對“超循環(huán)” [4]的生命生態(tài)結(jié)構(gòu)的無意識探索。
二、超越:超驗主義之外
1845年12月,當梭羅還在瓦爾登湖畔進行他的超驗主義價值觀實驗時,托馬斯·卡萊爾的一本著作《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書信和演講》(Oliver Cromwells letter and Speeches)經(jīng)愛默生的引介來到了康科德鎮(zhèn)。在這本書里,卡萊爾對克倫威爾的書信和演講進行了精彩的評論和“注釋”。梭羅并沒有對書的內(nèi)容有太多感觸,但是他被其夸張無拘的言辭和文風深深吸引了。于是,他開始為鎮(zhèn)上的民眾撰寫一篇關于卡萊爾的演講稿。1846年2月,他在康科德演講廳關于卡萊爾的演講是感人至深的。1847年3月和4月,梭羅整理出來一篇長篇評論題為《論托馬斯·卡萊爾及其作品》(Thomas Carlyle and His Works),并發(fā)表在了一家著名雜志上。而且在這篇評論中,梭羅高度贊揚了卡萊爾:他“并沒有強迫我們?nèi)ニ伎迹覀兊乃伎家呀?jīng)早就足矣。可他迫使我們?nèi)バ袆印!盵5]Ⅳ,355
事實上,梭羅在1846年7月的時候就已經(jīng)找到了以行動代替思想的機會。這個月末的一天,梭羅從瓦爾登湖畔回到鎮(zhèn)上去取回送去修補的鞋子時,被當?shù)氐亩愂展僖云溟L期拒付人頭稅為由抓起來關了一夜。梭羅相信自己是為了信念而甘愿坐牢的,所以對于第二天因一個女性親戚幫忙而被釋放感到十分憤怒。更糟糕的是,愛默生對此嗤之以鼻。梭羅發(fā)現(xiàn)自己的導師盡管也倡導實踐但卻吝于行動,這讓他感到很痛苦和失望。然而無論多么痛心,他還是決定為自己辯護,而這個辯解的文章竟然成了美國政治思想經(jīng)典著作之一。
這些都顯示了,梭羅對超驗主義社會改革的可能性產(chǎn)生了懷疑,對個人在“鼓動”社會大眾改革中的地位和價值逐漸喪失了信心,隨后便轉(zhuǎn)向了對自我的“改革”。梭羅在瓦爾登湖畔開展的生活實驗證明,他開始從行動上去探討個人生活的基本內(nèi)涵,為個人的自我教育尋找理論與現(xiàn)實的依據(jù),并論證了個人改革的重要價值。在《瓦爾登湖》一書中,我們都可以尋找到他試圖超越超驗主義思想局限的努力,即通過行動把精神的體驗和肉身的體認結(jié)合起來,讓生活和藝術(shù)立足于具體實在。[6]195這說明,在超驗主義形而上思想和美學觀念的統(tǒng)攝下,梭羅在行為中還有著明顯的經(jīng)驗主義趨向。[7]65因為,對于梭羅而言,“物質(zhì)與精神一樣真實”[2]704,這促使他走出書齋,走向自然,對自然展開了自覺性地探索。
三、發(fā)端:《馬薩諸塞州的自然歷史》
學者斯蒂文·芬克認為《馬薩諸塞州的自然歷史》代表了梭羅在文學創(chuàng)作事業(yè)上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不僅僅是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嘗試通過大眾話語模式把其超驗主義價值觀傳遞給更大的讀者群,而且這是他第一次嘗試自然散文寫作。
愛默生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梭羅對大自然的感情與感知。盡管當時自然史寫作還未成為美國文學發(fā)展過程中一種被人們所普遍接受、認可的文學體裁。另外,盡管熱愛大自然并通曉其中諸多奧秘,但是梭羅顯然還未曾想過把自然作為文學主題或文學素材。相反,他似乎受到愛默生形而上觀念的“束縛”,從其早期日記和雜文就可見一斑:大部分主題都是“友誼”“服務”“勇敢”“希臘詩歌”“英雄”“印度教經(jīng)典”等等。這個階段的梭羅繞不開愛默生作為文學知識分子的成功模式,但是他又缺乏前者的宏大、尖銳、辛辣的寫作風格。而作為旁觀者,愛默生當然知道梭羅的獨特稟賦,所以他讓梭羅寫一篇關于馬薩諸塞州動植物群里的調(diào)查報告以發(fā)表在《日晷》上,作為對本地區(qū)社會生活環(huán)境的一種描寫和評論。在這篇報告的基礎上,梭羅于1842年拓展成了《馬薩諸塞州的自然歷史》并于當年的7月份發(fā)表在了《日晷》上。
謝爾曼·保爾也同樣強調(diào)了這篇文章在梭羅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重要性,他認為:“如果沒有愛默生的耐心敦促和其對物質(zhì)意義的認識,那么梭羅可能會繼續(xù)撰寫關于高尚道德與超驗主題的文學評論和抽象文論。愛默生促使他認識到了自然事實的文學價值,并令他意識到自己的日記是一個暗藏的寶庫。”[8]102保爾同時還指出,梭羅用自然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對象還有一個私人的價值就是這些自然散文可以實現(xiàn)梭羅越來越強烈的隱退出社會的意愿。保爾分析其原因,覺得是因為梭羅“尋求更美好社會的希望落空后,自然而不是友情成為了社會的對立概念。” [8]103在保爾看來,雖然梭羅對社會的發(fā)展失望,但是對自己文學事業(yè)卻從未放棄。尤其是摯愛的哥哥突然故去,使梭羅產(chǎn)生了一種強烈的道德使命感,他覺得有責任和義務把哥哥身上圣潔、高尚的品質(zhì)傳播出去,以紀念、慰藉哥哥的在天之靈。這個觀點得到了米爾德的認同。米爾德也同樣認為是失去親人的哀傷使梭羅迅速地成熟了起來。[1]83這種心理變化促使梭羅把寫作當做建立與世界的溝通、連接與實現(xiàn)其社會責任的一種工具或途徑。
1842年3月26日,即愛默生把這篇文章轉(zhuǎn)交給編輯富勒之前,梭羅在自己日記中這樣寫到:“我將非常樂意將我生命的財富分享給人們,我將認真地把自己最寶貴的禮物獻給他們。我將為了他們把珍珠從貝殼中剝離出來、在蜂群中采集蜂蜜。我將為了公眾的益處撒下陽光。我知道我將不會獲得任何財富回報。我不需要任何個人的好處,除非我能以我的獨有能力服務大眾。這是我唯一的個人資產(chǎn)。” [5]Ⅻ,350 在瓦爾登湖畔的實驗報告中,這種語氣更是滲透在了整個文本中,因為他實驗的目的就是給公眾提供一種生活方式的參考,以期進行社會道德的改革。
《馬薩諸塞州的自然歷史》的細節(jié)描繪栩栩如生,在內(nèi)容上是《瓦爾登湖》和19世紀50年代后有關自然史寫作的發(fā)端,在修辭上回應了其早期的社會改革論文如《兵役》等,而在語言上則保留了超驗主義深沉華麗的風格。不過,在這篇文章中,梭羅顯示出來一種明顯的經(jīng)驗主義傾向:“讓我們別小看了事實的價值;有一天它們可以開出真理之花。” [9]131霍桑曾經(jīng)這樣稱贊這篇文章:“如此真實、詳盡、細致的觀察,除了將其所見訴諸于文字外,還賦予了文字以精神。” [11]355正如米爾德指出的,《馬薩諸塞州的自然歷史》“預示了梭羅寫作的真正風格” [1]40,并“發(fā)展了最初的先驗的經(jīng)驗主義” [1]73。最值得稱道的是,這種體裁不僅綜合了梭羅探索自然的愛好和理想,而且將他懷有的社會責任和文學事業(yè)融入對自然地思索和觀察中,也拓展了他自我探求的空間和維度。
四、旅居與旅行:內(nèi)與外的探索
謝爾曼·保爾指出,梭羅嚴格區(qū)分了藝術(shù)家和詩人。[8]211在一篇關于歌德的論文中,梭羅認為歌德的教育和生活都證明其是藝術(shù)家,理由是歌德從小開始一直生活在城市,就連玩具都是藝術(shù)設計和生產(chǎn)的產(chǎn)物。在文章中梭羅批評歌德過于局限于自己社會地位的規(guī)定和限制。用歌德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崇高只能“在那些不受約束和未經(jīng)歸訓的民族”中找到。梭羅由此論證了崇高只能產(chǎn)生于“沒有門的林中”,所以人應該過著“有機的生活”,從美學意義上來講就是人應該知道自然法則可以打破藝術(shù)規(guī)則。梭羅得出的結(jié)論是詩人是自然法則的言說者,是傳遞神諭的天才,詩人主要是依賴意識來感知上帝。[5]Vol.2,348-351據(jù)此,保爾發(fā)現(xiàn),對于梭羅來說藝術(shù)家的主要貢獻在于對深度的探究,但是他的理想是成為詩人——能透過表象透視事物內(nèi)在法則,并以此進一步發(fā)現(xiàn)宇宙本身的有機法則。換句話來說就是梭羅對自己的期待是能在外在事物中發(fā)現(xiàn)內(nèi)在真理,而且這些真理必須是“有機的”——這點強調(diào)了思想觀念更新的必要性。在《瓦爾登湖》的結(jié)尾,梭羅闡發(fā)了自己的這一觀點:
把你的視線轉(zhuǎn)向內(nèi)心,
你將發(fā)現(xiàn)你心中有一千處
地區(qū)未曾發(fā)現(xiàn)。那末去旅行,
成為家庭宇宙志的地理專家。
……
你還是要聽從古代哲學家的一句話,“到你內(nèi)心去探險。”這才用得到眼睛和腦子……現(xiàn)在就開始探險吧,走上那最遠的西方之路,這樣的探險并不停止在密西西比,或太平洋,也不叫你到古老的中國或日本去,這個探險一往無前,好像經(jīng)過大地的一條切線,無論冬夏晝夜,日落月歿,都可以作靈魂的探險,一直探到最后地球消失之處。[3]281-283
這是梭羅在決定結(jié)束瓦爾登湖畔的實驗去過其他“好幾個生命”之前對其讀者說明的理由。他在瓦爾登湖畔完成了一個階段的“向內(nèi)旅行”,現(xiàn)在他聲稱他要離開去嘗試更多的生活方式,他還要不斷的向外探索、探險以便更多地了解豐富的內(nèi)在世界、挖掘出更具廣泛意義的宇宙本身的有機法則。
事實上,在其創(chuàng)作生涯中,第一次把事實和思想結(jié)合起來的嘗試是題為《到沃楚特山的散步》(1842年)的短文,這也是梭羅首次嘗試“短途旅行”的體裁,后來成了他獨具特色的體裁。米爾德認為,這篇文章“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沉思,又不是艱苦卓絕的英雄行為,而是數(shù)次‘未完成的尋求中的第一次尋求”。在離開瓦爾登湖畔的小屋后,即19世紀50年代,梭羅仍然延續(xù)這種尋求,他到大山、海洋、森林等等地方去,為的是尋求大自然拒絕給他的啟示。這個階段對于梭羅來說“近處與褻瀆相連,而遠處與神圣相關”。[1]41-43這或許就是超驗主義者們包括愛默生在內(nèi)對精神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溝通聯(lián)接的共同的不懈追求。
梭羅開始了頻繁的旅行,并寫下了不少的短途旅行散文,似乎在某種形式上也告別超驗主義的精神探索和冥想。實際上,1852年底,即在對《瓦爾登湖》進行第二階段修改的時候,梭羅已經(jīng)淡去了對浪漫主義的熱情。因為在1851年,他開始勾勒自己的閱讀計劃,其中最重點關注的一本書是J.J.巴斯· 威爾金森的《人類的身體以及它與人的聯(lián)系》。這是一本關于神學唯靈論與科學的書,對梭羅后期的思想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幫助梭羅“可以開始把他的經(jīng)驗傾向和想象傾向合成起來”,令他“沉迷于他的植物學研究”。這種向外探索的轉(zhuǎn)向“把他的先驗主義淡化成了更加模糊不清的教條,使他能夠照樣可以宣揚它們,而實際上他已經(jīng)另辟他徑”。[1]193-195但值得注意的是,梭羅從始至終都堅持聲稱自己為“超驗主義者”,而且他是唯一把此當終身職業(yè)的人。他通過內(nèi)外兩個方向展開有張力的探索,在自然中用行為去檢驗超驗主義觀念、用寫作去探尋超驗主義詩學精神。
五、自然寫作:生態(tài)文學的先驅(qū)
19世紀50年代前半期是梭羅創(chuàng)作的高峰期,除了越來越出彩的日記和廢奴演講稿之外,作品和其他演講稿還包括《散步》(Walking,or the Wild)、《在加拿大的新英格蘭人》(A Yankee in Canada)、《科特角》(Cape Cod)、《緬因森林》(The Maine Woods)、《秋色》(Autumn Tints)、《野蘋果》(Wild Apples)、《越橘》(Huckleberries)、《森林樹木的更迭》(The Succession of Forest Trees)、《種子的傳播》(The Dispersion of Seeds)等等。“梭羅在后期的自然歷史散文中擴大了他的興趣范圍和主題,以一個新的形象出現(xiàn)在大眾面前。” [1]序4這些標志著梭羅離開瓦爾登湖畔后的新事業(yè)新方向。但是由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這些手稿大都從未出版,所以我們對其新“生命”知之甚少,這個新方向也被稱為“梭羅的未竟事業(yè)” [11]12。這事業(yè)儼然就是梭羅日趨成熟的自然寫作,而所謂的“未竟”其實主要是因為梭羅的寫作體裁是日志——他忠實地記錄了自己富有情感的自然觀察而不是慣常的主題性創(chuàng)作,也為后來的地理、氣象變遷等生態(tài)科學研究提供了歷史記錄。
學者霍阿閣認為,梭羅后期的自然史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高度科學話的,例如《森林樹木的更迭》和《種子的傳播》;另一種是預言性的,如《在加拿大的新英格蘭人》、《野蘋果》等。霍阿閣指出,要理解這些作品必須把握兩個關鍵詞:感知和關系(perception & relation),理由之一是因為這些作品深刻地描述了自然——這是目光短線的人很難輕易體會的;另外,這些作品記載了一個理想主義者對新大陸自然世界和人的“最美好自我”的精心呵護,所以必須要學會把心態(tài)放平,順其自然地去看、去生活才能更好的體會人與自然的關系。[12]值得注意的還有,梭羅是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學習運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自然的。
和《瓦爾登湖》的敘事模式不同,在這些作品中,梭羅一改以往注重精神思想表述的偏好,而更多的是講述事實、描述所見所聞,并清楚地說明了自然界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而且還揭示了大自然“黑暗”的一面,例如他耳聞目睹的大海和山中暴風雨是那么的瘋狂、野性十足,甚至是十分殘忍,它們能輕易而無情地剝奪無數(shù)人們的生命。《科特角》的第一部分寫的就是“海難”,是梭羅到達科特角第一天的經(jīng)歷。他和朋友還沒有看到大海就收到了關于這個半島的傳單:145人在海難中喪生。于是他們決定先去事故現(xiàn)場看看。他們看到的是人們在忙碌地打撈尸體:“那種冷靜、快速處理的方式足以令人動容,但是人們的臉上看不到哀傷的表情。”這時,在美國的這片海岸,梭羅少有地發(fā)現(xiàn)并贊揚了新英格蘭人的堅毅和頑強,如他心目中的古希臘人。
或許因為感受到了美洲大陸的英雄氣息,梭羅在接下來的游記《散步》中展現(xiàn)了他創(chuàng)作中最歡快的一次旅行。在這篇長文中,梭羅敘述了自己在孤寂的樹林和荒涼的沼澤地里散步時感受到的野性和活力,力圖說明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可以和古希臘古羅馬并提的英雄時代。為此,梭羅開篇就給散步和散步者做了闡發(fā):
在我的生命歷程中,我只遇到過一兩位真正理解了步行藝術(shù)——更準確地說是散步藝術(shù)的人,可以說,他們都是天才。“散步”一詞源自于中世紀時,過去的散步者們以往圣地為由,在鄉(xiāng)間流浪、乞討,村里的孩子們見到后都這樣呼喊:“一個圣徒來到了這里!”——即一個散步者、朝圣者之意。[5]Vol.5,205
梭羅對散步者進行了嚴格地篩選。在他看來,散步者就如同精神領域和現(xiàn)實世界中的十字軍,而不是那些為求得一瓢飲、半碗羹的流浪漢或懶惰者,也不是為了鍛煉身體而散步的職員或者商店老板;真正的散步者必須走上返璞歸真的旅途,在接觸荒野、自然中感受到喜悅和靈感。
在這篇文章中,梭羅聲稱自己每天至少用4個小時以上的時間散步,尋找人跡罕至的地方。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后期他的肺結(jié)核經(jīng)常有繁復發(fā)作的緣故。[13]199-201但是無論如何,梭羅總能在單調(diào)的世界里通過細致的觀察獲得精神上的高漲和愉悅。在華麗的花園和荒涼的沼澤之間,他選擇了后者,他在荒野中找到了生意盎然和無拘無束的活力,或許確實是能平衡他日漸衰弱的身體,給他一種生命的力量。梭羅在自然四季循環(huán)的體驗中,感受到了生死循環(huán)的必然性和自然性。正是在這個意義是上他更能深刻地體到身體存在的暫時性和精神存在的超越性。
勞倫斯·布伊爾的專著《環(huán)境的想象》不僅是美國生態(tài)批評研究的扛鼎之作,也是梭羅研究的里程碑。在書中,布伊爾將梭羅置于廣闊的、多樣化的“自然寫作(nature writing)”的背景中,通過“瓦爾登湖的朝圣”,“梭羅的經(jīng)典之路”等問題的探討,闡明了環(huán)境的想象作為一種文學和文化的力量是如何塑造經(jīng)典、如何表現(xiàn)美國的綠色思想的,由此確立了梭羅在美國自然寫作和生態(tài)文學中的開創(chuàng)意義。[14]關于梭羅作為美國生態(tài)文學之父、環(huán)境主義先驅(qū)的論述已經(jīng)很多了。但是對于梭羅作為個體自然寫作作家的創(chuàng)作歷程剖析往往忽略了他在完成《瓦爾登湖》之前的掙扎和努力。從前文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梭羅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始于彼時的超驗主義,而促使他走上自然寫作之道的恰恰是在反叛性地繼承和發(fā)展超驗主義之上開始的,這一歷程中最突出的節(jié)點則是他在其導師愛默生的點撥之下完成了第一篇廣受公眾認可的自然史散文。初嘗自然寫作成功之時,梭羅不僅找到了自己興趣之所在也確認了合適自己的創(chuàng)作體裁(即散文),最重要的是他在與自然的互動關系中達成了對自我內(nèi)與外的探索,確立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將人的自我成長和自然的歷史性與周期性發(fā)展對應、結(jié)合,這或許是梭羅成為后來的生態(tài)文學之先驅(qū)的重要原因。可見,梭羅的自然寫作歷程揭示的是一個作家對人與生境(社會與自然)潛能互動的從外到內(nèi)、從內(nèi)到外并循環(huán)上升的體悟之心路,展現(xiàn)了生態(tài)文學作品生發(fā)的機制。
六、結(jié)論:自然作為一種信仰
米爾德指出,梭羅發(fā)展新事業(yè)新方向后,“把他的先驗主義淡化成了更加模糊不清的教條,使他能夠照樣可以宣揚他們”。[1]193-195那么這個所謂的“模糊不清的教條”是什么,又有什么意義呢?這些米爾德并沒有在他的書里給出明確的答案。
在1851年底至1852年初之間的日記中,梭羅表達了他直接描述自然后的喜悅心情:“我感到幸福,我熱愛生活”。[9] Ⅳ,159接下來的日記表明,這種如天真孩子般的信心并非一日或一時的感嘆。1852年1月,他又在日記中激勵自己要“跟上季節(jié)轉(zhuǎn)換的步伐” [9] Ⅳ,244。種種跡象表明,作為博物學家和自然史作家的梭羅發(fā)展得相當順利,而且技巧也已經(jīng)很高超了。但是,到了1852年中,精力衰退、視力下降,失落和冷漠這些情緒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他對自己日常活動的評估中。這很大程度上跟他自己的身體狀況有關系。但是梭羅顯然不是一個輕易承認失敗和妥協(xié)的人。在日記中,他總是在失落地表述之后又突然在結(jié)尾表達了熱烈的渴望,以期獲得精神上的振奮。在一則日記中,他這樣確立自己的接下來的任務:“記錄下精選出來的經(jīng)驗,這樣我的寫作就會給我啟發(fā)。——最后我能夠把各個部分串聯(lián)成一體。” [9]Ⅳ,277這說明他需要一個積極的信仰來尋找、塑造一個完整的自我。
因而,“上升的修辭成了1852和1853年鞏固他超越自我的動力的方法,抵制身體的下滑以及日常經(jīng)驗的精神摩擦。”[1]200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瓦爾登湖》的最后定稿出現(xiàn)了一種有意而為的樂觀向上,而且加入了大量對自然的精微描述。最明顯就是對秋天和冬天兩個章節(jié)的添加和大量擴充。這應該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如此“集中地對普通事物做過如此詳盡的欣賞性描寫”。[1]302米爾德就此認為自然對梭羅具有三種救贖功能:凈化、調(diào)解和指導。[1]211-223
自然對于愛默生而言其功能則是“傳統(tǒng)道德真理的指南”,這基本合乎了18世紀“廣義自然”的認識:自然是人類生活的背景(background),而不是個人經(jīng)驗的前景(foreground)。在愛默生看來,藝術(shù)的價值和自然類同,即對大眾進行道德倫理的啟示和指導。[6]13這和梭羅致力于尋找自然對個體信仰的激發(fā)不同。在自己的自然觀察和實驗中、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梭羅試圖把倫理道德與審美體驗的狂喜區(qū)分開來,其真正的用意在于把握自然本身所激發(fā)的瞬間花火。這顯然是一種類宗教的體驗。
由此可見,自然對于愛默生是一種工具,而對梭羅則是一種信仰。到了其創(chuàng)作后期,梭羅更細致地觀察康科德叢林、湖泊、山川,而追憶古代圣者、英雄的文章在《瓦爾登湖》之后更是明顯減少,其自然寫作的特征基本形成。梭羅的意欲是很清楚的:他在試圖建立與自然的直接關系,而深層內(nèi)涵是重建與宇宙的原初關系,聯(lián)接或親自去感知宇宙無聲無臭中傳遞給每個人的信息,獲得一種崇高感。可以說,“梭羅的宗教意識滲透在他所有的自然觀察中”。[15]257這種“宗教意識”儼然已失去了傳統(tǒng)基督教的意味;而是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超靈”隱身于天地萬物之中,是表面繁復多樣的自然現(xiàn)象背后的那個“一”。這就回答了米爾德提出的“模糊不清的教條”的含義:自然是梭羅靈性得以滋養(yǎng)和不斷更新的源泉——但這是一種只可意會卻難以言傳的體驗。這一點倒是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理念有著深層的契合:道生一,一生萬物;天人合一,萬歸一。參考文獻:
[1]〔美〕羅伯特·米爾德.重塑梭羅 [M].馬會娟,管興忠,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2]〔美〕沃濃·路易·帕靈頓.美國思想史[M].陳永國,李增,郭乙瑤,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3]〔美〕梭羅.瓦爾登湖[M].徐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
[4]袁鼎生.超循環(huán)生態(tài)方法論 [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5]Henry David Thoreau.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20 vols [M].Bradford Torrey, ed.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6.
[6]Joel Porte. Emerson and Thoreau: Transcendentalists in Conflict[M].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6.
[7]Steven Fink.Thoreau and His Audience [C]// Harry R. Garvin,ed.“Natural History of Massachusetts”,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New Dimensions.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8]Sherman Paul.The Shores of America: Thoreau's Inward Exploration[M].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8.
[9]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5 vols [M]. John C. Broderick, e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
[10]Nathaniel Hawthorne. The American Notebooks[M].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2.
[11]Robert D. Richardson, Jr., Thoreau and Concor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reau[M].Joel Myerson, 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12.
[12]Ronald Wesley Hoag.Thoreaus Later Natural History Writing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reau[M].Joel Myerson, ed.1995.
[13]Joel Porte. Emerson and Thoreau: Transcendentalists in Conflict[M].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6.
[14]Buell Lawrence.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C].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Christopher A. Dustin, Thoreaus Religion[C] // Jack Turner, ed. A Political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2009:257.
[16]袁鼎生.生態(tài)藝術(shù)哲學 [M]. 北京:商務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