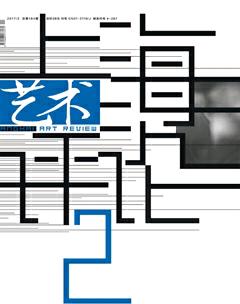早春的溫暖與寒意
車驍
如果說《早春二月》舞臺上那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喻示的是步入絕境的中國傳統文化,那么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機遇是否可以鼓舞中國的舞蹈家們修補那艘破船,使它重新煥發生機?正如詩仙李白在《行路難》中慷慨激昂地表述的那樣,盡管“行路難,難于上青天”,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上海的三月,乍暖還寒,陣陣暖意不時地被不愿離去的寒氣驅散。在春天與冬天你推我攘中,我有幸觀看了上海歌劇院出品的現代舞劇《早春二月》。這是一部表現迷惘、彷徨、猶豫、放逐與救贖的劇。從中我不僅看到了劇中人物的糾結,也看到了創作者們的糾結。這種糾結來自于近二百年來一直困擾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大命題,即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作為現代中國文學經典的中篇小說《二月》,通過一個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蕭澗秋在一個江南小鎮的遭遇,反映大時代的風云變幻給予個人命運的影響。民國時期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開始逐步解體,西方的文化、政治、經濟力量逐漸涌入的年代,社會在經歷巨大的轉型,戰爭頻仍,動蕩不安。作為一個在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蕭澗秋有著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救民于水火之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文情懷。他又經歷過現代文化的洗禮,會彈鋼琴,走南闖北多年,見過世面。但這種洗禮不足以讓他成為引入現代文明的先鋒,他厭倦了城市生活的喧囂,退隱到一個傳統氣息濃郁的世外桃源般的江南小鎮,通過教書育人和幫助身邊人來實現自己救國救民的理想。所以他既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又有道家的出世情懷,是在儒道二者之間徘徊的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敏感、文雅、中庸、矜持。與他相比,小說中不顧自身和家庭的安危投入時代洪流、在北伐戰爭中壯烈犧牲的李先生是堅定地改變舊中國的勇士。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文化決定著蕭澗秋的思想,是其行為的深層動力。小說中的文嫂更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她的悲苦與自殺都與中國傳統社會對婦道的種種清規戒律有關。小說中的陶嵐是富裕家庭中養尊處優的大小姐,她向往新事物,所以對遠方來的蕭澗秋非常感興趣。但她自小生活在江南小鎮,也帶著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小說中芙蓉鎮的居民們所代表的是傳統中國社會落后封閉、愚昧無知、內訌傾詐的惡習,即魯迅先生所感嘆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可憐又可恨的國民。所以小說結尾蕭澗秋認識到傳統中國社會不是可以安居樂業的桃花源,只有投身于大革命,徹底改變舊中國,才能實現個人理想和個人價值。
這是一個特定年代所發生的特定故事,脫離了民國江南小鎮這個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就不能解釋人物行為的深層動因。雖然王媛媛聲明“尋找自我價值”“自我彷徨”“自我救贖和自我放逐”“對人性的觀照”等是超越時代的共通話題,但是人物的思想和行為是具體的,有具體的社會、文化、歷史和個人原因。人性也是具體的,在不同的環境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要想成功地塑造出人物,就要用相應的舞臺藝術符號構建出人物所處的自然、人文、社會環境,才能讓觀眾理解作品的內涵和意義。
舞劇的舞美忠實地構建出了江南水鄉的小環境和廣闊的社會大環境。作為舊中國隱喻的傷痕累累、瘦骨嶙峋的大船殘骸、古樸灰暗的石墻和民屋、清冽枯干的老樹枝、稀疏零落的樹葉、孤零零的石拱門、風起云涌的天空、波濤翻滾的浪花,既有著中國水墨畫含蓄、雋永、空靈的意境,又隱喻了在時代洪流中衰敗凋零的中國傳統社會。男演員所穿的長衫、馬褂、中山裝,女演員身上的立領斜開襟的短襖、小褂、長裙,以及長辮和發髻雖然沒有完全復制民國時期的衣著打扮,卻具有鮮明的民國特色。群眾演員所穿的藏青色馬褂上畫著一道道如同繩索的黑線,暗喻小鎮中的人們所受的重重束縛。服裝的色彩也體現人物性格。陶嵐的藍色體現她的開朗大氣,向往海闊天空,紅色象征她青春的火熱激情,白色暗喻她少女的純潔無瑕。文嫂的褐色表現她的沉郁、黯淡與絕望,白色表征著她屢次遭遇的死亡打擊。群眾的灰色隱喻他們是帶來災難的黑暗力量。
舞劇的音樂以交響樂為主,運用了鋼琴、鋼片琴、長笛、弦樂、打擊樂等樂器。交響樂在塑造廣闊的時代大環境、群眾的力量和澎湃的激情方面非常有力。音樂從一開始就激昂有力,排山倒海,急促又揪心,烘托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氛圍。鋼琴和鋼片琴的明亮音色傳達出了蕭澗秋所帶來的現代文化氣息,長笛的悠揚表現了陶嵐的優雅美麗,弦樂的揪心喊出了文嫂郁積于心的哀怨。打擊樂敲擊出命運和時代的鼓點,預示著不祥的征兆。一身黑衣的歌隊站在觀眾席兩邊的二樓包廂中,起到了與古希臘戲劇中的歌隊類似的作用。作為本地人的代表,歌隊幫助建立起戲劇情景,構筑起道德和社會的框架,對劇情做出評論,對人物做出判斷。歌隊同時作為理想的觀眾,對事件和人物做出反應。歌隊大部分時候發出的是無意義的哼鳴,釋放出壓抑于心底的哀怨和掙扎。歌隊有時營造出廣闊的聲場,象征大時代的風起云涌。歌隊有時扮演劇中的角色,通過多聲部進行互動和對話,產生沖突和矛盾。當歌隊唱出可辨識的歌詞時,就直接參與了劇情的發展,例如:“可憐啊,可憐啊”“走開、走開、走開”“不要期待他,不要期待他,仿佛一個人……”。歌隊增加了戲劇景觀,強化了戲劇沖突,提升了戲劇效果,是有益的嘗試。
但總體來說,交響樂隊的洶涌澎湃和激昂有力與江南水鄉的地理人文氛圍并不十分契合,江南音樂的特色也不突出,這主要是因為要配合劇中的現代舞語匯而設計,而舞蹈語言是張揚、舒展、隨性且熱烈的。自由變換的身體語言毫不拘束地表達自我,毫不隱藏地宣泄情感,這種自由和開放正是王媛媛喜歡現代舞的原因。但問題是,這樣的身體語言表達出了那個時代和那個地域的人們的心理和性格了嗎?動作符號與繪畫和音樂一樣,是文化的產物,揭示著人物思想和行為的深層原因。如果沒有了江南小鎮含蓄、內斂、保守、古樸的風格,沒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庸、平衡、圓滿、蘊藉的身韻情致,如何理解人物苦悶彷徨猶豫的深層原因呢?在本舞劇中,我看到的是男主人公在兩個女人之間徘徊,一個女人火熱、活潑、青春、大膽,另一個女人憂郁、悲傷、拖家帶口,男主人公主動去擁抱安慰帶孩子的婦人,而年輕女子主動擁抱、追求他。群眾給三個主要人物施加重重壓力,同時也遭受著相似的命運。但人物除了身著民國服裝之外,身體語言都是現代作派,沒有表現出傳統禮教的束縛和中國文化的痕跡,也就沒有傳達出這是由于中國社會的閉塞、守舊、愚昧、內訌、傾詐所造成的悲劇。
在中國當代的舞蹈創作中,以現代舞的形式表現中國歷史內容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中國古典舞在20世紀50年代建立之初就先天不足,沒有形成自己獨立完整的體系,挖掘創造出來的語匯非常貧乏,演員的培養很大程度上根基于芭蕾的訓練,因此從中國古典舞者轉換成現代舞者是非常順暢自然的事。許多中國古典舞者自我放逐,紛紛加入到現代舞者的大軍當中。最常見的聲明是:現代舞最開放,最自由,最具備現代氣息,最能反映當代人的心聲,最符合當今觀眾的審美需求,最能超越時代與國界的限制,最能與國際接軌。但面向當代的價值取向,導致作為“國舞”的中國古典舞的羸弱以及中國人的身體語匯的缺失。
這種羸弱與缺失也是中國文化從近代開始衰弱的產物和表征。我們也許不能奢望風華正茂的舞蹈創作者們能像孫穎一樣,沉下心來十年磨一劍,從文物和故紙堆中挖掘出中國古典舞的精髓和表意體系,創造出《踏歌》一般可以代表中國的舞蹈。但云門舞集中運用太極導引等中國元素創造出的中國式的現代舞,是否可以啟發更多的舞蹈家們用舞蹈傳達出中國哲學、文化、美學和精神風貌呢?如果說舞臺上那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喻示的是步入絕境的中國傳統文化,那么中華文化復興的時代機遇是否可以鼓舞中國的舞蹈家們修補那艘破船,使它重新煥發生機?正如詩仙李白在《行路難》中慷慨激昂地表述的那樣,盡管“行路難,難于上青天”,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當今已煥發生機的江南小鎮們也在召喚著在茫茫大雪中自我放逐的蕭澗秋們,他們所留下的,并不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而是悄悄地走近的春天的腳步,正催發著中國文化萬紫千紅的又一個春天。愿中國舞蹈,也成為這百花園中無比璀璨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