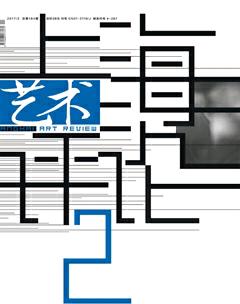國產文藝片與新的文化經驗
張慧瑜
中國電影市場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規模效應,這為電影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機和空間。但從近些年的電影中可以看出,一些電影工作者依然拘泥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邏輯繼續講述老故事,這就使得電影作品無法跟上或滯后于時代的步伐,而另一些藝術家對中國的變化有敏銳的感知,傳遞出一些新的中國經驗,這有益于形成有中國主體的文化表達。
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在制片方式和院線發行兩個方面采取更為市場化的機制,這一方面使得民營資本成為中國電影的主要投資方,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類型化的商業片作為中國電影的主流形態。曾經在上世紀90年代存在的體制內制作(地上電影)與體制外制作(地下電影)的區分失效,目前中國電影只存在根據投資規模確定的大片和中小成本電影或者按照類型化強弱劃分的商業片和文藝片。對于中國來說,原有的國營電影制片方式及現實主義的故事片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逐漸衰落,隨之出現了受到港臺地區、日本、好萊塢影響的商業片和歐洲作者電影影響的文藝片(藝術片)。這種商業電影的主導形態對文藝片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是因為文藝片融資難并受到商業院線的擠壓;機會是文藝片不用像上世紀90年代那樣主要走國際電影節路線而有一些機會進入院線,吸引文藝片的觀眾。2016年就有多部文藝片進入商業院線發行,盡管很難帶來市場效應,但其特殊的藝術表達和社會關懷,有助于提升中國電影的文化品質。相比情節緊張、快節奏的商業電影,文藝片有四個基本特征:一是藝術片屬于作者電影,帶有強烈的導演個人風格;二是對電影語言有高度自覺,追求特殊的影像表達,從風格上多使用長鏡頭、慢節奏,內容上去情節化,臺詞很少,往往是中小成本,使用非職業演員進行一種去表演化的表演;三是探尋哲理化的主題,對現代社會和生活有批判色彩,處理孤獨、異化、記憶、時間、生命等基本命題;四是,藝術電影的功能不是娛樂性的,給觀眾帶來思考和反思。我把近期上映的文藝片大致分為四個主題,一是歷史與記憶,如《百鳥朝鳳》《黑處有什么》等;二是詩電影或哲理電影,如《路邊野餐》《長江圖》《塔洛》等;三是現實諷刺劇,如《驢得水》《我不是潘金蓮》等。
歷史與記憶
在近些年的文藝片中,《百鳥朝鳳》是一部略顯特殊的作品。這部電影2013年制作完成,直到2016年才進入院線,是著名的第四代導演吳天明的遺作。制片人為了推動這部小成本影片的發行采用給院線負責人下跪的方式,這引發了爭議,也充分說明藝術片在商業院線中所處的邊緣位置。與其他帶有現代主義基調的文藝片不同,這部電影從影像風格到主題都延續了上世紀80年代現實主義電影的傳統,如同影片中的老嗩吶藝人面臨技藝無法傳承的文化困境,這種吳天明式的現實主義電影在當下主流的商業電影和文藝片中也顯得格格不入。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一般使用情節劇和戲劇化的敘事方法,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以現實問題為切入點,對所呈現的問題往往有清晰地批判態度。這種藝術對現實的干預本身與現實主義藝術試圖改變現實的訴求有關。隨著80年代對革命文藝的反思,這種現實主義藝術就處于失效狀態,藝術與現實的關系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不過,這部電影卻延續了現實主義電影對于鄉村、農民故事的敘述策略,從鄉土社會內部而不是他者的視角講述了具有主體性的鄉村故事。只是在人們惋惜嗩吶技藝以及鄉土空間的消失的時候,這種以鄉村為前現代、以城市為現代的二元對立是80年代的文化產物。在這個意義上,這部電影延續了80年代的文化邏輯,卻沒有對這種邏輯做出新的反思。
相比《百鳥朝鳳》,《黑處有什么》這部70后女導演王一淳自編自導的青春片處理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縣城少女的成長故事。與近些年熱映的白衣飄飄的、去歷史化的、去空間化的青春片不同,《黑處有什么》有著清晰的時空標識,地點發生在中原地區的一個飛機場,時間是1991年夏天。借助中學生曲靖的眼光一方面呈現了少女成長中的各種糗事,另一方面又展現了那個特定時代的氛圍。影片最大的特色是發生在社會主義單位制空間中,這是一個鄰里之間都認識的熟人社會,又隱藏著莫名的危險,就像處于性啟蒙階段的曲靖對外部世界既緊張又向往,總想弄清楚“黑處有什么”。這也是一部獻給父親的電影,曲靖的父親是一個在家自以為是、在單位不受領導重視的男人,這樣一個有點書呆子氣的父親,在曲靖的少女時代扮演著教育者和呵護者的角色。這部電影的意義有兩個,一是把90年代歷史化、相對化,變成與當下時代不同的另外的年代;二是,把90年代的故事放置在中小城市的社會主義單位制空間中(如地方國有企業),這是一個國企改制、商品房改革之前的歲月,如其他電影《少年巴比倫》(2016)、《八月》(2016)等都是如此。可以說,這種對90年代中前期社會氛圍的感傷和懷舊本身是一種對當下時代的不滿。
新的中國故事
2016年有兩部商業電影取得了不錯的票房,也講述了新的中國故事。一部是國慶檔上映的主旋律大片《湄公河行動》。這部電影改編自2011年中國公民在湄公河遇難的真實案件,正面呈現了中國警察到境外抓捕國際毒販的故事。中國刑警不再是“小米加步槍”式的游擊隊,而更像是被先進裝備“武裝到牙齒”的美國海豹突擊隊,這種主動出擊、境外作戰、為無辜受害的中國人討還正義的行動本身已經彰顯了中國崛起的大國地位和國家自信。另一部是2016年末張藝謀導演的中美合拍魔幻大片《長城》,中國電影也開始像好萊塢那樣以人類的名義講述故事。與這些“敏感”的商業電影相似,一些藝術電影也有意、無意地呈現了新的中國經驗。
80后青年導演畢贛用30萬的經費在自己的故鄉拍攝了《路邊野餐》,“路邊野餐”是一本詩集的名字,這些現代主義色彩的詩歌強化了這種特殊的空間與人的生存狀態的關系。這部電影具有兩個特征,一是嫻熟地使用現代主義電影的影像風格和敘事語言,處理的是時間、記憶、尋找等哲理化的、普遍的人類主題,二是這種“通用”的藝術電影“語法”又講述了一個高度本土和在地化的中國故事,影片選取了貴州凱里特有的氣候和陰雨中的山林,使得這種尋找帶有一種神秘的、亦真亦幻的色彩。
與文藝片對邊緣人群和中小城市的關注不同,70后導演楊超和臺灣知名攝影師李屏賓拍攝的《長江圖》講述的是長江的故事,一位男性河工高淳開著父親留下的運輸船從上海逆江而上,一直尋找長江的發源之地,由于長江本身是中國文化的象征,因此,這是一部帶有抽象和宏大主題的電影。這部電影的基調一開始看起來很像典型的第六代電影:一個父親死亡的兒子,在一本神秘詩集的引領下,游覽一個又一個長江沿岸的地點,呈現這些地方的風土人情和歷史傳說,中間還遭遇一次閹割式的刺殺。實際上,這部電影超越了第六代電影的視野,把個人(男性)葬父尋母的故事與長江這一具有高度符號化、象征性的空間結合起來。這種尋根故事所表達的不再是如80年代歷史文化反思運動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和否定,而是正面展現了一個煙雨縹緲的、詩意綿長的“長江”畫卷,如同影片的名字《長江圖》所包括的古典韻味。影片結尾處,高淳站在長江發源地青藏高原上回眸一望,出現了航拍鏡頭下的萬里長江,如此大的視野顯示了一種新的中國主體和文化自信。
2016年底藏族導演萬瑪才旦的《塔洛》上映,這是首部藏語電影進入院線,主要講述了名叫塔洛的牧羊人進城補辦身份證的故事。電影呈現了三種不同的社會空間,一是派出所,塔洛面對所長用普通話背誦《為人民服務》,顯示了塔洛一方面有毛澤東時代的文化記憶,另一方面又受到國家機構的管理,需要身份證來確認自己的身份;二是縣城空間,如照相館、理發館、KTV包房等,塔洛一進城,電影多拍攝鏡子里的塔洛,這些現代的、城市化的空間對他來說是一個帶有虛幻色彩的世界;三是牧場,塔洛在偏遠的山區給老板放羊,這里雖然生活很艱苦,但塔洛如同自由自在的牧羊人,過著自然、純凈的生活,而故事的另一面是,塔洛如同沒有尊嚴的農奴,經常受到老板的欺壓。影片表面上看起來是來自大山里的、長期在野外放羊的塔洛與文明、現代的城市生活之間的沖突,實際上是借塔洛的眼光(原始的、純潔的)對充滿誘惑的現代生活以及以“為人民服務”所象征的政治權力的反思。
與“現實”調情
2016年還出現了兩部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黑色幽默電影:《驢得水》和《我不是潘金蓮》。在商業化、娛樂化成為主流文化的氛圍里,拍攝帶有現實主義色彩的政治諷刺片是不容易的事情,這不只會有胎死腹中的政治風險,更要冒著血本無歸的市場風險,從這兩部影片上映后的平淡的市場反映也印證了這一點。
《驢得水》改編自同名話劇,講述了民國期間一群有理想的知識分子從事鄉村教育,卻將一頭驢虛報成老師冒領薪水,而教育部的特派員來追查此事,由此引發了一系列鄉村教師(知識分子)、銅匠(農民)與特派員(權力)、美國慈善家(金錢)之間荒誕不經又發人深省的故事。這部電影處理了80年代以來關于知識分子的兩個問題,一是知識分子是否具有特立獨行的品格,不為金錢、權力所折腰;二是知識分子能否走向民間、與工農相結合,也即是啟蒙是否有效的問題。而電影給出的是否定的回答,似乎是批判、諷刺了知識分子的虛偽和懦弱,實則是延續了80年代以來解構、污名化20世紀轟轟烈烈的大歷史的既有策略,沒有崇高的、超越性價值的人,每個人都是趨利避害的、物質主義的個體,這顯然吻合于市場經濟時代對人性的要求。
《我不是潘金蓮》借民女李雪蓮的軸勁現了一把官場的原形,也順便給各級官員上了一堂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黨課,這種“左右逢源”“嬉笑怒罵”的功夫來自于導演馮小剛的頑主底色。在馮氏喜劇中,既可以光明正大地開舊體制的涮,如《甲方乙方》(1997)中把地主剝削、嚴刑拷打等革命戲碼變成“好夢一日游”的文化旅游項目,又可以毫不客氣地站在小老百姓的立場上損大款,如《甲方乙方》中葛優坐在公共汽車上諷刺開大奔的、把大款送到農村憶苦思甜等。這種對權力、資本的嘲諷在《大腕》(2001)、《私人訂制》(2013)等電影中都有淋漓盡致地表現,只是這種帶有語言快感的諷刺并非真正的批判和拒絕,恰好相反,馮小剛電影在權力與資本之間游刃有余,經常實現雙贏效果。
不過相比馮小剛的其他電影作品,《我不是潘金蓮》最大的特點是一部高度風格化的電影。如果說劉震云的原小說講述的是李雪蓮為了證明“我不是潘金蓮”而與現實生活秩序抗爭的故事,那么電影版則把這種十余年的艱難上訪展現為一幅又一幅江南水鄉的圓形風景畫。本來以電影風格樸實無華見長的馮小剛卻劍走偏鋒,追求一種特殊的視覺效果,這就是圓形和方形畫面的使用。按照導演的說法,圓形畫面來自于對宋代扇面繪畫的靈感,方形與圓形表達的是“天圓地方”“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中國大義。在電影中圓形和方形象征著兩種不同的空間秩序,圓形是小橋流水、白墻黑瓦、陰雨連綿的江南小鎮,方形則是四四方方、莊嚴肅穆、戒備森嚴的京師重鎮。從圓形一路穿越到方形,對于李雪蓮來說并沒有本質的變化,這依舊是一個中國式的人情社會,這依舊是一面映照李雪蓮的“鏡中像”。這種遮住大部分畫面、只保留銀幕中間位置的鏡頭方式約束了攝影機的運動,也很難使用對切、特寫鏡頭,只能靜止不動地、有一段距離地“觀看”,以中景鏡頭為主。這種沒有反打鏡頭的觀看變成了一種無法提供觀看主體的觀看,也是一種暴露觀看者的戲劇式觀看。這種被預設的觀看依然是一種頑主視角,也只有“長不大的”頑主有挑釁官場的勇氣和窺視政治的欲望。
這種帶有窺視感的鏡頭方式呈現了兩種對權力的態度。一是,在這種被限定的、扁平化的空間里,官員之間形成了一種等級化的從屬、主奴關系,呈現了下級對上級的逢場作戲、唯唯諾諾的丑態,如法院荀院長請老領導吃飯、馬市長與鄭縣長在河邊密談、鄭縣長在辦公室訓斥賈聰明等,這諷刺了“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官本位現象;二是,電影中還經常使用后腦勺鏡頭,也就是在領導后面拍攝會議場景,這就使得遠遠地窺視變成了一種自上而下的審視,用一種更高的權力來批判這種官官相護的、脫離群眾的行為。這不僅為曝光官場的不正之風提供了“尚方寶劍”,而且把對官場生態的揭露變成了一種自上而下的反官僚主義自律。這種對官場隱秘生活的窺視以及攜更大的權力對官員的呵斥,與其說體現了馮小剛借李雪蓮的柔弱之軀來批判權力,不如說顯示了馮小剛及頑主一代對革命年代反官僚主義傳統的繼承。有趣的是,李雪蓮與各級官員在一起時,民與官的關系基本上是平起平坐,甚至李雪蓮更占據畫面中心位置,理直氣壯的李雪蓮身上或多或少帶有“人民當家作主”的底氣。
目前來看,中國電影市場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規模效應,這為電影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機和空間。但從近些年的電影中可以看出,一些電影工作者依然拘泥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化邏輯繼續講述老故事,這就使得電影作品無法跟上或滯后于時代的步伐,而另一些藝術家對中國的變化有敏銳的感知,傳遞出一些新的中國經驗,這有益于形成有中國主體的文化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