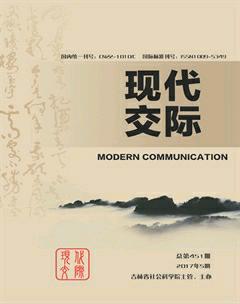緩刑適用“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之文義解釋
趙興洪

摘要:緩刑適用條件中的“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不能僅從字面含義解釋,而必須進行規范的文義解釋。“沒有”從實體上講不是零風險,而是指風險可控;從程序上講是對證明要求的強調。“再犯罪”應從預測重點和預測方向兩個角度進行考察。“危險”既指已經實施的犯罪體現出來的再次犯罪可能性,還包括可能實施的后罪的社會危害性。
關鍵詞:緩刑 沒有再犯罪的危險 再犯預測 文義解釋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5-0053-04
《刑法修正案(八)》對緩刑適用條件進行了修改,特別是增加了“沒有再犯罪的危險”這個核心要素。但是對于其含義,目前卻是眾說紛紜。立法機關工作人員認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是指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其不會再次犯罪,如果犯罪人有可能再次侵害被害人,或者是由于生活條件、環境的影響而可能再次犯罪,比如犯罪人為常習犯等,則不能對其適用緩刑。[1]顯然,這個解釋方案過于簡略了。筆者認為,要合理解釋“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必須解決好四個問題:第一,如何妥當解釋其字面含義,這需要進行文義解釋;第二,如何妥當安排與其他三個實質要件要素的邏輯關系,這需要進行體系解釋;第三,如何理解“沒有再犯罪的危險”與“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關系,這可能需要進行歷史解釋和體系解釋;第四,把握不同法律制度(如假釋制度)里“再犯罪危險”的異同。本文僅從第一個角度加以闡釋。
一、“沒有”之規范涵義
“沒有”的字面含義過于絕對化,從經驗上講并不合理,因為很難說一個人犯罪后完全不會再次犯罪。況且預測本身就意味著概率判斷,零概率預測難以實現。此外,刑法的相關規定也表明,“沒有”不等于“零”。如刑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法律對緩刑犯同時規定禁止令,實際上就是承認緩刑犯是存在再犯罪危險的。總之,“沒有危險”不等于“零危險”,而是一種低風險、可接受的風險,或者說相對安全的風險(safe risk)。[2]如果要求罪犯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才適用緩刑,必然導致法官不敢適用緩刑。故“沒有”宜理解為一種強調,其規范含義可以從實體和程序兩方面來理解。
從實體上講,“沒有”是指再犯罪的可能性低,再犯罪的危險性小。即從實體上講,“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之“沒有”是指風險低、風險可接受、風險安全可控。至于風險小到多少才算“沒有”,無法也不應該用一個具體的概率來作為標準。這是因為:
1“沒有”首先涉及緩刑政策問題
如果國家要嚴控緩刑適用,則可能性應該趨近于零才好;如果國家要鼓勵適用緩刑,則再犯罪的可能性低于50%也是可以接受的。在犯罪形勢寬松的時候,“沒有”的標準可能會寬一些;而犯罪形勢嚴峻的時候,“沒有”的標準可能會更嚴一些。
2.“沒有”與國家的治理能力有關
如果國家犯罪控制能力強,則可以容許的危險性就可能相對高一些;如果國家犯罪控制能力較弱,則“沒有”的標準可能就會更嚴。
3.“沒有”與一個國家、民族的“犯罪觀”有關
在犯罪的質、量問題上,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公眾容忍度是大不一樣的,也是不穩定的,這都會影響公眾和司法工作人員對“沒有”的理解。比如,其實大家都不確信交通肇事罪罪犯“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但是公眾對交通肇事罪的緩刑適用接受度相對較高——至少反感度相對較低,其實就與公眾對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觀”有關。公眾自然不期望看到因交通肇事導致人身和財產損失,但在現代社會背景下,人人都高度依賴各式交通工具,都在參與各種交通活動,這種“風險參與”角色自然會增加其對交通領域犯罪的同情式理解。
4“沒有”與犯罪種類也有關系
比如,對那些“無被害犯罪”,“沒有”的標準可能就會相對寬松一些;而那些與人身和財產安全高度相關的犯罪,“沒有”的標準可能就會更嚴格一些。
從程序上講,“沒有”應指再犯可能性低有充足的事實基礎,有高度蓋然性的證據予以支持。即“沒有”其實是強調程序上的“確信”,是對證明要求的強調。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定罪的證明要求都是“確實、充分”,沒有體現出證明要求的“梯度”。筆者認為,由于再犯罪的風險是未來的風險,是一種預測,其證明要求可以稍微低于定罪的“確實、充分”要求,即滿足高度蓋然性要求即可。
總之,“沒有”不能單從字面含義以數理科學的眼光來進行解讀,“沒有危險”不等于“零危險”。
二、“再犯罪”的范圍
再犯罪,顧名思義就是再次犯罪,簡稱再犯。再犯既可以指再次犯罪的人,也可以指再次犯的罪,還可以指再次犯罪的過程、行為。再犯不同于累犯。在我國,累犯主要是一個規范概念,而不僅僅是多次、頻繁犯罪的意思。再犯不一定是累犯,累犯一定是再犯,而且是再犯中最危險的人。刑法規定的是“沒有再犯罪的危險”,而不是“沒有累犯的危險”,表明了立法者不容忍任何再犯的立場以及期待預防、遏制所有再次犯罪的美好愿望。然而要預防所有再犯幾乎不可能,因為預測所有再犯就不可能。這不僅僅因為“測不準”是普遍原理,還因為犯罪人和犯罪行為有其特殊性。首先,犯罪人包含理性犯罪人、部分理性犯罪人和無理性犯罪人[3];有極端的觀點甚至認為,犯罪人在本質上可以認定為非理性。[4]對于非理性的犯罪人,自然難以預料其將來行為。其次,有些犯罪因偶然性因素觸發或與環境因素結合而觸發,不是或不只是犯罪人“理性計算”的結果,當然也難以有效預測。既然并不是所有犯罪都能有效預測,與其“面面俱到”,不如“有的放矢”——科學劃定“再犯罪”范圍顯然有利于提高預測準確性,進而有利于合理分配司法資源、刑罰資源,制定針對性的監督、矯治措施,提高預防效果。
筆者認為,關于“再犯罪”的范圍,可以從兩個層面予以探討:預測重點與預測參照。前者討論的是能不能有效預測的問題,后者討論的是預測方向的問題。
(一)預測重點(預測可能)
預測再犯實際暗含一個假定,那就是犯罪人具有一定的理性,犯罪是理性計算的產物。如果犯罪人不存在理性,或者犯罪發生是非理性的結果,那么預測實際上只能是猜測。就犯罪人而言,只要他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我們當然要推定其是理性的;而犯罪是否理性產物則需要具體分析。一般來說,大部分故意犯罪是行為人主動追求的結果,是“理性計算”的結果。如根據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人受快樂和痛苦的主宰,而且人性必然是“趨樂避苦”。因此,經過“苦樂計算”后,如果發現實施犯罪所得的快樂少于遭受懲罰的痛苦,人就不會去犯罪。[5]根據貝克爾的犯罪經濟分析學說[6],犯罪人像正常人一樣,在實施犯罪前會進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預期所得大于預期損失,犯罪行為才會發生。用公式表示就是:EU=P(s)×G-P(f)×L。其中,EU表示預期收益(expected utility);P(s)表示犯罪成功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success);G表示預期從犯罪行為中得到的利益(gains),例如金錢、財物;P(f)表示犯罪失敗的可能性(possibility of failure);L是如果犯罪失敗就會隨之遭受的損失(losses),例如被判處監禁等。由此可見,預期收益越高,犯罪越可能發生。而這些理論,針對的也只能是“故意型犯罪”①。如果行為人壓根兒就沒有考慮實施某種犯罪行為并獲得某種結果,自然也就不會有“苦樂計算”或“成本收益分析”。
但是“過失型犯罪”②。就不一樣了。在大部分過失型犯罪情形下,行為人并非主動追求某種犯罪結果的發生,因此就不存在“理性計算”的可能。邊沁曾經指出,以下三種情形,懲罰必然是無效的[7]:(1)“無意”(unintentionality)情形。行為人不希望因而也不知道他將要實施某個行為,但最終實施了該行為;(2)“無知”(unconsciousness)情形。行為人知道將要實施某種行為,但不清楚伴隨該行為的所有外在環境,不清楚該行為產生危害的趨勢——基于該種危害,該行為在多數情形下被“刑罰化”;(3)“誤知”(missupposal)情形。行為人知道某種行為很可能造成某種危害,但誤以為伴有特定條件,該危害不會發生,或者會產生更大的好處,因而不會被立法者“刑罰化”。應該說邊沁使用的三個專有名詞比較晦澀,但是結合后文的解釋,我們還是可以大致了解其含義。邊沁所謂“無意”可能等同于我國刑法中的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無知”大致等同于我國刑法中的疏忽大意過失;“誤知”大致等同于我國刑法中的過于自信的過失和違法性認識錯誤。懲罰為何可能無效?因為這些過失型犯罪不存在理性計算。“過失型犯罪”往往發生在人的正常認知之外。對于這樣的犯罪,自然也就很難進行預測了。
需要注意的是,現代刑法理論往往從規范層面將過失犯罪理解為結果預見義務或結果避免義務的違反。但從存在論層面講,過失犯罪注意義務的違反可能是在“潛意識”里完成的[8]p477,而人類很難對“潛意識”進行有效控制。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油門當剎車”導致的交通肇事案件。類似這樣的過失犯罪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十分常見。顯然,我們很難預測這樣的犯罪是否再次發生。
當然,這并不是說所有過失犯罪都無法預測。事實上有些過失犯罪恰恰比較容易預測,比如實施高度危險行為導致的交通肇事行為——如醉駕、毒駕——就具有較高的預測可能性。因為交通肇事是與行為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緊密聯系的,只要行為人生活方式、行為模式沒有改變,“在同一個地方跌倒”的可能性就非常高。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角度來思考過失犯罪的預測可能性:
第一,區分行為故意與行為過失。
根據要素分析法[9],罪犯對過失犯罪不同構成要件要素——比如行為和結果——可能持有不同的主觀心理態度。就過失犯罪的行為而言,罪犯既可能持過失心態,也可能持故意心態。對犯罪行為持過失心態的即屬筆者所謂“過失型犯罪”,而且是“過失型過失犯罪”;對犯罪行為持故意心態的即屬筆者所謂“故意型犯罪”,而且是“故意型過失犯罪”。相對而言,對“故意型過失犯罪”的預測效果會更好。
第二,區分業務過失犯罪與普通過失犯罪。
我國刑法并未單獨規定業務過失犯罪,但實質上存在業務過失犯罪。[8]p504一般來說,業務過失犯罪可能比普通過失犯罪更適合預測。因為業務過失犯罪對應的業務行為,往往有非常詳細的操作規程。業務過失犯罪的發生,往往也是因為行為人違反操作規程而導致的。
第三,區分特殊主體與一般主體。
即便是業務過失犯罪,也可能由普通主體來實施。比如交通肇事罪是業務過失犯罪,但既可能由職業的駕駛人員實施,也可能由普通公民實施。相對而言,普通駕駛員更可能因為駕駛技術和駕駛心理原因——如駕駛技術差、油門剎車混淆、變道不當、對速度不敏感等——而構成交通肇事罪,而職業駕駛員更可能因為違反安全駕駛規則——如超速、超載、疲勞駕駛等——而構成交通肇事罪。顯然,因違反安全駕駛規則的交通肇事行為更值得威懾,刑罰對其更有預防效果,也因而更可能有效預測。
總之,從三個角度切入分析,就過失犯罪而言,能夠有效預測的應該是下表中1-4四種類型的過失犯罪,即“故意型過失犯罪”。
當然,盡管5-8這四種“過失型過失犯罪”很難預測,但由于這類犯罪不是行為人追求的結果,整體發生概率非常低,完全可以推定其“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即對于“過失型過失犯罪”,法官完全可以一律宣告緩刑。
(二)預測參照(預測方向)
犯罪學上有所謂犯罪方向之研究。如日本犯罪學家吉益修夫劃分了四種犯罪方向:單一方向(monotrop),指反復實施同一犯罪;同種方向(homotrop),指反復實施同一種類的犯罪,如財產犯罪、暴力犯罪;異種方向(ditrop),如先犯財產犯罪再犯風俗犯罪;多種方向(polytrop),指犯罪涉及三種以上犯罪類型。實證研究表明,盡管不是所有再犯都實施同一、同類犯罪,但實施同一、同類犯罪的最多,財產犯罪尤其如此。[10]預測再犯是根據已經實施的犯罪來預測可能會實施的犯罪,因此,已經實施的犯罪就成了一種預測參照,可以用于預測再犯之方向。已經實施的犯罪既包括本次犯罪,也包括本次犯罪之前的犯罪。當然,行為人之前實施的違法行為、越軌行為也可以納入考量。比如行為人在學校里經常欺凌小同學,盡管未構成犯罪,甚至未構成違法行為,但這足以表明其具有再次實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一般來說,大致可以根據同類原則來預測可能實施的犯罪,進而采取有針對性的監督、矯正措施。事實上由于罪名太多,不可能完全憑空想象可能實施的犯罪。當然,這里的同類犯罪可以適當寬泛,比如,罪犯本次實施搶劫罪,那么可以以此為參照,預測其更可能再次實施財產犯罪、暴力犯罪。預測參照的主要作用有二:一是為法官決策提供參考。假定罪犯甲的再犯可能性為40%,且可能再犯暴力犯罪;假定罪犯乙的再犯可能性為45%,且可能再犯賭博類犯罪。兩相對比,罪犯甲的再犯可能性更低,但是法官對罪犯乙宣告緩刑顯然風險更小。此外,法官還可以有針對性地宣告禁止令。二是有利于制定矯正干預措施。假定罪犯丙可能再次實施性犯罪,那么就有必要對其進行個性化的性癮癖、性犯罪抑制治療,采取適當的社會防衛措施。這也正是“風險-需求-回應”模式(Risk-need-responsivity model)的要義。[11]
綜上所述,盡管從規范上看,刑法并沒有限定“再犯罪”的范圍,但在判斷“再犯罪危險”的實踐中,基于預測可能和預測方向的考慮,有必要合理劃定“再犯罪”的范圍,進而作出更加科學合理的決策。
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再犯罪”的解釋學意義:第一,指明了緩刑實質要件的判斷方向:面向未來。再犯罪是沒有實施的犯罪,再犯罪是需要預測的假想犯罪。第二,指明了緩刑適用的核心標準。即主要判斷再犯罪危險性、可能性,而不是犯罪已經造成的社會危害性。這對于從整體上把握緩刑實質要件具有重要意義。
三、“危險”與“風險”
要理解“危險”的含義,首先有必要區分“危險”與“風險”。在漢語和英語里,“危險”(danger,dangerousness)與“風險”(risk)的含義都存在重合、交叉,但兩個詞仍各有側重。就再犯評估而言,英語使用(Recidivism) Risk Assessment這個詞組。《布萊克法律詞典》(第十版)對dangerous的解釋為:“(針對情勢、狀態等)危險的、冒險的、不安全的;(針對人、物體等)可能導致身體損害。”但對Risk的定義則主要圍繞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可能性(chance)以及保險(insurance)相關事項展開,其對Risk Assessment的定義為:“1,家庭法。確定一個人——經常指父母——傷害孩子可能性(likelihood)的程序。2,識別、預測、評估與活動有關的危害可能性(probability)并決定一個可接受的風險水平的活動。”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危險評估就是評估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因此,所謂“再犯危險評估”之“危險”,是指可能性,與中文“風險”的含義更加契合。當然,也有學者嚴格區分了“危險”與“風險”,認為人身風險性評估除了包括行為人自身主觀因素之外,著重對行為人與外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預測。在分析行為人自身危險性的基礎上,來判斷特定環境下行為人是否具有實施犯罪行為的風險。[12]筆者認為,刑法使用的“再犯罪的危險”而非人身危險性,故危險仍可包含可能引起再犯的外在環境因素。
我國刑法使用了“危險”一詞,但筆者認為,這里的再犯罪危險仍然主要指再犯罪的可能性。事實上從語法結構上分析也應該如此。“再”與“危險”的組合表明,這里的危險是指再次發生的可能性、概率、機會。此外,刑法條文用“的”字將“再犯罪”和“危險”分隔開來,說明“再犯罪”是整體修飾“危險”的。“再犯罪的危險”既不同于“再犯(的)罪的危險”,也不同于“再犯(人)的危險”。總之,這里的“危險”其實是“可能性”的代名詞,是一種可能再犯罪也可能不再犯罪的概率。統編教材也持這種觀點,認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是指“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評價較小”。[13]
但是還需指出,再犯罪概率判斷不可能只是一種形式判斷,而必須結合前罪與“可能后罪”的危險性來進行推斷、預測。就結合前罪預測而言,主要是看前罪(包括本罪和以前實施的犯罪)本身體現出來的再次發生可能性。比如,罪犯實施的是習癖性犯罪,如詐騙罪、招搖撞騙罪、盜竊罪、搶劫罪等,那么該罪犯就有更高的再犯可能性。就結合可能后罪預測而言,主要是指法官對可能后罪會有一個預期,而這個預期一般以前罪為參照。比如一個人犯了搶劫罪,那么法官自然會聯想該罪犯可能再次實施搶劫罪或類似暴力性財產犯罪(同種犯罪假定),或者實施更嚴重的犯罪;但一個人犯了交通肇事罪,法官一般不會直接聯想到其可能再次犯搶劫罪。而法官對可能后罪的預期必然會影響“危險概率等級”標準的判斷。簡單地講,如果可能后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小(犯罪嚴重性較小),法官對再犯概率會適當放松;如果可能后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大(犯罪嚴重性較大),法官對再犯概率會適當收緊。也就是說,法官在判斷再犯可能性時,有可能會選擇不同的參照標準。這種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刑事政策意義。如果我們需要擴大緩刑的適用范圍,那么就可以將“沒有再犯罪的危險”解釋為兩種情形: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小;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較大但可能實施的新罪的社會危害性小。比如假定某人再犯誹謗罪的可能性較大,但由于誹謗罪的社會危害性較小,且公眾容忍度較高,法官完全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對誹謗罪維持較高的緩刑率。
總之,“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之“危險”,既可以理解為整體的再犯可能性,也可以理解為由已經實施的犯罪體現出來的再次犯罪可能性,還可以理解為可能實施的后罪的社會危害性。如此一來,這里的“危險”事實上就包含了兩層含義:再犯可能性;犯罪的嚴重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使用“危險”這個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過筆者認為,“沒有再犯罪的危險”之“危險”主要仍指整體的再犯可能性。因此,如果認為該條文需要修改,宜將“沒有再犯罪的危險”替換為“再犯罪風險低”——“風險”不但可以包含犯罪嚴重性的意思,而且可以凸顯可能性這層核心含義。
注釋:
① 不同于規范意義上的故意犯罪,強調對犯罪行為的故意。故意犯罪一般都是“故意型犯罪”,但過失犯罪也可能是“故意型犯罪”,是為“故意型過失犯罪”。
② 不同于規范意義上的過失犯罪,強調對犯罪行為的過失。過失犯罪一般都是“過失型犯罪”,但間接故意犯罪也有可能是“過失型犯罪”,是為“過失型故意犯罪”。
參考文獻:
[1]王尚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解讀[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100.
[2]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Probation and Related Measures,New York,1951:4.
[3]張保剛.激情犯罪刑罰與立法的經濟學分析[J].河北法學,2013(11):71.
[4]陳和華.犯罪人的適應性非理性及其防控[J].政法論叢,2012(4):54.
[5](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M].時殷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57.
[6]Becker G S.Crime and Punishment:An Economic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8,76(2):169-217.
[7]Bentham J.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Batoche Books,2000:136.
[8]陳興良.教義刑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9]Robinson,Paul H.,and Grall Jane A.Element Analysis in Defining Criminal Liability: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beyond.Stanford Law Review 35.4 (1983):681-762.
[10]張甘妹.犯罪學原論[M].臺灣:漢林出版社,1976:127.
[11]Bonta J,Andrews D A.Risk-need-responsivity model for offender assessment and rehabilitation[J].Rehabilitation,2007(6):1-22.
[12]肖揚宇.從“人身危險”到“人身風險”——刑事禁止令的理論進路與制度基點[J].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13(2):135.
[13]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285.
責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