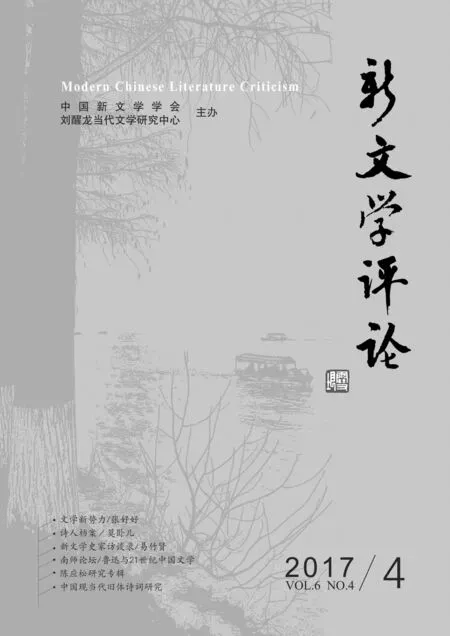邊地敘事中的人世與心史
———“70后”作家張好好長篇小說探析
◆ 烏蘭其木格
“70后”作家張好好出生于新疆的阿勒泰市布爾津縣,在這個西北的邊地小城,張好好度過了她的青少年時期。盡管長大成人后的作家離開了滋養她的這片熱土,但壯闊蒼茫的西北邊域,變幻無窮的四時風光,獨具特色的民情風物以及俗世中熱鬧喧囂的日常生活成為張好好的寫作富礦。她的兩部長篇小說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到當下時代的歷史為經,分屬老少兩代家庭生活為緯,夾雜周圍的種種人事糾葛與個人心史,編織出帶有濃郁抒情風格的自傳體敘事詩。
“從20年代的鄉土文學到80年代的尋根文學,從延安文藝到懷鄉文學,現代文學的主流總召喚著原鄉情結。掩映在這原鄉情結之下的,則是國家政治的魅影。感時或是憂國,鄉土曾經幻化成各種面貌,投射文人政客的執念。”在張好好的長篇小說《布爾津光譜》和《禾木》中,作家深情地回眸故鄉血地,在濃烈的原鄉情結影響下,探究流民創痕與男女情愁。在時間與空間的灰燼中,作家挖掘往昔歲月的斷壁殘垣,進而剖析人性肌理,追問存在真諦。經由她的童年經驗和對心靈世界的探幽尋微,已被美化的與不該記取的,荒涼的與溫熱的,隱秘的與張揚的,生的歡欣與死的寂滅,繁復而有序地浮出時間的地表。
一、 西域邊地的時間簡史
“混沌未開,就是我們的童年,樸素的衣著,勤勞的家務勞作,分享辛勞的手工業勞動者的父親和母親的快樂和憂傷。生活的重擔,也壓迫在我們小小的心靈上。然而,歡快總是很多。放聲大笑,深夜里去到院子里看滿天的星星,覺出天地的闊大和神秘幽邃,和小動物們一起長大,心里涌動著純凈的愛,那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素養。”西北邊地小城的童年生活,牽引著張好好的心緒和思索,這也注定她的文學作品會沉溺于兒童記憶。兒童用純真的、尚未被世俗教化的眼睛打量世間的一切。西域邊地的自然風光和民情風俗成為她的情感皈依與寫作母題,在其不同的年齡段和創作時期,小說的主旨和情感基調雖然呈現出不同的書寫維度與精神旨歸,但童年經驗作為生活原型和重要題材在其創作中的重要性顯然是不可忽視的。動物的靈性,流民的歷史,世事的變遷,少年的成長記憶,交織在一起。憑借作家對日常生活綿密而扎實的現實主義書寫,讀者得以窺見西域邊地小城中一代人的成長歲月及他們心靈中所潛藏的精神譜系。
在長篇小說《布爾津光譜》里,張好好匠心獨運地借用了尚未出生即因計劃生育政策而被墮胎的爽冬的視角書寫布爾津小城里海生一家的日常生活。作者讓這個死去的、五個月大的胎兒以及小說中的大灰貓成為整個家族式生活史的參與者和解讀者。作為一個被剝奪出生權的魂靈,爽冬理解父母的苦衷,沒有滿懷恨意地評判人類,而是用善意和溫柔的態度對待世間的一切。他像一個自由的精靈,來往穿梭于家庭和布爾津的廣闊原野里,在他的認知系統中,認為“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地方能夠比布爾津更美了”,而父親海生、母親小鳳仙和三個姐姐組成的家庭也是幸福和美的。雖然他知道他的父母和許多人一樣都是異鄉人,是攜帶著各自的血色歷史逃亡到布爾津小城中的不幸的人,但只要他們落腳到布爾津,就可以被博大寬容的邊地小城接納并過上溫馨美好的日子——“海生決定周日一早趕去六道灣給小鳳仙帶些吃食。六點天剛亮出白薔薇的顏色他就起來了。在院角的小廚房里,他把頭天晚上炒好的羊肉、咸菜盛到大玻璃罐頭瓶里。又去地里摘頂著花的黃瓜,西紅柿發出蜇人的清香,豆角正壯大,已漸白。小鳳仙離不開辣椒,地里的尖椒打著螺絲卷,半紅艷著,海生多擰了些下來。這些夠小鳳仙她們吃一星期。”這些被主流社會和中原大地所棄置的失敗者在布爾津小城中默默地翻開生命的嶄新樂章,在一種穩妥、寧靜、親近自然中生兒育女,扎根邊城。曾經的傷痛歷史雖然給每個生命個體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現世生活的堅韌性和恒常性更具當下性與吸引力。生存在這里的人們將苦難稀釋,將為了活下去而艱辛的繁重勞作看成理所必然。他們最高的生活理想便是能夠吃飽穿暖與平安度日。在爽冬稚嫩拙樸的目光中,布爾津小城猶如世外桃源般美麗,人與人,人與大自然,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諧圓滿。
然而在張好好的另一部長篇小說《禾木》中,爽冬眼中的世外桃源遭到了無情的拆解。這部小說不再講述嬰兒眼中的小城民眾生活史,而是以一個睿智小說家的痛徹之思,把“講故事的人”換成了一個歷盡滄桑、成熟穩重的中年女性,讓她作為內地與邊地世界的體悟者和闡釋者,給古老的、日漸敗壞的西域邊地及當代中國的城鎮化發展歷程做一恰切的注腳。小說中的“你”和“你”的故鄉面臨的是“一個敗壞的時代就這樣到來了。清新的小城敗壞起來,不亞于中原大地漚爛的加速度。所以,別假想烏托邦的存在,你不迷信故鄉”。愛和美突然變成怨與丑,爽冬眼中和睦恩愛的夫妻,早已由天作之合轉換成天作之禍。在《禾木》中,關愛妻子、勤勞忠懇的木匠海生變得庸弱卑微,他“下海”后的小包工頭的事業屢遭失敗的打擊,而在遠離家庭、苦悶憂郁的情況下,他的生命中出現了另一個女人娜仁花。父親與娜仁花在禾木中相戀并生下了私生子,他們的越軌行為令曾經溫柔體貼的小鳳仙轉變成一個頭發花白、動輒怒氣沖天的怨婦和悍婦。相濡以沫的夫妻漸漸水火不容起來。與此同時,隨著商業浪潮的涌動推進,邊地小城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天、地、人偕順的關系不復存在。人被欲望和貪婪所掌控,潔凈高蹈的精神被踐踏,人類與飛禽走獸及草木山川建立起來的類似于親情般密切的情緣消逝無痕。邊地中的每一個人或主動或被動地卷入到急遽變化的潮流中,他們在驚慌失措中追趕著時代的步伐。為了追逐金錢實利,他們甚至不惜將自己的良知囚禁在牢籠中,在醉生夢死中渾渾噩噩地度日。
由此可見,張好好的長篇小說《禾木》承繼了19世紀以來寫實主義小說的正宗,下筆繁復而細膩。作家明白無誤地指出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其實早就四面楚歌。時代變換,不論內地的繁華都市,還是西部的遼闊邊地,原來都是如此令人失望和危機四伏——“人類進程的關鍵的一百年,文明到來得這樣迅疾,大地的腐爛來得太快了些。”作家憂懼甚至不乏憤慨地揭示出我們時代人心的朽腐,以及人類對大自然犯下的深重罪責。她用寓言般的文字提示讀者,只要我們不迷醉于日常生活,不回避良知的拷問,就能發現日常世界中令人驚心動魄的地方。
“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雖然張好好的兩部‘小長篇’存在著文化想象資源以及書寫原型等方面的共同性,但作家實際完成的這兩個文本之間,卻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誠然,《布爾津光譜》是作家回望故土家園,將童年記憶、家庭生活經過詩心和童心的調和,所建造起的烏托邦愿景,目的是在回望中達到情感撫慰功能和發現生活與存在的真諦。但隨后創作的《禾木》,則是長大成人的張好好通過自己的生活閱歷和深入省思后所描述的人類生活的“進化史”和對大自然的“掠奪史”。她更愿意用解剖刀般的目光去書寫日常生活的粗糲貧乏,普通民眾的倉皇貪婪,尤其是神性大地面臨的重重危機。由此,《布爾津光譜》中詩意、恬淡的敘述筆調與《禾木》呈現出的層層解剖、深入勘探的批判反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兩部小說一張一弛,呈現出繁復的思想與審美意蘊。
二、 市井人生的文學存照
在張好好的長篇小說書寫里,她在家長里短的講述中回到了偉大平庸的塵世,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為中心,力圖在文字中留住邊地小城在往昔歲月里的市井存照,更試圖在消費主義時代里記錄下邊地社會的發展史。在《布爾津光譜》和《禾木》中的市井社會里,作家除了講述飲食男女的塵世情緣外,還有對古今世道人心的洞悉與善解。在純凈通透的語言、簡潔深邃的對話和尋常故事的娓娓道來中,張好好“是要通過一個從故鄉走出去的女人的經歷和思索來寫人類發展史。人類發展史,多么宏大的主題!的確,就是如此宏大的主題”。作家和巴爾扎克一樣,意欲為我們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變遷提供一份可靠的記錄或證詞,并堅定地提出了對商業文明的質疑與憂懼。
立足于變化中的邊地小城,張好好在其長篇小說中精心建構了一個根植于中國人生活空間的市井世界。此市井空間既包括西域小城,當然也連接著迅疾發展的內陸城市,但她傾力塑造的人物大多為生活在西北邊地中的引車賣漿者——木匠海生、裁縫小鳳仙、燒飯的董師傅、做皮靴的林師傅、少年喪命的寶年、美麗癡情的梅、圖瓦女人娜仁花、哈薩克女教師、石灰窯的老楊、養蜂人老水、淘金子的戚老漢、磚廠老板……在張好好的文字中,她將普通小人物的吃喝拉撒、愛欲生死一一復現。這些立于人世的眾生,有的家世顯赫,命運多舛;有的操勞一生,悲苦謀生;有的為愛心傷,甘愿赴死;更多的則選擇隨波逐流,淡然度日。在這群處于社會結構中的小人物身上,作家不但為他們尋找到痛切的家史,而且察覺到平凡生命內蘊的傳奇,從而體悟并贊嘆人類生生不息的創世與滅世力量——在嚴峻混亂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卑屈卻又堅韌無畏地找尋生命存活的通途和心靈的慰藉,以堅韌、強悍甚或暴烈茍活于邊地;而在消費主義隆隆的車輪下,他們不惜拋棄人倫親情,以強盜般的罪惡行徑掠奪大自然的一切,彰顯出人類在現實主義律令下的殘暴與無情。
當然,這些市井小民的堅韌和殘暴都有其情非得已的前因后果。在一段特殊的歷史歲月中,不管是生活在布爾津這座小縣城,還是散落在禾木褶皺中求生的他們,都既是灰暗歷史的親歷者,又是政治劫難的受害者。這些流民攜帶著各自的生離死別,深藏著失敗的精神傷痕,小心翼翼地度過余生的歲月。譬如小鳳仙和董師傅都在狂謬的時代中失去了親人和故鄉,生活逼迫著他們必須出走。即便已經落腳在西域小城,這些曾經的政治受難者依然要在擔驚受怕中辛苦度日:“從前海生在家里悄悄做桌子板凳,也是要在單位里開小型批斗會的。小鳳仙在院子里種的小白菜,被紅小兵全部揪扯出去,扔在地壟邊被太陽曬蔫,她卻不能靠近把它們栽回土里。這些事情真像一場大夢啊。當時甚至以為是要捉去槍斃的。”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世界密切相連,歷史的夢魘依然在當代人的生活中重復流淌。“這些小說中的人物都被困在一張休戚與共的大網之中,動彈不得。他們是社會和歷史的產物——它們的威力遠比個人強大,同時深受時勢的影響——對此他們僅有片段認知。”這群遠離故鄉的流民是一群嚇破了膽子的可憐人,日常生活稍有風吹草動,他們便風聲鶴唳起來,而內蘊在他們身上的溫柔與暴烈也就不難理解了。
說到底,因為人的存在,所以就要面對種種苦難,苦難才是人類歷史和生活的本質。在張好好的長篇小說中,她的市井世界里固然有質樸、美麗、溫情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譬如人們對青木失身于礦廠老板的事件所抱有的寬諒態度:“那個礦上的老板是個壞人,青木還年輕,現在遇到了好人家,我們都不要為難她。”在古風猶存的邊地小城,這樣的同情、仁慈和體恤并不鮮見。與此同時,張好好也沒有回避人世中那些破碎、粗陋、苦難甚至卑劣的存在狀態。作家直面市井人生苦澀艱難而又藏污納垢的本然狀貌,與詩意的遠景回眸相較,后者顯然更為真實與復雜。
在《布爾津光譜》和《禾木》中,最觸動讀者心懷的恐怕就是個體生命的泯滅與消失。那些曾經鮮活的生命,在命運的劫難與生存的艱難面前,如塵埃落地般悄無聲息地選擇了死亡。例如美麗癡情的梅在未婚先孕又慘遭拋棄的情況下服毒自殺;不堪忍受生活重負的窯工老楊在妻子瘋癲、兒子眾多的境況下的上吊而死;還有患小兒麻痹癥的少年在家人的嫌棄調笑下決絕地跳入額爾齊斯河的溺亡。除了這些為愛,為尊嚴,為親情的失掉而主動赴死的人之外,更多的,則是被動而意外地遭遇死亡。如哈薩克女教師的女兒,待嫁的未婚新娘,戲水淹死的寶年……死亡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出現并重復上演。活著的人,盡管會悲痛哀悼,為逝去的親人痛哭流涕,但過不了多久,一切又會重回正軌,人們仍然一如往常般生活。這是生命的悲哀,也是生活的常情。顯然,張好好在其小說中觸及了人類死亡的沉重命題,但“沉重”沒有使她的作品變得笨拙、滯澀,憑借語言和形式的詩意捏合,她舉重若輕而又聰慧靈敏地述說了生的歡欣與死的悲哀。
值得注意的是,在張好好的思維視閾中,人類社會的世俗生活是不能沒有動物和植物存在的。在西域邊地長大的張好好實際是大自然的女兒,一望無際的草原與沙漠,咆哮奔騰的額爾齊斯河,大雪皚皚而又狂風呼嘯的原野,以及大灰貓、黃毛大狗、億萬只草蟲伴隨著她長大。現在,當這一切日益遠去之時,她將這些挪移在文字里。作家對大自然的情感,或者說她寄托在大自然身上的情感,有如血緣親情般的密切關系。在生態惡化、原野枯萎的當代,甚少有像張好好這般具有強烈的鄉野情結和動物情結的作家。在她眼里,大自然中的一切都絕非如它們的外表那么簡單,她對大自然的了解超出了常人的維度,那只在《布爾津光譜》中通靈的大灰貓代表著某種力量或能量——非人的、外來的、他者的、智慧的。它和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古老優美世界的一部分,是極富魅力而可珍惜的生命。只不過,被利欲蒙蔽了身心的現代人類難以切近和理解世界的本真。
“中國傳統文化,雖是以人文精神為中心,但其終極理想,則尚有一‘天人合一’之境界。此一境界,乃可于個人之道德修養中達成之,乃可解脫于家、國、天下之種種牽制束縛而達成之。個人能達此境界,則此個人已超脫于人群之固有境界,而上升到‘宇宙’境界,或‘神’的境界、‘天’的境界中。”張好好以個人的立場,深入西部邊地的世俗人生,探察生命的秘密,揭示人類與大自然共同的命運。對幽微人性的剖析,對生命終極價值的關懷,對世間萬物無差別的愛與痛惜構成了其作品的深邃與迷人。
三、 心靈世界的審判與救贖
在張好好的小說創作中,西北邊地的布爾津和禾木,不僅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而且是一片承載潔凈精神的心靈疆域。在她看來,唯有潔凈的事物和靈魂才是值得用心書寫的。為了充分地達到這一寫作目標,張好好有意采取了一種具有先鋒色彩的、類似復調小說的敘事方式。在她的兩部長篇小說里,作者給讀者展示了心靈世界的闊大和幽深——靈魂的沖突,思想的對抗,責任的困境以及人性的懺悔。小說中那種無處不在的自我追問,既詩意充盈,又充滿心靈的冒險。某種程度上說,張好好的作品都是關于個人心史的剖白與追問。作家通過對內心世界的勘探,重新理解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并試圖在破敗的現世圖景中用“潔凈”的力量來慰安心靈和救贖世界。
為此,她動情地宣稱:“人人逐利那是危險的,是萬劫不復的。我必須解剖,我的,父親的,母親的,我必須公正,不得掩藏那罪與罰。”罪與罰,善與惡,人類復雜而幽深的內心世界是她小說的真正“主人公”。這樣的敘事自然是危險而有難度的,它的哲理性、對話性、超驗性并不符合多數讀者的閱讀習慣。但同時,這也恰恰是張好好小說敘事的特異和迷人之處,是她從事文學這種職業的初心與信仰。
在《布爾津光譜》與《禾木》中的蕓蕓眾生里,生活著許多有罪的人。在或長或短的人生歷程中,他們一面犯下種種錯誤,一面又通過懺悔或自省來自證其罪,在自我譴責中尋求內心的安寧。典型的便是《禾木》中的父親和離開故鄉的“你”。當年的父親因為欲望和沖動而背叛了母親與家庭。作為丈夫,他是不忠的;作為父親,他是缺席的;作為情人,他是庸弱的。如果用世俗的眼光和倫理道德來衡量,父親無疑是被譴責和被鄙棄的人物。但是,作家并沒有如此簡單粗暴地對待這一人物,而是在理解中寫出了父親在情感與責任的“悲劇性兩難”中進退失據的可悲可憫。正因為父親想成為世俗意義上的“好人”,想擔負起他的責任,所以他才在沖突中猶疑而自責。主觀上,他竭盡全力地想保全兩個家庭、兩份情感以及他的兒女們。但客觀上,他的這一想法無疑是幼稚和不可能達成的。罪與罰,善與惡,如此的錯綜糾結。為此,他沉默、自苦地活著,以心靈的受難來減輕俗世的罪責,緩釋現實的苦痛。
而那個無處不在的“你”,也在清醒地審判著人類和自身所犯下的丑與罪,并時時在辯論與懺悔中呈現自我靈魂的黑暗和不堪。從孩童時代的懵懂,到人到中年的滄桑,從邊疆小城到中原大地,文本中的“你”經過自我審判和不止息的思索,意識到人類對大自然的殘暴和無止境的貪婪索取。雖然“你”用有限的力量阻止著暴行的發生,將即將被殺戮的動物重新放生,可同時“你”也清醒地知道,“你”是人類中的一員,“你”的救助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在人心堅硬、罪感麻木的時代,“你”的言行舉止被大多數人指認為潑婦和瘋子的行徑,而背后的偽善和機巧也令他們厭惡。當然,除了犀利地揭示他人之罪,“你”也毫不留情地解剖自我之罪。在此,張好好勇敢而誠摯地回到了內心,通過審視與自省,看到自我靈魂的殘缺——“你”為了追求世俗的成功,也曾受“誘惑”的引誘而遭受屈辱;“你”遠走高飛,不停奔波,沒有陪伴女兒的成長歲月,更不是一個合格的母親;而“你”作為父母的女兒,也沒能走入他們的內心,更沒有給他們足夠的理解與憐惜。
直到若干年后,“你”通過對每一個鮮活生命的深切的體恤、耐心的思忖和慈悲的打量,才能穿越淺表的事象,觸摸到冰山下隱藏的全部秘密,并最終確信只有“對美和善的信仰,對大自然的感恩,能夠挽回這大地和江湖潰爛的局面”。“你”理解了父親、母親、娜仁花以及一切掙扎在道德倫理與個人幸福困境中的弱小人類;“你”溫柔敦厚地愛著大自然的山川草木,憐愛生靈的堅毅和無欲;“你”真實而勇敢地表達了此時此地人心與存在的朽腐,毫不隱瞞地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和疏離。但同時,“你”對世界依然保留著信心與希望,確信良知和潔凈的力量。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張好好的寫作由自我到人心進而到更廣闊的世情與天道的精神縱深。作家不避卑微而幽暗的人性,更滿懷對人類的溫柔惜重。在《布爾津光譜》和《禾木》中,張好好潛入心靈世界開辟文學的廣闊疆域,寫出了西域邊地的靈魂,清晰地確立了屬于自己的寫作向度:向美向善,善愛天下弱小,潔凈而自尊地活著。


注釋
:①王德威:《如此繁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頁。
②張好好:《潛心寫作,讓生活慢下來》,《中華讀書報》2017年4月19日。
③張好好:《布爾津光譜》,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頁。
④張好好:《禾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頁。
⑤張好好:《禾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
⑥王春林:《以“罪與罰”為中心的箴言式寫作——關于張好好長篇小說〈禾木〉兼及“小長篇”的一種思考》,《當代文壇》2017年第2期。
⑦賀紹俊:《為了潔凈,一起出發(代序)》,《禾木》,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
⑧張好好:《布爾津光譜》,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頁。
⑨特里·伊格爾頓著,范浩譯:《文學閱讀指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頁。
⑩錢穆:《民族與文化》,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