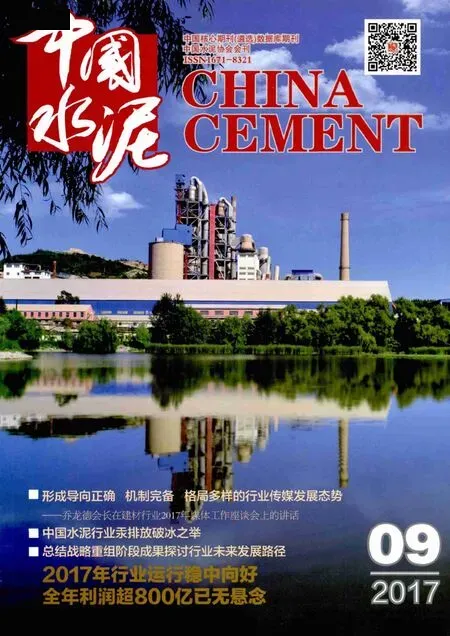水 泥
苗見旭

我第一次見到水泥的時候,還不知道“水泥”這個名字。
父親從鎮上回家,見人就問,你見過“洋灰”嗎?眾人一律現出艷羨,一律低了頭注視父親捧著的東西。這東西粉粉的、細細的,像鋼磨磨的綠豆面。有人干脆捏一點放進嘴里,骨碌著眼睛咂摸,立刻“呸呸”吐掉。“我當成雜面了,你咋倒人呢?”“誰倒你了,這是石頭面兒,不是糧食面兒。”父親得意并戲謔道。
其實,它比糧食面主貴多了,父親一路敬仰地捧著,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找籮。
我家院子西北角有一棵大槐樹,平日里,全家都在下面吃飯,一天,母親說,多時壘一平展臺面,省得木桌搬來搬去的。母親的話像圣旨,父親立馬就用殘磚碎瓦砌了臺面。臺面砌成,敷了一層黃泥,黃泥之上又施一層白灰,接下來,這一捧水泥就派上用場了。他用籮均勻地篩;一手端籮,一手震動籮框,水泥就灰雪一般灑在白灰上。及至用瓷片打磨幾遍,臺面就鏡子一樣光亮起來,我斜了眼睛去看,真就看見了槐樹的枝葉,枝葉間陽光的亮斑以及母親笑成一朵花的臉。
父親的水泥來自鎮上修架的三級提灌,父親是第一批選出的土木工程師,負責民工的筑建工作。
所謂民工,就是由公社從各個生產隊抽調的青壯年農民,吃住在工地。一個禮拜回家一次。剛開始抽調了一百多個壯年勞力。幾天下來,全部蔫了,無精打采。父親著急起來,一位年長的民工說話了,“嗨!弄幾個娘兒們過來,立馬就活泛了。俗話說,男女混雜,勞動解乏嘛。”
三天以后,勞動工地上紅旗招展,大閨女、小媳婦的加盟使勞動的陣營熱火朝天,人們說著、笑著、唱著,又見縫插針地打著諢,整個工地洋溢在大干社會主義的熱潮里。
公社書記坐著東方紅拖拉機來了,他穿著白襯衣,綠褲子,站在拖拉機的拖車上,叉著腰大聲說話。“老少爺們,大家辛苦了,你們知道車上拉的是什么嗎?這是高標號的水泥,無梁產的最好的水泥,縣上特批的,比咱燒的石灰強多了,誰不信舀碗水攪和一點試試。”
書記的話應驗了,下午的地基澆灌,這高標號的水泥真就發揮了威力。民工們把水泥和沙子按比例拌勻,然后澆水,立時,嗞嗞的聲音就拌著水泡響起來,民工們瞪眼、噤聲注視著這奇異的現象。就像三伏天,你向干裂的大地潑出一瓢水,“哧喇”一聲,水就不見了......
四十年后,站在提灌堅如鋼鐵的基座前,我就想,這是我最初見到過的原生態的焦渴。這焦渴是水泥對水的渴望的展現,或者說是水對水泥的心悅誠服、死心踏地的皈依。這是陰陽交和的典范,是先“和諧”而后產生凝聚的真理。
再后來,讀于謙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才知道石灰的精神以及水泥的前身就是石灰這些知識。是呀!千百年以來,石灰一直就是優良的建筑材料,外國也有石灰石,他們也燒石灰,也約定俗成地用石灰建筑各種雄偉的宮殿,可為什么用著用著就改成水泥了呢?查過典籍才明白,石灰在古時候的優點到了現代就演化成缺點,比如,凝結慢,凝結強度達不到現代建筑標準。也就是說它先天還不完美,還有不足,科學家就是花了氣力在石灰優良品質的基礎上又添加了活性的元素,使石灰搖身成為水泥,完成了自身的蛻變和升華。

由此,我想,一個人天生我材必有用。而這材又不是天生完美,它需要后天的學習和完善,就像石灰需要添加新的活力元素。而當自身修得完美之時,一旦機遇來臨,事業便如夏花之絢爛。
同樣的道理,一個家庭,夫妻雙方,互相比照,取長補短,久之,相貌也會趨于相似,萬事不就興盛了嗎?唉!這小小的家庭也有水泥“交融”的影子!
還是《圣經》說得好,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無論是水遇到了泥,或者是泥遇到了水,結果都是泥中有水,水中有泥,都是陰陽聚成的福氣。
“水泥”呀,誰起的名字,簡明的文字,深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