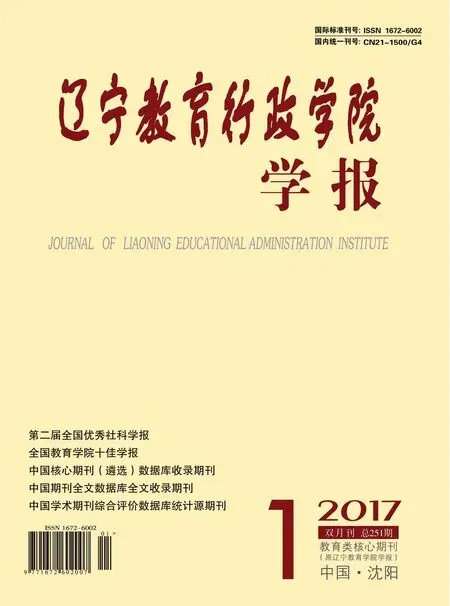在高揚與沉潛中徘徊
——論《塵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
王寧娜
沈陽音樂學院,遼寧沈陽 110034
在高揚與沉潛中徘徊
——論《塵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
王寧娜
沈陽音樂學院,遼寧沈陽 110034
《塵埃落定》作為藏族作家阿來的代表作,它根植于藏族的民族性與地域性,以詩意靈動的詩歌語言與寄寓深刻的內蘊主旨傳達出作家內在的文學向度。通過對小說中權利凌駕下的鬼魅形象、凌空高蹈的美艷形象、奴性外化下的卑微者形象加以深度解讀,可從中探知作品中潛藏著作家對男權主義的高揚以及對女權主義的沉潛,女性形象的背后是居于一種被男權所壓抑與遮蔽的幽暗狀態。
塵埃落定;女性形象;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阿來的《塵埃落定》以藏族作家所攜有的民族地域文化特征,通過小說這一文學視角,以魔幻般的色彩暈染了藝術的張力。文本中的語言自然輕巧,內蘊深刻豐厚,再一次將詩歌的藝術特征融匯于文本之中,從而獲得一種詩性的靈動美感。此部小說所敘寫的是發生于中國邊陲之地藏民群體間的生命歷程。小說所呈現出作者對藏族文化內在的敬仰與追慕,也詮釋著作家本人對自然淳樸生活的再度審視。文本并非單純地囿于小說的藝術特征,而是沖破慣常化的藝術傳達方式,將詩情畫意融匯于寫景狀物之中,以此凝構起詩意般的審美體驗。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角度觀之,作品中潛藏著作家對男權主義的高揚以及對女權主義的沉潛。本文將從如下幾大方面進行細致闡釋。
一、權利凌駕下的鬼魅形象
依憑權利得以重生的女性以無度的控制欲呈現個人的生活樣態。米歇爾·福柯認為:“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作在這個網上,個人不僅流動著,而且他們總是既處于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權力。”[1](P161)古往今來,每一個個體雖然有其自身生命的獨立性與自由性,但是個體均身處于一定的空間范圍之內,有其地域的限制,這不得不致使其處于一種交錯龐雜的權利關系網之中,而在雙向運動中,個體既可成為權利的執掌者得以實施權利,又可轉化為被權利所指使的角色。從《塵埃落定》之中,文本接受者便可從中探知女性主體身處于權利的漩渦之中,既有權利的既得利益者,又有受其蹂躪迫害的卑微者,兩相之間的互動以此融構成獨特的女性形象。
小說中最先出場的女性人物即為小說的主角二少爺傻子的生母。作為土司的夫人,尤其是深居于幽閉之處的邊地,身份意識對于封建的女性而言尤具重要。她出身卑微,源自妓女之身,此后下嫁于土司門下便轉換成為高貴之身。對于久居卑賤低位的女性而言,身份的瞬息轉變成為了炫耀的資本,深藏于心靈深處對權利的覬覦之心得以瞬間的滿足,由此便是人性罪惡的滋長蔓延。她每日清晨便用溫和稠密的牛奶浸潤那雙修長白凈的雙手,而又常以喘息之聲預示著自身的嬌貴,這全然是一種嬌嬈造作、貪圖安逸的貴族女性形象。土司夫人的尊貴身份使其尊享舒適安逸的生活境遇尚可理解,但是面對眾人,她內心深處的陰險與惡毒卻得到了全然的外露與張揚。當一個管家說一個因饑餓而從山中尋事而來的女麻風病人誤入虜獲野豬的陷阱之時,她竟然毫無任何的悲憫博愛之心,竟向下人吩咐“那還不趕緊埋了”,言語之間充盈著一種凌人之氣。這一絕情的話語下顯露出她內心的陰郁,也顯示出貴族女性內心的那種驕縱與恣肆。
在權利的托舉中,女性也以清寂孤冷訴說著自身的悵惘與哀愁。土司夫人雖然執掌著權利,常常以權利之名凌駕于眾人之上,致使他人無法得以喘息。她在他人眼中似有萬般的嬌貴與獲得物欲的自由,但是女性之為女性,其精神的幽微之處始終潛藏著人的原初本性。她原為漢人,而今存續于邊藏地區,雖然生活富貴,但是內心世界的孤寂與惆悵依然難以遮掩。地域的遙遠與習俗的陌生,致使土司夫人在獨身一人之時更顯凄清哀婉,內心始終依伴著思鄉的愁緒,盛氣凌人與驕縱恣肆的態勢將他人拒于千里,無法消解的孤寂感在土司夫人的生活境遇中得以凸顯。阿來在對權利女性人物的書寫之中并非疏離于人性的內在真實,以外在的縱橫恣肆同內在的柔弱清冷得以交融,將女性人物的塑造居于一種真實化的顯性狀態。作家在塑造權利執掌下的女性形象中,始終未曾隔絕“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在兩者間探尋到微妙的平衡支點,以此致使閱讀主體既有藝術的審美體驗又有現實的真實探觸。
土司夫人的形象是作家承繼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形象模式進行外化塑造。在中國古往今來的藝術作品中,對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大致可梳理出兩類:一類是傳統典型的光輝形象,可將其視作為“圣母”“女神”。她們的言行之間始終充盈著真善美,她們是男性主體始終追慕和渴求的首選對象,她們承載著道德文化所賦予她們的符號化象征。如穆桂英、花木蘭、文成公主、孟姜女等人物形象。另一種相對而立的對象則為帶有典型性對立反叛色彩的“蕩婦”“惡女”形象。此種人物形象典型地呈現于《水滸傳》中背棄忠貞的潘金蓮、潑辣兇悍的孫二娘等。無論是古典小說作品,亦或是現當代的小說之中,我們均可體察到文本中所涌現出的女性形象均是依存于以上兩種形象類別之中。無論是何種人物居于其中,文本作者均無法脫離慣常化的創作圍地,從而深陷其中無法躍出。此種創制方式雖然在一定層面上顯示了女性某一顯性的個人特征,但是人性并非恒久地孤存于某一方面而毫無變化的跡象。這一創制方式對于阿來而言,有其優劣所在,然而無論作家如何得以轉化敘述的模式,都是對女性人物形象的一種扭曲。阿來在對土司夫人進行形象塑造的過程中,雖然將其人性中的本真,將生活的一種真實性,也即為她因身處西藏邊陲而身心孤寂的一個側面得以外化呈現,但是依然無法遮掩作家對土司夫人罪惡性的直接表達。
在土司夫人的形象之下,是一種男權色彩的暗自呈顯,是游走于喧囂與沉寂之間的矛盾之體。雖然在作品中為了個性化人物形象塑造的迫切之需,需要對某一人物加以集中性的熔鑄,但是這一形式反而在作品中凸顯了男權色彩的濃重意味,在交織的情節敘述中顯性或沉潛著作家本人所持有的男性中心主義。文中的土司夫人,雖然并未身處土司之位,但是她以一種土司所特有的強權之勢欺凌眾人。這一創制方式足以體現土司夫人依然以持有的傲人之態呈示自身的強大。而這一慣常化的創作模式,也在同時代的作家創制譜系中依稀可見,作家在對強勢女性的描摹同男性形象存有相似性,始終無法消磨其深意的存在。似乎也預示著在男性作家的筆觸之下,有著難以改變的角色身份意識,也昭示著女性人物在當下時代的環境中依然有其尷尬的身份處境。
二、凌空高蹈的美艷形象
小說創作中始終無法缺席智慧的化身或嬌媚動人的女性形象。土司的女兒塔娜是《塵埃落定》中最為嬌美的女性人物。她的形象塑造傾注了作家內在的創制理想,以外顯與內隱的創制線索得以呈現。通過這兩條線索的分布排列,可從中抽離出此種人物形象所內蘊著的特定內涵,以此探視出作家本人對女性角色的個體化向度。
塔娜以明示的態度宣告自身對土司兒子傻子的無視。小說中多次以語言描寫的方式從側面映襯出塔娜那驚艷眾人的容貌之態,例如,傻子“我”看到騎駕于馬背之上的塔娜掀起她那神秘的頭巾時,“我”所展現出的失態之狀,以及管家的耳語“少爺,看吧,這個女人不叫男人百倍地聰明,就要把男人徹底變傻”。[2](P152)通過語言的直接呈示,便將塔娜如若天降圣女般的嬌媚得以直觀化展現。然而,命運總是在未知中得以逆轉,她的生母茸貢土司因為受到饑饉的生存困境,而將女兒的生活空間得以壓縮置換,以個體的幸福換取了物質的滿足,致使女兒在脅迫中下嫁于傻子“我”。作品所呈現的又是一個百年來始終未曾消逝的母題,貴族女子的婚姻之事始終無法逃脫封建禮教的內在規制,婚姻成為了女性走向絕望與苦痛的一條必經之路。
女性總在嬌媚的背后潛隱著命運的悲愴,此類創制手法總是在得以或顯或隱地重現。通過深入探及敘事的內在構造模式,欣賞主體依然可以從中探觸到女性作為世界中被遮蔽的客體,她在主體與附屬,凌駕與壓迫,高揚與貶低中始終居于低位,而這一卑微的身份在本文得以全然的展現。究其深因,根源依然在于“權利”圈的范域之內,女性似乎深居圈內,以其個體的內在存現而體現權利圈的價值。同時,女性似乎又身處域外,以無法自我言說的窘迫處境再一次勾勒出女性圍地的狹窄窘境。塔娜的形象就像一塊進退難堪的磁石,雖然作為茸貢土司的女兒擁有公主的高貴身份,但是在家族利益之前,她卻被斷然地拒之于磁圈之外。從中觀之,女性的身份意識并非掌控于自我的意志觀念之中,而是始終委身于特定的境遇之中。她無法加以真正的反抗,她只有選擇內在的靜默與沉潛,她不能直接拒斥家人的婚約而選擇逃避,他也無法在婚內選擇果決的離異之法,對她而言,她始終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
形象的背后是對女性非理性的神化與美化。阿來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一類是擁有絕佳外在形象的美艷女性形象,另一類則是內心陰惡的丑陋形象。這一二元對立的形象的塑造下,形成了作家對女性獨斷化、非理性化的創作理念。尤其是所塑造的純情、美艷的女性人物形象,這類人物形象在作家的筆觸之中居于一種神化的定位,似乎以一種刻意抬高的創制策略,加以構筑人物類型化的特征。看似高揚抬升的背后,卻始終潛藏著一種貶低壓制的內在考量。作家應用此類創制的方式,可將其視之為“實際上一邊將男性審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邊卻剝奪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們降低為男性的犧牲品”。[3](P347)塔娜即為典型的創設形象,雖然作家在文本中將塔娜充滿魅惑感的形象得以高揚之后,又將其內心的人性欲望得以外化,似乎以一種人性的真實維度作為創制的旨歸,但是依然無法脫離女性貶低壓抑為男性的附屬品的地位,女性依然無法崛起抗爭于男權社會的強大勢力,她的力量在男權世界中最終得以銷聲匿跡。
從中觀之,塔娜的人物形象是對人性欲求的極度張揚,是對個體需求的過度宣泄,同時也是對女性地位的沉潛。雖然人性的本真欲求是正常化的一種體現,但是阿來筆下的塔娜并非以理智與理性抗爭于傳統的規約之下,她以一種婚內背叛,違背婦道的形式得以反抗。塔娜的絕情背叛并不是基于對傳統規制的突圍,而是以滿足個體的欲求作為真正的旨歸。作家對塔娜的形象塑造并非是一種對女性自由的一種高揚,而依然是對女性角色的一種潛隱式扭曲。女性依然是一種動物式的存在,女性以一種獸性的特征得以存續于男權社會的野地之中,她的崛起反叛是在同時犧牲某種正常道德框架下的錯誤行為而獲得自身的自由,這依然是女性的悲哀。女性最終走向了一種沉潛,塔娜無力反抗家族的指令,無法在婚內以果決的形式加以婚變,沉默成為了她最終的選擇。
三、奴性外化下的卑微者形象
女性在封建時期往往以非自由人的身份得以存續,以一種依附式的生存模式得以延續。女性身份雖然在當下現代化的時代得到了極大的轉變,平等自由也成為了女性本應有的內在渴求,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居于一定的差異性,不對等性。但是大體而言,女性具有外在平等身份地位的實現性。女性在封建時期從始至終均處于一種二元對立的狀態,在男權社會之中,男性與女性構架起“中心”與“邊緣”、“主導”與“附屬”、“尊貴”與“卑微”的二元不對等。女性在傳統時期并非獨立性的個體,如若是官家夫人或是千金小姐等貴族女性,依然難以逃脫封建禮制的規約束縛。在其中生存的女性大多是居于一種卑微者的身份,甚至是奴隸的卑賤地位。魯迅先生就曾以簡明的話語涵蓋了兩個奴性的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文本之中,阿來創構了一系列深居奴隸身份的女性形象。例如,侍女桑吉卓瑪和土司的少爺“傻子”的奶娘德欽莫措即為典型的奴隸女性的代表。
侍女桑吉卓瑪以卑微低下與盛氣凌人的雙面姿態面對自身的對象。在文本中,卓瑪面對主人會降低自身的身份,她所真正奉獻給少爺的,也只是自己的肉體。而這一肉體并非出于一種被動和饋贈,而是作為奴隸所本應有的職責和義務。而在這肉體賦予的同時,卓瑪的內心是渴求少爺能將自己許配給心愛的郎君——曲扎。但是這一切卻是出于內心渺茫與無望的狀態,女性奴隸的命運始終處于一種飄忽不定的狀態,愛與被愛成為了無法自我決斷之事。雖然卓瑪的身份是卑微的,但是在卑微之下已然有自身對高位的希冀,而這奢望在面對相比自身更為卑下弱小的奴隸身上得到了全然的滿足。當面對傻子的兩個奴隸索朗澤郎和小爾依時,她因自身的穿著打扮更為精致些而時常展現出自傲的姿態,時常“以不曉得規矩的東西,敢在少爺面前坐著喝茶!去,到門邊站著喝去!”[2](P66)這一命令式的口吻面對索朗澤郎和小爾依,一種盛氣凌人、自恃清高的半主子姿態得以外顯。
奴隸女性的內在特征并非居于單面性,更多的是兩面性或多面性。此種判斷這也正契合魯迅先生對奴性的界定,“凡奴才總有兩面性,一方面對主子和有權有勢者奴性十足,另一方面對無權無勢者和不如自己的奴隸霸氣十足”。[4](P61)文本中的奴隸女性雖然身處低位,但是依然在伺機尋找可以獲得身份認同與滿足的機遇瞬間。她們身處奴隸的群體之中,卻無法用悲憫之感同情與自身共同處境的奴隸群體。她們用脅迫、鄙夷、無視的非理性行為對他者奴隸加以攻擊,這實屬人性的悲哀。魯迅亦對此番悲哀現狀加以直觀闡釋,他認為:“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著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并且不平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于這生活。”[5](P588)桑吉卓瑪的人物形象巧妙地貼合了魯迅先生所言奴隸的特性,并在當時的現實境遇中確乎存有此種個性特征。對于同處相同處境的女性奴隸而言,本應是同命相憐,以互愛互助的方式在悲戚的生活境遇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以此在不安局促的主仆關系中得以暫時地化解。但是人性的罪惡卻無法抵擋善意的召喚,最終迎來的將是更大的黑暗和迷茫。
簡言之,文本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她們始終在高揚與沉潛中左右搖擺。文本塑造了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同時在此類女性群體之中亦可探尋到漢族與藏族女性的多樣化形象特征。她們的個性富有張力,具有基于民族地域化與年齡層級化的顯性特征。她們自身以一種本能的欲求作為行動的旨歸,這是一種外化張揚的真實展現。但是,此類形象的塑造均出自于男性作家的筆觸之下,在男性話語的敘述描摹之下,依然無法疏離于男權主義的內在束縛。通過對女性典型形象進行癥狀化地闡釋,可從中觀出男權主義得以進一步高揚,而女性主義所宣揚的平等、自由則被無盡的淹沒。同時,通過對文本的探析,我們可探知藏區傳統女性的生命歷程、身份意識等諸多富有地域化的征象,亦可得以在男權話語的主宰下得以較為清晰地探觸到女性話語的微弱。
[1][法]福柯,著,嚴鋒,譯.權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阿來.塵埃落定[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3]朱立元.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4]魯迅.忽然想到:七[M].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魯迅.南腔北調集:漫與[M].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責任編輯:彭琳琳)
2016-12-15
I206.7
A
王寧娜(1980-),女,遼寧沈陽人,沈陽音樂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