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家”里的“人民”和“家”
——1930年代瑞典福利國(guó)家烏托邦的理想與實(shí)踐
閔 冬 潮
(上海大學(xué) 文學(xué)院,上海 200444)
“人民之家”的概念,在20世紀(jì)瑞典歷史和政治中占據(jù)著中心位置。甚至有人認(rèn)為,一提到瑞典的“人民之家”,就如同提到英國(guó)的“帝國(guó)”和法國(guó)的“共和”,其國(guó)家特點(diǎn)一目了然。[1]因此,要想搞清弄懂20世紀(jì)至今瑞典福利國(guó)家的歷史與現(xiàn)狀,“人民之家”是個(gè)關(guān)鍵詞。
提到“人民之家”就一定會(huì)想到其設(shè)計(jì)者——瑞典社民黨主席和首相的佩爾·阿爾賓·漢森 (Per Albin Hansson) 在1928年對(duì)“人民之家”期許的愿景:“在美好的家里,一個(gè)人不會(huì)看不起別人;沒(méi)有人會(huì)占便宜,也不會(huì)以強(qiáng)欺弱。在美好的家里,會(huì)發(fā)揚(yáng)平等、關(guān)愛(ài)、合作和互助。應(yīng)用到偉大的人民和公民之家,這就意味著要打破所有的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障礙,這些障礙將公民分成有特權(quán)的和被遺忘的、統(tǒng)治的和被統(tǒng)治的、富有的和貧窮的、有產(chǎn)的和貧寒的、掠奪的和被掠奪的。”[2]這段至今一再被人們引用的漢森關(guān)于“人民之家”的“語(yǔ)錄”,為我們提供了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利用“家”這一比喻來(lái)設(shè)想美好的社會(huì)和國(guó)家的烏托邦圖景。漢森所強(qiáng)調(diào)的美好之家,是以“平等、關(guān)愛(ài)、合作和互助”為特征的,不允許任何的特權(quán)和排斥。正是在這一烏托邦式的愿景下,自1930年代開(kāi)始,使瑞典走上建設(shè)福利國(guó)家之路。不錯(cuò),“人民之家”是一種烏托邦的比喻。然而,拿“人民之家”做個(gè)烏托邦的比喻是一回事,如何將這一理想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實(shí)現(xiàn)則是另一回事,特別是在1930年代。
1930年代是橫掃世界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大蕭條的時(shí)代,也是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的年代。當(dāng)前,全球性的經(jīng)濟(jì)政治危機(jī)不斷涌現(xiàn),極右翼的民粹主義在不斷冒頭,1930年代的幽靈在資本主義世界又出現(xiàn)了。*英國(guó)《衛(wèi)報(bào)》近來(lái)出了兩個(gè)關(guān)于1930年代經(jīng)濟(jì)大蕭條的特輯,見(jiàn)Guandian, 4, 11, March/2017。因此,重新追溯20世紀(jì)30年代瑞典“人民之家”草創(chuàng)階段的歷史,有了更緊迫和重要的意義。本文將把“人民之家”里的“人民”和“家”作為切入點(diǎn),試圖盤點(diǎn)如下問(wèn)題:為什么在1930年代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會(huì)提出建立“人民之家”?“人民”都包括哪些人?這個(gè)“美好之家”又是怎么回事?(由于篇幅的關(guān)系,本文特別關(guān)注“家”與住房的聯(lián)系)。由此探討瑞典福利制度起步階段的理念、特點(diǎn)和路徑。
為什么要建立“人民之家”?
直到19世紀(jì)末,瑞典還是個(gè)農(nóng)業(yè)國(guó)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nóng)村,從事農(nóng)、林、漁業(yè),是歐洲當(dāng)時(shí)最窮的國(guó)家之一。1867—1868年,瑞典農(nóng)業(yè)歉收,在史上被稱為“死亡之年”[3]。饑餓和貧窮引起了移民美國(guó)的浪潮,到20世紀(jì)初,五百萬(wàn)人口中有一百萬(wàn)人移民北美,電影《冰海沉船》底艙里的乘客十有八九都是移民美國(guó)的瑞典窮人。貧困引發(fā)的移民高潮,反過(guò)來(lái)又加劇了貧困和不平等等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問(wèn)題,迫使統(tǒng)治階級(jí)不得不建立《濟(jì)貧法》,救助那些失業(yè)者、殘疾人和貧困的老年人。
此時(shí),瑞典正處于向現(xiàn)代國(guó)家轉(zhuǎn)型的階段,前現(xiàn)代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與現(xiàn)代的工業(yè)化、城市化的矛盾帶來(lái)了各種激進(jìn)的群眾運(yùn)動(dòng)。在19世紀(jì)中后期,盡管全國(guó)性的大規(guī)模運(yùn)動(dòng)斗爭(zhēng)不多,但各地小規(guī)模的斗爭(zhēng)卻廣泛發(fā)展,各種社會(huì)主義、激進(jìn)主義、自由主義、無(wú)政府主義的思潮到處涌現(xiàn),為其后的農(nóng)民運(yùn)動(dòng)、勞工運(yùn)動(dòng)和社會(huì)主義運(yùn)動(dòng)埋下伏筆。
其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場(chǎng)農(nóng)民運(yùn)動(dòng)是19世紀(jì)60年代在瑞典南部發(fā)生的圖伯格運(yùn)動(dòng)(Tullberg Movement)。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以農(nóng)村無(wú)地貧民和租地農(nóng)民爭(zhēng)取土地權(quán)利為主,斗爭(zhēng)的目標(biāo)指向擁有土地的貴族階層。最后,這場(chǎng)歷時(shí)一年多,有成百上千人參加的斗爭(zhēng)在1869年以失敗而告終。[3]但運(yùn)動(dòng)對(duì)日益增長(zhǎng)的不平等制度的批評(píng)和反抗,對(duì)社會(huì)和政治權(quán)利的伸張,迫使政府建立有效的福利制度來(lái)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工作的權(quán)利。
1879年發(fā)生了第一次重要的工人大罷工,其后30年連續(xù)不斷。1880年之后,工人斗爭(zhēng)也風(fēng)起云涌。據(jù)歷史學(xué)家的分析,這一階段記錄在案的瑞典工人罷工運(yùn)動(dòng)在西歐歷史上數(shù)量最多。在1900至1913年,勞工沖突比世界其他地區(qū)都猛烈,暴力和開(kāi)火時(shí)有發(fā)生,直到1930年代后期才逐漸平息。[4]這與1930年代經(jīng)濟(jì)大蕭條后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的社會(huì)改革有直接關(guān)系。1930年代,全球性的大蕭條嚴(yán)重打擊了瑞典的經(jīng)濟(jì),失業(yè)率從1930年的12%快速攀升到1934年的34%。[4]到處都在裁員減薪,引起了持續(xù)不斷的罷工斗爭(zhēng)和社會(huì)動(dòng)蕩。例如,1931年5月,5位參加罷工斗爭(zhēng)的工人被軍隊(duì)開(kāi)槍射殺,這一事件直接引發(fā)了共產(chǎn)主義“蘇維埃共和”的建立(堅(jiān)持了兩個(gè)星期)和斯德哥爾摩以及其他地區(qū)大大小小的示威運(yùn)動(dòng)。[5]
這些暴力斗爭(zhēng)隨時(shí)會(huì)引發(fā)革命或者陷入法西斯主義的陷阱,甚至威脅到剛剛上臺(tái)的社會(huì)民主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畢竟,瑞典與1917年發(fā)生了十月革命的蘇聯(lián)只有一海之隔。而德國(guó)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大陸的膨脹,1930年代中期是法西斯主義最活躍的時(shí)期,瑞典法西斯組織的代表——瑞典民族社會(huì)主義黨(the Swedish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SNSP))的黨員已有3萬(wàn)人之巨。另一極右組織——瑞典民族聯(lián)盟(the Swedish National Federation (SNF))有成員4萬(wàn)人,該組織代表了反民主的極端民族主義。[6]這些組織在人口只有600多萬(wàn)的瑞典,也是個(gè)不小的勢(shì)力,對(duì)新上臺(tái)的社會(huì)民主黨形成了嚴(yán)重的威脅,迫使社會(huì)民主黨認(rèn)識(shí)到,如果不能解決持續(xù)增長(zhǎng)的失業(yè)和社會(huì)貧困等問(wèn)題,遲早會(huì)為法西斯主義的壯大提供生長(zhǎng)的土壤。
在這種經(jīng)濟(jì)政治危機(jī)四伏的狀況下,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構(gòu)想。而討論人民之家的問(wèn)題必然先得從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說(shuō)起。
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成立于1889年,很快成為瑞典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該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dǎo)思想,與工會(huì)聯(lián)系密切,比如,所有工會(huì)成員都自動(dòng)成為社會(huì)民主黨的黨員。甚至有種說(shuō)法,瑞典工人運(yùn)動(dòng)具有政治(社會(huì)民主黨)和工會(huì)兩翼。[7]然而,這樣一個(gè)以工人階級(jí)利益為重的政黨,在20世紀(jì)30年代成為執(zhí)政黨之后卻出現(xiàn)了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大轉(zhuǎn)變,將原來(lái)聚焦于一個(gè)階級(jí)的利益擴(kuò)大為關(guān)注國(guó)家整合,并且選擇了一條介于社會(huì)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這一提法首先來(lái)自于美國(guó)作家Marquis Child的著作The Middle Way, London: Faber, 1936.
關(guān)于中間道路的選擇,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內(nèi)部也是意見(jiàn)分歧,但大致來(lái)看,這條道路可以說(shuō)是社會(huì)主義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自由主義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再摻進(jìn)一些適量的凱恩斯主義的“新經(jīng)濟(jì)政策”。[7]對(duì)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來(lái)說(shuō),社會(huì)主義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不是新發(fā)明,1930年代之前就已經(jīng)開(kāi)始了這方面的計(jì)劃;而自由主義也一直在瑞典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占主導(dǎo)地位,同時(shí)也是保守黨一貫攻擊社會(huì)民主黨的利器。1928年,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在大選中失敗,痛定思痛,引進(jìn)了凱恩斯的“新經(jīng)濟(jì)政策”,大力進(jìn)行改革,這才使該黨走出了意識(shí)形態(tài)的死胡同。正是在這種形勢(shì)之下,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提出了建立“人民之家”的主張,為瑞典福利國(guó)家的建立描畫(huà)了藍(lán)圖并奠定了基礎(chǔ)。
“人民之家”中的“人民”包括誰(shuí)?
1930年代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贏得大選之后,其社會(huì)改革的焦點(diǎn)由工人階級(jí)轉(zhuǎn)變?yōu)椤叭嗣瘛保@一意識(shí)形態(tài)和政治實(shí)踐的轉(zhuǎn)變?yōu)槠溱A得長(zhǎng)達(dá)40年之久的執(zhí)政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一點(diǎn)已成為大家公認(rèn)的歷史事實(shí)。
回到19世紀(jì)末至20世紀(jì)初瑞典的語(yǔ)境中,“人民”的概念,表示人口或是與精英對(duì)立的階層(有點(diǎn)像我們所說(shuō)的‘群眾’)。各個(gè)黨派為了爭(zhēng)得更多的選票,紛紛打出“人民”這張牌,除了社會(huì)民主黨一家,保守黨、自由黨、農(nóng)民黨等都拿“人民”說(shuō)事,爭(zhēng)先恐后地自稱代表人民。隨著社會(huì)民主黨在選舉中的勝利,1934年以自由黨為背景的“人民黨”也應(yīng)運(yùn)而生。[8]當(dāng)然,這些黨派所說(shuō)的“人民”內(nèi)涵也是五花八門,是否真拿人民當(dāng)回事,那就另當(dāng)別論了。正如很多人一再?gòu)?qiáng)調(diào)的,在這場(chǎng)政治斗爭(zhēng)中,能使社會(huì)民主黨勝出的關(guān)鍵,或者說(shuō)是能讓其真正獲得人民支持的,不是對(duì)人民如何進(jìn)行抽象定義的問(wèn)題,而是其主張的民主、平等的福利政治(welfare politics)的成功并獲得人民支持的問(wèn)題。[8]說(shuō)到底,人民(或者說(shuō)老百姓)所支持的還要看誰(shuí)最終能改變生活。在反民碎主義甚囂塵上的今日,重溫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處理危機(jī)、大膽改革的歷史,可能會(huì)給我們新的啟迪。
許多社會(huì)民主黨著名思想家都曾提出過(guò)將瑞典建設(shè)成為“人民之家”的觀點(diǎn)。但是,真正比較全面論述并提出“人民之家”計(jì)劃的是上文提到的時(shí)任社會(huì)黨主席的佩爾·阿爾賓·漢森。漢森在1928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值得關(guān)注的是,漢森所說(shuō)的人民之家的“人民”包括整個(gè)國(guó)家的人民,它取代了將工人階級(jí)作為社會(huì)政治改革的唯一的關(guān)注點(diǎn),這一變化代表了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社會(huì)改革思想根本上的變化。作為黨的領(lǐng)袖,漢森指引和領(lǐng)導(dǎo)了社會(huì)民主黨從代表階級(jí)的政黨向代表全民的政黨的轉(zhuǎn)型。
意識(shí)形態(tài)轉(zhuǎn)變之后,社會(huì)民主黨采取重大舉措,聯(lián)合其他黨派和群體推行其社會(huì)改革。其中重要的舉措之一是與農(nóng)民黨的合作。面對(duì)工人罷工運(yùn)動(dòng)特別是法西斯主義的威脅,社會(huì)民主黨主席佩爾·阿爾賓·漢森作出重要決定,開(kāi)始與農(nóng)民黨進(jìn)行談判協(xié)商。之所以走出這一步,與瑞典社會(huì)歷史的特點(diǎn)有關(guān)。此時(shí)的瑞典剛剛進(jìn)入工業(yè)社會(huì),社會(huì)民主黨成員雖然以工人為主,但工人們大多是從農(nóng)村進(jìn)城打工的農(nóng)民,他們?nèi)耘c農(nóng)村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因此,盡管農(nóng)民擁有大量土地,并參與工商業(yè)經(jīng)營(yíng),但社會(huì)民主黨成員同情農(nóng)民黨的許多政策目標(biāo)。總之,社會(huì)民主黨并沒(méi)有將農(nóng)民黨作為對(duì)立的敵人,而是作為合作的對(duì)象。[9]社會(huì)民主黨與農(nóng)民黨的聯(lián)合行動(dòng),使其在議會(huì)取得了多數(shù)席位,削弱了其他激進(jìn)黨派的地位,這才使社民黨有機(jī)會(huì)推行其社會(huì)改革計(jì)劃。
與此同時(shí),聯(lián)合了農(nóng)民黨也就不能不考慮農(nóng)民們的利益。這里順便提一句,北歐的農(nóng)民一貫以具有政治覺(jué)悟、有組織、有談判能力著稱。因此,聯(lián)合了農(nóng)民黨的社民黨的福利改革就要保證工人和農(nóng)民都要受益。在社會(huì)民主黨的福利政策中既有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社會(huì)改革,也有對(duì)農(nóng)民和農(nóng)業(yè)的支持。例如,面對(duì)1920至1930年代的食品短缺,社會(huì)民主黨采取了降低農(nóng)業(yè)稅和限制農(nóng)產(chǎn)品的政策,這對(duì)農(nóng)民來(lái)說(shuō)當(dāng)然是個(gè)利好的消息,通過(guò)鼓勵(lì)瑞典食物自給,極大地提高了農(nóng)民們?cè)谵r(nóng)業(yè)方面的收入。[9]
在建立“人民之家”的過(guò)程中,瑞典的階級(jí)關(guān)系和力量對(duì)比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出現(xiàn)了“三足鼎立”的狀態(tài):農(nóng)民階級(jí)具有比較強(qiáng)勢(shì)的地位,地主階級(jí)相對(duì)處于弱勢(shì),而工人階級(jí)能夠進(jìn)入議會(huì)并在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與工廠主談判。由此帶來(lái)了收入差別逐漸縮小、貧困現(xiàn)象逐漸消失的局面。同時(shí),由于“人民之家”推行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原則,全體人民都享有普遍的社會(huì)權(quán)利。各種服務(wù)和現(xiàn)金補(bǔ)貼不僅面向窮人,也覆蓋到中產(chǎn)階級(jí)。這一原則不但導(dǎo)致縮小階級(jí)之間的差異,同時(shí)還推動(dòng)了性別之間的平等格局的創(chuàng)立。
簡(jiǎn)而言之,1930年代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的“人民”概念將國(guó)家作為一個(gè)共同體來(lái)看待,這種民主民族主義的社會(huì)主義將民主、國(guó)家共同體和福利改革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lái)。自此,“人民之家”成為瑞典福利國(guó)家的關(guān)鍵概念。所以要建成“人民之家”,就要承諾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quán)利和平等的機(jī)會(huì),這就意味著,如果社會(huì)要為每個(gè)人建立美好之“家”,就要特別體現(xiàn)在1930年代建設(shè)“家”的過(guò)程之中。
“人民之家”中的“家”
在瑞典建造“人民之家”的過(guò)程中,對(duì)“家”的建設(shè)和改造是其中關(guān)鍵的一環(huán)。“家”的概念即是一種比喻象征,同時(shí)也是建設(shè)福利國(guó)家邁向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關(guān)鍵。談到“家”就離不開(kāi)住房的問(wèn)題,因此,在1930年代瑞典福利國(guó)家起步階段,瑞典的社會(huì)民主黨和各個(gè)階層對(duì)住房問(wèn)題給予了極大的關(guān)注和投入。正像瑞典歷史學(xué)家伊馮·赫德曼所描繪的:如果對(duì)1930年代的瑞典加以觀察,幾乎大事小情都圍著房屋或者說(shuō)“家”轉(zhuǎn)。[10]
為什么住房問(wèn)題會(huì)成為全社會(huì)關(guān)注的中心?
先看看這段歷史。20世紀(jì)初期,瑞典的住房水平處于歐洲的低端,在城市里,有三分之一的住戶至少是5個(gè)人擠在一間或兩間的單元房里,還有許多人根本就無(wú)處所居。[2]相比英國(guó)與德國(guó)工人,瑞典工人們的住房差多了。房屋很小(大多一戶只有一居室),而且設(shè)備簡(jiǎn)陋,沒(méi)有室內(nèi)的取暖設(shè)備、廚房和廁所。而英、德等國(guó)工人住房在20世紀(jì)初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一戶至少有兩居室。顯然,此時(shí),瑞典的住房問(wèn)題與失業(yè)問(wèn)題一樣,成了社會(huì)發(fā)展的重中之重。
直到1930年代初,瑞典政府并沒(méi)有國(guó)家住房的政策,住房一貫作為私人的問(wèn)題,由市場(chǎng)供應(yīng)或者是地方政府所解決。1932年,社會(huì)民主黨上臺(tái)之后,瑞典國(guó)家住房政策出臺(tái),其關(guān)注點(diǎn)不僅是要建設(shè)更好的住房(better housing),而且是要建立美好之家(better homes)。自此,“家”的建設(shè)在瑞典公共話語(yǔ)中占據(jù)著中心地位。
這一轉(zhuǎn)變實(shí)際上反映了瑞典大的政治和經(jīng)濟(jì)變局。特別是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計(jì)劃經(jīng)濟(jì)理念的轉(zhuǎn)型。
首先,社會(huì)民主黨轉(zhuǎn)變了對(duì)“工作”與“家”的認(rèn)識(shí),將關(guān)注“生產(chǎn)”轉(zhuǎn)變?yōu)榇蠹业摹肮餐辉!薄T?930年代之前,傳統(tǒng)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思想就已經(jīng)存在,在瑞典工業(yè)化過(guò)程中,國(guó)家倚靠外債對(duì)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主要用于修橋鋪路。在社會(huì)政策上,政府借鑒德國(guó)的經(jīng)驗(yàn)解決工人階級(jí)的問(wèn)題,保障工人們的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以便保證長(zhǎng)期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傳統(tǒng)的工人運(yùn)動(dòng)對(duì)應(yīng)于這種計(jì)劃經(jīng)濟(jì),首先是關(guān)注勞動(dòng)工作的法律條例的改革,勞動(dòng)條件的改善,等等。因此,不論是在國(guó)家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中,還是在工人運(yùn)動(dòng)里,“工作”與“家”是分開(kāi)的兩個(gè)領(lǐng)域。“工作”(也就是經(jīng)濟(jì))被認(rèn)為是創(chuàng)造價(jià)值的、重要的主動(dòng)的領(lǐng)域,而“家”則是不創(chuàng)造直接價(jià)值、不重要的和被動(dòng)的領(lǐng)域。顯然,“工作”是主角,“家”是配角。沿著這個(gè)思路走下去,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的社會(huì)主義之路離海對(duì)面的蘇聯(lián)模式就不會(huì)太遠(yuǎn)了。然而,在建造“人民之家”的過(guò)程中,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的理念發(fā)生了重要的轉(zhuǎn)變,“工作”與“家”這兩個(gè)領(lǐng)域的位置出現(xiàn)了戲劇性的變化。
不錯(cuò),在1930年代“人民之家”的設(shè)計(jì)中,社會(huì)民主黨的理念是發(fā)展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資本主義無(wú)計(jì)劃的自由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相對(duì)立。但這種瑞典式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里有其新的一面,提出將食物、衣服、住房等生活的基本“需要”作為基本人權(quán),而社會(hu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huì)就要滿足這些基本的需要。因此,“需要”就有了雙重意義——作為一種人權(quán)與作為一種維持生命的可測(cè)量的條件。這樣一來(lái),就為政治干預(yù)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做了鋪墊。[10]
有人將瑞典的社會(huì)主義稱為“實(shí)用的社會(huì)主義”(practical socialism)。更為值得關(guān)注的是,這種實(shí)用的社會(huì)主義與凱恩斯所強(qiáng)調(diào)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中的“需求”這一關(guān)鍵因素不謀而合。他們把家庭的社會(huì)支出作為對(duì)社會(huì)總需求的投資,作為對(duì)未來(lái)社會(huì)資本的投資,而不是作為成本。因此,婦女與兒童的權(quán)利就通過(guò)在公共服務(wù)領(lǐng)域的大型投資與宏觀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起來(lái)。[11]瑞典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特征是“來(lái)自需求側(cè)的社會(huì)化”,而不是“來(lái)自供給側(cè)的社會(huì)化”[7], 這一點(diǎn)是非常值得人們關(guān)注與研究的。
顯而易見(jiàn),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要滿足人們的消費(fèi),滿足“需要”在某種意義上說(shuō)就是要滿足消費(fèi)。特別是涉及到住房政策,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與消費(fèi)更是密不可分,因?yàn)榇笠?guī)模的公共住房建設(shè)必將創(chuàng)造新的工作,這就意味著經(jīng)濟(jì)的振興,這也是瑞典1930年代經(jīng)濟(jì)大蕭條經(jīng)濟(jì)問(wèn)題中的重中之重。同時(shí),建筑大量的住房也會(huì)帶來(lái)兒童養(yǎng)育和教育的振興,這也是培養(yǎng)社會(huì)主義新公民的過(guò)程。
其次,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市場(chǎng)、消費(fèi)如何結(jié)合?從傳統(tǒng)的社會(huì)主義思潮來(lái)看,對(duì)家的角色或消費(fèi)的角色(從生產(chǎn)的立場(chǎng)來(lái)看)歷來(lái)有兩個(gè)策略:一個(gè)是消除市場(chǎng),用嚴(yán)格的計(jì)劃來(lái)控制消費(fèi);另一個(gè)是依靠訓(xùn)練民眾的消費(fèi)觀來(lái)控制市場(chǎng),也就是說(shuō),讓人們消費(fèi)“合適”的東西,這也叫做:以消費(fèi)為導(dǎo)向的社會(huì)主義化[12]。顯然,瑞典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選擇的是第二個(gè)策略——由受教育的民眾控制市場(chǎng),這一舉措無(wú)疑是個(gè)創(chuàng)新。這意味著,計(jì)劃經(jīng)濟(jì)不是由個(gè)別的權(quán)威和精英所決定,計(jì)劃和市場(chǎng)中的民主問(wèn)題擺到了桌面上,同時(shí)也提出了新的問(wèn)題:如何由民眾控制市場(chǎng)(而不是少數(shù)人)?如何對(duì)民眾進(jìn)行教育或如何理解人們的日常生活?
從政府的層面來(lái)看,住房建設(shè)既有短期的計(jì)劃,也有長(zhǎng)期的設(shè)想。1933年成立了社會(huì)住房委員會(huì),委任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jiàn)W費(fèi)·喬納森為主任。在1933年的國(guó)家預(yù)算對(duì)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保留的資金中,有1/4用于住房。[7]同時(shí),各個(gè)市鎮(zhèn)政府也有專門的貸款支持政府建筑部門和非盈利的建筑公司為貧困家庭修建單元式住房。[13]這些重要舉措對(duì)市場(chǎng)中脆弱的建筑行業(yè),特別是建筑工人猶如雪中送炭。因此,從計(jì)劃的起步階段,建筑工人聯(lián)合會(huì)在規(guī)劃房屋政策方面就成了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民眾來(lái)看,如何應(yīng)對(duì)房屋短缺和房?jī)r(jià)上漲是住房問(wèn)題的重中之重。一戰(zhàn)之后,面對(duì)房租房?jī)r(jià)的快速攀升,瑞典各地的中低收入租房客組成互助協(xié)會(huì)共渡時(shí)艱。在此基礎(chǔ)上,1923年成立了全國(guó)性的“租客儲(chǔ)蓄和建房協(xié)會(huì)”(HSB),為工人階級(jí)提供廉價(jià)住房。1930年代,“租客儲(chǔ)蓄和建房協(xié)會(huì)”有了實(shí)質(zhì)性的發(fā)展,他們依靠協(xié)會(huì)成員的房租和買房款,并且從政府及銀行獲得貸款,為會(huì)員提供低價(jià)和優(yōu)質(zhì)的“合作住房”。1937年,斯德哥爾摩一半以上的合作住房都是由HSB建設(shè)的。至1930年代末,該協(xié)會(huì)為25,000個(gè)家庭提供了住房,其中60%是工人家庭。[14]由此可見(jiàn),居住在“人民之家”的人民也有權(quán)利參加住房建設(shè),形成經(jīng)濟(jì)上的民主參與制度。
此外,在“人民之家”的設(shè)計(jì)和建設(shè)中,還有一群由年青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建筑師和社會(huì)科學(xué)家組成的“社會(huì)工程師”。這一群體不但是“人民之家”的設(shè)計(jì)者和執(zhí)行者,而且還承擔(dān)起對(duì)民眾進(jìn)行啟蒙與教育的工作。這些激進(jìn)的年青知識(shí)分子,不想單純地在學(xué)術(shù)上“作秀”,而是力圖做群體合作的建設(shè)者。他們不但是各方面的專家,同時(shí)也是朋友和大膽革新創(chuàng)造的一個(gè)群體。其中最有名的是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貢納爾·默達(dá)爾和社會(huì)學(xué)家阿爾瓦·米達(dá)爾夫婦。例如,集實(shí)用、簡(jiǎn)約和低價(jià)為一體的集體住房成為瑞典1930年代的住房設(shè)計(jì)先鋒模式之一。參與設(shè)計(jì)和施工的不但有建筑師,還有社會(huì)學(xué)家阿爾瓦·米達(dá)爾。[14]
在建設(shè)人民之家的問(wèn)題上,這些“社會(huì)工程師”們認(rèn)為,理想的社會(huì)折射出理想的家庭,居住的房屋應(yīng)該是現(xiàn)代的、既有品位又建造合理,而且是普通民眾住得起的。另外,房屋的建造和裝修與家務(wù)勞動(dòng)、孩子的養(yǎng)育及休閑都有關(guān)聯(lián),因此,住房問(wèn)題不但是個(gè)人的私事,房屋的建造與家庭的改革、兒童的教育緊密相連。在這一點(diǎn)上,“社會(huì)工程師”們認(rèn)識(shí)到,提高人民的品位與提高物質(zhì)生活標(biāo)準(zhǔn)是同等重要的。
自19世紀(jì)中葉,在北歐設(shè)計(jì)改革運(yùn)動(dòng)中就有通過(guò)教育提高公共民眾品位的理念,其目的在于改善推動(dòng)消費(fèi)的模式。在國(guó)際上美學(xué)運(yùn)動(dòng)和理論的影響下,許多瑞典的藝術(shù)家、建筑學(xué)家和知識(shí)分子對(duì)此進(jìn)行了反復(fù)討論,認(rèn)為人民需要更好的生活條件,這不僅是物質(zhì)上的也是美學(xué)意義上的。在著名的婦女活動(dòng)家和教育家愛(ài)倫凱倡導(dǎo)的提升人民品位的推動(dòng)下,瑞典工業(yè)設(shè)計(jì)協(xié)會(huì)(SSF)成立,并成為這方面最重要的組織。該組織同時(shí)還通過(guò)改革室內(nèi)裝修等致力于瑞典房屋的改善[2],其中最為著名的活動(dòng)是其在1930年組織的斯德哥爾摩博覽會(huì)。通過(guò)這個(gè)博覽會(huì),不但將建立在對(duì)美的新理解基礎(chǔ)之上的現(xiàn)代的產(chǎn)品、現(xiàn)代的日常生活和現(xiàn)代社會(huì)介紹給了公眾,同時(shí)還直接影響了瑞典的住房政策和建筑模式。瑞典工業(yè)設(shè)計(jì)協(xié)會(huì)還通過(guò)一年一度的公眾居住調(diào)查,了解公眾對(duì)于住房及家具使用等方面的要求,以及組織關(guān)于居住的課程、學(xué)習(xí)小組對(duì)公眾進(jìn)行品位方面的教育,以便對(duì)住房政策、住房的設(shè)計(jì)和生產(chǎn)進(jìn)行改革。
至1930年代末,經(jīng)濟(jì)大蕭條結(jié)束,瑞典經(jīng)濟(jì)恢復(fù)增長(zhǎng),住房建設(shè)達(dá)到空前水平,住房供應(yīng)充足。[13]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瑞典雖然沒(méi)有直接參戰(zhàn),但在二戰(zhàn)期間,住房建筑在此停滯。而“人民之家”的建設(shè)也只好推遲到二戰(zhàn)之后。
1930年代的全球經(jīng)濟(jì)大蕭條,引起許多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與政治上的沖突與對(duì)立。特別是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引發(fā)了二戰(zhàn)的爆發(fā),至今仍像是一場(chǎng)噩夢(mèng)。而瑞典“人民之家”的理論和實(shí)踐像是給黑暗的1930年代帶來(lái)了一抹希望的光亮,有力地化解了瑞典國(guó)內(nèi)階級(jí)之間的對(duì)立與矛盾,這不能不說(shuō)是一種奇跡或是異數(shù)。
結(jié)語(yǔ)
“人民之家”的“人民”包括整個(gè)國(guó)家的人民,它取代了將工人階級(jí)作為社會(huì)政治改革的唯一的關(guān)注點(diǎn),這一變化代表了瑞典社會(huì)民主黨社會(huì)改革思想根本上的變化,從代表階級(jí)的政黨向代表全民轉(zhuǎn)型。這種轉(zhuǎn)型導(dǎo)引了該黨與其他黨派的妥協(xié)和合作,特別是與農(nóng)民黨的聯(lián)合。這種包容性的理念調(diào)動(dòng)了各個(gè)階層和群體參與“人民之家”建設(shè)的積極性,從而避免了極右的法西斯主義的泛濫,解決了政治經(jīng)濟(jì)的危機(jī),為瑞典走上福利國(guó)家之路奠定了政治基礎(chǔ)。
更為重要的是,“人民之家”的理念承諾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權(quán)利和平等的機(jī)會(huì),要為每個(gè)人建立美好之“家”,這在1930年代建設(shè)“家”的過(guò)程之中有特別的體現(xiàn)。其深遠(yuǎn)意義在于:美好之家不光是給大家建立物質(zhì)層面上的房屋,而是體現(xiàn)了一種人的價(jià)值和尊嚴(yán),以及對(duì)每個(gè)人需求的承認(rèn)。如何將這種具體的“人民”的價(jià)值和需要落在實(shí)處,這是瑞典社民黨對(duì)社會(huì)主義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創(chuàng)舉。
在傳統(tǒng)的社會(huì)主義計(jì)劃經(jīng)濟(jì)理念中,工作被看作是生產(chǎn)性的,具有重要性和主動(dòng)性;而“家”則是被動(dòng)的,次要的。“工作”起主導(dǎo)作用,而“家”的社會(huì)作用是要附和工作需要的。這種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話語(yǔ),我們是再熟悉不過(guò)了。“先生產(chǎn),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窩”不僅僅是口號(hào),而且已經(jīng)浸透到我們幾十年的社會(huì)實(shí)踐里。而瑞典“人民之家”的理念或?qū)嵱玫纳鐣?huì)主義對(duì)“家”這一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將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消費(fèi)和市場(chǎng)緊密地連接在了一起,力圖打破國(guó)家與市場(chǎng)消費(fèi)的對(duì)立。這點(diǎn)是我們不熟悉的地方。可以說(shuō),有了這一創(chuàng)新之舉,瑞典才能將資本主義的效率與平等的沖突、社會(huì)與市場(chǎng)的矛盾,在“人民之家”這一烏托邦社會(huì)得以解決和緩和,使福利國(guó)家得以建立。
[1] Andersson Jenny. Nordic Nostalgia and Nordic Light: the Swedish model as Utopia 1930—2007.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2009,34(3).
[2] Goransdotter Maria. A Home for Modern Life: Educating Taste in 1940s Sweden. DRS 2012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2012.
[3] Olofsson M. The Tullberg Movement: the Forgotten Struggle for Landownership. in L. Edgren and M. Olofsson (eds.) Political Outsiders in Swedish History, 1848—1932,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09.
[4] Svensson M?ns, Urinboyev Rustamjon, ?str?m Karsten. Welfare as A Means for Political Stability: A Law and Society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2012,14(2).
[5] Wilensky HL.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6] Berggren L. Swedish Fascism: Why Both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2,37(3).
[7] Olsson Ulf. Planning in the Sweden Welfare State. i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34, Spring, 1991.
[8] Edling Nils. The primacy of welfare politics. Notes on the language of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ir adversaries in the 1930s. In H. Haggrén, J. Rainio-Niemi & J. Vauhkonen (Hg.), Multi-layered historicity of the present. Approaches to social science history (S.125—150). Helsinki: Unigrafia.Onlineauf, 2013.
[9] Baker R Josiah. Constructing the People's Hom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Swedish Modal”(1879—1976), 2011.
[10] Hirdman Yvonne.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Woman Question: Sweden in the Thirties. I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44, Summer, 1994.
[11] Andersson Jenny. Investment or Cost? The Role of the Metaphor of Productive Social Policies in Welfare State Form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S 1850—2000. Paper to the World Congress in Historical Sciences Sydney, 2005.
[12] Hirdman Yvonne, Vale Michel. Utopia in the Hom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Political Economy,1992,22(2).
[13] Hedman Eva. A history of the Swedish System of Non-profit Municipal Housing,Stochom Swedish Board of Housing, Building and Planning,2008.
[14] Gearty Giuliana Vaccarino. ARCHITECTURES OF COLLECTIVITY: Swedish Cooperative Housing in Stockholm, 1935—1945, 2016.
——《篳路藍(lán)縷:計(jì)劃經(jīng)濟(jì)在中國(guó)》評(píng)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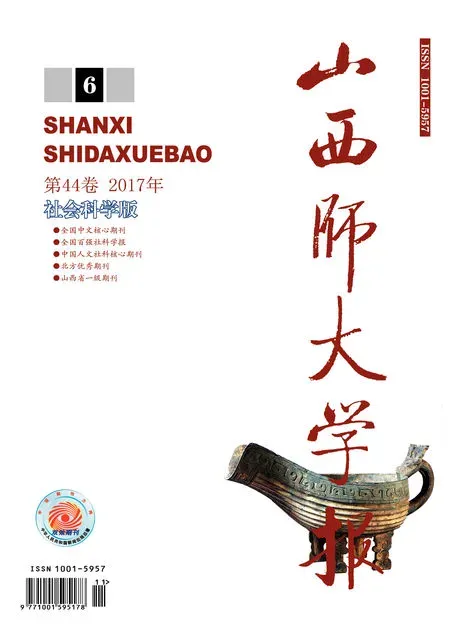 山西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6期
山西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6期
- 山西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平衡木上的華北父母:日常表現(xiàn)、實(shí)踐邏輯與意外后果
——基于農(nóng)民人生價(jià)值的視角 - 農(nóng)地流轉(zhuǎn)與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的相互關(guān)系研究
——基于北京、山東、山西、陜西四省(市)的調(diào)查分析 - 對(duì)山西省煤炭采空區(qū)農(nóng)村人口遷移的思考
——基于制度均衡理論視角的考察 - 弱勢(shì)的疊加與突破
——從營(yíng)養(yǎng)與受教育狀況看西部農(nóng)村女童的生存和發(fā)展 - 北大秦簡(jiǎn)《教女》與秦代性別關(guān)系的建構(gòu)
- 山西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7年總目錄
